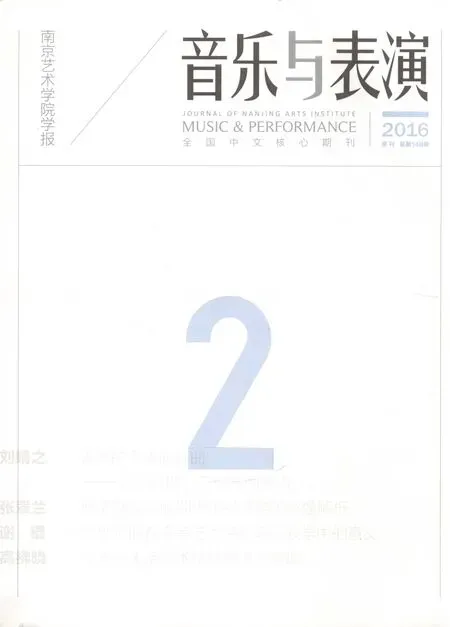潘德列茨基美学观念对其创作风格演变的影响
李鹏程(浙江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4)
潘德列茨基美学观念对其创作风格演变的影响
李鹏程(浙江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4)
潘德列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1933-)是波兰先锋乐派的代表人物。1970年代,潘德列茨基开始转向新浪漫主义风格,这一做法在音乐界引起了巨大争议。作为一位文化修养深厚的作曲家,潘德列茨基的每一次风格转折都源于美学观念的转变。1998年出版的《时间迷宫:千年末的五篇演讲》收录了潘德列茨基的五篇演讲,在旁征博引中表达了对于世纪末的文化境况的看法,并以“树”、“迷宫”和“方舟”象征自己的创作基础、世纪末的文化状况和拯救艺术的方式,深入阐述了作曲家的艺术追求,本文以此为主要参照,通过探讨潘德列茨基的美学观念,揭示影响作曲家风格演变的主观因素。
克里斯托夫·潘德列茨基; 现代音乐; 美学观念 ;创作风格
一、 源自地中海的融合理念
潘德列茨基是一个混血儿。父系祖辈来自波兰的东部,奶奶是亚美尼亚人,相关亲属居住在罗马尼亚和立陶宛[1]16。母系祖辈来自波兰的西部城市弗罗茨瓦夫(Wrocław),这座城市在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和文化名城,名为布雷斯劳(Breslau),德国战败后被划归为波兰,因此潘德列茨基说他的外公是德国人[2]17。潘德列茨基成长于波兰东南部城市登比察(Dębica),历史上曾被哈布斯堡帝国统治,1772年波兰被第一次瓜分时归奥地利统治,长期作为西部德国和东部乌克兰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潘德列茨基自幼熟读奥古斯丁和阿奎奈等神学家的著作,并深深迷恋荷马、欧里庇得斯、维吉尔等古希腊、古罗马诗人,潘德列茨基在少年时的理想是做水手、画家或艺术史学家。1951年,潘德列茨基进入雅盖隆大学①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建于1364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位于波兰古都克拉科夫,前身为克拉科夫学院。,学习艺术、文学、哲学和拉丁语,在综合类大学受到的系统性的人文学科训练为他以后广博的创作主题打下基础。他曾感叹:“在古老的克拉科夫,我能感受到传统意味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我认为自己是被地中海文化养育的。”[3]成长于如此多元环境中的潘德列茨基接受东西方文化带来的不同的影响,“融合”逐渐成为其创作的核心理念,他将这归因为地中海文化深远影响:
我常常被东正教礼拜仪式所吸引,同时又着迷西方文化和它的理性主义,以及它表达最复杂感受的能力。别忘了,地中海文化——从广义上讲这是我的家乡——正是在多种元素的丰富交流中形成的。
我感受到自己对多样性的需求,这多少归因于我那如海神普罗透斯的特性,他能不断改变自己的外表。[2]17-18
潘德列茨基在出道之作《诗节》中便展现了其多元的文化积淀,作品的人声文本分别采用了犹太人的《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希腊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及阿拉伯人欧玛尔·海亚姆的诗歌。在海纳百川式的“融合”理念推动下,潘德列茨基长期汲取着西方各个时期的音乐风格,并表明自己将像马勒那样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交响世界:
看看上个世纪末音乐界发生了什么吧。马勒将他那一个世纪的一切承接过来,写他的音乐,但也借用其他作曲家的技巧并加以发展。我现在做的也是写我自己的音乐。当然也会从其他作曲家那里借鉴一些元素:肖斯塔科维奇、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等等。[2]77
作为一位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作曲家,他和同时代人一样坐拥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大量音乐风格,他在1960年代前后的做法是像其他先锋派作曲家那样避开传统,以激进的实验精神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新风格。然而,当他们走出实验室,发现自己因难以被听众所理解而被孤立,和许多其它先锋派作曲家一样,潘德列茨基选择了融合过去和现代的音乐风格来触及听众:“对于融合的渴望引领着我,渴望整合当代人所拥有各类经验。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留下了各自可辨识的语言。巴赫或莫扎特知道他们为谁而写,并且知道那些人可以理解。”[2]16当然,必须承认,后现代文化思潮推动了融合风格“合法性”进程,历史语境的改变使得潘德列茨基在1962年迈出融合的第一步后,能够继续走下去——毕竟他是当时先锋派阵营中较早迈出这一步的。
除了个性使然,另外一个促使潘德列茨基融合各类风格的原因是对普遍性音乐语言的追求。在他看来,先锋派的各类实验已经粉碎了音乐存在的基础,“共性写作”时期积累下来的统一性和伟大性荡然无存:“我常深思在我们这个世纪,普遍性(universal)音乐语言的缺失。早些时期,音乐“共性语言”的产生可能是由于音乐家和他们的听众均认可某一固定的参照点。二十世纪的作曲家们在彻底改变音乐根基的同时,又在某一空虚的瞬间找到自我。激进个人主义与实验的主张已经导致了所有支撑点的粉碎。”[2]60
潘德列茨基对普遍性音乐语言的追求,最终停留在“新浪漫主义”风格上。1975年之后,他基本抛弃了早年开创的音响主义风格,沉浸在浪漫主义晚期的“世纪末”氛围中。在他看来,音响主义风格不可能被广泛应用,新浪漫主义风格则更容易被普遍应用和接受。潘德列茨基如此描述他所追求的普遍性音乐语言:
主要是想找到一种不仅适合于我和我的音乐,且适合我们时代的音乐语言。我在60年代运用的配器法过于个性以至于只能适用于我的音乐。其他作曲家在作品中难以采用。而我现在写的音乐就拥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它们将过去的音乐元素转换为我们时代的风格。例如,配器法更贴近像布鲁克纳这样的作曲家:乐队的加倍组合产生音响密度。这种普遍性风格有来自19世纪末的元素,那是令我着迷的时期。但作品中也有从先锋派来的元素。[2]76
潘德列茨基1975年之后的作品中仅残存极少的音响主义片段,具有明显的“回归”倾向。以“融合”为核心理念的潘德列茨基,在对“普遍性”音乐语言的追求中,最终回到了令他心醉神迷的浪漫主义晚期。这一从音响主义风格到回归调性家园的历程,恰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描写的那样,英雄依靠愤怒的力量开疆辟土,却在战胜后的归途中积重难返。
二、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讲述了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城的英雄故事。《奥德赛》讲述了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罗马神话中称为“尤利西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突破重重险阻返回故乡的故事。
潘德列茨基将自己的创作生涯比喻为这两个阶段:伊利亚特——“拼搏前进的时期”;奥德赛——“追寻回归的时期”。60年代前后的先锋探索像是不顾一切地攻打特洛伊城池的英雄行为,在实现胜利之前不可以回归故里;70年代前后的回归传统则像是战争结束后,英雄尤利西斯经历重重险阻,终于回到故乡与妻儿团聚。由于回归传统,潘德列茨基被称为“先锋派的特洛伊木马”,意即先锋派内部的叛徒。他如此回忆这一历程:
我也拥有自己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对我来说,特洛伊是先锋派,是年少的反叛期,对通过艺术来改变世道常情的可能性充满信心。先锋派呈现出普遍性的假象。受到在波兰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的阻碍,我们年轻的作曲家把施托克豪森、诺诺、布列兹、凯奇的音乐视为一种自由。我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了我的事业,那时仍有许多激进分子有待发现。然而,我很快便意识到革新的破坏大于重新建设,大部分归结于形式上的实验与思索;在那些日子中,普罗米修斯的说法只是一个乌托邦。从形式主义的先锋派陷阱中逃离出来,这使我回归到传统。我甚至被称为 “先锋派的特洛伊木马”。无论如何,直到70年代初的《宇宙的诞生》(Cosmogony),我才试图使自己从那种建设 “全人类伟大家庭”的乌托邦信仰中解放出来,这种信仰也是先锋派信条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这是我的尤利西斯冒险开始的时刻,他 “通过艰辛劳作、危险与痛苦,前往遗失的伊萨卡岛”。也就是说,我的奥德赛,正用自己的方式创作,寻找这个中心。[2]15-16
1948年,当苏联把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方针强加于波兰时,潘德列茨基15岁,这个少年将苏联视作继德国法西斯之后的侵略者,曾因在学校厕所墙壁上涂写反斯大林标语被老师惩罚[1]17;1956年,紧接在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波兰举办了第一届华沙之秋国际现代音乐节,西方现代音乐如潮水般涌入,此时的潘德列茨基23岁,尚在音乐学院就读的他,带着一股叛逆劲头学习被苏联官方批判为“形式主义”的序列主义音乐;1959年,留校任教不久的潘德列茨基在波兰作曲家比赛中凭借《诗节》、《放射》、《大卫赞美诗》包揽三项头奖,这一年他26岁,以极富想象力的音响主义风格为先锋派开辟了新的疆土;1973年,潘德列茨基已誉满天下,刚抵不惑之年的他,以《第一交响曲》为自己的“伊利亚特”时期画上句号。在三年后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中,他回到了遗失已久的伊萨卡岛,发现“普罗米修斯的说法只是一个乌托邦”。此时的他将先锋派称作“陷阱”和“形式主义”——这个长期被苏联官方用来打压先锋派的词汇,却最终被当年先锋派的领军人物所认同,这是多么荒诞的反讽!他老了,他想回家。真的是这样吗?刚过四十岁的他过早进入了“晚期风格”?
在潘德列茨基看来,以探索新音响、推动历史前进为目的的先锋派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完成了使命,新音响资源如矿产般已经被开发殆尽,如今再创作实验音乐不过是对60年代实验风格的重复:
所有事在60年代已经完成了,创造出先锋派风格,发展出一种新音乐语言,为乐器发明新技巧,为乐队引入新乐器。当然还有电子音乐的影响,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现在世纪末我们不再需要这些。60年代意味着一场重要的历史运动,但我们今天不能重复那种风格。[2]74
潘德列茨基指出,20世纪有两个时期推动了音乐向前发展,分别是20年代、50年代中叶至60年代,之后则是新音乐创作的衰退时期,各类现代音乐技法沦为“新的传统”,更新的艺术观念要寄希望于未来的年青一代去开发,在此之前需要先回归至传统:“我认为音乐史中的其他时期无法同我们所在的时期一样以衰退为标志。难以窥见任何新的发展道路。艺术家们正在利用旧理念,并退回到过去。然而,真的有必要惧怕回归吗?”[2]39
斯特拉文斯基在1920年抛弃了《春之祭》的野蛮音响,在《普契涅拉》开启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中“回到巴赫”。类似地,潘德列茨基在1975年彻底抛弃了《挽歌》的音响主义风格,在《失乐园》开启的新浪漫主义风格中回到瓦格纳。同为曾经的革命者,斯特拉文斯基和潘德列茨基在多重风格演变过程中皆对自己当年的革命行为进行过反思。1998年,罗宾逊对潘德列茨基的这段访谈,揭示了这位当年音响主义革命的“急先锋”对先锋派革命行为的深层认识:
我最近读到你曾说过的一句话:“艺术本质上是建设性的。革命引起骚乱。”在你早期探索实验音乐语言时你相信“革命”是必要的吗?
毫无疑问!直到现在我也相信革命。我确信在下一个世纪,可能在开端又或许在之后,将会出现一群更年轻的音乐家、作曲家发现新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现在忙于尝试找到一种综合体,不仅是我,其他作家也在这样。这是本世纪的转向,这种探寻对于这个时代的作曲家来说很典型。
在你职业生涯的什么时候决定不再革命?
我早年是一个革命者,非常坚定,但渐渐我发现这不是我作为作曲家进行表达的唯一道路。这类音乐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就是说在某一个时间点,你的音乐直觉导致你认为国际公认的先锋派运动是死路一条。在你最具实验性的器乐作品《荧光》和声乐作品《颂歌》之后,就无路可走了。
没错,或许只有电子音乐还能往前走。
在最近的演讲中你引用了斯特拉文斯基的一句名言:“我在革命中背离了自己的初衷!”你如何作为先锋派运动的引领者而非追随者时做到这样?
这不过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从50年代末作为一位革命者……直到《圣母悼歌》(1962)。那时我试图找到一条离开这场运动的道路。我创作的音乐与我的同事们相背离,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派作曲家。当然,我为此饱受批评。[2]82-84
如果仅将音响主义阶段(1959-62)视作潘德列茨基的革命时期,这三年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实际上只占极小一部分,这位先锋派代表人物冲锋陷阵的革命时间并不比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城的十年要长。他像奥德赛一样,是当年攻入特洛伊城的功臣,在海上漂泊了十年(1963-73),历经千难终返“调性家园”。当年是他引领了音响主义潮流,如今又是他率先向19世纪撤退,在其先锋派同行眼中,回归调性无异于“反革命”行为:“他们将我视作先锋派的叛徒,他们转而反对我,特别是我过去的同事,也包括我在波兰的同事。我的问题在于,我是第一个转向19世纪的人。”[4]
无论怎样,潘德列茨基还是回到了家乡,在克拉科夫附近的Lusławice镇建起一座迷宫,花了30多年时间亲手种下超过1500种的树木。他说:“在Lusławice种树,我找到了我的奥德赛天堂、我的伊萨卡岛,我感觉仿佛在自我净化、在向自我及音乐的本质靠近。”[2]19
三、迷宫中的树
“迷宫”是潘德列茨基对当代文化的隐喻。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当代文化,逐渐被商业化的大众传媒所湮没,艺术品沦为大量复制的商品,高雅与低俗的标准亦被消解,这场“瘟疫”浸入整个人类社会,艺术家不得不在重重迷雾中找寻出路、找寻自己:
“一百年以前,艺术尚有杰出的个人主义品质;今天,我们正位于大众文化的束缚中……为了追求商业的成功,经营者始终将精神寄托在浮华不实的包装与组合上:著名男高音歌手在运动竞赛中一同演唱流行的咏叹调;高科技产品——录像带与光碟——代替了关于文学、电影、戏剧和音乐的直接经验。这些都是遭受信息万花筒之后的幻象。这种幻象的危机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2]22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早已指出,统一标准的文化工业导致作品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复制”,“美的幻象”引导人们以物质和感官为中心进行娱乐消遣,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流行音乐使得个性化的艺术面临瓦解,艺术正面临自身的衰落。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1901-1991)感叹道:“在世纪之交,社会哲学展望未来所抱的强烈悲观主义,看来不无道理,因为吞没了个人,大众获得了胜利,艺术的丧钟就敲响了。”[5]潘德列茨基站在相似的立场指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大众文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负面意义,如今从美国到波兰,平民神话已将精英艺术挤压至最底层,在大众文化的占领下,克拉科夫广播交响乐团遭遇解散,歌剧作曲家因资金问题陷入困境,曾经置于金字塔顶端的贝多芬也变得低俗化。尽管语调悲观,潘德列茨基却深信“千年末”(fin de millénaire)并不意味着艺术的末日,新一代的现代主义者会凭借天才的力量突出重围:“我不怀疑艺术的再生能力。按照世代更替的自然规律,近来的折衷主义者会被现代主义者以及即将问世的重建者所继承。”[2]32
“迷宫”的另一方面含义,是指身处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人类命运,以及艺术家在其中百转千回的创造力。在非理性因素控制下的艺术创作,必然在这个迷宫中“误入歧途”而后“迷途知返”,在如此迂回前行中寻求最终的出路:
看看整个二十世纪,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种错综复杂的构造是艺术家们的宿命,比如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普罗科菲耶夫、毕加索、康托①塔德乌什·康托(Tadeusz Kantor, 1915-1990),波兰艺术家、戏剧导演。。康托曾写道:“传统发展呈现出的是一条直线、一个螺旋或同心圆,而我的作品图表则成为了一个迷宫。出路的缺失恰恰显示出我们并未在正轨上。在艺术界,也是如此。”因而,我们必须在矛盾中寻找希望。[2]74
我们能够在潘德列茨基的创作和言谈中明显感受到后现代史观对他的影响——假如不再将艺术史看作是直线向前发展的,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路线,那么“回归”便有了充分的理由。不无矛盾的是,在潘德列茨基的创作和言谈中,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这位作曲家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作是“后现代主义者”,因为他始终站在现代主义者的立场警惕着后现代主义的肆意侵蚀,他说:
我既不相信后现代主义者所宣称的 “作者已死”,也不相信 “伟大形式的黄昏”。我拒绝当前对艺术作品结构消解的主张。我也不接受诡辩的胜利。不仅保持智性与意识是必要的,倾听内心世界也同样如此。
这段话表明他在创作中,刻意避免了后现代主义的“开放”和“解构”特征。他像执意为协奏曲写下每个华彩段的贝多芬那样,坚守对每部作品的控制权,始终将结构的有机统一视为自己创作的形式法则。而无论在哪个阶段,对内心音响世界和情感的表达始终是其创作的主题。
潘德列茨基将文化的发展比喻为一棵树的成长过程,它会成长和衰老。他将现代文明视作欧洲文化的衰落阶段,并认为音乐史中没有任何时期像我们所在的时期这样,以衰退为标志。然而,他深信文化内永存再生机制,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要像一棵树那样从根部汲取养料,才有可能获得新生。身处世纪末的迷宫中,潘德列茨基为自己的创作寻求的出路是回归至起源,所以他对传统的依赖是如此根深蒂固:
看看一棵树吧。它教导我们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必须植根于两个方面:土地和空气。没有任何创作来自于无根。
这就是我为什么冒险 “回归母体” 的原因。人种学家使我们确信,这样一种朝向起源的回归可以拥有新生的力量。在为耶路撒冷建城三千周年而创作《耶路撒冷的七座城门》时,我决心回归至《大卫赞美诗》。这是多重回归:回到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根源;回到音乐的起源;最终,回到我自己的创作之初。
在Lusławice的迷宫里种树,潘德列茨基不仅在躲避周遭社会的纷扰,也在抵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衰落的比喻:“再无一人种树了”。他的创作不正像一棵伫立在迷宫中的树吗?在四季更迭中变化成长,根基也随之越扎越深。“树”的结构也存在于他的作品中,有学者以异质同构的方式,将潘德列茨基新浪漫主义时期的主题旋律发展模式比作一棵树的形状,称之为“潘德列茨基树”(Penderecki tree)[6]。他像许多伟大的作曲家那样,在晚年回到内心深处,转向更为内省简洁的室内乐创作:
在寻求最集中、最精练的形式时,我也在思考这种融合。对我来说,正是室内乐引领我靠近音乐的原始材料。这个阶段是否能将我引向期待中的伟大融合,引向杰作? 对我来说,似乎只可能通过已存在的万物的净化与衍变,来重获本真与自然、音乐的普遍性语言。[2]19
“树”的理念在潘德列茨基的《第八交响曲“无常之歌》(Lieder der Vergaenglichkeit,2005)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部作品采用了13首浪漫主义和20世纪初的德语诗歌,每一首都以树为主题,每个乐章像是一棵大树上的树枝。一部交响曲通篇以德语演唱关于自然的诗歌,使人想起百年前马勒的《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潘德列茨基在形式上继承了马勒“歌曲化的交响曲”,在内容上则专注于“树”:“我在Lusławice种植的树木成为这部作品的主题。这也是为什么我找了这么多关于自然的诗歌。”[7]8实际上,无论是种树或是创作关于树的交响曲,都是潘德列茨基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和精神环境的一种抵抗,同时也试图唤醒世人对大自然和精神家园的回归意识。
四、作为方舟的交响曲
潘德列茨基认为,在世纪末的后现代文化困境中,末世的洪水已经泛滥,艺术则是拯救的象征。然而,艺术家必须警惕陷入实验形式的陷阱中无法自拔,他借用康定斯基的话指出这类危险:
康定斯基感知到了三类危险,他自己也在设法绕开或拒绝。艺术家的警告是值得借鉴的,因为他们具有普遍特征。每一位艺术家都会受到这种威胁:
1、形式的程式化风险,已经死亡或是复活的形式太过虚弱从而无法生存。
2、形式的装饰性风险,它从本质上已经沦为外观的美感,因为它们可能(通常如此)充斥着表象的表达同时又缺乏内在表达。
3、形式的试验性风险,它源于实验,因此缺少直觉的参与。更是因为任何形式都具有内在含量上的一些等级,而这被错误地认为是一种内在需求。
最困难的事情在于识别实验性形式的真实或虚伪。在后先锋派的时代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7]55
尼采之后,虚无主义渗入欧洲文化的每个角落,解构浪潮像大众狂欢一样,令固守古典精神的人们不知所措。潘德列茨基指出,当代艺术若要拯救自己,必须建造起精神的诺亚方舟。与后现代主义的消解中心和非深度模式相对,传统价值和标准亟待重建:
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在如今规范与价值消融的时代中,我们的方舟恰恰象征着范例与标准的感受,是一个人自我边界的标示。尽管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提出了无用的哲学,但没有这艘方舟就没有创作任何艺术作品的可能。[7]56-57
当凝聚性的缺失已然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特征,艺术家又当如何创造伟大的形式?潘德列茨基将目光转向马勒,指出他成功地将交响曲作为整合世界和推动音乐语言演进的形式,分崩离析的世界和自我在马勒的交响曲中得到记录。面对世纪末的十字路口,潘德列茨基像马勒一样选择了交响曲作为承载人类希望的诺亚方舟。
当我再三被问及有关建造方舟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时,我想到了交响曲——我们想对下一代表达在二十世纪音乐创作传统中什么是好的,这艘音乐的方舟使之成为可能……1973年,我在四十岁时写下了第一部交响曲。这是一个人穿过阴影线的时刻。然后我试图对这二十年来我的音乐经验价值——激进的时期、先锋派的探索——做一个清算。这是我作为先锋派艺术家的最后总结。四个对称的部分——Arcbé I, Dynamis I, Dynamis II, Arcbé II——证明了想要重塑世界的欲望。根据先锋派的逻辑,这个巨大的毁灭同时表露对新宇宙的诞生的渴望。
第二交响曲(圣诞)完成于七年后,整个参照十九世纪晚期的交响曲传统——瓦格纳、布鲁克纳、马勒、西贝柳斯和肖斯塔科维奇——渗透了一个经历过先锋派的作曲家的情感与技法表现。[7]59-60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潘德列茨基自1970年起开始加速风格的蜕变——之前一年的《自然音响第二首》还在向前走,1970年的《宇宙的诞生》已经开始向后撤退,在此已经表露出“对新宇宙的诞生的渴望”,作曲家很可能在这时已经计划以交响曲的形式向先锋阶段作最后的道别。《第二交响曲》以浓厚的浪漫主义晚期风格实现了对马勒世界的复兴,并在对圣诞歌曲《平安夜》主题的引用中宣告了对传统调性和宗教音乐的彻底回归。这意味着诺亚方舟正式建成,自此以后,潘德列茨基再也没有下船——其后的五部交响曲虽各有不同的结构方式,但整体风格都是对《第二交响曲》的延续。
实际上,对于潘德列茨基来说,交响曲只是方舟的一个表现形式,背后隐藏的是他对古典结构传统和浪漫情感表达的深深怀恋。潘德列茨基像诺亚那样,将洪水中幸存下来的传统形式装进交响曲这艘巨大的方舟内,等到洪水退去的那一天,重建一个崭新的世界,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问题是,洪水会退去吗?潘德列茨基是诺亚吗?他倒像是作为英雄的唐·吉诃德,对早已过时的骑士精神的迷恋,让他举矛力战风车,而在这个庄重持续被戏谑的时代,每个人都是塞万提斯。当哲学也演变为语言的游戏,理想主义的坚持必然被现世理念轻易解构。但无论如何,潘德列茨基建起了理想中的方舟,且还有交响曲尚未完成,更重要的是,他还活着。
[1]Wolfram Schwinger. Krzysztof Penderecki, His Life and Work:Encounters, Biography and Musical Commentary,Translated by William Mann, Schott, 1989:16.
[2]Krzysztof Penderecki. Labyrinth of Time: Five Addresses for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Edited by Ray Robinson, Translated by William Brand, Hinshaw Music, 1998.
[3]Mieczysław Tomaszewski: “Penderecki’s Dialogs and Games With Time and Place on Earth”,edited by Ray Robinson and Regina Chłopicka, Studies in Penderecki, Triangle Productions, 1998:15.
[4]K. Robert Schwarz, "First a Firebrand, Then a Romantic. Now What?",New York Times, 20 Oct. 2006:H33.
[5](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顾连理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45.
[6]Scott Murphy. “A Model of Melodic Expectation for Some Neo-Romantic Music of Penderecki”,Perspectives of New Music, 2007:19-25.
[7]Agata Cholewińska:“Krzysztof Penderecki.VIII Symfonia ‘Pieśni przemijania’”, DUX0901, Booklet:8.
(责任编辑:王晓俊)
J601;J614
A
1008-9667(2016)02-0043-06
2015-09-25
李鹏程(1989— ),安徽亳州人。文学博士,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研究方向:西方现代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