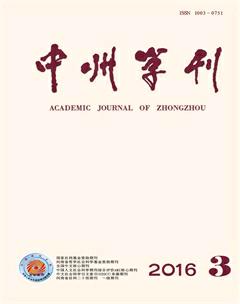重论《吕氏春秋》的音乐美学体系
刘 成 纪
【文艺研究】
重论《吕氏春秋》的音乐美学体系
刘 成 纪
摘要:在中国先秦时期,《吕氏春秋》因广采诸子之言而被后世称为“杂家”,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汇编或大杂烩,而是有一个比诸子学说更稳健、也更具包容和超越精神的思想系统。单就音乐而论,它在音乐的自然起源和心性起源上打通了一条顺畅的通道,从而使儒、道在自然和心性之间制造的对立得以克服。它赞同墨家的节俭,认同儒家对侈乐的批判,但也肯定人嗜欲的正当性。这看似矛盾,但由于有“自有道者观之”这一更高的视点,有主张适情、性养等更趋中道的立场,诸子围绕音乐价值产生的争论至此也就被顺利消解。以此为背景,《吕氏春秋》重点探讨了音乐的自然和心性起源、音乐的空间地理分布、音乐的时间性及历史沿革、音乐的创作和鉴赏原则等问题。其中,自然、心灵、空间、时间、适音、知音是它介入音乐认知的主体词,也构成了其音乐理论体系的主干性内容。就其展现的体系性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先秦诸子无人能出其右。
关键词:《吕氏春秋》;音乐美学;理论体系
近世以来,先秦乐论研究一直是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目前取得的成果看,存在着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现代学者习惯于以西方学科门类划分重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边界,这使原本横贯哲学、美学、艺术的先秦音乐史失去了自身的理论统一性。二是学界往往因过度重视诸子之间的思想差异而对一些融创性成果视而不见。事实上,先秦诸子乐论不仅一源分流,而且殊途同归。这个“一源”就是西周创立的乐制,而其“同归”则是《吕氏春秋》在兼采诸子基础上实现的理论融创。也就是说,中国先秦音乐史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再到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鲜明地体现出从“一源分流”到“殊途同归”的递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吕氏春秋》最终起到了集大成作用。
但是,在中国哲学、美学和音乐思想史中,《吕氏春秋》却往往因为它的“集大成”而被后人视为思想的大杂烩,认为它只有综合,没有创造。受这种学术偏见的影响,现行的中国美学通史或专史著作,要么对《吕氏春秋》弃置不论,要么对它的理论贡献难以做出合乎历史地位的评价。现在是对这一偏见做出校正的时候了。下面,笔者将通过对自然、心灵、空间、时间、适音、知音六个概念的分析,重建《吕氏春秋》的音乐美学体系,并对其理论价值做出新的引申和判断。
一、音乐的自然本源问题
按照现代人的艺术观念,音乐的价值在于审美。能够给人带来精神或情感愉悦的音乐就是好音乐。但是在中国社会早期,音乐却是哲学乃至神学的重要命题。比如在西周和春秋中前期,音乐主要被用于神灵祭祀活动,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艺术是建立人神感通的重要媒介。①此后,从春秋晚期至战国,音乐被形而上学化,像老子的“大音希声”、庄子的“天籁”之论,均意味着音乐成了哲学本体论的隐喻形式。从《吕氏春秋》对于音乐的定位来看,它无疑延续了这种关于音乐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观念,但是就理论表述的清晰性和系统性而言,却是对这一传统的卓越发展。
《吕氏春秋·大乐》云:“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这里谈到了音乐的两个哲学起点:一是音乐生成所依据的法则,即“度量”;二是音乐的本体论依据,即“太一”。对音乐而言,“度量”主要指音律。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音乐的创制首先要以音准或声调作为法式,然后才能根据声音的高低变化形成音乐。那么,这种作为法则的音律是如何产生的?按《吕氏春秋·音律》篇:“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也就是说,制定音律的依据是天地之气运动的合规律性(“天常”)。具体言之,天地之气在交合中产生风,风与物的撞击产生声音。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中,风会随着季节和月令的变化而产生规律性的变化,这种规律也就成为确定音乐调式或音律的根据。据此可以看到,从自然界的气、风到音乐的声、律,有一个顺向的生成过程。这样,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法则,也就成了人间音乐创制所依托的法则。《吕氏春秋·古乐》记黄帝令乐师伶伦作律,伶伦以吹奏不同长度的竹管发出乐音的不同来确定音律,道理与此一致。
再看音乐所本的“太一”。比较言之,“度量”作为天地运演的法则,是形式性的;“太一”则侧重于自然天道的内在本质,更具本体性。那么,这种形而上的“太一”与音乐的关联性是什么?《吕氏春秋·大乐》这样描述: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
从这段话看,《吕氏春秋》所言的音乐虽然最终必然诉诸人的倾听,但它的存在根据却源于宇宙的本体。按照《吕氏春秋》设定的自然创化序列,宇宙的本源首先是太一,然后一分为二成为阴阳,阴阳交合绽放出生命的萌芽,进而出现事物的形体。进而言之,有形体的事物必然会发出声音,如果这声音是适度、和谐的,那么它就是音乐。这种音乐起源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但为音乐的产生确立了一个超越性的本体,而且也因此使作为艺术的音乐与作为自然的宇宙获得了同质关系。这种同质性意味着,无限浩渺的自然世界与人间的音乐相互贯通,宇宙可以理解为音乐性的,音乐也可以弥散为整个宇宙。这种“太一”论,为建构音乐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哲学的基础。
《吕氏春秋》从形式(“度量”)与内容(“太一”)两个方面理解音乐的起源,但无论它谈到的音乐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即自然。因此,所谓的音乐的形式起源或内容起源问题,可以归并为音乐的自然起源问题。这种自然起源论为《吕氏春秋》对自然的音乐化理解或音乐的自然化理解提供了哲学前提。比如,在《吕氏春秋》“十二纪”每篇的篇首,作者均用大段文字谈论每月的天象和物候变化,音乐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要素。自然界一年四季的变化,相应配合着不同的音乐调式,月与月之间的递变则应和着音乐的音高之变。这样,自然界的时间变迁被音乐化了。②与自然的韵律化和节奏化相一致,人事则应随着四季变化做出相应调整,所举行的礼乐活动也应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在这种音乐与世界的相互应和中,音乐因为对自然法则的遵循以及与自然的同质关系弥散四野,贯通天人,世界则因为自身运动变化的节奏和韵律而成为一个富有乐感的世界。
关于音乐与自然世界的联动关系,《吕氏春秋·应同》曾讲:“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则宫动,鼓角则角动。”这段话说明,音乐与自然的同质性,是两者相互感应的前提。人工音乐要想获得自然的呼应,就必须遵循自然的法式,摹拟自然运动变化的节律。这种同类相召、同气相合、同声相比的观念,打破了庄子在自然之音(“天籁”)与人工之音(“人籁”)之间制造的隔离或对立,同时也为儒家的“大乐与天地同和”提供了根据。从这个角度讲,《吕氏春秋》关于音乐与自然关系的探讨确实推进了战国时期音乐理论的发展。
二、音乐与心灵之关系
除自然外,心是《吕氏春秋》乐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牵涉到音乐哲学由自然本体向人本体的转换,也牵涉到音乐由对象性的艺术形式向主体性的快乐体验的转换。中国哲学自西周开始,心作为人的生命中枢、情感中枢和思维中枢的地位逐步明确,因此人与音乐的关系,最终也聚集于音乐与心灵的关系。
关于人心之于音乐的重要性,《吕氏春秋》主要有两点判断:一是以心灵作为音乐的起源,二是以心灵愉悦作为音乐审美体验的决定因素。关于第一点,《吕氏春秋·音初》云:“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这种判断乍看起来与《吕氏春秋·大乐》中“生于度量,本于太一”的讲法相矛盾,但事实上,却正是自然之音向人工之音、音乐对象向音乐体验转换的必然结论。也就是说,虽然音乐发于自然,但就具体的艺术形式来讲,它毕竟是人工的创制。自然是音乐的原创者,人的心灵则是音乐的直接作者。关于第二点,《吕氏春秋》认为,人有五官百体,音乐为人带来的快乐是全身心的,但心灵的快乐是获得音乐愉悦体验的基础,也是最终的判断标准。如《吕氏春秋·适音》云:“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口鼻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口鼻有以欲之。”在这段话中,《吕氏春秋》作者将人心视为五官百体的主宰者,也因此成为音乐体验能否形成的内在根据。
音乐到底发端于自然还是人的心灵,这是先秦乐论长期纠结的核心问题。如《乐记·乐本》③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这一般被认为是儒家讲究音乐心性起源的证据,但这篇文献马上接着又讲:“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意味着音乐虽然直接源于人心,但人心的意动又源自外物的触发。正是因此,儒家乐论到底是认同音乐的心理起源还是自然起源,或者是心物交感,理论界至今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对此,《吕氏春秋》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有启发意义的。
首先,在《吕氏春秋》的乐论体系中,自然与人心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存在着顺向的层级关系。如《音初》篇“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一句,明确指出音乐来自人对外部世界的感应,然后逐步向心灵内化。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构成了音乐起源的第一层级,心灵构成了第二层级。前者是哲学的、宏观的、本体性的,后者是心理学的、具体的、经验性的。音乐创作源自人心对自然之音的接引,然后再以心灵为基础,外发为具体的音乐。这就将儒家乐论中长期的心物对峙,转换成了一个顺向的连续过程。
其次,《吕氏春秋》肯定人的自然本性,所谓音乐的自然起源,并不单指对象性的自然界,而且也包括人的自然本性。如其所言:“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智愚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吕氏春秋·情欲》)按照儒家的观点,这种自然本性代表了人兽性的侧面,其艺术的表现则是郑卫之音或欲望性艺术。这样,如何遏制人性之恶,如何用雅乐与郑卫之音相对抗,也就成了儒家乐论的核心问题。对此,《吕氏春秋》认为,艺术的任务不是遏制人欲,而是养欲,即使人“六欲皆得其宜”(《吕氏春秋·贵生》),这就为人的自然本性确立了不可缺省的重要位置。按照这种观点,儒家反对郑卫之音或欲望性艺术,也就是反人性。相反,《吕氏春秋》肯定欲望是人的自然本性,并认为艺术的重要任务就是养欲或适欲,这就变相肯定了郑卫之音存在的合理性。
最后,关于人心与人的自然之欲的关系,《吕氏春秋》认为,心灵的快适以人自然之欲的满足为前提,即“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吕氏春秋·适音》)但是,自然之欲的满足又并非让人心灵愉悦的充分条件。如果欲望的膨胀超出了心灵可承受的限度,就不但不快乐,而且会因此痛苦并伤害生命。这样,《吕氏春秋》虽然重视人从音乐艺术中获得快乐的重要性,但评判快乐的标准并不是欲望,而是心灵,即“乐之务在于和心”(《吕氏春秋·适音》)。据此来看,在艺术接受的层面,心灵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它是艺术效果的评价尺度。它既源于人的自然欲望又朝精神层面超越,在两者之间起着调节和制衡的作用。《吕氏春秋》所讲的自然与心灵的关系,正是在此意义上不再是儒家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而是立于欲望又超越欲望的递进关系。
三、音乐的空间呈现
《吕氏春秋》对音乐空间分布的认识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十二纪》中以四季配四方,赋予不同的空间方位以不同的音乐属性;二是《音初》篇对四方音乐源流的考察。前者是理论性的,后者则是经验性的。
中国上古时期对四方的完整认知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④;将空间方位按东、南、西、北的顺序理出一个有序的系统,则可追溯到《尚书·尧典》中“曰若稽古”一节⑤。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上古时期对四方空间的认知与后世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方位的排序方式。比较言之,先秦时期方位的排序基本是圆周式的,即按东、南、西、北的顺时针方向构建出一个空间体系;汉代以后,这种圆周式的空间体系逐渐被东、西、南、北的坐标对称形式取代。就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来看,圆周式的空间定位法应是源于人对天象运动的观察,与中国早期的天文学有关;坐标式的空间定位则应源自人的地理经验,是人以自我为中心形成的地理学知识。
认清中国社会早期空间定位方式的天文学起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天文学与中国早期历法密切相关。其中,自然空间按照东、南、西、北的顺时针方向运动,历法则使抽象的时间按四季的变换流转,这就将时间和空间共同组入一个统一的自然经验系统。古人认定春天来自东方,所以东方与春天相配;夏季因太阳悬挂于南方而炎热,所以南方与夏季相配;秋天因西北风而转凉,所以西方与秋季相联;冬天因北方寒气的侵袭而寒冷,所以北方是与冬季相联的季节。以这种四方与四季的组合为基础,由于音乐首先是来自自然界的天籁之音,四季的变化也必然体现为音乐音阶和调式的差异。这样,音乐不仅随着四季的流转而具有了时间性,而且也因为四季有不同的空间归属而使四方具有了不同的音乐属性。
先秦至两汉时期,将音乐组入四季并进而进行空间配置的文献,计有《逸周书·月令解》《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时则训》。按一般的历史时序判断,《逸周书》应该出现最早,其次为《礼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事实上,《礼记·月令》来自汉代经学家对《吕氏春秋》的抄录整理,《逸周书·月令解》更是清人卢文弨根据《吕氏春秋》对《逸周书》所作的补录⑥。通过文献比对也可以发现,为了将四季与五行、五音相配,《淮南子·时则训》将季夏独辟出来,以对应于五行的土和五音的宫调;《礼记·月令》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改造,即将夏秋交接之际单独列出,以对应于五行。这证明,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礼记·月令》体现出中国历法体系逐步趋于完备的发展过程。《吕氏春秋》则因为尚待修改和完备,证明它才是这一音乐化空间体系的最早创立者。《淮南子·时训解》《礼记·月令》《逸周书·月令解》则是后发性文献,是对《吕氏春秋·十二纪》进行修改、完善的产物。那么,《吕氏春秋·十二纪》如何将音乐组入一种相对固定的空间架构中?
首先,这部文献以五音对应于四季,进而赋予四方不同的音阶或调式属性。其中,春季对应于东方,即“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吕氏春秋·孟春》)。这一季对应于五音中的角音,也即东方是与角音相配的方位。依次类推,徵音在南方,商音在西方,羽音在北方。其中,作为五音之主的宫并没有出现。但是,按照先秦至两汉东南西北中的方位排列法,宫显然对应于中,即被四方环绕的中间地带。此后,《淮南子·时训解》和《礼记·月令》对这一环节作了补充。
其次,与五音相比,十二律对音乐音高的测量更趋细密。十二律与地理方位的对应关系,《吕氏春秋》并没有明讲,但从《十二纪》中所列音律与一年十二月的配置关系不难发现,它同样具有与地理方位的对应性。比如,孟春之月,“律中太蔟”;仲春之月,“律中夹钟”;季春之月,“律中姑洗”。这说明太蔟、夹钟、姑洗都是与东方相关的音律,应依次对应于东偏北、东、东偏南。孟夏之月,“律中仲吕”;仲夏之月,“律中蕤宾”;季夏之月,“律中林钟”。这说明仲吕、蕤宾、林钟都是与南方相关的音律,分别对应于南偏东、南、南偏西。依次类推,夷则、南吕、无射分别对应于西偏南、西、西偏北,应钟、黄钟、大吕分别对应于北偏西、北、北偏东。这样,从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到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既是音律的变化,也是对圆周形的自然地理方位的音乐化指称。在此,五音十二律不仅使整个以中央之地为中心的地理空间音乐化了,而且也使不同的地理方位具有了不同的音乐属性。这种音乐地理学的形成,应与早期中国人对四方水土风气的神秘感知有关⑦,但真正将人感知经验音乐化、并建构成一种有序的空间系统,却应是《吕氏春秋》的一大发明。
《吕氏春秋·十二纪》每篇篇首对音乐空间方位的定位,是理论化、图式化的。与此比较,《吕氏春秋·音初》则通过对四方之音的历史考察,为这种音乐地理学提供了经验层面的证明。这篇文献将音乐分为东音、南音、西音和北音,其中东音的产生与夏桀的曾祖父夏后氏孔甲有关。据《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孔甲在东阳的萯山打猎时领养了一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用斧头砍伤了自己的脚,沦为看门人。孔甲作《破斧之歌》表达哀伤,这是东音的起源。南音与夏禹的妻子涂山氏之女有关。夏禹南行治水,娶涂山氏之女,女子为了表达对夏禹的思念,作歌“候人兮猗”,这是南音的起源。此后周公、召公依其风格创作了《周南》和《召南》。西音起于殷王河亶甲的思乡之歌,西周时期被周昭王的辅臣辛余靡继承,后在秦缪公时发展成秦音。北音最早源于有娀氏之女,其内容是对燕子的歌吟。
《吕氏春秋·音初》篇对四方之音的史源考察,是否具有真实性,今人已不可知,但这种努力却为战国时期音乐的区域差异提供了历史的依据。中国社会自西周起,就形成了以乐观风的传统,《吕氏春秋》为这种观风传统提供了史源学上的根据,是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
四、音乐的时间秩序
音乐是一种时间艺术,大自然则以星移斗转、草木枯荣体现出韵律、节奏和动感,这使音乐与自然具有天然的类同性。中国古人之所以能从天道运行、四季变化中体验到音乐式的律动,大致与此有关。如前所言,在《吕氏春秋》以前,至今尚没有发现将四季、月令变化与音乐调式进行配置的案例,这或能说明,以音乐描述四季变化并因此使时间音乐化,是《吕氏春秋》的一大创造。
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角、徵、商、羽分别被视为春、夏、秋、冬四季的音乐调式;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则是一年十二个月体现的不同音律。据《周礼·大司乐》,美好的乐音并非单来自音调或音律,而是多种音乐元素的协奏,即“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这说明,不同的音律与调式的组合,使音乐的旋律表现出无限的复杂性。据此可以看到,《吕氏春秋·十二纪》在讲述每一月的音乐属性时,往往音与律相配,如“孟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太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对音乐的音高和调式进行了协同式的规定。这样,在四季与月令之间,既有音乐的主调,又有音乐的变奏,自然界时序的变迁和时间年年岁岁的流转,也就成了一首乐曲终而复始、始而复终的过程。在此,无限的自然空间就被组入时间的运动之中,时间因季节之变而表现出的乐感,则使空间世界成为音乐进程的表征。后世中国文学艺术中体现的生命意识、时间意识,尤其是对这种意识的音乐化表达,其理论源头应该可以追溯到《吕氏春秋》。
除了对一年四季的音乐化体认外,《吕氏春秋》的另一个贡献是关于音乐自身的,即它整理出了一个连续的中国音乐的早期历史。比较言之,《吕氏春秋·音初》追溯了东音、南音、西音、北音的历史源头,这主要是为散布四方的民间音乐探源,但除了四方之音外,显然还应有处于天下之中的圣王之音。这才是音乐的“主旋律”,它的历史才是音乐史的主线。《吕氏春秋》对音乐史的梳理,占主导的就是圣王之音的历史沿革。
《吕氏春秋》对这种主流音乐史的记述见于《古乐》篇,顺序大致为: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黄帝→颛顼→帝喾→舜→禹→殷汤→周文王→周成王,这些人物基本贯穿了中国上古音乐史的进程。其中,朱襄氏之臣士达制作五弦琴;葛天氏创作歌乐;陶唐氏编制乐舞;黄帝命伶伦作律,并创作《咸池》之乐;颛顼命大臣飞龙作《承云》;帝喾命大臣咸黑作《声歌》;尧帝命大臣质作《大章》;舜帝命大臣延作《九招》《六列》《六英》;禹命皋陶氏作《夏龠》;汤命伊尹作《大护》。此后,周公为文王作颂诗,为武王作《大武》之乐,为成王作《三象》之乐。《吕氏春秋·古乐》对上古音乐史的这一追述,总体上仍有些简单,但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却十分值得注意。比如,儒家讲到上古之乐,往往直接将其视为圣王的创造,这一方面将圣王神化,另一方面也将音乐充分政治化。与此比较,《吕氏春秋》将音乐的“著作权”还给了每一时代的乐师或懂音乐的大臣,这显然更符合音乐史的实际状况,也反映了《吕氏春秋》对圣王的态度与儒家无条件的崇拜有区别。
同时,《吕氏春秋》对上古音乐史的叙述潜藏着它对音乐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其中,朱襄氏制作五弦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然界“万物散解,果实不成”的问题;葛天氏之乐是为了“遂草木,奋五谷,达帝功,依地德,总万物之极”;陶唐氏作舞是为了解决自然界的“阴多,滞伏而湛积”;黄帝作律是为了“听凤凰之鸣”,以与自然呼应;颛顼作《承云》是为了“效八风之音”,“以祭上帝”;帝喾作《声歌》是为了“以康帝德”;帝尧作乐是为了“以致舞百兽”,“以祭上帝”;帝舜作乐是为了“以明帝德”;禹作乐是为了“以昭其功”;殷汤作乐是为了“以见其善”;周公为文王作颂诗是为了“以绳文王之德”,为武王作乐是为了纪念牧野之战的胜利,为成王作乐是为了纪念对殷遗民战争的成功。
这一历史过程,凸显着中国上古音乐主题的逐步变迁。其中,自朱襄氏至陶唐氏,音乐的作用基本被定位在解决自然界对人的具体危害,自然本身是人实际生活的对象。但自黄帝始,自然逐步被神化、精神化,成为被人祭祀、敬拜的人格神。但自舜帝始,自然性的人格神开始转化为人间的圣王,像舜帝用来“明帝德”的《韶乐》,到底“明”的是自然神的德行还是舜本人的仁德,已无法分得清楚。到了禹,他用来“以昭其功”的《夏龠》,则彻底甩脱了自然,成为对人间帝王治水之功的颂扬。至殷汤的《大护》,音乐主题有新的发展,它不再像禹一样歌颂人在征服自然时获得的成功,而是颂扬商汤赶走了无道的暴君,使人间的正义得到伸张。再至文王、武王、成王,音乐的主题则基本摆脱了人间战争中的善恶问题,成了对胜利者的赤裸裸的歌颂。这种音乐主题的变化,总体上可概括为从自然主题向人的主题的变化。具体言之,则是首先从物性的自然转变为神性的自然,从自然神(天帝)转变为人间圣王(人帝),从人与自然的斗争转变为人与人的斗争,从彰显仁德的正义之战到胜王败寇的武力较量。如上分析是否符合《吕氏春秋》作者的本意已不可考,但其中体现的音乐主题的变迁却提示人们,《吕氏春秋·古乐》绝不仅仅是对音乐史的客观叙述,而是潜藏着作者的哲学思考和价值判断。音乐史的意义也因此超出了历史本身,成为一种关于音乐的历史哲学和价值哲学。
《吕氏春秋》作者在《古乐》中讲述了代表主流价值的上古音乐史,在《音初》中也理清了四方之音的源流。两者的组合因勾勒出先秦音乐体系的整体框架而富有价值,同时也在主与从、中央与四方、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设置中,凸显出作者天下一统的政治观念。这是《吕氏春秋》音乐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音乐创作的“适音”原则
《吕氏春秋》对音乐自然和心性本源的讨论,为这门艺术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对音乐中时空问题的讨论,则为其提供了宇宙论的框架。以此为背景,何种音乐是最好的音乐,成为《吕氏春秋》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吕氏春秋》认为,音乐最重要的创制原则是适宜或合适,“乐不适则不可以存”(《吕氏春秋·大理》),“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吕氏春秋·大乐》)。
在音乐创作和欣赏中,适宜是一个中介性原则,它意味着音乐的存在方式要在诸多对立因素之中寻找协调,比如适自然天道、适人性命之情等。关于音乐与自然天道的适宜,首先要注意《吕氏春秋》对道的界定与前人存在差异。比如对于老子,道是至高无上的范畴,它玄而又玄,不可诉诸名相,这为人对道的体认带来了巨大困难。但至《吕氏春秋》,道的位格明显向人的经验层面下降,如《吕氏春秋·大乐》云:
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悦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
这种“道”向“太一”的下降很重要,意味着抽象的天道可以被经验、被认知、被把握。在音乐活动中,天道之所以是“可适”的,就是因为它向人的经验显现了可遵循的规则和可把握的本质。如《吕氏春秋·大乐》讲,音乐“生于度量,本于太一”,这里的“度量”,就是音乐所要适宜的自然形式法则;所谓“太一”,则是音乐所要揭示的宇宙精神。
除自然外,音乐需要适宜的另一个对象是人自身。《吕氏春秋》认为,人生在世,以对个体生命的养护作为基本目标。圣王除了自养外,还要养护他的人民。与此一致,有利于这一目标的音乐就是适宜的,反之就是不适宜的。正如《吕氏春秋·本生》所云: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也就是说,感官快乐并不是判断音乐是否与人适宜的标准。如果它让人快乐但“听之使人聋”,必然会为人拒绝。这意味着,音乐之适存在着适耳、适心、适性(生)等不同层次。如果感官之适与心灵之适相矛盾,适耳就要让位于适心,即“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吕氏春秋·适音》)。进而言之,如果心灵快乐与全生之道相矛盾,则以全生作为音乐的最高目的。
适天、适人是《吕氏春秋》为音乐的适宜性确立的两大标准,也是音乐创作所应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对于音乐的“适”,《吕氏春秋·适音》中这样解释:
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大小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乐无太,平和者是也。
在这段话中,作者以“衷”释“适”。“衷”是指乐器的体量要遵循制器的法度,即“大不出钧,重不过石”。这意味着“适”首先是指乐器的合乎度量。但是,乐器是否合乎度量,根本的判断标准还是乐器发出的乐音是否适宜人的欣赏。对此,《吕氏春秋·适音》云:
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窕;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谿极,谿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耳不抟,不抟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
这里提到的乐音的大小清浊,虽然与乐器有关,但最终还是要看它能不能为耳所“容”,为耳所“充”,为耳所“鉴”,为耳所“抟”。也就是说,除了乐器的制作合乎法度叫作“适”,主体感受更是判断音乐是否适宜的重要标准。《吕氏春秋》认为,和谐的音乐之境来自适宜的音乐对象与适宜的主体感受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过程被称为“以适听适”,即“以适听适则和矣”。
《吕氏春秋》之所以提出音乐制作和欣赏中的适宜问题,是以战国时代艺术的普遍不适宜作为背景的。具体到音乐而言,《吕氏春秋》的两句话颇有概括力,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吕氏春秋·侈乐》)。当时的统治者热衷于用体量庞大的乐器和规模壮阔的乐队来炫耀自己的威势和权力。这种乐器和乐队,“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躁”(《吕氏春秋·大乐》),《吕氏春秋》将其称为“侈乐”。
对于侈乐,《吕氏春秋》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但与儒、墨对音乐的批评视角又有明显不同。比较言之,儒家对此类音乐的批评是伦理性的,即它僭越礼制,并诱发人道德堕落。墨家的批评是经济性的,即它浪费社会财富,并使统治者忽略为国家创富承担的责任。《吕氏春秋》的批评则更多基于全生、重己的观念。它认为,音乐的作用在于安性自娱,使人的生命得到养护,但是侈乐背离了这一目标。《吕氏春秋》认为,巨型乐器发出的鸣响,超出了人的感官所能承受的限度,必然对人的耳目造成伤害。同时,人对音乐这种欲望性的对象,往往贪得无厌,日夜追求,得到了就迷失其中不能自拔,这必然伤害人的天性。如其所言:“世之富贵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吕氏春秋·本生》)正因如此,《吕氏春秋》将这种无节制的欲望性音乐称为伤生害命的利刃,即“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吕氏春秋·大生》)。
以此为基础,《吕氏春秋》将侈乐的危害进一步向社会层面引申,认为音乐的僭越礼制、浪费财富必然导致“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吕氏春秋·大乐》)。这就产生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统治者愈是要从音乐中追求超强度的快乐,结果往往愈是失去快乐;愈是想让生命得到超量享受,反而愈会加速丢掉性命。根据这种关于求乐与失乐的辩证法,《吕氏春秋》既捍卫了生命本位主义的音乐立场,同时也把儒、道对音乐的批判包括了进去,体现出其音乐理论综合性与创造性兼备的特性。同时,它主张音乐不可过侈,但也不可因此彻底否定音乐的享受,这也将它以适宜为本的音乐创制原则,贯彻到了艺术观念之中。
六、音乐鉴赏的“知音”原则
知音是中国音乐艺术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它涉及对音乐的理解力、演奏者与鉴赏者之间的共鸣,以及以音乐为媒介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知相惜等。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知音因难觅而珍贵,说明无论音乐艺术还是人心,都以交互性的妙会和共赏作为个体价值实现的重要通道。
音乐史上的“知音”之论,最早见于《列子》和《吕氏春秋》。由于《列子》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定,直至东晋张湛才最后成书,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作为先秦史料使用,学界一直存疑。与之相比较,《吕氏春秋》不仅具有历史的可信性,而且它对知音的论述也更为深入而完整。如《吕氏春秋·长见》记云:
晋平公铸为大钟,使工听之,皆以为调矣。师旷曰:“不调,使便铸之。”平公曰:“工皆以为调矣。”师旷曰:“后世有知音者,将知钟之不调也,臣窃为君耻之。”至于师涓而果知钟之不调也。是师旷欲善调钟,以为后世之知音者。
《吕氏春秋》提起这一历史轶事,本是要论述博通古今的重要性,但对音乐鉴赏中的知音问题却给予了全面的阐明。其中,师旷之所以能对钟声是否合调做出精准判断,是因为他有高出常人的音乐修养和对声音的辨析能力。同时,师旷的判断后来被卫灵公的乐师师涓认定是正确的,则说明师旷遇到了真正理解音乐也理解自己的人。这就涉及中国古代知音理论的两项基本内容:一是知音乐本身,二是以音乐为媒介知人。同时,中国音乐至春秋时代开始逾越礼制,与师旷同一时代的周景王,曾因铸大钟受到单穆公的尖锐批评。从技术层面讲,这一时代乐器体量的增大,最大的问题是声音失调,并因音量过大对人的听觉造成不适。⑧据此可以看到,知音者判断一种音乐是否合调,标准就是它对礼制以及人的感官是否适宜。这样,《吕氏春秋》提出的“以适听适”的音乐鉴赏原则,就成了使“知音”成为可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以此为背景,《吕氏春秋》对“知音”的界定如下。
第一,知音以“知音乐本身”为本义。《吕氏春秋》认为,良好的音乐修养是知音的前提。如其所言:“凡能听音者,必达于五声。人之能知五声者寡,所善恶得不苟?”(《吕氏春秋·遇合》)也就是说,只有通达五声等乐理知识,才能获得音乐的欣赏能力。乐理知识的匮乏,是人对音乐丧失美丑判断,甚至以丑陋、粗鄙为美的原因。如其举例讲:“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吕氏春秋·遇合》)在《吕氏春秋》作者看来,越王之所以出现这种选择的错乱,并不是因为“野音”更具艺术魅力,而是因为他缺乏必要的音乐知识,不懂音乐。据此也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帝王权贵普遍喜好世俗之乐,并不仅仅是因为先王之乐已经过时或者时代已充分欲望化,而是因为这一时期全面抛弃了西周以降的乐教传统,统治阶层普遍缺乏必要的音乐教育。
第二,从“知音乐本身”向“借乐以知人”引申,这也是对后世艺术理论影响最大之处。《吕氏春秋·本味》举了伯牙摔琴的例子,如其中言: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要理解这段轶事的意义,同样需要理解西周以降漫长的乐教传统。从历史看,这一乐教起码在音乐认知方面结出了两大硕果:一是在“技术—自然”层面,孕育出了师旷等一批对乐音具有超强辨析能力的音乐大师。这些人不但是乐师,也是音乐哲学家,他们善于捕捉大自然借音乐向人类传递的隐秘信息,并用于指导现实政治实践。如春秋时期晋楚之战,师旷骤歌南风,通过“南风不竞”,就得出了楚师“必无功”的结论等⑨。二是在“审美—伦理”层面,出现了季札、孔子这类伟大的音乐鉴赏家。他们不但为音乐之美陶醉、忘情,而且通过审美体验进一步辨析出音乐的社会伦理意向,并以此为国家政治提供借鉴。至《吕氏春秋》中提到的俞伯牙和钟子期,人对音乐的理解显然已不局限于辨音技术以及对音乐社会伦理价值的外向引发,而是转进到对音乐内在表意指向的深入领悟和洞察。
孔子时代,音乐属于公共性的鉴赏活动,音乐演奏者被淹没在乐队的整体架构中,无法凸显个性;鉴赏者则因为艺术传达的公共性而使私人性体验受到制约。与此比较,伯牙鼓琴是个体性行为,这使音乐由公共情感表达转换为私人情感表达;子期的聆听也是个体化的,这有助于欣赏者与演奏者形成具有专对性的交互关系,从而使音乐成为个人表情达意的媒介,也使个体体验成为音乐艺术中最重要的体验。从这个角度讲,自春秋至战国,一方面音乐在统治阶层日益膨胀它的规模和豪侈程度,但另一方面也在朝更个体、更私人、更注重精神本质的方向发展。可以认为,知音从春秋时代的知技、知理发展到战国时期的知意,音乐从注重公共伦理价值转进到关注个体情感、精神价值,是《吕氏春秋》对于战国时代音乐变化的重要启示。这种变化,为中国音乐从贵族音乐向士人音乐的转变开了先声。甚而言之,在中国,一部知音史就是一部音乐鉴赏史,更是士人以音乐为媒介寻求友谊和精神慰藉的历史。《吕氏春秋·本味》中“伯牙鼓琴”一节之于中国美学的意义,既存在于士人私人化的音乐体验中,也表现于这一阶层千古一贯的生存理想之中。
注释
①参见刘成纪:《上古至春秋乐论中的“乐与神通”问题》,《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②如《吕氏春秋·孟春纪》:“其音角,律中太蔟。”“命乐正入学习舞。”《仲春纪》:“其音角,律中夹钟。”“上丁,命乐正入舞,舍采。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季春纪》:“其音角,律中姑洗。”“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帅三公、九卿、大夫亲往视之。”《孟夏纪》:“其音徵,律中仲吕。”“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天子饮酎,用礼乐。”《仲夏纪》:“其音徵,律中蕤宾。”“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埙、篪,饬锺、磬、柷、敔。”《季夏纪》:“其音徵,律中林钟。”《孟秋纪》:“其音商,律中夷则。”《仲秋纪》:“其音商,律中南吕。”《季秋纪》:“其音商,律中无射。”“上丁,入学习吹。”《孟冬纪》:“其音羽,律中应钟。”《仲冬纪》:“其音羽,律中黄钟。”《季冬纪》:“其音羽,律中大吕。”“命乐师,大合吹而罢。”③《乐记》是西汉经学家戴圣对先秦文献的集录性成果。由于它的内容与《荀子·乐论》多有重合,也由于后世史籍中对其出处的记载相互龃龉,它的作者到底是谁,已成为中国音乐美学史中难以破解的悬案。笔者认同郭沫若的观点,即《乐记》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但最终成果经历了从战国至西汉时期儒家思想者的修订和整理。公孙尼子生活在战国初期,《乐记》因此可视为了解战国时期儒家音乐美学观念的代表性文献。④如甲骨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见郭沫若:《卜辞通篡》,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68页。)⑤按《尚书·尧典》:“(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在这段话中,尧帝让羲和总掌天地四时,然后按照顺时针顺序,让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居于东、南、西、北四方,并掌管四方事务。这为当时的自然地理划出了基本的空间格局。另外,《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帝一年中东巡至于岱宗,南巡至于南岳,西巡至于西岳,北巡至于北岳,也是按照顺时针方向来规划中华帝国的空间地理架构。⑥参见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57页。⑦将五音与一个地区的水土风气、谷物种植相配,早期文献见于《管子·地员》。这应该是在音乐与自然地理之间建立对应模式的早期雏形,但仍不涉及空间方位问题。⑧参见《国语·周语下》。⑨按《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责任编辑:采薇
A New Study on the Aesthetic of Music Theoretical System of Lüshichunqiu
LiuChengji
Abstract:Lüshichunqiu is a work written in the pre-Qin period, which has been considered as Eclectics for its inclusiveness of most of the philosophers of that period. Nevertheless, Lüshichunqiu is not simply a grab-bag of its contemporary thoughts, but a steadier system of thought with more inclusiveness and transcendence. Specific to Music, it opens up for music an approach from its natural origin towards its dispositional origin, which overcomes the nature-disposition conflict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It agreed upon the austerity in Mohist tradition as well as the critic towards extravagant music in Confucianist tradition, but it also recognized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appetitive imperative of human being. This seemingly contradiction raised by its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concerning the value of music is well resolv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on the view of people with Dao",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aking a moderate position in the sense of its assertion on adaption to temperament, cultivation of Xing, etc. With the above said as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Lüshichunqiu concentrated on the subjects, such as the natural and dispositional origin of music,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usic in its time, the temporality and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music, and the appreciation and creation of music; and involved itself in the discussion of music at pre-Qin period through various main concepts as nature, mind, space, time, appropriate music, music understanding, which are also the constituents of its main content. There′re hardly any philosophers in pre-Qin period that can excel Lüshichunqiu in the sense of the systematics and the influence upon aftertime it presents.
Key words:Lüshichunqiu;aesthetic of music;theoretical system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3-0145-09
作者简介:刘成纪,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收稿日期:2016-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