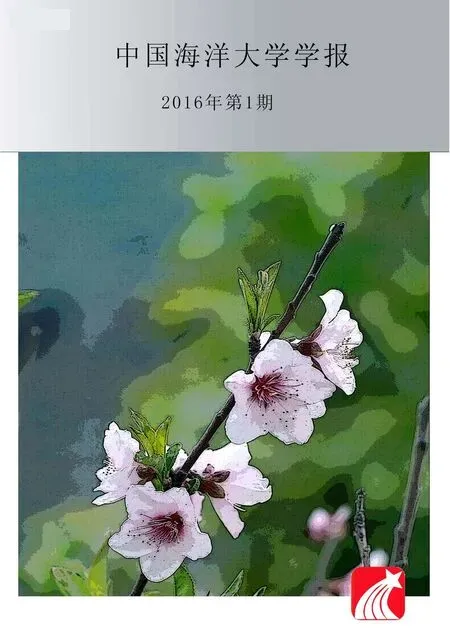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
[德]米夏埃尔·诺特 孙立新
(1.格拉夫斯瓦尔德大学 哲学系历史学部,德国 格拉夫斯瓦尔德;2.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
[德]米夏埃尔·诺特1孙立新2
(1.格拉夫斯瓦尔德大学 哲学系历史学部,德国 格拉夫斯瓦尔德;2.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本文系提交2015年8月23—29日在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圆桌会议讨论稿。其主旨是通过引进“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这一概念,拓展历史研究领域,加强国际的和跨学科的合作。在对厄勒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这些充满了多民族交往历史的场域进行了宏观考察后,作者强调指出,未来的历史研究有必要将各民族“共享的记忆”或者更确切地说“分割的记忆”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以便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关键词:海洋;海峡;记忆场域;跨民族交往
本文旨在将“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这一概念引入历史学之中。与重构海洋在文学、艺术和音乐中的再现的做法不同,我们希望讨论一些已被概念化的宽泛概念,要求国际的和跨学科的合作。
将海洋当作一种全球性的、历史性的现象进行考察,这一行为超越了仅仅研究海洋在美术中的再现的活动。因为生物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民族的和跨民族的诸多方面都被包括在内,所以诸如“作为一个全球性记忆场域的海洋”的较宽范概念可以克服传统的单个学科的局限性。
这种新方法是在几年前兴起的,而其始作俑者是一些文学家,他们试图解构神秘主义的海洋观,按照这种海洋观,海洋是“疯狂的象征、非理性的女人、不守规矩或浪漫主义的反文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理性的、“立足于陆地的”现代性建构)[1](P2)
通过“将海洋历史化”,这些同行们竭力解构有关海上接触的主流观点,从而超越了民族国家和传统的海洋史。保罗·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便是此类开拓新路的著作之一。黑色大西洋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现代的跨文化实体,主要由作为一种“移动的、鲜活的微型文化和微型政治系统”[2](P17)的海上航船所代表,同时也主要由它们所构成。
海洋和船只因此被评价为文化冲突或文化合作发生的空间和场所。其他的学者,例如马尔库斯·雷迪克尔,则将海洋视为真正的“红色大西洋”,一个充满革命动力、新兴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暴力与反抗的海洋空间(一个工人的大西洋)。*参阅Marcus Rediker, "The Red Atlantic, or, 'a terrible blast swept over the heaving sea'," in: Bernhard Klein and Gesa Mackenthun, eds., Sea Changes: Historicizing the Ocean, New York 2003, 111-130; Peter Linebaugh and Marcus Rediker, The Many-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Commoner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 Boston 2000.
有趣的是,在这些方法中,记忆这个概念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仅仅是被隐式地或间接地强调了一下。这也是“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概念之所以还能够释放更多科学潜力的原因所在。
接下来,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记忆场域概念,然后将这一概念扩展到作为记忆场域的海洋上。
记忆场域概念
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记忆场域这一概念是在法国由皮埃尔·诺拉阐发的。法国对于集体记忆的重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这里,国家、民族和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局势促成了里程碑式的七卷本著作《记忆场域》的出版(1984—1992年)。*参阅Pierre Nora,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7 vol., Paris 1983-1992.按照诺拉的见解,“记忆场域是指所有意义重大的实体,不论其实质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些实体已经成为某一共同体(在本案中指的是法国共同体)记忆遗产的符号元素”。[3](PXV-XXIV)诺拉强调符号的价值,而在过去这种价值通常是与历史科学相分离的,被降低到历史叙述层面(因为它们构成历史的一个整体部分,经常是与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记忆场域包括:
——诸如档案馆、博物馆、教堂、城堡和墓地等地方
——诸如庆典、世代、格言警句、仪式等概念和实践
——以继承的财产、纪念碑、手册、徽章、课本、符号为代表的物品。[3](PXV-XXIV)
皮埃尔·诺拉挑选了几处法兰西民族遗产诞生地作为他的研究的起点,直到后来才逐渐创立了一种新形式的(符号的)历史编纂学。这种簇新的历史编纂学在上列著作的第三卷(该卷以“法国”(LesFrance)这个意味深长的词汇为标题)之中浮现出来,并且,按照诺拉的见解,包含有“很多声音”,与“经典历史编纂学”相比,这些声音更能满足我们所处时代的科学和社会要求。记忆场域这一概念分别促进了符号的历史或象征意义的历史的发展,并为构建法兰西的“符号拓扑”做出了贡献。记忆场域因此将法国定义为一个符号现实,反映了一个“伟大民族”(GrandeNation)的风貌。后来,在有关意大利、德国、奥地利、丹麦和荷兰的研究项目中,“记忆场所”(Erinnerungsorte)或“记忆场”(plaatsen van herinnering)则更多地涉及或更好地定义了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文化记忆。*参阅Maarten Prak, Plaatsen van herinnering Nederland in de zeventiende en achttiende eeuw, Amsterdam 2006; Wim Blockmans and Herman Pleij, eds., Plaatsen van herinnering. Deel I: Nederland van prehistorie tot Beeldenstorm, Amsterdam 2007; Jan Bank, Nederland in de negentiende eeuw, Amsterdam 2006; Hagen Schulze and Étienne François, eds., Deutsche Erinnerungsorte. Eine Auswahl. 3 Vols., München 2005; Mario Isnenghi, ed., I luoghi della memoria. 3 Vols., Rom/Bari 1997-1998; Ole Feldbaek, ed., Dansk identitatshistorie, København 1991-1992; Moritz Csaky, ed., Die Verortung von Gedächtnis, Wien 2001; Sonja Kmec, Benot Majerus, Michel Margue and Pit Peporte, eds., Lieux de mémorie au Luxembourg, Erinnerungsorte in Luxemburg, Luxemburg 2007.记忆一般是有选择性的,文化或民族记忆甚至更多的是供选择的主题。*参阅Elizabeth Hallam and Jenny Hockey, Death, Mem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Oxford 2001; Johannes Fried, Der Schleier der Erinnerung. Grundzüge einer historischen Memorik, München 2004.荷兰的“记忆场”项目仅仅记录地点和狭义的纪念碑,而德国的“记忆场域”则包括记忆中的抽象对象,比如宗教改革、德国马克、德国联赛等等。
由于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视角,乍看起来,记忆场域似乎是与跨民族的海洋概念的需求相对立的。然而,恰恰在这一结合中,该概念的挑战和前景同时并存。如同将海洋概念化一样,对记忆场域概念加以跨民族的扩展将会为有关海洋再现的研究提供一种工具。通过贝克和加利马尔等出版商在法国发行的《德国记忆选编》(Mémoires allemandes)和在德国发行的《法国记忆场所》(Erinnerungsorte Frankreichs),人们已经在这一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参阅Étienne François and Hagen Schulze, eds., Mémoires allemandes, Paris 2007; Pierre Nora, ed., Erinnerungsorte Frankreichs, München 2005.其主旨是,通过法国和德国历史学家的紧密合作(Etienne François),展现法、德两国历史和记忆的相互纠缠。[4](P14)
不论在整个欧洲还是在欧洲之外,我们都会看到种种纠缠的记忆。即使绝大多数的记忆和记忆场域是从民族角度来接受的,这些记忆和记忆场域本身却是易受影响和超越民族的。因此,今后的研究需要关注共享的记忆,或者说分割的记忆(memoria divisa)和纠缠的历史,而特别需要关注的则是共享的记忆场域。这些分割的记忆场域(lieuxdemémoiredivisés),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在文化、空间和时间之间构成了众多符号交叉点,不仅同时影响着相邻的国家和记忆的民族文化,也影响着社会、种族和宗教团体等组织。*参阅Ann Rigney, "Divided Pasts: A Premature Memorial and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Remembrance," Memory Studies, 1 (2008): 89-97; Idem., The Afterlives of Walter Scott. Memory on the Move, Oxford 2012.对于此类共享的记忆场域范畴来说,海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和研究对象。
但是,将“海洋”这个范畴分割为诸如大洋和海域这样的次级范畴是很有必要的。所有这些次级范畴构成分割的记忆场域,并为纠缠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进一步细化这些范畴,我们便可以对海岸线、海峡、海战和沉船事件等进行研究了。
本文中,我们将通过仔细考察海峡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为此,我们选取了厄勒海峡(Øresund)、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和马六甲海峡(Malacca)作为案例,因为它们作为记忆场域具有很大的潜力。
厄勒海峡
松德海峡曾经是而且现在仍旧是从波罗的海通往北海和大西洋的门户。它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水道之一。出入波罗的海的要道由克隆堡宫把守,这座城堡位于埃尔西诺(赫尔辛堡),此处的海峡只有4公里宽。
艾瑞克国王于1429年开始征收松德海峡通关税,穿行海峡的船只起初需要缴纳一个金诺布尔,后来则是所载货物价值的1—2%。松德海峡通关税是丹麦一项最为重要的收入,它为历代丹麦国王在哥本哈根和西兰岛上开展的许多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提供资金支持,这其中就包括克隆堡宫。从20世纪初开始,海洋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就围绕着松德海峡通关税的报关单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参阅Nina E. Bang and K. Korst, Tabeller over skibsfart og vaeretransport gennem Oeresund 1497-1783, 7 volumes, Copenhagen/Leipzig 1906-1953; P. de Buck and J. Th. Lindblad, "De scheepvaart en handel uit de Oostzee op Amsterdam en de Republiek,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96(1983): 526-562; A. E. Christensen," Der handelsgeschichtliche Wert der Sundzollregister. Ein Beitrag zur seiner Beurteilung,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59(1934): 28-142; A. E. Christensen, Dutch trade to the Baltic around 1600, Copenhagen/The Hague 1941; P. Jeannin, "Les comptes du Sund comme source pour la construction d'indices généraux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Europe (XVIe-XVI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231(1964): 55-102, 307-340; W. S. Unger, "De Sonttabellen,"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41(1926): 137-155.
图表“办理松德海峡通关税手续船只的数量”*参阅Presentation by Jari Ojala, "Research potential of the database and guidebooks" for the conference "Baltic connections," Denmark 29-31 October 2007; Peter Borschberg and Michael North, "Transcending Borders: The Sea as Realm of Memory," Asia Europe Journal, 8(3) (2010): 279-292.

通过松德海峡的各国船只使这个海峡成了航海民族共享记忆的地方。然而,荷兰人和后来的英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支配着其他商贸民族。因为丹麦利用此地控制波罗的海的入口,克隆堡宫和松德海峡就成了丹麦、瑞典、波兰和俄罗斯为争夺波罗的海控制权(dominiummarisbaltici)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对象,而荷兰人和英国人又经常与波罗的海沿岸的航海大国结成各种各样的联盟。
16世纪时,吕贝克的舰队曾数次进攻埃尔西诺,而在17世纪,丹麦和瑞典则为争夺海峡的入口,特别是斯堪尼亚(斯科讷)的控制权而反复交战。荷兰人,作为一个主要的航海和贸易强国,也插手双方的事务以确保它能够安全前往自己的贸易区域。1644年,荷兰舰队在未受任何阻拦的情况下穿过海峡,加入瑞典舰队,最终大败丹麦。此次瑞典——荷兰联盟的根源在于克里斯蒂安四世打算提高松德海峡通关税的税率。但是,等到1657和1658年,荷兰人又认识到,如果让瑞典人控制松德海峡,荷兰自身的贸易力量同样会受到破坏。纵使如此,瑞典还是在1658年占有了斯堪尼亚。
所有这些冲突都在荷兰媒体中有所描述,而这些描述至今仍在塑造着我们关于松德海峡的记忆。
只有在俄罗斯—丹麦联盟在北方战争(1721)中获得胜利之后,丹麦才由于自己的中立态度而享受了一段长时间的太平光景。1750年前后,通过松德海峡的海上交通量激增,一年中会有4000到5000艘船只缴纳松德海峡通关税,而且这个数字一直在上升。在申报通关货物和计算不同货物的关税时,船长们愈发依赖领事和报关代理人的协助。而为了换取领事和报关代理人的帮助,船长会从这些人那里购买补给品。
领事馆的视觉遗产至今仍然存在,但对领事们的报告需要进一步研究。
松德海峡丹麦一侧的埃尔西诺也是一座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17世纪时,埃尔西诺有“小阿姆斯特丹”之称。18世纪时,由于英国在波罗的海的贸易量激增,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定居于松德。在多数情况下,家族的生意会做得很成功,并且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些商人在埃尔西诺的城市中心,即港口的滨水区,建造华丽的住宅和仓库,这些建筑物很多保存至今。还有一些富裕的商人在乡间购置庄园,用来夏季休假。当然,他们会给这些庄园起一些恰到好处的英国名字,比如“法瑞赫尔(Fairyhill)”,或者“克雷索普(Claythorpe)”。这些英国人并不和埃尔西诺的当地人套近乎,而当地人认为他们有种难以名状的傲慢。当这些家族的成员逝去,他们被安葬在埃尔西诺公墓,但是他们的墓碑是从英国特别定做的。很多墓碑保存至今。[5](P102-105)
哥本哈根之战(1801)和英国炮击哥本哈根(1807)导致商人、领事和报关代理人的生意无以为继,但在到1815年之后,交通重新恢复。现在,就连一些小国也会每年派遣几百艘船通过松德海峡达到西方。
松德海峡的水路通行不仅为通关税的报关单所记载,也为画家所描绘。这些画家为每一位船长勾勒一幅他们船只的速写,一种标准化的船长图画。

安东尼斯号,19世纪30年代中叶(Ojala 1997/GSF)

索维奥号三桅船(拉赫),1860(RM/Raahen historia)

凤凰号,奥卢1827(Snellman, Oulun laivoja ja laivureita…)
这些来自芬兰的样本可以回溯到19世纪60年代,那时的人们还仅仅从文化角度观察松德海峡。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拒绝缴纳松德海峡通关税,一份国际协定最终令松德海峡通关税寿终正寝。作为补偿,所有与波罗的海地区有贸易往来的海洋国家总共支付给丹麦35,000,000里克斯元。但无论如何,至少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说,松德海峡仍旧是通往西方的大门,也是一个记忆场域。数不清的画作描绘了克隆堡宫和松德海峡。
然而,厄勒海峡大桥的建成再次改变了松德海峡的意义;2000年6月1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宣布该大桥建成。哥本哈根人再度迁往斯堪尼亚,并在那里寻找价位可以接受的住房,而斯堪尼亚的瑞典人则通过大桥到丹麦去上班(每天有14000人通过厄勒海峡大桥)。这些穿行大桥、往返于各地区之间的人们令这个地方焕发新生。*参阅Orvar Löfgren, Regionauterna. Öresundsregionen från vision till vardag (Centrum för Danmarksstudier; 24), Gothenburg 2010.此外,伴随着大桥通车,政治家们尝试着创造一种“厄勒身份(Øresund identity)”用来克服老一套的丹麦——瑞典人观念。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厄勒大学的创建,一所由松德海峡两岸4所瑞典大学和8所丹麦大学构成的联合体,它面向该地区的所有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共同的课程、图书馆和其他设施。
直布罗陀海峡
“我来到我的家乡丹吉尔并拜访了她,还去了沙贝德(休达),我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月。我病了三个月,但是真主使我恢复了健康。从那以后我打算参加一场圣战(jihád)并且保卫前线,因此我登上一艘阿斯拉人(Asilá [Arzila])的三桅船,从休达渡海来到安达卢西亚(愿万能的真主保佑她!),当地人提供的报酬以及为定居者和来访者提供的补偿就摆在那里。这时基督徒暴君阿德弗努斯(阿方索十一世)已死,他对杰贝尔(直布罗陀)长达十个月的围攻也惨遭失败。他原本以为他可以捕获穆斯林在安达卢西亚拥有的所有东西,但是真主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刻带走了他,他同其他人一样患上了致命的瘟疫,并且死于这一瘟疫。来到安达卢西亚,我首先看到的就是征服之山(直布罗陀),我围着山绕了一圈,看到了由我们的主人(已故的摩洛哥苏丹)阿布·哈桑在山上完成的杰作,也看到了他为了保卫这一杰作而部署的工事,还有我们的主人阿布·伊南增加的部分;真主赐予他力量。我真该留下来,成为它的一名守卫者,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伊本·犹札补充道,“征服之山是伊斯兰的堡垒,一根卡在偶像崇拜者咽喉中的硬刺。伟大的征服就从这里开始了。”[6](P311f)
这一出自14世纪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手笔的文字,把直布罗陀海峡描述为一个引发接连不断冲突的主体。直布罗陀开始属于穆瓦希德帝国,后来被划归格林纳达的纳斯瑞德王国,它经常受到卡斯蒂尔的围攻,并于1462年最终被后者攻占,但是直到1502年才归于卡斯蒂尔王室控制。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断向北非扩张,所以地中海入口的两侧全部落入他们的手中(葡萄牙人控制的休达在1580年两国共尊一主时被合并了进来)。直到80年战争期间,西班牙的主宰地位才遭遇荷兰人的挑战。时至今日,荷兰人关于直布罗陀的记忆还是和1607年的直布罗陀之战联系在一起。那时,一支荷兰舰队偷袭了一直在直布罗陀海湾内停泊的西班牙舰队。
无论如何,英国人在直布罗陀的存在是1704年占领的结果。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盎格鲁—荷兰—哈布斯堡联军以奥地利大公、哈布斯堡家族王位索取者卡尔的名义攻占了直布罗陀。尽管卡尔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放弃了他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英国人却继续盘踞直布罗陀,直接控制了地中海的入口。西班牙在签订《乌特勒支条约》时曾将直布罗陀城和直布罗陀要塞割让给英国,但是后来又试图收复失地,多次发动毫无成果的围攻。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1779—1783年对直布罗陀展开的大围攻,此次大围攻主宰着集体记忆,相关解说也不断受到调整和纠正。其他记忆则是那些遭到直布罗陀海盗劫持的人质们的回忆。*参阅Daniel J. Vitkus, ed., Piracy, Slavery, and Redemption: Barbary Captivity Narratives from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York 2001.
自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来,直布罗陀巨岩又获得了一种新的战略价值,这与国际航运和不列颠对于其前往印度的通道的关注有密切关系。这种价值在世界大战期间不断上升。因此,大不列颠拒绝了弗朗哥政权提出的主权要求;后者则在1969年单方面关闭了边界。直到2006年(9月18日),在不列颠和西班牙外长与直布罗陀首席部长举行会晤之后,西班牙才解除了对交通、航空和国际长途电话业务的限制。*参阅David Abulafia,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 2012; Molly Greene, Catholic Pirates and Greek Merchants: 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Princeton Modern Greek Studies, Princeton 2010; Peregrine Horden, A Companion to Mediterranean History, Chichester, West Sussex 2014.
达达尼尔海峡
达达尼尔海峡也是一个引发连续不断冲突的主体。对于特洛伊来说,自公元前13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以来,控制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就是至关重要的,这就促使希腊水手千方百计要立足此地,并从富饶的黑海贸易中获得厚利。*参阅Good overview of the following James T. Shotwell and Francis Deák, Turkey at the Straits.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1971, 1-31; Charles King, The Black Sea: A History, New York 2011.随着希腊方面在特洛伊战争中获得胜利,控制海峡和不受限制地航行黑海便成为希腊商人和贸易扩张的头等大事。自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建立以来,晚期罗马帝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与日俱增。然而,这座融合希腊、罗马和东方文化于一体的城市,后来却受到来自意大利商业城市的挑战。11世纪时,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不仅纷纷到拜占庭从事贸易活动,还要求自由航行至黑海。1204—1261年,君士坦丁堡为威尼斯所占领,而对君士坦丁堡的争夺同时就是对黑海控制权的争夺。在黑海沿岸,热那亚建立了殖民城市卡法作为奴隶、蔗糖和其他东方产品的贸易中心。这一局势在奥斯曼帝国崛起后始发生改变。1356年,苏莱曼控制了加里波利并在此建设要塞。现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达达尼尔海峡两侧都筑起了防御工事,海面宽幅为1.5公里。
尽管如此,君士坦丁堡仍力求自保,热那亚和威尼斯也从奥斯曼人那里获得了自由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许可。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人在博斯普鲁斯建立了新的海峡控制点,并且逐步取消了基督徒船只驶出黑海的许可,这样一来,热那亚人的卡法殖民地也难以维持了。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不仅仅意味着对于黑海的控制,也意味着对于东地中海的控制。与黑海港口和黎凡特地区的贸易需要依赖于特许权,这种特许权给予领事治外法权,并承认他们的一些特殊权利。1535年,法国第一个得到了这种所谓的“投降条款”。此后,英国在1579年获得这种条款,尼德兰则是在1598和1612年获得。如此,达达尼尔海峡再次开放,在加里波利的城堡停留之后,船只可以抵达君士坦丁堡。由于土耳其仍旧禁止欧洲船只在黑海上航行,欧洲的商人们不得不租赁土耳其人的船只。
虽然如此,在整个17世纪,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依旧冲突不断。面对奥斯曼人的扩张,威尼斯试图保卫它在东地中海的剩余据点,其中包括克里特岛,该岛是威尼斯面积最大、最为富有的海外领土。为了阻挠奥斯曼人的舰队,威尼斯每年都会封锁达达尼尔海峡。这导致17世纪中叶在威尼斯和奥斯曼之间爆发了一系列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由于威尼斯战舰上配有英国和荷兰水手,这些战斗便以众多基督徒被奥斯曼海盗俘虏的方式进入欧洲人的视觉记忆当中,反之亦然。*参阅David S. T. Blackmore, Warfare o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ge of Sail. A History, 1571-1866, 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2011 91-94, 103-105.
17世纪80年代见证了奥斯曼人兵败维也纳城下,失去了像摩里亚这样的希腊港口,以及俄罗斯人在黑海地区的扩张。尽管彼得大帝攻击亚速的战役十分成功,奥斯曼帝国仍旧阻止俄罗斯的船只驶出亚述海,俄罗斯的商品不得不穿过黑海运抵君士坦丁堡。直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才成功征服了黑海北部。为了达成这一目标,1770年,叶卡捷琳娜让波罗海舰队穿过直布罗陀,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并从西部接近君士坦丁堡。这个尝试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奥斯曼和俄罗斯之间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74)声明“缔约双方的商船可以自由地畅通无阻的航行。”[7](P21)
其他欧洲列强接踵而至,也获得了商船自由通航的权利(奥地利1784,英国1799,法国1802,普鲁士1806)。奥斯曼人在商船方面的垄断虽被打破,但是奥斯曼帝国依旧禁止任何战舰穿行。鉴于此,在拿破仑时代,法国、俄罗斯和英国均极力争取奥斯曼土耳其作为自己的盟友。而当奥斯曼帝国站在法国一边时,英国舰队便在1807年远征达达尼尔,入侵君士坦丁堡。几乎同奥斯曼帝国一样,不列颠也成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实际控制者。
这样一来,很多商业民族就出现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其他海峡了。除了商人团体之外,领事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领事是外交使团的前身,并且与商贸活动有密切联系。当奥斯曼帝国将所谓的“投降条款”作为特权授予非穆斯林人员,允许他们居住和贸易时,商贸的拓展经常有领事机构在达达尼尔和加里波利的建立相伴随。热那亚和威尼斯的代表早在15世纪末期就常驻此地了。此后,法国于1535年派驻了领事,尼德兰(荷兰)则在1598和1612年,奥地利在1718年,瑞典在1736或1737年,两西西里王国在1740年,托斯卡纳、汉堡及吕贝克在1747年,丹麦在1756年,普鲁士在1761年,西班牙在1782年,俄罗斯在1717和1783年,撒丁王国大概在1825年前后,美国在1830年,比利时在1839年,汉萨同盟也在1839年,葡萄牙在1843年,希腊在1855年,巴西在1858年。最初,犹太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同时代表着不同欧洲国家的商业利益。一位领事同时是尼德兰和法国或尼德兰和英国的代表的情况在那时是十分常见的。除了犹太人家庭之外,所谓的德拉戈曼家族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也十分重要。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臣属,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此定居。他们附属于使领馆,担任翻译工作,并在黎凡特地区建立起了家庭的信用网络。在达达尼尔有沙贝尔(撒丁王国)、丰东(俄罗斯、丹麦、瑞典和挪威)或者福尔内特(法国)这样著名的德拉戈曼家族成员,他们在调和不同的贸易利益以及避免贸易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阅Collaborative online research project "Consuls of "The Dardanelles" and "Gallipoli", www.levantineheritage.com/pdf/Consuls_of_the_Dardanelles.pdf, updated Version no: 4 February 2013.有关领事的视觉遗产现在依旧可见,同(驻埃尔西诺的)领事报告一样,这些遗产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冲突将达达尼尔问题摆上了欧洲外交事务的日程。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土耳其战败,俄罗斯通过《温凯尔·伊斯凯莱西条约》(Treaty of Hunkiar Iskelesi)向土耳其施压,要求土耳其为俄罗斯守护海峡。这一结果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警觉,它们在1841年7月缔结的《伦敦协定》中达成共识,规定在和平时期只有奥斯曼帝国的军舰可以穿越达达尼尔海峡。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法国和英国以奥斯曼帝国的盟友的身份,派遣军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1856年的协定或多或少重申了1841年协定的内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希土战争(1919—1922)期间,将海峡非军事化和重新军事化的尝试最终在《蒙特勒协定》(1936年)中取得成功。根据该协议,海峡是国际航运通道,但是土耳其享有限制非黑海国家(例如希腊)海上交通的权利。这个最终解决方案在20和21世纪都没有再受到挑战。20世纪有关海峡的记忆被加里波利战役的阴霾所笼罩。1915年,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计划打通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共造成交战双方20多万人伤亡。英国的失败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记忆,即“澳新日”,时至当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旧纪念这一天。*参阅Peter Hart, Gallipoli (New York 2011); Mehmet M. Ilhan, Gallipoli: History, Memory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Ankara 2014; Robert Bollard, In the Shadow of Gallipoli: The Hidden History of Australia in World War I., Sydney 2013.
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也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海洋的记忆场域,因为它与马六甲海峡的历史和有关这条海峡的想象紧密相连。*参阅Peter Borschberg and Michael North, "Transcending Borders: The Sea as Realm of Memory," Asia Europe Journal, 8(3) (2010): 279-292.今天,马六甲海峡是指马来亚半岛西海岸和苏门答腊岛东海岸之间的一片狭长水域,从北部的亚齐和普吉岛延伸至南部的吉里汶岛。
在欧洲的地图和手稿中,马六甲城以北的海域总是被标注为马六甲海峡,而马六甲城以南的海域有时(尽管并不总是)则被称作新加坡海峡。*参阅Peter Borschberg, The Singapore and Melaka Straits. Violence, Security and Diplomacy in the 17th Century, Singapore 2010; Aileen Lau and Laure Lau (eds), Maritime Heritage of Singapore, Singapore 2005.
游记、地图、视觉再现以及物质文化共同创造了一种马六甲商业中心的想象,这一想象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欧洲人前往东方。
在早期的阿拉伯航海者眼中,马六甲海峡是一条凶险的河流,两岸居住着以打劫为生的部落,但是15世纪的中国人却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从宋代和明代有关“西洋”的原始资料中可以得知,马六甲海峡标志着一种心理上的分水岭,用今日的术语来表示就是“边缘区域”,或者说是“外围区域”,是保持定期商贸往来的地区的最西部。*参阅Roderich Ptak, China, the Portuguese and the Nanyang, Aldershot 2004; Roderich Ptak, Die Maritime Seidenstraße, Munich 2007.在这里,必须对“定期商贸往来”这一表达方式加以强调,因为中国人很清楚在这片区域之外还有陆地和海洋,而且最迟在唐宋两代就已经造访过这片水域。郑和七下西洋时也曾不止一次搜索过这片海峡,但他的主要目的是宣扬大明威德,教化海外诸番国。
当9—13世纪的阿拉伯商人谈论加沙河(River Gaza)时,这一拥有无尽财富的贸易中心尚未建立。最初,马六甲只是暹罗王国治下的一座滨海小镇,15世纪初,它成为了一座繁荣的商贸城市。根据现存的证据,有两件事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崛起。第一件事是当地的王公迎娶了一位苏木都剌的公主,当时,苏木都剌已经是当地一个兴旺发达的贸易和政治中心了。另外一件事是郑和赐给这个王公更高的封号。在这里,郑和仅仅注入了“中国元素”。*参阅Peter Borschberg and Martin Krieger, eds., Water and State in Europe and Asia, New Delhi 2008; Paul Wheatley, Impression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in Ancient Times, Singapore 1964.这个小邦在15世纪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贸易方面,在那个时期就已经闻名欧洲。瓦斯科·达·伽马远航印度之后,热那亚人吉罗拉莫·达·桑托(Girolamo da Santo Stefano)和博洛尼亚人路多维科·德·法特玛(Ludovico de Varthema)关于马六甲记载吸引了葡萄牙人的关注。
当像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这样的欧洲人首次来到这一地区之时,他们将欧洲人的邦国观念投射到东南亚的政治舞台之上,视马六甲为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控制着苏门答腊岛和马来亚半岛上的大片地区。渐渐地,欧洲人自己的文学想象扭曲了绝大多数东南亚地区邦国真正的起源和其内部的政治动态。海峡代表了“马六甲帝国”的脊梁。这片海域不仅没有分割,反而是连接并最终将这些虽然星罗棋布却又十分繁荣的邦国凝聚在一起,就像这个地区之前的历史中存在的三佛齐帝国一样。*参阅Borschberg/Krieger, Water and State.
1511年,葡萄牙人侵略并占领了这一商业中心,迫使苏丹流亡。马六甲转变为葡萄牙帝国亚洲领土中一个贸易节点,这片散布在广大区域中的一系列据点在原始资料中被称作印度公司(Estado da India)。
在16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在如此恶劣的周边环境之中,安全问题始终是该地区的首要关注对象。葡萄牙人在遏制红毛劳特(海人)、花阿鲁以及海峡周围其他劫掠性部落上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实际上还远不止如此。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东南亚海域,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17世纪以降,葡萄牙人愈发意识到马六甲以及与其相邻的新加坡海峡是一片极易遭受攻击的地区。
尽管葡萄牙人把马六甲设想为一个巨大的商易中心,他们的征服却引发了贸易中心的大规模更迭。伊斯兰商贸网络转移到苏门答腊和爪哇的港口,而福建的中国商人搬到帕塔尼(暹罗)。此外,马尼拉也成了中国人的重要贸易地点(白银)。
但是荷兰仍认为马六甲十分重要。他们对马六甲周期性封锁逐渐破坏了葡萄牙人控制的商业中心。1641年1月,马六甲城及其周围的一些土地划归荷兰,并一直保持到十八世纪末。*参阅Borschberg, The Singapore and Malacca Straits.
尽管为了在旷日持久的围攻之后支持经济复苏,荷兰人容忍了葡萄牙语和天主教,马六甲经济重要性却逐渐消失。
早在17世纪20年代,雅克·德·库尔特(Jacques de Coutre)为西班牙王室撰写了一份备忘录记忆,内容就是有关“在荷兰人到来之前发生在印度,特别是马六甲的商业活动”。[8](P221ff)
来自果阿(Goa)和其他地方的船舶过去常常带来不少马六甲没有的小麦、葡萄酒、橄榄油和黄油。还有四艘商船曾经常去中国和日本,另外两艘船过去经常自马鲁古群岛驶来,每年都满载着献给国王陛下的丁香,这是过去那些地方献给国王陛下的赋税。我提到的所有这些船以前每年都会来马六甲贸易,他们都曾经为国王陛下纳税。
葡萄牙人常常出售自己的纺织品,随后购买香料和其他商品。他们以前总是在船上装满货物并且航行到果阿和科钦;除了那两艘为国王陛下满载着来自马鲁古群岛的丁香的船只,其他所有的船会再次为国王陛下缴纳税金。除此之外,过去每年来还会有三四艘船从中国到果阿,满载着生丝和丝绸、天鹅绒、锦缎、绸缎;许多床罩、华盖、用来装饰房屋的华丽丝板;还有大量的麝香、晶粒珍珠、小珍珠;以及大量的黄金和樟脑*Ms. alcamfor.、菝葜(radix Chinae)、安息香、明矾,还有染色剂、中国瓷器、糖和其他商品。*China root taffeta=silktintinago=copper-zink-nickel alloymusk=excrements of musk deerbenzoin=raisincolchas=fine cottonalum stone, containing potassium[9](P224f)
1619年,当巴达维亚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之后,马六甲就只能退居二线了,其贸易被荷兰人监管。
在十九世纪和帝国主义的时代,马六甲城及马六甲海峡在功能和观念上历经另一个转型,转变的结果保存至今。这种新功能是创建帝国管理单位的结果:一方面是英属印度、海峡殖民地,以及后来的马来西亚;另一方面则是荷属东印度,以及之后的印度尼西亚。此外,近代中国把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在马六甲和南洋一带的活动视之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行为,对这一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多有支持。
1795年,英国接管马六甲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此的所有财产。新加坡的建立以及贸易在槟榔屿的集中,使得马六甲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很多旅行者都目睹了这一转变过程。但尽管如此,视觉再现和物质文化仍旧铭记着这段伟大的历史。
英国人查尔斯·戴斯(Charles Dyce)就是一位此类作品和绘画的见证人:
“除了近水岛屿,从新加坡到马六甲的这一段航道没有什么值得关注之处,这些小岛及几乎与城镇平行。它们很美,但是和像海峡其余的地方一样,上面也是一小片延伸至水边绿叶红树林。可是,从远处看马六甲城还不错,因为停靠的船只相互间至少间隔三四英里……。”[10](P110)
“快到岸边时,可以看到聚集在河流或是小海湾附近当地人和中国人的城镇。与海峡其他地方的相比,这些城镇更具大陆风格,而且你绝对不会弄错,荷兰人曾经是这里的主人。从马六甲城的一端到另一端,全都是泥泞的浅滩,离岸边足有一英里,任何吃水超过几英寸的船只都无法靠岸,除了在高潮位时,尝试穿过这里令人十分不快。然而小海湾倒是风景如画,可以补偿人们在烂泥地里跋涉时举步维艰的不快。码头处,市政厅和老教堂那古怪的钟形山墙以及荷兰式的外观令人眼前一亮,但除了这两座建筑和山上的修道院之外,城里没有什么可看的。”[10](P110)
“马六甲是出生在海峡地区的中国人的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这些人真的喜欢住在这里,领略这个‘世外桃源’的闲适和与家人在一切的美好生活。”[10](P111)
因此,若是能够研究(海峡地区的)中国人对马六甲的记忆和感知的话就更好了。
结语
即使大多数记忆和多数记忆场域是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所感知的,它们还是共享的。通过以上的案例,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将记忆场域概念延伸到海洋,尤其是航运频繁的地区可以为考察变迁过程和研究各种各样的感知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
尽管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厄勒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马六甲海峡在自然和地理上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们还是要重建它们的不同,以及它们在历史变迁中的角色转化。作为集体记忆和意识,历史本质上是人想象力的构建。它指导我们如何看待跨越时间的场所和事物,如何在当今的决策过程中运用我们对往事的感知与记忆。例如,目前中国政府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就是将21世纪的安全问题和中国几个世纪以来贸易与航海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此处,厄勒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达达尼尔海峡或马六甲也不例外。从多方面的可考证据和原始资料中可以看出,与海峡相关的命名问题没有太多疑问,但根据特定的文化背景,对其功能、角色和状态的感知则全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重大变化。对比当下的厄勒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可以展现感知进程的差异。“欧洲”的海峡同时也代表欧洲的边界,马六甲海峡则实际上既连接又划分了印度洋和中国南海(还有伴随着它的所有冲突)。同时,海峡一直是而且仍旧是人们相遇的一个重要地点,在历史中不停地变换着角色,给人以不同的感知。例如厄勒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已成为欧洲认同和融合的象征,但同时它们也代表着保护和分离。
记忆场域的概念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通过它我们可以在长时段语境内观察海洋。直到现在,记忆场域依旧保持着其惊人的创新性,因为在海洋史的研究中这种范式并未被广泛接受。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研究历史的范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的图画,与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建构截然不同。
通过国际比较的角度研究国家和区域的海洋历史是未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纠缠的海洋文化和分割记忆中的共享成分值得进一步地考察。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乐意将观察的视角延伸至整个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主要原因。我们也期待着与在这些领域中从事研究的同事们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1] Bernhard Klein and Gesa Mackenthun, "Introduction. The Sea is History," in: Bernhard Klein and Gesa Mackenthun, eds.,SeaChanges:HistoricizingtheOcean, New York 2004.
[2] Paul Gilroy,TheBlackAtlantic:ModernityandDouble-Consciousness, Cambridge 1993.
[3] Pierre Nora, "From lieux de mémoire to realms of memory," in: Pierre Nora and Lawrence D. Kritzman, eds.,RealmsofMemory:RethinkingtheFrenchPast.Vol. 1:ConflictsandDivisions, New York 1996.
[4] Étienne François, "Pierre Nora und die 《Lieux de m moire》," in: Pierre Nora, ed.,ErinnerungsorteFrankreichs, München 2005, 7-14.
[5] David Hohnen,Hamlet’sCastleHamlet'sCastleandShakespeare'sElsinore, Copenhagen 2000, 102-105.
[6] Ibn Battú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translated by H. A. R. Gibb, London 1983.
[7] James T. Shotwell and Francis Deák,TurkeyattheStraits.AShortHistory, New York 1971.
[8] BNE, Ms. 2780, fol. 268 recto-269 verso. Peter Borschberg, ed.,TheMemoirsandMemorialsofJacquesdeCoutre.Security,TradeandSocietyin16th-and17th-centurySoutheastAsia, Singapore 2014.
[9] Peter Borschberg, ed.,TheMemoirsandMemorialsofJacquesdeCoutre.Security,TradeandSocietyin16th-and17th-centurySoutheastAsia, Singapore 2014.
[10] Irene Lim, Sketches in the Straits. Nineteenth-Century watercolours and manuscript of Singapore, Malacca, Penang and Batavia by Charles Dyce, Singapore 2003.
责任编辑:高雪
The Sea as Realm of Memory
Michael NorthSun Lixin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Greifswald, Germany;2. College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a discussion paper handed in the round table section of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 held in Ji'nan from Aug. 23 to 29, 2015. Aiming at broadening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 sea as realm of memory (lieu de mémoire) into history. After taking a closer look at straits like the ?resund, the Gibraltar, the Dardanelles and the Malacca Straits as realms of memory (lieux de mémoire) that are full of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s emphasized that in order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nations, historical researchers should take as important research objects the shared memories of different nations, or more specifically, the divided memories (memoria divisa) of different nations.
Key words:sea; straits; realm of memory (lieu de mémo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6)01-0037-09
作者简介:米夏埃尔·诺特(1954-),男,德国吉森(Giessen)人,格拉夫斯瓦尔德大学哲学系历史学部教授,主要从事尼德兰史、波罗的海区域史以及货币和银行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10
译者:邢宽,顾年茂,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