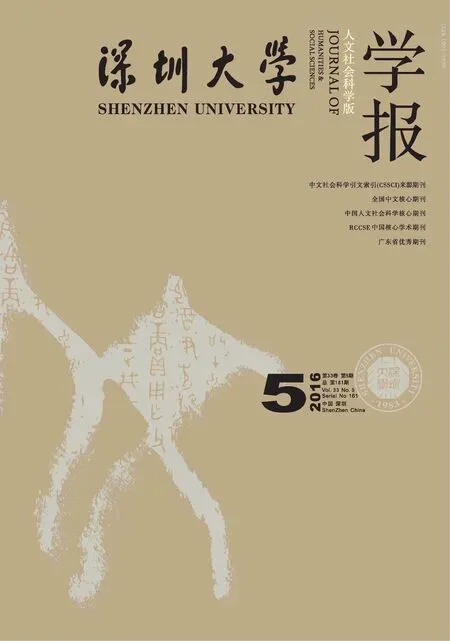周秦文学认知与“文学”的概念生成
曹胜高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周秦文学认知与“文学”的概念生成
曹胜高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孔门四科之“文学”,常被视为“文学”的概念形成。然详细考证,可知孔门所谓“文学”指的是礼学,即对文治之道、礼乐之法的概括。与之相关的“文章”一词,则指的是礼仪制度。荀子所提倡的“积文学”,强调人文化过程;墨子出于对礼乐的抵触,将“文学”限定为典籍、著述,却指向了后世“文章”的涵义。韩非子对“文学”的排斥,是出于对文学修饰性的清醒认知,而主动采取的行政策略。
周秦诸子;文学本义;文学认知;文学观念
中国文学的起点何在?这是讨论中国文学特质、功能和格调的原点。我们之前所进行的笼统描述,大而化之,是将原始歌谣与上古神话视为文学的滥觞;小而言之,是将孔门四科之“文学”视为文学概念的确立①。若仔细思考,孔子所谓的“文学”之“文”,本义为何?其何以与“德行”、“政事”、“言语”并列?《墨子》《管子》《韩非子》对“文学”有何歧见,如何区分?周秦语境中“文学”的义谓,又如何演生?并最终形成了“文学”这一概念?唯有详细辨析之,方才能确定“文学”概念的形成过程,由此审视文学认知的发生过程②,是如何决定了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本文试论之。
一、“文学”的概念生成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为孔门四科之一。皇侃疏引范宁云:“文学,谓善先王典文”[1](P146),言“文学”乃为《诗》《书》《礼》《乐》等文献。邢昺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2](P2498)钱穆《论语新解》进一步释为“孔子言诗书礼乐文章”[3](P277),稍有拓展,但仍将释义局限于文本。我们习惯以此解释,较少进一步辨析。既然德行、政事、言语是对孔门弟子才能的概括,那么对“文献”、“文章”的解释就不宜与之并列。一则《论语》中有“文献”一词,出自孔子之口:“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2](P2466)周秦独见于此,显然与文学有所分别。二则“文章”一词,《论语·泰伯》载孔子言:“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2](P2487)朱熹注曰:“文章,礼乐法度也。”[4](P207)这里的文章,显然指的是礼乐之事,与今日“作文”之意义无涉。孔门重名,文学、文献、文章等词汇同时出现,其义自然有别,不可随意替代。三则既然“文学”与德行、政事、言语并列,用于描述修辞、表达能力自然归于“言语”一门,而不必另立“辞章”之学。邢昺以“博学”释“学”,牵强不足辨,故钱穆不取。
孔门论文学,先子游而后子夏,则子游之学最能代表孔门“文学”之义。《论语》另载子游之事七,有问孝、论交、言友、论治、言礼、评人、论学诸条。其中与子夏辩论事,最能看出二者所持之不同: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2](P2532)
子游认为,子夏之学重洒扫应对等具体礼节,“特恐子夏之泥于器艺而忽于大道”[3](P490),即重视礼节而忽略礼义。子夏反唇相讥,言二者皆为君子之道,先学什么、后学什么本无区别。可见二者对礼的认识之分歧,表面看为孰先、孰后之问题,实则反映出二者在学术上的根本分歧。《论语·阳货》载子游随孔子至武城,孔子有“杀鸡焉用牛刀”之论,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2](P2524)孔子遂改口,以子游所言为准。子游论治,先言大道而后言行事,即先通礼义、后学礼节;子夏则主张先教行事而后大道,即先学礼节、后通于大道。故孔子曾告诫过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2](P2478)这可以看作是孔子对子夏之学过于注重琐事细节而忽略君子之道的委婉批评。
子游之学所侧重者,不在文章、文献,而在礼学③。《礼记·檀弓》载子游向孔子问古礼,又载其论礼之道,并举例言有若之丧,子游依古礼居左之事;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之别;司寇惠子之丧,子游服之以礼;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子游吊丧之别,引诸事以证明子游行为合乎礼之本义,而曾子、子夏等人皆看似依礼,实未得礼之宗旨,只是注重礼的外在形式。
《荀子·非十二子》批评子夏与子游的后学,也可以看出二者差异:“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5](P105)抛开荀子推崇子弓之学的门户之见[6](P16-21),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子夏之后学常拘泥于形式,稍显拘谨;子游之后学多通礼学,不重形式而多言君子之道如何,亦显浮泛。二者后学的弊端,实为二人学术旨趣的流波所及,与前文所言子游之学重礼义而不拘形式、子夏之学重形式而不善变通的特征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子游、子夏之学,分而言之为二者之别,合而言之为二者之同。后世之所以用“文献”、“文章”解释“文学”,在于子游之学寝息,子夏之学因文献传承而彰显。至《孟子·公孙丑上》中,便以“子夏、子游、子张”之次序,言其三人“皆有圣人之一体”;至《荀子·非十二子》的次序,则变为子张、子夏、子游。《论语》以子游、子夏排序论文学,显然更多地肯定子游的“文学”高于子夏。子夏长于文献文章,若子游亦以此为长,则不至于子游之文章皆付阙如。故孔门“文学”之本义,并非文章,乃指礼学。
“文”之本义,《说文》言为“错画也”,《释名·释言》言为“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此二义周秦典籍皆用之。《周易·系辞下》言:“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2](P90)《论语·颜渊》载子贡回答棘子成“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之问,答以“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2](P2503),以“外在文饰”为“文”之义。
虽然孔门亦用“文”之本义,然孔子论“文”,多从匡国理政的角度着眼。卫公孙朝曾问子贡“仲尼焉学?”子贡对答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2](P2532)在子贡看来,孔子无事不学、转益多师,意在继承周之文武之道。所谓文武之道,是文王、武王得以建立周朝的策略。《礼记·祭法》言:“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2](P1590)文武之道为周政之经验。《鲁颂·泮水》言:“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2](P611)其所谓“文”,与克定祸乱之“武”相对应,更多强调经天纬地之道,故孔子将文治视为周区别于夏商的标志性特征:“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P2467)自成王起,周行“偃武修文”之政,放弃武力威胁而以怀柔之德服民,孔子描述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2](P2520)故孔子所谓的“文”,是与“文德”相对应的“文治”之道,是与“行、忠、信”相并列的四教之一。
文德是以礼作为表现形式的。孔子曾言“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2](P2479),颜回也曾感慨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2](P2490),将“文”作为内在的修为,其外化则是“礼”。顾炎武解释“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7](P539)“文”就整体而言,是人之为人、人之能群的道德积淀、文明经验和制度形态的总称;就个体而言,是按照礼的宗旨自觉追求行为得体。孔子将之视为四教之首,在于其事难知,其义难明。《论语·学而》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P2458)先谨言慎行,明晰人之为人之根本;再爱众亲仁,知道人之能群的关键;然后才能有余力去学文,正在于“文”的内容的繁杂和意义的形上,孔子认为只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才是实现“文”的途径。
就有形之制度言之,孔子认为“文”表现为礼乐之事。《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事,孔子答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2](P2511)以礼乐为人之文。其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论中[2](P2479),“文”是经过人文化之后的文明形态和文化教养,而“质”则以原初形态面貌出现的本质存在。与“质”对举时,“文”是礼乐、制度等形态;与“礼”对举时,“文”则是带有义理、秩序、教化等意味的内在规定性。
礼学对“文”的解释,正是从形而上的人文本义和形而下的制度形态两个角度展开的。《礼记·礼器》言:“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2](P1430)礼之本义,在于确立人之为人的原则;礼之形态,在于明确人之能群的方式。故“礼”作为人之“文”,是对人行为的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被固定下来,便作为基本的秩序,成为礼制。《礼记·仲尼燕居》言:“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2](P1614)人人遵守,便成为被视为社会规范的“礼”。
礼的规范是采用节、文两种方式进行的:“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2](P1618)节即节制,文即附益。《礼记·檀弓下》:“辟踊,哀之至也。有筭,为之节文也。”[2](P1301)孔颖达疏言:“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极也,若不裁限,恐伤其性,故辟踊有筭为准节、文章。”[2](P1301)即通过制定规则,使得哀伤有节制,不至于毁伤身体;又有一定的仪式感,使情感表达更合理。这种做法,从制礼的角度来说,是“称情而立文”:“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2](P1663)儒家解释“三年之丧”,强调服丧期间的陋居简食,是用来表达丧痛之情的形式。礼之“文”,正是由礼的仪式、形制、器物等所组成的外在形式。这些带有约束、区别、规定意味的形式,正是礼的重要标志。《礼记·礼器》言:“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2](P1433)其中的“文”,不仅是文饰,更是形式化的制度,这些制度正是基于社会秩序、道德认知和人类文明而形成的行为方式。
这些基于理念而形成的礼,是可以内化为个人修为,并在人际关系得以体现。《礼记·表记》言:“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2](P1640)君子不仅要懂礼服、礼容、礼言,更要能够对“礼”进行义理上的解释和制度上的修订。由此来看,这些关于“礼”的学问,便是制度意义上的“文学”;而支配“礼”的那些人文观念,便是理念上的“文学”。
所以说,孔门所言之“文学”,是比文献、文章更为形而上的概念,其源自周立国而形成的文德之治,体现为人文化成之道,表现为礼乐形态。孔门将子游列为“文学”第一,与子夏长于文献相比,在于子游更精通礼义、熟悉礼仪、明晓礼制、掌握礼度[8](P5-13),是孔门中最为精通礼学者。由此可见,《论语》中所谓的“文学”,乃指以制度为形态、以文化为指向的礼学。
二、周秦“文章”概念的展开
周秦礼学所言“文章”一词,绝少“作文”一义,其本指礼器之花纹。《周礼·考工记》解释其本义:“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2](P918)后渐指色彩斑斓、花纹纵横,如屈原《橘颂》言:“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9](P154)以“文章”形容物品之华美。
周礼对黼、黻、文、章等花纹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礼记·月令》载季夏之月,“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2](P1371)。将丝织品染成不同的颜色,制作祭祀的服装、旗帜。这些不同的花纹体现着贵贱等级,《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周之“别贵贱等级之度”:
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2](P1742)周制中等级的区别,一是服形有别,二是数量有差,三是图案不同,四是用具有异。在这其中,火龙黼黻的图案和五色比象的颜色,是用以区别尊卑贵贱的重要标识,是“文物以纪之”的体现[2](P1301)。在周之分封制度中,图案和色彩被作为封赏的符号,成为级别的象征。《左传·隐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杜预注“文章”为“车服旌旗”[2](P1727),车制、服制、彩饰、旗帜,是古今区别高低贵贱的最外在的符号,后渐以指代礼制中尊卑贵贱的安排。
《礼记·大传》言:“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郑玄注:“文章,礼法也。”[2](P1506)周秦所谓“文章”,本出于花纹图案,进而指礼乐制度,如《韩非子·解老》言:“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中心怀而不谕,故疾趋卑拜而明之。实心爱而不知,故好言繁辞以信之。”[10](P132)认为礼是对社会关系的形式化设计,是区别尊卑贵贱的基本手段。在这其中,最精通文章之义的便是儒生。《礼记·儒行》以此自砺:“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2](P1671)认为儒生修身养性,精通礼乐制度,以担负文化传承为己任,以人格养成为诉求,并不求荣达富贵,仍以“近文章”作为学问之本。由此可知,孔门“文学”之本义,本谓礼学;而儒门所言“文章”,乃指礼乐制度。
至荀子,则将学礼视为君子的基本人文修为,其提倡的“文学”,是指以礼学为基础而进行的人文化教育,他将之称为“积文学”、“被文学”。《荀子·王制》言为政之事,提出贤能与庶人的区别,不在贵贱,而在是否能正身:“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5](P148-149)礼义是对礼的本质性的要求,在荀子看来,贵族子弟如果行为处事不合乎礼的规定,可以黜为庶人;而庶人如果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则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修身养性,合乎礼的要求,则可以直接提拔为官员。这个“积文学”的过程,便是以礼乐精神来熏染心性,使之合乎君子的标准。《荀子·大略》言: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5](P508)
荀子论人以德,论治以礼,希望通过约束人性之恶来修养君子之风。荀子举例来说,子贡、子路因为在孔子处受到了礼乐教化,能够按照礼义行事,才从普通民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士大夫。值得注意的是,荀子以长于言语的子贡、长于政事的子路为例来言“被文学”,便是强调二人接受教化而提升了人文修为。礼乐,既可以从内让人洗心,又可以从外让人革面,内外兼修,庶人可以成为贤君子。故荀子所论之“积文学”,乃是担负礼乐教化职能的人文化的全部实践:
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5](P435)
荀子以性恶论人,其能够化善,在于起伪。伪,即后天修为对人性之恶的约束、抑制。积文学(被文学)、道礼义,是对纵性情、安恣孳行为的约束。在荀子看来,君子与小人在原初人性上是一致的,差别在于君子能够通过后天修为改变自己的性情,逐渐弃恶向善。在这其中,正是用礼乐制度这一人文化的手段来改变人之恶。所谓的“化师法”,乃是对儒学的继承;而“积文学”,则是对礼乐制度的熟悉和践行,使言谈举止、心性修为合乎礼的规定。
如果说孔子眼中的“文学”是指礼学,那么荀子眼中的“文学”,则具有了“人文之学”的含义。他将礼仪制度的概念界定与礼乐教化的功能特征结合起来讨论,强化“文学”对个体修为的作用,从而使得“文学”由一项专门的技能,转而成为人人必须接受的人文教养。在这其中,荀子强化了文学与“质”相对的“修饰”要素,认为以礼乐为形式的文,正是通过形式要求,来体现质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学说继续沿袭文学为礼学,并在这一路径上继续深入讨论的同时,其他学说对文学概念的理解,则越来越具象化。墨家学派在节用、节葬、非乐的视角下,对形式化的礼乐有着天生的厌恶,因而其所论的文学,便抛弃了“礼乐”的含义。我们知道,在孔门“文学”之中,子游长于礼、而子夏长于经。当“礼”被边缘化之后,墨家对“文”的理解,便只是经典的存在,而不是经典中蕴涵的学说。《墨子·天志中》言:“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11](P307)在这其中,墨家将“文学”和“言谈”并列,对举而义别:言谈是平民化的言语,言语是逻辑化的言谈。孔门中言语和文学的区别,在于言语谓应对,而文学谓礼学。墨子眼中的二者之别,在于文学是严谨的表达,可以落实到纸面上;而言谈是相对自由的说法,其应该按照经典的做法确立逻辑法则。《墨子·非命中》载子墨子言曰:
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政。此言之三法也。[11](P413)
其所谓的言谈,是说法、论点、观念。在墨子看来,要想把观点表述清楚,就要按照文学(即经典)的传统和要求,先确立立言的义法(即规则)。这一规则是墨子表述观点的基本要求,他因之而提出的三表法,便是从本之、原之、用之的角度对言谈的逻辑形态进行思考。墨子将“文学”与言谈对举,与孔门四科似相呼应,但意义却已有差异。但他认为言谈应按照文学的传统、原则和方式才能确立,显然是认为以经典为标尺的“文学”的要求,其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言谈。
墨子的看法代表了儒门之外学者对“文学”的理解,文学遂被赋予了今之所谓“文章”的含义。《吕氏春秋·荡兵》也进一步将说、谈、文学分立:“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12](P161)是说那些期望偃兵之人,有说辞、能辩论、引经据典广博,但并不能说服君王们休兵。作为与说、谈相并列的“文学”,指的是引经据典的文章。由此可见,儒家所提出的“文学”、“文章”,是从文治之道、文学之法的立意上审视,更多徘徊在礼学、礼乐制度、礼乐教化等本质含义之中,并未展开。反倒是厌弃儒家礼乐繁文缛节的墨家,出于立论的需要,将“文学”的概念转移到“先王典籍”的义项上,并通过三表法的阐释,进一步将“文学”转入“文章创作”的义项上,使之成为与后世“文学”概念同向的表述。
三、法家的文学认知及其学术取向
孔子所提出的“文质彬彬”理想,即便在儒家学说内部,也并没有得以实现。就个人修为而言,孟子以性善为质,荀子以性恶为质。荀子试图通过礼乐教化,以文修质。但这一做法的悖论在于,荀子强化礼的形式,不仅没能使之成为外在的约束,反倒成为可被模仿、可被复制的形式,其极端便是有文而无质、或重文而轻质的形式主义。其弟子韩非,便看到了“文”的形式化,并不必然带来正面的效果,转而开始否定“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
韩非子对文的形式化的反感,一在于礼学文饰太过,二在于文章修饰过甚。有意思的是,他对文学的反感,不是出于不懂文质关系的武断,而是在于洞察文质差别之后的理性选择。《韩非子·难言》从文章写作的角度比较了文与质的差异: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厚恭祗,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拙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摠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僭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10](P20-21)
孔子主张文质并重,只是原则性的阐述。落实到文章中,文与质如何体现,韩非子进行了区分,他将“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的语言、“多言繁称,连类比物”的技巧、“闳大广博,妙远不测”的想象、“言而远俗,诡躁人间”的手法视为“文”。若按照时人的习惯,文章应该注重形式而多用修辞,但这样做,容易被视为华而不实。而“敦厚恭祗,鲠固慎完”、“摠微说约,径省而不饰”、“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家计小谈,以具数言”、“言而近世,辞不悖逆”等特征则被视为“质”。在韩非子看来,若不用文饰,直陈己意,则容易被视为简陋。这样来看,理想中的文质彬彬,别说落实在社会风气中,就是落实到文章中,也难以兼顾。
韩非子在文与质的对举中,看到了文的特质,在于通过修饰而形成形式美,可以纠补质之木讷与粗野。若站在行政的角度,文学之巧文,长于议论、善于论辩,常以虚辞游说,误导君主、吸引百姓,与国无益,与实相左,故韩非子认为应该加以禁止。他认为国有八奸,其六为“流行”,即能蛊惑民众的歪理邪说、流言蜚语:“人主者,固壅其言谈,希于听论议,易移以辩说。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此之谓流行。”[10](P53)其所谓的“巧文之言”,既指修饰之辞,更指充满说服力的非议朝政之言。从富国强兵的实用角度,禁文巧是治国者通用的策略。《管子·治国》曾言:“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13](P924)文巧之末禁则民重农耕之本。《管子·牧民》又言:“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13](P2)认为文巧过甚,于生产则耗民财力,于朝政则浮言虚辞,无益于治。
有意思的是,在韩非子的论述中,“文学”不再被视为文化技能或学说形态,而被作为某一类人的概括。《韩非子·六反》认为“奸伪无益之民六”,其中将“学道立方,离法之民”称之为“文学之士”[10](P415)。学道,即继承古之传统;立方,即注重礼仪。在韩非子看来,文学以修身为用、博学为识,坐而论道,率民不事生产,与农战立国之论极不相符,故这类人应该严加禁止。《韩非子·说四》举例说王登为中牟令,向襄主推荐“其身甚修,其学甚博”的中章、胥己,结果襄主任用为晋之要职的中大夫,并赐以田宅,导致“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10](P280)。韩非子认为这正是尊文学的结果:平时空论者多,而生产者少。这些“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礼之则惰修耕战之功,不礼则周主上之法;国安则尊显,危则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于居学之士哉?”[10](P264)久而久之,百姓便会弃武从文,而无法强国。
韩非子最为担心的是,学士们“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10](P459),他们精通古学,能以今例古,常以旧章议论朝政,很容易削弱君主的专断之力,对于确立“言无二贵,法不两适”的帝制,危害甚大:“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10](P394)没有实用功能的议论就是胡扯,削弱君主权威的议论就是非议,文学采用坐而论道、师徒相传的方式,很容易形成私议,在君主专断之外另有舆论导向,不仅会削弱政权的威严,而且会扰乱民心:“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10](P450)出于政令一统的需要,韩非子认为国家所推崇的,便应该是民众所尊崇的;国家所厌弃的,便应该人人喊打。文学修身养德,自立其说,容易形成一种独立于朝廷之外的社会风尚、舆论导向,因而不应该加以尊崇,相反应该进行约束。所以他开出的药方是:
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10](P425)
我们习惯说墨子反对文采、管子反对文巧、韩非子反对文学,似乎他们不解文学的风情之美。其实韩非子比荀子更为清晰地理解了文学的特质在于巧饰,对文学之士的“学道立方”的特点也了然于心,因而他才对文学进行坚决的抵触。之所以坚决,是因为韩非子能够意识到文学具有源自先王典籍的厚重、出自坐而论道的超然、拥有内外兼修的德行,很容易形成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势力,容易与君主专制分庭抗礼,是摧毁君主专制的利器。
战国后期诸子对文学特质的明确,使得“文学”走出了礼学的局限,转而广泛被用于描述精通“文学修辞”进行著述的人。司马迁言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14](P1895)。其中所列之人,皆非出于儒家,可见其眼中的“文学”,实乃能文之人。《史记·蒙恬列传》又言:“恬尝书狱典文学。”司马贞《索隐》:“谓恬尝学狱法,遂作狱官文学。”[14](P2565)言蒙恬初为负责以文书记录案件的狱官,“文学”乃负责记录、制作文书的小吏。这样,“文学”不再局限于礼学、礼制的范畴,不再专指代“经典”,开始有了“文章”、“文章之士”的含义。
“文学”在秦的际遇,从实践印证了韩非子对文学之士的非议,绝非莫须有之辞。秦一六国时,并未废弃文学,用秦始皇的话来说,自己“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14](P258),可见秦始皇最初并未拒纳文学之士。叔孙通便“以文学征,待诏博士”[14](P2720),但侯生、卢生却在背后非议秦之杀伐过重,以致相约逃亡。秦始皇处罚的理由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言其以古非今,以义非治。秦始皇要坑杀文学之时,扶苏劝谏时便承认“诸生皆诵法孔子”[14](P258),这些说法验证了韩非子“儒以文乱禁”的预判。
以此为鉴,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因封建、郡县之争,淳于越非议周青臣,李斯继续对文学的判断,同于韩非,其认为“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强调出于天下一统、权力一尊的需要,民间必须禁绝“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的“私学”[14](P255),以确立国家行政系统对学术的主导权,民间不得私相传授学术,以吏为师而绝师道,以国为用而断家法。随着秦挟书令的颁行,在民间层面中断了《诗》、《书》和诸子之学的传播,以致秦之吏民多不习文学,造成了文学传统的暂时中断。而秦之百姓对文学亦乏理解,以致汉初君臣质木少文,如汉高祖“不修文学”[15](P80),周勃“不好文学”[15](P2071),灌夫也“不好文学,喜任侠”[15](P2384),从而使得西汉之文学必赖百年之培育,才能从“秦无文”的荒芜中成长起来。
注:
①参见袁行霈师:《中国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30、76-79页;《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38页。
②我们采用“文学认知”(literature cognition)一词描述周秦时人对文学的理解,是基于认知最本原的概念,即通过概念形成、知觉、判断和想象等心理活动,对文学进行理解和认识,这中间当然包括对文学的感觉、对文学的理解、文学记忆和文学思维等过程。这并非是从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微观角度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而是侧重描述周秦学者如何理解“文”的概念,并对之进一步深化,形成接近于后世的“文学”概念。
③《礼记·礼运》一文,康有为、郭沫若皆认为出自子游之手。参见康有为:《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1](南朝·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宋)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林桂榛.大儒子弓身份与学说考:兼议儒家弓荀学派天道论之真相[J].齐鲁学刊,2011,(6).
[7](明)顾炎武撰.(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曹胜高.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4).
[9](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向博】
Literature Cognitive and Concept Formation of“Literature”in Zhou-Qin Dynasty
CAO Sheng-gao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anxi Xi'an,710119)
The“literature”of four subjects in Confucius(孔门),is often seen as concept formation of“Literature”.However,through the detailedtextual research,we can knowthis“literary”in Confucius is the theory of rites,which is the summary of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rites and music education.But the related word“paper”refers toetiquette system.Tsunzi(荀子)advocated“gradually accumulation literature knowledge”(“积文学”),which emphasized the process of humanized tendency.Mo-zi(墨子)collided rites and music,and the“literature”was limited to document or writings,pointed the meaning of“paper”in later ages.Han Fei-zi(韩非子)rejected“literature”,which i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n the modification of literature,and positive takeadministrative strategy.
the philosophersin Zhou-Qin dynasty;original meaning of“literature”;literature cognitive;literary concept
I 206.09
A
1000-260X(2016)05-0113-07
2016-03-07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2-0821);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国家建构与两汉文学格局的形成”(12YJC751005)
曹胜高,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