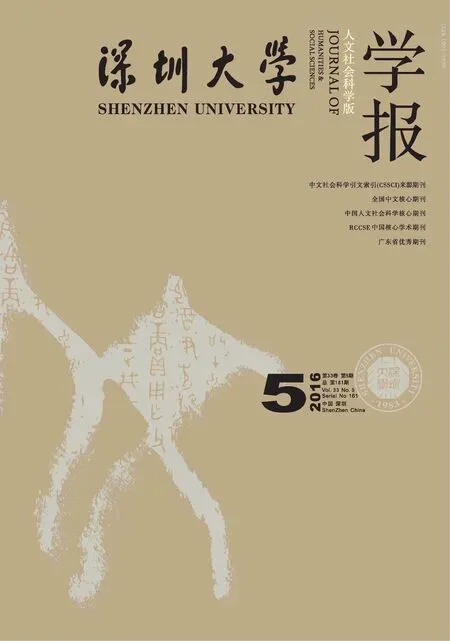翻译学发展背景之下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
辛广勤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翻译学发展背景之下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
辛广勤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与翻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翻译学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过程中,既引发了翻译研究伦理转向的萌动,也限制了其转向的真正实现。翻译伦理作为翻译的固有属性,关注翻译所涉各方的利害得失,如翻译中所涉静态客体如文本、语言和文化,以及动态主体如个体、群体与国家等的得失。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处在萌动进行之中,远未完成,应以对上述翻译所涉各方的减害增利为目标,努力推动。
伦理转向;翻译学;翻译研究;翻译伦理
在翻译学界,一般认为,自霍姆斯(James Holmes)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著名文章《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开始,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自那时至今已有四十余载。国内,如从改革开放算起,众多译界学人如谭载喜等大力倡导建立翻译学至今,也已三十多年。如王大智所言,人们已基本接受翻译学“两个转向”与“三个阶段”的划分[2],即“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语文学研究阶段”、“现代语言学阶段”与“文化学阶段”。但其它如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国际转向”、“技术转向”、“伦理转向”等则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作为一项古老的人类实践活动,任何翻译必然影响有关各方的利害得失,即伦理问题。如此重要问题,国内外的既有成果却各执一词,既有认为翻译研究正在发生伦理转向的,如戈达尔(Barbara Godard)[3]、许宏[4]和王大智[2](P19),也有认为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尚未正式开始”的,如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5](P77),还有学者认为,翻译研究的伦理途径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仍是一笔糊涂账,如英格莱莉(Moira Inghilleri)[6]。那么情况到底如何,翻译学历经四十余载的发展,是否存在伦理转向?如果存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伦理转向?真的转向抑或只是转向的萌动?如果转向未成,是否需要推动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在翻译研究中又当如何定位?本文将从翻译学发展背景之下讨论并回答这些问题。
一、翻译学的发展
翻译活动与持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交往、思想文化传播等密切相关。伴随翻译实践的是对翻译的思考。如果称作研究,迄今为止,中西方的翻译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7](P2)。除了文艺作品的翻译,早期中西大规模的翻译活动都与宗教典籍有关。后来翻译内容逐步涵盖人类所有具备传播与共享价值的成果,如科学、哲学、技术等。但西方翻译研究真正进入理论层面可以说是从1953年开始[7](P8)。据翻译学创立者之一的霍姆斯,1953年以前,西方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前所有对翻译的探讨都停留在“怎么译”的个人经验层面[8]。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一批学者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讨论翻译问题,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理论、弗斯(John Firth)的语境功能理论等,从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等角度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与方法。其中著名的包括雅克布逊(Roman Jakobson)、尤金·奈达(Eugene Nida)等。1959年雅克布逊发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从符号学角度理解翻译,并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分法: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到了20世纪60年代,卡特福德(John Catford)、奈达等人进一步从语音、语法、语义等值等问题入手深入讨论翻译行为本身的问题,即重点关注微观的翻译过程。这些系统的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就是前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也发生在20世纪人文社科的其它领域。而语言学系统研究之前的翻译研究主要是语文学或文艺学的途径,关注的是个人经验层面的“怎么译”问题,如关于“直译”还是“意译”的讨论,“可译”还是“不可译”的争论等。
霍姆斯1972年文章标志着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成立。此后的70、80年代,一批比较文学出身的学者不再关注翻译文本本身,而开始关注翻译发生的环境及译者的主体作用,把翻译视作动态体系,在更加宏观的层面讨论翻译的结果、功能等。霍姆斯之外,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弗米尔(Hans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译学都在这段时期登场亮相。上述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图里在其1980年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及其1995年改进版《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中提出的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DTS)。图里在DTS中给翻译下了最宽泛的定义“译入语文化中的事实”[9],不规定如何翻译,只描写已有翻译,描写一定时空范围内,如某个民族或国家历史上出现的翻译作品,试图找出翻译发生背后的规律。其核心词是“翻译规范”(norms)。DTS及“规范”概念对其后的翻译研究,包括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以及现在国内研究成果丰硕的语料库翻译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后西方译学界又引入了“模因”(memes)概念[10]。“规范”与“模因”概念实质上直接引向了“关键的伦理问题”[5](P164)。而这些新的研究路径与前述的语言学微观研究途径已大相径庭。
在此进程中,1990年,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主编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出版。他们在共同撰写的引言中宣称翻译研究正经历着该文集中斯内尔-霍恩比所倡导的‘文化转向’[11]。即翻译单位或翻译的研究单位不应是词句甚至篇章,而应是文化。这批主要来自以色列、荷兰、比利时的学者研究发现,除了原文,译入语文化语境与历史时期对翻译的产生、接受、流通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前文提及的两大转向之二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历时久远影响巨大。伴随着文化转向之后的西方翻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近乎达到高潮,成果甚为丰富。后殖民途径阐明翻译在帝国殖民与文化侵略中的帮凶作用等;以及反过来,翻译也同样可以起到抗殖、解殖的作用等。简言之,后殖民翻译途径揭示和强调了翻译中所涉及的语言文化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及其影响。女性主义途径的翻译研究则发掘女性译者的历史作用、翻译对女性弱势地位的强化作用、以及女性主义翻译家试图打破翻译中所涉的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主张尊重女性差异等。后现代主义尤其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对翻译研究的介入引发了翻译研究的解构主义阶段。解构主义视角侧重原文文本意义的开放性、流动性以及读者/译者的阐释空间,这为译者自主性的彰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对译者可以“为所欲为”的担心。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与文化、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政治及权力的关系得到了详实的探讨。
当历史进入21世纪,翻译学在理论上除了叙事学被引入翻译而增加了对翻译现象新的认识维度以外[12],更多的是社会学视角研究的增加[13]。尤其是随着口译研究,如社区口译、法庭口译的迅猛发展,翻译与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探究,翻译与时代冲突或战争的关系等都进入了西方翻译学者的研究视野。翻译伦理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以上所述因篇幅限制只是简略勾勒了翻译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国内翻译研究经过这么多年的追赶,在很多方面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而这其中,中西翻译研究中的翻译伦理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是否发生了所谓的伦理转向?朱志瑜在其2009年文章中曾归纳翻译研究的历程,即翻译研究经历着从规定到描写,再到伦理的过程,试图说清楚他眼中的翻译伦理[14]。从翻译学的整个发展历程看,描写翻译学对翻译学学科的真正建立功不可没。朱志瑜对描写翻译研究的任务说得很清楚:“发现翻译的规律,包括翻译过程、产品、影响、效果等等。”[14]语料库翻译学主要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他同时指出,“仅仅描写是不够的。翻译理论必须面对伦理问题”[14],因为“失去价值意识很危险,描写研究不谈价值,或没有能力谈价值,不等于价值问题不存在。”[14]也就是说,翻译伦理问题不论谈不谈都是客观存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翻译研究中是否出现了伦理转向。
二、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
翻译伦理研究与翻译研究或翻译学的发展轨迹有直接联系。首次明确提出翻译研究伦理转向的是加拿大著名女性主义翻译家和理论家芭芭拉·戈达尔。她认为翻译研究从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Antoine Berman)1984年正式提出“翻译伦理”概念开始,在发生着缓慢的伦理转向。戈达尔提出此说的时间是2001年。而同年,澳洲翻译学者皮姆(Anthony Pym)在国际著名翻译学刊《译者》特刊“回归翻译伦理”的引文中开宗明义高调宣布,翻译研究已回归到对伦理问题的讨论。皮姆观察,西方译学因20世纪80、90年代描述译学的兴起,强调科学精神、价值无涉,因此伦理成了不受欢迎的词(“an unhappy word”)[15]。近年国内亦有学者认为翻译研究经历着伦理转向,即前述许宏和王大智等,在其专著中专节讨论。许宏认为翻译研究存在伦理转向,并总结了三个方面的动因:人文社科领域出现了伦理转向、翻译研究本身的发展、全球化时代规范翻译活动的需要等[4](P69-90)。王大智把其专著第一章即命名为“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2](P19-57)。她分三节讨论。第一节主要讨论贝尔曼“尊重他异性”的翻译伦理思想,并认为贝氏所发起的是翻译研究伦理转向的萌动。第二节,讨论作为“翻译政治的翻译伦理”,包含美国当代译学领军人物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倡导的所谓“存异”伦理和“因地制宜”伦理、加拿大女性主义译者所代表的“彰显女性差异”的翻译伦理和以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为代表的“保留第三世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伦理(引号原文作者加)。这一节可以概括为“尊重差异”的翻译伦理,与贝尔曼虽有不同但有明显的承续关系。第三节,王大智讨论功能主义的翻译伦理,首先是德国功能学派“功能”加“忠诚”的翻译伦理,以诺德(Christiane Nord)为代表,然后是皮姆的所谓“译者伦理”①。两位学者的讨论能证明翻译研究真的出现了伦理转向吗?对翻译中的伦理问题进行研究,是回归,还是转向?何谓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真的发生了吗?
这就需从贝尔曼讲起。1984年,法国当代著名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在巴黎国际哲学院发表讲座,首次正式提出“翻译伦理”概念,针对西方翻译传统中盛行的“我族中心主义”翻译实践展开批判,提出要尊重“异文化中的他异性”的理念(其著作1992年译为英文出版)[16](P4)。但如前述皮姆所言,当时描述译学和改写理论大热,研究重点是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翻译成果,译界学人都不认为伦理问题是翻译研究的核心或关键。这样,可以说,翻译伦理研究自贝尔曼开始的是转向的萌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转向。上文王大智的判断正确。十年后,即1994年,皮姆受贝尔曼启发但不满贝尔曼翻译伦理排斥靠翻译生存的职业译者,在同样地方发表演讲,提出针对大量职业译者的“译者伦理”,强调翻译是为了交换和翻译的社会经济性,认为贝尔曼的伦理思想过于偏狭与抽象。皮姆文稿1997年以法文发表,影响不彰。多年后由人翻成英语,皮姆本人修改补充于2012年再版[17]。其立场有变,主要是因为技术革新后的翻译情势促使皮姆加进了所有可能做翻译的人,而非像十多年前仅限职业译者,即他的伦理模式已不再以所谓的职业译者为对象,而是任何可能从事称作翻译的活动的人。但其核心观点,即译者处在跨文化空间、翻译是为了长期的跨文化合作则未变。但译者的所谓跨文化性和他几乎把所有翻译都视作交换也是他的主要问题所在。
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1997年预言“翻译研究的下一阶段将以伦理主题为特征”[10](P48)。韦努蒂1998年出版其引发争议的专著《翻译的窘境:翻译差异伦理探索》,阐发他的翻译“差异伦理”[18]。韦努蒂的问题已遭译学界的大力批判,核心问题是他所谓的“差异”并非异语和异文化之异,而是他所强调的由译者努力,经过“异化翻译策略”的使用,而对译入语文化所造成的差异,即改变或改造译入语文化及其中的各种建制,使之变异,而非他在作品引言里所宣扬的伦理立场:“带着对语言文化差异更大的尊重完成翻译、阅读翻译和评估翻译”[18](P6)。他立论所据主要是英美国家的文学翻译情况,因其单向度的适用性而不具伦理规则所应有的普适性,引人挞伐与批判。2000年,芬兰学者考斯基南(Kaisa Koskinen)出版其博士论文《超越模棱两可:后现代性与翻译伦理》,提出后现代的翻译伦理观[19],即翻译伦理最终是要落实到由译者自定,延续的是后现代尤其解构主义倡导的不确定性统治一切的立场,她批判的是皮姆和韦努蒂的翻译伦理,但结果是顺带也否定了自己。所以,斯内尔-霍恩比2006年断言,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尚未真正开始,因为转向意味着范式的转变(“new paradigm”)。而上述贝尔曼、皮姆、切斯特曼和韦努蒂各是其是,互非其非,远说不上有共同的范式和目标。斯内尔-霍恩比同时指出,翻译伦理的研究远未穷尽,亟待深入系统的研究[5](P164,172)。
这样,翻译研究伦理转向之说并未得到译界和译学界的认可。那么翻译研究需要伦理转向吗?翻译研究的伦理途径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三、翻译研究需要伦理转向
翻译伦理研究在西方经过了皮姆、切斯特曼、韦努蒂和考斯基南的关注后,到本世纪初的喧嚣后稍显停滞,但随后很快在2004年以后就引发了更大的关注[20]。如蒙娜·贝克(Mona Baker)、英格莱莉和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等都从译者的伦理能动性角度进一步探讨翻译伦理。国内自2005年以来对翻译伦理的关注可以说持续升温,甚为热闹,似乎可用转向来形容。2014年2月17日笔者以“翻译伦理”为主题词在中国期刊网搜索,共得429条结果。其中竟然有13篇是直接和翻译伦理相关的博士论文(还有2篇未收录)。这些论文有的已改成专著出版。给人的印象是翻译伦理研究已经过热,热得似乎到了令人反感的程度,因据申连云博士论文,传有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放言会随时毙掉翻译伦理一类的申请[21]。但实情又是如何呢?翻译伦理真的已经没有研究的必要甚至问题终结了吗?
实际上,通览发现,上述著作有的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伦理研究,而更适合归为描述性的社会学研究。而且,除了上述王、许明确提出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后不再见类似提法。诸多研究明显存在伦理概念混淆不分、翻译伦理界定不清或缺乏界定的问题。翻译学者对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似乎像对翻译学这门学科一样,心存犹豫。戈达尔所称的翻译伦理转向语焉不详,而许宏和王大智所述,也仅限于概述西方学者就翻译伦理或所谓的“翻译伦理”的讨论,而“翻译伦理终结论”不是出于无知,就可能是出于权力的傲慢。因为翻译伦理与翻译一样,是翻译的固有属性,只要翻译存在,翻译伦理就会存在。好在近期国内已有清醒的学者呼吁,“翻译伦理问题亟待译学界更为深切的关注、更为系统的研究”[22]。上文提到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蒙娜·贝克教授,乃当今国际译坛领军学者,在她为2014黑井版《翻译学伴读》所著首文“变化中的翻译与口译研究景貌”中预测,伦理思考与研究在翻译学科的未来发展中将会占据更加中心的位置[20](P23)。
翻译伦理研究按照贝尔曼的设想本来处于翻译研究的核心位置,另外两个关键是翻译史和翻译分析[16](P5-6)。那么到底何谓翻译伦理?在翻译研究中应该如何定位?按笔者意见,翻译学宏观上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翻译科学,探索翻译所涉及的真理问题,如翻译普遍规则、翻译本质属性等;翻译伦理学,针对翻译之用及译者和其他可能参与者之为,主要是善的行动与价值问题;翻译诗学或美学,讨论翻译中的语言美等问题。翻译伦理研究完全应成为与翻译社会学结合的一个新的方向,并值得长期研究。
翻译学走过了语文学阶段、语言学阶段、文化学阶段。虽然这种阶段的划分已被接受,但事实是,翻译作为涉及文本、语言、文化、个体、群体、民族国家、权力、性别、意识形态的复杂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密切关系,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都与翻译相关,翻译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也可以是殖民与冲突的帮凶。翻译绝非单纯的语言转换已成为译学界的共识与常识。翻译所涉语言、文化、社会等很难截然分开。翻译与语言一样,既可助人,亦可杀人,端赖任何翻译项目所涉翻译个体或群体以什么立场行事,以什么为参照点,既可以仅顾及自己所属社群、种族、阶层的利益,也可以从更大的关注对象出发,如文明对话、天下或人类的立场从事翻译活动。任何翻译都可能涉及到翻译所涉有关各方的利害得失。翻译伦理除了需要进一步讨论翻译中可能涉及的不同主体外,还需针对不同原文本的类型与质量、目的文本的不同要求和不同读者对象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减少甚至消除可能的伤害,增加双方或多方的可能益处。这样,翻译伦理实质是研究被接受为翻译之物的翻译对所涉相关静态因素如文本、语言与文化和动态主体如个体、集体及民族国家所造成的伤害,并研究如何减少甚至彻底消除可能的伤害,同时增加上述各方的相互益处,属于文本伦理和一般伦理的结合。
如果进一步从单一翻译项目出发,翻译伦理则更容易看清楚。任何翻译项目都会涉及待译文本、各类不同译者和其他可能的参与者、以及该翻译项目发生的语境。而待译文本有不同类型、不同质量,可能有明确作者或著作权拥有者,也可能是集体创作无明确作者的实用类文本。同时,不同客户可能对翻译有不同的需求,如只需摘要或梗概,不需非常严格意义上的准确翻译等。文学(经典)文本,可能涉及大量的美学元素,比如节奏、音韵、意象等,对译者的要求就会非常之高。而哲学性或思想内涵丰富类文本,即便是对很多专业译者,也可能构成极大挑战。在这些情况下,皆需译者有清晰的自我认识、反省意识,拒绝翻译或及时停止翻译以免造成对作者和读者的双重伤害。
同时,只有翻译伦理才能融合各种翻译研究视角或途径,面对翻译所涉及的文本、语境和社会脉络,翻译主体、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译前、译中、译后所涉问题,回答译不译、为何译、为谁译、译什么、怎么译的问题。真正的翻译伦理应该既可以指导伦理判断,又可以进行伦理评估,还可以对翻译所涉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解释。
袁筱一在讨论翻译批评时指出,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翻译研究在(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翻译史、翻译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但翻译批评却相对薄弱,而翻译批评的依归是翻译伦理,翻译伦理需要依托翻译事件,翻译事件是需要构建的[23],所以翻译伦理同样需要构建,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则需要译学界的持续推动,直到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之一,形成范式转变,即真正的转向,而非仅限于个别学人东鳞西爪似的摸索。
综上所述,翻译研究需要推动伦理转向,研讨各种文本翻译中所涉的可能伤害及益处,一方面达成文本之间、语言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与互动;另一方面促成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甚至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互惠与共生。这是推动翻译研究伦理转向的努力方向。
虽然翻译研究伦理转向之说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翻译伦理研究永远不可能是完成时。正如只要人类存在,伦理就会存在一样,翻译活动存在一天,翻译伦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而且,翻译伦理需要人为推动,而不是任其自然生长。在笔者看来,贝尔曼认为翻译伦理是翻译研究的三大主攻方向之一是颇有先见之明的。但他对翻译伦理的界定确实过于狭窄,尤其是仅限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伦理。皮姆对其不满自有道理,但皮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极端看重翻译的社会方面、经济交换的一面。总之,推动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已成当务之急。
注:
①笔者已撰专文讨论皮姆的“译者伦理”,详见“‘译者伦理’抑或‘翻译伦理’?——皮姆翻译伦理思想探疑”,即出。该文提到本文下述的15部有关翻译伦理的博士论文或专著。
[1]Hermans,Theo.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M].Manchester:St. Jerome,1999.30.
[2]王大智.翻译与翻译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Godard,Barbara.The Ethics of Translating:Antoine Berman and the“Ethical Turn”in Translation[J].Traduction,Terminologie,Redaction,2001,14(2):49-82.
[4]许宏.翻译存异伦理研究——以中国的文学翻译为背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5]Snell-Hornby,Mary.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6.
[6]Inghilleri,Moira.Ethics[A].Mona Baker and Gabriela Saldanh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2nd edition)[Z].Abingdon and NY:Routledge,2009.100.
[7]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Holmes,James S.Translation Theory,Translation Theories,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Translator[A].Holmes.Translated: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C].Amsterdam:Rodopi.93-98.
[9]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5.26.
[10]Chesterman,Andrew.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M].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1997.
[11]Lefevere,André and Susan Bassnett.Introduction: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The‘Cultural 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A].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C]. London:Pinter,1990.4.
[12]Baker,Mona.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6.
[13]Wolf,Michaela.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C].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7.
[14]朱志瑜.翻译研究:规定,描写与伦理[J].中国翻译,2009,(3):5-12.
[15]Pym,Anthony.Introduction: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J].The Translator,2001,7(2):129-138.
[16]Berman,Antoine.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M].Trans.StefanHeyvaert,New York:SUNY Press,1984/1992.
[17]Pym,Anthony.On Translator Ethics:Principles for Mediation between Cultures,a version of Pour Une Ethique du Traduteur[M].Trans.Heike Walker and revised and updated by the author,Amsterdam/Philadephia:John Benjamins. 2012.
[18]Venuti,Lawrence.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8.
[19]Koskinen,Kaisa.Beyond Ambivalence:Postmodernity and 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M].Tampere:University of Tampere Press,2000.
[20]Baker,Mona.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A].Sandra Bermann and Catherine Porter.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C].Chichester,UK:Wiley Blackwell,2014.
[21]申连云.从“操控”到“投降”——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伦理模式构想[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67.
[22]刘云虹.译者伦理:身份,选择,责任——皮姆《论译者的伦理》解读[J].中国翻译,2014,(5):18-23.
[23]袁筱一.翻译事件是需要构建的[J].外国语,2014,(3):4-5.
【责任编辑:向博】
The Ethical Tur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XIN Guang-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
The eth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much to d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The“linguistic turn”and“cultural turn”in TS led to th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ethical issues in translation,but they at the same time hinder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ethical turn.As an integral property of translation,translation ethics addresses the possible harm and mutual benefits incurred b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to the passive entities like texts,languages and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active parties including individuals,collectivities and nations.The eth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s found still in the state of increasing propensity and in urgent need of the propelling on the part of scholars in the field to help realize the goal of minimized harm and mutual benefits to the parties and entities involved.
Ethical turn;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 ethics
H 059
A
1000-260X(2016)05-0155-06
2016-04-26
辛广勤,深圳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翻译学及翻译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