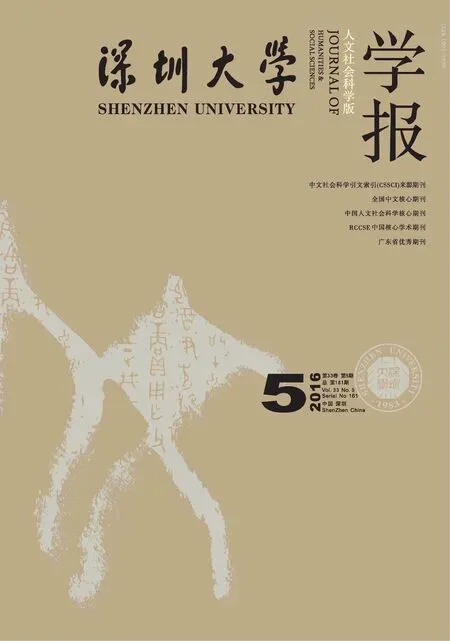从“小区制”到“街区制”:行政公权力介入的法理分析
朱玳萱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广东深圳518049)
从“小区制”到“街区制”:行政公权力介入的法理分析
朱玳萱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广东深圳518049)
“街区制”改革是2016年国务院确定的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大改革项目。然而,如何合法、合理地推进“街区制”改革,是我国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必须回答的基础性重大问题。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难以适用于“街区制”改革,因而难以成为行政公权力介入“街区制”改革的合法性依据,须进一步修订完善。应将现行的以“小区”为基本单元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改革为以“楼栋”为基本单元,从而为推广“街区制”奠定合理性基础——更安全的物业管理服务、更配套的街区公共设施等;实际操作上,行政公权力介入必须符合行政目的,对现有小区合理分类,推进渐进式改革。
街区制;行政公权力;法理
2016年初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第十六部分指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将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与“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此意见一出,便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有部分学者片面地认为该《若干意见》缺乏情理和法理基础,属非理性、非科学的超前决定,不具备可操作性。也有学者从城市规划学角度阐明“街区制”是当前实现宜居城市资源共享的最根本途径,是世界主流城市的共同选择。笔者认为,《若干意见》是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部署。但对于地方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而言,理解和推进“街区制”改革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引领,须对逐步推进“小区制”到“街区制”改革可能面临的行政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不当介入,从行政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的角度进行法理分析的研判,从而强化政府决策的科学价值,使“街区制”改革“理直气壮”地从“纸面”走向现实。
一、概念辨析与行政公权力介入分析
我国目前实行的“小区制”是建国后效仿前苏联“居住区千人指标计划”建立起的相对封闭的居住、办公等区域。主要包括两类,其一是建立于土地有偿使用基础上的个人通过支付合理对价取得的受法律保护的私人住宅小区;其二是俗称的“大院”,即党委、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通过国有土地划拨无偿取得的封闭办公区域。本文所研究的“小区制”特指私人住宅小区。
“小区制”重视对私权的保护,对房屋产权人(包括与产权人有租赁关系者)提供居住、办公、生产生活等服务,呈现出封闭特点。同时,由于其天然的排他、排外属性,致使其与我国当前日益发展和形成的开放性、包容性、国际化、现代化的都市格局呈现矛盾。
街区,属城市规划学概念,是舶来词汇,即英语中的“BLOCK”,由五个英文单词的缩写组成:Business,商业;Lie fallow,休闲;Open,开放;Crowd,群众;Kind,友善[1]。“街区制”是城市街区的一种布局形式,是与城市功能相融合的、适度开放的、资源共享的一种充满活力的城市布局。20世纪90年代,在新都市主义运动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城市重新定义城市与住宅的意义,强调高密度的土地利用和密集路网形成的便捷生活以及配套公共设施的资源共享,如美国芝加哥和纽约第五大道、英国牛津街、韩国独栋住宅聚居区、日本的“无门”大学等,皆是“街区制”典范。因此,“街区制”在推进有限资源共享、解决人口“爆炸”带来的各类“城市病”问题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作用。
街区与小区之区别,在于小区封闭,街区开放。
从“小区制”到“街区制”,无论是对国家、社会,还是企业、个人,既是思维和观念的变革,亦是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若干意见》中对“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的具体要求,必然触及小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基于国人根深蒂固的“围墙”意识,可以预见的,未来绝大多数已建成住宅小区的开放必然涉及到行政公权力对居民私权利的介入。
人类迈进现代社会的成果之一便是对私人领域的发现和保护。一如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述:“在私域里私权应受到尊重,最大程度的防止行政权的恣意。”因此,行政公权力的介入必须具有合法性、合理性,这也是行政法学关于行政公权介入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时,基于《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推行“街区制”的目的,而是否符合这一目的成为行政公权力介入是否合法合理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二、行政公权力介入“街区制”的行政合法性分析
行政合法性原则被视为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政府行政行为上的体现。尽管我国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研究较西方国家晚了近一个世纪,但这一原则的确立也是我国宪法倡导的民主与法治以及法制观念不断深化的结果[2]。正如《宪法》第五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确立的法理基础。
行政合法性原则首先要求行政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即“一切行政都必需有直接的法律依据”(Everything must be done according to law)[3]。因此,行政公权力介入“街区制”改革的第一重拷问,即该行为是否合法?
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度包括两种形式,即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城镇土地属国家所有。城镇的居住和商业用地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向当地政府支付土地出让金后取得的附使用期限的土地,而非具备完整所有权的土地。随后,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商品房出售形式将土地使用权和地上附着物(房产)一并售予业主。此时,业主经过支付合理对价取得的是针对两类对象的“复合权利”,即对土地享有附期限的使用权和对房产享有受《宪法》和《物权法》保护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所有权。此外,以“小区制”为基础建成的小区建筑区内包括共有和专有两个部分。专有部分泛指业主用于居住的空间,也就是俗称的“房子”,对该部分业主拥有完整排他的所有权。共有部分由小区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包括建筑物本体除专有部分外的面积,以及小区绿地、道路、车位、经营性用房等设施。无论是专有部分,还是共有部分,皆属于小区全体业主的合法私有财产,受到我国《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①。政府如要推广“街区制”,将小区内路网、绿地、车位等共有部分由“私”变“公”,只能以征收方式通过回购未到期土地的使用权加以实现。
我国现行的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补偿条例》)是当前各地方政府实施土地征收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是该法律文本对于“街区制”改革并不完全适用,有其局限性:一是公共利益的外延界定模糊。我国《宪法》和《物权法》允许国家出于公共利益需求对公民的合法财产予以征收或征用②。《补偿条例》以列举的方式确定了国防外交、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安居工程、旧城改造等五种类型的公共利益。但由于公共利益本属于一种价值选择,其外延界定十分困难,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很难保证对所有公共利益的价值判断都是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二是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单一。《补偿条例》授权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的做法使得政府在拆迁行为中获得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同时具备“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加之现行法律对政府做出公共利益的判断缺乏相应的法定程序和制度制约,实际上降低了政府做出拆迁决定的法律标准和政策风险,也致使决策层试图通过立法来遏制政府“暴力强拆”的初衷大打折扣。三是《补偿条例》事实上无法适用于“街区制”改革。现行《补偿条例》的主要征收对象为成片区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即对业主的专有和共有部分一同征收。而“街区制”改革由于其仅涉及到对业主共有部分的征收,因此在征收对象上,与现行《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差异,同时也为行政公权力的不当介入留下了“后门”。综上所述,行政公权力如要介入“街区制”改革,首先必须使该介入行为“于法有据”,即要对现行法律法规,特别是对《补偿条例》进行修订完善,或制定专门法规,既切实规范行政公权力介入行为,又为行政公权力介入提供合法依据。进一步明确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和程序性制度;进一步明确合理补偿的对象、范围、价格、程序等规定。在此基础上,将小区制推广为街区制,才切实具有合法性基础。
三、行政公权力介入“街区制”的行政合理性分析
如果说行政合法性原则解决的是行政公权力介入私权必需合法的问题。那么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又一基本原则,其解决的就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无序扩大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言:“在国家管理中不仅有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有合理性问题。”[4]目前,学界对行政合理性原则包含的内容和标准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所谓行政合理性,即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合乎理性。具体内容可衍生为应符合:立法目的,基于正当考虑基础、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平等适用法律、不得差别对待,符合自然规律,符合社会道德、职业道德等。”[5]另有学者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执法人员主观意识必须符合法治理念的要求,不能以人治理念、强权治理理念、党治理念等作为支配权力行使的主流观念。”[6]亦有学者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正当性、平衡性、情理性。”[7]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将合理行政解释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因此,从广义上来理解,笔者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首先可理解为合乎理性、合乎道理(如哲学视阈下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词源“rational”所示);其次应当符合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尊重立法目的,自然规律、社会道德等因素;最后,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应该从公共利益出发不偏私、不歧视。
显而易见,《若干意见》所推广的“街区制”并非国内某些媒体所解读的政府单方面“拆围墙”。如果改革本身不能满足居民对“街区制”小区的安全、卫生、停车等诸多问题的需求,居民必然认为“街区制”不合理,从而形成种种阻力。也就是说,行政公权力介入“街区制”改革仅具备合法性是不足的。政府应当进一步推动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改革当前的物业管理服务体系、街区公共配套设施、小区治理结构等来激发居民对“街区制”生活的美好向往,打消其对“街区制”改革的种种顾虑,增加“街区制”之魅力(合理性)。
(一)推动物业管理服务向综合服务提升,让“街区制”比“小区制”更安全
显而易见,如果“街区制”比“小区制”更安全,那么推行“街区制”无疑更具合理性。但是《若干意见》出台后,老百姓最关心的却是改革可能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人们认为,传统物业管理服务的模式是针对“小区制”小区开发设计的,其服务事项、人员配备、硬件设施、服务标准与流程等难以解决“街区制”带来的安全隐患。因此,要以“街区制”建设为目标指引调整和升级物业管理服务,从而增强“街区制”改革的合理性。
当然,政府在推进物业管理服务向综合服务提升的改革中应发挥主导作用。首先,政府应做好政策引领性工作,尽快推动物业管理服务行业形成符合“街区制”的新的行业标准和规范,改革行业准入门槛,并加强监督;其次,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应尽可能弱化“大包大揽”的管理者角色,以多元共治理念为指导,将政府权责清单中可通过购买服务实现的职责皆以签订服务合同形式赋予物业服务企业等,充分调动和发挥物业服务企业的专业服务能力,使其在“街区制”社区文化、安全、卫生、医疗等事务性工作中发挥好协同管理的主体作用。例如,深圳市福田区侨香社区是香蜜湖街道于2013年打造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试点,其最大特色就是社区不设工作站。
(二)完善街区公共配套设施,让“街区制”比“小区制”更具吸引力
显而易见,如果“街区制”的公共配套设施优于“小区制”,那么,推行“街区制”的合理性便优于“小区制”。但是,据新浪网的一份的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网友不支持“街区制”改革。除了对安全问题存有疑虑外,另一大问题就是小区开放后会给“原住民”的生活带来停车位被挤占、公共设施被滥用、人员难以管理等诸多不便。其中,最不容易调和的矛盾就集中在小区停车位严重供不应求。当前,我国私家车保有量一直居高不下,并且还在持续上涨中,致使停车难问题成为一、二线城市和道路规划相对滞后的三、四线城市的“城市病”。那么,在本身停车位都难以消化本小区居民需求的现实压力下,如何将小区开放给他人使用呢?因此必须完善街区公共配套设施,增强“街区制”合理性。
在完善街区公共配套设施方面,从某个视角看,“街区制”天然拥有优势。因此《若干意见》提出要通过建立“街区制”来解决上述各种矛盾。如前文所述,街区是一种融合的、适度开放的、资源共享的城市布局。一个完善的街区应当是由物业和居民生活所必需的一系列公共设施共同构成。如果这些公共设施不仅能足够满足本地居民生活需求,而且对其他街区的居民具有吸引力,能够创造更多经济价值“反哺”小区发展,那么,本地居民必然愿意开放小区。这就是合理性!例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就是国内知名的街区。又如,2012年由宜宾市政府建设的莱茵香街就是在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指导下,借鉴欧洲莱茵河畔小城设计统一规划的“街区制”小区③。
为此,政府首先需从规划上完善“街区制”小区的公共设施配套,也就是在停车位、小花园、社区医院、幼教资源、图书馆等配套设施上做足文章,让小区居民不仅无需为“挣资源”打得“头破血流”,而且在政府进一步的合理配置下拥有更多的公共资源;其次,政府应科学评估已建成小区的现有资源,在完善上述配套设施后再行推广“街区制”;其三,对于停车位问题,政府一方面应立法对新建“街区制”小区的车位数量的配建比例做出最低限制的要求,另一方面应加大对人口密集度高的城市中心区的公共停车场的建设投入,当然,同时也应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配套停车场的建设和运营;其四,“街区制”应统筹规划,重视形成类似北京王府井等特色街区资源,使小区保值增值。
(三)改革社区治理结构,让“街区制”比“小区制”更优治理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以封闭的小区为治理单元。一旦推广“街区制”,小区管理的难度必然提升。可以预见,物业服务企业将会把区域管理化整为零,“退守”每栋大楼,使楼栋成为小区治理的基本单元。
但是,依据我国2007年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小区是治理的基本单元。第三十四条规定:“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由一个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第九条规定:“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并相应地分别规定了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的权利义务从而形成“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治理结构,并以该治理结构来自主管理小区。
如果社区治理区域因“街区制”改革从小区封闭的地理区划分散为一栋栋独立的楼栋,那么,楼栋长的选任便成为社区治理的基础性环节。但是依据上述规定,目前以楼栋为社区治理的基本单位并建立相应的治理结构还缺乏法律规制的支撑。在此意义上,笔者建议应修订《物业管理条例》,对以楼栋为单元的治理结构给予合法化,并完善楼栋长的相关制度建设,包括组织规则、联席会议和楼栋长参与其他各类主体议事会议的一系列制度。
一旦社区治理结构从“小区制”治理结构演变为“楼栋制”治理结构,“街区制”的合理性不言而喻。
四、行政公权力介入“街区制”的行政合目的性分析④
凡行政行为必然有其目的,行政行为的推进和展开皆受行政目的的制约。正如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8]按照学界通说,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的、行使行政职权和履行行政职责所实现的一切具有法律意义、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9]。换言之,行政行为的目的即为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的、行使行政职权和履行行政职责。而超过行政目的的行政行为就难以逃脱越权和滥权的嫌疑。
《若干意见》第十六部分已明确阐述了推广“街区制”的行政目的是为解决当前城市交通路网布局不合理问题,促进土地的节约利用。因此,超出该行政目的的行政行为就应当属于行政公权力的不当介入。住建部曾就《若干意见》中有关推广“街区制”等问题做过专门解答,并回应“街区制”不是“一刀切”,而是要考虑各方实际情况,回应各方利益诉求的“逐步实现”。也可以说,未来的“街区制”改革只能是在各方面条件皆成熟的情况下的一种渐进式改革。
从符合行政目的的角度出发,行政公权力介入就不可能“一刀切”。政府应围绕目的,按照达到目的之必要性和可行性将现有小区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有条件开放的小区:地块容积率不高;小区内楼群呈“井”字合理布局,且内部路网发达;地处市中心,属交通要道,有开放的必要性。
二是有部分条件开放的小区:地块容积率不高;住宅区内楼群排列不规整,但有将住宅区“一分为多”的可能性,且内部路网发达;地处市中心,属交通要道,有开放的必要性。
三是暂时无条件或开放成本过高的小区:地块容积率较高;住宅区内楼群呈“○”形环抱,实行人车分流,内部路网不发达;虽地处要道,但开放成本远高于维持现状。
四是暂时无开放必要的小区:地块容积率较低,远离市中心;从区域规划看并没有占据交通要道,没有打开的必要性。
结合以上四种分类,“街区制”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先公后私。以国有土地划拨形式无偿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具有公共属性的单位和大院属“有条件开放的小区”之一,应当优先全面开放。第二,适度原则。对于“有条件开放的小区”,在法律、法规、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细则修订完成后可适时推进;对于“有部分条件开放的小区”,政府可推进“半开放”,即以内部路网将小区重新划分为若干个新的“小区制”小区,实现交通主路网的贯通;对于“暂时无条件或开放成本过高的小区”,政府可在充分评估其开放“效益”后再决定是否开放。第三,统筹兼顾。“街区制”是对世界城市规划经验的总结,也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但这种做法并不违背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任何改革都应当是惠及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其中既包括了穷人,也包括了富人。因此,“街区制”改革并不排斥传统的“小区制”。对于地处郊区、暂时无开放必要的高档社区,政府当从公权力介入的行政合目的性角度考量,统筹兼顾,留有余地,不应“过度”施政。第四,民主协商。“街区制”不意味着“有条件开放的小区”都应完全开放,私权对公权的退让是有限度的,小区的开放程度应由小区业主和政府协商决定。如美国芝加哥市虽已实行“街区制”,但为了保护小区业主的人身安全,芝加哥市政府对使用小区内部路网的机动车严格限制其行驶速度(一般限速每小时25英里)。也有小区业主委员会通过与政府协商限制高峰时段的小区车流量。甚至还有小区禁止车辆高峰时段的“抄近道”行为[10]。
综上所述,“街区制”改革既然是一项对老百姓固有生活习惯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涉及到行政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介入,那么,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做出前就应当对其进行行政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的法理分析。同样的,只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出规划合理、舒适安全、配套完善、理念先进、自治有序的“街区制”小区,才有可能冲破国人“围墙”意识的藩篱,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注:
①《宪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②《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③莱茵香街既是商业步行街开放给全市市民休闲娱乐,同时也建设有莱茵社区便民服务站为社区居民提供计生、民政、劳动保障等社会事务的“一站式”服务。
④从学理角度而言,对行政行为的合目的性研究属广义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研究的范畴,本文以之独立成章,是为突出分析现阶段渐进式推进“街区制”改革的可行性。
[1]糜毅,陈仕娇,田叶.街区制在我国的发展与展望[J].住宅与房地产,2016,(9).
[2]胡建淼.关于中国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的探讨[J].中国法学,1998,(1):65.
[3]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 319-321.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88.
[5]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1.
[6]关保英.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合理条件[J].中国法学,2000,(6):82.
[7]胡建淼.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5.
[8]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43.
[9]王连昌.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20.
[10]滕玲.各国开放式街区大起底[J].地球,2016,(2):24.
【责任编辑:张西山】
From Neighborhood System to Block System:Legal Analysis of the Intervention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Power
ZHU Dai-xuan
(Shenzhen Communist Party School,Shenzhen,Guangdong,518049)
The“block system”reform is an important program initiated by China’s State Council in 2016 to strengthen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However,how to promote“block system”reform by legitimate and reasonable means is a major issue Chinese legal system and theory have to address.China’s current land system and“House Acquisition from State-owned Land and Compensation Ordinance”can hardly be applied in“block system”reform,and therefore can hardly be its legal basis.They need to be amended and improved.We should change the current grass-root governance with“neighborhoods’as basic units into the one with“buildings”as basic units so as to lay reasonable basis for the promotion of“block system”reform,such as safer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 and better supporting public facilities.In practice,the intervention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power should conform with administrative purposes,make reasonable classification of current neighborhoods,and pursue gradual reform.
block system;administrative public power;legal theory
D 921.1
A
1000-260X(2016)05-0102-06
2016-06-04
国家行政学院课题“深圳多元共治试验与中国特色城市社区权力秩序重构”(13HZKT419)
朱玳萱,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福田分校讲师,从事政府依法行政、社会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