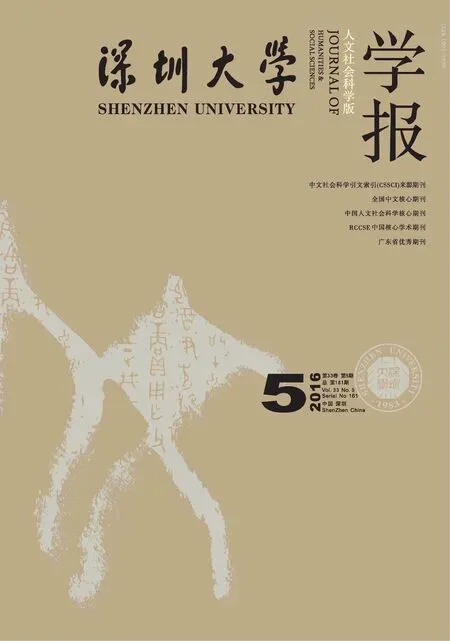论孟子的精神修炼
匡钊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026)
论孟子的精神修炼
匡钊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026)
孟子对人心的探索和对于精神修炼工夫的发掘,使早期儒家在这方面的思想变得真正丰满与完整。孟子曾用一系列大体对等的术语来指称精神修炼工夫,如“存心”、“求放心”、“养心”。对于“养心”,孟子首先明确将其与“寡欲”联系起来,这与他对于“求在我者”和“求在外者”的分辨有关,人欲属于“求无益于得”的那些内容,在精神修炼中应通过负面的工夫加以制约。对于“养心”的目标,在孟子看来大约不外就是让“良心”袒露,既不受外来因素也不受内在欲望的威胁,对于这样的精神状态,孟子称之为“不动心”。达到此种状态,需通过“知言养气”的修养技术。这套工夫论是孟子对精神修炼的全部理解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被视为“知言”、“集义”与“养气”两种精神修炼技术的平行开展。孟子“知天”、“事天”的言论,最终是在“天人有分”的前提下,强调我们应通过精神修炼之途径而达成理想人性,在取决于人自己的修身与不取决于自己的命运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
精神修炼;知言养气;践形
在孔子所奠基的可被称为“为己之学”的问题域当中[1],其后学已经将相应的获取德性、改变自己的修身路径,清晰分判为三条:心术或精神修炼、围绕《诗》《书》展开的经典学习与礼乐训练[2],其中精神修炼的自身技术的作用被放大,相对其他修身路径占据主导或核心位置——所谓“心术为主”。这种传统,在孟子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最终将具备一定潜能的人心设立为引导我们达到本真的生存之理想境界的主宰者,而他所关注的使人自身主体化的技术,也完全局限于精神修炼领域。孟子因专注于人心而放弃了较早的儒家在“为己之学”问题域中开辟的另外两条与经典学习和礼乐训练有关的修身进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并因为文献缺失等原因而对儒家后世的历史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孟子对人心的探索和对于精神修炼工夫的发掘,却使早期儒家在这方面的思想变得真正丰满与完整。
一、“养心”不可谓“命”
孟子曾用一系列术语来指称精神修炼工夫,如所谓“存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孟子·离娄下》);“求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孟子·告子上》);“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通过这些修身活动,孟子认为我们最终应该达到“不动心”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理想的状态的达成,还会有一定的外“形”上的表现——这就引出了“浩然之气”和“践形”两个问题。
孟子认为人自身具有引导自己达到本真生存的潜能,即人性拥有向善的可能性①,如果能够健康地发展这种“四端”或者“良知”,我们一定可以在人性全面展开的过程当中获得德性或者理想的人格品质,以实现自身价值之所在。于是,如何完成这一过程就显得至关重要。聚焦于精神修炼问题,在谈论相应的修养过程时,孟子所运用的一系列术语,如“存心”、“求放心”和“养心”,所要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通过这些工夫,他所要把握住的,都是有良知之心,或者说心之良知,也就是具有“四端”的“良心”:“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告子上》)孟子所谓“存心”、“求放心”所要“存”、要“求”的都是这种“良心”,此“良心”也正是他所欲“养”的目标。这样的“良心”也就是孟子所称的未受到污染的“赤子之心”,据此他要求我们“不失其赤子之心”(《孟子·离娄下》)。所有这些说法的意思都是要我们克服自身的无能与意志薄弱,经由种种存养的方法,通过涵养、提升、扩大心中原有之“四端”来达成德性,达到人自身应有的主体地位。对此孟子曾引孔子言语加以强调:“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
孟子思想中“赤子”的意象,未必与来自老子的影响无关,而他在对于修养方式的讨论中涉及“气”的一些思考,则很可能受到稷下道家的影响——如孟子所谓“存夜气”的问题,便与《黄帝四经》中的有关说法明显存在前后联系。虽然大家的目标不同,但在先秦哲学的语境中儒道两家共享一些工夫论层面的东西或为不争的事实,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与“气”有关的话题上面。早有论者有见于此,并认为:“孟子的心气论……除了孟子本人创造性地发挥外,还与此前和同时代人的思想成果有关。特别是《管子》中《内业》《心术》上下和《白心》四篇中丰富的气论和心论思想,同孟子养气、养心的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3](P161)如果孟子关于精神修炼的一系列术语所要表述的内容最终可归结到“养心”二字,那么下面我们的考察便可首先从“养心”的角度入手。
对于“养心”,孟子首先明确将其与“寡欲”联系起来:“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对于不能为善的问题,孟子认为对于德性的无知可以克服,而对在拥有相关知识的情况下故意作恶的情况未加考虑,同时实际上并不承认我们会因为意志薄弱而存在能够并且愿意但无法做到的情况,如他与梁惠王的对话中便以比喻的方式亮明自己的观点: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意思是,追求德性,完全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只要主观上愿意,就不存在其他的障碍。于是不能为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在于梁惠王的“寡人之疾”。孟子要梁惠王推恩,所要解决的是梁惠王的欲望和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而对于人欲与人自身的德性追求之间的矛盾,孟子则拈出“寡欲”二字。单看“寡欲”的字面,这个观点似乎又和道家或者墨家有关,但在儒家系统内部,对于“欲”的看法远比前两者更为正面,饮食男女都是人伦题中应有之意,因此孟子讲“寡欲”只怕和道家或墨家相去甚远,在思想上也未必受其影响。孟子对于“寡欲”的看法,与他对于“大小体”的分辨有关,饮食之类的欲望所养的只是口腹“小体”,这方面内容本来也是必要的,但在与心之“大体”相比的情况下,则我们不应因为满足只能养“小体”的欲望而威胁到“大体”的修炼:“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孟子·告子上》)如此可见,“寡欲”的理由不是因为人欲本身不好,而是当对于欲望的追求威胁到对于人心的养护的时候它才是负面的,也正是因此才须对其加以限制。至于为什么过分追求人欲会危及到人心,回答这个问题大概仍然可以从儒家一贯“天人有分”的根本看法入手。孔子早已明确区分“可求”的和“不可求”的,前者为取决于人自身的道德价值与理想人格,而后者则为因涉及外部因素而不取决于人自己的那些富贵寿夭之类,而人欲的内容之所以不应该受到过分的重视,便是由于其本属后一范畴——欲望能否得到满足与客观状况有关。这个分别,在其后学中继续存在,如郭店简书《成之闻之》所谓:“君子之求诸己也深,不求诸其本而攻诸其末,弗得矣。”这里的“本”所指应该就是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东西,而“末”的意思当然相反。孟子也对这种分别有极为清醒的认识,这便是他对于“求在我者”和“求在外者”的分辨:“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此“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相对,而所谓“求在外者”,也就是孔子早先所谓“不可求”者,此中区别,诚如冯友兰所言:“孟轲把人生中的事情分为两类。一类是‘求在我者’,如果努力追求,一定可以得到,……这是关于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事情。另一类是‘求在外者’,有一定的办法去求,可是能得不能得是由自己所不能控制的条件所决定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天命’所决定的。”[4](P89)而人欲便属于“求无益于得”的那些内容,因此根本不应该对其过分重视②。上述分别,大概同样也与孟子所谓义利之辨有关,义的内容无疑是“求在我者”,而利所代表的,也恰是那些不取决于人自身、且对于人格养成和其价值实现并无直接益处的外在之物,从这个角度讲,它当然应是“不为”、“不欲”的对象,如孟子所言:“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尽心上》)认为“欲”和“利”不应被作为追求的目标,在《吕氏春秋·必己》也有类似的儒家思路上的说法:“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欲”“利”既然不值得追求,那么这些内容自然与正面的存养之道无关,相反,在精神修炼活动中,对于这些内容反而应通过负面的工夫加以制约。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参照《孟子·尽心下》中一段著名的文字:“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段话的意思历来便被多加阐释,特别是其中“性”字的意思,更能见出孟子之前儒者便已经开始的对于其意义的重大改造,使之由与生俱来的生命禀赋转化为对于人之所是的一个理论回答。理解这段文字的关键,便在于领会到“性”字包含上述两层意思,而其中“命”字,则只有一层意思:“‘命’字之指涉,正与‘天’字相近。”[5](P147)上述内容正如劳思光所言:“取前一‘性’字之意义,则其指涉即在形躯之各种官能;取后一‘性’字之意义,则其指涉即在于人之价值意识,即孟子所谓‘四端’所显现者。而‘命’字在意义上则为‘命定’之意,所指涉者则包括经验界之一切条件系列。”[5](P147)“性”字的前一层意思,也就是孟子欲其“寡”的“欲”,而其后一层意思,则是道德价值之“求在我者”,这种分辨,程朱便已经体会到,就前者朱熹“集注”云:“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愿,不止为贫贱。盖虽富贵之极,亦有品节限制,则是亦有命也。”就后者朱熹又说:“程子曰:‘仁义礼智天道,在人则赋于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浊,然而性善可学而尽,故不谓之命也。’……愚按:所禀者厚而清,则其仁之于父子也至,义之于君臣也尽,礼之于宾主也恭,智之于贤否也哲,圣人之于天道也,无不吻合而纯亦不已焉。薄而浊,则反是,是皆所谓命也。愚闻之师曰:‘此二条者,皆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为性,虽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后五者为命,一有不至,则不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处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总括的看法,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六十一还有言云:“君子不谓性命一章,只要人遏人欲,长天理。前一节,人以为性我所有,须要必得;后一节,人以为命则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说性处,却曰‘有命’;人说命处,却曰‘有性’。”可见这段话由来便颇可认为是对由“寡欲”而“养心”的一个深入说明。
类似上述孟子对于“求在我者”和“求在外者”的看法,希腊化时期的重要哲学学派斯多葛派也对于依赖于我们的东西和不依赖于我们的东西做出过区分,并且一方面认为这种分别乃是基于价值判断和事物自身的区分[6],另一方面也认为“只有德性才是因其自身而值得选择的”[7]。将他们的思路与孟子的思路稍加比较,更能从其他角度来加深我们对于孟子和儒家传统的某些了解。在孟子看来,人的欲望的可实现性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这种“求在外”的内容属于应受到控制的对象,我们不应该因为过分追求这些东西而损害到那些真正的“求在我者”——孟子以“寡欲”“养心”不外就表达了上面这些意思。与此类似,斯多葛主义者也主张人只应当追求那些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伦理价值,他们认为,“人类的一切苦恼来自于寻求获得或保有可能或会丧失或不能取得的东西,也来自于试图避免常常是不可避免的灾祸。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教育众人,使他们只寻求可获得的善,并仅试着避免能避免的恶。之所以某些善可获得或恶能避免,是因为其必然完全依赖于人的自由;而满足这些条件的唯一事物乃是道德上的善与恶。仅它们依赖于我们;其他一切都不依赖于我们”[8](P83)。对于上述分别,罗马斯多葛主义者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论断更为明确,他的思考“基于传统的斯多葛派在依赖于我们的事物和不依赖于我们的事物之间做出的区分:‘依赖于我们的乃是价值判断、行为取向、好恶(desires and aversions),以及——一言以蔽之——取决于我们的所有事情。不依赖于我们的乃是肉体、财富、光荣、政治上的高位,以及——一言以蔽之——不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所有事情。’(Epictetus,Manual,5.)依赖于我们的乃是我们自身灵魂的行为,因为我们能够自由地对其加以选择。不依赖于我们的乃是依赖于自然与命运的普遍进程的那些事情”[8](P192)。稍后的马克·奥赫留在其《沉思录》中回应了爱比克泰德所提出的上述三个基本主题(价值判断、行为取向、好恶),并进一步强调作为一种精神修炼的哲学就在这些依赖于我们的事情向度上展开[8](P195-202)。观察斯多葛派的论点,我们会在对哲学活动定位的大的相似性下面发现一个非常不同于上述我们对于儒家的了解之处:斯多葛派哲学家乃将人欲(desires)作为取决于我们的事情。从人的欲望或者好恶源自心灵的角度讲,在不考虑这些内容的客观实现性的情况下,将其视为取决于我们的事务完全正确——我们当然可以训练、培养自己某一方面的意欲而主动克制其他方面的意欲。前面对于孟子“寡欲”主张的考察,完全是从其外在实现性的角度入手而没有考虑到人心对于欲望的主观控制,这里参考斯多葛派的思考,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孟子以“寡欲”“养心”的说法,并不排除上述斯多葛式的对于精神修炼的思考。也就是说,无论从欲望的外在实现性上讲,还是从心灵对于由此生发出来的意欲的主观控制的角度讲,孟子以“寡欲”这种精神修炼技术来达到“养心”之目标的工夫论思考,都是可理解的。
二、何谓“知言养气”?
对于“养心”的目标,在孟子看来大约不外就是让“良心”袒露,既不受外来因素也不受内在欲望的威胁,对于这样的精神状态,孟子称之为“不动心”。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记录了一段孟子与公孙丑之间就“不动心”问题而展开的重要对话,且这段话历来被认为是孟子言修身工夫时的关键所在。孟子在对话里揭示了除以“寡欲”“养心”之外最为重要的一套“知言养气”的修养技术。这套工夫论是孟子全部精神修炼技术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此话题从字面上首先与孔子“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的言说有关,其次也与稷下道家和郭店简书中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就前者而言,孔子所谓“知言”基本上是比较朴素的“听其言,观其行”的意思,但孟子显然不是在这层意思上使用这个观念;就后者而言,“抟气”对于老子和黄老学家是非常重要的修炼工夫,而孔孟之间的儒者也已经将气视为与道德德性的获得密切相关的动力性因素[9],孟子在自己的思考中,对上述内容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孟子与公孙丑之间这段著名的关于“知言养气”的对话曾受到反复的讨论③,这里仅结合朱熹的经典理解而将其分层次梳理。
对话首先从公孙丑的问题开始,孟子告诉他,“不动心”“不难”,甚至“告子先我不动心”。于是公孙丑继续询问“不动心”之道,孟子先举北宫黝、孟施舍的例子,说明第一个层次上通过“养勇”所能达到的“不动心”。在这个层次上,孟施舍因“守约”而强于北宫黝。这层意思如朱熹所谓:“黝务敌人,舍专守己。……论其所守,则舍比于黝,为得其要也。”也就是说,针对外在目标的“养勇”之训练,从境界上讲不如以自身为目标的精神修炼。但孟施舍的修炼方式的“守气”,在孟子看来大约又近似于“强把住不动”,而比起曾子的修炼来仍然不如:“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对此朱熹注云:“孟施舍……所守乃一身之气,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动心,其原盖出于此。”对话至此,可以推测孟子是将“守气”或“守约”作为达到“不动心”的要件,但他尚未说明孟施舍式的“守气”与儒家或曾子式的“守约”差异何在,也未说明这些修养方式与“不动心”的关系如何。
于此便进入对话的第二个层次,公孙丑问孟子的“不动心”与告子“不动心”之间的差异何在。“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从告子的各种观点来看,笔者以为他所代表的大体是较早儒者的某些过时观点,而在此意义上,他同样可能认为“气”的修养与某些德性的获得密切相关。告子的大体意思,是从修养层次的角度在言、心、气之间建立了一个递进的关系,这个过程中言是最基本的,而气出现在修养的最终层次上,心的地位则居于此两者之间。“言”字应做何解,须从后面孟子“知言”的说法中探求,“知”与“思”相关,“知言”的重点恐怕在于“思”而“知”,所谓“得于言”,乃是“思”这种精神修炼工夫的后果。“心”字所指,在此则应是孟子其他地方所讲的“才”,也就是人心具备的某些潜能。至于“气”的意思,其在先秦文献中以往的用法可能覆盖了从自然界的空气、人的气息与生命力、精细的质料到精神活动的多个领域,而此处告子所谈论的“气”,无疑是关乎精神状态,早有论者有见于此:“孟子所言‘气’,乃在人的物质实存性一端所显现的人的内在精神状态或精神力量。它既不同于西方哲学那种与形式原则相分离的质料概念,亦不同于宋儒表现人的个性才质差异的‘气性’、‘气质’概念。”[10]孟子同意告子关于心与气关系的看法,但不同意他关于言与心之间关系的看法。黄老道家主张气在精神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在他们看来,“气”就是“精气”,而心则为“精舍”(《管子·内业》)。有论者指出:“精气(‘鬼神’)超乎心思之上。心如房室,扫除嗜欲,腾出空位给精气,心的主君作用自然发挥。但孟子则不然,他讲‘志至气次’,以心使气,却为道家所忌。《老子》五十五章曰:‘心使气曰强,物状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老子》认为柔弱生之徒,坚强死之徒,而柔弱一定可以胜刚强。只有虚心以纳气,不能将心志来役使气。孟子与道家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心和气在人体的定位不同。”[11]孟子与道家的确对于“气”与“心”的定位不同,但在“知言养气”的理论结构中,孟子与黄老道家观点差异的焦点却不在于主张哪一个更根本、谁能役使谁,而在于在心气关系中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黄老道家视气为“精气”,与“道”接近,而孟子如以往孔子后学那样,视气为个人精神活动中的某种动力性因素,即是与道德德性的获取密切相关的工夫层面的东西[9];黄老道家视心为某个接纳精气的场所,而孟子在此则视心为实现德性的潜能。在孟子的意义上,类似于道家的认为气对于心而言居更高层次的优势地位的看法,当然并不成立,只是从修养次第的角度讲,无论告子还是孟子均同意,对于心灵道德潜能的某些发掘,应优先于获取道德德性所经由的气之修炼。这也就是“先立乎其大者”的意思,即对于“四端”之心的确认,优先于任何一种实现德性的工夫,而任何工夫,反之均是对于“四端”的扩充:“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从这个角度讲,在告子和孟子看来,心之潜能优先于气之涵养。
如果孟子与告子都同意“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则他们对于“不动心”之道的看法的差异,完全在于对言与心关系的不同理解。劳思光曾解释上述差别如下:“‘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盖心志未能得理,徒恃意气以为矜持,是沽勇之流,非儒者所许。”[5](P127)“‘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盖讲论有不得理或不得正者,正须求之于心志,以心正言,方是人文化成之精神。”[5](P127)这是从得“理”与否的角度处理问题,难免带有宋儒的影子,而在笔者看来,无须设定“理”的存在,仅从对“四端”的确认应优先于任何修养工夫的角度,已经完全可以说明问题。关键在于,不但“气”是工夫论方面的题目,孟子所谓“言”,如其与“思”相关所暗示的那样,仍然是在工夫论的意义上被言及。在孔孟之间儒者看来,“思”或“知言”与理智德性的养成有关,告子认为这种工夫,或者说思考优先于人心之潜能,也就说在他看来,心灵所能把握的内容一定都是已经通过思辨言说呈现出来的内容,这种对于“言”的看法,更接近纯粹的对于客观事物的认知,不但完全没有考虑到“思”之中可能包含的“情”的因素,且如果继续发展,大约也会呈现出类似与西方式的认识论的理论构造。但孟子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一方面如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同意没有实践智慧是不可能发展出道德德性,如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另一方面,则充分考虑到心之“四端”所包含的“情”的因素,并且继承先前儒者的观点,仍然认为此种可表现为“情”的心灵潜能,乃是人性成长的真正起点。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人心之潜能对于“言”所标识的成就理智德性的工夫具有优先地位,无论得言与否,首先还是要“求心”——确认“四端”之心的基础性地位。如果缺少对于“四端”与“良知”这些人心本来潜能的体会,缺少对于“情”的基本感觉,思知的工夫毫无意义。
了解上述这种告子与孟子间立场的根本差异,也就能了解他们两人两种“不动心”的差异何在。对于告子而言,他虽然先于孟子达到“不动心”,但他取得这一效果的过程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可能如康德一般取决于对于思辨性道德规则的先行理论言说,这就像孟子前面所批评的“养勇”与“守气”一样,都是根据某些外在的标准来训练自己,达到“不动心”的状态。于是便会产生进一步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追问这些外在标准的来源,那么就不得不引入类似于道家之“道”这样的超越性观念,而一旦出现这样的观念,整个思考问题的路径便可能偏离了孔子所开辟的那种反求诸己的内向转向了——这可能接近于荀子与汉儒的思路,但绝对与孟子的思想相左。更为重要的是,出于这种思路来把握人的价值,通过某种超越性观念来确定德性的合法性,表明了一种“不自由”的哲学,如果我们仅仅通过“得言”、“养勇”与“守气”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训练自己获得自身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就不是自由的,而不自由的道德同样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曾子式的“守约”作为自省的结果乃是出于充分的知识的自觉,具有远远超出前面所举出的北宫黝、孟施舍的例子的理论意义。孟子所主张的“不动心”,就是曾子式的,这可谓是“自由”的“不动心”。儒家先前所强调的“贵心”之论在孟子这里通过其对于“四端”和“良知”的把握又更深入了一层,而同样的思考上的深入也出现在工夫论的层面,如果说以往儒家已经对于通过精神修炼等等修身活动来改变自己、使自己成为本真之应是的活动有相当明确的认识,那么这种活动本身的合法性,或者说所能获得的德性与人格品质的合法性问题则尚未发生,如孔子,以及孟子之前的儒者均未正面提出各种修身教化的依据是什么的问题。但孟子则对此有极大的敏感,并以“四端”之心加以总的回答,且将此答案作扩展到对精神修炼工夫的思考之中,即心之潜能既是德性合法性的根源,同时推广来说也是获得德性的修身技术的合法性根源,“四端”之心即是“思”而“知言”,也是“养气”的优先条件,而同时也只有从这个方向出发,才能获得优良的德性品质并达到真正的道德自由。此前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孟子明确认为伦理价值和修身工夫必须是自由的、“自我立法”的才是有意义的,如冯友兰解释后文所谓“浩然之气”:“浩然之气的主要内容是不动心,……不动心也有二种情况,一种是强制其心使它不动。另一种是心自然而然地不动。”[4](P93)在如何使心不动的修炼技术上,如果告子与前人均属“强制其心使它不动”,那么只有孟子发现,“不动心”的真正意义在于“心自然而然地不动”,或者说“自由地”不动。
为了说明上述自由的精神修炼工夫,孟子随后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观点:“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孟子此处所谓“志”,仍然也就是“心”,“‘志’与‘心’为一事”[5](P127),而他上述言论的要点在于“壹”这个观念,朱熹认为此“壹”也就是“专一”:“孟子言志之所向专一,则气固从之;然气之所在专一,则志亦反为之动。”这个论断大体不错,而此处出现的“壹”或“专一”的观念,无疑是对《五行》中所谓“能一”的思想的继承,在某些意义上,可能也与稷下黄老学文献,如《管子》“四篇”与新出土文献《凡物流形》中“能一”的说法未必完全无关。“壹”指的是“一于心”、“全心”或“独心”的状态,也就意味着人专注于内心、摆脱了各种困扰而关注自己。这实际上也就是“不动心”的状态,而如果我们能达到此种内心状态,当然也就达到了在不同情况下表现出的各种精神面貌的统一,相反,如果我们所有的精神面貌或者气质表露已经达到某种高度统一、相互结合的状态,同样也意味着心灵的“专一”——“反动其心”的意思不是说心受到气的影响,而是从上述后一个角度继续对心之“壹”加以说明。基于这种对于“壹”的了解,孟子继续向我们揭示了达到此种心灵自由而专一状态的路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对于“何谓浩然之气”,孟子本人也认为是一个难以说明的问题。他首先对这种“浩然之气”加以笼统说明:“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朱熹对于孟子上述言语解释说:“知言者,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失养故馁,惟孟子为善养之以复其初也。……告子之学,与此正相反。其不动心,殆亦冥然无觉,悍然不顾而已尔。”特别就“配义与道”而言,朱熹以为:“配者,合而有助之意。义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他的这些说法,在我们看来有不少成问题的地方,比如反复引入“理”或者“天理”来说明问题便是多余和不必要的。孟子所谓“知言”,重点在于揭示此活动的精神修炼意义,谈不上新老新儒家意义上的“究极其理”,同时,朱熹所谓“复其初”的说法也不恰当,孟子的意思不是要人返回到某种原始的“善”的状态,而是要我们从“其初”之时的“四端”与“良知”出发,通过一系列的修养活动,自己引导自己达成理想人格的最终目标。至于理想人格所展现的精神面貌,孟子便称之为“浩然之气”,这个词所表达的内容,一方面与工夫论层面的“气”有关,而另一方面不外就是对“壹”于心之后,人的某种综合性的精神品质之整体说明,这样的精神状态在孟子看来,“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这里孟子最后以“集义”的说法点明从“知言”到“养气”的工夫次第,而自己与告子的差别,也仍然以告子“义外”的看为根本分野。
告子“义外”的说法,本来意味着他仅从外在的行为层面把握某些伦理品质化的德性,但孟子这里发挥了告子的原意,认为“义外”归根结底也意味着对外在道德规范的强制性有所依赖,而“得于言”对于进一步的修身活动而言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而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认为告子既“不知义”也不真正“知言”,他不理解对于道德修养和伦理价值而言必不可少的内在的合法性根源和自由的意义,也不理解作为精神修炼工夫的“思”与“知”一定要在“四端”之心的基础上方能开展出去。“集义”的说法所表明的,实际上就是通过“思”而“知言”的工夫论层面上的内容,笼统而言也就是致良知,是让人内心的“四端”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也就是孟子后面讲述的寓言所要表达的意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既不能放弃、忘记对于“四端”或者“良知”的培养——这不外就是《告子上》中“牛山之木”章中所谓的“放其良心”;同时,对于良心的培养也不能通过不自由的、外在的强制性手段来达到目的——此处所谓“义袭而取之”,也就说人不能比照某种外在的“义”或“言”的标准来改变自己、塑造理想人格,并最终达到“浩然之气”的精神面貌。此中所包含的道理,孟子在其他地方也有出于同样理路的表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这里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意思,不外也是说我们自由、自主地展现出德性,而并不是依据某种现成的德性之标准来强制规范自己的行为。
“浩然之气”的说法,与孟子在“牛山之木”比喻后提及的“夜气”的概念也有明显的关联。孟子谈到所谓“存夜气”:“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孟子·告子上》)以往郭沫若已经注意到孟子在论及“知言养气”时所谓的“浩然之气”可能与稷下道家所提倡的修养理论有关系④,而张岱年曾专论此关联:“《内业》有‘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这‘浩然’二字同于孟子所谓‘浩然之气’的‘浩然’。《内业》又云:‘抟气如神,万物备存’,意与孟子所讲‘万物皆备于我’相仿佛。”[12]此处孟子所言及的“夜气”,同样也出现在为郭、张二老所未及研究的马王堆新出土文献《黄帝四经》中,其中《十大经·观》有言:“是[故]赢阴布德,[重阳长,昼气开]民功者,所以食之也;宿阳修刑,童(重)阴长,夜气闭地绳(孕)者,[所]以继之也。”这一状况,或许印证了孟子在涉及气的内心修养工夫方面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稷下道家的影响。
至于孟子所谓“存夜气”,无疑是一种精神修炼工夫,而“夜气”二字的所指,则与未受“好恶”污染的心灵本然状态有关。朱熹《集注》中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便是从“良心”的角度来对文本加以说明:“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好恶与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言人之良心虽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间,亦必有所生长。故平旦未与物接,其气清明之际,良心犹必有发见者。但其发见至微,而旦昼所为之不善,又已随而梏亡之。昼之所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又不能胜其昼之所为,是以展转相害。至于夜气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义之良心,则平旦之气亦不能清,而所好恶遂与人远矣。”他本处的解释,无疑是比较接近孟子本意的。所谓“良心”,也就是“本心”,徐复观便以后者论“夜气”:“孟子又在《告子》上的‘牛山之木尝美矣’一章中提出‘平旦之气’、‘夜气’,以为此是人的善端最易显露的时候,也是当一个人的生理处于完全休息状态,欲望因尚未与物相接而未被引起的时候;此时的心,也是摆脱了欲望的裹胁而成为心的直接独立的活动,这才真正是心自己的活动;这在孟子便谓之‘本心’。”[13]“良心”与“本心”,也就是“四端”之心,乃是人道德活动发动的原点、未受到外界影响的内心状态,如此“存夜气”不外也就是通过一定的修养工夫而使“良知”袒露,通过“存夜气”,人便能保有作为具体的道德行为和伦理价值的根本源泉的“良心”。
与孟子相比,《十大经》中的“夜气”则并无这样深刻的内涵。前引《十大经》原文,其意思大体而言是从阴阳二气的角度来说明自然与人事的变化,讲的是在黄老学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阴阳刑德相互依存转化的道理”,陈鼓应曾释全文如下:“阴气满盛时阳气便开始萌生,所以此时长养之德开始布散;阳气逐渐积累,昼气发动,成就事功,人类因此而得到饮食养育。阳气积久时阴气便开始萌动,所以此时肃杀之刑开始酝酿;阴气开始逐渐积累,夜气闭合,孕育生机,人类因此而得到后继繁衍。”[14]陈鼓应并未对“夜气”的术语加以专门的解释,但从上下文推断,其所指应是质料意义上的天地之气、自然之气,大约也就是“阴气”聚集的结果,这种“夜气”孕育生机,并最终会转化、生成新的生命。在比喻的意义上,孟子所言“夜气”之生发出现实的伦理道德,由善之“端”成长为善的品质与行为,正如《十大经》中的“夜气”孕育生命一样——虽然孟子所谓之“夜气”从意义上要比《十大经》中的“夜气”复杂,但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相互关联的语义线索。
对于上述这些术语上的关联,有论者认为:“孟、管两家何以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相通相似之处呢?……我们既不能视之为偶合,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一家对另一家的‘学舌’或‘剽窃’,……相通相似之处表明两家关心的问题存在着某种一致性,遵循着相同的逻辑规律。两家一个是探讨道德修养,一个是探讨身心修养,在‘心’这个交汇点上取得了共识,……两家探讨的是同一运动过程,……他们各自从自己的角度独立地揭示了该运动过程的内在规律。”[3](P183)这个判断,或许对儒家与黄老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估计略有不足,虽然他们之间对于“气”的看法差异很大,但从《五行》《学》《庸》和《孟子》文本来看,他们对于心灵与相应的修养工夫的看法之间,肯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从他们“贵心”的判断与将“气”作为精神修炼中的重要因素都可见这一点。
“浩然之气”除了作为一种精神面貌的象征,“气”字本身所指的内容,同样包含工夫论的含义,在此意义上,“养浩然之气”与“存夜气”一样均也可被视为精神修炼技术。从孟子前面有关言、心、气的观点来看,他是从作为德性与工夫的合法性根源的人心潜能出发,一方面提倡“得言”,或者说与“思”、“知”有关的修身技术,另一方面则提倡“得气”或“养气”的修身技术。在此意义上,孟子“知言养气”的说法,可被视为“知言”“集义”的精神修炼技术与“养气”的精神修炼技术两者的平行开展。在郭店简书中,对于上述两者修身技术有明确的运用上的区分,大体认为前者关乎理智德性而后者关乎道德德性⑤,但因为孟子并未从上述角度出发对德目加以划分,虽然在他的思想中两类精神修炼工夫的分野仍然存在,如“养浩然之气”、“存夜气”的说法,与“知言”、“反身而诚”和“心之官则思”的说法之间所形成的对照,但是这两类工夫与不同类型的德性之间的关系却付之阙如,就此点而言,不能不说是孟子思想中除了未顾及经典学术与礼乐训练之修身途径之外的另一个遗憾。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孟子》中对于与“气”和“思”有关的两种修身进路均有涉及,但孟子本人似乎更强调与“气”有关的工夫,并有专门的讨论,而对与理智活动有关的工夫较少特别的言及——未对“智”之端加以独立的研究,而是笼统将其置于另外三种道德德性之中。在获得理智德性的诸工夫中间,在孟子之前的儒者眼中,恰恰是“诚”而非“思”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此点在《中庸》与《大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意思,孔子早有言及,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知”与“思”相贯通,属同一层面或类型的事情,而孔子上述言语的意思不外是说,如欲达到真知,实际上还是要着落在“不自欺”的态度上,也就是说,任何理智活动的意义,最终都需要一个“诚”字来做保障。孟子对于这个思想传统从他对“反身而诚”的强调来说,应该同样十分了解。仅有“诚”的工夫,在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并立的视野中显然并不完整,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孟子虽然对于上述两种德性的划分缺少清晰的见解,但显然却在工夫论的层面上对于“诚”的不完整性有较深的体会,因此孟子专门论与“气”的涵养有关的工夫,却在无意中补足了早期儒家精神修炼领域内,对于获得伦理德性的核心工夫的思考。
“知言养气”的精神修炼工夫,最终服务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专一的、有德性的精神状态的养成,这在早期儒家与孟子的逻辑里,完全是一个关乎人的价值的实践问题。但这层意思早在朱熹处便受到曲解:“朱子通过对孟子‘知言养气’说的诠释,基本上把孟子学中的德性问题转化为知识问题。”[15]对于我们而言,最为重要的则是通过上述分析,将以人为认识对象而展开知识探求,通过对于人如何成为其所应是的过程的揭示,转化为对于人自身的生存论的(existential)回答。至于朱熹的思路则完全与孟子继承自孔子的先秦儒家主流思想相左,反而与近代西方哲学有相通之处——这大概是因为朱熹的问题意识难免受到西来的佛学影响,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新儒家总不放弃为道德问题寻找形而上基础的原因——实质上他们只要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朱熹的思路便一定会展现出如此的理论趣味。
三、“践形”与“知天”
在考虑孟子对于“养心”和成就人性的种种说明时,这个精神修炼问题最终还与他所谓的“践形”有关。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他的主张便已经明确将作为代表了人格修养之理想境界的圣人与“践形”的观念联系起来,而后者显然是一个涉及身体层面的观念。这种“践形”的说法,在孟子这里应该单纯从一种自内而外的角度来理解,这便是表现了孟子所谓君子“睟面盎背”的“气象”:“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孟子·尽心上》)这不外是主张,个人的精神面貌肯定会在外形外貌上有所表现,拥有较为高尚人格的君子大约在外形上也有过于普通人的非凡之处。
正如《管子·内业》看来,具有大智慧的理想精神状态不但与“耳目”有关,也与“四肢”有关:“安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其所谓“全心”也同样会在“形容”和“肤色”上有所表现,而所“抟”之气也依旧包括气息在内。后面这些内容就不仅仅属于精神修炼的范围了,而更与以往老子对于人的形体的关注相关,从这一角度看,《管子》“四篇”仍然遵循了老子在过程和目标方面同样的身心并重的修养主张,《管子·内业》“修心而正形”,所要表达的就是这种对于“心”的精神修炼和对于与之平行的“形”的调整养护并重的态度。
在以往的思想传统中,已经存在一个漫长的对于身心关系的思考传统,主流的看法,除了老子与道家之外,对身体问题的思考总是从属于对于心灵的思考。如前所见,春秋时代人们对于身心问题已经有所关注,大体上认为心灵对于身体居于支配的地位,孔子继承这一传统,虽然强调涉及身体训练的礼乐等修身活动,但他对这些活动的定位,最终是使之服从于对于人的内在人格的养成的,只有老子对于长生久视之道有专门的关注,并在精神修炼之外专门探讨以身体为最终目标的修炼活动。在孔子后学中间,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更早的心为身之主的春秋以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发展了孔子所开辟的内向转向,在对于人之所是的探索中,仍然是将身体问题置于心灵问题的大框架之下来考虑的,这种状况对于孟子而言也是如此:“严格来说,孟子没有独立的‘养气’、‘践形’工夫,孟子说的‘养气’、‘践形’其实是心性修养所得的附产物。”[16](P11)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以往有学者对这种儒家式的身心观的考虑中,往往错误地将气作为一个具有某种骑墙性质的观念而独立于身心两者,并总设想存在一种东方式的“形—气—心”三元论:“如果我们将儒家身体观放在传统的工夫论或医家、武术家的理论架构来看,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反而是独特的,孟子的形—气—心一体论才是正常当理之谈。”[16](P4)这种假设在我们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从气观念的用法上看,气要么可被视为构成身体的质料,要么可被视为遍在万物的精气或者个人的某一方面的精神面貌,像“气,体之充也”这样论断,从上述不同角度均可得到解释,同时却也无需另外设定一种独立于心灵或者身体的“气”。从逻辑上看,此种三元论的思路仍然是出于近代西方式的认识论或者形而上学的预设,而比照其二元论理论结构建立起来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对于中国哲学的解释完全是多余的。二元论的思路是否适用于中国哲学或尚有讨论余地,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哲学中存在某种三元论之类的结构,笔者认为,解决身心问题的关键在于转换基本的理论立场,也就是完全放弃以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为基础的哲学讨论模式,将问题还原到此在的生存中,本实践问题而从修身或者说主体化的角度来考虑哲学的意义,这意味着将理论问题作为实践问题的一个推论而非相反。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于孟子在早期儒家“为己之学”问题域中地位的一些最为重要的思考的探查,孟子完全从人心中自由的价值意识出发确定人的本真之应是,而他的思考在我们看来正是一种真正的基于生存论的基础存在论分析——虽然这绝对不意味着孟子已经完全达到了20世纪某些哲学家的思想深度,但从其上述思路来看,孟子的思想的确达到了先秦哲学的最高峰。在结束本文之前,让我们回到一个熟悉而同时也相当棘手的问题上。《孟子·尽心上》开篇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常被视为孟子对于哲学层面上的“天人合一”的一个论说: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在早期儒家主张“天人有分”的意义上⑥,笔者认为天可以排除在儒家“为己之学”问题域的外面,那么在孟子这里,天又是如何回到这一问题域当中的呢?孟子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要求我们“知天”、“事天”呢?欲理解孟子的意思,我们可能需要“上下求索”。
向上回溯,郭店简书《物由望生》中明言:“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这里“知天”与“知人”相对,和而言之,仍然表达了来自孔子的那种对于天人之分,或者说取决于我们和不取决于我们的东西有明确觉察的意思。一同出土的简书《尊德义》中也有类似“知人所以知命”的说法,其中所谓“知人”与“知命”要表达的意思,大约还是希望强调,在天人有分的背景中,人既应该知道何为“可求”的、取决于自己的东西——“知人”,也应该知道何为“不可求”的、不取决于自己的东西——“知命”,而如果对于前者有所了解,便不会对后者有所挂怀。同样的意思也出现在《中庸》中:“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里“知人”、“知天”都是被视为修身的条件,而这些言语所要表达的应仍是对于取决于自己的东西和不取决于自己的东西之间差异的领会。探后言之,荀子也明确表述过继承自孔子的对于“可求”与“不可求”的伟大分判,所谓“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篇》)。他也以与孔子“知天命”般同样的冷静洞识断言道:“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篇》)这个“不求知天”恰恰与《物由望生》与《中庸》里的“知天”意思一样,都是在表明明天这种外在于人的客观限制,无论其如何运转都不会影响人专注于自身的道德完善的主张,因此专注于自身德性价值的完善的人,根本无需试图通过了解天的秘密而开展自身的伦理选择。孟子所谓“知天”的意思,应该也是处于同样的语义线索中。孟子不外仍是用这个词表达了与孔子所谓“知天命”、郭店简书和荀子讲“不求知天”相同的意思:知天人有分,且无论在个人还是人群的层面,我们都无需关注那些无益于人的自身道德完善的不可抗力;至于“事天”的意思就是,即使人间存在着人力所不能及的东西,也并不意味着就此便解除了人自身面对自己和他人时所应承担的责任、所应尽的努力——仁义乃是并行的,特别在涉及大的历史尺度和公共事务之时,更需要我们有孔子般“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勇气,“尽人事,听天命”、“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才是我们与天这超乎人力控制之外的客观限制打交道的应有心态。劳思光判断:“以人力所不能决定者归于‘天’,是《诗》、《书》中隐含之思想。日后在孟子学说中有一大进展,遂成为明确理论。”[5](P69)此种判断与孟子“知天”、“事天”的教导正相契合,而孟子的意思与早期儒家完全一致,都是在主张人将自身从天的控制下彻底解放出来之后,只有人自己才能为自己内在的人生价值担负起责任,这种责任可能包含社会责任的意味在内,但无论如何对于外在的那些根本上不受人力所控制的东西——无论个人利益还是社会责任的现实效果——则都是无需挂怀的。
孟子“知天”、“事天”的言论,还是在“天人有分”的前提下,强调我们应通过精神修炼之途径而达成理想人性,是希望在取决于人自己的修身与不取决于自己的命运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孟子最终希望告诉我们,无论个人的命运之寿夭如何,都不应该对于修身的努力有所影响,从主观上无论如何都应该努力使自己获得理想的人格品质以实现本真的生存,而这便是所谓“立命”了。从上述角度来说,孟子言论显然与“天人合一”之类的解说毫无关系,他所强调的不外是人对于自身价值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敢于担当这种责任的人,其改变自己的实践活动也就是所谓“事天”,而其中并没有将天或与天建立某种神秘联系作为个人修养目标的意思在内。这也就意味着,当年钱穆对于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因素的辨识,或许可能符合董仲舒之流汉儒的见解,但绝对与早期儒家对于修身与人性的基本立场毫无共同之处。
注:
①孟子言性,是“性善”还是“向善”,历来聚讼纷纭,笔者倾向于“向善”说,接近葛瑞汉的立场,视孟子论人性为人实现自身意义的完整过程(参见葛瑞汉:《孟子人性理论的背景》,江文思、安乐哲编:《孟子心性之学》,梁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类似于此,劳思光亦以为若将“性善”当做价值意识所在的“实然之始点”“自不可通”(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②劳思光对儒家“义命分立”的看法,也可与此处所论相互参照。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第102-105页。
③详细的研究状况可参考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中的有关部分。
④如郭沫若在《宋钘尹文遗著考》(《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中均持如此看法。
⑤参见匡钊:《早期儒家的德目划分》,《哲学研究》2014年第7期。该文以为孟子使与“思”有关的精神修炼工夫,成为了“养气”的一个部分或环节,并不正确,笔者在本文中主张此两类平行展开的工夫之分野依然存在。
⑥参见匡钊:《<论语>中所见孔子的天人观》,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编:《孔庙国子监论丛》(2012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第259-273页。
[1]匡钊.孔子对儒家“为己之学”的奠基[J].深圳大学学报,2012,(6).
[2]匡钊.简书《性自命出》中“道四术”探析[J].江汉论坛,2012,(7).
[3]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Cf.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oucault,edited by Gary Gutt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5.Arnold I. Davidson:Ethics as ascetics:Foucault,the history of ethics,and ancient thought.
[7]Martha C.Nussbaum:The Therapy of Desire: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359.
[8]Pierre Hadot: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Spiritual ExercisesfromSocratestoFoucault,Englishedition. translated by Michael Chase.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5.
[9]匡钊.早期儒家的德目划分[J].哲学研究,2014,(7).
[10]李景林.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279.
[11]杜正胜.形体、精气与魂魄:中国传统对“人”认识的形成[A].黄应贵.人观、意义与社会[C].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3.45.
[12]张岱年.管子书中的哲学范畴[J].管子学刊,1991,(3).
[1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J].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6.
[14]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18.
[15]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21.
[16]杨儒宾.儒家身体观[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
[责任编辑:来小乔]
On Mencius'Virtue Cultivation
KUANG Zhao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Beijing,100026)
Mencius’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discovery of virtue cultivation approaches made early Confucian thought rich and complete.Mencius used a series of roughly equivalent terms for virtue cultivation approaches,such as“cunxin(存心,retaining innate goodness)”,“qiu fangxin(求放心,finding lost innate goodness)”,and“yangxin(养心,nourishing the mind).As for“yangxin”,Mencius first clearly related it to“guayu(寡欲,reducing desires).This is relevant to his differentiation between“qiu zai wo zhe(求在我者,pursuit of what is inside ourselves)”and“qiu zai wai zhe(求在外者,pursuit of what is outside ourselves)”.Human desires are“qiu wu yi yu de(求无益于得者,what our efforts do not help get as they are outside ourselves)”.We need to restrain our desires by means of negative approaches in virtue cultivation.In Mencius’opinion,the purpose of“yangxin”is nothing more than showing“liangxin(良心,innate goodness),and not allowing it to be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or inner desires.This kind of mental state Mencius called“bu dong xin(不动心,not wavering in the heart)”.To reach this state,one need to take the approach of“zhiyan yangqi(知言养气,understanding words and cultivating virtues)”.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Mencius’understanding of virtue cultivation.It can be taken as a parallel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ultivation approaches,“zhiyan’,“jiyi(集义,promoting righteousness)”and“yangqi”.Mencius’argument of“zhitian(知天,knowing one’s destiny)”and“shitian(事天,following one’s destiny)”suggests that we can only achieve perfect human nature by way of virtue cultivation on the premise that we understand nature and human follow its own law.We need to draw a clear line between virtue cultivation and destiny as the former depends on ourselves while the latter does not.
virtue cultivation;zhiyan yangqi;jianxing(践形,embodiment of natural qualities)
B 222.5
A
1000-260X(2016)05-0042-11
2016-03-30
山东省孟子研究院课题“孟子的学说和心灵之道及公共生活:历史、语境和当代开展”
匡钊,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从事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