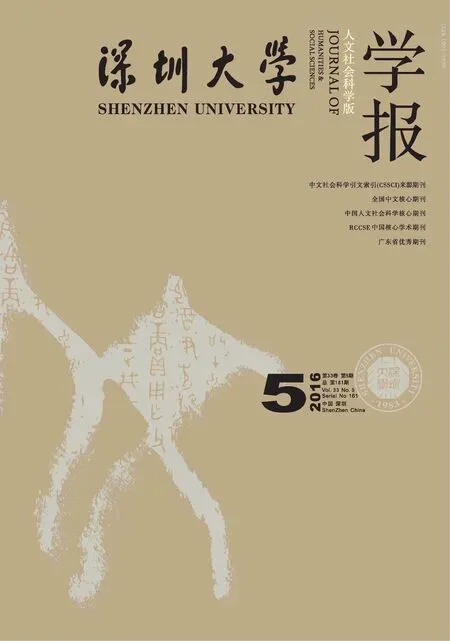后现代媒介文化批判的三个价值维度
曾一果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后现代媒介文化批判的三个价值维度
曾一果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西方社会的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的现代文化开始向后现代文化转变。在此过程中,电影、电视和其他新兴的大众传媒作为后现代社会的表征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学者批判性地思考了各种后现代媒体文化现象,有人赞美后现代主义颠覆了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和美学观念,承认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合理性;另外一种态度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毫无个性、缺乏深度、雷同化和复制化,完全被商业和大众传媒所操纵的消费文化。整体来看,在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中,纷繁复杂的后现代媒体文化现象表述了快乐、消费和意义的三个价值批判维度。
后现代主义;媒介文化;快乐;消费;意义
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社会文化发生新的转向,一些学者认为“新型社会”即将来临。丹尼尔·贝尔将新的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詹姆逊则用“晚期资本主义”表示后现代社会来临;波德里亚干脆用“消费社会”指称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强调的是工业生产,后工业化社会则不再注重生产,而是以信息和消费为主。与此相应的是,后现代社会产生了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它们贯穿在建筑、音乐、小说、美术、电影、电视和各种大众媒介之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概念已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化领域,借以描述与现代话语相对立的文化和艺术现象。不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纷争此起彼伏,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人认为“后现代”只不过是现代文化的发展,后现代主义的所有文化现象都在现代社会中发生过。如詹姆逊就把后现代文化看成是现代文化的高级阶段,“后现代主义至多不过是现代主义本身的又一个阶段……我将列举的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特征,都能在以前这种或那种现代主义里找到,而且有着充分的发展。”[1](P153)另一方面,利奥塔、波德里亚等人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作为现代主义文化的对立面出现,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现代主义的诞生。后现代主义是指一种与现代主义分裂而形成的另一种新的现代主义。”[2]后现代批评家默克罗比就认为“后现代”一词尤其适用于媒体社会,纷繁复杂的媒体文化现象是后现代社会的表征。“‘后现代性’这一名词在大众传媒研究中尤为有用,它推动了从文本分析转向研究不同传媒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不仅发生在全球性传播的拥有与控制这一层次上,而且也发生在不同艺术形态和效果相互作用的层次上,在广告、通俗歌曲、录像带和电视系列片中。后现代传媒批评已经意识到,快速检视大众传媒和徘徊于某个单一的图像以寻找它的特殊意义在理论上同等重要。”[3]欧美“新型社会”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后现代社会的媒体文化突显出娱乐、消费和意义的价值维度和文化立场。
一、作为“娱乐”的媒介文化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从20世纪70年代始涉足后现代主义问题,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性地审视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的文化转向问题,在他看来,这一后现代文化转向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的必然结果,根据马克思理论,詹姆逊将资本主义划分三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其中每个阶段都对应着相应的文化和艺术,分别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不是现代主义的中断,而是现代主义的高级阶段。詹姆逊比较了现代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诸多差别,例如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缺乏深度的“表象文化”,“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直接性或浅显性,一种在最刻板意义上的新的表面性,这或许是一切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的形式特征”[1](P160)。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仅仅有呈现物体本身的兴趣,并产生娱乐性的“快感”,才是后现代追求的目标,至于这些物体有没有意义,那不是艺术家关心的事,甚至呈现这些事物本身就是为了消解某种意义。
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用“快感”取代了现代主义的美学概念,“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中。后现代性使用的语言与现代性的语言也有很大区别。现代性的语言是私人化的,它沉溺于单一和癖好之中,它的流行和社会化是通过注解和经典化的过程实现的,而后现代性使用的语言是通用的、套话式的,具有非个人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称为媒体语言。”[4]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个人主体的消失,“个人风格越来越难以实现”,取而代之的是用拼贴、戏仿和反讽等手段组织起来的“混仿文化”。注重个人风格的现代主义作品强调主题的统一性,但是后现代主义作品没有统一主题,而是喜欢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拼凑在一起,从而获得一个“新的形象”,这种“混仿文化”充满着娱乐性。詹姆逊认为拼贴在现代主义时期并不鲜见,后现代主义者大量使用拼贴手法,说明了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文化生产者不能创造出新的风格,只有转向过去,模仿死去的风格。
表象化、肤浅化和主体的丧失在詹姆逊看来不仅是后现代主义的内容,而且代表了作品背后“世界本身的变化——现在变成一套文本或影像——也包括主体控制的变化。”[1](P163)“世界表象化”的标志是随处可见的图像影像或者说形象,而这些图像、影像都是由各种大众传媒所提供。詹姆逊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兴大众文化的一个特性就是“在技术上是先进的”,这些技术与大众文化有意识地相互联结而成为“媒体或新媒体导向的文化”,新媒体文化总的特点就是文化由“艺术”走向了“娱乐”。
今天大众文化在技术上的完美(在后现代“意象”中,高科技也被列为其内容,并且它也作为一个商品形式,指称了作为文化消费特有对象在技术上的新东西)似乎的确使所有这些商业艺术对象新的尊严更加合理,在这些对象中,阿多诺关于艺术的技术创新概念的一类漫画,现在与对更深的乌托邦智慧的认可紧密相连,而这个智慧恰恰是验证消费大众“品位”的。与此同时,阿多诺过去习惯作为“高雅文化”反对的东西——即现代主义本身——实质上消失,空下了场地,并且留下了现在某种普遍化文化的印象,这个文化逻辑现代描述了一个从“艺术”到“娱乐”的绵延,以取代更老的高雅的和低俗的价值对立面[5]。
电影、电视机里的图像,路边的巨幅广告牌,在詹姆逊看来并不显示现代主义者们所强调的深刻意义。在这个时代里,形象、影像和图像越来越多,但是它们仅仅是一种消费符号:“我们消费各种形象和符号,恰恰因为它们是形象和符号,而不管实用和价值的问题。这一点在通俗文化本身之中很明显,在其中,外表和风格(事物看上去的样子),以及嬉笑和玩笑,据说处于支配的地位,并以牺牲内容、实质和意义为代价。结果,品质(例如艺术价值、完善、严肃性、本真性、真实性、知识深度和有力的叙事),都有可能受到破坏。”[6](P225)“嬉笑”和“玩笑”取代了昔日的“崇高”、“严肃”,在媒体泛滥的时代,公众喜欢的只是媒体所营造的“景观”式的娱乐环境。
景观只是媒体泛滥的表现。媒体就其本质而言无疑是好的,因为它为传播提供了便利,但它有时也被推向了极端。统治者总是指责他们的媒体雇员工作不到位;更为常见的是,他们常常指责观者举止粗俗,日渐沉浸在媒体营造的欢乐氛围中,难以自拔[7]。
对于从“艺术”发展到“娱乐”的新媒介文化的观点,詹姆逊是不满意的。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立场,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总体历史框架下,重建具有主体性、深度性和战斗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甚至重建乌托邦的希望寄托于穷苦的“第三世界”和不受人关注的“边缘地区”。不过,他也肯定了新媒介文化的积极意义,指出伴随着文化工业和大众消费的兴起,本来属于少数精英所掌握的文化,在后现代社会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中,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已经消弭。“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8]
在影视、互联网等媒体发达的时代,对于文化的“娱乐化”现象,波兹曼的批判更加猛烈。在波兹曼看来,当代社会是一个“娱乐业时代”,由电视等媒体主导的世界只有“娱乐”,无关“艺术”与“文化”。波兹曼批评了麦克卢汉那种将新媒介视为旧媒介延伸和扩展的观点,认为电视“无法延伸和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他强调电视的根本特性就是用“娱乐”来吸引观众:“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9]当然,波兹曼的媒介批判是有点过激的,不过,他对媒体泛娱乐化现象的批判,对日益沉浸在电视、手机和网络中的人们而言,乃是一种警醒。
三、作为“消费”的媒介文化
资本主义由物质生产转向了大众消费,这是后现代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在詹姆逊看来,正是市场对于生活和文化的入侵,使得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的文化开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斯特里纳蒂认为,早在18世纪时,在英国这样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就对消费的需要变得比对生产的需要重要[6](P259)。商品消费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雷蒙·威廉斯曾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考察了“消费”(consume、consumption)一词的历史变化。他指出“消费”(consume)在早期英文的用法中都具有负面的意涵,指的是“摧毁、耗尽、浪费、用尽。”[10]这种涵义一直持续到19世纪;但是从18世纪开始,“消费”的涵义发生了一些变化,具有了中性化意涵,主要用来描述中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约翰·霍尔、玛丽·乔尼兹则将西方资本主义消费观念的变化分为三个时期:16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在他们看来,正是在19世纪时,生产逐渐被消费所代替,百货商店、商业广告和媒体宣传开始出现。约翰·霍尔认为,百货商店和广告都是劝服大众如何消费,百货商店不仅出售商品,而且也出售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广告则是试图抛弃新教伦理,取而代之以如下观念:“消费是做一个好的美国人的一部分。”[11]
绝大部分学者则将20世纪视为一个大规模消费的时代。伴随着城市发展,伴随着交通的改善,伴随着电影、电视和广告等大众传媒的发展,消费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丹尼尔·贝尔认为促进消费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技术革命,特别是大规模地使用家用电器(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12]。这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文化已经转向了“享乐主义”。
在关于消费文化的论述中,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巨大的。“他早期对消费社会及其客体系统的研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着消费商品的消费、展示以及使用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中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13]波德里亚理论结合了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消费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波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物体、符号和大众传媒所构成的消费社会,并且不断地增长和繁殖,丰富的物质商品包围了人。波德里亚认为这些商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特点,而且还具有符号价值——即风格、威信、豪华、权力等标识,丰富的商品不仅是用来满足基本需要,更重要的是代表某种地位、权力和风格。波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生产型社会,生产的东西是满足物质需要,但后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物质生产不单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更是为了满足欲望欲求。所以“机器曾是工业社会的标志。摆设则是后工业社会的标志。”[14](P116)人们购买商品并不是因为它有实用价值,而仅仅是将它们当作摆设和炫耀的符号。波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一切都可以变成摆设。家庭的装修、身体和汽车上各种装饰品,包括汽车本身都成了炫耀某种地位和权力的摆设。后现代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广告和大众传媒增加了人们对于物品符号价值的追求,艺术品本身的生产也是按照消费逻辑被生产出来,文化艺术和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其它商品没有本质区别:
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内容在此将只不过是内涵的、次要的功能。于是我们可以说,它像那台再也不作为工具而作为安逸或声誉要素而成为消费物品的洗衣机一样被消费。我们知道,其实,这台洗衣机再也没有特殊的存在意义,许多其它物品可以代替它——确切地说其中就包括文化。文化,当它朝着另一种论述滑去的时候,当它变得与其他物品同质(尽管在等级上更高一些)并可相互替代时,它就变成了消费物品[14](P112)。
媒介在后现代社会中自然是很重要的,波德里亚将后现代社会称为是“仿真”(simulation)社会——一个由广告、电视新闻等大众媒介所制造的符号社会,这个符号社会看起来像现实社会一样,甚至比现实社会还要真实完美,但这只是一个无法区别真伪、现实与非现实的超现实世界,波德里亚以广告媒介为例指出,广告的大众传播功能并非是出于真实内容,也不是出于真正的受众,而是出自其自主化媒介的逻辑本身。广告既不让人理解,也不让人学习,而是让人去希望,但是受众却将广告所构建的世界当成了真实世界。同样,电视新闻看起来好像都是真实的,其实这个世界也早已被编排和重新组织过。在波德里亚看来,越是“直播”这种看起来越真实的节目,实际上“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电视新闻和纪录片为了追逐真实而刻意制造一些虚假新闻。关于越南战争的报道、关于水门事件的所谓“真实报道”掩盖了“真正的事实”,因为所报道的事件其实就没有发生过,而是媒体图像所提供的符号“真实”变成人们消费的一个过程。
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或者说,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晕眩,因为亚马逊平原的中心、真实的中心、激情的中心、战争的中心,这个作为大众交流的几何地点并令人头晕目眩的、令人伤感的“中心”。确切地说,它们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地方。那是激情和事件的寓意符号。符号令人产生安全感[14](P12)。
对于波德里亚来说,现代世界是由各种各样媒介符号构成的“仿真世界”——一个缺乏深度、缺乏自我认同和分裂的超现实世界。对于这个超现实世界,大众媒介要负主要责任,斯特里纳蒂直截了当地指出,“后现代主义和某些长期存在的、有关消费主义与媒介饱和之规模与效果的观念有着联系”[6](P258)。
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明显变得更加重要。大众传播的现代形式的出现,以及相关联系的通俗媒介文化的激增,因而对于后现代理论的解释框架变得很重要……有人论证说,世界将日益由媒介屏幕、电脑游戏、个人立体声系统、广告、主题公园、购物中心、“虚构资本”或信用——它们都是通往后现代通俗文化之趋势的重要部分[6](P259)。
英国文化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大众消费的是符号和影像,正是各种媒介符号和影像为人们提供了快乐、欲望和梦想。他指出在19世纪中期,在巴黎等城市,随处可见的大型游乐场、主题公园、购物中心、街道上大屏幕广告以及新兴的社交媒体,为大众营造、建构了新的消费空间和场所,同时为大众制造了快乐、欲望和梦想。除了精心的后现代景观的营造,费瑟斯通还提到一种后现代消费社会里出现的“新型文化媒介人”,这些文化媒介人往往“专门从事符号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工作”,例如广告人、公共关系专家、广播和电视制片人和记者等等。这些人能够很快适应后现代社会,着迷于强调新体验的消费社会环境,在他看来,这些新型文化媒介人为消弭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距离做出了不小贡献。像詹姆逊一样,费瑟斯通也强调在后现代社会中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距离日渐消弭,艺术不断侵入日常生活之中,反过来,日常生活也出现了审美化趋向。“日常生活审美呈现”是因为充斥在生活中的各种符号、影像对社会的特殊构建正在逐渐改变人们的“现实感受”:
通过媒体与陈列的广告宣传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城市建筑景观与表现,进行影像生产的商业中心就必然通过影像来经常地再生产人们的欲望。因此,绝不能把消费社会仅仅看作是占有主导地位的物欲主义的释放,因为它还使人们面对无数梦幻般的、向人们叙说着欲望的、是现实审美幻觉和非现实化的影像。鲍德里亚、詹明信所继承的就是这个方面。他们强调影像在消费社会所起的新的核心作用,也因此赋予了文化以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15](P99)。
无处不在的媒介符号和影像充斥了生活,模糊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导致了“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费瑟斯通并不像波德里亚那么悲观,他认为大众媒介的日益发达是有好处的。他说如果站在全球层次思考,就会发现原来在西方世界中不受重视的第三世界文化借助于新兴的大众媒介,扩大自己的力量[15](P205)。
三、作为“意义”的媒介文化
詹姆逊和波德里亚都严厉批判了媒介符号泛滥的后现代社会,他们认为这是个意义过剩和意义匮乏同时存在的社会,“意义的丧失”成为后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现象。不过,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强调新兴的媒介文化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丰富内涵,需要从媒介符号学的角度加以重新认识。
费斯克批评了詹姆逊和波德里亚的“媒介商品论”,提出要重视媒介文化产品本身是一个“意义系统”。例如在谈到电视这种媒介文化时,他强调应该把电视及其节目“看成是意义的潜在体,而不是把它们看成商品。”[16](P21)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将符号学、结构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研究等理论结合起来,“来解释电视如何(或者力图如何)生产为社会主流利益服务的意义,如何把这些意义传播到构成其观众的各社会群体之中”[16](P6)。费斯克将电视及其节目都看成是一个大的媒介文本,透过这个媒介文本,他认为能够发掘出隐藏在文本深处的意义,以及控制意义的意识形态机制。
费斯克对新兴媒介与大众文化持有乐观态度,他认为大众在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中并未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那样完全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具有一定的能动性。费斯克接受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大众文化一直是权力关系的一部分,它总是在宰制与被宰制之间、在权力以及对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抵抗或规避之间、在军事战略和游击战术之间,显露出持续斗争的痕迹。”[17]费斯克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合理性,视大众文化为社会进步的力量,他认为具有主动性的大众,凭借自己的力量对抗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大众文化显示了活力和创造力,体现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当然,在费斯克这里,大众对于社会的抵抗并非是直接的,往往是隐藏在其日常生活行为中,例如另类打扮、逃学和逛商场不买衣服等等,这些都被费斯克视为一种抗争形式。而这样一种斗争在费斯克看来是一种微观政治,代表了进步的力量,他说:“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多样而散乱的。最微观的微观政治是幻想的内在世界(见《解读大众》,第5b章)。将幻想保留在内在空间,处于意识形态的殖民势力范围之内,具有想象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行为的能力,等等,这些并不一定导致无论是在微观或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行动。但是,这些却建构了任何行动的发生所必需的基础。”[16](P198-199)
当然,费斯克没有完全忽视当代媒介文化产品的商业特征。在《理解大众文化》、《电视文化》等著述中,他讨论了大众媒介与商业社会的关系,进而提出了“文化经济”和“金融经济”的概念,他认为从商品的角度出发,大众文化自然是一种工业化文化,这种工业化文化是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二者共同的商品”——金融经济在整个文化商品的流通中控制的是财富,而文化负责的是意义的“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费斯克认为,光靠金融经济不能很好地描述文化商品,如若很好地描述文化商品的特征,还必须依靠“文化经济”,因为文化产品虽然也和经济有关,但主要是与意义密切关联:
在文化经济中,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当然,主要基于金融经济的商品在文化经济中也能发挥作用,消费者在相似的商品中作出选择时,通常不是比较其使用价值(尽管给消费者提供建议的人注重使用价值),而是比较其文化价值;从诸多商品中作出一种选择,就成了消费者对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的选择[16](P448)。
“金融经济”控制着财富,文化经济控制意义、快乐和身份。费斯克认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在文化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流通的过程中是平行的,它们虽然分离,但却相互联系和作用。金融经济主要管生产和发行,而文化经济则主要由观众来承担,并且在文化经济中,作为生产者的观众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按照费斯克的理解,这是因为大众在金融经济中被支配的地位在文化经济中已经不复存在,文化经济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既然不需要财富,而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又是难以控制的,观众便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人们想消费多少都可以,想消费什么都可以,无须受购买力的限制。”譬如在家里看电视,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电视节目,也可以选择不看电视。当然,像凯尔纳等人所批评的那样,费斯克的文化研究夸大了大众的能动性和反叛性。
而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则提出用“媒介建构主义理论”去理解后现代媒介文化。格罗斯伯格指出今天的媒介越来越重要,人们是通过“媒介认识自己和历史”,媒介不仅建构世界,反过来,媒介自身也不断被建构:“建构是媒介的主要行为:挣钱、形塑日常生活、建构意义和身份认同、创建真实、建构行为、建构历史。在这些活动中,媒介自己也被建构了,我们所说的媒介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媒介[18](P7)。要理解媒介与世界之间是如何互相建构,就有必要将媒介放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加以考察。
作为詹姆斯·凯瑞的弟子,格罗斯伯格在继承凯瑞的两种传播观念——传递观和仪式观的基础上将传播的模式分为了传递模式和文化模式两种。他强调了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传播的文化模式旨在将传播看成共享意义和空间的建构过程,这使得人们能够和谐相处。传播的线性模式是将信息孤立出来单纯地从一地(人)传递到另一地(人),文化模式则强调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意义共享的世界里,并且认同这些意义。没有这种认同,传播就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传播都仅仅是在复制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18](P21-22)但格罗斯伯格也强调应该不要将传递模式和文化模式截然对立,而要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媒介传播影响力”。他认为自己是商业化和本地化的大众传媒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我们同时也是‘摇滚的一代’,这一代年轻人的青春凝聚成共同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不是通过分享经历而是通过分享流行文化来完成的。我们宣称这种文化是我们自己的,尽管它是被商业生产出来的。我们是完整地浸泡在媒介文化中的第一代人。对于我们来说,媒介是文化的主流机制……”[18](序P10)各种媒介所产生的意义本身就是“人类文化自己生产的”。因而要了解和认识各种媒介文化,不仅要从自身的生活出发去理解,而且也是为了理解自己。
四、结语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媒体的电影、电视、互联网及其他新兴的媒介贯穿了后现代的文化逻辑和精神,使艺术不再陌生化,审美变得日常生活化,体验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后现代媒介文化中的影像化、信息化、符号化的视觉表征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媒介文化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在后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作为娱乐和消费的媒体,还是作为意义展现的媒介,毋庸置疑,媒体及其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理解媒体及其文化,这是为了了解人类自身,也是为了认知人类自身建构的这个世界。如格罗斯伯格所言:“我们必须想法设法把‘媒介建构’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整合在一起。我们所有人都面临一个挑战:把握媒介的重要性,把握我们关于媒介的知识——媒介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媒介如何变成一种力量?利用这些知识,我们能够认知我们自己建构的这个世界。”[18](P481)
[1][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M].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9.
[3][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9.
[4][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译者序言[M].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
[5][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晚期马克主义[M].李永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5-156.
[6][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M].梁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8][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62.
[9][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4.
[10][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3.65.
[11][美]约翰·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周晓虹,李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1.
[1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14.
[13][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绪论:千年末的波德里亚[M].陈维珍,陈明达,王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14][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5][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6][美]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7][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1.
[18][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M].祁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来小乔】
【】【】
Three Value Dimensions of the Postmodern Media Cultural Criticism
ZENG Yi-guo
(Phoenix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uzhou University,Suzhou,Jiangsu,215123)
Culture in Western countries changed greatly during their transition to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ince 1960s:Western modern culture began to transform into postmodern culture.In this process,the film,television and other emerging mass media a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ostmodern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Many scholars critically think about all kinds of postmodern media cultural phenomenon.Some celebrate that postmodernism subverts the artistic and aesthetic ideas of modernism and recognize the rationality of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Sometake a different attitude,believing postmodern culture is nothing more than a clutter of similar or identical products which are very shallow and have no personality whatsoever.It is a consumer culture completely manipulated by commerce and mass media.On the whole,the study of postmodernism reveals the complex postmodern media cultural phenomenon take on three value dimensions of happiness,consumption and significance.
postmodernism;media culture;happiness;consumption;significance
G 112
A
1000-260X(2016)05-0006-06
2016-06-1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14FXW008)
曾一果,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媒介文化、城市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