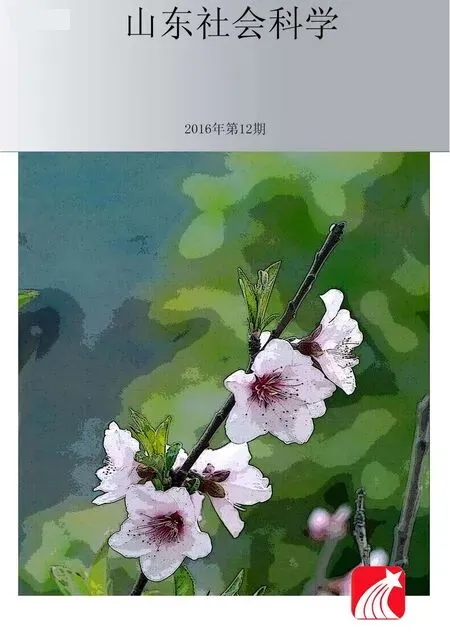同性恋身份、“橱柜”政治与消费主义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同性恋身份、“橱柜”政治与消费主义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强制性异性恋的性政权不仅制造了恐同症主体,还导致了同性恋者的自我憎恶。反规范化政治将身份理解为管控性欲与差异的手段,认为排他性身份将产生本质化效应,从而难以抓住性政治的丰富内涵。由于过分强调同性恋身份会抑制其他身份,因此以特定身份类别为中心的对抗性政治在挑战支配性性政体的过程中仅是有限的策略。“橱柜”意义的竞争性阐释与“石墙骚乱”的神话反映出身份政治的复杂性。石墙骚乱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它是现代同性恋运动之结果,而非开端。同性恋消费主义与身份政治、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它具有强化同性恋身份与共同体的作用,但个体性的私人消费无法取代进取性的集体政治。
同性恋;“橱柜”;性政治;石墙骚乱;消费主义
性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它还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塑造与制约。在特定的社会里,关于性行为或感知的定义、性道德的合法性判断以及相应规范的制定等,都充满了政治色彩*Steven Seidman, “Queer-Ing Sociology, Sociologizing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12 (July, 1994), pp. 166-177.。在历史上,导致同性恋的制度性歧视和社会不可见性的重要机制是性类别(sexual categories)的产生。持社会建构主义立场的研究者认为,身份并非本质性自我的反映,而是社会与政治过程的结果。作为一种医学范畴的同性恋身份是19世纪末的发明,同性恋不能被看作是一种跨越历史的身份,它只有在现代西方社会才成为一种独特的心理和生理类别。在很多非西方社会里,同性恋并没有遭遇相似的类别化、污名化、病理化和罪化。在同性恋从“个体性病理行为”转向“群体性亚文化”的过程中,身份政治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同性恋身份也成为政治动员和话语竞争的核心。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石墙骚乱”(Stonewall riots)以来,西方同性恋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发生变化,它从一种“越轨的亚文化”进而成为“性少数族群”和“社会运动共同体”。现代西方的诸种肯定同性恋权益的理论和话语在自然化(naturalize)和正常化(normalize)同性恋主体、推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等方面起着促进作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同性恋关系、实践和理论的深入发展,有必要重新审视与反思身份政治、“橱柜”(closet)结构以及同性恋消费主义。本文主要探讨“后石墙骚乱”时代同性恋身份政治的得失、同性恋的压迫性结构(“橱柜”)、“石墙骚乱”的神话制造以及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下的同性恋消费主义。
一、身份政治及其抵抗策略
“性政权”(sexual regime)的诞生是现代西方社会的重要政治事件,它是一个充满性意义、话语和实践的场域,与所处社会的制度、文化和社会运动密切关联。符号统治的正当性源自将人为的歧视塑造成自然化特征,并与促使其产生的各种条件相结合而获得客观性基础,从而成为理所当然的接受形式*[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本质主义的性态理论为宰制性的性政权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它视性态为根本性的,由此启动了一系列性差异的规范化进程,性差异被简化为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本质差异,与种族、阶级、性别、能力、年龄、教育、宗教、品位、性格、生命历程以及国籍等因素无关。性欲、性身份成为自我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同性恋被视为病理性的欲望,因而其自我也是病态的、倒错的。在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所说的“强制性异性恋”的社会权力结构中*参见Adrienn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in Ann Snitow,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 (ed),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异性恋优于同性恋,并且被视为更自然、更健康和更正常。异性恋统制不仅创造了恐同症(homophobia)主体,还导致“自我憎恶的同性恋者”。在同性恋的医学话语将同性恋病理化的同时,它也逐渐使同性恋成为公共话题。正是在污名化与脱敏化并存的社会进程中,同性恋者逐渐形成了共同体意识和亚文化,并最终产生了以正当化自身为目标的身份政治。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同性恋身份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是对社会压制作出的反应。因此,传统的性身份产生了悖谬的社会性后果:它为同性恋者谈论自身以及寻求权益和包容提供了一套话语机制,但同时也成为异性恋统制和恐同症话语的基础。与之相应地,性本质的观念也具有类似的效应:它一方面使同性恋个体被病理化、污名化;另一方面,也使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能够进行抵制与反抗。直到20世纪60年代,尽管同性恋理论和同性恋运动出现了激进化倾向,但是很少有人对同性恋作为一种自然特质或自我身份之核心标志的观点提出质疑。许多女同性恋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同性恋解放理论通过主张同性恋的自然属性和正常性试图推翻居于支配地位的强制性异性恋的秩序。同时,反同性恋暴力的社会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父权制与性别关系。这一时期的同性恋活动家主要关注恐同症,而不是制度化的异性恋主义,这导致同性恋在性别关系的具体表达中变得不可见*Valerie Jenness and Kendal Broad, “Antiviolence Activism and the (In) Visibility of Gender in the Gay/Lesbian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Gender and Society, Vol. 8 (September 1994), pp. 402-423.。
20世纪90年代以后,同性恋研究开始反思身份政治。人们逐渐意识到,以既定身份类别为中心的对抗性政治在挑战支配性性政体的过程中仅是一种有限的策略,因为过于强调同性恋身份会抑制其他身份类别,如性别、种族、国籍和阶级等。即使普遍存在某种特定的性实践,但是“同性恋”与“异性恋”这样的范畴也并没有描述跨历史的文化形式,因为同样的性实践在不同的社会里可能意味着颇为不同的事物。也就是说,关于身份的自我描述与呈现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与冲突,同性恋共同体内部亦会产生各种形式的“身份战争”,即各类宣称“真实的”群体身份彼此相互竞争*Daniel Ortiz, “Creating Controversy: Essenti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Gay Identity”, in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79(Octember 1993), p. 1856.,围绕着“gay”这个词本身产生的争议就反映出这种现实状况。同性恋政治寻求终结对同性恋社群的歧视、污名与偏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些研究者主张同性恋身份的同化与整合,认为这将有助于增加同性恋者的选择,并通过允许同性恋者进入公共领域以重构公共-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而倡导身份多样性与独特性的学者则认为,同化将导致同质化、抹杀独特的同性恋感受性,而这种感受性正是亚文化和创新之源泉。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身份与文化的同化模式低估了恐同症和异性恋主义对国家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同化能够产生的解放效果仅是幻象,其结果不过是“虚拟的平等”*Amin Ghaziani, “Post-Gay Colle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Social Problems, Vol.58 (February 2011), p. 103.。身份政治的反思结果是反对简单的、总体化的身份描述,摒弃追求一致性的、整体性的身份和群体,而转向更加具体、复杂和微妙的共同体与文化观。
大体而言,由于受到社会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种族与族群研究、女性主义以及酷儿理论的影响,当代西方学界关于同性恋身份与文化的研究在探讨性身份和性意义之建构性的同时,也逐渐解构了身份与文化的恒定性和不同社会类别的稳定性,并质疑身份共同体的实质与意义。也即,性身份的意义随着历史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主体性在历史和政治环境中是持续不断地进行创造和被型塑的。因此,文化身份也必然是多重的和交叠的,文化、身份与社会类别都是流动的和不稳定的,它们在矛盾与冲突中不断地发展和创生。这种反身性的理论视角对本质主义的传统身份观构成了挑战,它强调“文化的各个维度,诸如价值观、共享的语言、地理、主体观念或文化系统等,都不是普遍性的、决定性的或静止不动的。文化的各类人工物、主体性与身份则更是破碎化的和分化的”*Janice Irvine, “A Place in the Rainbow: Theorizing Lesbian and Gay Cultur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12 (July 1994), pp. 241-242.。因此,将同性恋身份作为建构同性恋共同体和政治动员之基础的观念,可能仅是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经验或立场,“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这样的分类束缚了同性恋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同性恋群体内部也存在分化和身份的不一致感。如同历史与现实中的异性恋者通过排他性地确立“越轨的”、“非正常的”和“非自然的”同性恋群体以维持社会规范并获得安全感,同性恋共同体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规范化、正常化,从而生产新的规范、制造“主流”。也就是说,同性恋共同体内部也在不断地隔离与污名化“他者中的他者”,以使不断细分的小群体获得某种“统一的”和“正常的”性身份,这些排他性的对象和他者包括MB(Money Boy,即“金钱男孩”)、娈童、S/M(施虐/受虐)、双性恋和乱性等。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主体是一种张力的存在,性别身份从本质上而言是展演性的。若要确立和维持同性恋身份的一致性,那么异性恋作为其对立面则必须处在被否定和拒斥的位置,摒弃成为政治上的必要。然而,这种原本试图达成整合的文化实践和策略却起到了弱化的后果,它错误地将异性恋身份视为单一性的,并因而错失拒斥异性恋主义的政治机会*[美]朱迪斯·巴特勒 :《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144-145页。。传统的身份政治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无法为新的政治空间提供可能性,也无法继续发挥解放功能,相反却成为一种自我束缚。身份总是多重的、复合的和构成性的。在通常情况下,特定的身份建构都是任意的、不稳定的和排他性的,而身份政治“起着定义自我和行为之模板的功能,它排除了勾画一个人的自我、身体、欲望、行动和社会关系的诸多可能方式”*Steven Seidman, “Queer-Ing Sociology, Sociologizing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12 (July 1994), p. 173.。当然,也不排除杰弗里·威克斯(Jeffrey Weeks)所说的情况,即同性恋身份有时也可能是“必要的虚构”*Jeffrey Weeks, Against Nature: Essays in History, Sexua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Rivers Oram, 1991, p. viii.或是“策略性的本质主义”。在酷儿理论看来,以身份范畴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一整套知识系统并未能表达和揭示关于性自我的真相,它掩盖了权力和知识之间的芜杂关系,使西方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生活进一步结构化,并通过全球化蔓延到非西方世界。但是,酷儿理论并没有摒弃作为知识和政治类别的身份,也无意彻底解构身份与文化,它强调建构性的意义和内在的矛盾性,从而使这种“意义和政治角色处于永远开放和竞争性的姿态”*Steven Seidman, “Queer-Ing Sociology, Sociologizing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12 (July 1994), p. 173.。
近些年来,女性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和酷儿理论家倡导“反规范化”(anti-normalization)的政治,他们将“身份”理解为管控性欲与差异的手段,认为排他性身份会产生本质化效应,而且对身份的聚焦难以抓住性政治的丰富内涵。规范性政治承认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各种规范与常态,而反规范性政治则挑战支配性的性道德和性常态,并试图去中心化。反规范性的理论家不仅谈论性少数族群的正常化,也设法取消和废除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对立,因为“只要存在将整个世界在性方面划分成洁净与不洁这样的话语并继续支配着欲望,那么性压迫就会持续存在”*Chet Meeks, “Civil Society and the Sexu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Vo. 19(November 2001), p. 330.。性少数族群并不是有着明确边界和固定成员的群体,它是开放的,其性取向的构成也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多样。异性恋社会采用一系列范畴、标签和身份使性少数族群异常化、病理化和罪化,同性恋者最初在进行抵制时挪用了这些术语,以使欲望自然化、合法化,这便是“逆向话语”的运作机制。因此,性话语原始的政治意图可能被逆转,被污名化者在保留原身份标签的前提下能够颠倒附着在该身份上的价值观,以对抗性政权。但是,从根本上而言这仍是一种规范性的性政权对抗方式,因为它基于这样的假定:性身份是自我的关键性表征,同性恋者可以利用这种性征创造和实现新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
对此,切特·米克斯(Chet Meeks)区分了两种抵抗性压迫的方式:一种是反应性(reactive)抵抗,它试图正常化某些被污名化的群体;另一种是生成性(productive)抵抗,它解构那些僵化的、狭隘的和同一的欲望思考方式,打破欲望与身份之间的“天然联系”,以彻底转变性愉悦的经验*Chet Meeks, “Civil Society and the Sexu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Vo. 19(November 2001), p. 328.。简言之,性压迫的反应性抵抗采取规范化的方式,生成性抵抗则以反规范化为特征。这两者也可以分别被称作传统的“同性恋身份政治”和反规范化的“酷儿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情境中,规范化与反规范化是相对而言的。在米克斯看来,规范化策略并没有消解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与之相对的是,酷儿政治并不试图从与异性恋的对立中寻求差异,而是从自身的共同体内部确证差异,其目标是“使性领域保持多重的、流动的、去二元化的和处于不断改变中的差异”*Chet Meeks, “Civil Society and the Sexu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Vo. 19(November 2001), p. 339.。在身份政治的早期发展阶段,规范化的抵抗政治使同性恋群体获得了诸多权益,如婚姻权、抚养权与继承权等,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规范化政治将性差异简化为性形式,忽略了由于其他社会差异和不平等的“轴心”(如性别、阶级、种族等)而产生的不同经验,尤其是忽略了各种经验轴心之间的交互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多重压迫。同时,规范化策略并没有彻底挑战“性身份作为自我之表征形式”的观念,相反,它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观念。而反规范化政治则认为,性政治不该仅是试图寻求性少数族群的合法化,而应彻底改造“性景观”。其目的不是为了抹除差异,而恰恰是为了生成差异,它包括不同的性实践、欲望、亚文化、身份与社会关系模式的不断增殖。
二、“橱柜”政治与“石墙骚乱”的神话
至少从17世纪以来,西方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传统,即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个体逃离欧美主流社会,以摆脱异性恋主义的压制。一些零散的证据表明,19世纪前往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探险者、殖民地官员等,其中有相当高比例的同性恋者。到了20世纪,不少同性恋者进入人类学领域,如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和露丝·本尼迪克特是同性恋者,玛格丽特·米德和埃文斯-普理查德是双性恋者。自从露丝·本尼迪克特之后,美国人类学协会(AAA)出现了很多女同性恋者*Walter Williams, “Being Gay and Doing Research on Homosexuality in Non-Western Cultures”, in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Vol. 30(May 1993), p. 115.。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启了欧洲新的性自由和宽松的氛围,同性恋权益运动和亚文化蓬勃地发展壮大。这种新气象延续了19世纪末以来医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也继承了战前深嵌于同性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同性恋解放运动凭借颠覆性的文化创造出自己的准则,“语言、服装、俱乐部、勾搭技巧构成同性恋行为认同的基础,也是同性恋解放的基础”*[法]弗洛朗斯·塔玛涅 :《欧洲同性恋史:柏林、伦敦、巴黎 1919—1939》,周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17页。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大都市进一步增强了性选择的多样化、社会宽容度以及同性恋亚文化的可见度,相应地,性规范和性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这为争取社会支持、组织动员和社会运动提供了大众基础*Steven Seidman, “Transfiguring Sexual Identity: AIDS &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Social Text, No. 19/20(Autumn 1988), p. 187.。
自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以来,性取向被塑造成个体内在的本质属性。在这种意识形态下,隐匿的同性恋身份是制度性暴政的必然结果,“橱柜”也成为同性恋压迫的结构。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是西方国家压制同性恋最为严重的时期。当时大多数同性恋者被迫过着地下生活,“橱柜”的观念就是该时期产生的。“后石墙骚乱”时代的同性恋者试图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说的“受损的身份”转向具有正当性的身份,使同性恋身份“去自然化”和“去性化”*Cheshire Calhoun, “Denaturalizing and Desexualizing Lesbian and Gay Identity”, in Virginia Law Review, Vol.79 (Octomber 1993), pp. 1859-1875.。社会建构主义试图解构本质主义的同性恋历史,同性恋社群也出现了肯定性政治,并致力于进行共同体建设、个人赋权和各种地方性的斗争。然而,在现代西方的同性恋历史上,压制与反抗、束缚与解放从来没有彻底分离过。“石墙骚乱”很快遭致第一波反同性恋运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艾滋病之后又掀起第二波反同性恋高潮。在西方社会,引起同性恋恐慌的因素错综复杂,通常包括宗教、现代性和性别文化规范等。此外,战争、经济衰退、艾滋病等非常规性的重大事件也会引起同性恋恐慌,这些突发性事件触发了常规性的结构性要素,同时伴随着产生许多新的、微妙的压制手段。
根据阿敏·贾兹尼(Amin Ghaziani)的观点,同性恋的橱柜政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Amin Ghaziani, “Post-Gay Colle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Social Problems, Vol. 58(February 2011), pp. 102-103.:第一阶段是二战前的“橱柜时代”,其基本特征是向亲朋好友隐瞒自己的性取向(隐藏)、断绝与同性恋社交网络的联系,同性恋个体感到羞耻、愧疚(孤立),将社会对同性恋的观点内化(恐惧),过着表里不一的双重生活;第二阶段是“出柜时代”,其时间大致是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尤其是1969年的石墙骚乱之后。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随着公众对同性恋接受程度的提高,同性恋的可见度也随之增加,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向周围的人们甚至父母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他们积极建构同性恋的社交网络,并感到“同性恋是美好的”;第三阶段则是新世纪以来的“后同性恋时代”,其特征是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融入主流社会,尽管其内部存在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意味着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等的英文缩写)社群内部不同的性生活方式,并且同化与多样化在同性恋生活中产生了持续的张力。在当代的同性恋话语里,出柜成为一种“根本性的政治行为”*Mark Blasius, “An Ethos of Lesbian and Gay Existence”, in Political Theory, Vol.20 (November 1992), p. 655.,而它也是提高同性恋主体和共同体可见性的重要前提。出柜不仅仅是向他人披露自我的性身份,它还可能是伴随终身的“成为”(becoming)的过程,因为同性恋者将不断地面对新的情境与他人,需要不断地在互动中创造作为同性恋身份的意义。
尽管人们对橱柜政治存在诸多争论,如同性恋活动家号召自我认同良好的同性恋者“现身”(coming out)以表达主体性,而酷儿左派的理论家则批判这种出柜策略,他们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出柜的政治意义,认为“橱柜”只是同性恋者自我设限的神话。由于同性恋身份政治在初始确实具有解放和增权的效果,但它很快便触及其局限性。与这种悖谬性的身份政治相关联的一个著名实例是“石墙骚乱”的神话制造。事实上,石墙骚乱并非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同性恋骚乱,它本身也并不具有内在的特殊纪念性,那么为何石墙骚乱能够成为美国同性恋者的集体记忆并被符号化为现代同性恋运动的开端呢?它之所以能够获得历史性的纪念意义,是因为它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满足了两个必要条件:其一,同性恋活动家认为该事件具有纪念价值;其二,特定的情境能够动员甚至创造用于纪念的各种媒介,从而使它符合这样的定义*Elizabeth Armstrong and Suzanna Crage, “Movements and Memory: The Making of the Stonewall Myth”,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1(October 2006), pp. 724-751.。在石墙骚乱之前,纽约以及全美各地就已经掀起了同性恋解放运动,正是由于这些早期的铺垫才使同性恋活动家能够充分意识到并抓住这个机会发起纪念活动、呈现并建构集体记忆和同性恋运动的创始神话。此后,通过同性恋骄傲大游行(Gay Pride Parade)这样的年度纪念仪式,石墙骚乱成功地被制度化,它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流传到世界各地,这也离不开同性恋活动家的精心策划、与媒体之间的默契配合以及文化权力的施展等。“星星之火”的石墙骚乱“点燃”了现代同性恋运动并传播到全美乃至世界各地,形成了燎原之势,它成功地被塑造成美国历史上的同性恋者第一次大规模地反抗制度性压迫的象征,也因此被视为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滥觞。现代同性恋运动的“野火神话”由此诞生,石墙骚乱的叙事也成为同性恋政治的常识。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石墙骚乱的神话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成就,而不是对其起源的解释。石墙骚乱的叙事在政治上对当时的同性恋运动是有裨益的,但它同时也阻碍了同性恋运动进一步动员、发展以及对它的学术性阐释。因为这种叙事隐藏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同性恋解放运动其实在石墙骚乱之前就已经存在。当时既有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是同性恋活动家认识到石墙骚乱事件具有政治潜质的重要前提。倘若缺乏激进的既有政治取向,这些活动家不会作出升级冲突势态的反应,不会创造或传播关于石墙骚乱之重要性的宏大叙事,也不会筹划纪念性的仪式*Elizabeth Armstrong and Suzanna Crage, “Movements and Memory: The Making of the Stonewall Myth”,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1(October 2006), p. 743.。此外,关于石墙骚乱的神话还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认为同性恋运动是自发的、不可避免地,它毋需经由充分的社会动员。然而,同性恋运动显然并非像野火燎原那样是自发性的,它是由众多的同性恋共同体和活动家积极争取、塑造和发动的结果。有些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意识到石墙骚乱的历史问题,他们提出各种质疑,试图解构这种胜利叙事。例如,有些同性恋活动家认为1965年发生在费城的“年度纪念”(Annual Reminder)才是当代同性恋运动的起源*Elizabeth Armstrong and Suzanna Crage, “Movements and Memory: The Making of the Stonewall Myth”,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1(October 2006), p. 743.。但是,这些异质性的声音却通常被学术圈内外的主流话语所堙没。
三、同性恋消费主义与身份解放
性态既是文化和话语实践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作为一种管控性的制度设置,性规范不仅渗透在现代世界的各种社会组织里,也与其他社会设置(如资本主义、父权制、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等)协调一致地运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性身份的可见性还通过商品化表现出来*Rosemary Hennessy, “Visibility in Commodity Culture”, in Cultural Critique, Vol.29 (Winter 1994-1995), p. 70.。在同性恋词汇中,“可见性”(visibility)是一个斗争性的术语,它是政治话语等复杂的社会条件之后果。可见性不仅是经验性的身体展示,也是构成身份的各种知识、话语、意义和认知模式的展示。在现代社会中,酷儿全球化主要通过情色观光业、同性恋媒体的消费以及社会流动而实现。资本主义商品化的物质过程并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它还使西方社会的同性恋身份、亚文化和共同体得以可能。资本主义发明了对劳动力进行社会控制的各种方法,工业资本家还创造了各种手段以促进大众消费。这种以大众消费为目标的广告宣传催生了身份的同质性,生产者和广告商为了制造需求、销售商品而竭力抹除身份差异。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数十年的移民浪潮,美国的广告业试图消除或超越基于国籍和族群的身份差异,以创造更加广阔的大众消费品市场,这个过程也促进了少数族群的美国化。同性恋市场的扩大与同性恋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Alexandra Chasin, “Interpenetrations: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y/Lesbian Niche Market and the Gay/Lesbian Political Movement”, in Cultural Critique, No. 44(Winter 2000), p. 145.。出版商和广告机构是文化同化和消费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性恋出版机构的扩张有力地推动了同性恋政治和社会运动。20世纪70年代,也即在石墙骚乱之后,新的同性恋书店、出版社和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它们帮助传播同性恋政治活动的各种信息,包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运动策略等,也记录了同性恋运动的风起云涌和兴衰成败。同时,资本主义市场也为塑造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同性恋身份创造了新的机会。
同性恋运动和同性恋市场生产、复制着同性恋亚文化,以身份为基础的同性恋运动和市场活动在个体和群体的层面上促进了统一性。在市场的作用下,同性恋身份与共同体得到了有效的巩固与强化。20世纪90年代,市场成为同性恋个体最容易获得、也最有效的身份塑造机制,身份群体成为政治权利运动的基础,资本主义也因而具有自由、解放的功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同性恋权利的政治斗争得以可能*Alexandra Chasin, “Interpenetrations: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y/Lesbian Niche Market and the Gay/Lesbian Political Movement”, in Cultural Critique, No. 44(Winter 2000), p. 151.。在石墙骚乱中,那些拒绝被逮捕的同性恋者深受公民权益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和新左派思潮的影响。正如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所指出,在公共空间中,同性恋者的这种集体抵制行为从根本上而言是对消费权的捍卫*David Johnson, “Physique Pioneers: The Politics of 1960s Gay Consumer Culture”, 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43(August 2010), p. 888.。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石墙骚乱不是同性恋运动的起源,而是同性恋消费权益革命的高潮。这种消费权益意识由各类同性恋消费品的生产商开启,并得到同性恋消费者的认同与强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是见证了以同性恋市场为目标的商品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繁荣。个体与消费品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个体对自我、共同体甚至国家身份的重要媒介。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同性恋消费主义是实现身份认同、进行资源动员的特殊手段,它能够在现代商业社会里获得意外的政治解放效果,消费主义有助于实现在商业经济与身份政治之间的转换。例如,戴维·约翰逊探讨了同性恋杂志的出版商如何与法律审查作斗争,并如何最终获得生产和消费某些商品的权利。他认为在美国出现全国性的同性恋政治共同体之前就存在全国性的同性恋商业市场,而由同性恋企业家促成的同性恋市场的发展则是身份运动兴起的重要催化剂。同性恋消费市场的兴起为培育同性恋政治运动提供了修辞话语,并建构了社会网络;同性恋消费品为同性恋者理解自身以及更广泛的共同体提供了认知手段*David Johnson, “Physique Pioneers: The Politics of 1960s Gay Consumer Culture”, 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43(August 2010), pp. 867-892.。同性恋风格和身份的商品化与后现代的同性恋/酷儿主体性的形成也具有内在关联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消费文化促使人们思考身份的延展性和可塑性,从而模糊了社会等级差序。消费主义强调无差别性、肯定个体权利,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道德训诫的束缚。消费实践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交换,同时也会影响感受性与品位的形成,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主体*Rosemary Hennessy, “Visibility in Commodity Culture”, in Cultural Critique, Vol. 29(Winter 1994-1995), p. 58.。大致而言,同性恋消费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消费文化中同性恋形象的流通能够在异性恋和同性恋受众中强化同性恋的主体性和共同体意识。
然而,身份政治和同性恋消费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中基于消费的身份构成不同于建立在性行为基础上的身份。消费实践固然革命性地消解了原有的地位群体和身份阶序,但是这种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市场活动与身份政治并不利于进步性的政治变迁,因为进步性的政治议程寻求联合,它不仅关注歧视性立法和社会包容,还关注整个人口中的经济不公正现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消费主义文化以身份为基础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相对晚近才发展起来,而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消费主义文化本身也是较晚才出现的现象*Alexandra Chasin, “Interpenetrations: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ay/Lesbian Niche Market and the Gay/Lesbian Political Movement”, Cultural Critique, No.44 (Winter), pp. 146-147.。亚历山德拉·蔡辛(Alexandra Chasin)质疑个体的私人消费行为成为政治参与之基础的模式,指出个体性的私人消费无法取代进取性的集体政治行动。在蔡辛看来,如果认为消费主义最有可能产生性自由和性权利,那是因为它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若要改变不公正的地位,同性恋政治必须直面这些社会结构。此外,丹尼尔·哈里斯(Daniel Harris)认为,由于当代异性恋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和宽容,使同性恋者不再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因此,他们不再有动力向主流的异性恋社会表明自身的价值,也不再以文化为手段获取社会声望,这导致同性恋爱情的异性恋化、同性恋感受性的终结甚至同性恋文化的消亡。与此同时,消费市场上却到处兜售和贩卖一些空洞无物的同性恋文化*参见Daniel Harris, The Rise and Fall of Gay Culture, New York: Hyperion, 1997.。文化可见性能够促进同性恋权益的保护与发展,但是同性恋者仅是作为消费的客体而存在,因而,商品文化中的可见性仅是一种有限的胜利。世界性的同性恋旅游(tourism)是性身份和消费自由的象征,但它消解了原有的性实践与身份认知。同性恋社群的跨国流动和全球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的身份、关系、矛盾、斗争以及抵抗政治等,而地方性的同性恋共同体共享着同一种民族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民族主义”*Jasbir Kaur Puar, “Mapping U.S. Homonormativities”, in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Vol. 13(January 2006), pp. 67-88.又将是身份政治的另一个重要话题。
四、余论
本文论述了同性恋身份、抵抗策略、“橱柜”政治、“石墙骚乱”的神话以及同性恋消费主义,其核心是身份政治及其反思。通过对文化与身份的去中心化、对规范性的解构以及对异性恋正统性的拒斥,当代酷儿理论在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性与其他因素(如性别、阶级、种族和国家等)的交叉性中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任何理论范式都根植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酷儿理论能否适用于非西方文化仍值得商榷。需要指出的是,同性恋的性态并不必然是非规范性的,它也并不一定以二元论的方式呈现。在新的身份政治的感召下,人们对自主性的争夺日益加剧,越来越倾向于定义和掌控自我的性态。在这个过程中,同性恋活动家建构集体身份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早期采用对立的“我们vs.他们”的话语,从而将LGBT社群与异性恋社群截然分开,以策略性地产生差异和边界。如今,同性恋活动家以更包容性的逻辑,即“我们&他们”的话语来建构集体身份。这种从“对立”(versus)向“包容”(and)的转变意味着活动家不再竭力设法与主流的异性恋群体划清界限,而是更多地在两者之间构筑桥梁*Amin Ghaziani, “Post-Gay Colle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Social Problems, Vol. 58 (February 2011), pp. 99-125.。
这种重新联结和涵括的策略也影响着学界对酷儿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例如,亚当·格林(Adam Green)批评酷儿理论的过度解构与颠覆并无助于理解现代的性行动者和性政体*Adam Green, “Gay but Not Queer: Toward a Post-Queer Study of Sexuality”, in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1(August 2002), pp. 539-540.。格林辨识了两种类型的酷儿理论:一种是“激进的解构主义”,它掩盖性范畴在社会设置和社会角色中的具体表达方式,从而消解了它们作为社会组织之主轴的作用;另一种是“激进的颠覆”,它忽略性行动者共享的、被社会化的社会环境,从而无法理解性的边缘地位之复杂性以及与其他制度性身份与社会角色的依附关系。同性恋与异性恋因不同的性取向占据着独特的社会结构,性取向的分类具体呈现在制度设置与社会角色之中,这将对自我观念和社会互动的模式化产生重要后果。但是性的社会行动者不仅仅通过性取向本身定义他们占据的所有制度性身份,他们还共享着许多社会特征、意识形态与经验等,因而不同性取向之间达成联通是一项重要的事业。
(责任编辑:陆影)
2016-07-14
王晴锋(1982—),社会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南亚民族志。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同性恋者生存现状研究”(项目编号:13CSH082)的阶段性成果。
C913
A
1003-4145[2016]12-0068-07
——基于对国内某大型形式婚姻网站征婚广告的内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