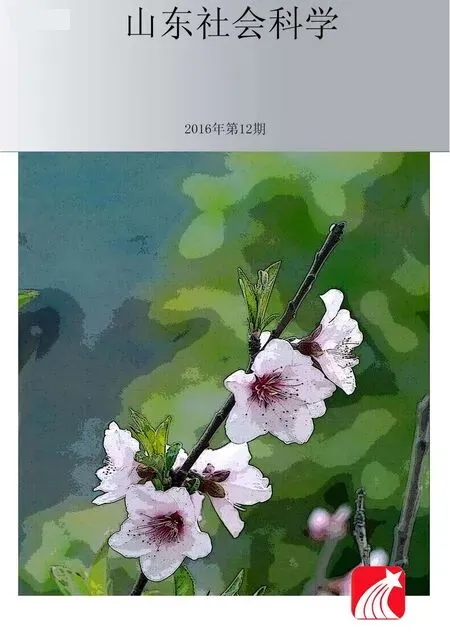经济理性泛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宏大叙事批判
何丽野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经济理性泛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宏大叙事批判
何丽野
(浙江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经济理性是在市民社会中被运用于经济领域的理性。经济理性泛滥,就是经济学的前提“经济人”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并运用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经济学成为宏大叙事,追求物质利益代替了为理想与信仰奉献。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经济理性泛滥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于传统的宏大叙事方式失效产生的,也与中国特殊的国情有关,同时还由于现代经济运行的复杂性。经济理性的泛滥,严重损害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整体发展,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对此进行批判。
经济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宏大叙事批判
一
在当今的中国哲学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对“经济理性”及其泛滥进行批判。所谓经济理性,是指理性在经济领域或者说市民社会的运用。*关于市民社会,有多种说法,本文采用哈贝马斯的表述“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德]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这是一个在哲学史上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康德曾经写过三大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大批判分别针对理性运用的三大领域:认知领域、道德领域和审美(艺术)领域。同时这三大批判又回答三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他认为,回答了这三大领域内的问题,也就可以回答第四个“人是什么”的问题。但其实这是不够的。因为他把经济领域内的理性运用给漏掉了。*需要说明的是,康德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理性在经济领域里的运用。但他认为,如果理性仅仅被用作为自己谋利益,那标志着理性的堕落:“他具有理性就根本没有将他在价值方面提高到超出单纯动物性之上;这样理性就会只是自然用来装备人以达到它给动物所规定的同一个目的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而并不给他规定一个更高的目的。”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页。在这个领域里,理性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能得到什么?”具体地讲,就是:我在经济活动中能得到什么以满足我的需要?相对于认识论、道德论,这个问题属于“需要论”。理性在认知领域里是面对感性经验,人为自然立法;在实践领域里是面对主体自己,人为自身立法;而在经济领域里,理性则是用于主体与他人通过市场进行的利益交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活动是其它一切活动的基础。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从事各种社会职业活动,首要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本质上都是经济活动。因此,人们在认知领域内的知性、道德领域内的实践理性、审美领域内的判断力,都必须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研究人的理性,研究人之所以为人,如果离开了经济理性,那么所研究的就是虚幻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人。
经济理性的本质是交换。人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人类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人是能劳动的动物,同时也是从事交换的动物。人们在现实中的物质资料生产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供自己消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供他人消费,满足他人的需要。分工活动的本质就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包括劳动或其它活动)与他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通过满足他人的消费愿望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愿望。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都要在交换中才能实现。例如在雇佣劳动中,生产者拥有的是使用价值(商品),他以其换来价值(货币);消费者拥有的是价值(货币),他以其换来使用价值(商品)。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也是这样:资本家付出了交换价值(资本),获得了使用价值(劳动力),工人则相反,付出了使用价值((劳动力),获得了交换价值(钱),从而“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114页所以,说人的劳动实践的目的是改造客观世界,这只是从类的角度来讲的,从现实中的个人来说,从事劳动实践的目的是为了交换。马克思曾经讲,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有两种尺度:内在尺度(美的尺度)和外在尺度(实践对象的客观规律)。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还有第三种尺度,那就是交换尺度。即自己的劳动成果如何能“卖出去”。交换是个人的存在方式。所以经济理性也是交换理性。
交换理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里,人们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依赖的主要不是交换,而是血缘、等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权利格局。人们依此获得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资本主义社会与前此的封建社会等等的区别,不在于前者崇拜金钱,而在于前者经济的运行方式是理性的,也就是交换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这就意味着,这种行为要适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有条不紊地利用商品或人员劳务作为获利手段。”*[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8页。因此,“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资本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
所以经济理性是“非道德”的。所谓非道德不是说可以损人利己(损人利己叫做不道德),而是这里(经济领域)运用理性时不能讲道德。因为道德的本质是牺牲自己以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求。但人们之所以从事经济交换活动,恰恰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欲望。交换理性的前提是承认人性为私,承认每个在经济领域活动的人都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但他们是通过交换来做到这一点。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每个人的活动首先是满足他人自利的需求。因为只有如此,才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在这里理性不讲道德、排斥道德(当然也有人会在经济领域内讲道德,但这个时候他运用的是实践理性而非经济理性)。黑格尔讲:“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09页。是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二
经济理性泛滥,也就是经济学越出了自己的范围成为宏大叙事,经济理性被滥用。这在当代中国特别明显。它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个人层面。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例如为私谋利的“经济人”)为许多人接受并运用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成为其衡量、评估一切行为的普遍的思维方法,理想、信仰等均为物质利益追求所代替,权钱交换、权色交易变得肆无忌惮;二是政府层面。世界被看作一个交换的大市场、一个经济的大“台子”,经济以外的其它工作都是“搭台”,为“经济唱戏”服务。所有事物都被视为可用于交换的商品资源,所有社会问题都必须服从于“经济发展的大局”;三是意识和学术层面。学术研究活动大多成为经济和利益交换活动,“为学术而学术”几近绝迹。与此同时,经济学家成为明星,经济学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任何其它学科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在这个框架中的不同的地位。就连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不能例外。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材料来证明,人们便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它们,或者牵强附会也能扯上一点。看起来似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取得“通行证”,实际上毋宁说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座架”中谋得自身的地位。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些一再强调的、但是不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思想,就在“与时俱进”当中被舍弃了,仿佛他们从来没有说过那些话。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拐杖”,这大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时始料未及的。
经济理性被滥用,首先是由学科“形而上学冲动”造成的。各门具体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式,它包括对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研究方法的预设。比如经济学必须假定人是“经济人”(即在经济活动中追求自己利益),也同样必须用经济学的方法(比如边际收益等分析方法)解释财富的生产和经济运行,等等。这些不可追问的“第一性”的预设,是学科本身的存在所必须的。各门学科的研究者把它们当作自明的规范和前提接受下来。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们往往也会把该门学科所特有的思维范式应用于世上一切事物,作为衡量标准。例如,经济学家会认为追逐利益就是人性的全部,因此,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用“市场手段”来解决;道德家会把人们在某些特定时刻所表现的道德行为(如“见孺子将入井”时即发“恻隐之心”)认作人性之本,因而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道德教育;法学家会认为人性本恶,必须用法律加以约束。社会问题皆因法制建设不健全,等等。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知性虽然能对经验进行整理归纳,却不能自己给自己规定所运用的范围界限,知性不知道什么是处在它们的领域之内的,什么是处在它们的领域之外的,会把物(在某些领域内)所呈现的个别现象当作“物自体”本身的性质。所以总是不停地跨越自己领地的界限并沉陷于妄想和假象。*[德]康德 :《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专业学者往往会认为自己学科是不可批判的、但同时却以自己的学科来评价批判整个社会和其它学科。这就是学科“形而上学的冲动”。
在中国,经济理性的泛滥还有自身的原因:中国属于东方落后国家,长期因为落后而饥饿、贫困而“挨打”,有着“赶英超美”的急切心理。因此容易赋予生产力以某种超越时空的形而上的地位,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仅仅归结为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把社会主义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归结为马克思早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实现哲学”,把人的自由平等的“类本质”从抽象变成现实(这个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被表述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样就为经济学成为形而上学和宏大叙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来说,经济学成为宏大叙事的转折点,是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此案的处理结果对中国社会道德水准影响巨大、极为深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案在缺乏相关的直接证据情况下,法官宣称:彭宇在扶起老人后将其送往医院,并在医院等待其观察治疗的行为“有悖情理”,故断定彭宇为事故责任人。*http://alha.blog.163.com/blog/static/29305220078833757987/也就是说,“经济人”假设被法律所承认,并且作为法院的判决根据。利他主义的道德行为被否定、被认为是不可能了。中国社会中躁动已久的利己主义思潮终于找到了“合法化”的突破口喷涌而出而泛滥成灾,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和道德水准急剧下降。各种匪夷所思的不良行为、无德行为纷纷涌现。虽然后来当事人彭宇自己也承认了撞人的事实,证明法官在这次审判中并没有误判,但这并不能改变此案对中国社会道德水准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
经济学之所以在中国成为形而上学,成为宏大叙事,还与原有的哲学宏大叙事方式失效以及经济形式本身的发展有关。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一直有这样一个叙事机制:在这种叙事机制中,个人通过感觉经验、生活实践等得到的具体知识被放到宏大的叙事(元叙事)当中,特殊性的命题被放到普遍性的命题当中,具体学科的真理性和价值取决于它们在这个宏大叙事中所占据的位置。康德认为,个别的经验通过知性范畴的整理而成为有普遍性的知识。黑格尔说,具体科学的知识还要由逻辑所构建的理性大厦赋予其合法性。只有合乎理性的存在才是真实的“现实”,不合乎理性的存在是虚假的“现存”。从表面上看哲学是以形而上学来规定具体的存在,实质却是以具体的存在来推导形而上学,反过身来赋予自身以“合法性”。即如阿多诺批评海德格尔时所说的那样,所谓超越时空的永恒的“存在”(Sein)本身,其实都是特定的时空中的“存在者”(Dasein)的存在。但所有关于存在的学说,都是把这种受时空限制的“存在者”当作超越时空的“存在”本身。“没有存在物便没有存在这一事实变成了一种形式:存在物的存在具有存在的本质。因此,真理成了非真理,存在物进入了本质。”*阿多尔诺 :《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利奥塔说,形而上学(元叙事)并不是真正的知识,而是把自身的知识合法化的结果。元叙事其实都是些经验的知识,但是它为了充当元叙事这一角色,“改变了自己所处的层面,……而成为关于这些知识的知识,即成为思辨的知识。知识用‘生命’、‘精神’等名称命名的正是它自己。”*《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江怡编,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9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了形而上学冲动背后的利益关系,“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哲学就是把这种利益关系用思想关系掩盖起来。所以,在哲学“求真”的表面背后,隐藏的是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的诉求。
经过马克思和后现代的批判,传统哲学的宏大叙事方式已经基本失效。但是社会对此的需求仍然存在。于是,经济学(主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新形式的形而上学与宏大叙事粉墨登场。个别利益已经不需要经过思想这个中介,不需要以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出现,而是直接以社会普遍利益的形式出现。蒲鲁东当年为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辩护,尚须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拐杖,但今天至少在中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引用哲学家的思想来阐述经济学,相反地,他们公开宣称不需要哲学,哲学帮不上忙。经济学本身直接成为了形而上学。这是因为经济形式本身的发展,如互联网等产生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交互作用,经济全球化等,经济运行越来越具有一种悬在空中的、抽象的性质,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的感觉根本无法触及这种整体的实质。但另一方面,个人生活与这个整体的联系却越来越密切。例如,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消费行为可以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企业,从而影响在沿海地区企业工作的劳务工人的就业和收入情况,进而影响中国西部地区某个农村家庭的生活,伦敦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在同一时刻直接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影响中国普通人的基金与股票资产,进而影响中国人家庭的餐桌。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生产者自给自足,产生的是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那个商品经济时代,生产者是为交换、为他人生产商品,“生产——消费”的交换关系,产生的是辩证思维方式,而当代全球化经济,生产者的生活用品是由千里之外甚至地球的另一边的某些人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整体效应所决定,经济运行成为一个高度复杂的巨型系统,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是非线性的系统化的思维方式。“蝴蝶效应”,本来是气象学家洛伦兹对大气环流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一个通俗的说法,但现在被人们广泛应用,经常出现在媒体上,尤其是出现在对经济运行状况的描述上,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当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高度的系统化,说明了当代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有机性,以及个人在这种高度复杂的巨型系统面前所感到的自身的无能为力。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个人要做出一个正确的投资决定,他所需要的、所面临的信息之多、之复杂都是特定的个人根本没有能力获得与处理的。如果说,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能从个人的“感性存在和需要”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话,那么今天这种批判是远远不够了。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包括与经济学有关的如金融学、投资学等等)成为了“显学”。往日在平民百姓面前显得高深莫测的经济学开始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和大众媒体的信息中出现了许多经济术语,例如“GDP”、“CPI”、“基尼指数”等等。这些专业术语中,除了少数几个,大多数并不为经济学以外的人们(包括其它学科的学者们)所了解。这应该说是专门学科积累和发展以后,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今天,任何一个学者专家在自己的专业以外都是外行,都是普通群众。但由于很多专业学科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并不大,再加上囿于精力时间所限,一般说来,人们不会去特意跨专业去了解其它学科的术语、数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蕴含的意义。但是经济学的术语和数据就不同了。人们不能对它们置之不理。如前所述,到了今天,每个人的生活都与世界经济的运行联系在一起而密不可分。而世界经济的形势就是由这些数据来体现的。人们不能不关心它们。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经济论坛上听众满座,聚精会神,甚至炒股票的退休金领取者也在认真地阅读财经类报刊,通过各种媒体和交谈来努力获取经济与金融信息。但经济学也是一门高门槛的学问,掌握经济学的术语、数学公式、进行数据的统计、解释数据变化所象征的意义,以及通过这些变化来预测经济未来的运行,更是普通人所望尘莫及的。于是,人们对这些“经济数据”便产生了一种敬畏,它们就像古代人心中的神一样——它们决定着人们的命运,但人们对它们一无所知。
于是,经济学本身成了“宏大叙事”,经济统计数据成了“上帝”,而经济学家则成了“神父”,他们负责对这些数据中所代表的经济运行状况,即“上帝的旨意”进行解说。所以,经济学成为新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不再用思想来掩盖利益,不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思想的普遍联系”,而是把它说成是“经济数据与数学公式的联系”,这种联系又被说成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数据掩盖了利益关系。例如,“人均收入”掩盖了社会贫富差距。于是就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数据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感觉相去甚远,往往看宏观的经济数据是“形势一片大好”,而人们生活中的感觉却并非如此。人们往往忘记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也同样掌握着意识形态。而掌握意识形态的集团同时也掌握着经济数据。因此,所谓经济数据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经济运行态势。数据本身虽然是客观的,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采集数据,用什么样的数据,公布什么数据、不公布什么数据,以及对数据本身采取什么样的解读方式,却是由特定的人们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更不用说人们还可以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数据同样属于上层建筑,它是意识形态。齐泽克早就指出,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存在,原因只能在于人们不知道它属于意识形态。正如宗教之所以能有效用就在于人们不知道它是“麻醉人们的精神鸦片”。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这个批判的对象首先是这个时代的观念(思维方式)。因为一个时代的问题是由这个时代的观念造成的,“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未完成著作——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今天中国的问题仍然适用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交换。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分工和交换的扩大,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马克思所反对的是私有制社会中强势群体利用自己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剥削弱势群体的不公平交换,以及把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变成了用金钱招募的雇工,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甚至家庭关系都变成了金钱交换关系。孟子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指出:在一个国家里不可以人人追逐利益交换,因为“上下交征利,国危矣。”国君必须以道德阻击“利”的泛滥,将其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众所周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经济历来不曾占据重要的地位,更谈不上成为形而上学和宏大叙事。儒家历来主张“正义不谋利”。但是,儒家以“义”否定“利”,本身却为经济理性的泛滥、经济学成为形而上学提供了思维方式的基础。因为以义否定利是一种泛道德化思维。即用道德标准涵盖所有社会领域,以是否合乎道德衡量人们的一切活动。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讲,它的特点就是没有“边界意识”。总以为万物必然有着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凡事总有一个“最根本的大道理”,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大道理适用于一切领域,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它有的时候表述为“本”,有时候表述为“纲”、“中心”,表述不一,意思一样。这种思维方式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推动下,很容易造成经济理性的泛滥。
对各种具体学科进行理性划界批判,阻止其“形而上学的冲动”,这是哲学的任务。因为唯有哲学有权对各门具体学科进行批判。康德第一个意识到这项工作。他赋予理性一种新的用途:对知性进行考察,为其划界。知识必须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知性如果企图越出这个范围,也就是把从经验得来的知识扩展到经验以外,那就会造成二律背反。康德说,由此,哲学就通过自身建立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的任务是阻止各门具体学科越出自己的经验范围成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按照理性的各种要素和那些本身必须为一些科学的可能性及所有科学的运用奠定基础的至上准则来考察理性。形而上学作为单纯的思辨,更多地被用于防止错误,而不是扩展知识。……通过它的审查职权使科学的共同事业的普遍秩序与和睦乃至福利都得到保障。”*[德]康德 :《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页。
马克思在康德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不仅从经验得来的知识具有学科空间的限制,而且所谓先天的理性和知性范畴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历史运动的产物。因此任何学科不仅有其空间的限制,而且有时间即现实历史的限制,当它到达这个界限的时候,便丧失其合理性。《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像黑格尔那样的包罗万象的抽象哲学思辨必须为实证的科学所替代,这些科学,是从对人类特定的地域的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74页例如经济学如果只限于在经济范围内解释人的活动,那么它把人只看作劳动力,看作经济人,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经济学还想以此作为对一般意义上的人性的概括,把它当作人性的全部,以经济学代替伦理学,则是已经越出了自身领域。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批判,遭到马克思迎头痛击。“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自己与那些把他的一些思想观点公式化、形而上学化,用它去套一切国家、解释一切事件的人区别开来,数度宣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理性的泛滥,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挺身而出。近代以来,随着各门具体学科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哲学的领域不断缩小。有人形象地说,形而上学(哲学)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把自己的王国都分给了子女,自己落得个孤苦伶仃,只好自怨自艾,靠回忆过去的好时光打发日子。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有过类似的悲叹。*[德]康德 :《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哲学现在确实有点这样,好像除了整理以往哲学家的思想,就没有其它事情可以做。其实并非如此。哲学在把自己的领地分给各门学科的时候,却还保留了一样东西没有分出去,那就是对这些领地的解释权和裁判权。当有学科僭越它的本分,企图成为各门学科的霸主也就是成为形而上学的时候,唯有哲学可以给予迎头痛击,让它乖乖地缩回自己的领地里去。从这点上来说,哲学不像李尔王,却有点像《西游记》里的唐三藏,虽然什么也不会,整天呆坐着,手里却捏着紧箍咒,随时可以让那些虽然能干却不听话的徒弟们败下阵来。这就是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职能与存在意义。
(责任编辑:刘要停)
2016-10-23
何丽野,男,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A811
A
1003-4145[2016]12-0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