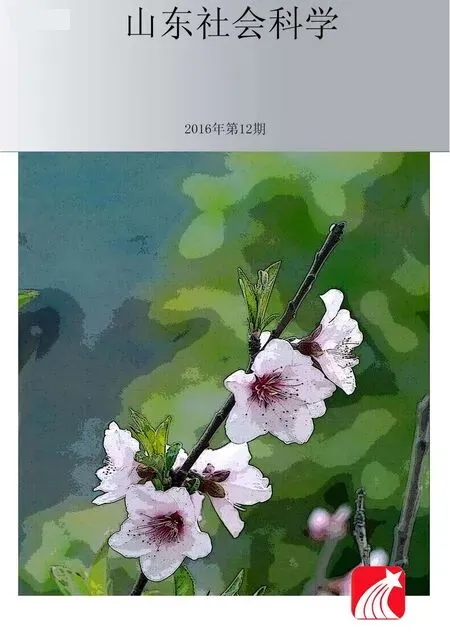哲理与诗性:论王弼《周易注》诗学意义
刘运好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哲理与诗性:论王弼《周易注》诗学意义
刘运好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王弼《周易注》的诗学(美学)意义,不仅表现在《周易略例》有关言象意关系的论述上,而且在具体解经过程中所建构的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刚柔中正的审美观念、情性合一的主体认知、质文并重的理论导向,也表现出鲜明的哲理与诗性的统一。这四个方面,对于两晋名士柔心应世、内怀文明的人格建构,柔性诗风中追求阳刚之气的诗歌风貌,基于情性合一的“缘情”理论,以及以义理为美且又结藻清英的诗格选择,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这几个方面恰恰为学术界所忽略。
王弼;《周易注》;诗学意义
《易经》是筮占卜蓍之书,与诗学并无直接关联。由于受研究对象的限制,《周易注》也没有自觉的诗学观念。然而,不仅《周易》的诗化语言,以卦象“以类万物之情”的特殊认知方法,具有鲜明的诗性审美特质,而且《周易注》在论天人之际的哲理中也部分地折射了王弼的诗性审美世界。在具体解经过程中,王弼所建构的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刚柔中正的审美观念、情性合一的主体认知、质文并重的理论导向,表现出鲜明的哲理与诗性的统一。这四个方面,对两晋的名士人格、诗歌风貌、缘情理论以及诗格选择都有深刻影响。
以往学界对王弼美学(诗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本体哲学、言象关系、素朴之美的哲学命题,这对于深化王弼美学(诗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王弼《周易注》所蕴涵的美学(诗学)理论体系研究,基本付之阙如,故简要论述如下。
一、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
“人格”一词,虽然源于西方,指人在特定环境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思想和情绪的整体特征,但是在文明进化中,人格却是一个伴随着族群的永恒存在的价值评判,任何一个文明民族都以人格作为衡量自然人的社会标准,因此中国传统的儒道二家都注重主体人格的建构。正始时期的“才性论”和《人物论》都探讨了主体人格的本质属性问题。
柔顺文明是王弼所推崇的融合儒道的理想人格模式。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柔顺偏向于外在处世方式,文明偏向于内在人文品质,但是人生践履中,柔顺与文明又是相生相成的整体人格模式。
柔顺文明人格模式的建构始于《易传》。《明夷·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孔颖达疏:“内怀文明之德,抚教六州;外执柔顺之能,三分事纣。以此蒙犯大难,身得保全,惟文王能用之。”明夷之象,象征暗主在上,明臣唯有内怀文明之德,外持柔顺之性,才能避祸全身。然而柔顺事主,又非曲阿逢迎,而必须秉持贞正之性,故又疏曰:“既处‘明夷’之世,外晦其明,恐陷于邪道,故利在艰固其贞,不失其正。”*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可见,柔顺之容、文明之德、贞正之性,是柔顺文明人格的基本内涵。周文王正是这种人格的典范。
王弼《周易注》所建构的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既汲取《易传》的基本内涵,又丰富了具体内容。以文明之质,柔心应世,而不自役;以柔御刚,而秉持贞正,是其基本特点。如《未济·六五》注:“以柔居尊,处文明之盛,为未济之主,故必正然,后乃吉,吉乃得无悔也。夫以柔顺文明之质,居于尊位,付与于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刚以柔,斯诚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则竭力,功斯克矣。”下居尊位,必以文明之质;事未济之主,必内怀贞正。以能使物,而不自役;因文使武,以柔御刚,上不见疑于主,下使物尽其力,是则君子之德,光辉显著,功亦成矣。
“柔顺”是以《坤》为代表的卦象引申而来的,“文明”是以《离》为代表的卦象引申而来的。孔颖达曰:“《坤》则顺,《艮》则止,《巽》亦顺,《离》文明而柔顺,《兑》柔说,皆无健。”*李鼎祚 :《周易集解》,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14页。就卦象而言,“柔顺”有以阳居阴、以阴居阳、以阴居阴、以阳居阳四种情况。每一种情况所表现的柔顺特点各不相同。但是,综合考察,柔顺的基本特点是:尚谦、尚中、尚柔,又尚正、尚道、尚刚。如《困·九二》注:“以阳居阴,尚谦者也。居困之时,处得其中,体夫刚质,而用中履谦,应不在一,心无所私,盛莫先焉。夫谦以待物,物之所归,刚以处险,难之所济。履中则不失其宜,无应则心无私恃。”又《履·九二》注:“履道尚谦,不喜处盈,务在致诚,恶夫外饰者也。而二以阳处阴,履于谦也。居内履中,隐显同也。履道之美,于斯为盛。”可见,“柔顺”首先必须谦逊、中庸、冲和,即“谦以待物”“处得其中”“不喜处盈”;但又不是失去了自我的曲意迎合,所以又崇尚中正之质,践行君子之道,保持阳刚之气,即“居内履中”“履道尚谦”“体夫刚质”。此外,王弼还特别强调心性之诚、超越物累、性真、无私、唯德,如上文所言之“务在致诚”“心无私恃”;《中孚·九二》注“不徇于外任,其真者也”,“不私权利,唯德是与,诚之至也”;《中孚·九三》注“四履乎顺,不与物校”等等,皆属于此类。
“文明”者,明其文也。考察《易传》,其意有三:一谓文采炳焕。《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万物生长,色彩缤纷,,故天下之文采炳焕。这一点特别具有诗学意义,后文再论。二谓文治教化。《贲·彖》:“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颖达疏:“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诗书礼乐谓之人文,圣人以人文教化天下,此即文明之道。三谓道德诚信。《革·彖》:“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王弼注:“文明以说,履正而行,以斯为革,应天顺民,大亨以正者也。”孔颖达疏:“能用文明之德以说于人,所以革命而为民所信也。”*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文明之德,指天地之四德、君子之道德诚信。由此可见,除了文采炳焕的意义外,《周易》之“文明”与《论语》之“文质彬彬”意义相通,就其君子人格模式而言,都强调主体的道德与人文修养。
王弼《周易注》所言之文明,取《周易》文明之德的原意,又有所发挥,自立新说。主要强调柔顺中正的处世原则。如《离·六二》注:“居中得位,以柔处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黄离元吉也。”孔颖达疏:“黄者中色,离者文明,居中得位而处于文明,故元吉也。故《象》云‘得中道’,以其得中央黄色之道也。”*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据此可知,王弼所言之“文明”是指《离》卦,而“离之为卦,以柔为正”,柔顺且又合乎中正之道,此是王弼所论文明之德的基本内涵。又如《旅·六五》注:“寄旅而进,虽处于文明之中,居于贵位,此位终不可有也。以其能知祸福之萌,不安其处,以乘其下,而上承于上,故终以誉而见命也。”胡瑗注曰:“虽有柔顺中正之德,然寄身托迹于外方,知其所亲比者寡而未尝固,必其所求不必志其所得。”*胡瑗 :《周易口义》卷九,载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册,第540页。据此可知,文明则是指君子柔顺中正之德。意即羁旅之人不可居于尊贵之位,然而持柔顺中正之德,则能洞明祸福;居安思危,不侵权而凌驾于下,而是承上意以自保,即可成功。《明夷·九三》注“处下体之上,居文明之极”,《睽·上九》注“以文明之极,而观至秽之物”等等,皆是此意。由此,王弼所论之“文明”,虽也多取文明之德的意思,但内涵与《周易》却有所区别。
此外,王弼所说之“文明”,还包含符合典制、合乎情理的治政原则。如《丰·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王弼注:“文明以动,不失情理也。”孔颖达疏:“雷者,天之威动;电者,天之光耀。雷电俱至,则威明备足,以为丰也。……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罚,亦当文明以动,折狱断决也。”*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所谓断狱决讼,动之以文明,也就是强调断狱必须既符合典制,又合乎情理,必须洞察“虚实之情”,得于“轻重之中”。遵从国家典制、合理合情是治政的基本准则。由上可以看出,王弼除了申述《周易》所注重的君子道德与人文修养之外,主要则突出柔顺中正的处世原则。
概括言之,内养文德、柔心应世是柔顺文明人格模式的基本特点。而柔中寓刚、谦而正直、中庸由道,则是其基本内涵。这恰恰是儒道二家所推崇的人格模式的折衷调和。钱志熙先生说:“儒玄结合,柔顺文明是西晋文人的人格模式,它的基本表现是谨身守礼、儒雅尚文、谦柔自牧、宅心玄远、通达机变。这是一种折衷的、调和色彩很浓厚的人格模式。”*钱志熙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这种人格模式正是建立在王弼玄学的基础上。如果说王弼哲学的基本特点表现为超越性,那么王弼所试图建构的理想人格模式,恰恰表现了浓厚的世俗性。这与正始名士思想超越于现实、行为泥身于世俗的悖离现象,是非常吻合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那个时代名士人格模式的理论阐释。
正始名士所建立的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虽在竹林名士中有所反拨,如阮籍《达庄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酒德颂》,皆纵恣而言,其应世则“越名任心”,其思想则顺乎自然,但是随着阮籍去世、嵇康被杀、向秀入洛,余下的竹林名士也在无可选择的选择中投向了司马氏集团的怀抱。向秀的《思旧赋》成为竹林名士人格转折的一曲挽歌,自此以后,柔顺文明又成为两晋名士人格的主体特征,潘岳、石崇是其典型。即使如张华、陆机之流游心于儒道,而不得不缘夤世俗。
二、刚柔中正的审美观念
先秦儒道虽未将刚柔中正作为一种概念加以解释,然而道家刚柔相济的人性组合论、儒家弘毅贞正的君子人格论,其本身即蕴涵着审美化的心理元素,后来在文化累积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易传》的审美观念。
《易经》是以探究天人为旨归,并无明确的审美观念。但是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则已浸润了当时的审美观念。由于王弼注《易》采用以传释经的方式,进一步拓展了《易传》的审美观念,遂形成了以刚柔中正为美的美学思想,从而对魏晋诗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善为美,以柔为美,是《易传》的基本审美观念。第一,以善为美是审美的本质特点。《乾·文言》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孔颖达疏:“乾始,谓乾能始生万物,解‘元’也;能以美利利天下,解‘利’也。谓能以生长美善之道,利益天下也。”*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乾道有四德:“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利者义之和也”。天之体性,生养万物,故谓之善;利生万物,使物各得其宜,故谓之和。而利生万物,和谐共存,则为美。可见,美的核心是善,善的核心是利生万物且使之和,故以善为美是《易传》的核心审美观念。《论语·八佾》赞美《韶》“尽善尽美”,正是因为《韶》乐包含着社会和谐的内容;《易传》赞美乾道有利生之善,使万物和谐,二者在思想上是相通的。第二,以柔为美是审美的表现形态,《老子》主张以柔克刚,《周易》主张以柔应刚,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以阴柔为美。阴柔,体之为性,用之则卑,卑顺之道是阴柔之美的具体表现。《坤·文言》曰:“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王弼曰:“阴之为道,卑顺不盈,乃全其美。”坤道、妻道、臣道,皆为阴,必待阳方有善终,故孔颖达疏:“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地道卑柔,无敢先唱,成物必待阳始先唱,而后代阳有终也。”*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阴必待于阳而成体,卑必顺于上而成功。此即王弼所说,“卑顺不盈,乃全其美”——身居卑位,顺应于上而不过之,则其美全矣。综上,从伦理行为上说,以善为道德准则,以柔为行为准则;从美学意义上说,“善”是美的本质,“柔”是美的形态。二者相合则谓之天人之美。
《周易注》也主张以“善”为美的审美本质论,如《大有·象》注曰:“《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恶扬善,成物之美,顺夫天德,休物之命。”休者,美也。“遏恶扬善”就可以成就万物的性命之美,这也明确表达了美的本质在于“善”的美学思想。然而,王弼审美观念的核心在于强调刚柔相济、刚健和谐、柔顺中正之美,这又拓展了《易传》的审美理论。
先论刚柔相济之美。与《易传》特别彰显阴柔之美不同的是,王弼特别凸显刚柔并存、相辅相成的审美关系。如《卦略》曰:“《大壮》,未有违谦越礼能全其壮者也,故阳爻皆以处阴位为美。用壮处谦,壮乃全也;用壮处壮,则触藩矣。”“《大过》者,栋桡之世也。本末皆弱,栋其桡矣。而守其常,则是危而弗扶,凶之道也。以阳居阴,拯弱之义也,故阳爻皆以居阴位为美。”一方面,王弼强调阳过强盛,则以阴济之,如《大壮》。“大壮”者,乃强盛之名。此卦乾下震上,以阳刚为主,故阳爻必处于阴位,以阴济阳,方成美境。以柔用刚,则阳刚存;以刚用刚,则阳刚亡,阳刚亡必进退维谷。另一方面,王弼又强调阴过柔弱,则以阳拯之,如《大过》。“大过”者,言衰难之世,唯以阳爻乃能越过常理以拯救衰难,故曰“大过”。此卦巽下兑上,上下皆为阴爻,象征本末皆弱的衰难之世。若墨守常道,以阴守之,则凶;惟阳爻皆居于阴位,以阳济阴,方可拯弱,此则为美矣。“刚长则柔危,柔长故刚遁”(王弼《遁》注),唯有刚柔相济,才是一种审美的境界。这一思想虽然植根《易经》,取自《易传》,但是王弼着眼于美的二元构成关系,比经传更具有抽象辩证性。
再论刚健和谐之美。与刚柔相济之美相应的,则是刚健和谐之美。王弼论刚健和谐,将其上升到“道”的层面,从而揭示出美的基本存在规律。如《夬·象》注:“‘泽上于天’,《夬》之象也。泽上于天,必来下润,施禄及下之义也。夬者,明法而决断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决而能和,美之道也。”“夬”者,决也。此阴消阳盛之卦。此卦乾下兑上,五阳爻而一阴爻,以刚决柔,象征明法决断。王弼认为,明法决断,必如“泽上于天,必来下润”,即恩泽降于天而润于下,故必须居德谨慎、威惠兼施。所谓严者,刚也;施者,柔也。唯有刚柔兼济,才能达到“悦”“和”的愉悦和谐之美,此即“美之道”——美的基本规律。由形下之象上升到形上之道,揭示美的基本存在规律,也使王弼美学观念有了更深刻的抽象思辨性。
后论柔顺中正之美。王弼认为“阴之为道,卑顺不盈,乃全其美”,“不盈”即非一味卑顺,而是蕴涵着寓中正于柔顺的美学意义,从而在一个侧面上揭示出美的表现形态。一方面,柔顺与“中”密切关联,如《坤·象》注:“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坤为臣道,美尽于下。夫体无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任夫文理者也。垂黄裳以获元吉,非用武者也。极阴之盛,不至疑阳,以文在中,美之至也。”此所谓“中”,一谓中和,且通达物理;二谓中德,即内有文德。从卦象意义看,黄为中间之色,裳为下体之饰,象征臣下之美。而位在五爻,此乃君位,人臣居之,是尊贵之极。处尊位而能不用威武,藉中和之性、柔顺之德,以通达物理,故云“文在其中”,斯是至美的境界。另一方面,柔顺与“正”不可分割。如《坤·六三》注:“三处下卦之极,而不疑于阳,应斯义者也。不为事始,须唱乃应,待命乃发,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贞’也。”“正”,即“直以方”,正直、方正之意。“含章可贞”,即内含其美而外表贞正。从卦象意义看,六三爻处于下卦之极,关于其象征意义,干宝指出:“阳降在四,三公位也。阴升在三,三公事也。……唯文德之臣,然后可以遭之,运而不失其柔顺之正。”*李鼎祚 :《周易集解》,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9页。三公位居人臣之极,能自降退而不凌驾于王权之上,唯顺从王事,内含文德之美,外柔顺而贞正。可见,王弼所强调之柔顺,是以贞正为内核,非止于柔顺,这就发展了《易传》的美学观念。
概括言之,以善为美的审美本质论、以柔为美的审美表现论,是《易传》美学的两大支点。这两种美学观念,在思想上与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具有统一关系,在美学上又与道家思想构成互补关系。如果说以柔为美的审美表现论是易学与道家共同的审美蕲向,那么以善为美的审美本质论则是易学与儒家共同的审美蕲向。道家审美本质论的核心是“真”,《老子》强调“德真”(第五十四章)、“质真”(第四十一章),故王弼《老子注》谓“守其真”(第三章注)、“不渝其真”(第四章注);《庄子》强调“真人”(《大宗师》)、“真性”(《马蹄》)、“无为谓真”(《知北游》),故郭象《庄子注》亦谓“独任天真”(《齐物论》注)、“养真寄妙”(《人间世》注)。而《易传》以“善”为美、道家以“真”为美,这就构建了华夏美学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审美本质的学说。
王弼刚柔中正的美学观,深入阐释了审美构成论。首先,“刚柔相济”所论述的刚柔并存、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普遍性上揭示了审美的二元构成关系。《易》分阴阳,而一切卦象都由此而生发,这种二元生成论也成为华夏美学的核心命题。任何一种审美关系在本质上都是阳刚与阴柔的关系,因此清姚鼐《复鲁絜非书》提出文章之美有“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种。其次,由此引申出的“刚健和谐”论所言“健而能说,决而能和,美之道也”,则从社会性上揭示了刚健与和谐的辩证关系,即所谓“泽上”而“润下”,唯有“泽上”与“润下”的统一,才能产生美,其本质仍然是一种基于阴阳的二元构成关系。再次,由《周易》以柔为美所生发的“柔顺中正”论,又从主体情性上揭示了审美的二元构成关系。所谓“含美而可正”强调的柔顺与贞正,正是主体审美行为的二元构成。总之,王弼美学观念之三层,都是基于二元构成关系,前者是普遍存在的二元构成,其次是社会存在的二元构成,后者是主体存在的二元构成。其中刚柔相济的二元构成论是其美学理论的核心。
三、情性合一的主体认知
从哲学范畴上说,情性论渊源于先秦儒道。郭店楚简、孟子、荀子都对情性作了充分的论述。郭店楚简“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将情性引入审美文化中;而荀子“称情而立文”,则将情性引入礼乐文化中,故后代诗学皆以“情性”为诗歌构成的主要元素。
诗歌的抒情意义,现象上是抒发作者之情,本质上则又是表达作者之性。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说,情与性是不可分割的二元一体的关系。《周易》虽非讨论诗歌理论的著作,但其情性理论与诗学也有相通之处。《周易注》发挥了《周易》的情性理论,强调情性合一的主体认知。
《易传》论天人亦言性情,如《乾·文言》“利贞者,性情也”。孔颖达疏:“所稟生者谓之性,随时念虑谓之情。”*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可知,性指禀受自然的本性,情指因时而生的欲念。一方面,性与情不可分割,二者的关系是本与用的统一关系,如《大壮·彖》:“天地之情可见矣。”情是性的外在表现。性为本体,情为表现,即王安石《性说》所云:“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王安石 :《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27页。此即哲学上的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性与情本质属性不同,二者的关系又是制约与被制约的从属关系,如孔颖达说:“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则不能久行其正。”*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自然之性纯正无邪,发之于情则羼杂着现实欲念,所以必须以性约情。这既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将情与性分为两个方面:天地(自然)之情与性是统一关系;人事(世俗)之情与性则是从属关系。
然而,《易传》所言之情却有更为丰富的内容,概括言之,约有以下几端:第一,指情感。《系辞上》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情谓真实之情,伪谓矫饰之情。第二,指意向。《系辞下》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孔颖达疏:“辞则言其圣人所用之情,故观其辞而知其情也。”*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圣人之情就是圣人之意。第三,指义理。《系辞下》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韩康伯注:“易之情,刚柔相摩,变动相适者也。……存事以考之,则义可见矣。”*王弼、韩康伯注 :《周易王韩注》,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222页。“易之情”,即指《易》所蕴涵的义理。鉴此,《周易》所说之情,包括情、意、理三个方面。
此外,《易》所言之“情状”,既与现象界的物质形态密切关联,也与精神界的联想想象密切关联。《系辞上》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韩康伯注:“精气烟煴,聚而成物,聚极则散,游魂为变也。游魂,言其游散也。尽聚散之理,则能知变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王弼、韩康伯注 :《周易王韩注》,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98页。鬼神之情状并非是现实物态的真实呈现,而是由现实万物的“变化之道”联想想象而来的。
《周易注》虽也随文释义揭示情与性的从属关系,如《乾·文言》:“利贞者,性情也。”王弼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利而正者,必‘性情’也。”也就是说,如若失去性对情的制约,则不能使情久行其正,唯有以性制情,才能“利而正”;但是王弼又特别强调《易传》宇宙现象界的情性统一关系,如《大壮·彖》注:“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弘正极大,则天地之情可见矣。”“弘正极大”是天地的本然之性,所以这里所言之情就是性。《周易》的主体是以天象比附人事,故《乾》《坤》二卦居于经首。因此,探究天人之际也成为王弼哲学的基本出发点。《世说新语·文学》载:“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周易注》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探讨情性时尤其凸显主体精神界的情性统一关系。如《乾·彖》注:“静专动直,不失大和,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宁静、专一、刚正,合于太和、可正性命之情,既是情也是性,二者统一于主体精神之中。从这一核心观点出发,王弼阐释了同类相互感应对于认识情性的意义,如《咸·彖》注:“‘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王弼由天地互相感应而显现万物之情性,推导出一切情性都产生于同类的互相感应,这就使得天地万物的情性与认知主体的情性构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所以《萃·彖》曰:“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注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情同而后乃聚,气合而后乃群。”类聚、群分所构成的“气合”“情同”,就是在主体与主体之间形成了心理同构的关系。而上述所论之情亦即性,因此这也从另一个视角揭示了主体精神的情性统一关系。
情性的统一关系并非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有时情与性也构成一种悖离关系。其《明爻通变》曰:“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夫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乖。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巧历不能定其算数,圣明不能为之典要,度量所不能均也。”爻之变化,生乎情伪,情伪之变,不是象数可求。所以,或性与行乖,情与貌违;或形躁者其性静,质柔者其性刚,此则性与情互相悖离。王弼所言之“情伪”指情之真伪;“体”“质”指本然之性。“体与情反,质与愿违”是就伪饰之情而言,并非指真情。伪饰之情悖离性,真实之情合于性,情性的统一关系是以真实为前提条件的。可见,王弼之论源于经传,又不同于经传。
正因为王弼论宇宙自然之情性的统一关系,始终放在主体认知的角度上,所以《周易注》所论卦爻所象征的宇宙自然的性情,都与主体的性情构成异质同构的关系。唯此,使《周易注》的性情论也特别具有诗学意义,从而使王弼所论之情与性、情与意、情与理的关系问题,也同样具有了诗学意义。其《明爻通变》又曰:“故苟识其情,不忧乖远。苟明其趣,不烦强武。能说诸心,能研诸虑。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邢璹注曰:“苟识同志之情,何忧胡越也。苟知逃散之趣,不劳用其威武也。诸物之心,忧其凶患,爻变示之,则物心皆说。诸侯之虑,在于育物,爻变告之,其虑益精。……知趣舍、察安危、辩吉凶、知变化,其唯明爻者乎?”*王弼、韩康伯注 :《周易王韩注》,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244页。此之所谓“情”即理,《坤·六五》注明确指出:“夫体无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极物之情则通于理,故亦以情指理;“心”即性,《复·彖》注亦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以本为心,故知“心”即为性;“虑”即意,《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韩康伯注:“虑虽百,其致不二。”*王弼、韩康伯注 :《周易王韩注》,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213页。“意”乃思虑所得,故以虑而言意。因此,王弼所言之情与性、意、理,或是统一的关系,或是互相包容的关系。
王弼论情与性的统一关系,凸显情真的表达意义。从哲学角度上说,强调现象与本体的统一性;从诗学角度上说,强调本然之性与情感表达的统一性。论情与意、理的互相包容关系,凸显情在表达意、理上的意义。从哲学角度上说,强调情感的认知功能;从诗学角度上说,强调情感的表达功能。此外,王弼还论述了“性”与“志”的关系。《贲·上九》注曰:“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以白为饰,而无患忧,得志者也。”质素者,为物是本然之色,为人是本然之性。守志任真,得其本性,故言得志。至此,诗歌之“志”与“情”关系,在王弼情性论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就为“诗缘情”说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土壤。
四、文理并重的理论导向
这里所说的“文理”,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文理是指文饰与义理,如《易传》之《文言》解释《乾》《坤》二卦,孔颖达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亦即《系辞下》“其旨远,其辞文”之意。又《说卦》之“穷理尽性”,郑玄注:“言穷其义理,尽其人之情性。”*王应麟辑、惠栋补 :《增补郑氏周易》卷下,载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册,第176页。广义的文理是指形式与内容。如《序卦》曰:“贲者,饰也。”贲,离下艮上,艮为山,离为火。顾易生、蒋凡先生说:“山有草木花叶,再加上火光照耀,构成色彩交错、鲜明夺目的景象,所以《贲》卦有文饰的意思。”*王运熙、顾易生主编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上言“文饰”指语言的文采,此之“文饰”指形式之美,二者微有不同。另外,《说卦》之“穷理尽性”,既指具体的义理,也指《周易》的内容,故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显然,“顺性命之理”是《易》的整体内容。王弼《周易注》合“文”“理”而并称之。以理为美、文理并重的理论导向,是《周易注》特别具有诗学意义的美学思想。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理与文、质与文两个方面上。
理与文并重发端于《易传》。《坤·文言》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孔颖达疏:“黄中通理,是‘美在其中’,有美在于中,必通畅于外,故云‘畅于四支’。……外内俱善,能宣发于事业,所营谓之事,事成谓之业,美莫过之,故云美之至也。”*王弼注、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黄为中色,坤道为柔,柔则“体无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故云“黄中通理”;施于人事,美在其中,则必然表现于外,外内俱善,事业可成,此即达到美的极致,故曰“美之至”。据《六五》爻可知,“黄”又指“黄裳”,象征臣下的美饰;“黄中通理”,亦即外在的美饰(文)与事物之理(理)相通。由文可以及理,文的本身也就包含理,文与理互为一体、不可分割,这就深刻揭示了形式美与义理美的辩证关系。此外,理与文的关系,也包括情与辞的关系,如《系辞下》“圣人之情见乎辞”,藉辞以传达情;还包括性与辞的关系,如《乾·文言》“修辞以立其诚”,诚即性也,藉辞以显现性。辞与情、辞与性,从表达的角度上说,是载体内容的关系;从存在的角度上说,又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二者也是互为一体、不可分割。
王弼补充了《易传》以理为美的内容,尤其凸显义理之美,并且进一步深入揭示了文理相互依存的关系。
王弼把“道”分为爻道、卦道、至道三个不同层次,或称为道,或称为义(意),或称为理。这既扩展了《易》所言之理的内涵,又将《易》理上升到美的层面。如:“以刚逼难,欲进其道”(《需·九三》注);“《家人》之为义,以内为本”(《家人·彖》注);“大明乎终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时而成”(《乾·彖》注)。爻道是一爻之理,《需·九三》所说的“道”,即“九三”一爻之道;卦道是一卦之理,《家人·彖》所说的“义”,即“家人”一卦之理。卦理是通过具体的爻理所体现出来的,二者是个别与局部的关系。爻道、卦道皆为美,如《略例下》曰:“《彖》者,通论一卦之体者也。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一卦之义。”至道是《周易》整体的抽象意义。从卦象上说,是“终始之道”;从哲学上说,是无、一、太极。天地虽大,运化万变,然“寂然至无”(《复·彖》)是其本,“执一御众”(《明彖》)是其用,“《易》之太极”是其体。道也是美,且是无用之用,天地之大美。《文心雕龙·原道》所说:“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也就是这个意思。爻道、卦道、易道层层递进,阐释了深刻的天人之理,都是美的一种显现,故曰以义理为美是《周易注》的重要审美理念。
王弼以传解经,将《易传》有关“礼”的内容引入以理为美的审美理念中,使之所言之理也包含“理性”的意味。如王弼所论君子的谦诚,不仅是“道”的表现形态,也受到“礼”的规范制约,所以他反对“违谦越礼”,强调以礼义为美。《周易略例·卦略》又曰:“《履》者,礼也,谦以制礼。阳处阴位,谦也。故此一卦,皆以阳处阴为美也。”《易传》言礼,如《大壮·象》“君子以非礼弗履”,《系辞上》“德言盛礼,言恭谦也”等,王弼取《易传》之意解释《履》卦,认为《履》卦的核心是说“礼”,以阳处阴,则履于谦让,而履谦又必须制约于礼,如此方为美。《易传》强调“恭谦”“盛礼”,王弼强调尚谦、尚礼,二者都将“谦”受礼制约为前提,但王弼认为这种人生行为是美的外在表现形态,这与《易传》的理论有别,而与《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相同。论述义理之美,又强调以“礼”约理,对两晋诗学有较大影响。两晋诗歌,既以表达哲理为审美蕲向,如玄言诗;又有浓郁的政治伦理的说教色彩,如应制诗。这不能说与王弼的审美观念毫无关联。
质与文并重是《易传》的另一审美观念。如上文所引《序卦》云“贲者,饰也”,然《杂卦》又云“贲,无色也”。饰为文饰,无色是素朴,二者似乎前后矛盾。顾易生、蒋凡解释说:“为什么《贲》既是‘文饰’又是‘无色’呢?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说:‘无色为素,素为素质,犹如说内在本质。饰文文饰,文饰则加于外,犹如说外表现象。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和现象,二者构成对立统一。程颐: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由此可见,《贲》卦之释为‘饰也’‘无色也’,犹孔子所谓‘文质彬彬’……反映一种富有辩证因素的审美思想。”*王运熙、顾易生主编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6-97页。《贲·彖》反复突出“文”:“贲,亨。柔来而文刚……分刚而文柔……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虽然这里的“文”意蕴复杂,有交错、现象、典制等意思,甚至亦有专指卦文,但是“交错为文”就具有文饰的意味,而且包含了“一与不一”的辩证关系。钱锺书《管锥篇·周易正义二四》曰:“《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按刘熙载《艺概》卷一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国语》:物一无文。徐锴《说文通论》:强弱相成,刚柔相形,故于文:人、乂为文。朱子《语录》: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为文者盍思文之所生乎?’又曰:‘……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刘氏标一与不一相辅成文,其理殊精:一则杂而不乱,杂则一而能多。古希腊人谈艺,举‘一贯寓于万殊’为第一义谛,后之论者至定为金科玉律,正刘氏之言‘一在其中,用夫不一’也。”*钱锺书 :《管锥篇》,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8页。物相交错,是“一与不一相辅成文”,“一”即质,“不一”即文,谓文饰,引申言之则谓文章。《革·象》所言“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实质上也包含着质文的关系问题。
王弼既更明确地强调质文并重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又论述了质文同体的互相包融的关系。前者是对《易传》审美观念的强化,后者是对《易传》审美观念的拓展。
第一,质文相辅相成的关系。质待文而成,文因质而生,亦即刘熙载所言“一与不一相辅成文”。他提出“文在中,美之至”的审美观念,所涉及的黄中之色与下裳之饰,恰恰象征了质与文的关系。以中和之性、柔顺之德为质,以下裳之饰为文,二者相辅相成,既符合《论语》所说的“文质彬彬”的君子境界,也是至高的审美境界。而他所提出的“含美而可正”,从美学意义看,柔顺为柔,贞正为刚;柔顺贞正是文德之美的外在表现,柔顺是其“文”,贞正是其“德”,文与德也是一种文与质的关系。这就补充说明了“文在中,美之至”的内涵。王弼还指出,质文一旦相悖,行之则凶,如《中孚·上九》注:“翰,高飞也。飞音者,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居卦之上,处信之终,信终则衰,忠笃内丧,华美外扬,故曰‘翰音登于天’也。”“翰音”象征美誉。一旦诚信衰减、忠厚丧失,唯有盛名外扬,名实相悖,则处于凶险之境。从儒家伦理美学而言,“信终”“忠笃”为质,“华美外扬”即文,质文悖离,就违背了“文质彬彬”的审美要求。这就从反面论证了质文并重的必要性、唯一性。
第二,质文异质同体的关系。质为内质,文谓外饰,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王弼又认为,二者之间也互相包融、同处一体。“一”即“不一”,“不一”即“一”。如上文所引《履·九二》注,王弼指出,践行于道,贵在谦让,不喜自满,务在诚信,而不文过饰非。以阳处阴,能够履中谦退,隐之与显,在心齐等,斯则“履道之美,于斯为盛”。“履道”是君子之行的基本准则,所履之道以谦诚为具体表现,而谦诚之行是行为之至美。可见,谦诚既是君子履道的内在之质,也是君子行为的外在之文。二者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是异质同体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王弼看来,质文既有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也有异质同体的包融关系;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是“举一贯寓于万殊”,异质同体的包融关系是“举万殊寓于一贯”。从哲学上说,前者涉及现象与本质的二元性,由现象抽象本质;后者涉及现象与本质的同步性,由现象直接呈现本质。以佛理喻之,前者是缘色证空,后者是即色即空。从诗学上说,前者是无限与有限的关系,后者是有限即无限的关系。玄言诗或直接说理,或因象寓理,都与王弼的审美思想有密切关系。
由上所论,王弼审美理论由形下而向形上抽象,即由爻道、卦道逐步向至道进行本质抽象,凸显义理为美的审美理念,通过论述质与文、理与文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刻揭示了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与正始以降诗歌风貌的转变、诗学观念的转变有或隐或显的直接联系。
从嬗变趋向上看,上述四个方面,对于两晋名士柔心应世、内怀文明的人格建构,柔性诗风中追求阳刚之气的诗歌风貌,基于情性合一的“缘情”理论,以及以义理为美又结藻清英的诗格选择,都有着深刻影响。
(责任编辑:陆晓芳)
2016-08-22
刘运好(1955—),男,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8BZW032)的阶段性成果。
I01
A
1003-4145[2016]12-004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