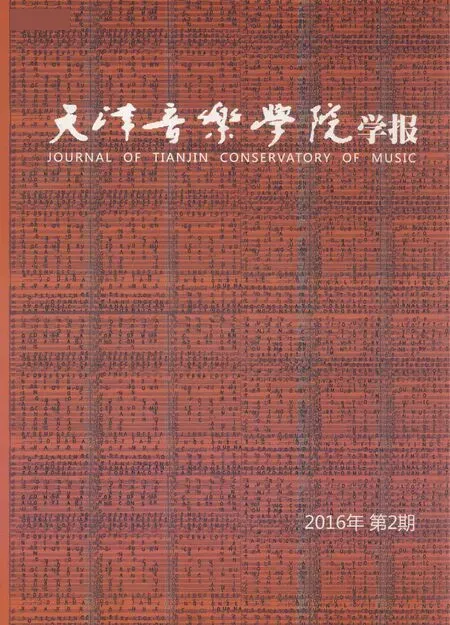在“香港中乐团国际作曲家高峰会”上的发言
姜莹
在“香港中乐团国际作曲家高峰会”上的发言
姜莹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大家好!很高兴这次来参加由香港中乐团举办的国际作曲家高峰会。本来我只是想讲一讲关于民族器乐配器方面的内容,但香港中乐团希望我对北京地区的中乐(编者注:与中国大陆所称“民乐”的范畴大体一致)发展进行综述,而这个论题涉及范围较大,除中央民族乐团之外,北京地区还有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刚刚成立的北京民族乐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学生民族乐团、其它大学学生乐团及社会非专业乐团等等,这么大范围很难在短时间内做深入阐述,经过思考之后,我决定缩小范围,仅就中央民族乐团的创作历程进行系统梳理,随后我再对民族乐队配器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与各位同行进行探讨交流。
一、中央民族乐团创作综述
我试从四个时期对中央民族乐团的创作进行详细阐述:
(一)20世纪60年代
1960年中央民族乐团建团之初,当时周恩来总理对乐团在音乐创作提出了两个主要方面的建议:第一,广泛搜集、发掘、整理各个兄弟民族的优秀曲目;第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创造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为此,以李焕之、秦鹏章先生为代表的中央民族乐团老一辈民族音乐家们创作、改编了一大批优秀民族音乐作品,如《将军令》《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春节序曲》等;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原创作品,如刘文金《太行印象》、王铁锤《赶路》、《油田的早晨》等。这一时期乐团创作主要以挖掘整理优秀民族音乐遗产为目的而展开,体现了乐团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进行多方面的保护。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
以刘文金先生为代表的众多专业作曲家开始关注各类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这使得中国当代民族器乐作品的发展进入一个历史性的高峰。这一时期由我团作曲家原创和社会委约创作的作品主要有:笛子独奏《春到湘江》(宁保生1976年创作,作曲者时为中央民族乐团演奏员);民族管弦乐《难忘的泼水节》(刘文金1978年为纪念周总理而作,中央民族乐团首演);民乐合奏《非洲战鼓》(霍庆桥、朱啸林、王志信创作,团史自1979年起有该曲演出记载,三位曲作者均供职于中央民族乐团);交响音画《水之声》(阎惠昌1982年创作,并于1983年在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民族器乐)评奖获奖作品,曲作者1983年-1991年在中央民族乐团任首席指挥);民族拉弦乐合奏《二泉映月》(李焕之1985年编配);民族交响音画《塔克拉玛干掠影》(金湘1985年创作,曲作者亲自指挥中央民族乐团首演)、民族交响组歌《诗经五首》(金湘1985年创作,中央民族乐团委约)、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刘星1986年创作,首演于1987年,张鑫华独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笛子协奏曲《咏春三章》(张小夫曲,首演于1988年北京第一届中国艺术节,王次恒独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这一时期,随着作品的繁荣,民族乐队在编制组合上也逐步完善定型。
(三)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
乐团的创作管理逐步转型到以正式委约方式邀请作曲家创作,这一时期乐团委约创作的优秀作品有:笛子协奏曲《鹰之恋》(刘文金,1990年)、民族管弦乐《茉莉花》(刘文金,1998年)、民族管弦乐《戏彩》(刘文金,2002年)、琵琶协奏曲《春秋》(唐建平,1994年)、民族管弦乐《后土》(唐建平,1997年)、笛子协奏曲《飞歌》(唐建平,2002年)、民族管弦乐《龙舞》(徐昌俊,1999)、民族管弦乐《日月山》(郭文景,2002)、琵琶协奏曲《古道随想》(许知俊,2003)以及1998年乐团赴维也纳金色大厅委约首演的一批作品等等。
(四)21世纪以来
自新世纪以来,中央民族乐团的音乐创作呈现出多样化、职业化的发展态势,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承办了文化部主办的历届全国民族音乐作品比赛活动,通过比赛视奏了大量全国各地的作品,这为民族器乐多视角、多思维的创作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如获奖的作品:程大兆《老鼠娶亲》(第九届,2003年);刘长远《抒情变奏曲》(第九届,2003年);常平《乐队协奏曲》(第十二届,2006年)、王建民《第三二胡狂想曲》(第十二届,2006年)、《第四二胡狂想曲》(第十五届,2010年);王丹红《云山雁邈》(第十二届,2006年)、《弦上秧歌》(第十五届,2010年);李滨扬《天下黄河》(第十五届,2010年);姜莹《丝绸之路》和《印象国乐·大曲》(第十八届,2014年)等。2016年举办了《全国青少年民族管弦乐作品征集展演》涌现了一批为广大青少年量身定制的优秀作品,由于海内外的学生乐团为数众多,而适合学生乐团的作品相对匮乏,有些作品内容太深奥、技巧太难,对于学生乐团特别是中小学生乐团并不适用。因此,乐团希望通过征集,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更多适合他们排练演出的作品,这也是为民族音乐传承与普及做出的具有特殊社会意义和贡献的活动。
第二,大型主题性音乐会。其中包括:纪念建国六十周年音乐会《江山如此多娇》(2010)、系列音乐会《泱泱国风》(该音乐会是乐团自2011年创建的品牌音乐会,每年都有一套新作品)、纪念建党九十周年音乐会《艰难·辉煌》(2011)、唐建平作曲的民族音乐诗剧《牛郎织女》(2012)、易立明导演、郝维亚作曲的音乐戏剧《西游梦》(是早期的探索性的后现代剧,2012)、大型佛教祈福音乐会《梵呗之音》(2012)、“一带一路”专题音乐会《丝绸之路》(201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音乐会《国乐的追思》(201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音乐会《土地与生命的赞歌》(我们邀请了众多民间不同剧种的乐手来呈现原生态的音乐,如福建南音、陇东道情,甘肃花儿、舟山锣鼓、侗族大歌等等,这场音乐会里也有根据这些原生态的素材来重新创作、改编的曲目。该音乐会是向民间音乐学习、向传统致敬的音乐会,在同一场音乐会既听到了传统、又感受到当代作曲家如何运用传统素材来体现当代人对传统的理解和发展,2015)等。
第三,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让演奏家与作曲家加强合作。如在吴玉霞《千秋颂》琵琶独奏音乐会上推出的琵琶协奏曲《春秋》(唐建平,1994);冯晓泉、曾格格《泉释风格》笛子、唢呐独奏音乐会推出的《雪山》(冯晓泉,2010)、赵聪《指上天下》琵琶独奏音乐会上推出的《绽放》(马久越曲、赵聪改编、胡廷江编配,2013)、《云想花想》(王丹红曲);吴琳《空谷幽兰》箜篌独奏音乐会推出的箜篌协奏曲《空谷幽兰》(刘长远,2016);王次恒作为演奏家也积极与作曲家合作推出了《空山望月》(王直、王次恒曲、姜莹改编,2012)、《燕归来》(王次恒曲、胡廷江配器,2013)、《梦家园》(王次恒曲、李博配器,2015)等多首笛子与乐队的作品。2014年王丹红《弦上狂想》作品音乐会中推出的《太阳颂》、扬琴协奏曲《狂想曲》等,以及新一代青年演奏家在独奏音乐会中与青年作曲家的合作等。
第四,为帮扶全国各地民族乐团共同发展,委约创作多台具有地方风格特色的剧目。例如,帮扶新疆民族乐团推出的《美丽新疆》(2011);西藏民族乐团的《西藏春天》(2012);贵州黔东南州民族乐团的苗族歌舞剧《仰欧桑》(唐建平曲,2013);侗族大歌音乐剧《行歌坐月》(陈思昂曲,2014);成都民族乐团《锦城丝管》(2013);浙江民族乐团《海纳百川》(2015);甘肃省歌舞剧院《甘声肃韵》(2016);重庆民族乐团民族管弦乐清唱剧《大地悲歌》(2016)等,共计帮扶十个地方民族乐团。我们不光是请地方乐团来和我们同台演出,更为他们委约适合他们风格的作品。我曾经问席强团长为什么要帮扶这些地方乐团,他说:“民族音乐真正的蓬勃发展不是只把自己乐团或是几个主流的这几个乐团建设好,加快各个地区的乐团一起发展起来,这种大繁荣、大发展才是一个事业的真正蓬勃!”
第五,委约创作及改编当代民族管弦乐单曲体作品每年达70首以上。如:琵琶与乐队《听江南》(叶国辉,2007年)、民族管弦乐与合唱《我的祖国》(刘文金,2009年)、《忆江南》(顾冠仁,2010年)、民族管弦乐《天下为公》(程大兆,2011年)、二胡协奏曲《风雨思秋》(关乃忠,2011年)、二胡协奏曲《天籁华吟》(关乃忠,2014年)、二胡协奏曲《故园》(瞿小松,2011年)、民族管弦乐《百年华章》(王丹红,2011年)、箜篌与乐队《伎乐天》(王丹红,2014年)、箜篌与乐队《秋江月夜》(郝维亚,2012年)、二胡协奏曲《塞上弦鸣》(李滨扬,2013年)、二胡协奏曲《天香》(常平,2013年)、民族管弦乐《桃花红杏花白》(张朝,2013年)、民族管弦乐《平沙落雁》(杨青,2013年)、琵琶协奏曲《坐看云起》(陈思昂,2014年)、琵琶协奏曲《丝路飞天》(赵聪、尹天虎,2014年)、二胡协奏曲《重上井岗》(何占豪,2015年)、二胡协奏曲《丝银》(罗麦朔,2015年)、《广板》(徐孟东,2015年)、胡琴与乐队《川戏》(张坚,2015)、民族管弦乐《开洋》(赵东升,2015年)、民乐小合奏《猜嬉》(赵东升,2015年)、民族管弦乐《如意》(王崴,2015年)、民族管弦乐《国风》(赵季平,2015年)等。乐团在委约创作上是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进行作品创作和推广,一部分是以学术探索性为前提的创作、另一部分是面对普通观众群体的市场化的改编创作,大量的委约新作品不仅为乐团演奏员提供了更多接触不同风格作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更多专业作曲家提供了视奏及演出新作品的平台、这是民族管弦乐作品发展的必经之路。
除了以上四个阶段的梳理,我还想着重讲一讲关于民族音乐会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多元化创新。
最为典型的就是2013年的《印象国乐》和2015年的《又见国乐》。这两部剧目都是由著名导演王潮歌执导,我是这两部剧目的作曲和编曲。2013年,当时我刚从上海民族乐团调入中央民族乐团,正值乐团计划做一场大型的音乐会剧目,作为这个剧目的作曲,我跟乐团领导提出一个建议:如果我们的音乐会想要创新,那一定要请一位大导演来和我们做一次跨界合作。我在学生时代就看过王潮歌的一些实景演出作品以及她的一些访谈,所以我当时坚信地认为要是能请到王导来执导,一定会为乐团带来一种全新的音乐会模式。后来我和席强团长一起拜访了王潮歌导演,在经过数次与王导的沟通后,终于请到了这位具有创新精神的导演。这两部剧目的创作经过了无数次的讨论与修改,因为创作之初,没有先例可寻,不像歌剧、音乐剧国外已经有很多成功例子可参考,所以当时我们真的探索得很辛苦也很努力,值得欣慰的是,这两部剧真的成功了!
现在看来,我很肯定的预测,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音乐会类型,就如同当时西方创造了“歌剧”这样的新品种,歌剧或者音乐剧是用歌词和语言做为主体呈现的音乐会,而我们的这两部剧目及未来要创作的新剧目,是用器乐演奏与语言共同来讲述及呈现类似歌剧的具有戏剧性及故事性的新形式音乐会,当然包括运用多媒体、舞美装置等现代化技术来辅助完成。就因为这两部剧目对舞台要求的特殊性,我们常常无法预定到剧院歌剧厅的档期,有人问:“你们不是民族乐团吗,为什么要去歌剧厅演出啊?”或者说:“你们为什么要说台词、要表演、还要演唱呢?这不是话剧团、歌剧团的事儿吗?”可是我想表达一种理念,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创新时代,早在十几年前,电视机就只能看电视,录音机就只能听音乐,照相机就只能拍照,电话机也只能打电话。但是现在一个手机上很多传统的单一性的功能都综合在了一起,你能说它不是一种必然的发展吗?你能否认这种具有多功能的综合体所带给人类的全面感受吗?所以,我认为要想让民族音乐不被时代所淘汰、不成为博物馆的艺术,那就必须寻求新的发展,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摒弃传统的音乐会模式。我们每年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新创常规音乐会就有好几十场,而每两年大胆尝试创作一部具有探索性、颠覆性的新形式音乐会也是中央民族乐团为民族音乐的多元发展所必须去探索、尝试的发展之路。为当今民族音乐文艺舞台创作与表演摸索一种新的音乐会类型。这两部剧目近三年来的一百多场演出所反映的社会效应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有信心认为,这是符合当代民族音乐在继承、改革、创新指导思想下的舞台艺术精品,而且在全国巡演时,所到之处受到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与喜爱,很多年轻的观众开始重新认识民乐、重新喜欢民乐。两部剧改变了民乐以往在他们心中的老旧印象。2013年《印象国乐》剧目一年的商业演出为乐团创收经济效益达2200多万元,《又见国乐》2015年为乐团创收达到2300多万元。2015年12月,我们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乐团不仅得到了美国主流观众和媒体的认同,《华盛顿邮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又见国乐》,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大力宣传,演出后肯尼迪艺术中心决定把《又见国乐》的海报和《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卡门》《天鹅湖》等诸多世界经典歌剧、音乐剧海报一起被永久悬挂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后台展览墙上,我想这就是中国民族音乐走向西方主流艺术殿堂的标志!
二、关于民族乐队配器的思考
(根据不同乐器特色对民族管弦乐配器的思考)
在阐述观点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去年我去新疆采风的时候,一个当地的音乐家朋友组织了十位新疆乐手接待我们,我怀着非常好奇和期待的心情想在现场聆听那些独特的乐器所发出的声音,可是你知道,他们给我们演奏的第一首乐曲居然是《喜洋洋》。我开始觉得挺好笑的,但是听着听着就觉得这些乐器挺受委屈,他们被不适合他们的语言和配器方式束缚了,所以完全听不到光彩和灵魂。后来他们又给我们演奏了纯正的新疆音乐,这让我有了很鲜明的对比,那个艾介克(编者注:拉弦乐器,是维吾尔族乐队伴奏和合奏中的主要乐器)瞬间变成了一个风情万种的维吾尔族姑娘、热瓦甫(编者注: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弹弦乐器)就突然变成了一个热情奔放的小伙、而萨塔尔(编者注:维吾尔族弓拉弦鸣乐器)那种苍凉的声音就像是一个老者的歌声,直接把你带到了茫茫的戈壁大漠,他们的演奏在那一刻才给了我无限的想象和感动。后来我们又去了新疆的一个大型艺术团,走进他们的排练厅,我们看到了整齐划一的新疆乐队按照汉族民族乐团的乐器摆放法排列,有高中低艾介克,热瓦甫也是有高中低的,代表着我们的弹拨乐组,还有在卡龙琴(编者注:维吾尔族古老的民间弹拨乐器)边上还配了一个扬琴,卡龙琴外形有的像扬琴,演奏者在右手拿拨片演奏旋律,左手拿铁制揉弦器在琴弦上推抹,出现了很多装饰音,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乐器也是很有特色的,但是当一个扬琴在大乐队里和这个卡龙琴演奏同一旋律时,你完全感受不到那种特点了,这好比我们配器中把古筝与琵琶用作同一音型同一旋律,其实他们是互相抵消、互相削弱的。还有他们的那些高中低艾介克演奏和弦铺底的效果其实就是模仿西方的弦乐组和声,让热瓦甫整齐划一的齐奏,没有加花,没有节奏自由的空间,不像在独奏时的那种灵动和自由,所以新疆乐队这种写法带给我的感受和我所期待的有很大落差。从这件事给我带来一个思考,作为汉族人我在听新疆乐队的时候其实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在感受的,同样就像一个外国人在听我们的民族乐队,他一定是希望听到那种独特性,就像我去听新疆的民族乐队一样,我不希望新疆的少数民族乐器抹杀自己的个性去追求共性,就如同外国人不希望中国的民族乐队在模仿他们而没有了我们自己的特点。所以,作为一位作曲家,我开始思考,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种除了西方作曲法之外的创作理念去写作一个民族乐队吗?我们的多声思维能否从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音乐里去挖掘借鉴呢?我们的配器是否可以让乐队中的每件乐器都展示出他们的特点而变得无可替代呢?而且根据不同音乐的风格,每种乐器都有千变万化的演奏法。
其实在我们的民族乐队里,一件乐器就是一种音色,无谓的做音色叠加很难融合但会同化不同乐器的个性,甚至是脏了乐队的音响。弦乐组、弹拨乐组、管乐组,每一组本身还包含着多种音色,比如,唢呐和笛子怎么融合?更不用说弹拨乐组和拉弦乐。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西方音乐作品中的那种音色的融合性,如果我们能用好每件乐器的个性,在表达个性的同时处理好这种声部关系的平衡,当把他们加在一起所达到的那种个性张力以及戏剧性,可能是很独特、很有威力的。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作品在配器时没有挖掘出民族乐器的特点,比如说:在独奏琵琶谱里有很多左、右手技术,我们在写作大乐队的时候有这么细致地去考虑吗?不要说左手的推拉吟柔了,就光右手的很多演奏法已经很丰富,并且是西方乐器不能替代的,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让每件乐器演奏谱面上的一个直白的音,那个性就会被追求共性的同时,切得一干二净,诸如装饰音、推拉音、滑音、自由的节奏呼吸,都被压缩成统一化,那么我们民族乐队的长处和特点就根本展现不出来,那我们还拿什么去和西方乐队去抗衡呢?!如果一个我们自己写的中乐作品,没有其乐器演奏上及配器上的独特性,很容易的就移植到交响乐队,那还需要民族乐队来演奏吗?!
所以,经过反思,我认为西方经典音乐作品好的地方是需要去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自己那么多民族的风格、特点我为什么不深入的去研究、去借鉴、去提炼呢?还有除了西方之外的,比如印度音乐、东南亚音乐、中东音乐中也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而这种同属于东方国家的音乐语言及风格是否更适合中国的乐器语言特点及文化背景呢?
我去年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里看到了上百种中国乐器,当时第一想法就是如果把这些乐器集合在一起来写一首作品的话,该怎么写?我绝不会抹杀他们的个性而去追求共性,如果这些品种不一的乐器放在一起却不把他们的特点展现出来,那还不如就用同一种乐器。所以反观我们现在的民族管弦乐队的创作,什么样的配器、什么样的音响,当然首先取决每个作曲家自己的美学观,其次我觉得我们的确还有很大空间,只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家“孩子”身上的潜力和优点,不要一味和邻居家的“孩子”去比,或许,只有当我们把自己乐器的潜力发挥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因为自己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受到别人的关注和尊敬!
2016-05-26 中图分类号:J604
A
1008-2530(2016)02-0100-05
姜莹(1983-),女,中央民族乐团驻团作曲家(北京,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