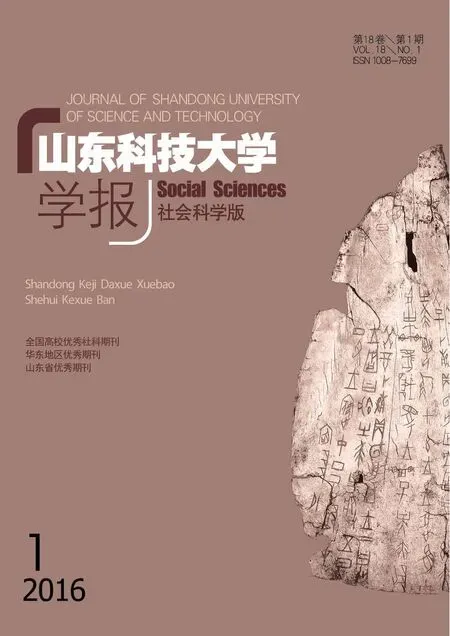何谓启蒙:自康德至福柯的经典文本
——新千年之启蒙再论(一)
胡长兵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 贵州 贵阳,550002)
何谓启蒙:自康德至福柯的经典文本
——新千年之启蒙再论(一)
胡长兵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 贵州 贵阳,550002)
摘要:什么是启蒙?18世纪末以来,理论家们作了种种的解说。康德将其定义为理智的成熟;霍克海默认为它是自由与统治间的抉择;哈贝马斯则主张,启蒙是一项自由和解放的人道主义事业;按照福柯,启蒙却是一种永久批判的气质。在当今,启蒙的未来仍在人们的不懈阐释中。
关键词:启蒙;康德;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福柯
“一个幽灵——启蒙,徘徊在社会科学领域。”[1]12托马斯·奥斯本如是写道。据德雷福斯等观察,自康德的经典论文面世以来,关于启蒙,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引起一场论争。[2]274步入新千年,此一议题仍未过时。“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之后……启蒙运动的传承已经成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争议的领域。人权经常被用来作为独裁权力的意识形态借口;西方国家的安全成为限制个人自由的理由”。[3]1人们指出,“以警察国家来应对恐怖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失策,而且是对人类的践踏……我们曾经走过那条道路。”告诫已然发出,“在秩序的力量面前‘暂时’牺牲自由永远不会是暂时的”。[4]当下,启蒙或应重申。
一、康德:启蒙是谓成熟
1784年,德国一家报纸《柏林月刊》以“什么是启蒙”为题征文,康德关于该题释义的名作《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源此而出。文中,康德对启蒙一词作了典范的定义:启蒙是人们摆脱幼稚的未成年状态、监护状态,迈向理性自由的成熟自立阶段。在意志、权威和理性三者交织营构的三度空间中,它最终将完成对其前身即蒙昧状况的根本替换。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5]22
康德的这篇应试文章不长。在当时德国的智识生活中,人们正试图思量施行思想启蒙与否,或有论者惊惧其将引发革命的祸乱或道德的堕落。因此,论文的目标在于简明地阐述启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及对人类进步的基础功用。(1)预设了一个先验理念:理性自由、意志自律为人类的天性,启蒙是神圣的人权;(2)给出了一个著名区分:理性之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按康德的说明,“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5]24-25*关于康德的这一划分,米歇尔·福柯曾作解说,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这三者相互重迭时,便有“启蒙”。米歇尔·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532.后者的原则是消极顺从性的:“惟命是从,勿需推理”。但在前者,理性之积极的自由的使用,对人们而言甚至意味着一种天职和责任。
关于启蒙的论证,康德采取了二个主要步骤:(1)依据设定的绝对性精神层面的要求即天赋的理智自由,对启蒙必要性的阐明;(2)凭借基本的约束条件即理性能力的二重划分,考虑到体制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等诸种实在的社会结构性限制,对其可行性的证明。具体而言,首先,根据上面开列的第一个前提,在世俗算计理性下的懒惰、怯懦和短视,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甘受监护之“伪天性”被简单剥除后,这便仿佛与人们曾经摆脱自然的束缚一样,启蒙的必要性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依康德的形象说法,“绝大部分的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5]23同时,这一论据也为启蒙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既然意志和理性的自由自主是人的天性,当然也就无需额外的成本。
其次,社会共同体依其定义,必然在和成员个体的内在关系上对理性的行使施加一些确凿的制约。康德坦言:“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坏这一目的。”这就是说,在理性的私下使用时,“人们必须服从”,而不应恣意争执。但是,这一羁束因素不会构成重要的困扰。因为,在理性的公开运用中,“作为公民社会的成员而论,则他是绝对可以争辩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损于他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所从事的那种事业。”[5]25正是根植于个体自我同时承负的公共理性批判和限定性经验职责的必要张力,现行社会中诸多制度和规范才能获致稳妥、顺畅的运行,进而开启潜在的进化时空。据此,通过理性二分法的界说,启蒙的可行性显见得有理有节、难以挑剔。
最后,康德指出,尽管当前时代未能完成启蒙,但毕竟正处于启蒙之中。若依上所论,则其显见为人类希冀、献身之要举。
应该说,虽然以上康德对启蒙论题作了如许的畅想,却仍旧遗留下太多的问题和疑难。更紧要的,应是缘于种种繁复多变的历史经验的未曾降临。19世纪后,现代历史的亲历者依其自身的体验络绎续写了启蒙这一关乎现代性本质的深重话题。
二、霍克海默:启蒙返转神话
“思想启蒙运动……使人变得更无主见、更无意志……在‘进步’的幌子下,会使人变得更卑贱,使人变得更顺从统治!”[6]31对尼采这一辛辣的点评,霍克海默等极为赞同,它深刻洞察了启蒙理性的辩证本性,“正是尼采,揭示了启蒙与统治之间的矛盾关系。”[7]45假设说,18世纪下半叶的康德眼中,启蒙理念尚是一朵亟需呵护的娇弱花朵,但候其漫漫长成至20世纪中期,在霍克海默等看来,其枝头垂挂的更多却是累累恶果。理想和现实间的极度反差与失落,激荡出一轮康德以来对启蒙问题的最为彻底沉重的反思。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明了,霍克海默等之所以将启蒙概念与神话一词相并置对照,进行范畴泛化的缘由。按照他们的诊断,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这一特称术语,不过是广义的启蒙精神史里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一个样本,“理性的自我破坏倾向的一个例证”。[8]372
《启蒙辩证法》开篇伊始,霍克海默等便即痛陈:“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设若原初的梦幻之花,亦即“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7]1,那么,近乎荒诞悖谬地,在历史大潮的冲击下,下列每一领域收获的却是截然相反的苦果:(1)启蒙向神话的吊诡转化。“启蒙转变成了实证论,转变成了事实的神话,转变成了知性与敌对精神的一致”。[7]新版前言(2)人与自然的对抗。“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3)人本身的异化。“泛灵论使对象精神化,而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物化了……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4)社会的总体化、极权化。“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换言之,“在机器发展已经转变为机器控制的地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趋向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的是对人的总体把握。”[7]10,25,32,33一言以蔽之,“在个人那里,独立思考败坏了;在社会那里,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分离了……理性……从洞察万物之意义的力量中蜕变成为自我保存的纯粹工具性”。[8]369
曾经康德那一乐观的、常识的理性概念及其煞费苦心之二重界分,已不再有效。理性之实证主义的自我消解与破坏的内在机制,将其一直贯彻到概念本身。因此,“在这里区分个人理性和社会生活中的理性是无用的”。[8]372
按照霍克海默等的描述,启蒙理想之自我颠覆的酷烈病象与终极病因如上所揭。作为联结二者的媒介,其主导病理则可简述如下:(1)理智生活中,科学的客观化扩张成自在的客观性,理性简缩为单纯的工具理性,对意义、价值问题的摒弃最终使思想丧失批判性力量;(2)社会生活里,技术理性的普遍化和冷漠自治,则催生了机构的集权和个体的空乏。
启蒙初衷是,发展客观抽象的科学理性以替换原始的神话思维,从而对抗、摆脱大自然主宰的恐惧和奴役,但这一理性依其自身逻辑逐渐普遍化和破坏性地扩展。“就法国的启蒙运动而论,它试图攻击一切形式的神话……包括被认为对共同体的运行起着核心作用的一套原则,即伦理的真理,有时候也包括宗教的真理。”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持久地攻击对诸神灵的敬畏而同时仍然保持对普遍道德的范畴和原则的崇敬”。[8]370
向工业主义和大众文化时代的过渡中,形而上学作为某种神话被攻击、废黜了。这且仅非一种内向的思想进程。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个人观念,无论灵魂、先验自我,和所有形而上学范畴一样,“面对现代科学的概念框架时,它们显得毫无理性”,科学及其单一真理的观念“绝对反对认可灵魂和个人之类的实体”。另一方面,有形的物质力量同时参与了这一态势的因果构造。“就个人而言,意识形态的衰退显然反映了他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削弱。他的起落是与中产阶级财产的命运深刻地交织在一起的。”早先农耕社会里,作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人们曾倚赖自律的个性来安排制造、销售等各项经济业务;可“在我们的时代,这些事情正越来越被各种集体的力量所接管。”[8]372,373主体性、自我被强大的客观化的社会结构力量无情地碾碎磨平,残留的仅是适应与服从。
若如说,个性的匮乏乃至消失从一个角度确证了经济领域集权格局的形成,那么,政治系统亦是如此。当“技术发展割断了与任何假想的永恒实体或原则的直接或质朴的关联”,往昔的形上理论便失去了其现实的社会基础而被偷运为一些受人操控的意识形态,民众别无选择地以一种盲目的姿态来领受这些替代性赝品。于是,“目标就取代了真理,狂热的效忠就取代了质朴的信仰。这就是我们在历史中(现在又在德国和其他法西斯国家中)如此频繁地目睹的东西。”[8]373,374极权主义诞生了。
面对如此惨烈的启蒙之曾非意料的结果,这仅仅是一个或可绕开的历史陷阱还是注定的致命危局?在霍克海默等看来,本质上正是后者。这便是他们将其分析结论取名为“启蒙辩证法”的来由。
三、哈贝马斯:启蒙仍待推进
“在哈贝马斯的当代批判理论里,经典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僵局不再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9]身为该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继承了霍克海默等前辈的事业。他一方面续守启蒙与理性信仰,同时大幅修正旧有解释,作出了全新的阐发:(1)理性扩充为交往理性,主体性进展至主体间性;(2)启蒙范畴不再与神话相对,而是回复到惯常用法,启蒙亦即现代性。
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霍克海默于启蒙分析中的“工具理性批判坚持的依然还是主体哲学的前提”。[10]373自近代笛卡尔以来,这一理性主义哲学始终囿于个体的内在主观性中寻求主体的奠基地位,但实际上,“纯粹理性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体现在交往行为语境和生活世界结构当中的理性”。[11]因此,和霍克海默等的误认不同,“最能反映现代意识地位的不是自我持存……社会生活关系是通过其成员受媒介控制的目的理性行为以及通过扎根在每个人交往实践过程中的共同意志而获得再生产的”。进而,最为着重的异化或“物化问题……与其说是源于已经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不如说是源于以下方面:即已经释放出来的功能主义理性对交往社会化过程中所固有的理性要求视而不见,从而使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流于空泛。”[10]380,381
依赖于以上的范式转换,哈贝马斯得以推演出,启蒙现代性仍是一桩未竟的事业,进步、解放的内涵尚未耗竭。这在1980年阿多诺奖的领奖致词“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里,从社会理论视角给予了简明的阐述。
由18世纪启蒙哲学家开创的现代派工程的任务是,分别依照它们自己的特性,坚定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力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释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践,也就是理性地塑造生活。[12]112-113
例如,准此定义,可以指出,“康德的三大‘批判’是对不同的理性区域彼此独立所做出的一种反应”。[13]可是,随着这一幅宏伟画卷的史诗性展开,却衍生了种种偏颇或片面的理解和设计。比方说,一种对现代之断代观念的无限崇尚。
据哈贝马斯的粗略追溯,虽然“现代的”一词早于5世纪使用,但迟至1850年,人们依恃浪漫主义思潮才释放了一种极端的现代性意识——连法国启蒙之永远进步的完美主义都未曾彻底割断古代经典的某些遗韵,“这种意识摆脱了所有的历史关联,整体上保留的只是一种对传统、对历史的抽象对立。”按此,“所有能帮助自发更新的时代精神的现时性得到客观表达的,都被视为现代的。”[12]108惟一的标志就是新。
精神性的审美领域里,现代性之于现时、新的阐释与追求获得了最充分纯粹的展示。源自波德莱尔的推举,先锋派等美学现代派对“变幻的时间意识”极度敏感和张扬,表现在对新事物的崇拜以及对昙花一现、过眼云烟之物的抬升与欢庆等。哈贝马斯指明,如此种种所演绎的抽象的反历史立场,理论后果之一就是:“颓废直接在野蛮、野性和未开化之中看到了自己”。更概括地,美学现代派“想打破历史连续性的无政府主义的意图说明了一种美学意识的颠覆力量,这种意识反对传统的标准化成果,依赖于对一切标准进行反叛的经验而生存,使道德上善的与实际有用的都变得中立”[12]109,便似波德莱尔之言,“真善美不可分离……不过是现代哲学胡说的臆造罢了”。[14]73藉此,他们能够“沉醉于那种源于世俗化进程的惊恐带来的魅力——又在不断逃避这种进程的庸俗结果”。[12]109
在更广泛的社会场域,文化现代派或文化理性主义一直与美学现代派血肉相系。20世纪70年代新保守主义者丹尼尔·贝尔对此曾作过批评性的描述:先锋派艺术渗入了日常生活的价值导向,以现代主义观念感染着生活空间。更具体地,“文化(在严肃的领域)已被颠覆资产阶级生活的现代主义原则所支配,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被享乐主义所支配,享乐主义又摧毁了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新教伦理。”由此而来的后果是,“今天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将自我目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依丹尼尔·贝尔的论断,这种“机制断裂就形成了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15]
对于贝尔的结论,哈贝马斯并不认同,因为它错误地将启蒙工程推进中所引致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直接归罪于一种仅仅间接地介入了此一进程的文化因素。进一步地,无论文化现代派还是新保守主义,它们都应置放于前一工程的预想目标——广阔的生活世界理性化的现象中加以理解,都是对这一宏大历史旅程的一些片段反应。
遵循启蒙现代性的指引,在上述文化理性主义的行动中,曾经存身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世界构想中的实质理性一分为三,分别在科学、伦理与艺术领域内细化出特定的有效性要求:认知与真理性、准则与正确性、审美与品味。其后,这些文化行为体系的专业化和机构化随之兴起,其各自区域中的内部历史和自身规律也日益凸显出来。然则,紧要处是,人们未及足够重视到理性的分化及其发展,这一切无可避免地意味着,专家文化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急遽拉大,其理智成果不再能够毫无前提地为日常实践所享有。随着文化的理性化,生活空间的传统实质被贬低,面临着贫困化的危险。
缘于此一轻忽及其导致的结果虚张效应,即便像“启蒙的后卫队”如霍克海默等,乐观主义业已踪影全无,“现代派工程也是支离破碎。他们各自只信任理性细化后的某个因素。”比如,卡尔·波普尔坚守启蒙的科学批判信念但全然盲视于美学;相反,“在阿多诺那里,强烈的理性要求则退入了深奥的艺术作品的抨击姿态中”。[12]113
至此,启蒙现代性使命的几种主要阐释,即美学现代派、文化现代派以及某些批评者如当代的新保守主义等,已如上论。在哈贝马斯看来,这诸种思想规划的失败根源在于,未能深刻觉察出近代以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所引发的理性分化及其相应的文化领域和专业系统的分隔。举例来说,新保守主义所赖以立身的新民粹主义氛围乃是针对大规模的无可逆转的单一系统理性之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一种自发的情绪反应,即这种抗议“集中表达了对那些破坏城市和自然环境、破坏人类和谐生存的力量的普遍存在的恐惧”。可因昧之于此,丹尼尔·贝尔仅仅开出一付某场宗教改革或承继往昔传统的简单药方。固然,对专门领域与生活世界间的分离,也曾有过修弥裂痕、“扬弃”专家文化的一些尝试。最明显的例子出现在艺术中。譬如,超现实主义便试图打破貌似自给自足的艺术范围,“将一切视为艺术,将所有人称为艺术家,将美学评判与主体经历的表述等同起来”,凭此希望填平其与生活间的鸿沟。但这一过激的纲领及其举措终究难脱失败的结局。按哈贝马斯的判定,超现实主义对先锋派的反叛及其流产证实了一种错误扬弃行为的双重误解:一方面,某一我行我素自在发展的文化容器被打破,则其在语义学上必将枯萎,从而无能兑现其解放的承诺。更重要的,“一种已经物化的、致力于认知与道德实践和美学表述的无拘无束的共同作用的日常实践,并不能通过某一强行打开的文化领域的联系而康复。”超现实主义的简单化举措“充其量也只能是让一种单向性和一种抽象性由另一种取代”,哈贝马斯强调,“生存世界的理解过程需要全方位的文化传承”。[12]112,115,116
迄今为止,无疑存在着各种迷失、歧误,但哈贝马斯仍然强烈建议,亟需的是吸取教训,“而不应当放弃现代派及其工程本身”。根据上面的讨论,其可能性绝非完全的玄想,并且得以一些反向间接的理论启示和支持。另外,即便依正面论证的视角,市民艺术——即从生活世界的视角出发来接收专家文化,它的某种成功或许也可大略提示出对启蒙现代性的坚持的可行性。当普通民众以非专家的身份却熟谙地将艺术批评溶入到个人、集体的生活形式中时,“审美经验革新的不仅仅是对需求的阐释,我们正是借助这种阐释感知世界的;它同时也介入了认知阐释和准则方面的期待,改变所有因素间互指的方式。”在此,专门的文化领域与生活世界间的深度分裂获得了相互的和解,曾经启蒙的某些奢想已经转化成一些现实的解放力量。当然,哈贝马斯并未轻视通往启蒙现代性理想的道路上种种复杂艰难的状况,他列出了一些更具挑战性的制约与阻遏因素:即使像市民艺术的范例中,“只有在能够把社会的现代化也领入其他非资本主义轨道,只有在生活世界能够从自身派生出限制经济和行政行为体系的系统性自身动力的条件下,对现代文化与日常实践进行有区别的反馈尝试才能够成功。”[12]116,117,117-118
四、福柯:启蒙之为气质
1984年,值前述的康德范文发表200周年之际,福柯专门撰文《何为启蒙》予以纪念。文中,同样将启蒙和现代性作勾连,但与哈贝马斯恰相对立的是:现代性应被视作一种态度,而非一个时期;启蒙应为一种抽象的气质,却非一项实际的事业。
根据福柯的读解,康德对启蒙的提问*正如柯林·戈登看到的,康德本人对启蒙问题的回答激起了福柯的极大兴趣与重视,但他自己思想的最宝贵线索却是在这个问题本身找到的。柯林·戈登.问题、精神特质、事件:福柯论康德和启蒙[C]//汪民安,等.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247.,既不关乎历史的渊源,也无总体的合目的性,诸如某项工程之类。“问题则涉及纯粹的现时性”,更具体地说,“康德对他的写作的现时性的思考”,即将“今日”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差异,一项完成特殊哲学使命的契机来求索。鉴此,现代性更宜看做一付总体的姿态而不是一段实存的分期,它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气质。”[16]530,534
上文里,因对时间意识的极度追捧,哈贝马斯曾将波德莱尔树作批评的靶子,但到福柯眼中,他却转被誉为正面的积极的代表。在其19世纪的作品里,现代性气质被赋予了最为典型的刻画。
大体说来,这包括下列三个方面:(1)对现时的倚重。“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时间的非连续性维度之强调,表达出这样一种情绪:与传统的断裂、对新颖物的感情和对逝去之物的眩晕。但现代性区别于时髦,不是简单浮面地对短暂的当下的敏感,而是一种使现在“英雄化”的意愿:对于现时,波德莱尔宣示,“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2)对现实的改造。现时的英雄化也非单纯将正在流逝的时光永在、神圣化,它更意味着对现时、现实的主观创作,一种介于现实的真与自由的运作之间的游戏,借此,“自然又超越了自然,美又不止于美”。相关地,现时的崇高价值同对它的热切想象密不可分,就波德莱尔而言,“想象力是真实的王后,可能的事也属于真实的领域。”[14]485,484,405(3)对自身的形塑。除去以上的关联,现代性还是一种与人己身建立关系的方式。它和必不可少的苦行主义相牵连,把自己看作一种艰难而复杂的制作过程的对象。换言之,现代人不是那种发现自己的内在的秘密或隐藏的真理的人,而是设法创造自身的人;现代性也不在人的现存中解放人,却是强制人完成创制己身的任务。
在福柯这里,筑基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理念之上,这二者思想更加广泛全面的衔接与批判性的整合,包括康德的批判概念、波德莱尔的主体观念等,最终便形成、激活了一种可称为气质的概念,一种对待启蒙和现代性的适宜的哲学态度。按照福柯的定义,所谓启蒙或现代性,就是一种永久质疑、批判的形上气质,而非对某些教义的刻板忠诚。这些质疑根植于启蒙中,它既使得同现时的关系、历史的存在方式成为问题,也使自主的主体自身成为问题。具体而言,启蒙的气质可从正反二面加以界定:(1)否定方面,拒绝启蒙“敲诈”;(2)积极方面,则推行坚定持久的哲学分析,阐发一种批判的历史本体论,即“对我们之所说、所思、所做进行批判”[16]539,旨在“加工自我和回应时代”。[2]277
从消极的一面看,应当提防“知性的和政治的敲诈”,即支持或反对“启蒙”。福柯强调,无论启蒙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思想规划,抑或哲思方式,都不意味着必须表明二者择一的特定立场:赞同抑或责难。将此关系解作二律背反是一种褊狭的、绝非必要的厌食思想。可取的做法是,作为由启蒙在某个方面从历史上加以确定的当下的人们,应设法对自身进行历史性调查和分析。但不像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这些调查并非意在发现、挽救启蒙的“合理性的基本内核”,而是指向它的“必然性之现在的界限”。
在建设性的层面,批判的历史本体论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1)一种极限的态度。在康德那里,批判是对极限的分析、对界限的反思。但与其消极性的质询理性的限度的做法不同,现今,批判的问题是:“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普遍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专断强制的成分。”换言之,将在必然的限定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这样,“事关我们自身”的批判本体论的结果便是,“批判不是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而是通过使我们建构我们自身并承认我们自己是我们所作、所想、所说的主体的各种事件而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调查。”在此,“批判在其合目的性上是谱系学的,在其方法上是考古学的。”[16]540(2)一种实验的观念。历史经验已经揭明,企图逃避现时的体系而去制定另一种社会、思维方式、文化、世界观的总纲领,这只能导致最危险的传统卷土重来。故此,批判的本体论摒弃所有一切所谓的总体的、彻底的方案,而是一种“对我们能超越的界限的历史-实践的检验”。(3)一项明确的工作规划。批判的本体论的研究目标是,启蒙诺言的自我破坏悖论——有如前文中霍克海默等观察到的:技术的进步、权力的强化、自由的消退三者的同步正向和逆向的增长,将如何解决?探究的路径与方法是对各类社会场域里繁复交织的推论与非推论话语实践的历史-批判分析。这些实践不是指人对自身的表白,或在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决定人的各种条件,而是指他们的技术、策略行为及其方式。总体上,它们隶属于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对物的控制关系、对他人的行为关系、对自身关系。据此,应对它们采用问题化的研究形式,这是一种有效的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其在历史上的奇特形式所进行的分析。
启蒙,在18世纪末期的康德看来,正处于初始的旅程之中,人类尚未成熟。20世纪晚期即整整两个世纪之后,福柯则在其纪念文章里写到:“我不知道我们有期一日是否会变得‘成年’。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16]542
五、结语
何谓启蒙?以致争执如斯。康德的成熟论、霍克海默的辩证论、哈贝马斯的事业论、福柯的气质论等,每一者都依据自身的形上理念和所处的时代体验而予以了独特精到的理解和阐发。延至当今的作者,分歧与论辩仍在持续不休。例如,斯蒂芬·布隆纳力主哈贝马斯式的启蒙重扬[3],托马斯·奥斯本则坚信福柯式的启蒙之永恒质疑原则[1]。
鉴此,新千年中的启蒙,无论其为沉重的遗产抑或重申的旗帜,更多的辨析和论证尚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尤其考虑到上引福柯的最后之言,“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这里,本文权作引论,后续研究还待络绎展开。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M].郑丹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赫伯特·德雷福斯,等.何为成熟:哈贝马斯与福柯论“什么是启蒙”[C]//汪民安,等.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3]斯蒂芬·布隆纳.重申启蒙[M].殷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拉尔夫·赫梅尔.官僚经验[M].韩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12.
[5]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31.
[7]霍克海默,等.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霍克海默.反对自己的理性:对启蒙运动的一些评价[C]//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彼得·杜斯.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C]//汪民安,等.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74.
[10]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1]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74.
[12] 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C]//汪民安,等.现代性基本读本:上.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13]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8.
[14]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5]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32,83, 42.
[16] 米歇尔·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黄仕军)
What is Enlightenment: Classic Texts from Kant to Foucault——On Enlightenment in New Millennium(1)
HU Changbing
(GuizhouAcademyofSocialSciences,Guizhou550002,China)
Abstract:What is enlightenment? Since late 18th century, theorists have made a lot of explanations. Kant defined it as a mature mind, and Horkheimer considered it a choice between freedom and rule, and Habermas advocated that it was a humanitarian cause for freedom and liberation. According to Foucault, it was a kind of temperament of permanent criticism. Today, the future of enlightenment is still in people's diligent interpretations.
Key word:Enlightenment; Kant; Horkheimer; Habermas; Foucault
收稿日期:2016-01-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从可能到实现:康德自由理论的存在论阐释”(10YJA720014);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人之终结的法律蕴涵——米歇尔·福柯法哲学的若干研究”(12GZZC01)
作者简介:胡长兵(1971—),男,安徽芜湖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B50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6)01-004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