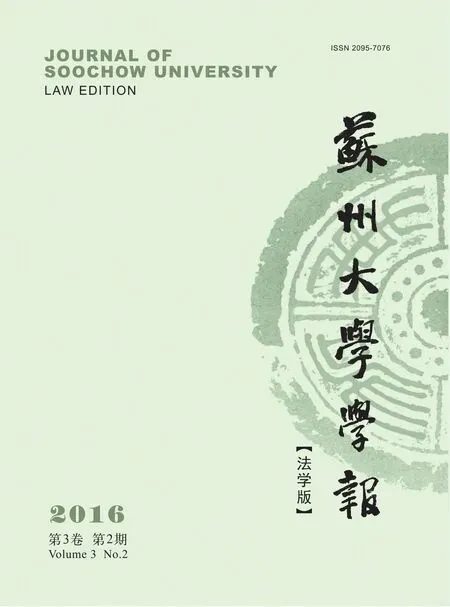实行的着手*
[日]桥爪隆著 王昭武*译
● 域外译文
实行的着手*
[日]桥爪隆**著王昭武***译
“实行的着手”的判断标准应采取实质的客观说,只要从实质的角度来看存在法益侵害之具体危险性,该阶段即成立未遂犯。而且,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也是这种具体危险性的判断材料之一。具体而言,在间接正犯与隔离犯的场合,主张在出现了结果发生之具体危险性的阶段始成立未遂犯的“结果说”更为妥当;对于构成要件上要求必须是通过特定手段而引起既遂结果的结合犯而言,不以实际开始实施构成要件所要求的手段、方法为必要,只要存在实际实施这种手段、方法的危险性即可肯定实行的着手。
实行行为;着手;未遂犯;间接正犯;隔离犯;结合犯
一、引言
要成立未遂犯,行为人必须“着手实行犯罪”(第43条)。有关“实行的着手”的判断标准,学界曾一度主张主观说,强调以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即行为人的犯罪意思的发动为标准;现在,客观说属于通说,以引起构成要件该当事实的客观危险性作为标准。传统通说采取的是形式的客观说,通过将“实行犯罪”(犯罪的实行)解释为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实行行为),认为在开始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阶段,即成立未遂犯。不过,现在,实质的客观说属于有力学说,该说主张不应形式性地划定未遂犯的成立时点,只要实质性地判断是否存在客观危险性即可。
然而,对于如何理解客观危险性的内容,观点不尽一致。而且,作为危险性的判断材料,具体应考虑哪些情况,对此也存在观点之间的对立。为此,对于为实行的着手奠定基础的危险性的含义,本文尝试做些探讨。
另外,就未遂犯而言,围绕所谓不能犯的相关问题亦很重要。也就是,尽管实施了某种行为,但由于不能认定存在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危险性,因而否定成立未遂犯,而归于不可罚的情形,被称之为不能犯。按照对于不能犯的文义解释,这也属于未“着手实行”的情形。因此,不能犯的问题最终就为“实行的着手”这一问题所消解,不可能将这两个问题截然区别开来。①从这一视角,尝试统一解决二者的问题领域的观点,参见和田俊憲:《未遂犯》,载山口厚编著《クローズアップ刑法総論》,成文堂2003年版,第188页以下。尽管如此,也还是可以大致区别二者的:不能犯问题探究的是,在行为人已经实施了所预定的全部行为,但并未发生结果的情形下,是否存在发生结果的危险性;反之,一般来说,“实行的着手”问题要解决的,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看进行到何种阶段就能肯定未遂犯之成立。本文集中研究后一问题。
二、有关“实行的着手”的基本理解
(一)由实行行为概念所做的形式的限定
传统的通说采取的是形式的客观说,在开始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实行行为)的阶段,即肯定存在“实行的着手”。②参见団藤重光:《刑法綱要総論》,創文社1990年第3版,第354页以下。但团藤博士认为,“即便行为本身并未显示构成要件的特征,但如果从整体来看,能被理解为属于定型性地形成构成要件之内容的行为,将该行为认定为实行的着手,亦无不可”(団藤重光:《刑法綱要総論》,創文社1990年第3版,第355页注4),因而也并未严格要求开始实施实行行为。这种观点是将第43条之“着手实行犯罪”解释为“着手实施实行行为”。并且,这里所谓“实行行为”,正是指该当于构成要件之行为,因而,在盗窃罪中,要求开始实施“窃取”财物的行为;在放火罪中,要求开始实施向客体(犯罪对象)“放火”的行为。③直至今日仍严格维持这种立场的观点,参见浅田和茂:《刑法総論》,成文堂2007年补正版,第371页以下。
对于这种形式的客观说,批评意见提出,这会使得未遂犯的成立时点过晚。例如,在盗窃罪中,要求开始实施物理性地接触财物并转移占有的行为(即窃取行为),因而在出于盗窃目的而物色财物的阶段,就不能认定成立未遂犯。但是,为了确定意欲窃取的财物(财物的选定)而实施物色行为的,盗窃发展至既遂阶段,就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而否定该阶段成立未遂犯,并不妥当。受到这种批评之后,有学者通过修正形式的客观说,开始主张“修正的形式的客观说”。该说认为,开始实施“位于实行行为之直前的行为”的,就成立未遂犯。例如,盐见淳教授提出,开始实施位于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之直前的行为,就是实行的着手,要谓之为是“直前行为”,必须是(1)发展至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过程,可谓之为是自动发展而至的行为(行为过程的自动性);或者,(2)时间上接近于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行为。④参见塩見淳:《実行の着手について》(3·完),载《法学論叢》第121卷第6号(1987年),第15页以下。基本属于同样旨趣的观点,参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397页以下。按照“直前行为”这种理解,会直接推导出第(2)点那样的定义,但该观点的特征在于并用这两个标准,亦即,即便没有满足第(2)点标准,但只要满足第(1)点标准即可。⑤参见塩見淳:《実行の着手について》(3·完),载《法学論叢》第121卷第6号(1987年),第17页。井田良教授认为,在可以谓之为,行为人已经完成了为引起结果而必需的大部分行为之时,就能从行为不法的角度为未遂犯处罚奠定基础(参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398页)。
该观点重视实行行为的“直前行为”这种形式的限定,作为合理限定未遂犯成立范围的标准,应予以积极评价。不过,在“直前行为”的判断中,为何可以并用这两个标准,其理论根据未必明确。⑥也有学者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例如,佐伯仁志:《コメント②》,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04页;等等。而且,即便重视行为过程的自动性,但仅仅从住宅内的物色行为是不可能自动发展至盗窃行为的。在该场合下,物色行为之所以能被定位于“直前行为”,想必完全是因为,若实施了物色行为,其后转换为窃取行为就不存在特别困难。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然难以完全从形式的角度来判断“直前行为”,而不得不一并从实质的角度予以考虑。⑦例如,齋野彦弥:《基本講義刑法総論》,新世社2007年版,第238页。
(二)作为实质性危险的未遂犯
1.作为危险行为的实行行为
现在,实质的客观说日益成为学界有力观点。该说力图摆脱实行行为这种形式的限定,主张从实质的角度来判断实行的着手时点。亦即,由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引起了法益侵害(即实现既遂结果)的具体危险性,①由于危险犯也有未遂犯,因而既遂结果也并非总是意味着法益侵害。为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实现既遂结果的危险性”。作为强调这一点的观点,参见浅田和茂:《刑法総論》,成文堂2007年补正版,第370页;等等。因而,在存在法益侵害之具体危险性的阶段,就成立未遂犯。例如,就出于盗窃目的物色财物的行为而言,由于在该阶段既已经能认定存在实现盗窃的具体危险性,因而能肯定实行的着手。
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以什么为对象来判断危险性之有无呢?对此尚存争议。行为说是一直以来的通说。该说认为,由于物色行为本身存在具体的危险性,也就是,物色行为与(按照行为人的犯罪计划)此后继续实施的窃取行为一起构成“一系列的实行行为”,因而在“一系列的实行行为”的开始阶段,就能认定实行的着手。②例如,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12年新版第4版,第365页;等等。另外,“一系列的实行行为”这一概念,也并非是因为此前的通说采用而始出现,在笔者看来,只要以让实行行为与“实行的着手”发生联动的(此前的)通说为前提,就会得出这种解释。这里,“开始实施具有实质危险性的行为”,就成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原本来说,实行行为是指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因果性起点,因而盗窃罪的实行行为就理应只是“窃取”行为,但这里是在能认定存在发生结果之实质危险性的限度之内,实行行为概念(以被提前的形式)得以扩张,由包括准备行为在内的行为所构成。
这种理解与修正的形式的客观说并没有太大不同,但由于是在能认定存在实质危险性的范围之内肯定着手,因而根据对危险性的理解,可能会超出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的直前阶段,而在更早的阶段肯定实行的着手。
2.危险结果的引起
结果说也是学界有力观点。该说认为,即便是以实质的客观说为前提,也并不是因为实施了具有危险性的行为而成立未遂犯,其结果是,应在发生了“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性”的阶段,认定成立未遂犯。③参见平野龍一:《犯罪論の諸問題(上)〔総論〕》,有斐閣1981年版,第130页以下;内藤謙:《刑法講義総論》(下Ⅱ),有斐閣2002年版,第1242页;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269页以下;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300页;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342页;等等。在该说看来,与既遂犯以引起既遂结果作为成立要件一样,未遂犯也要求“引起既遂结果的危险性”这种结果。以上述物色行为为例,正因为物色行为引起了产生窃取结果的具体危险性,以此为根据,就能认定成立未遂犯。
无论是行为说还是结果说,都是以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性作为标准,因而在通过开始实施一定行为而产生了具体危险性的场合,两者之间不会存在任何结论上的不同。采用结果说的(也许是唯一且最大的)实际意义体现于,行为阶段虽然尚未发生充分的危险性,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具体危险性被现实化的场合。这正是间接正犯、隔离犯的问题。就此,下面再专门论述。
(三)对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的理解
有关“氯仿事件”的最高裁判所决定(最决平成16年〔2004年〕3月22日刑集58卷3号187页),针对涉及构成要件的提前实现的案件,肯定成立故意的既遂犯,在这一点上,该判决具有重要意义;④详见橋爪隆:《遅すぎた構成要件実現·早すぎた構成要件実現》,载《法学教室》第408号(2014年),第113页以下。不限于此,作为推导出成立故意的既遂犯的前提,对于杀人罪中的实行的着手的含义,该判决也做出了具体判断,(即便是脱离了构成要件的提前实现这一问题)对于考虑未遂犯的成立要件而言,其内容也具有重要的意义。①有关本决定之解读的具体分析,参见仲道祐樹:《実行の着手》,载《法学セミナー》第705号(2013年),第9页以下。也就是,本案被告等出于伪造被害人A死于交通事故的假象而杀害被害人从而骗取人身保险的目的,具体商定了犯罪计划:先让实行犯乘坐的车辆与A驾驶的车辆相撞,假装要协商解决问题,将A骗上他们乘坐的汽车,强行让A闻氯仿,使之处于昏迷状态之后(第一行为),再将其转移至B港口,使之连人带车一起坠入海中淹死(第二行为)。且实际将犯罪计划付诸实施,但不能确定,A的死因究竟是第一行为还是第二行为。对于该案,最高裁判所判定,“三名实行犯的杀人计划是,先让A吸入氯仿致其昏迷之后,利用该昏迷状态,将A转移至港口,让A连人带车一起坠入海中淹死。可以说,要切实且容易地实施第二行为,第一行为是必不可少的行为;能够认定,在成功实施第一行为的场合,对于实施此后的杀害计划,并不存在其他可成为障碍的特别情况;通过比照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之间在时间上、地点上的接近性等,能够认定,第一行为是与第二行为紧密相连的行为,在三名实行犯开始实施第一行为的时点,就已经明显存在发展至杀人的客观危险性,因此,认为在该时点已存在杀人罪的实行的着手,这是适宜的。”
本决定设想的是由第二行为引起死亡结果的情形,并由此判断实行的着手时点。②对于因第一行为而死亡的案件,当然能在第一行为的着手阶段(在客观方面)肯定实行的着手。在该情形下,严格来说,引起结果的实行行为就完全是第二行为,但本决定认定第二行为是与第一行为“紧密相连的行为”,在开始实施第一行为的阶段,肯定存在(由第二行为)“发展至杀人的客观的危险性”,由此肯定实行的着手。也就是,在该判例看来,即便是位于实行行为之前阶段的行为,倘若该行为(1)属于与实行行为“紧密相连的行为”,并且,(2)能够认定该阶段存在发生结果的“客观的危险性”,就成立未遂犯。就第(1)点与第(2)点之间的关系,尽管并未做出明确判断,但可以理解为,该判例并用了与实行行为之间的紧密关联性这种形式的标准以及引起结果的客观危险性这一实质的标准。③关于这一点,参见平木正洋:《判解》,载财团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6年度),第162页。
作为这种紧密关联性、客观危险性的判断材料,本决定考虑了被告人的犯罪计划。总之,是以存在“三名实行犯的杀人计划”——实施第一行为之后再实施第二行为——为前提,判断第一行为的客观危险性(以及与第二行为之间的紧密关联性)。而且,作为判断之时需要重视的情况,本决定提到了以下三点:(1)要切实且容易地实施第二行为,第一行为是必不可少的行为;(2)在成功实施第一行为的场合,对于实施此后的杀害计划,并不存在其他可成为障碍的特别情况;(3)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之间存在时间上、地点上的接近性。在本案中,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就能肯定紧密关联性以及客观危险性。④紧密关联性、客观危险性与正文中的三点标准之间的关系也会成为问题,但本决定是一揽子地考虑紧密关联性、客观危险性,而无法看到个别判断二者的痕迹。关于这一点,参见松原芳博:《実行の着手と早すぎた構成要件の実現》,松原芳博编:《刑法の判例〔総論〕》,成文堂2011年版,第182页。
鉴于判例、学说的这些动向,本文意欲具体探讨以下问题:首先,(1)正如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所显示的那样,在判断是否成立未遂犯时,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计划有何意义。而且,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要求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即结果引起行为)之间存在时间上、地点上的接近性,这里也想进一步考虑,(2)与引起结果之间,是否应该存在时间上、地点上的接近性。最后,(3)对于与实行行为“紧密相连的行为”这一限定的意义,还想做些简单探讨。
三、行为人的犯罪计划与危险性判断
(一)考虑主观方面的必要性
按照实质的客观说的立场,实现既遂结果的具体危险性可成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但究竟是应基于纯客观的立场来判断这种危险性,还是也有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学界以前曾经历过激烈的论辩。①有关论辩的详细介绍,参见佐藤拓磨:《実行の着手と行為者主観との関係について》,载慶應義塾創立150年記念法学部論文集《慶應の法律学刑事法》,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版,第113页以下。然而,要基于纯客观的立场判断结果发生的危险性,想必是不可能的。本文以为,无论以什么立场为前提,都只得承认,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也是危险性的判断材料。
按照纯客观地判断危险性的观点,例如,行为人持枪瞄准被害人的,就能认定持枪这一客观行为本身存在危险性。②持这种立场的,参见曽根威彦:《刑法の重要問題〔総論〕》,成文堂2005年第2版,第252页;内山良雄:《未遂犯総説》,载曽根威彦、松原芳博编:《重点課題刑法総論》,成文堂2008年版,第189页以下;等等。但是,在行为人完全是出于胁迫目的而持枪,绝对不打算开枪的场合,(根本就不能认定存在杀人罪的故意,但在此之前)能认定该行为存在针对生命的现实危险性吗?当然,也并非完全不存在手指滑动(而扣动扳机)或者手枪走火的可能性。然而,那种偶发性的可能性并不能为实质危险性奠定基础。③按照纯客观地为危险性奠定根据的观点,最终要么是依据这种极其抽象的危险性为未遂犯之处罚奠定根据,亦或即便仅仅是客观方面,也要等到具体危险性已经明确的阶段(例如,就要实际扣动扳机的阶段)才认定着手,但这两种结论都不妥当。关于这一点,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271页。只有考虑到行为人试图向被害人开枪这一意思,持枪行为才能被评价为,是具有针对生命之具体危险性的行为。盗窃罪中的物色行为也是如此。即便是目不转睛地凝视商品,瞄准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倘若“只是看着”,绝对不会转移财物的占有。之所以能认定物色行为具有窃取财物的危险性,完全是因为行为人存在窃取财物的意图。由此可见,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会影响对危险性的判断,这一点难以否认。
对于这种考虑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观点,批评意见指出,这样会造成仅凭行为人内心而判断危险性之有无的局面,并不妥当。但是,正如从上面的例子也能明确的那样,这种观点也并非是仅凭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来肯定危险性,最终仍然是以那些使得犯罪行为成为可能的客观事实,作为危险性的判断前提。也就是,(1)判断前提是,尽管仅凭该行为尚不会发生结果,④为此,如果仅凭该行为本身就能认定存在发生结果的很高危险性(例如,在有火星的地方,泼洒大量汽油的行为等),在这种情形下,就存在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也能认定存在具体危险性之余地。关于这一点,参见和田俊憲:《未遂犯》,载山口厚编著《クローズアップ刑法総論》,成文堂2003年版,第216页;二本柳誠:《未遂犯における危険判断と行為意思》,载《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法研論集》第120号(2006年),第152页以下。但存在通过实施下一行为(即法益侵害行为)而可能引起结果的客观状况;(2)在行为人实施该“下一行为”的盖然性很高的场合,就能认定成立未遂犯。并且,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即“实施下一行为的意思”,不过是用作判断后者(第〔2〕点)之可能性的判断材料。由此可见,最终仍然是在判断客观行为之危险性的基础上,作为预测其后走向的材料,而考虑行为人的主观。上述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是一边考虑被告的犯罪计划,同时肯定存在发展至杀人行为的“客观的危险性”,因而也可以按照这种旨趣来理解。⑤关于这一点,参见鈴木左斗志:《実行の着手》,载西田典之等编:《刑法の争点》,有斐閣2007年版,第89页。
(二)犯罪计划的考虑
1.作为行为意思的犯罪计划
如上所述,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在一定范围之内)会成为危险性的判断材料。但正如持枪瞄准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能够提升危险性的主观情况并不是故意本身,而是“实施下一行为的意思”(即“行为意思”)。⑥参见鈴木左斗志:《実行の着手》,载西田典之等编:《刑法の争点》,有斐閣2007年版,第89页;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271页;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109页;等等。反之,佐藤拓磨则认为,作为为行为的规范违反性奠定基础的要素,在判断实行的着手时,要考虑故意(参见佐藤拓磨:《実行の着手と行為者主観との関係について》,载慶應義塾創立150年記念法学部論文集《慶應の法律学刑事法》,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版,第123页)。不管怎样,要成立未遂犯,要求存在故意,这一点确实如此,(规范违反性的判断暂且不论)但从法益侵害的危险性这一角度来看,就不得不承认,没有考虑故意本身之必要。例如,行为人误将被害人认作是熊,出于杀死熊的想法,持枪瞄准打算开枪的,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存在杀人罪的故意。但是,因为存在“瞄准(被误认是熊的)被害人的身体,打算开枪的意思”,就能认定持枪瞄准行为存在针对被害人生命的高度危险性。当然,在该情形下,由于行为人不存在杀人罪的故意,无论如何都不能成立杀人罪未遂。但是,严格解释的话,这种情形应该是:在客观方面,发生了足以成立杀人罪未遂的客观危险性,但在主观方面,由于不存在成立杀人罪未遂所必要的故意,因而不成立未遂犯。
并且,既然认为,是否存在“实施下一行为的意思”,会影响对行为人实施法益侵害行为之盖然性的判断,那么,行为人打算在什么条件之下,或者在什么时点、出于什么形式而实施下一行为,亦即,作为未遂犯之危险性的判断材料,就应该考虑行为人的整个犯罪计划。这里并不是在“故意”这一框架之内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而是作为预测“行为人多大程度上存在实施法益侵害行为的可能性”的判断材料,而考虑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情况,因而是脱离了构成要件性评价,完全作为“鲜活的”意思内容,而将行为人的犯罪计划作为判断材料。上述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就正是在将行为人的犯罪计划作为判断材料的基础之上,在开始实施第一行为的阶段,肯定存在危险性、紧密关联性,本文认为,这种判断是妥当的。
另外,如上所述,为行为的危险性奠定基础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的行为意思,作为这种行为意思之内容,要考虑整个犯罪计划。由于未遂犯也是故意犯,因而要成立未遂犯,当然以存在故意为必要。并且,由于未遂犯是对既遂犯构成要件的修正,作为未遂犯之故意的内容,就要求对既遂犯构成要件之实现存在认识或者预见。例如,要认定持枪瞄准被害人的行为成立杀人罪未遂,作为为行为之客观危险性奠定基础的内容,就以“打算向被害人开枪的意思”(行为意思)为必要。反之,作为未遂犯之故意,则要求对于自己持枪、被害人(即“人”)会因自己此后的开枪行为而死亡,存在认识或者预见。因此,行为意思是为危险性奠定基础的违法要素,故意则是作为责任要素而发挥作用。
2.犯罪计划为危险性奠定基础
在上述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中,第一行为是“强行让A闻氯仿”,这一行为本身就属于对生命存在很大危险的行为,为此,也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存在与实行的着手相对应的危险性。但由于实行担当者并未认识到,第一行为本身就存在引起死亡结果的危险性,因而不能以该危险性为根据而肯定成立未遂犯。为此,最高裁判所指出,如果不是以氯仿本身的危险性,而是以实行担当者的犯罪计划作为判断材料,只要实施了第一行为,就存在直接转而实施第二行为的很高的危险性,从而肯定存在足以相当于实行的着手的危险性。这样,在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中,同时存在两个危险性:(1)即便是仅仅实施第一行为,也有发生死亡结果的可能性,(2)按照犯罪计划,实施第一行为之后会立即实施第二行为,由此存在发生死亡结果的可能性。因而与行为人的犯罪计划相对应,后者(第〔2〕点)的危险性就为实行的着手的危险奠定基础。
为此,即便将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的案情修改为,实行担当者在与本案同样的犯罪计划之下,不是“强行让A闻氯仿”,而是使用一般不会危及生命的安眠药使得被害人昏睡,①当然,与“强行让A闻氯仿”的情形一样,长时间、切实地排除被害人的反抗,是这里进行讨论的前提。由于同样能认定存在第(2)点危险性,因而在该阶段也能认定杀人罪的实行的着手。②参见橋爪隆:《判批》,载《ジュリスト》第1321号(2006年),第235页;平木正洋:《判解》,载财团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6年度),第171页。对于让被害人服用不危及生命的安眠药这一行为,认定成立杀人罪未遂,也许多少有些难以接受,但既然在该阶段发生了(通过马上有可能实施的第二行为而引起的)被害人坠海而死这种客观危险性,就不能否定,该行为属于对生命具有很高危险性的行为。
对于放火罪的实行的着手,在判断实行的着手之际,也有考虑犯罪计划的余地。例如,因妻子离家出走,被告悲观厌世打算自焚,基于向自己的房子放火的计划,在家里泼洒了大量汽油,对此,横滨地判昭和58年(1983年)7月20日判时1108号138页认为,在泼洒汽油的时点,“若考虑到汽油具有强烈的易燃性,只要在此地出现某种火星,就会点燃泼洒在家中的汽油而引起火灾,这是必然的事实状况,因此可以说,被告人通过泼洒汽油这一行为便已经完成了放火的大部分企图,此阶段业已发生了引起法益侵害即烧毁本案房屋的紧迫危险”,从而认定泼洒汽油的行为属于实行的着手。①在本案中,被告在实施放火行为之前,“打算在死前再吸最后一支烟”,遂用打火机点烟,结果引燃了已经气化的汽油而引发火灾,属于所谓构成要件的提前实现的问题。按照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的逻辑,如果在泼洒汽油的阶段,就认定实行的着手,那么,被告对实施实行行为就存在认识,应成立放火罪既遂。汽油具有很强的挥发性,一旦出现某种火星就会着火的危险性很高,因此,与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一样,本案行为也同时存在两种危险性(两种危险性的并存):(1)所泼洒的汽油因某种火星而着火的危险性、(2)被告实施点火行为的危险性。并且,如前所述,在通过考虑犯罪计划而认定危险性之有无的场合,只有第(2)点危险性才真正具有意义。
这样考虑的话,即便是出于放火的意图而泼洒灯油的情形,如果被告存在马上实施点火行为的犯罪计划,而且客观上也有可能实施点火行为,就能认定存在上述第(2)点危险性,因而,也理应能认定实行的着手。但是,对于出于放火的意图而泼洒灯油的行为,判例一般认为,与汽油相比,灯油的易燃性要差很多,因而仅仅是泼洒灯油尚很少有具体危险性,因而应否定实行的着手。②在泼洒灯油的阶段否定实行的着手的判例,参见冈山地判平成14年(2002年)4月26日(裁判所HP)、千叶地判平成16年(2004年)5月25日判タ1188号347页、横滨地判平成18年(2006年)11月14日判タ1244号316页、青森地八户支判平成23年(2011年)6月8日(公开刊物未刊登),等等。福冈地判平成7年(1995年)10月12日判タ910号242页判定,在泼洒了灯油之后,再向泼洒了油漆稀释液的报纸点火的阶段,属于实行的着手,对此也可以理解为,其旨趣在于,在泼洒灯油的阶段否定实行的着手。这些判例的案情大多是,要么实现犯罪计划的可能性不大,或者,因犯罪现场还有其他人,有可能会阻碍行为人实施点火行为,为此,也许是这种事实关系向否定实行的着手的方向发挥了作用。尽管这一点并未超出可预测的范围,但也许司法实务存在这样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对于仅以犯罪计划为根据而肯定成立未遂犯,实务部门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原则上仅限于能同时认定存在第(1)点与第(2)点危险性之时,才成立未遂犯。例如,被告对被害女性产生杀意,但由于被害人动作敏捷,为了制止被害人的行动,制定了先开车撞到被害人,再用刀刺杀的犯罪计划,然后,被告开车以20千米的时速撞到了被害人。③撞到被害人之后,看到被害人的脸,被告心生悔意放弃了继续实施犯罪,因而认定成立犯罪中止。对此,名古屋高判平成19年(2007年)2月16日判タ1247号342页认为,在按照犯罪计划开车撞倒被害人的时点,“也能认定存在发展至杀人的客观的现实的危险性”,因而认定成立杀人罪未遂,但(作为对否定成立杀人罪未遂的原判决的批判)同时判定,“被告用四轮汽车以20千米的时速从背后撞倒被害人,该行为本身就会导致被害人的死亡,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该判例也一并重视撞车行为本身的危险性。
假设这种态度是司法实务部门的一般感觉,对于上述让被害人服用安眠药的例子,是否会因为让被害人服用安眠药这一行为本身鲜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危险性,而否定实行的着手,进而仅成立杀人罪预备(以及伤害罪)呢?在采取的手段行为本身鲜有危险性的场合,对于犯罪计划的具体内容,是难以举证的,在此意义上,判例的做法也不是不能理解,但还是应该认为,理论上并无做此限定之必要。
3.犯罪计划对未遂犯的限定
只要原样考虑行为人的所有犯罪计划,根据其具体内容,有时候会推迟实行的着手时点。例如,即便是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的案件,如果犯罪计划是,实行担当者“强行让A闻氯仿”使得被害人昏迷之后,将被害人转移至其他地方,并与(恢复意识的)被害人进行某种交涉,倘若交涉不成功就让被害人连人带车坠入海中,那么,即便第一行为本身是完全相同的行为,想必在第一行为的阶段也不能认定实行的着手。在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的案件中,其犯罪计划是,趁被害人尚未恢复意识,让被害人连人带车坠入海中,对于实行的着手的认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从这种视角来看,有关强奸罪的实行的着手的判例,也很重要。例如,被告与其他共犯一起将被害人拽入翻斗车驾驶室之后,转移至大约5 800米开外的某工地,在该工地、在翻斗车驾驶室内强奸了被害人。对此,最决昭和45年(1970年)7月28日刑集24卷7号585页判定,“在将被害人拽入翻斗车驾驶室的阶段,就显然能认定存在发展至强奸的客观危险性,因而该时点存在强奸行为的着手”。①在该案中,强奸行为达到了既遂,但在将被害人强行拽入翻斗车驾驶室的阶段,造成被害人受伤,因而围绕是否成立强奸致伤罪,着手时点成为问题。当然,也有观点提出,在将被害人拽入驾驶室阶段的暴力,并非作为强奸罪之实行行为的暴力,因而即便认定实行的着手,也未必能成立强奸致死伤罪(例如,松原芳博:《判批》,芝原邦爾等编:《刑法判例百選Ⅰ総論》〔第5版〕,有斐閣2003年版,第129页;等等)。不过,即便该暴力本身并非强奸罪的实行行为,但在由(构成)强奸未遂的行为导致了死伤结果的场合,也应认定成立强奸致死伤罪。本案被告的犯罪计划的具体内容并不清楚,但从实际实施的犯罪行为来回溯性地推测,想必被告等人是打算将被害人转移到路人稀少的僻静地方之后再实施强奸。②参见大久保太郎:《判解》,载财团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昭和45年度),第246页以下。按照这种犯罪计划,被告等人没有在将被害人拽入翻斗车驾驶室的现场直接实施强奸行为的打算,但要将被害人转移至僻静的地方,多少需要一点时间,③作为重视这种犯罪计划,而否定在将被害人拽入翻斗车驾驶室的阶段存在实行的着手的观点,参见野村稔:《未遂犯の研究》,成文堂1984年版,第302页。在此期间,既然被困在翻斗车驾驶室的被害人事实上已经难以反抗,因而即便存在这种程度的时间间隔,仍然能认定,存在与实行的着手相对应的“客观的危险性”。
不过,基于这种理解,如果按照行为人的具体犯罪计划,奸淫行为的实施,时间上还要往后延迟,在此期间有可能产生某种障碍,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通过考虑整个犯罪计划,就有可能否定实行的着手。例如,没有在车内实施奸淫的意图,而是打算开车长时间移动之后,在宾馆内实施奸淫行为,在此情形下,在汽车移动的过程中,甚至是在下车走向宾馆房间的过程中,出现某种障碍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因此,在将被害人拽入汽车之内的阶段,也有可能否定实行的着手。④松宫孝明教授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参见松宮孝明:《刑法総論》,成文堂2009年第4版,第239页)。另外,对于让出租车停在宾馆门口,打算从宾馆后门强行将被害人拽入宾馆,但最终归于失败的案件,东京高判昭和57年(1982年)9月21日判タ489号130页认为,考虑到本案宾馆“不是普通的宾馆,而属于宾馆员工对于住客的男女关系不太干涉的宾馆”,从而谨慎地认定,按照犯罪计划,在宾馆房间内实施奸淫的危险性是很高的。
另外,如果行为人的犯罪计划原本就鲜有实现的可能性,那么,就鲜有按照该计划而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具体危险性,因此,当然会否定实行的着手。⑤有学者提出,应限于那些“作为被客观化的、被现实化之顺序的计划”,在危险性判断中才予以考虑(参见金澤真理:《実行の着手判断における行為計画の意義》,载《大阪市立大学法学雑誌》第75卷第6号〔2012年〕,第112页),想必也是这种旨趣。例如,即便是出于强奸目的试图将被害女性拽入汽车之内,但从周边环境以及汽车结构等来看,是难以将被害人拽入车内的,或者即便有可能将被害人拽入车内,但难以按照犯罪计划在车内实施奸淫的,就不能认定,存在强奸罪的实行的着手。⑥作为否定着手的判例,参见京都地判昭和43年(1968年)11月26日判时543号91页、大阪地判平成15年(2003年)4月11日判タ1126号284页、广岛高判平成16年(2004年)3月23日高刑集57卷1号13页,等等。
四、间接正犯与隔离犯的实行的着手
(一)行为说、结果说
正如前面反复谈到的那样,要成立未遂犯,必须存在发生既遂结果的具体危险性。并且,如果实施了实行行为或者与实行行为紧密连接的行为,由于通常能认定存在结果发生的具体危险性,也会成立未遂犯。但是,对有关间接正犯的案件而言,在实行行为的阶段,是否发生了(将未遂犯处罚予以正当化的)具体危险性呢?例如,X命令因平素受到自己虐待而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女儿A在超市盗窃,X可能成立盗窃罪的间接正犯,但是X在什么阶段成立盗窃罪未遂呢?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该案中,X的实行行为(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完全止于向A发出的命令行为。A在超市实际物色并窃取商品的行为,那属于A的行为,而非X的行为。①间接正犯并非是设定了一种特殊的规则,通过将被利用者的行为完全等视于利用者的行为,从而将该行为归属于利用者。由于并不存在有关间接正犯的特殊处罚规定,因此,最终仅限于,能够将利用者的命令行为等评价为,属于个别的构成要件中的实行行为的场合,才成立间接正犯。为此,按照以“危险行为之开始”作为判断未遂犯之标准的观点(行为说),就只得是在X命令A实施盗窃的阶段认定实行的着手。②学界有力观点认为,在利用行为缺乏现实危险性的场合,由于利用者其后负有防止被利用者引起结果的作为义务,因而能认定为不作为的实行行为之持续(例如,大塚仁:《刑法概説〔総論〕》,有斐閣2008年第4版,第175页注17;佐久間修:《刑法総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85页;等等)。不过,(姑且不论这种情形下原本能否认定存在作为义务)由于利用行为之后并非总是能认定存在作为可能性或者结果避免可能性,因而这种解释也有其局限性。但是,在A甚至尚未进入超市的阶段,不可能发生窃取超市商品的具体危险性。从下面的例子来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X自己出于盗窃的意思走向超市,倘若尚未进入店内,并开始实施物色行为等,就不能认定存在窃取的危险性。对于本文这种理解,也许该说(行为说)会提出反驳:A的意思已经为X所压制,很少有改变主意的可能性,因而在A接受命令的阶段,就能认定存在窃取的高度危险性。然而,例如,正如利用过失行为的行为人的情形那样,被利用者察觉到真相,从而改变主意的可能性,这是完全能够想象得到的;而且,原本来说,如果以这种理解(行为说)为前提,对于那些强化了盗窃犯意、鲜有改变主意之可能的盗窃常习者而言,在盗窃常习者走向超市的阶段即会认定存在着手,这显然不妥。
这样,如果认为在X向A发出盗窃命令的阶段,尚不能认定存在足够的危险性,那么,立足于“行为说”,就会陷入解释上的困境。也就是,由于命令行为的阶段尚不存在足够的具体的危险性,该阶段理应不能成立未遂犯。然而,除了命令行为之外,X未再实施其他行为,因而,如果在该阶段不能认定成立未遂犯,其后,无论事态如何进展,也都无法认定成立未遂犯。反之,如果认为这样做不正确,最终就只得是,尽管命令行为阶段尚缺乏具体危险性,仍不得不认定实行的着手。③参见和田俊憲:《未遂犯》,载山口厚编著《クローズアップ刑法総論》,成文堂2003年版,第212页。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有学者提出,根据危险的发生,能回溯性地认定“实行行为”性(参见齋野彦弥:《危険概念の認識論的構造》,《内藤謙先生古稀祝賀·刑事法学の現代的状況》,有斐閣1994年版,第79页以下;山中敬一:《刑法総論》,成文堂2008年第2版,第713页)。这一问题正反映出,要在行为的阶段终局性地判断是否存在危险性,是勉为其难的。本文以为,在能够将行为之后的过程也包括在判断材料之内,而考虑是否存在危险性这一点上,还是“结果说”更为妥当:在未遂犯中,该说也要求引起具体的危险这种结果,从而在发生危险性的阶段,肯定成立未遂犯。
按照本文这种理解,所谓隔离犯,亦即,对于那些从实行行为到结果发生之间,时间上、地点上存在很大间隔的类型,没有必要总是在实行行为阶段认定实行的着手,而是在经过一定时间上的间隔,出现了结果发生之具体危险性的阶段,始成立未遂犯。因此,例如,X出于杀害A的目的,通过快递将有毒葡萄酒寄往A家的,对于该行为,不是在寄送阶段,而是在葡萄酒达到A家的阶段,才成立未遂犯。对于邮寄有毒砂糖的案件,大审院判例(大判大正7年〔1918年〕11月16日刑录24辑1352页)亦认为,在被害人收到邮件的阶段,有毒砂糖被置于被害人亲属“得以食用的状态之下”之时,就认定实行的着手,采取的就是到达时说。①对于将有毒果汁放在田埂边的案件,宇都宫地判昭和40年(1965年)12月9日下刑集7卷12号2189页判定,在被害人拾得果汁就要饮用的阶段,始能认定实行的着手。另外,被告是邮政局工作人员,打算将处于邮政局长管理之下的邮件投递至自己家里,遂改写投递地址,并将邮件置于投递用的邮件分类架上,对此,东京高判昭和42年(1967年)3月24日高刑集20卷3号229页判定,在改写投递地址并置于投递用的邮件分类架上的阶段,即能认定实行的着手。对此,有观点认为,该判例采取的是“发送时说”(参见野村稔:《実行の着手》,芝原邦爾编:《刑法の基本判例》,有斐閣1988年版,第55页)。然而,在该案中,是对于以转移占有本身作为既遂结果的盗窃罪探究实行的着手,不过是在早于转移占有的阶段肯定了实行的着手,这与有关杀人罪的着手的判断,完全处于不同层面。参见佐藤拓磨:《判批》,山口厚、佐伯仁志编:《刑法判例百選Ⅰ〔総論〕》,有斐閣2014年第7版,第133页。
对于“结果说”,批判意见提出,作为对第43条的“着手实行犯罪”这一表述的解释,很难采取结果说。但作为未遂犯的(修正的)构成要件的不成文要素,作为结果,要求发生了引起既遂结果的具体危险性,这是完全有可能的。②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另见高橋則夫:《刑法総論》,成文堂2013年第2版,第386页;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301页;等等。另外,也有学者更为直接地将“实行的着手”理解为,划定未遂结果之发生阶段的时间性概念(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271页;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300页;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342页;等等)。
(二)是否要求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
如上所述,对于上述快递有毒葡萄酒的案件,应该在到达被害人A宅的阶段,肯定实行的着手。这一点与下一情形在结论上存在整合性:X谎称是岁末礼物,自己带着有毒葡萄酒到A家,在该情形下,认定实行的着手的时点,就不是X拿着有毒葡萄酒出门之时,而是到达A家之时。④反之,佐藤拓磨则认为,在间接正犯的场合,由于存在对事态进展的“放手”,因而在“放手”的阶段即肯定实行的着手。参见佐藤拓磨:《間接正犯の実行の着手に関する一考察》,载明治学院大学《法学研究》第83卷第1号(2010年),第165页。不过,从现在的邮寄、快递情况来看,寄送的东西几乎都会切实地送达;而且,如果被害人没有意识到葡萄酒中有毒而完全有可能饮用的话,在寄送阶段,也完全有可能肯定,已经存在发生危害结果的高度盖然性。⑤基于这种理解,平野龙一认为,很多情形下,也可以在寄送时即认定实行的着手。参见平野龍一:《刑法総論Ⅱ》,有斐閣1975年版,第320页。尽管如此,仍然主张只有到达被害人住宅之后才肯定实行的着手,作为客观危险性的内容,这种观点就不仅是要求存在结果发生的高度盖然性,还要求存在结果发生的时间上的紧迫性。在尚需很长时间才会发生结果的场合,在此期间,存在出现某种障碍的可能性,当然也能想到,会由此相应地降低结果发生的盖然性。但就上述快递有毒葡萄酒的案件而言,事前几乎很难想到,在有毒葡萄酒到达被害人住宅之前会出现某种障碍。这样,结果发生的盖然性与时间上的紧迫性就分别具有独立的内容。⑥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343页;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300页;等等。
不过,也有观点主张,通常情况下,是在结果发生的盖然性(可能性)这一意义上理解“危险性”概念,⑦提出这种观点者,参见鈴木左斗志:《実行の着手》,载西田典之等编:《刑法の争点》,有斐閣2007年版,第89页。因而对于未遂犯的实行的着手,也只要存在结果发生的盖然性即可,没有必要要求,另外存在结果发生的时间上的紧迫性。⑧和田俊憲认为,不过是作为判断结果发生的切实性(盖然性)的判断材料而考虑紧迫性(参见和田俊憲:《未遂犯》,载山口厚编著《クローズアップ刑法総論》,成文堂2003年版,第219页以下)。佐藤拓磨也认为,虽要求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但那不过是用于限定处罚范围的外在制约(因此,对间接正犯来说,由于已经实施了实行行为,没有再特别限制处罚范围之必要,因而不要求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参见佐藤拓磨:《間接正犯の実行の着手に関する一考察》,载明治学院大学《法学研究》第83卷第1号〔2010年〕,第165页)。然而,只要有毒葡萄酒尚未到达被害人住宅,被害人就绝不会(因饮用该有毒葡萄酒而)死亡。①参见山口厚:《コメント①》,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197页。只有有毒葡萄酒到达被害人住宅,出现结果发生的“现实的可能性”,亦即,出现“随时有可能发生结果的状态”,才能肯定未遂犯之处罚,在本文看来,这种理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尤其是按照“结果说”的立场,也有这样理解的余地:仅限于达到发生既遂结果的直前阶段的场合,才会发生值得作为未遂犯予以处罚的危险。
然而,如果这样严格地理解时间上的紧迫性,例如,将设定为一个月之后爆炸的定时炸弹,放在绝对不可能被发现的、被害人住宅的顶棚后面的,放置定时炸弹的阶段就不能认定实行的着手。对于这种结论的合理性,有学者提出了质疑。②参见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398、404页。另外,佐伯仁志认为,这种质疑隐含着“也许定时炸弹会因出错而爆炸”这种考虑(参见佐伯仁志:《コメント②》,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05页),但如果真正是一个月之内绝不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在安放定时炸弹的阶段否定着手是否合适,这一点就应该成为问题。而且,如果在安放阶段不认定实行的着手,其后,由于直至爆炸之前,都不会对外界造成任何改变,因此,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本能否明确地认定着手时点?进一步重新审视的话,就有毒葡萄酒的案件来说,在有毒葡萄酒送达被害人住宅之后,由于完全不知道被害人何时会饮用,因而完全有可能在数月之后甚至数年之后才会饮用。想必实际难以采取这种观点:严格地理解时间上的紧迫性,在被害人开启葡萄酒瓶的软木塞之时,始认定实行的着手。在此意义上,就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时间上的紧迫性这一要求的余地。
对此问题,可能想到的做法是,即便是那些时间上的紧迫性未必充分的情形,在可以谓之为,行为已经影响到被害人领域的场合,在该阶段即肯定实行的着手。③盐见淳虽以将利用行为认定为实行的着手这一点为前提,但同时又对此做出一定修正,在对被害人或者被害人领域发挥影响(作用)的时点,肯定成立未遂犯。参见塩見淳:《間接正犯·隔離犯における実行の着手時期》,川端博等编:《理論刑法学の探求④》,成文堂2011年版,第28页以下。换言之,这种理解是,将时间上的接近性与地点上的接近性分割开来,通过综合考虑二者而要求“接近性”。④即便以这种理解为前提,仍然应该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时间上的紧迫性,因此,有必要“综合考虑”二者。在将10年之后爆炸的定时炸弹安放在被害人住宅的时点,要肯定成立杀人罪未遂,还是过于极端。按照这种理解,对于间接正犯、隔离犯的着手时点,虽采用被利用者标准说、到达时说,但也可以在一定时间上予以提前。笔者虽觉得这种解决方式有一定“吸引力”,但对于通过地点上的接近性来弥补时间上的紧迫性的不充分这种解释,还是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会受到过于“讨巧”这种批判。对此,笔者也将做进一步的思考。
五、作为紧密接近行为的未遂行为
(一)概述
如前所述,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以“第一行为是与第二行为紧密接近的行为,三名实行犯开始实施第一行为的时点,就已经能认定,显然存在发展至杀人的客观危险性”为根据,认定在第一行为阶段存在杀人罪的实行的着手。这里,除了第一行为阶段的客观危险性之外,还特别重视第一行为是与第二行为(实行行为)紧密接近的行为。由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引起了结果发生的具体危险性,因而也有可能存在这样的理解,即只要能认定引起了客观危险性,仅此即能肯定对未遂犯的处罚。但危险性这一概念未必明确,其判断也可能存在一定摇摆幅度,因此,从与实行行为之间的密接性这一形式的角度进行限定,也有充分的理由。⑤提出同样观点的,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269页;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288页;等等。平野龙一也认为,“在形式上或者时间上进行限制,还是有必要的”(平野龍一:《刑法総論Ⅱ》,有斐閣1975年版,第314页)。按照这种理解,未遂犯的成立要件就在于:(1)实施了实行行为或者与实行行为紧密接近的行为、(2)引起了发生既遂结果的具体危险性。
不过,最高裁判所平成16年判例本身并未严格要求与实行行为之间存在紧密接近的关联性(密接性)。本案的实行分担者计划的是,在第一行为之后,转移至离开现场大约2千米的港口,再实施第二行为,即便如此,判例也肯定存在时间上、地点上的密接性。①另外,由于是在第一行为的阶段判断实行的着手,因而时间上、地点上的密接性的判断,不是以实际实施的第二行为,而是以实行担当者计划实施的第二行为作为标准。而且,在前述有关强奸罪的最决昭和45年(1970年)7月28日刑集24卷7号585页中,将被害人拽入翻斗车驾驶室的地点与强奸行为的现场相距大约5800米,即便是这种程度的距离,判例也肯定存在时间上、地点上的密接性。②平木正洋也做出了这种评价。参见平木正洋:《判解》,载财团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6年度),第173页。在以这种判例立场为前提的场合,虽说是紧密接近的行为,也并未限定于在时间上、地点上处于直前阶段的行为,想必是在考虑到发展至发生既遂结果的客观危险性的基础之上,对于那些不存在特别障碍,“可能与实行行为相连接的行为”整体,广泛地予以承认。最终就是,能认定危险性要件的场合,事实上几乎都是那些能认定满足了密接性要件的情形。③关于这一点,参见平木正洋:《判解》,载财团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6年度),第163页。分别探讨二者的意义也许并没有那么大,但至少对于那些时间上、地点上相隔很大的场合、犯罪计划中存在某种中断的场合,就存在因缺乏密接性而否定实行的着手的余地。
按照这种理解,对于盗窃罪,也没有必要严格要求是位于窃取行为直前的物色行为,在侵入他人住宅之后,如果存在接近所试图窃取的财物的行为,在该阶段就完全有可能肯定实行的着手。例如,夜晚,侵入电气工具店之后,打算窃取现金而走向放置收银机的香烟销售柜台,最决昭和40年(1965年)3月9日刑集19卷2号69页就肯定该阶段属于盗窃罪的实行的着手,④在该案中,由于在该阶段被害人正好回到家中,被告为了免遭逮捕而刺伤了被害人,因而围绕是否成立事后抢劫致死伤罪,盗窃罪的实行的着手的时点,就成为问题。应该说,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而且,对于仓库、汽车等,如果成功地侵入其中,就会发现财物,继而窃取财物,因而在侵入行为的阶段,就能认定实行的着手。另外,在撬锁侵入的场合,究竟是在将锁撬开之后成功侵入的阶段肯定实行的着手,还是在试图撬锁的阶段即肯定实行的着手,这也会成为问题,但如果撬锁不是那么困难的话,就有在后一阶段肯定实行的着手的余地。⑤名古屋高判昭和25年(1950年)11月14日高刑集3卷4号748页在毁坏土窖的部分墙壁,毁坏门锁的阶段,肯定实行的着手;东京地判平成2年(1990年)11月15日判时1373号144页在将螺丝刀插入汽车门锁而试图打开汽车的阶段,肯定实行的着手。
(二)结合犯的实行的着手
与这种对于“未遂行为”的形式的限定相关联,这里还想谈一谈抢劫罪、强奸罪等结合犯的实行的着手。这些结合犯在构成要件上要求,必须是通过暴力或胁迫等特定手段而引起既遂结果,对于其着手时点,一般认为,应该是开始实施手段行为(例如,暴力或者胁迫)之时。⑥参见野村稔:《未遂犯の研究》,成文堂1984年版,第306页;大越義久:《実行の着手》,芝原邦爾等编:《刑法理論の現代的展開総論Ⅱ》,日本評論社1990年版,第143页;伊藤渉:《未遂犯》,载《法学教室》第278号(2003年),第99页;等等。也就是,对结合犯而言,要求部分实施了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对于盗窃罪、杀人罪等构成要件上并不要求通过特定手段实施的犯罪,即便没有部分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也有可能成立未遂犯,因此,特别标准的适用仅限于结合犯。对于这一点,相关论者的解释是,结合犯属于以“按照行为人的犯罪计划,法益侵害的危险直接迫近的行为”为手段,而被构成要件化的犯罪类型,因而只有着手实施手段行为,才能认定存在具体的危险性。⑦参见野村稔:《未遂犯の研究》,成文堂1984年版,第306页。
然而,并不是在满足了既遂构成要件的场合,而是在具有满足既遂构成要件之危险性的场合,认定成立未遂犯,因此,对于构成要件所要求的手段、方法,也没有必要实际开始实施,而只要存在实际实施这种手段、方法的危险性即可。在只有满足所有要素才能成立既遂犯这一意义上,构成要件的各个要素在重要性上并无区别,因此,鲜有进行这种区别的必然性:要成立未遂犯,不以结果的现实化为必要;但对于行为或者手段则以实际开始实施为必要。①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347页。同样旨趣的观点,参见佐藤拓磨:《実行の着手と実行行為》,载明治学院大学《法学研究》第82卷第1号(2009年),第372页以下。例如,在前述有关强奸罪的最决昭和45年(1970年)7月28日刑集24卷7号585页中,由于在将被害人拽入翻斗车驾驶室的阶段所实施的暴力,并非作为奸淫手段的暴力,因而就不属于强奸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作为奸淫手段的“暴力”。②为此,按照主张对于结合犯以开始实施构成要件所规定的行为或者手段为必要的观点,就会对最决昭和45年(1970年)7月28日刑集24卷7号585页的结论提出疑问(例如,大越義久:《実行の着手》,芝原邦爾等编:《刑法理論の現代的展開総論Ⅱ》,日本評論社1990年版,第144页;伊藤渉:《未遂犯》,载《法学教室》第278号〔2003年〕,第99页)。
不过,对于前述有关强奸罪的最决昭和45年(1970年)7月28日刑集24卷7号585页,多数说以及(也许是)实务部门的一般性理解是,尽管在将被害人拽入翻斗车驾驶室之时所实施的暴力本身,并非作为强奸手段的“暴力”,但属于与其后的、作为奸淫手段的“暴力”连在一起的行为,因而能认定,开始实施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系列的暴力”,在将被害人拽入翻斗车驾驶室的阶段,成立强奸罪未遂。为此,例如,掩藏想要将被害人带至偏僻的地方实施强奸的犯罪计划,欺骗被害人说,“我们去兜风吧”,将被害人骗上汽车的,对于该案,尽管按照行为人的犯罪计划,在将被害人骗上车的阶段,客观的危险性是相同的,但由于尚不能认定开始了“一系列的暴力”,因而只要未在车内开始实施某种暴力,想必就要否定强奸罪的实行的着手。③④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305页;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401页注28;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291页;等等。为此,在移动过程中,通过犯罪行为人之间的对话,察觉到行为人的强奸计划,被害人拼死逃走,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因摔下汽车而受伤的,也不成立强奸致伤罪。
这样,要求着手实施“一系列的实行行为”这种观点,作为比照条文表述而形式性地限定未遂犯成立范围的手法,是完全能得到理解的。但是,在本文看来,这仍然属于最终会走向形式的客观说的观点,而且,该观点也缺乏充分的根据。⑤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269页;佐藤拓磨:《実行の着手と実行行為》,载明治学院大学《法学研究》第82卷第1号(2009年),第374页。要处罚未遂犯,即便以实施与实行行为紧密相关的行为为必要,但这种与实行行为紧密相关的行为,也并无显示构成要件内容之必要。实际上,如果彻底贯彻这种形式的限定,即便是同种犯罪,根据是否属于结合犯,着手时点会出现很大不同。例如,第176条前段的强制猥亵罪也是以暴力或者胁迫为手段,⑥日本刑法第176条〔强制猥亵〕:以暴力或者胁迫手段对13岁以上的男女实施猥亵行为的,处6个月以上10年以下惩役;对未满13岁的男女实施猥亵行为的,亦同。——译者注为此,出于对13周岁的被害人实施猥亵行为的意图,将被害人骗入自己房间的,只有在开始实施针对被害人的暴力之时,才成立强制猥亵罪的未遂;但如果被害人未满13周岁(例如,12周岁),由于对行为手段并无限制(参见第176条后段),只要实施“与猥亵行为密切关联的行为”即可,因而根据具体案情,仅凭将被害人带入自己房间这一点,就能认定存在实行的着手。但是,根据被害人是12岁还是13周岁,强制猥亵罪的着手时点会随之不同,这并不妥当。⑦当然,对于第176条后段的犯罪类型,在开始实施暴力、胁迫或者猥亵行为的阶段,也存在朝着肯定实行的着手的方向,而确定着手时点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将这种理解适用于杀人罪、盗窃罪,与判例、通说一直以来的理解相比,着手时点会大幅延迟。
(责任编辑:钱叶六)
The Commencement of Crime Enforcement
[Japan]Hashizume Takashi(Author) Wang Zhaowu(Translator)
The criterion of commencement of crime enforcement should be understood by actual objective standard. As long as it has specific risk to the legal interest actually,the stage can be regarded as attempted crime. Perpetrator’s subjective aspect is one of judge material of this specific risk. Specifically,the consequence theory claims that as long as it has specific risk to the consequence,the stage can be regarded as attempted crime. This theory is more appropriate when there is indirect principal and offence of segregation. For combinative offence whos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ask it must led to accomplished result by specific means,it is not necessary to actually start to enforce the means and method of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As long as it has danger to actually enforce this means and method,it can be regarded as commencement of crime enforcement.
Enforcement;Commencement;Attempted Crime;Indirect Principal;Offence of Segregation;Combinative Offence
D913
A
2095-7076(2016)02-0129-14
*本文原载于日本《法学教室》2014年第12号(总第411号)。
**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