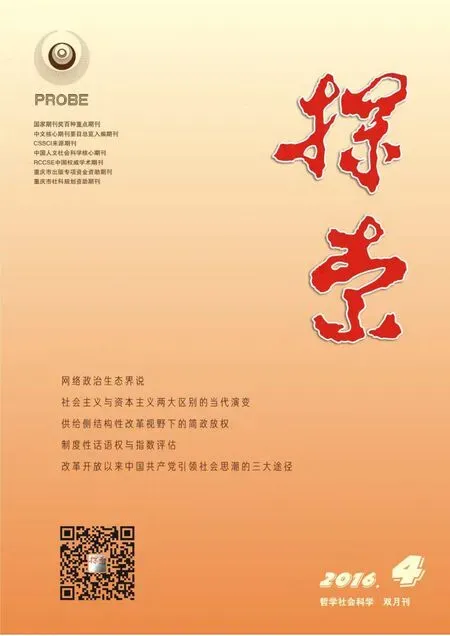我国国家安全视阈中的边疆生态治理研究
林丽梅,郑逸芳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由此生态安全成为一项基础性的国家安全战略。边疆地区是我国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区域,有着鲜明的地理区位边陲性、民族文化多样性、生态禀赋交错性、经济社会欠发达性等区域特点。在目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和国家安全战略下,边疆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与中心区域相对的边缘地带,而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和决定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的重要区域。习近平提出“治国必治边”的重要战略思想,强调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21世纪以来,我国正努力由工业文明步入生态文明,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组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边疆地区的自然要素禀赋特征使其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基地,而边疆生态建设则成为国家生态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生态安全是指一国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均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状态[1]51。陆疆是我国传统边疆的基本组成部分,而随着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建设海洋强国战略部署的提出以及海域主权问题的升级,海疆在我国边疆治理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故将海疆和陆疆共同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其中,陆疆包括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甘肃和云南在内的9个省区,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而海疆是指领海基线以外的国家管辖海域,主要以海岸线长进行测量,故不对具体省份进行界定。无论是陆疆还是海疆,其生态状况及其治理水平在国家安全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影响着国家安全的维护程度。
1 我国边疆生态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
相对于海疆,陆疆是我国生态过渡区和植被交错区,处于农牧、林牧、农林等复合交错带,具有特殊的生态禀赋、地理区位和民俗文化,也是我国目前生态问题突出、经济相对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等多项社会问题重叠区域[2]。特殊的地理区位、生态禀赋以及由此引发的复杂社会问题共同决定了边疆生态安全在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中的全局性地位和作用。
1.1 边疆生态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基础
国家生态安全视域中的边疆突破了传统疆界的概念,成为因气候条件、水域面积、海拔高度、经纬度、生态要素等的差异而形成的特殊生态屏障区,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的保障作用。我国边疆地区地理位置特殊,面积广袤,拥有丰富的源头性生产要素,在全国生态系统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对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起着生态屏障的作用[3]。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了构建“两屏三带”为主体的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除南方丘陵山地带外,包括边疆地区的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北方防沙带、东北森林带等。全国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名录中,涉及陆疆九省区的就有20个。另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我国森林覆盖面积2.0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21.63%,其中,覆盖面的56.3%分布在边疆地区。享有“三江源”美誉的青藏高原,聚集着我国大部分的冰川,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和上游;被誉为“绿色香格里拉”的我国西南地区,是水、清洁空气和独特动植物物种的富集区,仅云南一省,就拥有17 000多种高等植物,6 550多种药材,1 700多种脊椎动物,其种类占全国一半以上[3]。草原是我国大西北地区的保卫者,有草原植被的地区,能够降低地表的风速,减缓移动沙丘的速度,对固沙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边疆地区既是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主要集中区域,在生态上具有拱卫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战略意义。
1.2 边疆生态关乎国家能源安全的实现
能源是非原位性资源,地区间的合理配置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我国不同区域因资源赋存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显著差异,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承担着不同职能。边疆地区因具备能源开发、接替和储备等多重功能而享有深厚的国家能源安全底蕴。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十三五”期间将是我国能源革命全面爆发的关键时期,新能源革命将引发大规模新兴产业兴起,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新引擎[4]。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2014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可由目前的13%提高到26%。我国边疆地区地广人稀、少雨多风、阳光充沛、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发展风能、太阳能、海洋能及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重要基地。西藏、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边疆省区的太阳总辐射量和日照时数均为全国最高,属世界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之一。陆疆总长达20 000多公里,海岸线长18 000多公里,加之海疆的5 000多个岛屿,因此边疆地区无疑是我国风能资源丰富区。而浙江、福建、辽宁等海疆省份沿岸是我国潮流资源的汇集区,约占全国总量的42%,承担着目前海流能资源的开发研究任务。据《中国林业与生态建设状况公报》显示,边疆地区丰富的森林以其占陆地生物物种50%以上和生物质能总量的70%以上的优势成为新能源开发的重点。除丰富的生物质能储量外,森林的强大“碳汇”功能还是充分利用太阳能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改善能源结构、维护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算,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约储存了2.48万亿吨碳,其中1.15万亿吨碳储存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由此可见,我国边疆地区不仅蕴藏丰富的优质能源,更是发展新能源的重要基地,在国家能源安全格局中占据关键地位。
1.3 边疆生态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危机源头
当生态系统面临不可逆的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退化时,生态问题就上升到了生态安全层面。生态安全问题往往都是由小范围、局部的生态问题逐渐扩大演变而成,这种演变特征使边疆地区的生态问题及其威胁极易成为跨区域、跨国界的危机,成为国家生态安全的危机源头。生态环境的因果链联系是一道不可违抗的自然法则[5]。1997年创历史纪录全年226天的黄河断流、1998年的长江水灾和2000年北京等地区空前频繁的强沙尘暴,这些罕见灾害的发生正是西部边疆地区生态环境长期遭受破坏的“因”所引发的“果”。草原系统防风固沙功能的丧失是导致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的源头。贵州、四川、云南等西部省份的森林植被长期遭受乱砍滥伐,致使森林生态系统难以发挥调节径流的作用,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土地蓄水保水性能变差,成为主要河流洪灾和干旱并存的主要原因[3]。此外,海疆也因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减弱和海洋环境灾害的频繁发生等对陆域生态环境造成威胁。“一夜风沙起,埋没十八村”是福建平潭、东山海疆岛屿早期由于植被稀少引发沙埋村庄的历史典故,形象地体现了海疆地区生态破坏对于陆域危害的严重性。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生物多样性与物种灭绝之间存在量化因果关系,即1个物种的灭绝将会导致约200种数量的其他物种的灭绝[5]。边疆地区丰富的物种数量和种类使其成为国家的生态安全的基石,而边疆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也将相应地成为国家生态安全危机的源头。目前,我国广大边疆地区的源头性生态破坏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已上升为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的首要问题。
1.4 边疆生态治理是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重要保障
疆域是国家存在的物质载体和空间实现形式,疆域安全的建构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前提。非传统安全观强调和重视以人为核心,突破传统以军事对抗为特征的生存场域的争夺。边疆生态治理成为新安全观之下保障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的新内容。长期以来,我国边疆地区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使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错综复杂,成为影响边疆地区甚至国家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6]145,而生态环境的破坏更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辩证地看,生态安全在任何时候都应是保障民生的基础。特别是21世纪以来,生态安全日渐成为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民生保障。“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7]习近平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民生本质。但目前,针对边疆生态外部效益的调节政策往往要求当地居民牺牲生存和发展机会,生态退化引发的沙尘暴、水灾等自然灾害进一步压缩边疆地区居民的生存空间,产生大量的“生态难民”,这类人群因不能在原来的居住地生活而主动或被迫逃离,将对边疆与内地的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甚至因生存境遇的强烈反差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可能导致部分“生态难民”产生报复社会的扭曲心理,增加社会安全风险。另一方面,“生态难民”群体一旦被边疆地区的“三股势力”所利用,将对国家政治安全产生重大威胁。此外,由于边疆出境河流、跨境山脉高原、跨境草原荒漠和森林的存在,边疆生态问题还可能是超越主权国家和管辖范围的区域性问题[3],由此决定了边疆生态安全对于固边守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各民族团结昌盛和社会稳定等亦具有重要的全局性意义。从地理区位与自然条件来讲,边疆地区还是军事战略防御的前沿,辽阔的疆域能为国家提供宏大的军事战略纵深[8];甚至当面临军事挑战或战争威胁时,拥有优良生态植被的辽阔疆域还是谋划军事布局和实施攻防计划的屏障。这一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传统陆疆军事安全建设中,更在目前海洋利益不断拓展、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海疆军事安全保障中得以凸显。
2 我国边疆生态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在我国,边疆地区独有的生态赋存特质、地理空间特质、地缘政治特质和民族文化特质交织在一起,使得边疆生态治理在保障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从目前来看,我国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对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2.1 自然资源利用率较低
丰富的资源、能源禀赋是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但目前边疆地区仍然较多采用传统粗放型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以能源消费为例,表1为边疆省区能源消费总量的统计情况,从表中可知,除吉林和广西两省区以外,其他边疆省区的单位产值能耗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6—2014年,边疆各省区的生产总值能耗虽然总体有所下降,但相比全国平均水平,各省区的能耗绝对数值仍然较高,且近年来的能耗降低幅度也普遍略小于全国平均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边疆地区丰富的资源储量是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前提,低效自然资源利用的本质是生产方式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将阻碍全国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直接影响经济结构优化和能源供给安全。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新能源战略的重要阵地,边疆地区的能源使用效率将直接影响经济、环境治理、生活方式等的全方位变革成效,影响国家经济、生态、军事及民生等的国家安全战略格局。
2.2 生物多样性日益锐减
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掠夺式开发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边疆生态系统平衡遭受破坏,生态环境的改变使许多珍贵物种濒临灭绝的威胁,生物多样性日益减弱。相关研究指出,全国存在大量通过围垦湖泊、开垦沼泽来增加土地面积的现象,仅黑龙江三江平原湿地,遭受开垦的湿地面积就超过了400万公顷[1]371。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海疆污染程度日益加重,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也逐年下降。虽然我国森林覆盖率有增长的趋势,但主要是人工林的增长,而森林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原始林面积比较狭小。近年来,我国有200种植物灭绝,高等植物受到威胁种类达4 000~5 000种,占总数的15% ~20%[9]。表2显示了边疆地区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情况,2014年我国边疆地区自然保护区个数为929个,面积为9 835.7万公顷,相比2008年,自然保护区个数增加了26个,但面积减少了398万公顷,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比重下降了0.53个百分点。边疆地区自然保护区的破坏及退化直接威胁着物种的生存。生物多样性导致生态系统稳定性,当今边疆地区生物多样性危机中,生态环境的改变使物种濒临灭绝危险且最终导致物种灭亡,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又使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产生剧烈变化,进而加剧生物种类的消失[10]。如此恶性循环将直接影响与国家粮食安全息息相关的农业生态系统的协调稳定,粮食安全这一根本问题如果持续恶化,将严重危及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而生物多样性是维护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平衡的根本,生态系统平衡的丧失将使生态环境灾害频发,从而严重危及国家生态安全。

表2 边疆省区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
2.3 土壤侵蚀严重
土壤侵蚀是土地退化和生态恶化的主要形式,也是边疆地区生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据2010—2012年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边疆地区土壤侵蚀总面积为215.06万平方公里,土壤侵蚀率为35.94%,占全国土壤侵蚀总面积的72.9%。由表3所示,边疆各省区面临不同程度的土壤侵蚀问题,其中,内蒙古、新疆两区的土壤侵蚀率均在50%以上,甘肃有接近50%的土地遭受侵蚀破坏。自然因素是边疆地区土壤侵蚀的客观潜在条件,而人为因素是加速土壤侵蚀的催化剂。由于边疆地区陡坡较多,容易形成水流对土壤的强大冲刷力;而土壤结构和颗粒组成等土壤质地影响土壤抗冲性和抗蚀性,决定土壤侵蚀的程度[11]。以西北黄土高原为例,土壤中砂粒及粉砂粒含量多,粘粒少,颗粒间粒结力弱,稳定性差,易遭水蚀和风蚀[12]。除此之外,滥伐过伐林木,毁林毁草造田,过度放牧等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是边疆地区土壤侵蚀严重的重要人为因素。植被破坏导致林草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的功能下降,地表流量加大,加剧了土壤侵蚀。同时,开矿、修路等工程建设以及城市发展等使土壤侵蚀已不完全受自然规律支配,而成为不合理开发利用行为的恶果。边疆地区水土流失、风蚀沙化致使江河上游源头的大量泥沙涌入河床,降低河道行洪能力,导致下游断流或增加水患危险,对国家核心区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更为直接的是,土壤侵蚀将破坏土地资源、降低耕地生产力,恶化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制约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剧贫困程度,从而危及边疆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

表3 2011年边疆省区土壤侵蚀情况
2.4 草原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国家草原项目效果评估与草原治理政策完善》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严重退化草原面积近1.8亿公顷,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继续扩张,天然草原面积每年减少65~70万公顷[12]。除自然退化外,人为的过度放牧、过度开发也使草原生态系统整体退化,我国已有90%左右的牧区草场处于超载放牧状态。由过度放牧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主要表现在草原覆盖率的减少、土地沙化、动植物种类的减少和土壤肥力的下降。另据《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截至201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0%,沙化土地总面积172.1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93%,且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等边疆省区,这5省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总面积分别占全国的95.64%和93.95%[13]。内蒙古、宁夏、新疆等省区草原生态系统的退化造成土地荒漠化,所引发的沙尘暴对华北、西北、东北乃至长江以南广大地区造成危害,严重影响国家生态安全;另一方面,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还使可供农牧业使用的土地面积减少,压缩农牧民的生存空间,由此产生大量的“生态难民”,形成对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的潜在因素。
2.5 海疆污染严重
建设海洋强国,发展海上力量和海洋外交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但相应的海上突发事件应急救助、海洋灾害预警监控等公共服务体系比较薄弱,海洋环境保护队伍和能力建设无法跟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节奏,导致海洋生态承载力不断下降,海疆污染日渐严重。根据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15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2015年冬季、春季、夏季和秋季,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为6.7万、5.2万、4.0万、6.3万平方公里,而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44个大中型海湾中,21个海湾全年四季均出现劣四类海水水质[14]。由于人类对海洋生态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导致海洋生态功能失调而发生海洋自然灾害。东海为赤潮高发海域,赤潮发现次数占总数的43%;渤海赤潮累计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54%[14]。渤海、黄海和东海局部滨海地区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加重,砂质和粉砂淤泥质海岸侵蚀严重。海洋生态系统遭受破坏,极易出现海域富营养化、生物病蔓延等问题,严重影响海洋生态环境和近海养殖业的发展。而海洋环境灾害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对沿海陆域地区的生态安全和经济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此外,海疆环境污染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理,还将上升为区域性的公海海洋污染,增加我国海上外交纠纷,影响国家政治安全。
3 加强边疆生态治理维护国家安全的策略
加强边疆地区生态治理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要坚持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以下简称“三大效益”)相统一。基于丰富的生态禀赋条件发展特色生态文明经济是边疆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二是遵循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5]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一哲理性概括深刻强调了生态系统内在规律的重要性。遵循生态规律即指开发利用边疆地区生态资源需要注重生态阈值,善于运用生态系统协同演进规律,强调在维护绿水青山中打造金山银山。
3.1 创新利用边疆生态资源,实现“三大效益”相统一
生态环境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资产、特殊的生产力,合理利用边疆地区的生态、文化等特色资源创建相适应的发展方式是解决边疆地区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一是结合边疆地区特色文化发展体验经济[1]346。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背景下,可依托边疆地区的生态文化要素,创造与消费需求相适应、丰富多彩的体验产品新经济形态。如内蒙古借助典型性的节日“那达慕”展示少数民族独特的庆祝方式,结合草原内涵文化在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同时还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即为创新利用地方特色资源的成功案例。二是协调相关利益主体,营造共赢局面。边疆生态建设中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是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的代表性主体,如何在多主体目标函数和行为模式各异的前提下达到多元主体利益博弈均衡是实现边疆地区生态、经济和民生协调发展的关键。我国治沙英雄王文彪团队创造的“库布其模式”是“三大效益”相统一的成功典范。在治理过程中实践出政府政策性支持、企业产业化拉动、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的“生态、产业、民生”共赢模式。创新利用边疆生态资源发展特色经济,不仅能减少对边疆资源的破坏性利用,而且依托创新经济形态还可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提高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利于保障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此外,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均衡还能调动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加强边疆生态治理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3.2 转变边疆生产生活方式
发展是硬道理,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更为重要。传统工业文明生产生活方式对边疆地区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破坏,转变粗放低效的生产生活方式显得极为迫切,也是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必由之路。边疆地区的生态文明经济发展要在逐步改造提升传统经济基础上发展创新经济、体验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生态文明经济新形态[8]。云南省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积极实施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工程,形成了“林果+饲草+畜牧+沼气”一体化山区循环农业模式、“元阳梯田”生态耕种模式以及乡村“农家乐”生态观光旅游模式[16]。从生产力转变和创新角度来讲,应弱化经济发展对传统技术体系的依赖,加强生态技术体系的建设,发展生态生产力,转变工业文明的末端治理为生态文明的过程治理。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发展生态文明经济的重要引擎,以绿色消费、循环消费和低碳消费为主的生态型消费经济无论从消费行为本身还是从消费需求对生产市场的引领作用来讲,都是生态文明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特别是经济转型期,我国消费主导型经济终将成为经济重要支点,发展生态型消费的重要性也就毋庸置疑。持续加大宣传教育的同时,可适当利用资源型消费产品的价格调节机制来加以引导实现节能消费。转变边疆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能直接提高资源使用率,生态文明经济形态和生态型生活方式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还能减少人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实现保护性开发利用,以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
3.3 健全边疆生态补偿机制
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说,生态建设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如果不对提供这种正外部性的经济主体进行补偿,那么外部效应将很难持续[17]79。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供给和消费面临着市场机制失灵和政府外部性调节失效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边疆地区自然资源价格难以体现,缺乏清晰的生态产权,“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谁使用谁付费”等原则的市场补偿手段较少得以应用,表现为市场主体的低参与度。另一方面,不健全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体系、模糊的生态补偿主体和对象导致生态补偿不到位,挫伤了建设主体的生态保护积极性,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难以持续。完善对边疆生态建设主体的生态补偿工作,一是建议设立国家生态安全基金[18],加大生态安全建设投入并更好地统筹区域间的生态安全建设资金,以保障生态补偿的资金供给。二是要设计“造血型”生态补偿优化方案。加大在科技、人才、信息以及扶贫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加强政府购买生态系统服务的力度,促进生态与经济的优势互转,实现从单纯的“输血型”向“造血型”综合补偿转变。三是要加大市场机制在边疆地区生态补偿中的应用。减少以往以完成项目建设为目标的补偿方式,同时,健全生态利益相关方公平补偿的市场交易制度和自愿协商制度。最后,需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与民众的关系,强化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多元分担的融资机制,构建边疆地区多元协同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2]。应对边疆生态环境破坏形成的“生态难民”可能引发的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风险,健全的生态补偿机制能够减少因生态破坏导致的民生保障问题,以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生态补偿方案及措施的优化还能切实保障“三大效益”的统一,调动生态建设主体的积极性,加强对边疆生态屏障的保护,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从生态保护制度机制层面上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3.4 充分利用国际资本资源
面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挑战,国际社会在资源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协作成为客观需要,生态合作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合作交流的新内容。境外的生态恶化和生态侵略存在对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一定威胁和危害,使得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资本进行边疆生态治理具有现实要求与条件。“一带一路”战略也为边疆地区生态安全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19]。从保障国家安全角度出发,我国在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上应积极强调与邻国的协调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的资源和资本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强化本国生态安全的同时增强全球性生态问题治理的国际影响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将造林和再造林碳汇项目列为第一个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项目,并特别规定造林与再造林分别必须是在过去至少50年和自1990年1月1日以来的无林地上开展的人为造林活动。对应此规定,边疆地区无疑成为开展森林碳汇项目的主要首选区域。通过国际森林碳汇交易使生态产品转化为生态商品,同时利用国际资本促进边疆地区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湄公河流域是国际社会环境保护合作的典型案例,也是我国边疆地区充分利用国际社会资源治理边疆生态的重要实践。通过签订《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等规定,各国在可持续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湄公河的水资源和有关资源的领域里进行合作。通过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和资源开展合理治理,能够直接增强边疆地区生态治理的力量,加强环境保护力度,缓解边疆地区生态安全问题及其对核心区生态安全的威胁,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国际合作治理同时还能避免因跨界生态问题引发的外交冲突,从而有利于保障国家政治安全。
4 结语
生态安全是21世纪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生态安全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关系到国家安全,有着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边疆地区生态环境不仅是该地区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物质保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屏障,其生态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加强边疆生态安全建设是我国重建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部分,也是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边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及其严峻的安全形势决定了边疆生态治理的战略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而其生态禀赋的交错性和脆弱性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则加大了边疆生态环境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为推进边疆生态治理带来了新的时代性机遇。面对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只有高度强调边疆生态治理的全局性战略意义,认清边疆地区的自然、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把保护环境、修复环境和提高供应生态产品能力作为首要任务,处理好复杂的供给主体关系,厘清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将边疆生态治理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加以审视,才能为国家安全构筑牢固的生态屏障,实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安全战略。
参考文献:
[1] 廖福霖.建设美丽中国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 冯琳,赵亚娟.西部边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特点及其应对措施[C]∥2013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乌鲁木齐: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13:338-343.
[3]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课题组.生态文明与民族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6):5-12.
[4] 张孝德.“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新思维:新能源革命引领战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2):21-26.
[5] STRANDMARK,A.Climate change effects on the Baltic Sea borderland between land and sea[J].AMBI,2015(44):28-38.
[6] 周平.中国边疆治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7] 鹿心社.建设生态文明增进民生福祉[N].人民日报,2014-10-28.
[8] 白利友.国家治理视域中的边疆与边疆治理[J].探索,2015(6):116-120.
[9] 武建勇,薛达元,赵富伟,王艳杰.中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研究进展[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3(2):146-151.
[10]张步翀,李凤民,黄高宝.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及其稳定性的影响[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6(4):12-15.
[11]刘天军.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成因与治理措施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70-75.
[12]彭珂珊.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逆向演替之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3(2):19-25.
[13]屠志方.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及分析[J].林业资源管理,2016(1):1-13.
[14]国家海洋局.2015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N].中国海洋报,2016-04-08.
[15]王晓东.加快推动绿色发展变革[N].人民日报,2016-05-23.
[16]罗雁,陈良正,张思竹.云南山区生态农业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J].西南农业学报,2010(1):2137-2142.
[17]廖福霖.生态文明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
[18]胡鞍钢.关于设立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基金的建议——以青海三江源地区为例[J].攀登,2010(1):2-5.
[19]丁忠毅.“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西部边疆安全治理:机遇、挑战及应对[J].探索,2015(6):12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