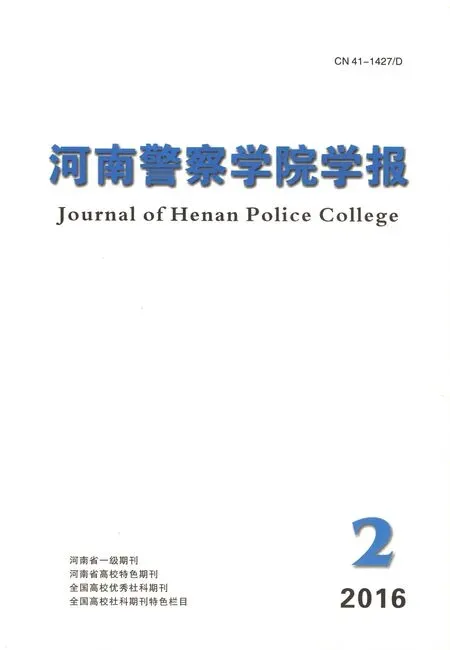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法律地位
——兼评《刑法修正案(九)》对该款的修改
叶小琴,吕大亮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法律地位
——兼评《刑法修正案(九)》对该款的修改
叶小琴,吕大亮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于行贿罪量刑具有重大影响,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特殊处罚规定。在重刑反腐思想之下,97《刑法》这一款被认为是妨碍惩治腐败的“缺陷”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进行了从严修改,加大对于行贿人的处罚力度。虽然该款在适用中出现诸多问题,但是这一修改不但混淆了该款应有的法律地位,并且将量刑规范化问题上升为立法问题。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行贿罪;量刑;刑法修正案(九)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公布的《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第四十五条中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1]《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该款的修改是否适当?《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修改前法院审理行贿案件中对于量刑发挥了什么作用?笔者拟从该条款对行贿罪量刑影响的定量分析和关于该条款法律地位定性两个角度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司法适用效果的定量分析
基于行贿案件时间新颖性、来源广泛性、地域分布随机性的因素,笔者选择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样本来源数据库。采用自然抽样与分层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抽取样本,即以数据库对判决的采集收录作为自然抽样过程,再将数据库内收录的判决按时间排列作为取样框架,从中截取最新时段抽取对应时段内的全部案例,在此基础之上用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方式,抽取本次研究样本。采用这种取样方法的原因在于:数据库收录判决即为一次抽样,通过截取数据库中的时段内的全部案例以保证案件的新颖性以及适用法律与刑事政策大环境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分层随机抽样,分层与随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案件来源的广泛性、实现取样的科学性,以及保证抽取样本的随机性。
首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选取时间段2014年8月1日-2015年8月1日,设置此时间限制的原因是保证案件的新颖性以及适用法律与刑事政策大环境的统一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以及“十八大”以后大力反腐的刑事政策环境),输入关键词“行贿罪”得到行贿罪案件刑事判决书1695份,①http://www.court.gov.cn/extension/search.htm?keyword=%E8%A1%8C%E8%B4%BF%E7%BD%AA&caseCode=&wenshuanyou=&anjianleixing=%E5%88%91%E4%BA%8B%E6%A1%88%E4%BB%B6&docsourcename=%E5%88%91%E4%BA%8B%E5%88%A4%E5%86%B3%E4%B9%A6&court=&beginDate=2014-08-01&endDate=2015-08-01&adv=1&orderby=&order=,中国裁判文书网,2015-9-1。其中一审行贿案件为697件,②http://www.court.gov.cn/extension/search.htm?keyword=%E8%A1%8C%E8%B4%BF%E7%BD%AA%E4%B8%80%E5%AE%A1&caseCode=&wenshuanyou=&anjianleixing=%E5%88%91%E4%BA%8B%E6%A1%88%E4%BB%B6&docsourcename=%E5%88%91%E4%BA%8B%E5%88%A4%E5%86%B3%E4%B9%A6&court=&beginDate=2014-08-01&endDate=2015-08-01&adv=1&orderby=&order=&page=1,中国裁判文书网,2015-9-1。由于数据库自身检索条件限制,在排除了混杂于其中的单位行贿罪案件137件、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罪48件、介绍行贿案件1件后,第一次抽样的结果为511件一审行贿案件判决书。其次,笔者以审理法院地区属于东部、中部、西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等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12个省(市、自治区)③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8/t20150812_1229213.html,国家统计局,2015-9-1。)的划分作为抽样层次,设置此划分层次是为了保证最终的抽样样本在地域上分布比较均匀,以克服案件裁判结果的局域性限制。将抽样的数量限制为100件,在审理法院属于东部地区的案例中抽取35件,在审理法院属于中部地区的案例中抽取33件,在审理法院属于西部地区的案例中抽取32件。将样本研究数量确定为100件,占到了抽取对象接近20%的比例,符合研究科学性的标准,并且各地区案件分布数量基本上符合地域分布均匀的要求。最后,对于分层次随机抽取的样本进行检验,对于选取的样本如果有本文研究的量刑情节以外的影响量刑的情节则重新抽取,让量刑结果尽量减少受到本文研究对象的情节以外的因素影响,提高定量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笔者作了上述的努力,通过科学的抽样方法与合理的案例选择,保证研究对象的100个样本具备以下特点,首先是案件审理范围广泛,内陆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涉及。其次是样本的重点突出,行贿案件具有“经济性”的特点,东部发达地区案件数量较多并且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中部主要集中在湖北、安徽,西部地区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再次是案件排除了前科、累犯、向多人行贿、共犯等可能影响量刑的情况,将研究的案例集中在案情较为简单的案例,使得分析结果尽量不受到研究控制变量以外的要素影响。笔者希望通过以小见大,在为数不多的样本研究下能够得出具有一定推广性的结论。尽管如此,所有的统计和分析仅仅来自这些材料的文字表述,无力进行更加深入的考证,因此只能说是朝着真理的方向努力,不免有管窥蠡测之嫌,但是笔者认为本文的定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量刑影响分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通过一系列数据统计分析,笔者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于行贿罪量刑的影响大于其他量刑情节
1.各情节比重的考察——形式影响力的比较
对于该100个案件,按照其裁判文书中所列明的法院最终认定的量刑情节进行考察,主要包括以下事实情节:(1)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2)犯罪以后投案自首,(3)归案后如实交代,(4)认罪悔罪,(5)主动退出违法所得,(6)未提到有任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鉴于此,笔者将100个案件按照事实情节情况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即《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情节,并将同时具备“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的案例归入其中;第二类为没有上述情节,但是具有“自首、坦白、立功”情节,即《刑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规定情节以及退赃等酌定情节归入“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类;第三类为无任何法定或酌定情节的行贿犯罪案件。

图1
如图1所示,具有“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的案件占到66%;具备“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的案件占到了26%;在行贿案件中没有任何法定或者酌定情节予以轻刑的案件占到了8%。毫无疑问,得出的结论是,在行贿罪案件中,绝大多数的案件都具有法定或者酌定的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事由,其中“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即《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量刑情节适用频率最高,该条文对于行贿罪量刑的影响从存在比重这一形式的角度来说要大于其他情节。
2.量刑具体影响力的考察——实质影响力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研究《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与其他量刑情节在适用上有无实质性区别,笔者将全部案件进行进一步分类,主要控制的是量刑情节变量(见表1、表2)。其中对于选取样本为全部案件以及同类案件(此处的同类案件是指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案件,此类案件在100个样本中有71件)。笔者在这两份样本基础上,控制量刑情节变量,分别得出全部案件中与同类案件在存在“追诉前主动交代”与“无上述情节”(表1中的“无上述情节”是指:不具备其上一栏的情节即不具备“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的案件)的平均量刑差值(见表1),具有“自首、立功、坦白等量刑情节”与“无上述情节”(表2中的“无上述情节”是指:不具备其上一栏的情节即不具备“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笔者提请读者注意区分表1与表2中这一变量具体所指范围的区别)的平均量刑差值(见表2)。从两个表分别单独来看,可以看出不同量刑情节在“全部案件”以及“同类案件”之下对于量刑的影响。从两表比较来看,通过“相差”数额的比较也可比对出“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与“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对于案件的量刑影响轻重。

表1

表2
如表1所示:对于研究对象的100个案例,其中具有“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的案件的量刑刑期平均为20.86个月,在全部案件中“无上述情节”,也即包括了“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和无任何法定或酌定情节的案件平均刑期在23.12个月,两者相差2.26个月。在全部研究对象中的66件“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的案例中有41个案例是属于在这里所说的“同类案件”,其平均量刑为13.6个月;在全部研究对象中的34个“无上述情节”的案例中属于此处的“同类案件”的有30件,平均量刑为17个月。
如表2所示:在100个研究对象中有66个案例属于具有“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的案例,在此基础上具有“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的共有23个案例,其平均刑期是23.13个月;表2中“无上述情节”案件是指在具备“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之内的无其他情节案件,共有43个案例,其平均量刑为19.65个月;具有“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案件中的“同类案件”共有41件,其中同时具备“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的案件15件,平均量刑14.67个月;具有“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案件中的“同类案件”不具备其他情节的有26件,平均量刑13个月。
在表1和表2的统计结果中,表1显示了具备“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与不具备该情节的案件,无论从整体分析,还是从同类案件的角度来看,“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对于轻刑化有重要影响。表2的数据统计显示,从整体以及同类案件比较分析来看,在具备“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基础上,不具备“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量刑反而更轻,这似乎不符合我们的经验逻辑,笔者揣测首先这是由于表2的分析案例是在具备了“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的基础上,而不是以全部案例为研究对象,因此“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其次案件的具体涉案金额以及法院审理地区差异也可能是导致的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表2从侧面说明在具备了“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基础上的案件,是否存在着“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与量刑没有直接关系,至少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没有这种联系。将表1和表2两者的“相差”进行比较,一个成正比,一个成反比,更能够看出,“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即《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于行贿罪的量刑实质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法定或者酌定量刑情节。
综上图1、表1、表2,《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于行贿罪的量刑的影响从深度与广度、横向与纵向、范围与实质层面都要大于其他法定或者酌定量刑情节。
(二)《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于量刑轻重的影响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作为刑法分则中行贿罪的量刑情节,对于量刑的影响必然存在,但是究竟在修正案出台前具体发挥着怎么样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法定刑幅度呈现出怎么样的影响趋势,尚不清楚。为了解决这几个问题,笔者依据刑法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①《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将案件根据涉案金额分为“一般案件”与“严重案件”(见图2),其中涉案金额1-20万元属于“一般案件”,20万元以上是“严重案件”。在同一分类的案件中控制的变量为“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无情节。

图2
如图2所示:从全部研究对象来看,三种量刑情节的平均刑期分别为20.86个月、18.77个月、37.25个月,总体可以看出有无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对于量刑影响较大,但是前两种量刑情节对于量刑的影响区别不怎么明显;在“一般案件”中,三种量刑情节的平均刑期分别为13.6个月、16.3个月、19.7个月,虽然区别不大,但是不同情节对于量刑的影响也可见一斑;在“严重案件”中,三种量刑情节的案件平均刑期分别为32.8个月、48个月、90个月,三种量刑情节的量刑差距明显。
(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于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影响
量刑情节对于量刑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于量刑的影响主要有“减轻”或者“免除”两种方式,在此笔者主要通过控制情节变量,根据行贿罪中缓刑的适用比率以及免除处罚的适用比率来分析该条款对于行贿罪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影响。

表3

表4
如表3所示,在研究对象的全部100个案件中,缓刑的适用比率为75%,免除处罚的适用比率为7%;对于具备“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的案件缓刑比率为79%,免除处罚比率为8%;对于不具备此类情节的案件即包括了本文分析控制的后两种变量的案件适用缓刑的比率为68%,免除处罚的比率为6%。相比较而言,具备《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情节的案件的缓刑以及免除处罚的比率高于平均水平。
如表4所示,对于缓刑的适用比率,“一般案件”中具备“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的,缓刑适用比率最高,同时在“严重案件”中,缓刑适用比率较高;从纵向比较来看,无论是全部案件平均水平还是“一般案件”以及“严重案件”,有无“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对于缓刑的适用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不排除受到刑事政策、个案公正等情况的影响,但是仅从此表格的数据分析来看,具备“追诉前主动交代”情节对于行贿罪判处的刑罚是否适用缓刑的影响,要远远超出对于其他因素的考量。
二、《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法律地位的定性分析
(一)理论争鸣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对于行贿罪量刑影响重大,那么该情节法律地位如何呢?即人民法院在行贿罪量刑时,该条款的法律地位是自首、立功、坦白或者是与上述情节都不同的特殊量刑情节?学界对此争议颇大,笔者将其归纳为特别自首说、立功说、坦白说和折中说。
第一种观点即特别自首说,在考察各种自首分类①关于自首的各种分类,参见莫洪宪著《论自首和立功》,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2期。的基础上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内容划入到自首范围内。持该种观点的学者指出区别于一般自首、准自首,特别自首无论从成立要件、处罚原则还是法典体系的设置上都是特殊的,均具有不同于一般自首和准自首之处,不能为上述两类自首类型所容纳,因而不可否认地成为一种全新的自首类型。《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的不是坦白而属于一种特别的自首[2];对于立功说,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凡是揭发行为引发他人作为犯罪人受到刑事追究,都可以构成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3],那么《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当然属于立功;对于第三种观点,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情形符合坦白的规定[4]。对于第四种观点即折中说,不同的学者对赞成这种观点的理由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实际上是立功、坦白、自首等情形可能存在的竞合形态,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学者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在成立标准上的规定明显低于自首,从行贿者的角度看,性质类似于自首,但从宽程度应低于自首;从对受贿案件破获的作用来看,其性质类似于立功,但不能满足立功的条件[5]。
笔者认为:首先,对于特别自首说,我国刑法学界通说将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分为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两种[6],这里的特别自首与持特别自首说的“特别自首”容易产生混淆,并且如果认定《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自首的特别条款,就必须要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自首成立条件是自首概念的具体化。通常认为成立自首的条件有三:(l)必须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2)必须在投案后主动如实地交待自己的罪行;(3)必须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三者同时具备,缺一不可[7]。文字中渗透着立法精神与目的,要把握立法精神与目的就必须从法律条文中找根据。解释者必须从法律条文的客观含义中发现立法精神与目的,而不是随意从法律条文以外想象立法精神与目的。这是对刑法进行客观解释的逻辑结论[8]。从对修改前的《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条文分析来看其明显不具备上述自首条件,该条款在成立条件、法定从轻幅度上都超出自首范围,因此不宜认定为自首或者自首的特殊类型;其次,对于立功说,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生效以后,根据《解释》第七条,该观点基本上已经站不住脚了。②因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而破获相关受贿案件的,对行贿人不适用《刑法》第六十八条关于立功的规定,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再次,对于坦白说,笔者仅仅从其他著作中转引到了持该观点的结论,并不清楚其具体论据,但是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与《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对比来看,两者之间前者除了具备“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条件以外,其内涵的外延明显大于坦白的范畴,因此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法律地位界定为坦白值得商榷。
(二)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1.微观:适用效果差别悬殊
松宫孝明教授指出:“法的解释和适用必须具有同样的事情做同样的处理,这种意义上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在每一个别问题上,如果采取的是仅在解决个别问题是看似较为妥当的权宜的解释,终究无法实现社会的统一。”[9]从微观上来看,《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在司法适用中的问题就是个案比较裁判差别悬殊。所谓公正公平的刑罚裁量结果,即法官的刑罚量定遵循同等情况同样对待的平等原则,避免相同事实、相同类型案件定差异悬殊的刑罚[10]。这里的适用效果差别悬殊,以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数据为基础,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在法院的判决中,在同样具备《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情节的情况下,裁量结果的差别巨大。如:湖北某法院对于行贿金额达到9.5万元的行贿人免予刑事处罚,安徽一法院对于行贿2万元的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①参见(2015)鄂樊城刑一初字第00020号,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刑事判决书;(2015)舒刑初字第00011号,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广东某法院对于行贿金额11万元的行贿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另一法院对于行贿金额3万元的行贿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②参见(2015)佛明法刑初字第127号,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穗越法刑初字第1284号,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对于缓刑的适用以及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是予以减轻处罚抑或免除处罚存在着适用上的差别,导致了案件最终裁判结果的悬殊。第二种情况是指,在有无《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情节情况下,适用上的差别。如海南某法院判处行贿金额9.8万元,仅具有坦白情节的行贿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五年;湖南某法院判处行贿金额160万元,具备《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情节的行贿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五年。③(2014)屯刑初字第105号,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桃刑初字第362号,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同时,前文定量分析已经对有无行贿罪特殊处罚条款对于行贿量刑的影响作了细致的比较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2.宏观:法律地位不明
由于学界尚对于该问题的法律定位存在着争议,因此在司法适用中对案件量刑情节的认定也存在诸多混乱的情形。从本文定量分析的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在符合《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情节的66个同类案件中,有23个案件存在该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把《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情节与自首情节相混淆。根据判决文书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将具备《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情节,认定为自首从轻处罚。④(2015)舒刑初字第00111号,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这种情况首先是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情节的法律地位与自首混同,其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价值在于限制刑罚权滥用……防止法官在量刑中滥用刑罚权,无疑是罪刑法定原则所面临的新课题”[11],该法院在原本可以适用“减轻”情节之下,适用自首的规定予以“从轻”,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第二种情况:将具备《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情节的案件,不予考虑该情形,只考虑符合自首的情况并按照自首适用“可以减轻处罚”的规定,这种情形将符合更为严苛的自首成立条件的案件,直接作为自首处理,对于是否构成《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不予评价。⑤(2014)普刑初字第1343号,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三)笔者的观点
对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法律地位学界存在着诸多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中该条款的适用也存在上述的诸多问题。学界的争鸣与司法的适用往往互为表里,只有在准确定性基础上才能解决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但是学界关于该条款法律地位的各种观点,如上述都是有缺陷的。笔者认为必须要在考察自首、坦白、立功的构成基础上,立足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条文规定(包括司法解释的适用规定),并参考长期司法实践中形成的该条款的司法适用效果,以确定本条款的法律地位。因此,折中说具有合理性。
笔者赞同折中说以及李少平副院长的理由,⑥笔者仅赞同该文章关于此条款法律地位分析的结论,并非赞同其主论点,详细内容参见李少平著《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赞同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作为刑法分则条文中对于行贿案件处罚的特殊条款,这一特殊条款区别于一般自首、坦白、立功等法定情节以及退赃、认罪等酌定情节。理由如下:
首先,从体系结构上来看,《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是作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下面一款。量刑是在定罪的基础上,对具体刑罚进行裁量。定罪完成了,就意味着量刑的“时候”来了[12]。《刑法》第三百九十条是对于已经构成行贿罪的处罚规定,其第一款是行贿罪处罚的法定刑配置规定即基本规定,第二款的内容仍然是对于行贿罪处罚的规定,是在构成行贿罪基础上的量刑特殊规定。因此从体系上看,将其确立为刑法分则关于行贿罪的特殊处罚条款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必要与总则的量刑情节相对应。
其次,从条款内容来看,该款内容可以划分为成立要件与处罚要件,成立要件为“行贿人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根据《解释》的规定,“被追诉前”,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即对于自己的行贿行为如实供述,至于是主动投案还是经传唤、通知后被动到案没有限制。因此从成立条件来看,“追诉前”符合自首的时间点条件,“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符合坦白的实质内容条件。《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处罚条件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处罚条件设定的从轻力度远远大于自首、坦白的规定。因此从条款内容来看,该款的内容也是与其他量刑情节不同的特殊规定。
再次,从实证分析角度来看,结合前文的定量分析,《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也具有独立的地位。(1)在司法机关的案件判决中,有司法机关对于既具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情节又具有其他情节的案件都作为量刑的参考依据,这反映在此类案件的判决书上的明文记载,①参见(2014)靖刑初字第000461号,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江刑初字第111号,贵州市江口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干刑初字第4号,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这种情况大多集中于判决书在作出宣告刑之前对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情节、坦白、立功等情节逐一进行考察,从侧面反映了司法机关量刑时考量的不仅仅是是否具有这个特殊条款,还反映了对于这些情节进行区分的态度以及对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情节独立地位的赞同。(2)从广度以及深度两个层面的实证分析来看,在行贿罪的量刑过程中,《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影响都是其他情节难以相比的。在行贿罪案件中半数以上的案件都具有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的情形,在量刑中对于刑事责任承担形式是判处刑罚还是免于刑罚处罚,是否采取缓期执行方式,都体现出该条款在行贿罪实务处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适用的必要性。
三、评《刑九》对《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修改
(一)存废之争
学界对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不同态度,主要可以分为保留说、废除说、修改说。首先持保留说的学者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关于行贿罪处罚的规定是正当合理的,有利于对于经常表现为“一对一”形态的行贿受贿罪的查处,笔者赞同此观点。其次,持废除说的学者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立场,第一种认为:“从统一立法的角度而言,其存在有画蛇添足之嫌……完全可以按照《刑法》总则的规定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彻底取消。”[13]这是基于简化法律条文、避免重复的立场,认为对于行贿罪的处罚,在符合自首、立功、坦白等情形下适用总则的相关规定即可,没有必要在刑法分则中对于行贿罪的处罚作出这一特殊的规定;第二种认为特殊处罚的规定是形成“重受贿轻行贿”的重要原因,这一条款对于分化瓦解行贿受贿利益共同体的作用有限,反而可能鼓励行贿行为,所以主张应当取消行贿犯罪的特别自首制度,对其适用刑法总则中的一般性自首、立功规定[14];第三种是建立在取消行贿罪立场上的废除说,其未明确表示废除《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但是其既主张行贿非罪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种废除说,当然不仅仅是废除这一处罚条款,还包括整个行贿罪。①具体内容参见姜涛著《废除行贿之思考》,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再次,持修改说的学者,主张对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修改,但是根据修改的内容以及基本立场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主张从严修改,对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从宽幅度,可以比照刑法关于自首和立功的原则修正,即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殊情况下可以免除处罚[15];第二种情形主张从宽修改,有的主张“只能在立法层面规定:凡主动交代自己行贿犯罪事实的,应当免除处罚”[16],有的主张“宜将‘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改为‘(应当)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17]。
(二)各观点梳理
1.对于废除说,笔者认为其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对废除说中第一种主张“立法统一论”,笔者认为其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对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法律地位没有明确的认识,②关于《刑法》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法律地位分析参见本文第二部分。从而将其与总则中的自首、立功、坦白等制度划等号,故此不足取。其次,第二种主张否认《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于实务中处理行贿案件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没有具体的调查结果的支撑,只是阐述了一种猜测与可能性,也没有考虑到职务犯罪的特殊形态问题,“在我国司法实际中,贿赂案件中‘一对一’的问题长期以来在立法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绝大多数的司法人员在此问题上感到困惑……贿赂行为越来越隐蔽,相比之下,我们的追诉侦查者却对之束手无策”[18]。再次,第三种主张其立场在于行贿的非罪化,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太过激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建设都因此必然显示出一种渐进的模式”[19],主张非罪化将行贿与受贿的关系完全割裂开来,忽视了行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而也是片面的。
2.对于修改说,笔者认为其主张也不太恰当。张明楷教授指出:“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而是法学研究的对象……信仰法律,就不要随意批判法律,不要随意主张修改法律。”[20]主张从严修改的学者首先对于“执法困局”进行阐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对于行贿犯罪惩治不力,比如大量行贿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缓刑适用率过高。第二,行贿惩处刑事政策不明确。第三,面临着法律技术难题。其次将执法困局造成的不良后果归纳为引起群众不满,行贿人有增无减,甚至蔓延,破坏了社会正义。再次,分析“执法困局”的原因包括社会心理、政策、法律三个方面。最后,提出对策,在法律方面主张修改行贿罪的法定刑与特殊处罚条款[5]5-24。该学者的总体逻辑值得商榷,从执法的困局推导出立法存在问题,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不可否认我国现行执法存在着各种困局,但是是否为了满足执法的需要就得修改立法,这个值得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对于行贿行为过于轻纵的现象,特别是在对受贿罪取证较为困难的现实面前,过多地依赖行贿人,放弃对其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些现象的存在只表明我们在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上存在问题,并不能说明是行贿罪的刑法规定本身出了问题或者说立法设置的刑罚过低。恰恰相反,从我国现行行贿罪立法看,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已是相当严厉的刑罚了”[21]。主张从严修改的学者对于其部分观点的论证也没有太强说服力,仅仅以个别的案例来说明群众不满、行贿人再次行贿,行贿案件蔓延的趋势,有以偏概全之嫌。当然笔者并不否认“行贿罪的量刑实践存在着趋轻的取向,也并没有遏制住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实践中,行贿行为越来越隐蔽、行贿数额居高不下”[22],但是把受贿的果归于行贿这个因,把行贿这个果归咎于立法这个因,是否恰当,值得进一步探讨。笔者以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在行贿罪适用中的问题,③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可能是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与其将问题归结于立法,不如将工夫花在规制量刑适用上。对于从宽修改的主张,笔者认为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已经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足以达到从宽处罚的效果,在此不赘述。
(三)笔者的观点
《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五条中,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笔者认为此条款的修改的妥当性与必要性值得商榷。
首先,“立法因果关系论”是否正确?修改说中从严修改论者的立论之一就是“没有行贿就没有受贿”的“立法因果关系论”,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立法因果论在逻辑上存在重大的瑕疵,目前我国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实行双罚制,尚不能杜绝贿赂犯罪的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仅靠加大处罚行贿行为的力度难道就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再说立足于立法因果论而加大处罚行贿行为的力度所带来的众多副作用也无法消除”[23]。犯罪不是从来就有的,“犯罪是行为人的人类学因素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同时起作用的结果”[24],贿赂罪当然也不例外,将一个罪行归结于另一个罪行的“立法因果论”具有片面性,不能以此作为加重处罚行贿罪、从严修改行贿罪特殊处罚条款的依据。
其次,依靠加重处罚行贿罪完成反腐重任有无合理性?对于惩治腐败,我们往往采取重刑措施。现存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正如该学者最终总结到的“我国刑事法治犹如刚刚破土而出的一枝嫩芽,尚十分脆弱需精心呵护,经不起任何折腾。反腐败过程,既是清除国家有机体内‘毒瘤’、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也是检验和构建法治的实践过程,任何国家的法治都不可能在破坏中建立”[25]。因此,我国的反腐应当是严格执法(广义的执行法律包括司法)的过程,而不是动辄适用刑罚严惩,频繁地动用刑罚严惩违反了刑法应有的谦抑精神。
再次,《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尽管在适用中存在着问题,但属于量刑科学化与规范化要解决的问题,与刑法本身规定的科学性无关。《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由于其自身的规定性,奠定了其在行贿罪处罚中的特殊地位。通过本文定量分析以及对其法律地位的学理思考可以看出在刑罚适用中该条款的特殊影响力以及其与自首、坦白、立功等情节的区别。按照《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改,其自身独立性地位必然丧失,与其如此,何不废除,直接适用刑法总则的规定?
最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特殊规定与我国行贿罪法定刑密切相关。我国的行贿罪法定刑较高,根据日本刑法的规定,行贿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惩役或者二百五十万元以下罚金”[26],这一法定刑明显轻于中国刑法关于行贿罪法定刑的规定,同时在日本“白领犯罪的起诉率是百分之百,从科刑的情况来看八成被判处徒刑,但是与严格判决相反的是缓刑执行率高达90%”[27]。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原有的特殊处罚规定有利于对于我国行贿罪法定刑进行调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EB/OL].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5-08/31/content_ 1945587.htm.中国人大网,2015-9-1.
[2]赵秉志,于志刚.论我国刑法分则中的特别自首制度[J].人民检察,2000(3):18-22.
[3]陈吉双.论揭发“他人犯罪”[J].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42-45.
[4]于志刚.刑罚制度适用中疑难问题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48.
[5]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J].中国法学,2015(1):5-24.
[6]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52.
[7]莫洪宪.论自首和立功[J].法学评论,1996(2):8-16.
[8]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8.
[9][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第四版补正版)[M].钱叶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9.
[10]王瑞君.体系性思考与量刑规范化[J].政法论丛,2014 (6):73-79.
[11]姜涛,吴文伟.量刑法定化: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应有拓展[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3):89-100.
[12]莫洪宪,叶小琴.量刑根据论[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2):5-10.
[13]曹子刚.行贿罪定罪与处罚若干问题之思考[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3.
[14]刘仁文,黄云波.行贿犯罪的规制与完善[J].政法论丛,2014(5):70-79.
[15]徐胜平.行贿惩治如何走出困境[J].人民检察,2012 (16):51-53.
[16]陈金林.通过部分放手的贿赂犯罪防控[EB/OL].“法律读品”(微信公众号),2015-1-16.
[17]吴大华,王飞.论我国行贿犯罪立法的缺陷与完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93-99.
[18]莫洪宪,王明星.论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其形式对策[J].犯罪研究,2003(2):13-24.
[19]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7.
[20]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
[21]卢勤忠.行贿与受贿能否同罚[J].人民检察,2008,(14):55-56.
[22]董桂文.行贿罪量刑规制的实证分析[J].法学,2013,(1):152-160.
[23]姜涛.废除行贿罪之思考[J].法商研究,2015(3): 63-71.
[24][意]菲利.犯罪社会学[M].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45.
[25]何荣功.重刑反腐与刑法理性[J].法学,2014(12):98-107.
[26]张明楷.日本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74.
[27][日]森田溢之,濑川晃,上田宽,三宅孝之.刑事政策学[M].戴波,江溯,丁婕,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53.
(责任编辑:付传军)
On the Legal Status of Article 390,Paragraph 2 of Criminal Law——A Review of“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9)”
YE Xiao-qin,LV Da-ling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China)
The Article 390,paragraph 2 of Criminal law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bribery sentencing,which is special punishment regulation with an independent legal status.Under the thought of severe punishment for corruption,Criminal Law 1997 is believed to get in the way of punishing corruption.In Criminal Law Amendment(9),penalties for briber have been strengthened in spite of some problems in application,however,this change has not only confused its due legal status but also shifted the sentencing standardization problem to the level of legislation.
article 390 paragraph 2 of Criminal Law;bribery;sentencing;Criminal Law Amendment(9)
D924.3
:A
:1008-2433(2016)02-0068-10
2016-01-20
叶小琴(1978—),女,湖北鄂州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吕大亮(1994—),男,安徽六安人,武汉大学法学院2014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以106份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