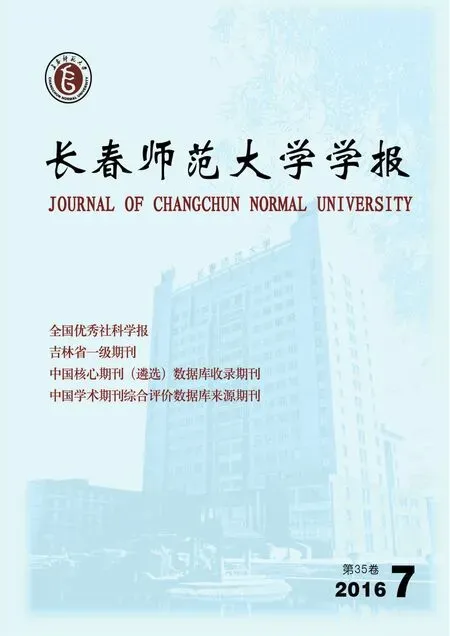“文学性”之广义修辞学阐释
郑晓岚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文学性”之广义修辞学阐释
郑晓岚1,2
(1.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文学性”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修辞问题,与修辞学紧密相关。广义修辞学是表达者与接受者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即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以广义修辞学对“文学性”的内涵进行观照,可以发现: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文学性”,既关注文本内部的语言特征,又兼顾文本整体结构和社会历史语境,同时将表达者和接受者综合考虑在内,是一种更为全面的阐释视域,从而说明中国本土理论可以为阐释西方理论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文学性”;修辞技巧;修辞哲学;修辞诗学;接受者
“文学性”一词最早由罗曼·雅各布森于1921年在《现代俄国诗歌》一书中提出。雅各布森强调,“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1]换句话说,“文学性”是文学作品的一种本质规定。以“文学性”为主题词,搜索万方数据库,共有四千多项研究记录,说明“文学性”仍然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议题。分析搜索结果,发现国内学界对“文学性”的探讨大致可分成二大类:一是理论研究,探索“文学性”的概念或本质;二是文本研究,将“文学性”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用于探讨新闻、广告、电影、音乐、舞蹈创作、手机短信等各种文本。这些探讨或是进行一种文艺思潮式的抽象论述,或是研究各种文本的“文学性”,阐释路径缺少较新创见,也较少从中国本土理论或中国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探索。
“文学性”问题关系到整个文学的观念革新。“尽管这一问题似乎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当承认,关于“文学性”,我们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定义。”[2]究竟何谓“文学性”?是形式主义强调的文本语言特征?还是结构主义观照的文本结构?抑或是接受美学关注的读者与文本的互动?韦勒克、沃伦说过:“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3]换句话说,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保罗·德曼认为所谓的‘文学性’不是文学的审美属性,而是语言的修辞功能,而修辞性正是语言的本质所在。”[4]由此可见,“文学性”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修辞问题,与修辞学紧密相关,可以通过广义修辞学加以阐释。
“广义修辞学是一个双向互动、立体建构的多层级框架,是两个主体(表达者/接受者)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5]2这三个层面是:修辞技巧,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修辞诗学,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哲学,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广义修辞学以一种兼容并蓄的广博视域包容了“文学性”的不同内涵:从修辞技巧关注文本语言特征,到修辞诗学关注文本的整体结构,到修辞哲学强调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密切联系,再到“双向互动”关注接受者在文本意义建构中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拟从广义修辞学的三个层面、两个主体探讨“文学性”内涵,揭示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文学性”,是文本内部的语言特征和文本整体结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内部,也产生于接受语境和接受者的解读,是一种比较全面的阐释视域,以期证明:广义修辞学具有强大的阐释力,中国本土理论可以为阐释西方学界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另辟新径。
一、修辞技巧与“文学性”
形式主义从诗歌的语言变异特征入手,区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关注具有审美效果的语言结构和形式技巧,强调“文学性”主要存在于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是独立于社会语境的文本内部属性。修辞技巧作为作为话语建构方式,同样关注文本话语特征,关注话语建构的自觉和不自觉、话语建构的陌生化和熟知化以及话语建构的合理和不合理等方面。[5]21-31修辞技巧观照下的“文学性”,包含了形式主义者关于“文学性”的思考,即“文学性”在于文本语言特征,尤其在于陌生化的语言特征。然而,语言是一种历史的语言,是一种活的语言,随着时代历史的变迁,从内容到形式发生巨大变化,很多原来不属于文学语言的语言也纷纷进入文学文本,出现了大量网络小说、弹幕小说、超文本小说等,从而改变了“文学性”的内涵。比如,2014年冯唐翻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运用了大量网络语言和粗俗语言,引发了广泛争议。这场争议的背后,是“文学性”之争。网络语言是文学语言吗?文学语言一定要词藻优美吗?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同样,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语言也已经融入到广告、影视、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中,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日益模糊。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大卫·辛普森认为,文学不再具有统治地位,修辞也不再为文学所专属,修辞成为各个学科的语言形式。“日常话语与诗话使用同样的手法、同样的隐喻游戏、同样的规则。”[6]“文学性”无处不在,不论是消费社会的商品广告,还是信息社会的大众传媒,都充满了隐喻性的语言或修辞手段,仅凭文本语言特征界定“文学性”的内涵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还需要考虑文本语言特征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文本结构。
二、修辞诗学与“文学性”
结构主义认为,文学活动体现为一种符号关系,“文学性”主要存在于文本结构中。修辞诗学也关注文本建构方式,蕴含了结构主义原理。修辞诗学观照下的“文学性”,强调透过文本语言形式考察文本功能,同时关注文本类型。就“文学性”而言,文本语言特征常常与文本功能发生修辞错位,因此仅仅凭借文本语言特征无法准确地界定“文学性”的内涵。比如,《僮约》以契约形式履行俳谐文功能,《马桥词典》以词典形式实现小说叙述功能,《提升报告》以公文文体实现小说叙述功能。[7]“形式-功能”修辞化错位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尤其普遍,比如晚清翻译小说,常常以小说形式实现救亡启蒙的政治功能。进入消费时代,大量以诗歌形式出现的商品广告,充满了隐喻性的语言,其文本语言形式是“文学性”的,其文本功能却不在于审美,而在于商品信息的传达,诱导言后消费行为。这种修辞化错位普遍存在于各种文本之中,产生的陌生化效果正是吸引读者的文学价值所在,成为观察“文学性”的一个切入点。同样,在不同的文本类型框架内阐释“文学性”,可能得到不同的阐释结果。“例如分析《史记》的话语,在历史叙述的类型框架或在文学叙述的类型框架中进行,会产生不同的文体压力。”[7]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模糊不清,文类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文类的糅杂反过来又使“文学性”变得更加幻化、虚化。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文学性”研究,以文类为切入点,透过种类繁多的文本,以一种文类或几种文类作为基础研究对象,可以比较快捷地接近研究目标,揭示文本属性。陈军对此曾进行专文论述,强调文类是“文学性”的研究对象、切入点及基本检验标准。[8]文类与“文学性”关系密切,没有明确的文类意识,“文学性”的研究是不切实际的。综合上述,修辞诗学层面关注下的“文学性”,在于包括文本功能、文本类型在内的整体结构。
三、修辞哲学与“文学性”
关于“文学性”阐释,不论是形式主义,还是结构主义,都隔断了文学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因而遭到学界的质疑与批判。巴赫金认为,形式主义提出的“文学性”概念,是消极的虚无主义,提倡将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语境联系起来。[9]修辞哲学层面强调修辞参与主体的精神建构,与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修辞使现实世界在言说中成为审美化的世界,使之更深入地植入人的意识,成为主体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并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人存在的标志。”[5]47换句话说,修辞已经成为人的一种普遍化存在方式。修辞哲学视野下的“文学性”也成为一种本体性存在。“文学性”“不仅是文本边界中的修辞游戏,还是弥散在大地上的某种历史性的意义。”[10]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向非文学领域扩张,“文学性”内涵蔓延,“文学性”自身的边界也日益消失。伊格尔顿甚至认为不存在“文学性”。[11]有些西方学者甚至将文本扩大为泛文本概念,主张用文本定义代替“文学性”的定义,以此回避纠缠不清的“文学性”问题。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消解了“文学性”,使“文学性”面貌变得模糊不清。的确,“‘文学性’有多种,不仅有虚构、假想、象征、叙事等语言修辞手法,更有文学之为文学的本体性存在。在后现代传媒时代,‘文学性’已经逃逸到文化中,仅仅成为大众文化的形象符码。”[12]换句话说,“文学性”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一种本体性存在。修辞哲学以文化诗学、文学人类学等广博的视域,重新审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思想、文学与文化等关系,对“文学性”的阐释蕴含了哲学层面的思考。
四、接受者与“文学性”
接受美学重视读者的审美经验和接受反应,把“文学性”视为一种读者参与其中的文学活动,强调“文学性”不是文本内在的语言特征,而是读者阐释文本的一种方式,其内涵取决于读者与作者、文本的互动,读者在“文学性”的内涵界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广义修辞学同样强调接受者与表达者之间的互动,认为“修辞活动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共同建构审美现的言语活动。”[5]66对于接受者的强调,契合于接受美学的主张。互动论观照下的“文学性”内涵,与接受者关系重大。的确,不同接受者阐释同一个接受对象,其结果可能大相径庭。鲁迅说过:对于《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留言家看见官闱秘事。”[13]对于“文学性”的阐释也是如此:形式主义者视域下的“文学性”是文本语言特征;结构主义者观照下的“文学性”是文本整体结构;解构主义者视角下的“文学性”不是文本的内在属性,而是“泛文学性”,是侵入其他非文学领域的“文学性”。同样,对于同一个接受对象,不同时期的接受者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五四时期的“文学性”等同于审美性;文革时期的“文学性”相当于意识形态性;80年代的“文学性”指文学的自足性;90年代的“文学性”则被赋于不同的内涵,或指文本的审美属性,或指遍布于各个学科的“泛文学性”。由此可见,“文学性”的内涵阐释,与接受者密切相关。只有将接受者纳入观察范围,才能对“文学性”进行比较全面的阐释。
五、结语
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文学性”,既关注文本内部的语言特征,又观照文本整体结构和社会历史语境,同时将一起参与“文学性”生产的接受者综合考虑在内,是一种更为全面的阐释视域。当然,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文学性”绝不是一种自足的存在。“文学性”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范畴。“伊格尔顿甚至认为,说不定哪一天莎士比亚将被逐出文学之列,而一张便条或者街头的涂鸦又可能获得文学的资格。”[14]在“文学性”与“非文学性”日益模糊的后现代社会里,要给二者划一条清晰的界限是不现实的,要给“文学性”下一个公认的定义也绝非易事。“文学性”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形式美学问题,也是“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神学和文化学问题,或者说它是后现代社会中最为基本和普遍的问题之一。”[15]“文学性”研究本身变得比以往更加跨学科,因此文学研究者必须拥有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以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文学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内涵,以一种广博的胸襟研究“文学性”问题。在这方面,广义修辞学反对非此即彼的研究方法,主张融合语言学、文学、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学术资源,倡导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域,兼顾文本语言特征、文本整体结构和社会文化语境等文本内外因素。这种较为全面的阐释视域,不仅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地把握“文学性”的内涵本质,也必将给中国学术界带来重要启示:对于包括“文学性”在内的各种学术研究,我们不能一味地“操持西方强势话语的概念范畴,用汉语语例验证外国学者的理论和预设导向,为西方话语霸权增加一份国产证明”[16]64;我们应该保持自己鲜明的学术形象,“在接受西方学术资源的同时,输入民族化的学术资源,以平等的文化身份进入国际讲坛”[16]62,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传播中国学术界的好声音。
[参考文献]
[1]PAUL, CARVIN.A Prague School Reader on Aesthetics, Literary Structure and Style[M].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64:104.
[2]CULLER, JONATHAN. The Literary of Theory[C]//What’s Left of Theory. Judith Butler,John Guillory & Kendall Thoma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2000:33.
[3]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16.
[4]李龙.解构与“文学性”蔓延问题—兼论保罗·德曼的“文学性”理论[J].当代外国文学,2008(1):26-30.
[5]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修订版)[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自序.
[6]谭学纯.一个微型语篇的形式、功能及话语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1(6):92-99.
[7]马克·昂热诺. 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M].史忠义、田庆生.天津:白花文艺出版社,2000:46.
[8]陈军.“文学性内涵新论”—文类意识对“文学性”内涵意识的揭示[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1):140-146.
[9]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80.
[10]乔纳森·卡勒.文学性[C]//马克·昂热诺.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天津:白花文艺出版社,2000:33.
[11]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2.
[12]王岳川.后现代“文学性”消解的当代症候[J].湖南社会科学,2003(6):129- 134.
[13]鲁迅全集:第8卷[C].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45.
[14]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J].文艺研究,2007(8):4-13.
[15]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J].文艺研究,2002(6):15-24.
[16]谭学纯.全球视野:中国修辞学研究学术观察与思考[C]//广义修辞学演讲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收稿日期]2016-01-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哈葛德小说在晚清:话语意义和西方认知”(2013BWW010);福州大学科技发展基金项目“英国冒险小说在中国的接受”(601312)。
[作者简介]郑晓岚(1978- ),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话语修辞、文学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IO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7-0096-04
Literar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Rhetoric in the Broad Sense
ZHENG Xiao-lan1,2
(1.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China;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Abstract:Literariness is actually a rhetorical issue and thus closely related to rhetoric. The Theory of Rhetoric in the Broad Sense advocates a three-tier exploration of rhetorical activiti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rhetorical devices, rhetorical poetics and rhetorical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 rhetor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ddresser and the addressee. An analysis of literar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Rhetoric in the Broad Sense lies not only in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within the text but also in the overall textual structure and the social historical context, as well as in the addresser and the addressee. This approach i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thus proves the fact that Chinese theories boast a reference for the solution to western theoretical problems.
Key words:literariness; rhetorical devices; rhetorical poetics; rhetorical philosophy; the addres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