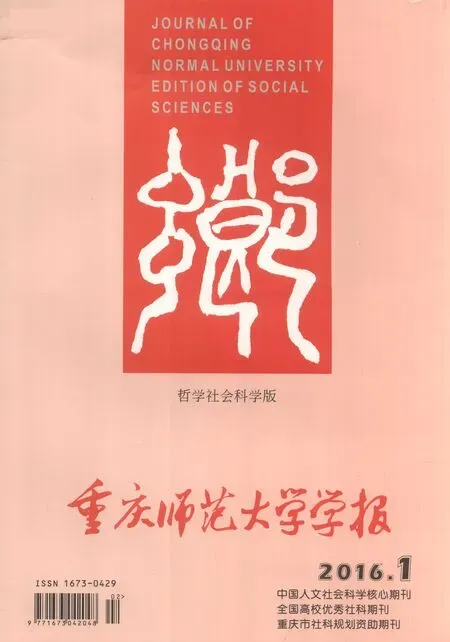故事能支撑到第七天吗?
——余华《第七天》结构上的纰漏
刘 琴 赵 黎 明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故事能支撑到第七天吗?
——余华《第七天》结构上的纰漏
刘 琴 赵 黎 明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第七天》结构上存在一些纰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七个板块之间内容不“平等”,显现了拼凑的痕迹;2.“堆砌”、“拼贴”新闻故事,导致章节之间的凌乱;3.部分内容刻意强调,导致一些句子或段落的重复、啰嗦。可以说,小说从句段到章节再到板块,都存在独立性或关联性欠缺的问题。这些结构纰漏不仅影响了作品思想表达的深度,也影响了作品艺术成熟的程度。
《第七天》;结构;纰漏;故事
《第七天》是著名作家余华的长篇新作,小说发表后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人们从内容到形式对其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是是非非,褒贬不一,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小说“结构”本身及其蕴含,更少有人批评其模仿结构的严重问题了。事实很明显,《第七天》是一篇模仿《圣经》结构,打上基督教鲜明烙印的作品。小说开篇即以《旧约·创世纪》中的一段话作为前言:“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1]更进一步考察你会发现,不论是小说题录,还是小说主旨,都不乏模仿《圣经》的痕迹,如小说中所运用的“七天”的结构方式、小说中所传达的平等观念,即是出自《圣经》。但这样说,并没有否定《第七天》的“中国特色”。实际上,小说的内容是纯粹中国化的,小说的形式也有作者独特的创造。问题是,不管是在结构形式,还是内在精神,作者的借鉴都做得不够圆融,不够天衣无缝。更具体地讲,是结构与内容发生了脱离,导致形式不能很好地为内容服务。
一
加拿大学者戈登·菲等在《圣经导读》下卷中,曾这样分析上帝造物的来历,并指出这“七天”在结构上的无可替代:“其中第一天与第四天相对应,第二天与第五天相对应,第三天和第六天相对应。注意这两组日子如何与地的‘空虚混沌’相对应:第一天至第三天地有了‘形’(光,天,旱地),而在第四天至第六天,有形的地有了内容。”[2]14第七天不同于前六天,到了第七天,“神歇了他创造的工”。可以发现这七天是平行并列的结构,其中不乏巧妙的对应。
《第七天》也用“七天”来构造全文,每一天看似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板块,实际上这些板块之间并不是“平等”的。笔者以为,第二、三、四、六、七天是主要的板块。因为不管是从篇幅还是从内容上来看,“温情”仍然是这篇小说的“主旋律”,而不是如张清华老师所说:“爱在这个小说里是不得以的一个因素,如果再没有爱,这个小说从精神上也好,从艺术上也好,就没法平衡了。”[3]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情感故事不仅仅只是黑暗现实的一个平衡因素,而是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小说的主体。陈晓明老师也认为:“这部作品可贵的地方是看到他写到的爱。”[3]特别是第二天和第三天,分别单独讲述了“我”和李青的爱情故事、“我”和杨金彪及李月珍的亲情故事。而第四、六、七天则重点讲述了刘梅和伍超的爱情故事。四个板块写爱情,一个板块写亲情,可见这两种情感在作者心中的分量。
第一天、第五天与这几个板块明显不同,第一天是多个新闻故事的串联,第五天则是对第一天的呼应。这样看来,第一天和第五天似乎成了陪衬。关于这一点,余华曾在一次研讨会上间接谈到:“真正涉及到现实事件的笔墨,我感觉在里面不会超过七分之一。”[3]他还提到:“我是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其实我的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3]问题在于,作者并没有真正着力营造“死亡的世界”,而是如梁振华老师所说:“那个阴间并不存在,那个阴间是余华老师比照现实所创作出来的另外的现实。”[3]也就是说,作者真正想表现的仍然是现实世界,是当代的大众生态,只是刻画这个“大众生态”所用的笔墨偏少、力度欠缺,结果成了情感故事的社会背景。另外,分三个板块来讲述刘梅和伍超的爱情故事,稍显拖沓,与其他板块不太协调。总之,这七个板块之间并不是“平等”的,有刻意模仿“创世纪”模式之嫌。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小说不同板块间的“平等”是必要的:“小说对位法(可以将哲学、叙述和梦幻统一)的必要条件是:一,各条‘线索’的平等性,二,整体的不可分性。”[4]95因此,他认为布洛赫的《梦游者》第三部分的缺陷不在于五条不同种类的线索(小说、短篇小说、报道、诗歌、随笔)衔接得不好,而是由于这五个声部的“不平等”。[4]94-95同理,小说《第七天》的缺陷不在于情感故事与新闻报道不能衔接,而是衔接得不够紧密。小说的七个板块之间是“不平等”的,它们之间并非紧密相关、缺一不可。换句话说,板块之间的独立性和关联性都有所欠缺。
首先,板块的独立性不够。如果说小说前三个板块的界线还比较明晰,后四个板块的界线则相对模糊,几乎是黏粘在一起的。其实,后四个板块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刘梅和伍超的恋爱史,二是各种新闻人物在“死无葬身之地”的新生活。其中,刘梅和伍超的爱情故事占据了三个板块,采用了五种视角,即邻居“我”与新闻报道的视角、朋友肖庆的视角、当事人刘梅和伍超的视角。对于这对情侣,作者采取了多角度透视的方式,深入挖掘两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因素,是有较强的艺术性的。然而,用三个板块写一个方面的内容,依然有人为拉长和切割之嫌。至于第六天中刘梅“净身”、第七天中父子见面这两个重要的情节,作者并没有详细展开。也就是说,后四个板块的内容是有些“单薄”的,板块之间的独立性是较弱的。
其次,板块的关联性不够。第二天明显缺乏内在的呼应。妻子李青的故事随着第二天的结束也就结束了,她有墓地、有盛大的葬礼,不用去“死无葬身之地”,她与“我”有过交集、最终分道扬镳,“我”继续游荡的视野里再也没有她。而且,这篇小说主要是想写尽社会底层者的无辜与无奈,李青又算哪个阶层呢?如果算上层者,作者对她的情感态度又是格外不同的,可以说又爱又恨,有别于其他众多面目模糊、令人憎恶的上层者。这样看来,第二个板块显得过于独立了。而且,第一、第五个板块与其他板块的关联性并不强,社会新闻故事与个人情感故事的“结点”太少。除了刘梅和伍超的爱情故事本身作为一则社会热点新闻之外,其他主要人物的情感故事只是“徘徊”于社会新闻的边缘,于故事的结尾才引出一二则新闻。而次要人物的新闻故事则普遍缺乏个人情感因素:另外的新闻故事与主要人物的联系就更弱了,主人公“我”偶然碰到这些事件,“我”作为旁观者,简单陈述社会人员基于不同立场而产生的针锋相对的观点,如政府如何声称,网上又如何流传。由此可见,文本中,新闻故事更重视因果、观点,而情感故事则更重视经过、情感。新闻故事和情感故事的讲述方式是有明显差异的,第一、第五个板块与其他板块的联系是较弱的。
总之,小说七个板块之间,既缺乏独立性,又没有足够的关联性,二者的缺少造成了小说生硬拼凑的浓重痕迹。
二
至今为止,已经有不少评论家批评《第七天》“令情节叙述变成了多个新闻事件的连缀”[5]。关于这一点,作者是有其原定设想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想,把这么多年在中国发生的,受人关注的公众事件集中在一部书里面完成。这是我有意为之的。”[6]把大量的类似性质的事件“集中”起来的这种写法,令笔者想起余华对于“主题重复”这一小说叙事手法的偏爱。
主题重复是指性质类似的事件在小说中重复发生,与损耗性的叙述重复不同,主题重复的过程却是意义增殖的过程。[7]从早期的《现实一种》、《往事如烟》等到后来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余华都运用了这一手法。《现实一种》中,接连不断的家庭内部凶杀案的发生,喻示了人类潜在的冷酷与残暴。《第七天》中,多个新闻事件的串联、底层民众接二连三的死亡,是否也达到了类似的效果,是否深刻地展示了上层者的自私与残忍?
文本中,大量地写新闻事件主要集中于第一天。第一天,亡灵杨飞在人间游荡的所见所闻基本上都是这种新闻事件,包括暴力拆迁、墓地昂贵、贫富悬殊、市长腐败、公务员吃霸王餐等。写到市长腐败这个话题时,作者一下连带出三个新闻事件,即贪色而死、葬礼隆重、先“烧”特权,这些新闻事件都如“蜻蜓点水”、一闪而过。例如,写到市长因贪色而死这个新闻事件时,作者只用了一个段落,这一个段落没有多少具体的感性的内容,只是凸显了民间与官方的“交锋”:“官方的解释是市长因为工作操劳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网上流传的是民间的版本,市长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行政套房的床上,与一个嫩模共进高潮时突然心肌梗塞,嫩模吓得跑到走廊上又哭又叫,忘记自己当时是光屁股。”(第13页)这种只阐明因果、观点的写法,会让故事理性化、简单化,进而让故事的独立性相对缺乏。作者把这些独立性较弱的新闻故事集中处理,就有了“堆砌”之嫌。
除了“堆砌”,作者还试图在别的板块穿插和拼贴新闻事件。例如,第三天,由父亲的不辞而别引出“商场火灾”这则新闻,作者用了差不多一页的篇幅,重点依然是比较官方和民间的不同话语。在主人公“我”忐忑不安、十分担心父亲安危的同时,仍然不忘抨击政府。这与这一板块的整体基调不太相符,不同于这一板块中出现的“厕所产子”的新闻故事。“厕所产子”这则新闻的加入,不仅不妨碍故事的可读性,反而在养父与亲身父母的对比中,显现养父对“我”深沉的爱,读来令人动容。这样的新闻故事是相对成功的,与类似于“商场火灾”的新闻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小说中大部分新闻故事都类似于“商场火灾”这则新闻的写法,技巧上是有欠火候的,导致小说内部变成了理性言说与感性延展的分裂的两个部分,变成了新闻报道与情感故事的杂糅。如果把一个新闻故事看作一个章节,那么这些章节间的独立性和关联性都是较弱的,是相对凌乱的。
因此,作者与其这样“堆砌”、“拼贴”新闻故事,不如适当铺展开,深入挖掘一些典型的新闻故事。小说中最成功的新闻故事要数那对穷困的情侣。虽然作者花费三天的篇幅来写一个故事有欠妥当,但也正好表明作者有意在挖掘和扩展这个故事。文本中,第四天先提到了一个热门新闻——“一个名叫刘梅的年轻女子因为男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山寨iphone4S,而不是真正的iphone4S,伤心欲绝跳楼自杀。”(第116页)接着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述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告诉读者故事中的人物并不完全像网络和报纸上所议论的那样,其实刘梅是个很重情的女子。第六天和第七天又分别从肖庆、刘梅、伍超这三种视角来讲述了两人之间的真挚爱情。作者为读者展现了新闻背后的某种可能,这个故事就变得富有文学意味了。
当然,除了像大多数作家所做的那样,适当扩充篇幅、深入挖掘新闻故事,还可以给短篇幅的新闻故事适当增加一些调料。例如,文本中两个下棋的骨骼之间的故事给笔者留下了一定的印象,主要是他们在“死无葬身之地”的相处模式显得有些荒诞而独特,很自然地融入那样一个场景、那样一种氛围。两人从现实中的仇人变成现在形影不离的棋友,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友情?’他们两个发出嘻嘻笑声。一个问另一个:‘友情是什么东西?’另一个回答:‘不知道。’”(第141页)这样的对话,既调侃了现实世界,又显示了现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很符合两个骨骼的身份。不同于“我”与火灾中被政府删除的死者之间的对话。“我说:‘你们的亲人为什么也要隐瞒?’‘他们受到威胁,也拿到封口费。’老者说:‘我们已经死了,只要活着的亲人们能够过上平安的生活,我们就满足了。’”(第146页)类似的这种对话太过于现实、过于平常了,没有在虚构的层面上处理现实问题,很难让读者感受到待在“死无葬身之地”的骨骼与世俗的人有多大的差异。因此,在这样一种文本语境下,“要是使用不确定的叙述语言来表达这样的情感状态,显然要比大众化的确定语言来得客观真实。”[8]这可以算是余华创作上的一个倒退,曾经的先锋作家变得不太会或者说不太敢使用“虚伪的形式”了,“世俗化的生活打败了一切的先锋”[9]。因此,笔者以为,那两个骨骼之间的故事是相对成功的。
或许,把短篇幅的新闻故事删减一部分、变更一部分、扩充一部分,让章节间的独立性和关联性更强,小说的整体结构就不会显得那样凌乱了。
三
人长多了赘肉会影响身材,小说中重复、啰嗦的话语也会影响小说的结构,影响小说带给读者的整体感觉。伟大的作家都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传达出无限的意义,寻求“一句顶一万句”的效果。作者余华也不例外,他的不少作品都显示了对于简约叙事的迷恋,如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再到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依然想运用这种叙事方式,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全文分七个板块,总共才13万字,细细读来,部分文字却给我们重复、啰嗦之感。
最明显的一处要算对于“死无葬身之地”场景的描写,文本中间和结尾都写到了。第四天,“我”跟随鼠妹来到这个地方,从“我”的视角出发,有几段细致的描写:“我惊讶地看见了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我看见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我问她:‘这是什么地方?’她说:‘这里叫死无葬身之地。’”“感到树叶仿佛在向我招手,石头仿佛在向我微笑,河水仿佛在向我问候。”(第126-127页)到了全文的结尾处,又出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他看到了我曾经在这里见到的情景——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他问:‘那是什么地方?’我说:‘死无葬身之地。’”(第225页)可见,两处的话语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变换了一下视角,由“我”的视角变为伍超的视角。
或许有人会说,作者只是用到了“细节重复”,不一定是败笔。而且,许多小说使用“细节重复”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鲁迅的小说《祝福》、《孔乙己》,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在《祝福》和《孔乙己》中,细节处理是采用了‘重复中的细小变化”的手法,它导致了小说“对时间的戏剧性跳跃”——时间迅速地消耗,而人物的命运与逻辑则迅速显现”[10]。同样,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不管是许三观一次次卖血时的“例行程序”,还是他一次次用嘴给三个儿子做红烧肉,或是许玉兰在助产台上的一次次叫骂,都暗含一定的戏剧性和节奏感,情感在跃动,节奏在加快,人物的命运在不断的重复中昭然若揭。《第七天》中部分细节的重复也恰到好处,例如“我”终于在殡仪馆找到父亲,父亲唯一的反应是,“哀伤地说:‘你这么快就来了。’”(第214页)这句话重复了四次,却很好地表现了父亲“沉溺在久远的悲伤里”(第215页),同祥林嫂对人一次次诉说阿毛之死的絮叨,如出一辙。作者是懂得这种“细节重复”的意义的。然而,对于“死无葬身之地”场景描写的重复则缺乏相应的意义。两处重复几乎不存在任何变化,时间不再是一种戏剧性跳跃的元素。第四天和第七天,两个不同的底层者——杨飞和伍超的感受完全相同,两人的性格和命运也基本一致。这种重复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只会让读者感觉作者有些“词穷”了。或许,前一处可以简写,后一处铺陈之后的戛然而止才会带给人更大的震撼感。
除了“细节重复”,文中还存在一些新闻故事前后的议论话语的单调重复,也许这才是不少评论家指责这部小说是“新闻串烧”的根源。如有关二十七个死婴的新闻故事,第三天和第五天的相关议论话语存在重复的问题。第三天,“市政府为了平息网上传言,让外地赶来的记者前往殡仪馆观看摆成一排的二十七个小小的骨灰盒,表示这二十七个死婴已经火化,接下去将会妥善安葬。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有人报料,说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的骨灰是从当天烧掉的别人的骨灰里分配出来的。”(第108页)到第五天,即“我”到达“死无葬身之地”之后,见到李月珍,“我想起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的神秘失踪,殡仪馆声称已经将她和二十七个死婴火化了,网上有人说她和二十七个死婴的骨灰是从别人的骨灰盒里分配出来的。‘我知道这些,’她说,‘后面过来的人告诉我的。’”(第167页)作者像个新闻播报员,似乎唯恐观众不信,要借主人公之口反复述说。杨飞作为一个到了阴阳交界处的亡灵,不应该像围观的民众一样絮絮叨叨,他似乎有更重要的使命。而且,作者在二十多年前就谈论过:“当我们就事论事地描述某一事件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件的外貌,而对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这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窒息了作者应有的才华。”[8]可以说,小说中新闻故事前后议论话语的重复是完全理智的、就事论事的,作者试图加强故事的意义,结果却是背道而驰。作者因为太注目于这些新闻故事背后的对抗,以致在部分细节处理上有些发挥失常。
总之,不管是细节描写中的“重复”,还是议论话语中的“重复”,都应该为小说整体服务,不能为“重复”而“重复”。《第七天》中的一些句子或段落的重复,不仅没能增进小说的意义,反而显得有些啰嗦,使句子或段落之间的独立性不够,破坏了小说整体的艺术氛围。
四
张清华曾经这样夸赞余华的写作功底:“形式在余华的小说中是起着如此神奇和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形式不是简单的‘外部结构’,而是与小说的寓意、主题、戏剧性与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0]《第七天》似乎成了一个意外。表面上看,《第七天》的结构是比较完整清晰的,作者把生前和死后的故事压缩为七个时间段,过去和现在两条线索交织、贯穿始终。然而,细心梳理一下全文,可以发现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并不和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七个板块之间内容不“平等”,显现了拼凑的痕迹;二、“堆砌”、“拼贴”新闻故事,导致章节之间的凌乱;三、部分内容刻意强调,导致一些句子或段落的重复、啰嗦。也就是说,小说从句段到章节再到板块,都存在独立性或关联性欠缺的问题,小说结构上存在一定的纰漏,令读者扼腕。
笔者试图思索原因何在。对于这部小说,余华曾经表明自己的初衷:“结果别人质疑,觉得公共事件是不是多了一点?其实我就是要这么写,否则小说的时代意义就没有了。因为文学具有社会文献的功能。”[6]余华渴望深入世俗的现实社会,不惜冒近距离书写的风险。可以说,《第七天》是余华的又一个探索性文本,存在一定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找到原因的。郜元宝认为:“先锋作家切入当下现实时有一种先天的虚症。”[11]陈晓明也曾经分析:“中国作家要么非常强硬地直接把现实塞到作品里去,要么无法在虚构的层面上处理现实,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学很致命的地方。”[12]《第七天》文本中暴露的缺陷,反映出作家在书写现实时的焦虑和不成熟。
余华认为这些年的现实世界是很荒诞的,有许多值得小说家发挥的地方,他在小说腰封上直言不讳:“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为了表现现实的荒诞,余华苦心构思多年。开始发现事件很多很杂,没有好的切入点,“后来找到了‘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视角,我很兴奋,告诉自己‘现在可以开始写了’”[6]。结果连带出了亡灵叙述者和《圣经》。余华曾说:“我愿意成为《圣经》的作者。但是给我一万年的时间,我也写不出来。”[13]可见,《圣经》在作者心中的分量。作者本以为借用《圣经》可以提升思想的深度、增强结构的暗示性,结果却是停留在表面,令读者遗憾。因此,社会现实加宗教的模式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适得其反,令小说的内容变味,令小说离讲好故事越来越远。故事讲不好,外在结构就容易发生偏离,出现一些纰漏。
[1] 余华.第七天·前言[A].第七天[Μ].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作品的其他引文只在文中标所在的页码)
[2] [加]戈登·菲,[美]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圣经导读(下卷) [Μ].李瑞萍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张清华,张新颖等.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J].当代作家评论,2013,(6).
[4]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Μ].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社,2004.
[5] 白草.死在模仿下——读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J].扬子江评论,2013,(5).
[6] 范宁.余华:写作像旅行,看得越多越好[J].长江文艺,2014,(7).
[7] 余弦.重复的诗学——评《许三观卖血记》[J].当代作家评论,1996,(4).
[8] 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5).
[9] 何家欢,孟繁华.论余华的小说创作[J].小说评论,2014,(4).
[10] 张清华.《兄弟》及余华小说中的叙事诗学问题[J].文艺争鸣,2010,(12).
[11] 郜元宝.当代小说发展的六个阶段[J].小说评论,2015,(2).
[12] 路艳霞.余华《第七天》被揭“致命伤”[N].北京日报,2013-06-26.
[13] 余华,杨绍斌.“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9,(1).
[责任编辑:朱丕智]
Could The Story Support Up To The Seventh Day?——Structural Flaws of the NoveltheSeventhDayWritten by Yu Hua
Liu Qin Zhao Liming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There are some flaw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 the seventh day,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between the seven plates, the content is not “equal”, revealing a patchwork of signs; secondly, “stuffing” and “collage” news stories, resulting in messy among chapters; thirdly, part of the contents deliberately stressed, resulting in a few sentences or paragraphs repeated, long-winded. We can say that from the sentence or paragraph to the chapter and then to the plate, the novel lack of independence or relevance. These structural flaws not only affect the depth of ideological expression of the works, also affect the degree of artistic maturity of the works.
theSeventhDay; structure; flaws; story
2015-10-08
刘琴,女,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赵黎明,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茅奖’小说的‘新历史’叙事研究”(CYS14134)的阶段性成果。
I206.7
A
1673—0429(2016)01—00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