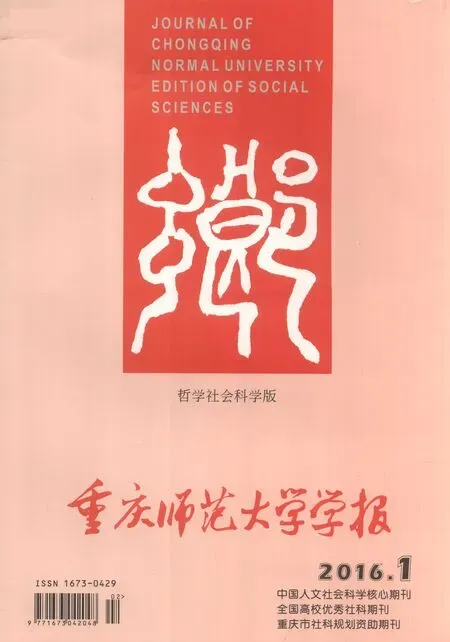论王符的文学观念
李 晓 敏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论王符的文学观念
李 晓 敏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王符文学观念具体表现为对文学美刺功能的重视,主张文学的实诚精神。其本末兼顾的思维方式,是这些文学观念的内在哲学基础。王符文学观念虽然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但是在东汉中晚期文学思想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其本末观念的思考对魏晋文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王符;美刺;文学观念;本末论
王符是东汉中晚期重要的政论文作家,其所著《潜夫论》指摘时弊,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在《潜夫论》的论政中,王符有意无意的涉及到了他对文学的认识,我们从其言论中爬梳甄别,探讨其在中国文学观念流变中的影响和作用,更能发现这位东汉文人的文学史意义及价值。然而,《潜夫论》是一部文史哲兼有的子书,并不是专门的文艺理论著作。那么,我们要考察王符的文学观,应该从何入手呢?程千帆先生曾言:“所谓古代文学理论,应该包括‘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这两个层面的涵义。因而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就应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既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也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工作,其研究对象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是古人着重从事的,主要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1]121先生的这一观点无疑给我们莫大的启示。由此反观《潜夫论》,王符政论文创作本身即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他在文章中对文学观念的阐释大致有两种表述方式:一种是正面对诗赋等文学作品创作及其价值的说明;一种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对时风的批判侧面表达的。与此对应,我们一方面要对其直接的文学观念表述进行阐释,另一方面要对其侧面的表述进行发掘,通过对这两者的总结和相互参证,大致可以看出王符在特定时代中崇实尚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总体看来,王符这一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审视。
一、美刺文学观念
重美刺的文学观念是自孔子以来的传统思想。《论语·阳货》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2499汉代文人将这一观念视为圭臬,这也变成了汉代文学观念的主导精神。许结先生总结说:“儒家审美思潮是推动汉代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精神。它以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力量紧扣汉代文人的心弦,又以道德和艺术合一的观念成为汉代文学思想的基调。……这种理论模式的思想核心,是汉人遵循的符合社会意志的文学教化意识,它突出的表现为这样三点:一是以仁义为本寻求文学之性情;二是以礼乐制度规定文学之审美范围;三是以致用精神倡扬文学之美刺功用。”[3]4王符身处东汉社会中晚期,社会危机严重,文学的美刺功用自然成为其对文学的基本认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王符文章对现在视为文学作品的诗、赋、文等体裁的直接论述来分析,一是通过他对《诗》等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侧面发掘。
首先来看王符对诗、赋等文学体裁的直接论述。《潜夫论·务本》篇曰:
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4]19
诗赋是汉代最重要的文学体裁。王符认为,这几类文学作品最主要的功用有两点:一是颂,颂美丑之德。即针对社会现实,尤其是统治者的治政进行一种评判。虽然王符此处仅言“颂”,但从其后的“美丑之德”来看,明显包含了颂扬和批判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文学创作与现实政治是息息相关的,或美或丑,皆是对社会政治的一种反映。这一观念就其指向而言是外在的统治者。这样,文学就变成了主体抒发政治见解的一种工具。二是泄,泄哀乐之情。即文学创作者要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包括自己在内的民众在现实政治情况下的情感,或哀或乐,同样是对现实政治好坏的一种情感表达。但就其指向而言是内在的,即主体情感的一种发泄。强调的是文学应该是民众在政治情势下的一种情感宣泄的工具。可以看出,王符对文学功用的以上两点论述,皆注重文学的工具性,即实用性。通过前者,可以为统治者的治政提供参考意见;通过后者,可以为统治者的治政提供现实依据。这两种工具性的统一,集中体现了王符思想中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文学的实用价值就在于其可以作为辅助政治的工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符很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上论王符认为诗赋具有“颂美丑之德”的作用。同时批判那些虚张声誉,品评人才不实之人“外虽有振贤才之誉,内有伤道德之至实”[4]22。此处对文章与道德关系的强调,又说明王符充分注意到了文学对社会道德形成所具有的教化作用。
其次,王符重美刺的文学观念,还表现在他对儒家经典的使用和阐释。许结先生说:“汉人的学问因建立在对先秦典籍、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故其文学思想也就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解释特征,先秦诗、骚传统在汉代的影响、消释,以及汉人对诗、骚文学的理解、诠评,构成汉文学思想的主要范畴。”[3]6王符的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同时还随文伴有对这些经典的解说和阐释。从这些阐释文字中,可以窥知其对文学功用的一些认识。我们对王符文章中的引书曾作全面统计发现,王符在引用《诗》等儒家经典时,往往直接标明其“美刺”的性质。《潜夫论》直接引用《诗》原文或化用《诗》句者,共104次,明确标明“《诗》*”(*代表标明美刺性质的词语)者27次。其中标明《诗》美性质者,如:
《边议》:《易》制御寇,《诗》美薄伐,自古有战,非乃今也。[4]272
《志氏姓》:其在周世,为宣王大司马,《诗》美“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后失守,适晋为司马,迁自谓其后。[4]412
《志氏姓》:《诗》颂宣王,始有“张仲孝友”[4]454。
标明《诗》刺性质者,如:
《浮侈》:《诗》刺“不绩其麻,女也婆娑”[4]125。
《述赦》:《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4]180。
《述赦》:《诗》讥“君子屡盟,乱是用长”[4]192。
《交际》:《诗》伤“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4]353。
可见,王符对《诗》的“美刺”观念尤为强调,这是明显受到汉儒解经影响的结果。先看“美”的一面,如“《诗》美薄伐”一句,出自《诗·小雅·六月》。据《汉书·韦贤传》刘歆议曰:“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5]3125王符对《六月》诗义的理解,与刘歆一样,认为它是诗人针对周宣王讨伐北方少数民族,治边安民的治政的一种赞美,《诗》的功用在这里是赞美治政的工具。
再看“刺”的一面,上引的“讥”、“痛”、“伤”同样表达的是《诗》作为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一种讽刺精神。如《浮侈》篇所引“《诗》刺‘不绩其麻,女也婆娑’”一句,出自《诗·陈风·东门之枌》。《毛传》曰:“《东门之枌》,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尔。”[6]376也就是说,《东门之枌》的创作,完全是对社会风气日坏,生产停滞而作的讥讽之词。《诗》的功用在这里是批判政治的工具。
不仅如此,在王符看来,除《诗》之外,《春秋》和《易》也皆有“美刺”作用。如其言:
《浮侈》:晋灵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非君。[4]139
《救边》:《春秋》讥:“郑弃其师”,况弃人乎?[4]263
《浮侈》: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七月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4]122
如果说王符强调《春秋》的“美刺”功能是受到汉人解经注重《春秋》的“微言大义”观念影响的话,那他对《易》的“美刺”作用的强调就显得独树一帜。此处王符所引《易》文,出自《周易·节·彖》:“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7]70可见其原文并没有“美”这一文本性质的标识,此“美”应该就是王符本人对这段经典的解读和阐释。
综上所述可见,王符对儒家经典的根本看法皆有“美刺”性质。所有经典皆是针对社会现实而发,同时也皆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指导。这是汉人解经用经的传统观念。由此,我们再来看上论王符对诗赋等文学作品社会功用的正面阐释,完全是与其对儒家经典的功用认识一脉相承的。王符并没有明确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审美认识,文学的实用性,即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是其最根本的文学观念。以此为基础,就必然引出王符文学观念的第二个方面,即对文学实诚精神的关注。
二、实诚文学主张
《易》曰:“修辞立其诚。”[7]321对于真和善的追求,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审美标准。汉代《诗》学思想为主题的文学批评,求真致善也是其主要的精神旨归。王符之前的王充就曾发奋著《论衡》并自述其主旨是“疾虚妄”[8]11。王符对文学的认识是功利主义的尚用观念。在此基础上,出于文学美刺的政治作用的考虑,他又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如此就又继承了我国文学中实诚的传统思想。王符要求文学的实诚是我国以真诚为善的审美结构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认为,王符强调文学尚用,根本的要求是文学作品的实诚,具体包括了事真、情真、辞真三个要素。
(一)事真。
王符主张文学尚用,其首要的内涵就是文章要“事真”。这一观念,王符在对诗赋等文学体裁的批判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他说:
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蒙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4]19
此处,王符明确表达了对时人文章和言论中的“虚妄”之词的反对。在他看来,在文学作品中写作“虚无之事”,“陈诬罔无然之事”是应该坚决予以批判和抵制的。这种不实言论,并没有客观的现实作为依据,对于接受者来说,非但没有实际的效用,而且往往会造成“惑蒙夫”、“长不诚之言”的社会危害。王符所提倡的文学创作,应该是具有实质内容的文章,强调文章要言之有物,也就是要做到“诚”“实”。此处,王符注意到了主体的文学创作动机的问题。他批判当世的创作者写作动机是为了“求见异于世”“索见怪于世”。正是在这样一种尚奇好怪,沽名钓誉的动机之下,文学写作中的“不诚”才成为一种风气。只有创作主体认识到写作是为现实服务,才能在作品中言真事,讲实理。
王符在批判时人的人才品鉴风气时,对事真这一主张有着更加明确的阐释。如其《贤难》篇曰:
且闾阎凡品,何独识哉?苟望尘剽声而已矣。观其论也,非能本闺□之行迹,察臧否之虚实也;直以面誉我者为智,谄谀己者为仁,处奸利者为行,窃禄位者为贤尔。[4]48
另,其《实贡》篇也说:
夫高论而相欺,不若忠论而诚实。[4]156
这里所谓的“论”,即主体对外在人物和事件观点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做到真实可信,以客观的现实作为依据和基础。如果虚张高论,那就是一种“不诚”的表现,所以王符主张要“忠论”。王符认为,由于文学作品包括言论都是和现实紧密相连的,其内容真实与否,是会造成很大的现实影响的。如果不能做到真实,通过文学表达的意见就是虚妄的,且如果人人相互仿效,必然使得社会风气虚妄不实,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所以,王符在强调文学的现实功用的基础上,为文学树立的第一标准就是“事真”。只有所言之事为现实社会中的客观事实,才能保证其发表的观点和意见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也才能保证具有现实功用价值。
(二)情真
我们说王符的文学观基本上是主张尚用的,那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是否就排斥文学的真情实感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在王符尚用的文学观中,用与情是和谐统一的。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文学在客观的基础上表现出“情真”。
首先,在王符看来,言辞是人的感情的一种外显形式。他在《潜夫论·叙录》篇叙述自己作文的缘由时说:
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阘茸而不才,先器能当官,未尝服斯役,无所效其勋。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字以缀愚情,财令不忽忘。刍荛虽微陋,先圣亦咨询。草创叙先贤,三十六篇,以继前训,左丘明五经。[4]465
这里王符明确表达了自己写作文章的原因就在于“中心时有感”。这实际上已经触及了文学发生论的思想。创作主体受到外在现实给予的一种精神上的刺激,从而导致了其内心情感产生波澜,最终要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情感。而对于王符来说,自然就是面对东汉社会吏治腐败、人才失选而导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王朝面临岌岌可危的社会现实,作为一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下层知识分子不得不发的情感。王符认为,自己所写的每篇文章都是针对社会现实而发,而字里行间皆倾注着自己的“愚情”。王符并没有否认情感与文学的关系。相反,文章的写作,本身就应该是由情而发的。所以他说:“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诗赋等文学作品的创作,本身也就是用来使得人们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的。这样,文学作品就变成了情感的载体,成了人们表现自己情感的工具。王符这种注重情感对文学发生作用的观念,秉承了自《毛诗》以来的文学发生观念。《毛诗大序》曾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6]262《诗序》的作者认为,《诗》的创作本身就是因为人们在现实政治情势下对自己哀乐之情的一种客观反映。因为有了现实作为基础,这里的“情”就变成了实情、真情。
这样的一种对文学的实用和情感表达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王符的其它言论中找到佐证。他在《述赦》篇中说:
人之情皆见乎辞,故诸言不当赦者,非修身慎行,则必忧哀谨慎而嫉毒奸恶者也。诸利数赦者,非不达赦务,则必内怀隐忧有愿为者也。[4]193
在此,王符分析了赞成和反对数赦的两类人的不同心理。这两类人由于内心动机的不同,对赦赎的政策采取不同的态度,表现在言论上就是完全相异的外在呈现。这段话本来是王符用来论证数赦政策之不当的,但是却包含了一定的文艺理论在其中。王符认为“人之情皆见乎辞”,这种说法本来自《易传》,原文是“圣人之情见乎辞”[7]78。王符这里把“圣人”改成“人”,使得指称的对象由特指的圣人变成了泛指的一般人。也就是说,言辞是每个人内在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言”由“情”生,“情”是“言”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这实际上也肯定了文由情生。
所以,文由情生是王符文学观的一个基本方面。所谓的“情”是人面对现实的情况下产生的。“文”是可以宣泄情感的,这就是“文”之“用”。而这里的喜怒哀乐,主要是政治影响下的一种喜怒哀乐。这种情感的表达,对现实政治而言就是一种明确的反馈,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反映和干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王符文学观中的“用”和“情”是相互贯通的。又因为这种“情”是一种难以遏制的真情实感的流露,所以,“情真”和“事真”也是相互统一的。事真,正是情真的前提和基础。
(三)辞真
王符这里强调的辞真,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主张文学的语言真实、质朴。他说:“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也就是说,言辞只要能够完全表达真情实感就可以了,不要浮夸、诡丽。王符这里提出的“信顺”的要求,秉承了孔子“辞达而已矣”[2]2517的言辞审美标准。王符并不追求华美的辞藻,他主张文学语言质朴的风格。这一点,我们从其文章中就能明显看出。王符文章的语言质朴、准确,力求语义表达的贴切。同样,这一主张还体现在王符对当时虚张高誉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中。他说:
夫说粱饭食肉,有好于面目,而不若粝粢藜烝之可食于口也。图西施、毛嫱,有悦于心,而不若丑妻陋妾之可御于前也。虚张高誉,强蔽疵瑕,以相诳耀,有快于耳,而不若忠选实行可任于官也。[4]153
王符这段话的论述同样是在说明选官要注重实际才干,徒有美誉的人才是没有实际价值的。王符这段形象化的描写,客观传达出的文艺思想是,在王符看来,审美对象能带给人的愉悦感受,相比起实用价值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过分追求形式上的感官刺激,对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没有实际的作用,相反会遮蔽事物的缺点,造成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
其二,语言的真实和质朴,并不排斥文章形式上的技巧和构思。粗看上去,似乎王符要求语言质朴的主张否定了事物形式的审美价值。那在这样的文学思想指导下,王符的文章是否就变成了枯燥的说教了呢?当然不是,我们看王符的文章,不仅具有精美的构思,而且还十分讲究技巧,具有很强的形象性。以其句法为例,王符自己的文章句法就千变万化,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如其《爱日》篇的首段曰: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4]210
这段文字王符使用了顶真的修辞格,这种手法运用,使得整个文章的论证如一线贯珠,层层推进,说理明晰而透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见,王符并不排斥文学创作中的技巧和构思。
我们从前引王符对诗赋的论述也可佐证以上的结论。王符言诗赋可以“兴喻以尽意”。也就是说,他是承认文学中是需要采用“兴”和“喻”等手法来委婉实现自己的表达情感目的的。这一理论继承了汉儒“主文谲谏”的讽谏模式,主张以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我们发现王符的文章中时时出现比喻说理和类比说理的句例。如《赞学》篇曰:
夫是故道之于心也,犹火之于人目也。中阱深室,幽黑无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此则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则为己明矣。[4]11
这里王符在说明道之重要性时,将其比喻为照亮人类前进道路的“火”。这一比喻形象而准确,如此说理,读者自然非常容易接受。所以,王符所谓的言辞的“信顺”,即辞真,同样是在事真,情真的基础上来谈的。这种“真”是对浮泛、虚妄言辞的一种摒弃,但是并没否定文学写作的形象性和技巧。相反,适当的文学构思和语言技巧的运用,正好可以使得自己要表达的观点和情感得到最好的呈现。
章炳麟在《与人论文书》中曾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9]337诚然,王符对文学情感和技巧因素的肯认,避免了其将文学单纯看成工具的片面性。这也就使得其文学观实际的表现是文质并重,更趋合理,同时实现了对汉代辞赋浮靡文风的纠偏。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出,王符所倡导的文学作品包括了事真、情真、辞真三要素,由此三者最终形成了其文章创作的“理真”。而“理真”的实现,又统一于王符文学观念的尚用主张。唯有“理真”,通过文学表达的情感和观点才是最真实和实用的,也才是对社会治政最有价值的。
三、本末论观念
王符文学观念主张重美刺的功用和重实诚的精神,这是否能在其哲学思维中找到根据呢?答案是肯定的,即王符对“本末”这一哲学思想的继承和思考。诚然,在这一组哲学命题的探讨中,王符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发展各方面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专指文学问题。但是,本末兼顾这一思维方式的存在,恰是上论王符文学思想的精神前提。“他在理论思维中,已经把‘本末’作为分析各种文体和治国安民的最高的、最基本的指导性观念。”[10]222它不仅是王符美刺文学观念和实诚文学的哲学基础,同时还开启了随后的魏晋玄学思维,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此有必要对王符的本末论思想作一探讨。
王符作为东汉社会杰出的思想家,在对社会政治提出批判和改良方案的同时,就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本末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全新的本末论思想。我们要对此问题进行考察,首先要看王符的《务本》篇,他主张的是: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阨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4]15-16
王符在这里所论述的八组本末关系,皆以“本”“末”相对,对“本”哲学概念的强调,本身就是希望掌握事物最基础的性质,从而为人的行为作指导。这种思维方式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这正是王符文学思想中重美刺和重实诚的哲学基础。但这是否是意味着王符仅仅重“本”而完全摒弃“末”呢?不然,我们认为,王符对本末这对哲学概念的认识是具有一定的辩证性的。且看其具体的论述: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阨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4]17
首先来看王符对“本”的重新定义。王符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不仅将农业生产视为“本”,而且将合理的工商业发展,也视为治国之本。重视农业是王符经济思想的基础。他在《务本》的开篇即言:“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4]14既然富民在其经济思想中是如此重要,那怎样才能实现富民的目标呢?《叙录》:“民为国基,谷为民命。”[4]474这句话简短而明确地将农业放在了发展经济最突出的地位。类似的表述又见《浮侈》篇曰:
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巿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为非则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4]120
可见,在王符看来,国家要安定,要发展,最基础的工作也正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通过发展农业使人民富足,才能“富乃可教”,即对人民进一步实行文化教育。最后实现人民知礼,国家富强的目标。王符在这里所说的“本”,不仅包含了传统的农业,而且包含了具有积极实用价值的工商业。他的这种经济思想,修正了汉代社会由贾谊、晁错等人一直宣扬并奉行的“重农抑商”的错误思想,对农、工、商的社会地位和实际作用给予了重新评估和肯定。相对于同时代的思想家来说,其对经济思想中的“本”的定义是相当全面的,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本末论。对此,王步贵先生称颂道:“(王符的)这种估计和肯定实际上是对轻工商的浅陋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显示了王符经济思想的理论火花和独到见解,为当时一般思想家的认识水平和理解高度所不及。”[11]55
其次,我们再来看王符对“末”的认识。王符既然也将合理实用的工商业视为“本”,那他的经济思想中的“末”又指的是什么呢?从以上的引文来看,王符的意思很明确,他为手工业制定的标准是“胶固”“便事”,也就是要既方便操作,同时又结实耐用。但是有些“奸工”所制造的却是“雕琢之器,巧伪饬之”,这就是王符主张废弃的了。他认为商业发展的价值在于“通用”,但是如果“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产”,那最终的后果只能是“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由此可见,王符所指的“末”,是那些在他看来没有实用价值的“雕琢”“淫侈”之器的生产和流通。他对当时社会“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的现实情况深恶痛绝。尤其是对其中不具有实用价值的“淫巧”末业持坚决的打击态度。他的主张是:“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则民富国平矣。”[4]17
由此可见,王符以富民为本作为根本目的,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经济本末论提出了自己全新的阐释。他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同时对有助于社会发展的合理的工商业也予以肯定的态度,同样将其视为“本”业。他要反对的,仅仅是那些助长社会浮靡之风,影响国家发展的“巧饰”“ 鬻奇”的工商业。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符并不完全排斥文学对华美的追求,他所要求的只是美必须建立在“真”的基础上。
可见,王符在对社会经济产业的思考中,用到了“本末”这一组相对的哲学概念。对于“本”的重视,让王符重视文学的实用主义精神,由此衍生出其对文学美刺观念和实诚精神的重视。对前人“末”的观念的思考和矫正,也使得其在主张文学实诚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排斥文辞的华美,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文学真善美统一的标准。同时,虽然王符显然并没有把“本末”看成是可以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哲学范畴,但是其思维方式对后世魏晋的玄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作用,促进了魏晋文学思想的发展。
总之,在王符所处的时代和他本人的思想中,并没有明确的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概念,我们这里所指的,也仅仅是王符作为“思想家的杂文学观念”[12]578。王符思想中的本末观念,既是其文学观念的哲学基础,又对后世魏晋玄学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启迪作用。王符文学观念虽然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但是在东汉中晚期文学思想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对魏晋文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1] 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2] (魏)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4] (汉)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汉)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魏)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M].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汉)王充著,汪晖校释.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 徐复点校.章太炎全集·与人论文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0] 刘文英.王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王步贵.王符思想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12]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左福生]
On WangFu’s View of Literature
Li Xiaomin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nxi Linfen 041004, China)
Wang Fu’s view of literature embodied in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of literary beauty thorn, claiming the sincere spirit of literature, it takes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give attention to two or more things is the inner philosophical basis of the literature concept. Although philosophic literature concept with strong utility color, but in the middle-late stag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literature history has certain representative ness, at the same time it takes the concept of thinking has produce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weijin literature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ang Fu;praise and critical;the view of literature;the theory of non-essentials and fundamentals
2015-11-18
李晓敏(1983—),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汉代思想与汉代文学。
I05
A
1673—0429(2016)01—004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