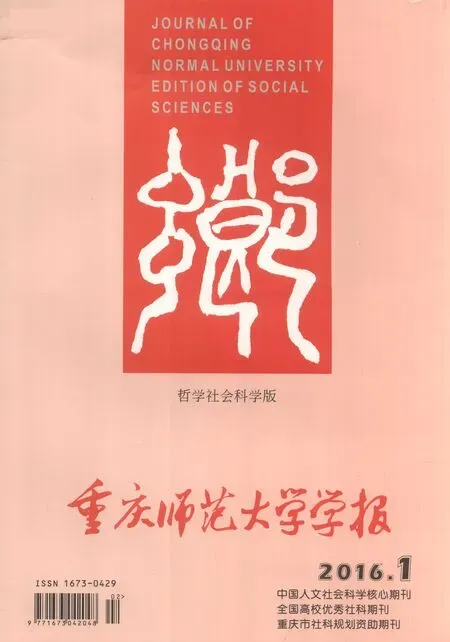抗战前后刘湘的政治抉择新论
刘 长 江 陈 显 川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达州 635000)
抗战前后刘湘的政治抉择新论
刘 长 江 陈 显 川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达州 635000)
对刘湘的评价长期以抗日战争为分野,形成二元对立的状态:抗战之前刘湘被视为“反动军阀”,之后则被誉为抗日“爱国将领”的模范式人物。其实,刘湘一生的政治选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非简单的“转变”:不管是在军阀混战还是在抗战时期,其身上均伴随有四川军阀“统一全川”和“川人治川”的观念,极力维护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即便是对抗日问题的选择,同样是对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即在“救国”的目的之外,还希望通过抗日来抵制蒋介石对四川的控制。而当时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升降变迁所造成的国家局势变化,是刘湘选择出川抗日背后重要的时代原因。
刘湘;反动军阀;爱国将领;川人治川;地方主义;国家主义
卢沟桥事变后,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日,“亲率师旅,杀敌疆场,尤为举国所钦许。不幸积劳过度,旧疾复发,国难未纾,竟先赍志以殁,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170。刘湘在遗嘱中仍勉励出征川军:“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1]168张澜在为刘湘写的祭文中称:“救亡必战,时论推许,李(李宗仁)白(白崇禧)刘(刘湘)齐。”[2]20-21可见,在抗战期间刘湘被当做抗日爱国将领的典范。
然而,刘湘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是割据一方的军阀,其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活跃在四川军阀混战的舞台上。在统一四川之前,刘湘与其他军阀之间连年征战;尔后刘湘率领四川军阀“围剿”川陕苏区红军,围堵中央红军长征北上,称其为“反动军阀”绝不过分。
“爱国将领”和“反动军阀”,是人们对刘湘最主要的两个评价。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从“反动军阀”成为了“爱国将领”,通常被认为是“他由军阀向民主主义者转变”。这种“转变”的解释不啻于认为刘湘的人生发生了从黑到白的颠覆。然而若追溯刘湘早年的政治态度,可以发现其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以贯之的因素,以及抗战前后其政治选择的连续性和内在的契合点。毕竟,“反动军阀”刘湘和“爱国将领”刘湘是同一个人,在“转变”之外,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有着互通的一致性,然而这一点却很少被学界同仁所关注。
一、“统一全川”与“川人治川”的政治观念
刘湘字甫澄,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十五日生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年19岁的刘湘赴成都考取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是为从军之始”[1]2。清末民初,各种政治风潮涌动,其中革命思想最为炽烈,刘湘虽生逢其时,却并无明显的政治思想。[3]3刘湘在速成学堂的同学鲜英就说:“当时他是不大关心革命的,如同盟会员余井塘、公孙长子等回到四川,暗中进行革命活动时,速成同学多有所闻,甚至有所接触,刘湘却从不与闻。”1911年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刘湘因为“未受革命影响,遂派他抵御围攻省垣的同志军”。刘湘虽奉命参战,却对此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认识,还问鲜英说:“不知为啥要打仗?”可见早年的刘湘并无多少政治理想和政治态度可言,尤其是“在护国之役以前,刘湘是一个职业军人,唯知带兵打仗,不及其他”。[3]13
时人曾批评四川军阀“并无何等远大思想,只求其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金钱狼藉,于意已足”,“护国护法”,也不过是“借题发挥”,“掩人耳目”而已。[4]刘湘等四川军阀“行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内斗,而不大参与全国政争”。和刘湘有过来往的高兴亚就说四川的军阀“没有统治全国的奢望”。这里的“‘奢望’二字颇能曲尽四川军人的心态。川军多头并立,军事竞争十分激烈,能站稳脚跟,立定地盘已不易,遑论‘统治全国’”。[5]尽管他们也偶有“统一全川,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言语和想法,但其实际活动基本未超出四川范围。刘文辉就一度“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最终败退只能回到四川争霸。[6]3和刘文辉相比,“四川的大部分军人还是要实际得多,政策以自保为主”,不做统治全国的“奢望”。[5]
然而,“统一全川”却是当时四川大多数实力派军阀共同的野心。这也是刘湘等四川军阀之间彼此争夺、混战的原因。为了“统一四川”,争夺地盘,四川军阀之间连年征战。据统计,从1917至1937年约20年的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共发生了“大小战事共400余次,其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为祸之烈,堪称全国之最”[3]1。时人有竹枝词曰:“刀兵二十二年多,蜀乱从头数此讹。战役四百七十九,伤心父老泪滂沱。”[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四川军阀之间彼此相争,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也多寻求川外的支援,但如果川外的势力觊觎四川,则会遭到他们一致的反对,甚至暂时联合起来抵抗。“统一全川”和“川人治川”的思想交织体现在刘湘身上。
在护国之役后,北京政府任命唐继尧一系之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戴戡暂署四川省长,滇黔势力有霸占四川的企图。这遭到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对,爆发了刘罗、刘戴成都之战,最后罗佩金败走,戴戡兵败自杀。[3]9这期间刘湘任川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坚决联合四川本地的势力,支持刘存厚,驱逐滇黔系势力。刘存厚与滇黔势力战事一开,刘湘即两次领衔与川军各旅、团长联名通电,指责滇将罗佩金,历数其“强滇弱川”等九大罪状。[9]274,275
1920年,川军与驻防四川的滇军、黔军隔阂日深,发生激烈战斗,刘湘加入到了“驱滇运动”当中,在短暂联合之后再次选择对抗以唐继尧为代表的“外来”势力。[1]15当时熊克武提出“驱逐客军,为四川争省格”的号召,获得了刘湘等其他四川军阀的支持,形成以熊克武为盟主的川军联合抗衡滇、黔的局面。[3]18刘湘等四川军阀拥护“驱逐客军”这一主张,自然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但背后同样反映了他们在“统一四川”这个问题上“一致对外”的共识。
1925-1926年间刘湘与杨森之间的分合更是“统一全川”与“川人治川”思想交织的典型例证。杨森曾是刘湘部属,后率部出川投靠吴佩孚,自成一系。杨、刘分裂后彼此独立但又关系复杂。1925年,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势力发展壮大,不断扩张地盘,发动了武力统一四川的战争,并且在“统一之战”的前期,取得了对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等部的胜利。为了对抗杨森,刘湘除了联合邓锡侯等川军反杨势力之外,还拉拢贵州军阀袁祖铭,组成“川黔联军”,最终打败杨森。杨森的威胁一解除,刘湘便加紧防备、排斥袁祖铭,并且联合杨森共同对抗黔军。尔后川黔军战事一开,刘湘发表通电称“川军必须一致对外,方能避免生灵涂炭”。杨森也响应称“以后本省军队,必须一致对外”。[3]77最终,刘湘和杨森等四川军阀联合把袁祖铭势力驱逐出川。可见刘湘与杨森之间虽然关系复杂,分合不定,为了各自“统一四川”的野心可以互相征伐,但是在四川的“内外”、“主客”之分上却又有很深的默契和认同。
二、“围剿”红军与拒绝蒋介石势力入川
“围剿”红军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刘湘“反动”的铁证。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川陕苏区,以及中央红军长征至四川后,都遭到了刘湘的“围剿”。刘湘对红军的态度与他“统一四川”和“川人治川”的思想有着紧密关联,他与红军的矛盾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上的对立,不如说是因为在四川“内外”“主客”这一观念上的区隔。在刘湘眼里,无论是先后进入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还是企图控制四川的蒋介石,都与前述滇军和黔军是同样性质的“外人”和“客军”。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至川北,占领了通江、南江和巴中三座县城,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根据地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并且在农村划分阶级,颁布土地法令,开展土地革命。红军入川立即遭到了四川军阀的反对,各军阀之间甚至暂时摒弃矛盾,达成“谅解”,共同围剿根据地红军。
在红军入川之前,即1932年10月,刚刚爆发了四川军阀之间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的“二刘大战”。当时,刘湘和刘文辉叔侄是四川最有实力的两个军阀,都有独霸四川的野心,二人在明争暗斗之后,终于演变成一场祸及全川的激烈战事。战争后期刘湘明显占据上风,至1933年8月,已逼迫刘文辉退至岷江一带。8月15日,刘湘向蒋介石报称:“昨闻‘共匪’有进扰仪陇之举,情势至急,非迅速结束岷江军事,必致贻误‘剿匪’时机……综合前方情况,大约岷江军事旬日内可结束,即当回师‘剿赤’,以纾钧系。”[3]135最终刘湘虽然大败刘文辉,但并未穷追不舍,置其于绝路,一方面是因为顾念叔侄情份,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川北红军迅速发展,迫使刘湘不能不迅速结束战争,以便‘回师剿赤’”[3]136。9月6日,刘湘与刘文辉发表联名通电,停止敌对行为,此后便集中全力对付川陕苏区的红军。[3]141这其实与之前联合杨森驱逐袁祖铭有很大的相似。
早在1933年1月,田颂尧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对川陕苏区进行“三路围攻”的时候,刘湘就对田颂尧在钱款和弹药上进行了支持。[3]1421933年10月4日,刘湘宣誓就职蒋介石任命的“四川剿匪总司令”。此时的刘湘已取得“二刘大战”的胜利,成为四川的“主宰者”,于是组织各路军阀,发动了对川陕苏区红军的“六路围攻”。面对川军的强势进攻,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战术,把阵地最后收缩至万源一带,并且取得了关键性的“万源保卫战”的胜利。最终,苏区红军在党的领导以及苏区群众和群团组织的大力支持下,[9]打破了刘湘的“六路围攻”。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四川,刘湘派兵追堵,同样以失败告终,红军最后在懋功胜利会师。
刘湘与红军作战,名义上是奉蒋介石之命令,实际上有他自己的考量。刘湘在“六路围攻”的部署阶段就对亲信幕僚和将领说:“只有拒‘匪’于川外,才是上策。如今‘匪’已盘据通、南、巴,那就只有配合友军,主要是我军部队负担起进剿任务,将‘匪’消灭;如不能消灭,也得驱出省界以外,才能够保境安民。”[3]143-144足见刘湘对红军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真正的底线其实只是“驱出省界”。如果红军不入四川地界,不妨碍到其“统一全川”的目的,则刘湘与红军也并无更多仇恨,所以他心里的作战目标是把红军“驱出省界”,而非一定要“消灭”。在追堵长征的中央红军时,刘湘也“不愿与红军作决战性的对消”,而是尽量寻求“付出最少代价来将红军送走”。[3]164
在拒绝红军入川的同时,刘湘也在抗拒蒋介石的势力深入四川。刘湘在蒋介石上台之初是支持蒋介石的。1927年4月,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的第二天,刘湘便领衔川中各军长发表拥蒋通电;8月,蒋介石辞职下野,三个月后由日本回到上海,刘湘再次电请蒋介石复职。在1929年蒋桂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中,刘湘均对蒋介石给予了支持。[10]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蒋介石为刘湘提供了不少支持,使得其在四川的争霸中成为了首脑人物。[3]9刘、蒋之间初期的关系可谓“蜜月”。然而,“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利益、派系利益基础上的,并不是以共同的政治原则和目标为基础的,属于军阀间的同盟。一旦蒋介石要吞并刘湘的时候,这种关系立即破裂”。[10]
蒋介石一直有控制四川军政事务的企图,因此曾准备在四川建立国民党党部,作为控制四川之基础。1926年12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建立的国民党党部被共产党包围。时刘湘任二十军军长驻于重庆,趁机对重庆市国民党党部“横施武力,加以解散”,并宣称是为了清除共党份子,故“忍痛割爱,作清党运动”。刘湘借“清党运动”之名解散国民党党部,故国民党人愤言:“(重庆市党部)不是直接被解散于共产党,而直接被解散于国民革命军军长刘湘……夫革命军者,固国民党指挥之军队也,以被指挥军队而解散受指挥之党部,事之荒谬孰逾于此。”[11]342可见即便是在蒋刘关系密切的时期,刘湘的底线依然是不允许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
在“围剿”红军时期,蒋介石同样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控制四川,一方面,希望在与红军作战中消耗川军的力量,故而“蒋介石宁愿红军少打败仗而要让四川将领多打败仗”[10];另一方面,则希望派中央军进入四川,名为“助剿”,实为“图川”,这自然遭到了刘湘的反对。刘湘等军阀只接受经济和武器支持,以及勉强同意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提供军事策划,坚决反对中央军入川。[3]168即便在对红军进行“六路围攻”时久攻万源不下、损失惨重,“刘湘之焦急,不在于‘剿匪’不利,而在于因‘剿匪’不利致中央军入川”[12]。蒋介石中央军虽未入川,但“参谋团”入川对局势的影响却比较重大。蒋介石曾声明“参谋团”只是策划“剿匪”军事,不过问政治。但随团而来的别动队却在蒋的支持下暗中从事“反刘”的活动,计划“在四川大搞军运、匪运、学运、绅运和商运活动,用以破坏秩序,制造混乱,企图趁机搞垮刘湘”[3]187。
蒋介石表面上“以四川交刘湘”,而实际上“仍以别动队领民众抗令”,“湘甚怨,矛盾日深”。[13]129刘湘表面对蒋介石敷衍,暗中联络各反蒋地方实力派,如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商震,山西阎锡山及陕西杨虎城等人,[3]192以使自己不至于孤立,并可联合行反蒋之事。1934年《大公报》发表的社论十分贴切:“二十年来川省对于中央,多处不即不离,谓其立异乎?则通电之拥戴,政令之响应,代表之周旋,虽亲信同志,无以过也。谓其忠乎?则反政府方面,随时皆有四川代表奔走接纳,或以文电示同情,或以金钱达诚悃,要以预防政局变动,保持割据地位为唯一之鹄。”[14]
在刘湘的政治立场里,无论是共产党红军还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威胁到其在四川的地位,皆以敌人目之。刘湘并没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追求,他“围剿”红军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排斥,这其实也是抗战时期与共产党合作的基础之一;而作为国民党领导下的地方长官,他却被骂作是“不知我党(国民党)主义为何物的无耻军阀”[11]341,显然也并不被国民党人视为“同志”。对刘湘而言,当时四川“红区”与“白区”的对立,或者说不同意识形态、不同阶级政权的斗争,都不及四川的“内外”、“主客”之分以及“统一全川”重要。
三、救国与反蒋双重目的下的抗日选择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7月10日,刘湘即向蒋介石请缨,并“通电全国,请一致抗日”;8月7日亲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表示决以四川人力财力,贡献国家,抵抗侵略”。[1]146刘湘表示为了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15]3748月14日刘湘回到四川,随即“分别召集各军,商出军事宜”。9月1日,“川军出川抗日部队,分东西两路出发”,奔赴前线。[1]146刘湘“由中央委任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自四川出发的十二个师分别奉命驰援京沪与山西战场,川军在各战场上虽伤亡惨重,而皆作战英勇,发挥同仇敌忾的精神,表现优良”[1]8。正因为川军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无畏的表现,“无川不成军”的说法才广为传颂。然而,带领川军出川抗日的刘湘却因胃溃疡发作,于1938年1月20日病逝于汉口,时年49岁。刘湘与川军为抗日战争所立下的功勋,以及在国家危亡时刻所表现出的民族大义,是客观的事实,历来都受到论者的充分肯定,笔者亦完全赞同。然而,刘湘选择抗日的原因和动机尚需进一步探讨。
有研究者认为,“刘湘在与蒋介石的矛盾斗争中,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由一个反共拥蒋的地方军阀转变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能够参加抗日的地方势力派。”[10]由追求自身利益的军阀“转变”为民族主义者,是大多数研究者对刘湘抗战前后政治立场的认识。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确实是影响其决定的重要因素,但仅以“转变”二字予以解释,实难令人信服。
从表面上看,刘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确实与在川中争霸时期大不相同,然而,从政治立场以及内在思想观念的角度看,则“转变”之说实有言过其实之处,至少说,抗战前后刘湘的政治观念里有很多“一以贯之”的地方。在是否抗战这个问题的决定上,对个人利害得失的考量从来没有被国家大义所完全替代。刘湘决定抗日,其实是出于对民族危亡和个人利害的综合盘算。七七事变之前,“抗日”甚至被国内各方势力(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用作制衡和攻击对手的武器。
早在1933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就策划“西南五省联防”,“对外宣传对日,其实纯为反对中央”,刘湘对此事积极“促成之”,并“催西南反中央”。[16]2041936年6月1日,广州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通电全国,吁请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抗日。6月4日,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领衔发表通电,对此表示拥护,并准备出兵进攻蒋介石。[3]193因此,蒋介石致电刘湘,要求刘湘表明态度并通电讨伐陈、李、白等人。刘湘却通电称:“诸公主张抗日救国,义愤填膺,无任钦佩,国人怵于危亡无日,强权胜于公理,救亡图存,舍自立奋斗外,宁有他途?”[3]194电文后虽然通过文字的润饰,表面上对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激烈行为表示否定,而对其抗日主张的赞同却是“溢于言表”的。实际上,刘湘通电表示“钦佩”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并非针对抗日主张,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反蒋。起初,刘湘帐下的邓汉祥就主张“冠冕堂皇地打一个通电,坐观成败”,而刘湘对此断然否定,认为“应响应两广,若两广失败,四川更没有办法抵制蒋介石”,因此要求邓汉祥拟出的通电“使两广看去,不是在帮蒋,但对蒋也要勉强敷衍得下去”。[15]368因此,才有了这通赞同抗日的电文。尽管文字上是“救亡图存”的国家大义,而真实的意图却在于支持两广以维护“抵制蒋介石”的同盟势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导致国内政局十分紧张。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闻讯赶回成都,急召亲信商讨是否趁机调集军队包围蒋介石安排在成都的军校和重庆行营等机构,斩断蒋伸入四川的触手。集众商议后考虑到:“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所谓学校、行营这些摊子还搬得走吗?如我们这个时候发动,假使张把蒋放了,我们怎么下台?”[15]370因此并未动作。但可见西安事变一发生,刘首先并且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趁机排挤蒋介石在川的势力。刘湘一直视张、杨为抵制蒋介石的同盟,故西安事变中有传言称:刘湘曾密电张学良,主张对蒋介石采取“断然处置”[3]202。此密电虽未见流传,但当时一位美国的外交官也确定刘湘曾劝说张学良要毫不犹豫地把蒋介石干掉。[17]157刘湘在12月13日发给孔祥熙、何应钦关于西安事变处理建议的电文亦暗含此意。刘湘建议说:“兵虽不可即用,但仍应积极备战,并使张、杨知悉中央军从河南、四川兵从陕西向关中作战之决心,可以促使张、杨早日觉悟。”[1]142刘湘虽表面说不可用兵,但以备战来促使张、杨“觉悟”的建议,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得知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刘湘是“颇感惊异”的。[3]219西安事变如何解决关乎抗日大局,而刘湘在这一问题的选择上,显然没有把抗日大局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
刘湘选择联共抗日,是为了民族和国家,同样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西安事变中,中共“为国家大局着想,抛弃历年和蒋的积怨,标举‘外御其侮’的大旗”,主张和平解决,这“的确感动了刘湘,并且转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15]371但转变对中共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力图与各方反蒋力量联结,庶期一旦有事,可以互为呼应,借免于孤立无援之境”。并且,刘湘之所以赞同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还在于“一致对外”可以转移蒋介石对准他的矛头,间接抵制了蒋对四川的觊觎。[3]218
其实早在1935年,冯玉祥就给刘湘提出了通过抗日来反蒋的建议。刘湘派张斯可到北平请教冯玉祥,如何应对蒋介石图川的阴谋。冯认为“必须主张抗日,蒋不抗日为全国人民所唾弃,刘只要坚决拥护抗日并作实际准备,这就可以博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可以联络一切反蒋力量”。冯的建议得到了刘湘的认可,并说抗日是全国人民的事,同时“也确是我进入全国政治舞台的好机会”。冯玉祥对刘湘的心态把握很准确,曾嘱咐高兴亚说:“对刘湘谈话不要只谈革命大道理”,因为“一般军阀心理皆以自己的利害为第一,即谈革命也不过是打官话、说空话,要关切到他本身的利害存亡问题”。[18]214-215
1937年8月26日,刘湘发表了《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川康军民书》,称“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中央领导之下,为民族救亡抗战而效命”[19]220。刘湘的“国家民族立场”未必不真诚,但肯定不是其“立场”的全部。刘湘的抗日立场中有反蒋的目的,而反蒋则是因为其始终如一的割据四川的野心。因此,选择抗日是刘湘从国家救亡和维护个人割据势力两个方面反复综合考量的结果。
四、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兴替下的抗日抉择
对于刘湘而言,无论是选择割据四川还是出川抗日,都有维护自身利益以及抵制外来势力控制四川的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存在从“反动军阀”到“爱国将领”的转变。然而,如果说刘湘的抗日举动完全出于主观“自私”的目的,则又不然。
刘湘选择出川抗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出于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也有维持自身在四川独霸势力的目的;既有对蒋介石的抵制,[10]也因为共产党方面积极的统战工作。[20]这些原因向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公认,此不赘言。然而,有一个重要的时代因素很少被研究者纳入思考,即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兴替变迁对刘湘选择抗日的影响。
中国近代的地方主义肇兴于晚清,在民国初年已经成为流行的政治“话语”。在时人眼中,“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兴衰变迁与“国家”的强弱分合息息相关。而这一“时代元素”深层而潜在地影响着当时的政局,左右着刘湘等很多人的政治选择。
从理论上讲,地方主义并不一定导致国家的分裂,很多人认为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由“爱乡”而“爱国”就是被普遍认可的“地方”与“国家”之间的一致性逻辑。[21]孙中山也认为由地方主义思想所培育出的“地方自治”是“共和自治”的基础,因此主张“联县而省,联省而国”。[22]代序2-4
然而,还有很多人认为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实际上存在巨大张力,甚至说“地方主义”的发达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统一和富强。由于地方主义强化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利益差别,而“这种区域性利益明显化的结果,自然对于国家整体化的观念,相对构成了一种损伤”[22]前言3。民国2年(1913),徐血儿氏就说:“近来观察社会,有至可悲可惊之现象,即地方主义之日形发达是也,事实上虽力谋于合,而心理上则力趋于分,有省界而复有府界,有府界而复有县界,使如此之地方主义,而不亟为打除,则适自兆分裂而已矣。”[22]前言2
徐氏断言地方主义的“日形发达”将会导致国家的分裂,而后中国确实陷入了军阀割据纷争的现状。在19世纪末,中国的地方主义是一种在“分”的客观上有利于“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已“偏离了以前具有的‘中央方向’”。[23]即便不能断言地方主义是军阀割据、国家分裂的内因,但是当地方主义与军阀势力互相借势时,两者交互影响、互为因果却是实情。各地大小军阀大多挟“地方自治”来抗衡外部的“统一”势力,故而“川人治川”、“湘人治湘”等类似的思潮在全国各地十分得势。所以从理论上讲,地方主义既可以促进国家统一发达,也可能导致分裂衰败,然而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把地方主义放在军阀割据的实际历史背景中,则不难发现其对分裂局势形成巨大促动的事实。
国家的分裂使得各地军阀大多标举地方主义,而地方主义的流行也为地方割据提供了思想基石。四川的“自治”就是因“南北纷争,局势靡定,遂成自治举动”[24]640。这其实是纷争的局势使得各地以地方主义来建立“小王国”。张澜也说“中国统一,早为北政府所破坏,川省自治,理极正当”,认为被怀疑具有“独立意味”的自治,在统一被破坏的时局下也是合理合法的。[25]7国家分裂是各地方“自治”甚至“独立”的合理性前提。故而,刘湘在1920年宣布自治时称,“对于南北任何方面,不为左右袒,永不许外省军队侵入本省境内”,这样的“自治”固然有自成小王国的倾向,但同时刘湘也声明:“四川自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俟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告成,乃能承认其命令”,并且称自治是为了“内以巩固地方之基础,外以促进国家之统一”。[24]640-641可见刘湘也深知四川自治仅仅是作为国家分裂时期的临时办法,一旦统一的局势出现,其主张的地方自治也自然无所倚恃。
北洋军阀时期的分裂格局,经历大革命之后,国家局势逐步趋于统一。而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除了破坏外,也使得“国家主义”遽升,并压倒了地方主义。抗日战争对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与日本的较量,从国内的角度来看,也使得国内的局势发生了扭转,“地方”不得不再次回归到“国家”当中。
“西安事变”中刘湘曾通电说:“我国年来上下努力,始由纷乱之局,扒疏整理,略具国家规模,组成强有力之政府,国际间之认识,始由地理名词之‘中国’,变易为政治名词之‘中国’。”[1]143“由纷乱之局”到“略具国家规模”,这其实是对当时“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消长变化最具体的观察。可见,不管对于“国家主义”的兴起是否乐见,但作为客观的政局大势的变迁,刘湘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
刘湘的政治生涯正好处在国家由分裂而统一、地方主义由长而消、国家主义由弱而强的历史变迁当中。他成长于分裂的时代,并成为其中重要的人物,因此这一时代的特征难以消除。他在各种情势下,都极力维持自己在四川的割据地位,着眼于自己的地方利益,这也是分裂时代的地方主义留在其身上的基因。而随着抗日战争所造成的国家主义上升,使得其行事选择也不得不与新的局势相契合,故而从“国家”的立场选择出川抗日。
地方主义的隐退和分裂格局的渐趋统一,使得刘湘不可能再如往日一样割据四川,即便刘湘依然反对中央政府对四川的控制。因此,出川抗日不仅符合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对刘湘等四川军阀而言也是新的格局下维持地方与中央博弈实力的最好方法。刘湘成为领导川军抗日的英雄,是其自身爱国精神的驱使,是针对蒋介石“图川”的反动,是中共统战工作的成果,也是当时中国地方主义隐退、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力量促生的结果。
[1] 周开庆.民国刘甫澄先生湘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2] 张澜.祭刘湘文[G]//王洪林.两平居集.澳门:国际港澳出版社,2003.
[3] 乔诚,杨续云.刘湘[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 凤兮.对于此次川战之感想和希望[J].上海:蜀评月刊,1925(7),“言论自由”栏
[5] 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识中的全国与四川[J].历史研究,2002,(3).
[6]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G].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7] 复兴月刊:第3卷,1935(6、7期合刊).四川专号
[8]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9] 陈显川.川陕苏区群团组织在反“围剿”斗争中的贡献[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3).
[10] 卜桂林.论刘湘的转变[J].民国档案.1991,(2).
[11] 居正.清党实录[M].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2] 川匪与川政[J].北方公论.1934,(78),时评.
[13] 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5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14] 刘湘入京与整理川政[N].大公报.1934年11月19日,社评.
[15] 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G].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精选:第10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16] 高素兰.蒋中正总统档案史略稿本:卷26[M].台北:国史馆印行,2006.
[17] (美)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8] 高兴亚.冯玉祥与刘湘的秘密往来[G].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19] 四川省档案馆编.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20] 邓前程,徐学初.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战场的——以四川为例的统战史考察[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5).
[21] 朱新屋.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J].唐都学刊,2013,(2).
[22]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3] 杨天宏.地方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北洋时期“联省自治”运动再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2012,(5).
[24] 许指严.民国十周纪事本末[M].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
[25] 张澜.与熊克武论四川自治书[G].四川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刘 力]
New Reviews on Liu Xiang’s Political Choices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Anti-Japanese War
Liu Changjiang Chen Xianchuan
(Research Centre of Sichuan Revolutionary Old Area in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The comment on Liu Xiang has been divided into two sorts for a long time and presented a binary opposition: before the Anti-Japanese War Liu Xiang was regarded as a “reactionary Warlord” and after that a model figure of “patriotic general”. In fact, his political choice has an inner coherence and continuity: during the time of warlords’ warfare or Anti-Japanese War, he held the idea that Sichuan Warlord should “unify Sichuan” and “Sichuan is governed by Sichuan people” in order to keep his governing status in Sichuan, even his choice to Anti-Japanese was the result of the balance between his own benefits and national interest.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ism and localism caused the change of country’s situation is the time reason of his choice to Anti-Japanese.
Liu Xiang; reactionary warlord; patriotic general; Sichuan by Sichuanese; localism; nationalism
2015-11-25
刘长江(1965—),男,四川渠县人,四川文理学院、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川陕苏区史研究。 陈显川(1987—),男,四川广安人,硕士,四川文理学院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K25
A
1673—0429(2016)01—0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