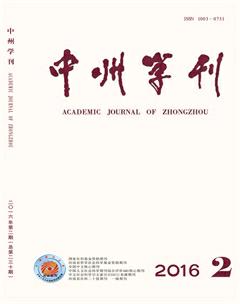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
杜鹏
摘要: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村民自治;转型动力;政府治理;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2-0068-06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产生至今,村民自治的实践样态经历了较大的转变,村民自治承载的民主化期许与其实践乱象之间的落差引发了媒体学界的普遍反思。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乡村社会基础和基层治理结构的变化考验着村民自治的实践效果。因此,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理解村民自治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做出相应的制度修正和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村民自治包含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要素,“四个民主”构成村民自治的完整意涵。但是,在西式民主话语影响下,学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主选举”这一环节,选举被认为是民主的核心价值。由此,村级的治理绩效被化约为选举的民主水平和规范程度。突出选举的实践取向和突出民主的价值取向主导着村民自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①村民自治一度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被赋予了自下而上推动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使命。上述取向导致了村民自治运行中的结构性失衡:村民自治沦为形式化的选举,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治理功能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和虚化了。②治理的弱化反过来降低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进一步加剧了选举的形式化。随着村民自治的常规化和选举制度的正规化,选举与治理的关系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③这意味着单纯通过加强和规范村民选举而改善村庄治理绩效的思路在实践中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
总体而言,学界更为关注的是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而忽视了其治理内涵和运行基础。村民自治最初是为解决村庄内部事务而产生的,具有向内的功能指向性。不过,从近30年的实践历程看,村民自治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治理效果,反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如“混混治村”“富人治村”“老好人治村”等等,都是一些地方村民自治面临困境的表现。村庄公共权威和公民社会并未能随着税费改革之后国家的撤退而自然发育,村民自治的结构性失衡也显化和放大了其负功能,即消极抵制国家的行政要求,增加了政府的治理成本。
既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联,或者将村民自治视为抵抗政府权力入侵进而培育公民社会的手段。税费改革之前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固然为这一理论架构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面临后税费时代的形势之变,需要转换村民自治的研究视角:村民自治不仅是一套发育基层民主和培育公民社会的制度体系,而且是一套有力的治理机制。在村民选举之外,滞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治理维度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这是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向,即从“谁在治理”向“如何治理”的转向。④“谁在治理”关注的是治理主体及其合法性授权,以“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作为理论预设;“如何治理”则关注规则及其实践逻辑,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在这个意义上,村民自治的转型方向应该聚焦于确立新的公共规则和治理秩序,而非仅仅局限于村级权力控制权的竞争。
因此,笔者将村民自治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的视野,重新思考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和治理机制。村民自治不仅在于自治目标内在价值的实现,而且在于通过“乡村民主的治理化”⑤,实现利益统合与秩序供给的能力。作为一种制度体系,村民自治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适应性,地方政府的服务型转型以及由此生发的治理需求构成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即“治理激活自治”,而村民自治的激活也反过来促进了政府治理绩效的提高,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近几年来,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一些基层民主治理的有益探索,例如,河南邓州的“四议两公开”、四川成都的“村民议事会”、浙江宁海的“五议决策法”等等,这些探索丰富了村民自治的内涵,并在不同程度上激活了村民自治的治理意义。本文将主要结合“成都模式”,讨论村民自治转型的动力与路径,由此进一步反思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与出路。本文的经验主要来自于笔者在四川省崇州市W村的田野调研。2015年9月,笔者所在的团队在W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研。该村人口3066人,共26个村民小组,目前全村已经基本完成了新农村改造,96%的农民搬入统一规划的新型农村社区,实现了相对集中居住,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W村自2009年即按照上级要求成立了“村民议事会”,目前运行已经比较成熟,提供了一个透视成都村民自治实践的窗口。
二、村民自治的国家视野
“国家—社会”理论设定了公民社会发育的自发性,它假定,随着国家从基层社会退出,公民社会必然随之形成。这种视角忽视了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基础和条件,村民自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的主导性作用尤其不可忽视。村民自治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产物,它接续了人民公社解体之后的基层组织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士绅自治的传统。⑥
1.汲取型与村民自治的政治逻辑
税费改革以前,基于赶超型现代化的战略考虑,国家需要通过代理人体制从农村提取资源,基层政权因此呈现为“汲取型政权”⑦。代理人体制的非正式激励结构导致了资源汲取的“内卷化”效应,并表现为“农民负担问题”,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爆发成为全国性的“三农危机”。村民自治在这种形势下被迅速推广,其主要目的是化解当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作为国家汲取型任务的代理人,村干部在村落权威结构中的正当性遭到弱化。村干部权力授权来源的改变有利于约束村干部的不当行为,改变基层权力运行失控的局面,也有利于防止基层政权合法性危机的上移。所以,村民自治所内含的“四个民主”在实践操作中也逐渐形成了突出“民主选举”的倾向,并集中表现为以政治合法性考量为本的政治逻辑。村民自治在这一时期的推行主要体现为中央的努力,得到中央政府更多关注和帮助的地方,民主选举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