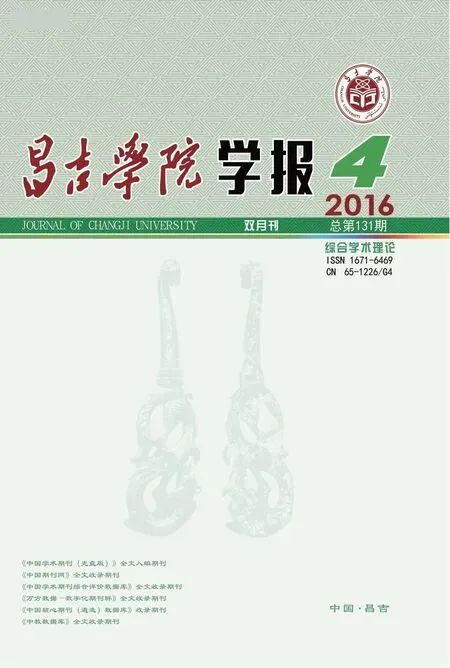文化生态视域下的土家族民歌研究
熊晓辉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文化生态视域下的土家族民歌研究
熊晓辉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文化生态保护与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文化生态视域下的土家族民歌研究主要拟在生态学及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土家族地区民歌的史实来进行实证研究。其一,围绕土家族民歌生态生成环境的内容与特征,用文化生态保护的立场和民族志方法来进行个案描述和理论分析,全面探讨文化生态视域下土家族民歌的内容、特征、形式、发展等等,研究土家族民歌在发展创新及基于文化生态视域下的发展策略。其二,针对土家族民歌所表达的方式、特点及对音乐文化研究的影响,采取历时态和共时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来组织材料与分析问题,通过时态性的文化把握,考察土家族民歌研究的重要意义。其三,对土家族民歌进行规律性的提炼和理论创新,在认真研究、鉴别运用现有文献资料的同时,丰富对土家族民歌的认识。
土家族;文化生态;民歌;环境;资源
21世纪初,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已经开始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来研究“民歌”,于是文化生态保护与“民歌”的联系等一系列问题就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人们试图透过各种纷繁复杂的“民歌”现象揭示环境因素的作用,以期做出具有规律性的解释。他们根据“民歌”与其文化生态环境的具体形态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地区的运动状况,来决定“民歌”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此后,自然、社会环境与“民歌”关系逐渐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在文化生态视域下,人们探讨、研究“民歌”已经取得了一些丰富成果,同时西方学者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音乐学等学科领域也奠定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一些学者如蕾切尔·卡森(美)、约翰·布莱金(英)、埃德加·莫兰(法)、卡尔·雅斯贝斯(德)等,更对民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歌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民歌的研究。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民歌研究对象有了相对基础,当论及民歌与生态的关系时,对影响民歌的环境因素展开了具体化的研究,并对可以观察到的层面给予定值、定型、定序分析,同时也对一般理论意义上的环境因素进行因子分解。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注意了民歌的生态分析,也借助了自然科学量化分析的方法,但其研究却显得有些零散,而且还受到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制约。
国内学者在2000年后才开始关注该问题的研究,并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专著有:田世高《土家族民歌论》,萧梅《田野萍踪》,余咏宇《土家族哭嫁歌之音乐特征与社会意义》,邓光华《贵州土家族宗教文化:傩坛仪式音乐研究》等。论文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约公开发表30余篇。综而观之,既有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民歌的发生、流源、类型与嬗变等方面。由于现有的民歌与生态环境研究大多是以民歌本体形态为中心而进行讨论的,故而对民歌与其生态生成环境、对民歌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关注不够,特别是对当前民歌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社会意义关注不够。所以,土家族民歌研究存在着值得深掘的空间。近年来,尽管土家族民歌研究似乎在相当充分的程度上被介绍与传播,但它的真正的学术价值不易在整体上被认识,在学术界,倡导这种研究的气氛并没有形成。随着民歌与生态环境等问题研究与应用的展开,土家族民歌的研究范围在不断拓宽,对土家族民歌研究及其意义上的肯定只有在经过一番批判性的工作之后才能达到。实际上,对土家族民歌研究,仍然是一种有待于结合当代音乐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及各学科种种具体问题,吸取新经验,从现代方法论水平上重新开展的艰巨的研究工作。
将土家族的民歌文化及其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类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揭示其间的内在关联性,以便将土家族民歌的流失与生态安全的维护纳入同一个问题去思考,从而从根本上化解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民族文化的流失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两大挑战。同时,对土家族“民歌与文化生态保护”的内涵做了前沿性的思考和理解。我们认为,土家族的“民歌与文化生态保护”是指该民族成员凭借其特有的民族文化艺术,在世代延续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一方面加工、改造了该民族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使之获得了文化的属性;另一方面,通过民歌文化适应环境的禀赋,不断地完善和健全民族文化自身,最终使民族文化与它所处的生态背景之间,结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耦合关系。文化与生态的这种耦合体就是该民族的文化生态。
一、民歌与文化生态环境的属性与内容
(一)民歌与文化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
民歌与文化生态环境的联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早在19世纪初,从鲍亚士到马林诺夫斯基都对民族文化及民歌文化的习得性作出了深入的探讨,而且还将民族文化定义为一套信息系统,积极揭示着文化的本质,努力把生态学和文化学共同感兴趣的适应问题、种间斗争、文化冲突、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问题,都纳入了信息系统创新的范畴去加以阐释。我们研究民歌与其文化生态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研究民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民歌产生的地理环境、社会政治、社会思想、政治制度等。民歌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在长期的位置生产、精神生活与社会交往过程中口头即兴创作的一种声乐艺术。[1](p3)从文化艺术角度来讲,民歌文化是社会文化整体中的一个面相,与其它文化类型一样,它最基本的一个特征便是群体性,而且这种群体性是通过人与文化这两个方面因素表现出来。[2](p17)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民歌”一词自古就有,如《诗经·国风》、《楚辞》、《汉乐府》等等都大量记录了中国古代民歌的表现形式、内容与结构,也可从中看出中国民歌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明代杨慎的《古今风谣》和冯梦龙的《山歌》都是较早研究、搜集与整理中国民歌的论著。纵观历史,事实上人类在几千年以前的渔猎、农牧生活中,就注意到了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是如何影响着收获的,同时也常常运用民歌演唱的形式,表达了狩猎与农作物耕种的技术特点与时令气节,这些其实就是朴素的民歌与生态环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观念。再者,从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我国北魏时期贾思勰所辑的《齐民要术》,都对人类改造自然环境以及各种生态现象进行了阐述。笔者认为,比较系统地观察与分析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关系的应首推美国生态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他于1955年提出了文化生态学概念,强调从文化生态变迁的角度研究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并提倡设立专门学科。早在17世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已经表述了“自然选择”理念,探讨了生物与自然环境的相互选择作用,生物进化论探讨的也就是生态学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在斯图尔德观点的基础上,对文化与生态的相互关系进行全面深刻地探讨,而且把文化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看成为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自从人类创造音乐起,民歌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们发现,音乐的历史,应当是从民歌开始的。音乐学家们认为,民歌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生产劳动。[3](p3)因为伴随着劳动节奏的呼喊和身体律动,就有了人类最早的音节与舞蹈节奏,民歌也由此产生。可见,民歌一开始就与人类的生产劳动环境分不开。《吴越春秋》一书中曾记录了一首相传是黄帝时期的民歌《弹歌》,其充分说明了民歌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关系。如《弹歌》中唱道:“断竹,续竹;飞土,逐宍。”[4](p128)歌中生动描绘了早期人类社会人们集体狩猎的情景,反映了劳动使人们获得了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民歌成为了人们民俗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人们集体创作的民歌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起主导作用的生态因素显然是社会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但自然环境一般来说只起外因作用,民歌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要通过心理机制的作用来体现。
既然我们认为“文化生态环境”通常关注的是环境影响下的文化生态生存状况,那么民歌与生态环境就要复杂的多,它是一门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与民歌关系的学问,它把民歌作为“核心物”,探讨民歌在创作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艺术文化环境场,着重研究与把握民歌生成与民歌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现代科学的发展拓展了我们视野,研究民歌与环境的关系,考察文化生态的形成与方法论,是十分必要的。民歌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问题,需要借助多学科综合方法进行研究。研究文化生态与民歌的关系,一定要把民族文化与历史过程、民族交往、民族生存环境纳入统一框架内。在此基础上,认识和了解民歌生态生成特征,加强对民歌保护,做到历史性、区域性、民族性有机统一,达到对民歌与其文化生态的整体性研究。研究文化生态与民歌的关系必须重视学者们对民歌文化的理解,民歌文化是实质正处于它是一种具体的人为信息系统,民歌生态学具有功能性、习得性、共有性、稳定性、整体性和单一归属性等。
(二)文化生态视阈下“民歌”的内容
对民歌与其生态环境的研究,我们还得回到文化生态的定义上去,应该先去探讨一下“生态学”。“生态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德国生物学家赫格尔于1870年首次提出。由于人类研究生态是从自身的价值取向出发,希望通过生态学的研究来解决切身的经济利益。于是历史上生态学曾被理解为有关生物的经济管理科学。[5](p279)但是,我们纵观人类文化艺术的进化与演进,每个民族在早期总是针对特定的自然生态系统去构建民族文化艺术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从纯粹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生命物质和生物能,而是从该民族生境中获取存在和发展的各种物质和能量。这样,生态变化如果与人类的活动有关联,那么它肯定不是发生于原生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中,而是集中表现在各民族的生境之中。民歌作为特定文化的产物,又受到特定文化的干预,其民族生境必然具有该种文化的特性,同时文化的固有属性在民歌中,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长期以来,学术界习惯于认定民歌与民族文化的环境与变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当今人类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与全球范围内的民族文化趋同存在众多关联性,但这仅仅是学者们的猜测而言。随着文化生态学逐步被我国学术界所接受,民歌与生态环境的理论与方法在民族文化和自然与生态系统之间构建了相互衔接的分析模型,使学者们的上述猜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支持,不过进一步的验证其内容仍属空白。民歌与生态环境其实就是以民歌发展与创作的生态环境为突破口,取材于生态学、民族学、音乐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已有的研究成果,具体实证当代及历史上生态环境保护对民歌的影响。
文化生态视阈下民歌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必须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而适应意味着民族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兼容,但同时会在一定限度内导致所处生态系统的人为性,具体表现为人们价值观、审美观的改变和民歌传承内容的改变。随着人们对环境认识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将意味着他们的民族文化也随着这种改变发生了变迁甚至消亡。据此可知,任何民族文化都具备通过改变生态系统,而改变民歌内容与结构的潜力。所以,这就为我们通过文化手段优化自然生态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生境内的生物物种构成格局总是以特定文化的需要为转移,并通过该文化的干预来维持这一构成格局的延续。一旦失去了文化的干预,民族生境内的生物物种构成以及物种间的配置关系,就会与原生的自然生态系统趋于相同。[6](p45)就在这一层面去理解,民歌的特殊性正在于它完全是特定文化在生态领域内的再现,并与特定文化的运行相始终。民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口头创作的歌曲,是人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又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最大的资源。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必然包含民歌资源可持续再生,中国民歌资源就当前调查表明,已经处于濒危的边缘,也是制约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首要因素。
二、土家族民歌的本体特质
土家族聚居于高山地带,这里树木茂盛,物产丰富,他们一直承袭着古老的宗教信仰。土家族人相信万物有灵,敬奉土王、祖先,敬猎神、土地神、梅山神、四官神、五谷神等。主持宗教祭祀的叫“梯玛”,梯玛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人们认为梯玛是人神合一的统一体,他既是神的代言人,又是人的代言人,能为人排忧解难、消灾祛病。武陵山地区土家族民歌的数量、种类繁多,主要有山歌、小调、号子、神歌、灯歌、跳丧歌、摆手歌、薅草锣鼓歌等,土家族民歌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厚的历史积淀、精巧的形态样式、洗练的表现手法。
(一)文化内涵丰富
土家族民歌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民歌成了土家族人相互交流和表达的主要方式,也是他们学习生活生产知识的重要途径。解放前,土家族的文化经济比较落后,普通群众是没有机会受到正式教育的,他们只有通过歌唱的形式来传递感情和学习知识,从而使得民歌成为了土家族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土家族社会,人们唱歌没有金钱、权利等世俗物质衡量标准,更没有封建社会门当户对的要求,唱歌是聪明才智的标志,会唱歌就能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土家族人都形成了以善于歌舞为美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种喜爱歌唱的文化模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民族思维习惯。土家族民歌曲调非常优美,并且紧密地与土家族语言相结合,曲调近似于朗诵调,在句末或腔末使用下滑音,形成自己鲜明的特征。土家族民歌大多数是用土家语来演唱,基本音韵的民族化不言而喻。在民歌中,土家族人的机智、憨厚、幽默往往贯穿始终,铸造出土家族民歌的个性风采。土家族民歌是土家族民族艺术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形式之一,除了演唱者运用演唱技术外,对于事物的描述与渲染还有着妙不可言的传递功能。作为一种在山野劳动生活中产生的歌唱形式,土家族民歌在传承中不断创新,歌手表演已经作了再度创作,它极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为了使演唱内容更贴近人们生活、风俗习惯,民歌力求和土家族生活相适应。从土家族民歌独特风味来看,它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已经具有了极富个性的民族地方化特征。如流传于湘西保靖县土家族地区的山歌《盘歌》,歌词大意是:“什么无骨钻硬土?什么无骨飘江湖?什么无骨鼎鼎坐?什么无骨有戏出?蛐蟮无骨钻硬土,蚂蝗无骨飘江湖,豆腐无骨鼎鼎坐,鸡蛋无骨有戏出。”[7](p122)土家族人幽默、俏皮,他们用优美的唱腔,用自己的语言,通过诗一般的艺术处理,构成了土家族民歌的浓郁民族特色,蕴藏着丰富的土家族文化内涵。
(二)历史积淀深厚
土家族民歌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它主要体现在土家族民族文化的遗存上,我们从土家族民歌中都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土家族人的音乐与民俗生活的踪影。如鄂西土家族丧葬音乐《撒尔嗬》至今还演绎着春秋时期《诗经》散遗的篇章,巴东地区土家族的《跳丧》仍然演唱楚辞中《国殇》的原词。土家族民歌演唱时程式特征鲜明,这种程式化的民歌尤能表现土家族人的审美情趣,在武陵山土家族地区,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节奏自由而绵长的民歌,程式简单,语言简洁,旋律优美。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土家族民歌与人们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宗教祭祀等有着直接的联系,是人们抒发内心情感和传达思想情意的特殊形式。如土家族《梯玛神歌》,其曲调来源于远古巴人的牛角号,舞蹈则来源于古代巴人的巴渝舞,它记叙了土家族的起源、繁衍、战争、迁徙、开疆拓土、安居乐业、生产生活等诸多内容。唐代在巴渝地区盛行的《竹枝词》仍然流行于武陵山土家族地区,它对研究古代土家族文学艺术、民俗民风、宗教祭祀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节奏鲜明庄重的土家族《摆手歌》则包含了人类生存、劳动创造等内容,是一部土家族生动的文明史诗。土家族民歌的历史积淀,还体现在其样式和表现手法对古代土家族先民,或者说对土家族传统歌乐的继承。
(三)形态样式精巧
土家族民歌在长期的发展与创作过程中,经过加工雕琢、传播变异,在艺术形式上可以说是十分成熟了,许多种类都有着独具特色和精致巧妙的形态样式。土家族民歌的节奏、节拍都比较自由、悠长,这种程式化的样式特征是许多民族民歌的共同特征。土家族民歌在演唱时,唱腔的节奏有时接近土家族语言的节奏,且能准确、清晰地唱出心里想说的内容。在土家族民歌的衬腔中,为了尽情抒发心中的情绪,歌手自由延长,也许,此时已形成了民歌中有规律的节奏和自由节奏的强烈对比,在我们常常听到的土家族民歌中,《破头腔》、《沿河腔》等最为明显。土家族民歌有着非常丰富的题材内容和形态样式,按歌手的演唱风格与形式来分,有固定唱词的热唱和即兴创作的冷唱两种,一般在休闲时,无论在什么地点,都是民歌演唱的场所。按旋律曲调创作手法来分,有五声调式体系、三音列、四音列、旋宫转调等等样式。“三音列”结构是土家族民歌最常见的旋律形态,土家族“三音列”民歌是由三个音构成,因而句幅短小,在三个音的运动下展开乐思,旋律下行、二度级进的现象比较多。[8](p7)土家族许多民歌的音乐思维都是建立在土家族“三音列”民歌的基础上的,它在发展与创作过程中必然从“三音列”中借用其固有的手法,并加以改造、发展,从而确定其独特的个性。由于土家族民歌源于生活,在歌手的再度精心创作中,它已经成为可以表达主观需要和获得美的享受的一种手段。在审美的需求中,土家族民歌能揭示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关系和各自的性格,并为民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吟唱提供现实依据。
(四)表现手法洗练
土家族的民歌善于运用素材,采用洗练的手法,塑造出一个个鲜明、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在土家族民歌中,有时为了加强情节的气氛,歌词内容很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有着浓厚的东方写意传神的固定模式。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土家族的民歌创作构思是依附于歌词内容的,人们在劳动中总是把歌词内容掌握的明白、透彻才进行民歌吟唱或创作。比如土家族民歌《蜜蜂只爱绕花台》,其歌词大意为:“阵阵春风吹过界,蜜蜂绕绕彩花来,蜜蜂见花双翅拍,花见蜜蜂朵朵开。”从这首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曲调和吟唱风格与人们生活是有直接联系的,民歌的内容都是人们对平时生活、劳动、爱情的体验。正因为这样,歌手在演唱土家族民歌时,觉得心中有数,土家风味入微入妙,既达意又传神,即便是新创作的民歌,也能在独特的演唱过程中潜移默化,独铸个性风采。
土家族民歌的创作是即兴的,是歌手一种心象示现。因为歌手的心理活动是捉摸不透的,是通过歌手运用唱腔艺术与表演来体现歌曲内容的。在土家族民歌中,用唱腔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和内心活动是最具特色的表现手法,也是心象示现最突出的手段之一。民歌,来源于劳动生活,但它又高于劳动生活,它有规律、有固定模式、有美的夸张,与其它民歌一样,它是通过历代歌手精心创作的民族音乐艺术。民歌是真实的,因为它从生活出发,经过艺术加工,并且准确地能将人物的情感和性格传达出来。尽管民歌的演唱形式很多,但叙事的倾向性很强,能在歌中紧紧扣合情节,在演唱中传达审美情志。我们发现,土家族民歌的表现手法非常丰富和细腻,而且能多侧面、多层次地勾画人物性格,是绝妙的心象示现。比如土家族民歌《沿河调》,歌词大意为:“正月喜鹊在树林,口含沉香树一根,口里有根沉香木,日不晒来雨不淋。”民歌借以十二种鸟的叫声,刻画了富于浪漫气息的日常生活,明朗乐观。《沿河调》唱出了土家族人对美的追求、对美的向往,民歌把对鸟儿歌唱的情感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土家族民歌形态分析与民歌范畴概念的意义
(一)土家族民歌形态
人们对于土家族民歌的认知首先是通过对其外部形态的直观感受来获取,民歌形态有着自身的结构层次,应选取适当的层次来进行分析、研究,但必须注意环境选择作用的焦点所在。
1.唱词内容
土家族民歌有山歌、小调、号子、梯玛神歌、猎歌、渔歌和劳动歌等等,就其内容来看,民歌与劳动生产及宗教祭祀活动有直接关系。或反映先民们渔猎及农作物收获后之喜悦;或伴随劳动过程而呐喊呼唤;或解释人类来源、万物始源等现象;或表述驱鬼逐邪、祈求人畜平安的愿望。[9](p32)比如梯玛神歌的内容取决于主持活动仪式的性质,即不同宗教活动唱不同内容的神歌。《梯玛神歌·请神捉鬼》这样唱道:“悬崖陡,刺丛深;水流激,路难行。尊敬的大神们啊,没有好路,让你行啊。”这首歌描述的是梯玛与大神对话,请大神捉鬼,在描述山区道路崎岖艰难、乘船注意安全时,却十分生动,生活气息较浓。又如这首《打猎歌》,它是这样描述土家族先民猎猴的:“背铳就往树林走,走进树林去赶猴。拿铳撵猴三天整,猴子跑得屁股冒红烟。”我们可以从短短的猎歌中看出土家族先民谋取生活资料的艰难,以及他们在猎猴时的耐心与机智。又如《船工号子》唱道:“里耶上来(众唱:嗨嘿)转个弯(众唱:嗨嘿),船儿要过(众唱:嗨嘿)螺丝滩(众唱:嗨嘿),上了一滩(众唱:嗨嘿)又一滩(众唱:嗨嘿),五家滩来(众唱:嗨嘿)过陡滩(众唱:嗨嘿),嘿哟(众唱:嗨嘿),吆嗬吆嗬(众唱:嗨嘿)。”这首《船工号子》属《酉水号子》,多为老船工即兴所唱,采用比拟、夸张等手法,生动地再现了酉水一带当年的地理状貌、风土人情及船工的艰辛生活。再如土家族的劳动歌,其歌词内容主要是一些知识性和解释性的农业歌谣,保留了土家族先民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原始农耕生产特点。
2.音乐结构
土家族民歌的音乐结构是由旋律、调式调性、节奏等组成,因为其民歌的个性化、色彩化,旋律是土家族方言民歌音乐特征中最具代表性的主导要素,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独特的语言音调,可以说武陵山区土家族民歌的旋律就是这种语言的音乐化。但是,它自己有约定俗成的表述风格与形态。
旋律特征。土家族民歌旋律是以“级进”或同音交替、同音重复较为普遍,并且旋律都是在“同音重复”中得到引申。级进和连续级进的旋法在土家族民歌中最为常见,较为独特的是,土家族民歌旋律在进行中一直保持着级进势头,乃至越过一个八度,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人声或乐器的音域造成的一种意欲超越极限的结果。在土家族民歌中,二声音列、三声音列序进是五声调式中最基本的运行方式,二声音列、三声音列依次向高、依次向低的序进形态,以及回旋形态都较常见。与汉族民歌一样,土家族民歌一般分为起、承、转、合四部分,起、承、转、合是土家族民歌旋律发展的必经程序,也是土家族民歌旋律发展的基本原则。
调式调性。土家族民歌以五声调式音阶为基础,旋律进行以级进、三度小跳为主,间以四度或四度以上的大跳的旋法为主为多,同时出现同音反复或舒而不展,形成一种平稳、怡然自得的旋律走向。[10](p31)土家族民歌常用的调式有:徴、宫、羽、商,其中徴、宫、羽使用较多,角调式很少使用。土家族民歌主要以羽、宫调式最为常见,在调的发展方面非常简单,主要表现在平行调式的交替上,转调极为少见。
节奏特征。在土家族民歌中,各个不同种类其节奏型是有很大区别的,往往又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些种类的民歌都是产生于人民劳动、生活之中,生活气息浓厚。笔者经过长期考察,认为土家族民歌节奏的形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语音节律的基础上逐步提炼而来,土家语音本身的律动美就是土家族民歌旋律形成的基础。二是由于受到人们长期的劳动生活的影响而形成的,劳动、祭祀、舞蹈等活动本身的节奏特点形成部分民歌的基本节奏。土家族民歌中不同类型的民歌节奏形态有不同的特点,如号子的节奏与劳动有关,其节奏规整,节奏型的顿逗适合劳动的气息运用,节奏重音突出。山歌则节奏自由、灵活,以散板居多。
3.演唱形式
土家族民歌在演唱时,有独唱、对唱、合唱等多种形式。在湘西自治州土家族地区,土家族民歌多是男、女声独唱,男、女对唱或两女对唱。多人合唱时,有女声合唱和男声合唱。唱歌时,歌手喜欢用手板托面腮吟唱,声音高尖,时值充足。一些祭祀仪式歌曲的演唱形式又有不同,其必须按仪式的程式来进行,比如《梯玛神歌》,演唱时梯玛头戴凤冠,身穿八幅罗裙,脚踏马蹄沙鞋,右手拿着司刀,左手握八宝铜铃摇晃,配以锣鼓伴奏,边跳边唱。《哭嫁歌》又是土家族民歌的一大特色,出嫁前一天晚上,姑娘和相邻姐妹十多人围着火坑同哭,称“陪十姐妹”;因此,不少土家族姑娘从小就要跟人学哭嫁,观摩或参与陪哭。
流行于湖北利川土家族地区的《灯歌》,其演唱形式独具特色。《灯歌》表演主要是划地为台,载歌载舞。一领众合,打一遍锣鼓就唱,打一遍锣鼓就收。表演者(演员)一般由一生、三旦、两丑组成,化妆、表演已具戏剧雏形,所以人们把《利川灯歌》又叫跳灯、玩灯、灯夹戏等。土家族《薅草锣鼓歌》是土家族先民在长期生产劳动中集体创作的一种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民歌,一般由两人演唱,一人按节奏击鼓,一人应节奏点敲锣,锣鼓间歇、歌声即起、轮流对唱。三人演唱与四人轮唱的形式也有,但很少。
(二)土家族民歌范畴概念的意义与民歌生态分析
1.土家族民歌范畴概念的意义
武陵山区土家族民歌是土家族人在长期生产劳动和民俗生活中集体创作、口传心授传承下来的音乐样式,根据内容、形式的不同,我们把土家族民歌分成为山歌、风俗歌、小调、劳动号子、儿歌等几大类。民歌文化是社会文化整体中的一个面相,从艺术文化的角度来说,民歌的群体性表现在它是一个协调人们的创作、表演和欣赏方式的文化角色集合体。或者说是人们在进行上述活动时所必须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11](p17)土家族民歌对于演唱者来说,是环境选择的直观感受,通过于自己的二度创作,达到表意抒情的目的和效果,实现审美价值。如果以抽象的范畴来描述,民歌可以是高亢、优美、细腻、粗狂等词汇,但如果仔细分析到具体的单元上,也许就会失去词汇描述的作用。鉴于土家族民歌范畴的侧重点在于探讨民歌背后的民族文化环境与差异性的人文原因,笔者认为土家族民歌基本范畴的根本任务就是,以民族历史为主线,以人物故事为内容,以环境为取材,在直观上使人可以感受到的具有同一审美表意的歌唱。
很显然,土家族民歌范畴概念的确立与发展,对于土家族民歌生态学研究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从民歌生态学方法论上观察,土家族民歌范畴概念的确立是对民歌特质分析的一种哲学思考,人们对方法论的探讨,使我们对于土家族民歌中普遍存在的精确性与模糊度的辩证关系,逐渐具有了高度自觉意识。受人类学、民族学、音位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启发,土家族民歌生态学研究引用了自然科学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同时建立了适合艺术特质分析的可操作性概念。这种认识论或思维方式的产生,在土家族民歌生态学研究中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也会对我们以后的民歌生态学研究产生事半功倍的作用。
2.土家族民歌生态分析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武陵山脉的高山地带,人口约800万。从自然生态条件来看,武陵山地区森林茂密,野果满山,雨量充沛,河溪交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因此可以说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场所。远古时期,武陵山地区就是土家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材料所证明。据土家族民歌《摆手歌》所述,土家族“八蛮”①最初是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迁徙到酉水流域,留下了不少历史遗迹。湘西龙山县里耶境内土家族传说是八蛮早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而得名,“里耶”为土家语,“里”即“地”之意,“耶”即“开”“辟”“耕”之意,“里耶”即“辟地”之意。从地名学角度看,土家族先民八蛮远古时代就活动于武陵山地区的酉水流域一带。土家族是一个古老且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有着漫长的历史,相继经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各个朝代,从五代到梁开平四年清代雍正年间,先是羁州后是土司政权的彭氏世袭领地,经历“改土归流”的二百年到全国解放。土家族经历了漫长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业绩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
由于居住地型的原因,土家族居住的地方多为依山傍水,后面靠山,前有流水,而且多是聚族而居,少杂他姓。有的村寨,山高谷深,村寨相望,鸡犬相闻,呼唤可应,但一上一下,相距十多里,有的村寨在高山密林之中,野猪与家猪同眠,家狗与野狗同嬉。甚至有时猴子会进屋翻鼎罐,开碗柜,做偷吃饭菜之事;在武陵山地区的土家族村寨,这样的事司空见惯。武陵山地区的土家族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节日,每逢正月到元宵节前,都要举行摆手活动,唱摆手歌、跳摆手舞,这是土家族大型的祭祀祖先的活动,土家族的宗教文化很深厚,他们信奉祖先信奉神灵,每家堂屋的神龛都有敬供祖先的神位,过年过节都要敬奉祖先,其中正月、七月,从初一到十五,早晚都要焚香敬祖,其余都只在初一、十五两天,焚香敬祖。[12](p114)解放前,由于交通闭塞,生产力、生产资料的落后,又由于封建统治,国民党反动派兵匪的残害,致使土家族生活水平很低下。
武陵山区土家族民歌浩如烟海,主要有山歌、小调、情歌、灯歌、儿歌、号子、风俗歌、时政歌、劳动歌、盘歌等,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表现了土家族人的性格,具有鲜明的土家特色。土家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一万余年的古人类化石演绎着古代蛮夷人群的生存图腾。刀耕火种沿袭了数千年,高山峻岭成了人们生存的障碍。为了追求幸福、自由与征服自然,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高兴了对着大山吆喝,愤怒了对着河流呼喊,久而久之吆喝成了美妙的乐章,呼喊成了动听的旋律,民歌成了土家族人舒心的感情释放。于是,高亢悠扬的山歌破空而来,委婉柔和的小调穿山而来,激越雄浑的船工号子踏水而来,欢快活泼的灯歌随舞而飞,昂扬的薅草锣鼓歌随风而飘。“一人歌唱万人和”、“村村寨寨都是歌”。唱起这些民歌,人们就会感受到先民们狩猎、生产的艰辛,体验到人类的艰难和团结的可贵,听着这些歌声,人们就会被它那古老神圣、变化多端的艺术魅力所陶醉。千百年来,土家族民歌传递着土家族人民的喜怒哀乐,表达着土家族人生生不息的爱的理念。走进土家族民歌,如同走进一个茫茫无边的歌的海洋。在这里大山长的是歌谣,溪涧流淌的是歌谣,村寨传出的是歌谣,那各种不同的曲调中流动的音符无不显示出土家族民歌永恒的魅力。
五、自然科学量化分析的方法对土家族民歌研究的作用
民歌研究引进了自然科学(生态学、物理学)和社会科学(语言学、音乐学)的方法论,顺应民歌研究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当代艺术和科学发展的总趋势。之所以要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是因为我们所确立的研究目标,不能靠传统的经验总结,更不能靠臆测,而应通过实地考察,进行相对精确的测查、计量,再经综合分析,探讨出科学规律,才能达到。[13](p32)因此,笔者认为,对土家族民歌研究的探讨,既顺应了民歌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应顺应当代艺术与科学发展的总趋势。
(一)土家族民歌研究需要自然科学量化分析
土家族民歌研究在实践中已经证明,在研究民歌具体现象,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如果孤立地对民歌进行研究分析,然后不假思索地将分析结果简单融合,妄想从中得出整体性的结论,这样的做法难以想象会达到什么目的。显然,这样做没能很好地探讨出民歌实质特性。土家族民歌是一门集体创作的艺术形式,美感是高度综合的,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它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所以,我们对土家族民歌的研究、分析、统计、录音录像、测查等等,决不能简单化。比如说对于土家族民歌唱腔分析,人们积极引用自然科学量化分析,可以也应该对其进行物理、数学或生理学分析。在这里,笔者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就此把土家族民歌艺术还原为数理化的精确描述,这种分析方法有悖于民歌研究的本质,也不能说其就是“科学化”、“合理化”。土家族民歌研究,重点是研究民歌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要特别注意在分析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中去考察各种文化行为,同时还得注意民歌本身的活性结构。从审美的角度分析与研究,对于民歌欣赏的研究必须与研究其它心理现象一样,应尽量克服主观同客观相割裂开的绝对化倾向。
(二)研究方法应有可操作性
土家族民歌研究在不排除基本逻辑构思和逻辑推断的情况下,应把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放在可操作、可测查的经验事实上。研究的结论是否合理、正确,但结论必须在分析考察之后才能做出,在研究过程中,假设的证实与否决都是非常有意义等。从可操作性考虑,我们研究土家族民歌与环境相互联系时,都必须仔细研究分析出可能测查到的因子。所谓因子指的是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些因子或者说是文化元素都应相互独立,统计出的总和必须能概括研究对象的总体效应。研究方法上应该遵循,实验从局部开始,逐渐向纵深展开。
(三)研究过程中注意共时性与定量、定性的描述原则
研究土家族民歌与其环境的具体关系时,必须弄清民歌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合部、层次与侧面,不能将它们含糊混杂地进行比较,不仅要注重对其共时性关系考察,还要注意传承、变迁、生灭、分合、兴衰、演进等历时性变化,更要研究与分析不同环境因素对文化因子的作用方式、影响程度,比如同步性、积累性等等。对土家族民歌生态学及其一些经验事实的分析总结,不能采取抽样的方式泛泛描述,应根据实际操作对象的特点,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定量、定型、定序的分析与描述,切忌过于简单化。当然,民歌生态因子的分解与确定还需要在测查研究中进一步证实,有的研究工作开始只能是假设性的。有些民歌生态因子与客观现象不易于直接测度或定型、定序,应该考虑用某种模式将搜集到的资料化为某种数值,类似心理学和生理学上所阐述的“量化度”,如果遇到像这样的现象与模式,都可依据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定。
(四)应对民歌研究结论作精确处理
土家族民歌研究引用与借助了大量文化生态的学术概念,如“生态灾变”、“生物制衡”、“文化适应”、“生态环”等,我们用这些名词来解释土家族民歌与环境因素关系的诸多现象。介于土家族民歌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在具体研究中,要求我们必须注意精确性与模糊度的结合,也就是把“或然率”与“因果律”进行交叉认识的思维方式。假设,我们把土家族民歌中的一些模糊现象当作一种绝对的精确性处理,即使理论上可行,但也会失去其蕴含的活力。民歌与环境的关系,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它们往往不是单线条的,而是交错复杂的网络,因此应对民歌研究结论作精确处理。考察它们历时性变化时,不能局限于线性变化关系,不一定会遇到平衡态和单解质。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中,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兴衰与演化,诸如土家族民歌所有导向民俗、祭祀、娱乐、交往、战争、禁忌等等的行为,根据民族文化内部逻辑发展起来的无意识选择原则转化为一致的模式。可见,文化模式与民族生境都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体系,由民族文化维系和生态环境规约的土家族民歌同样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共同聚合体系。
六、文化生态视阈下土家族民歌研究的价值认识
土家族民歌是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中宝贵的元素之一,在土家族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文化发生学来说,它的部分内容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古根;从艺术学来说,它是中国民族音乐的“活化石”。民歌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以其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理论体系出现,意味着人们认识民歌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通过对土家族民歌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和探讨,寻求一条能够清晰阐释民歌意义的路径,因为民歌意义有不确定性,人们把民歌与人类环境有机地连接上了,这是一个质的探索与尝试。实际意义上,民歌研究受到其它学科的启发,在吸收其它学科研究成果的同时,形成了多样化的、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研究领域,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理论意义上讲,我们从土家族研究、民歌研究与生态学研究中开拓自己的独特领域,这种理论创建有助于推动民族文化与人类生态的协调发展,推进民歌生态学学科建设的完善。我们把土家族民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探索它不断发展和组合的规律,指导民族文化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服务于人们文化需要,丰富人们文化生活与艺术享受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注释
①“八蛮”是土家族八个部落的俗称,因其共有八个部落或八个峒而得名,故又称“八部大王”。据土家族人世代相传,远古时代,土家族共有八个部落,各部落均有各自的首领,八部落的首领分别叫:熬朝河舍、西梯佬、里都、苏都、那乌米、农比也所耶冲、西河佬、接耶费耶纳飞列那。八蛮在武陵山土家族地区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1]周耘.中国传统民歌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
[2]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17.
[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3.
[4](东汉)赵晔撰,吴庆峰点校.二十五别史之吴越春秋[M].济南:齐鲁书社,2000:128.
[5]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79.
[6]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5.
[7]熊晓辉.湘西土著音乐丛话[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22.
[8]熊晓辉.土家族三声音列民歌形态研究[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1,(1):7.
[9]彭继宽,姚纪彭.土家族文学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32.
[10]熊晓辉.湘西土家族民歌旋法探微[J].民族音乐,2009,(1):31.
[11]陈铭道.书写民族音乐文化[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17.
[12]熊晓辉.湘西历史与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4.
[13]资华筠.舞蹈生态学学科阐释[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3,(3):32.
J607
A
1671-6469(2016)-04-0001-10
2016-04-06
熊晓辉(1967-),男,湖南凤凰人,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音乐、音乐人类学、钢琴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