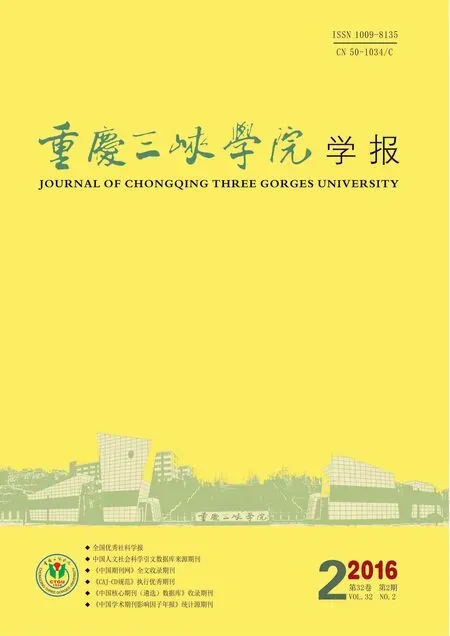论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的地方文化建设和事务管理
李良品 王 媛
论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的地方文化建设和事务管理
李良品1王 媛2
(1.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涪陵 408100)(2.长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重庆涪陵 408100)
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将主动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和日常事务管理视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在地方文化建设中,他们的重要贡献在于教育机构的修建、各类人才的培养、地方志书的撰修、礼仪教化的培育;在公共事业管理方面,他们在灾荒救济的实施、慈善事业的投入、公共工程的兴建、清末团练的举办等方面功绩非凡。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这些重要的社会职责,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参政,进而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明清时期;云南;绅士;地方;文化建设;事务管理
明清时期是我国绅士阶层发展相对成熟的时期,特别是在清代,伴随着皇权与中央集权的衰弱,绅士阶层发展达到高峰。清朝中叶以后,绅士阶层在社会事务,尤其是在基层社会事务中的权力和影响逐渐扩大,这也符合皇权和绅权关系的弱强变动规律。明清时期云南绅士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主动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和事务管理,进而控制乡村社会。
一、明清时期云南民间绅士阶层的构成、性质与作用
何谓绅士?目前学界是见仁见智。费孝通、吴晗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或认为,“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者是官僚的亲亲戚戚”,或者说,“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1]王先明在《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中认为,绅士是“一个处于封建官僚之下、平民之上的独特的社会阶层。”[2]张仲礼则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的,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功名、学品和学衔都用以表明该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官职一般只授给那些其教育背景业经考试证明的人。”[3]1应该说,张先生的观点在学界更具代表性。
(一)云南民间绅士阶层的构成
从上述观点看,专家学者们都把科举功名的获得者看作是绅士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对是否包括在职的官员、括生员、职官在乡的子弟、居乡的地主及其它具有较多财富和较高社会地位但未有任何功名职衔的地方精英分子等,还存在着较大分歧。杨银权在其博士论文《清代甘肃士绅研究》中将那些从最低级功名获得者的生员以及业儒者至进士都纳入绅士阶层,计包括业儒者、生员、监生、贡生、举人、进士等[4]21-41。王先明在《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中采用分类列举的方法,把绅士分为五类;吴佳佳则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把士绅归纳为八类[5]。无论怎样分类,明清时期云南那些科举功名的获得者都应该是绅士的主要成员。
在社会结构中,绅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同国家之间有着双重关系,一方面他们用自身力量支撑着国家,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国家的各种政策所控制。从明代中后期开始,云南绅士阶层在云南社会舞台和历史舞台上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当绅士在朝为官时,称为官绅;捐来的生员、举人,则称为商绅。绅士既可在朝为官,也可是候补或者退休的官员。到晚明时期君主专制力量减弱,绅士成为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逐步取得了农村中的控制权。尽管清代前期中央王朝通过各种手段压制绅士力量,但在太平天国势力强大后,清政府还是不得不仰赖绅士阶层来控制危机四伏的局面,而后绅士的权势则越来越大。
(二)云南民间绅士阶层的性质
明清时期云南的绅士阶层作为各级官员的最主要来源,当他们或通过科举考试,或通过捐纳、赏赐、恩荫、军功等挤入统治阶层行列之后,就代表着皇权实现对乡村社会百姓的直接统治,从这个角度讲,这些官员政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固与否;而那些没有挤入统治阶层行列或者从官场退出的绅士,他们同样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在明朝中后期及清代,除康乾盛世外,其余时间均属于多事之秋,统治阶级的时间和精力根本无暇顾及对云南乡村社会的治理,并且统治阶级也不可能真正对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统治,于是作为“四民之首”的“乡绅”、“绅士”们就成为实现代替统治者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的最佳人选,绅士阶层便充当了“官”和“民”之间的桥梁和中介,这就是明清时期云南民间绅士阶层的性质。正如张仲礼所言:“绅士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职责是,他们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地方百姓之间的中介人。”[3]54-58具体而言,一是在权力方面,绅士阶层是“官”和“民”之间的桥梁和中介。正是由于绅士阶层这一特殊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在云南乡村社会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在清朝中后期社会秩序不稳定的基层乡村社会里,他们的权力和作用甚至比代表皇权的官员的权力还大,当然,他们比乡村社会的其他平民享有更多更大的特权。二是在身份方面,绅士阶层仍然是“民”。无论是没有挤入统治阶层行列的绅士还是已经从官场退出的绅士阶层,他们虽然贵为“四民之首”,并且在封建社会里处于官和民的中间,充当着中介人的角色,但他们毕竟还是属于“民”的阶层。三是在移风易俗方面,绅士阶层是乡村社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作为云南乡村社会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绅士阶层不但享有比较高的特权和待遇,而且对国家事务、家乡社会事务有着其它阶层所无法代替的独特作用。明清时期云南乡村社会的广大乡民识字不多,判断力差,很大程度上只能听取本族、本乡绅士阶层的决断。因此,绅士阶层在履行一些职责的时候,无形之中又在控制着乡村社会。
(三)云南民间绅士阶层的作用
如前所述,绅士们一旦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大多会选择回归故里,颐养天年,充当乡村社会的领袖人物,发挥其绅士的作用。对于回归故里的绅士的特殊作用,学界多有论述,并充分肯定他们的作用与成就。王先明先生就曾经论道:
在地方政府——士绅——村民的权力网络中,士绅在完成国家权力对村落共同体的社会控制职能方面,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在乡村社区里,士绅是个管理社区的群体,执行着许多社会任务。如充当社会领袖,组织社区的防卫,调解人民的日常的纠纷,关心人民生活,为社区人民树立楷模,以及帮助人主持婚丧事宜等。……士绅并不象官员那样拥有钦命的权力,却享有基层社会赋予的天然的实际权威。“世之有绅衿也,固身为一乡之望,而百姓所宜衿式,所赖保护者也。……绅衿上可以济国家法令之不所不及,下可以辅官长思虑之所未周,岂不使百姓赖其利,服其教,畏其神乎?”[2]61
由此可见,绅士作为乡村社会的特殊力量,享有比较特殊的权力,有着高于其他平民百姓的社会地位,掌控着地方文化知识的话语权,其作用巨大。如建水县的王伟,为道光时举人。凡筹赈、育婴、修理河堤、仿照古代增加学生补助等各种善举,他都勉力倡成。知县重其贤能,曾几次保荐他出任官职,他都以父母年老,推辞不就[6]224。
二、民间绅士阶层的地方文化建设
明清时期,在文化教育事业并不发达的云南,绅士群体不仅是唯一享有文化知识的群体,而且在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方面也是发挥主导作用的群体。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云南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不仅离不开绅士阶层的积极参与与大力支持,而且对于绅士群体自身而言,这些地方的文化建设工作也被视为绅士阶层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
(一)学校教育的贡献
作为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执行者和代理人,士绅对学校教育和儒家教化的关注和执行,被视为士绅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这些具体的事务包括:创立和经理教育及文化机构,包括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的创办、运作,以及维持这些文化机构设施正常运转所需费用的筹措。所有这些教育和文化机构的负责人既需要经理能力,又需要文化才能。所以,只有士绅才有资格为其提供服务,于是,创建并经理这些机构者基本都是士绅。事实也一再表明,这些事务,均离不开地方士绅的介入、参与,甚至在各项事务中发挥实际的领导作用[4]160。
1.绅士阶层创建学校。明清统治者为了在云南乡村社会极力推行封建教化以达到加强对基层民众的控制与约束的目的,除了宣讲圣谕外,学校教育也是加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正是因为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了封建教化以及学校教育在维护良好社会风俗上的作用,所以,明清统治者大力提倡绅士阶层积极创办学校。特别是在中央朝廷和地方官的大力提倡下,绅士们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学校教育机构的创办之中。在云南,绅士办学始于明代。禄丰人王逵,解官归,建祠奉先,设塾训俗。复出赀创建学宫,置文明书院教授生徒,自是人物焕然,科第不绝[7]363。天启年间晋宁贡生苏民生,家居时,建馆置田,以教孤寒子弟,乡人德之[7]365。嘉靖年间赵州进士邹尧臣,丁艰归后设义田、立家塾,宗族德之[7]377。这些绅士或修书院,或立私塾,虽然规模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但他们毕竟是作为绅士阶层创办学校教育的先驱。虽然为数不多,但并非意味着无绅士阶层办学。时值清代,绅士阶层兴建学校之例则不胜枚举。如:光绪年间宜良举人崔寿仁,世居治南乐道村,倡义学,置学田为经久计。后人得因其基础改办小学校者,寿仁之力也[7]374。罗次贡生张□,授课之余,兼营公务。首建城池、文武庙,次及县署、学署、明伦堂、文昌宫、奎星楼、关圣宫,不十年而悉复旧观[7]374。定边县诸生汪于泗。首倡建学,不惜己赀,乡人矜式[7]426。通过地方志和相关文献记载,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学校教育机构的创办过程中,发挥实际作用的主要是士绅,即便有时是地方官捐资,但实际主持学校创办工作的仍然是士绅。当然,这里的情况也较复杂,他们或掌管学校的创办,或支付全部的资出,或由他们出面去筹资,但无论哪种方式,绅士在学校创建上的作用都不容忽视[4]162。
2.绅士阶层培养人才。在“绅”出仕为“官”,“官”退为“绅”的封建社会里,绅和官的关系比较特殊。办事自然比一般百姓方便,他们在为地方官员的种种作为和教化等的施行方面往往乐此不疲。在云南省现存的地方志中对这方面的记载颇多,如清代河阳人郭晋,为乾隆时举人。致仕归乡之后,“尤喜培植人材,凡郡人之贫不能就试者,悉助之资,一时寒唆多所成全”。[7]398嘉庆年间宣威举士朱光鼎,“屡主书院讲席,其教人以忠恕为要,不拘拘于章句。县属与蜀接壤,风俗多豪侈夸诈,光鼎导以敦朴诚笃。接待诸生,劝善规过,如待家中子弟,期以维纲常、厉廉隅,邑人敬而爱之”。[7]407尤其是一些绅士退居乡野后,他们期盼立功、立言,往往更注重培养人才。在云南的地方志书中,对这方面的记载也十分丰富。明嘉靖举人顾天佑“经学授徒”,“杜门讲业”[7]362;道光年间晋宁举人苏复,主书院讲席,因课训甚勤,最后实现了“受业门下者辄数十百人”[7]372的教学效果。这无疑是绅士阶层在地方文化建设上发挥的作用。
3.绅士阶层捐资助学。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经济较落后,这里的绅士阶层相对比较贫困。但他们对于读书应试、士子膏火费、捐资建学校等方面却大力支持、积极筹措。在具体资助方式上,除了直接给与应试者银两外,他们还常常通过建立市房,通过取租,或者捐助资金,通过发商生息的方式来作为对应试者的援助[4]168。如康熙年间阿迷举人伍士祺,告归里后,凡遇“乡会两试,置有卷金以赠行者,故乡党尤称之”[7]387。又如石屏人杨桂森,既解官归,……“其于石屏故里,则捐送举人会试卷金田、玉屏书院膏火田,至今学校犹食其利”。[7]389-390这实例都体现了云南绅士作为文化人代表对本地区教育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关注和重视。
(二)文化事业的参与
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作为维护儒家伦理纲常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除了兴建、修建学宫、社学、义学、书院、私塾(包括义塾和族塾)等直接的教育机构外,他们还乐于参与其它文化事业的建设。
1.修建考院、贡院、文庙等教育机构及文化名胜。如宾川人熊明,建议修复文武庙,乡人难之,乃独输银贰千两、谷百余斛,鸠工庀材,力为营度,卒用落成[7]381。万历年间姚安所举人陶希皋,归里后,养亲课子。修黉宫,捐资倡首[7]395。沾益人贡生孙文达,多善举,倡修文庙,移建奎星阁[7]408。由此可见,修建与教育有关的考院、贡院、文庙等机构以及文化名胜等,都是绅士阶层关注地方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涉及有关儒家伦理纲常设施的兴建和维护方面,云南绅士阶层的作用不可忽视。
2.地方志书的撰修。地方志书编撰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重视文化控制的明清政府都极为重视地方志书的编修,三令五申督促全国各地编修方志,从而全国各省、府、州、县的方志编修蔚然成风,形成了地方志书编修的昌盛时期。在明清两代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下,作为享有文化话语权的绅士阶层自然就成为各地方志编修的主力军。于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方志编修也成为地方构建文化知识体系的主要传承形式,并且作为一种文化理念渗透到各行政区。作为当地绅士,他们不但是本地的文化精英,而且他们熟悉本地的情况,便于调查,能够掌握比较可靠的素材。在地方志书的编修中,绅士乐此不疲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愿意服务家乡,千古留名;二是他们为能掌握地方文化的话语权而自豪。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载:嘉庆年间宣威举士朱光鼎,……为文贯串经史而有风韵,道光甲辰承修《宣威州志》……宣威人孙绍康,著有《宣威州志》[7]407。昆明人倪藩,参与修《云南通志》[7]374。蒙化人姚贺泰,与徐时行续修《蒙化直隶厅志》[7]427。河阳人郭锡恩,参互考订知府李熙龄纂修的《澂江府志》,不厌周详[7]398-399。可见,这些绅士通过或自修,或受地方官聘请,或与他人合修,或参修,或“参互考订”的方式对清代云南地方志的修纂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无论哪种形式,均说明地方官只有与当地绅士阶层有机合作,才能使政令顺利实行,政绩卓然,这是由明清时期社会的政治体制以及绅士阶层的依附性特点决定的,即官不能离开绅而有所作为[8]25。
(三)礼仪教化的培育
儒家思想认为礼仪教化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方法[9]161。因此,明清时期统治者在其谕旨中,一再强调“士风”对“民风”的相率作用。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谕旨中,要求绅士敦品励行,表率乡民外,朝廷形成了圣谕十六条,并作为制度在全国各级学校推广。《圣谕十六条》是清代中央政府对士绅的一个全面要求,包括忠孝、息讼、士风、学风、法律、风俗、赋税、治安等各个方面。它要求士绅在以上所有方面都能够起到表率作用,从而起到加强统治的目的。其中,“明礼让以厚风俗”就是要求士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乡民作榜样,从而培养良风美俗。雍正年间,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士绅的约束,达到对乡民的表率作用,从而实现巩固统治的目的,特别颁布圣谕。如雍正四年(1726)上谕说:“为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属编氓,皆遵之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庠之选,其所言所行,俱可为乡人法则也。故必敦品励学,谨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后以圣贤诗书之道开示愚民,则民必听从其言,服习其教,相率而归于谨厚。”[10]正是在外有统治阶级的提倡和要求,内有绅士阶层立德、立言、立功心理的驱使下,明清时期云南的绝大多数绅士都遵守着这些“圣谕”要求,并为当地良好礼仪教化风气的培育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云南一些保存至今的地方志中,仍有对绅士阶层引领的良好士风的记载。
当然,科史哲领域的情况较为复杂,这是因为科史哲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本身有交叉,因而有一部分研究内容被SSCI和SCI同时收录。为了客观地介绍科技史学和科技哲学期刊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界定科史哲学者的学术水平,以便更好地了解世界科技史学和科技哲学方面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笔者将结合自身的科技史学学科背景,借助2007~2016年期间WOS数据库的科技史类和科技哲学类英文期刊数据,借助社交网络和知识图谱软件SATI和NETDRAW,将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结合,分类反映国际科技史学和科技哲学学科的刊物、学者、机构分布情况以及整体知识架构。
云南士风的纯朴,一方面与明清统治阶级的提倡有关,另一方面与绅士阶层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密切相关。同时,由于这些绅士有着高于普通百姓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因而,他们的言行往往对乡村社会百姓的日常生活、习惯、心理及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下所形成的特定的社会习惯,就是一个特定地方的良风民俗。在现存的云南地方志的“人物志”之“乡贤”或“德行”中,有关绅士对儒家规范严格执行的记载俯拾皆是,如云南太和人周榛,于同治年间“尤殷殷以兴学校、振风俗为先”;[6]235-236云南罗次贡生张翰,他居住在该县属牛家营时,乡人有占行悖谬者,他“必严厉以绳,男妇皆敬畏之。以是,乡俗淳美,至今犹有遗风焉”[7]374;河西同治年间举人王善量,“奖藉后进,敦尚朴学,十余年间,士气复盛如承平时”[7]392。上述这些绅士不仅严格遵循儒家规范,使他们成为乡村社会民众学习的典范,而且由于他们的率先垂范和礼仪教化的培育,改变了本地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
三、民间绅士阶层的地方事务管理
明清时期,皇权势力要想到达乡村社会阶层,实现对整个云南的有效治理,就必须依靠地方官和地方绅士阶层来实现[4]175-176。因为在广袤的云南,地方官的势力也只能到达县级,对于县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地方官员的控制力相当有限。中央政府要想使皇权深入到云南乡村社会,实现对乡村社会民众的有效控制,官方势力必须借助居于乡村社会绅士阶层的襄助。在“士与民亲”的前提下,地方绅士阶层是当地民众最信得过的人,基于此,居于云南乡村社会的绅士们,在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其作用是无可替代,诸如“监督公共事项的财务、兴建和运作,组织和指挥地方团练,建立和经理地方和宗族的慈善机构,以及在和官府打交道时代表地方和宗族的利益”。[6]42总的来讲,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在地方事务管理中主要从事三方面的工作。
(一)灾荒救济的实施
明清时期,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云南乡村社会,广大贫苦农民几乎没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每遇较大灾荒,都有大批农民或流落他乡,或转死沟壑,或揭竿而起。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乡村社会民众生计和国家税收,而且危机社会安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明清统治者高度重视荒政工作,除了要求官吏定期奏报各地各种自然气候情况、庄稼丰歉情况以及赈灾情况之外,清朝统治者还督促编纂荒政专著(如《筹济篇》、《康济录》、《荒政辑要》、《赈济录》等)和救荒手册(如《宦海指南》),在当时形成一种地方官吏必须以荒政为己任的社会风尚,有力地促进了清代救灾事务的发展。为防御各种自然灾害,明清中央政府和云南的地方官员十分重视抗灾减灾工作,不但采取诸多积极性措施来防灾、备灾,而且在临灾赈济、灾后补救等方而实施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其中包括预备仓、常平仓、义仓和社仓等在内的备荒仓储措施[4]183。在明清时期,云南乡村社会的一些绅士,他们在面对义仓、社仓的粮食储备时,经常倡捐或主动捐谷。而面对频繁的各种灾害,除了由地方官府举办的赈灾救济之外,在实际的经营中大多是由地方绅士负责。通过地方志的记载,著者发现,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参与的地方灾荒救济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济贫穷,或直接救助其人粮食、衣物、药品等财物,或救济其人解决贫穷和饥饿的方式(如给耕具和种子);二是济灾荒;三是济战乱,如:万历年间昆明人王希尧,每岁终,以钱米济乡党之贫乏者[7]364。昆明人刘清元,性好施与,凡戚族中有孤嫠者抚恤之,贫不能自存者假贷周济之[7]373。光绪年间太和进士范宗莹,岁饥,则自请发仓以贷贫民而躬自料量,全活者众[7]382-383。蒙化贡生周文郁,赈饥抚孤,赡济贫困,助婚丧赀尤慷慨不吝焉[7]427。在救济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传统美德的情况下,绅士阶层对各种灾荒实施救济之善举,不但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赏,而且这种社会影响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11]。
(二)慈善事业的投入
明清时期的云南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十分落后,乡村社会有大量的贫民不但得不到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粮食、衣服等生活资料,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死后会因为贫穷等原因无法入葬。鉴于此,在地方官员对于慈善事业只是起一个组织者和审批者作用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的慈善事业与其他所有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一样,大多由一些有经济“殷实”的绅士来组织和经营。云南绅士参与地方慈善事务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们或助人婚嫁,或助人丧葬(包括施棺木、设义冢等),或帮人育婴。这些慈善之举,不仅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中乐于助人的良好传统,而且更体现了中国绅士群体“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贵品质。如正德年间楚雄举人何鑑,后归居乡,亲戚贫不能嫁娶者,捐资助之[7]394。嘉靖年间晋宁举人康金,及致仕家居,赈贫助葬[7]362。万历年间保山举人赵之炎,致仕归,捐建养生院,置义田义地,收赎被掳子女,人皆德之[7]420。昆明人官鏸,与邑绅李芬、保先烈、倪应选经理卷金,恤贫恤嫠,施棺诸会,均竭力捐办,井井有条[7]395。会泽贡生李均,好施与,乡里有急难者,辄资之。倡惜字、掩骸诸会[7]422。可见,在经济落后的云南,绅士群体对地方慈善事务的资助和救济是多方面的,以上所举只是云南省地方志中所载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并非明清时期云南是乡村社会绅士阶层关注地方慈善事业的全部。但这些事例足以体现绅士阶层对地方慈善事业的积极关注程度。这不但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国绅士阶层一贯的优秀品质和传统,而且有利于云南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三)公共工程的兴建
(四)清末团练的举办
团练制度始于嘉庆初(1796—1804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成熟运作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在清朝末期,清政府允许甚至大力支持乡村社会举办团练,其目的是期望借助民间的力量来遏制反对清朝统治的各种势力,它反映了清朝统治力量的急剧衰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和国家财政紧张的客观事实。
由此可见,清代云南的绅士阶层随着清朝统治势力的衰微,在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借助士绅的襄助来维系其风雨飘摇的统治时,“王权”和“绅权”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与衰微而发生的此消彼长。面对在这种情况,在清廷的允许下,在绅士或组织团练或指挥团练的影响下,云南的团练也在各地大规模兴办起来。据载:咸丰年间晋宁进士李鼎,会滇乱,同黄侍郎琮办理团务,以忧劳卒于军中[7]373。道光年间永北拔贡段永珍,癸丑勤理城丁,丙辰协办团防,颇形劳瘁[7]428。清代后期云南绅士阶层举办或参与团练,则与西南民族地区其他地方的情况大同小异。
四、结 语
明清时期云南乡村社会的绅士阶层的职责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地方文化建设、地方公共事务等方面,并在这些方面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社会职责。张仲礼先生所说:“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社会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与贡院等。”“同时,绅士作为本地的代言人,常常去说服政府接受他们的看法。”[3]54-58当然,绅士阶层自觉不自觉地在承担这些重要的社会职责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参政,进而控制乡村社会。
[1] 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2]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3] 杨银权.清代甘肃士绅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9.
[4] 吴佳佳.“绅士”的内涵[J].安徽文学,2006(8):48-49.
[5]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6]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7] [民国]龙云,卢汉.新纂云南通志:点校本·第八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8]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9] 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 [清]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83[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11] 李良品,周娥.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启示[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5(4):95-99.
(责任编辑:于开红)
The Theory of Loc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ransaction Management of the Gentry Class in Yunnan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Liangpin1WANG Yuan2
王 媛(1995-),女,重庆涪陵人,长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历史学2014级学生。
(1. Research Center for Wu Jiang River’s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2.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History,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gentry class in Yunnan took the initiati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 management of daily affai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e, their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were the education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talents training, local annals compilation and etiquette education cultivation. In public utilities management, they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disaster relief, charity and public works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militi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gentry class in Yunnan assumed these important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hose main aim wa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ffairs, and finally control rural society.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unnan; gentry; loc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ransaction management
D819
A
1009-8135(2016)02-0100-06
2015-11-06
李良品(1957-),男,重庆石柱人,长江师范学院教授,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研究西南民族历史文化。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批准号:11BMZ0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