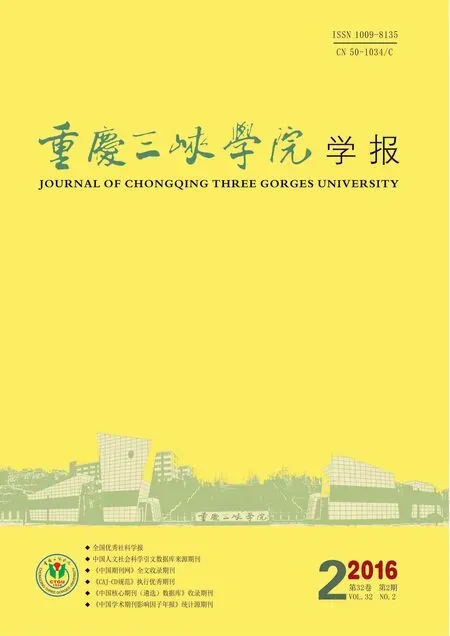高校英美文学课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苏冬凉
高校英美文学课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苏冬凉
(泉州师范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大学生必备的能力之一。如何利用高校英美文学课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已逐步成为课改的首要问题。文章以吴伟仁教授所编的高校英美文学教材美国文学部分为蓝本,提出以开放性问题主导教学、教材作品与同名改编电影对比教学两种模式,以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开放性问题;同名改编电影;批判性思维
一、引 言
黄源深教授指出,外语系的学生易患思辨缺席症。“思辨的缺席直接影响人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影响人的素质。”[1]12000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指出,要加强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并在教学中正确处理好语言技能训练和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作为高校英语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英美文学课旨在通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授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理解与欣赏英美原著的水平。然而,随着新大纲的出台以及近几年对如何提高高校英语专业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已然成为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改革的首要问题之一。以往的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主要是“作者介绍+历史背景+作品选读+人物性格和主题分析”,这种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使学生被动地接受信息,思维倦怠,难以提高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着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我们建议建立以教师为指导,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式教学模式,打破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授课模式,为学生创造一个能自主学习、充分展示自己才艺的舞台。”[2]2
要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只能采取隐形教学的方法,即在专业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文章主要以吴伟仁教授编的高校英美文学教材美国文学部分的内容为基础,提出以开放性问题主导教学、教材作品与同名改编电影对比教学两种模式,同时对相关的例子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笔者认为,这二者均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二、以开放性问题为主导展开启发性教学
美国长期从事批判性思维研究工作的尼尔•布朗教授和斯图尔特•基利教授在2013年出版了《学会提问》一书,此书被奉为批判性思维领域的“圣经”。书中指出,批判性思维内容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3]3。
第一,以西方文学理论为中心展开对教材作品的提问和总结。在美国文学中,可对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进行生态批评解读。1845年到1847年,梭罗住在瓦尔登湖附近的小木屋里,过起了亲近自然的生活。梭罗深刻意识到科技和文明的负面效应,他曾这样批判“铁路”:“如果一批人能在铁轨之上愉快地乘车经过,必然有另一批不幸的人是在下面被乘坐被压过去的”[4]162。梭罗的态度与为获取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不惜破坏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及社会生态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也可让学生对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进行女性主义解读。《红字》以17世纪的清教主义思想为背景,探讨了男权社会中主人公海斯特在与人通奸之后所遭受的一系列惩罚。小说描写了海斯特的坚韧和勇敢,展示了女性的魅力和能耐,赋予小说深刻的女性主义思想。同时,可用后殖民主义解读哈丽雅特•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中的白人是文化霸权代表,而黑人则成了失语的沉默的他者。在白人眼里,黑人是可以随意买卖的财产。谢尔贝太太对汤姆说:“等我筹齐了钱,我就会把你赎回来”。[5]32另外,从西奥多•德莱赛的《嘉莉妹妹》可看出人物的文化消费心理。嘉莉妹妹在去芝加哥的火车上认识了风流倜傥的查理,并被他表面的光鲜所吸引——“荷包,发亮的皮鞋,漂亮的新服装,以及他那一副派头,在她心里勾勒出了一个模糊的幸福世界,他是其中的中心人物。这使她乐于接受任何他所做的事。”[5]118等到了芝加哥后,嘉莉妹妹充满了消费的欲望,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最终沦落为别人的情妇。
第二,用对比法对作品进行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和创新。如可将《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童年汤姆与《哈克贝利•费恩》的哈克进行对比。汤姆和哈克都是南部美国传统教育中“坏孩子”形象,但两人本质上都非常善良。相对于汤姆,哈克的角色更具历史和政治意义。蓄奴制的斗争使哈克真正成长起来,而汤姆的成长过程充满了对传统教育的反抗,两人的异同点值得探讨。也可把华盛顿•欧文的《睡谷传奇》中的荷兰人和其它作品中的荷兰人进行对比。在他的其它作品中,荷兰人又胖又蠢,浮夸和贪图享乐;而在《睡谷传奇》中,“骨头布罗姆”是正面的荷兰人形象,他既强壮又有胆识,擅长骑马。“他精于马术,在马背上灵敏矫健得像个鞑靼人,这使他享有盛名。”[4]72另外,可对比沃尔特•惠特曼与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惠特曼和狄金森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两位诗歌革新者,在摆脱旧诗词的束缚、创造新诗形式方面不谋而合。威廉斯说:“迄今为止在诗歌这个人迹罕至的精神领域里,他(她)俩代表了19世纪美国心灵拓荒的最高才智。”[6]18但是两人的诗歌风格和诗歌主题却不尽相同。惠特曼侧重从宏观外向的角度表达对美国民主和自由生活的热爱——“高扬风帆的美国人的快舰,冲过了闪电和暴雨……”[5]10;而狄金森则擅长从微观内省的角度表达对爱情、宗教和死亡等问题的看法。
第三,结合文学作品与现实问题启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杜宾斯先生对学生的教育方式值得探讨。杜宾斯先生实行棍棒教育,而且只打瘦小的男生,“他手中的教鞭和戒尺现在很少闲着,至少对那些年龄较小的同学可以这么说。只有最大的男孩子和18到20岁的年轻姑娘才不挨打”[5]43。在小说中,汤姆代表了学校中不听话的学生,而如何对待像汤姆一样的熊孩子成了当代教育的首要问题。显然像杜宾斯先生那样对待学生的方式不会起到教育作用,因此,可以通过这个实例引导学生思考当代教育问题,以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另外,可引导学生对埃德温•罗宾逊的诗歌《理查•珂利》里所隐含的名利和人生问题进行分析思考。理查•珂利“风度翩翩、光彩照人,他富比王侯,谁都盼望有他的福份……而理查•珂利在宁静的夏夜,回家朝自己脑袋放一颗子弹”[5]136。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苦与痛,看淡名利踏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人生正确的选择。同时,罗伯特•弗洛斯特的诗歌《没有走的路》探讨了人生不同抉择的问题,启发学生对人生选择的思考,“树林里路分两股,而我呢——选上的一条较少人迹,千差万别由此而起。”[5]142
第四,就英美文学作品本身提出启发性的问题。在美国文学中,华盛顿•欧文《睡谷传奇》的依卡博德是失败者吗?有读者认为依卡博德是失败者,因为他没有得到卡特里娜的爱,从而失去了继承庞大遗产的机会,在荷兰社区里丢掉了面子。但是后来他到了纽约,当上了一名十镑法庭的法官。通过这个实例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所谓的失败。也可对威廉•福克纳《给艾米莉小姐的玫瑰》中玫瑰的含义进行探讨。标题中的玫瑰在小说中并没有出现,可以引导学生理解玫瑰的象征意义。玫瑰可能暗指艾米莉是南方传统和邦联老军人们心中的玫瑰,也许是象征她的爱情是超越死亡的爱情,从而值得献给玫瑰。另外,可对F•司格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美国梦进行探讨。盖茨比实现他的美国梦了吗?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他不惜从事非法买卖,积累了物质财富,但最终也没能换来黛西的爱情,他在精神上沦陷了。可以利用此事件引发学生对美国梦的思考。
三、教材作品与同名改编电影的对比教学
电影和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以文学为基础改编的电影非常有助于读者对文学的理解。同时,“一部改编自著名书籍的电影比一部由不知名的作家所创作的原版电影剧本拍成的电影更能吸引人”[7]5。在一次新华社的采访中,莫言指出:“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实际上,20世纪美国人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电影产业。电影忠于文学固然不错,但是在改编过程中难免加入导演自己的想法,可让学生对比文学作品和电影的异同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电影《睡谷传奇》(1999年版)由好莱坞导演蒂姆•波顿根据华盛顿•欧文的《睡谷传奇》改编,影片大力渲染了“无头骑士”这一传说,主角名字也用了欧文作品里的人物。小说没有具体交代无头骑士出现的原因,只是说明为何无头骑士没有头——“在独立战争的一次无名战役中,一颗炮弹炸掉了他的头”[4]63;而电影则指出无头骑士是为了找到他死去时被人割下的头颅才不断出现的。不得不说,欧文的小说更具幽默讽刺意味,而电影则更多渲染了哥特式的阴暗和恐怖。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船员与白鲸搏斗的片段。小说侧重描写船员们面对灾难时不同的态度,而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鲸记》(2010年版)删掉了许多细节描写,比如船长的话——“我冲着你这只能毁灭而不能征服一切的鲸,我要和你一起较量到底……”。同时,小说勾画了阿哈比船长半倚半站的轮廓,并告知读者他那条残腿是用“抹香鲸的颚骨加以磨光修整做成的”,而在电影中这部分并没有点出来。小说描述更加生动形象,但电影配以音乐更能让人身临其境,因剧中的高潮迭起而汹涌澎湃。
詹姆斯•库珀的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侧重对友情的描写,1992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则更侧重对爱情的描写。这种侧重点的转移,跟电影的商业化有关。同时,小说中呈现出来的“鹰眼”略带野蛮甚至凶残,而影片中“鹰眼”则更加可爱温和,甚至几乎是完美的。小说中的马古亚比较复杂,除了邪恶,他对柯拉充满爱意,而电影中马古亚完全是邪恶的象征,这也符合电影的一贯手法,好人总是近乎完美,坏人总是一无是处。另外,在小说中,虽然“鹰眼”珍惜跨种族的友谊,但是反对跨种族的爱情。然而,在电影中,他却带头与混血姑娘柯拉热恋,这一点与小说所塑造的形象大相径庭。同时,在小说中,男主人公恩卡斯为了救女主人公而死,而在电影里,柯拉被逼跳崖,恩卡斯为了复仇与杀害自己心爱女子的凶手同归于尽。电影中双双殉情比起小说中的结局更让人惋惜。
电影《汤姆•索亚历险记》(1938年版)还原了小说大部分的故事情节,赋予了小说新的活力。相比之下,小说侧重利用风景描写来烘托人物的心理、情感变化,而电影则更为直观地从人物神态和动作来呈现人物心理活动,使故事情节愈加具体形象。比如书中汤姆和哈克在墓地的画面,小说这样描写:“周围有一道歪歪斜斜的木篱笆……高高的野草遍布整个墓地……”而影片中则少了对风景的刻画,侧重突出孩子在目睹杀人事件后害怕的眼神,让人禁不住为他捏了把汗。同时,电影省略了很多对话和细节,比如小说中提到汤姆看到一个穿戴整齐的孩子,他俩面对面,眼对眼这样相持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汤姆先开了腔:“我能打得过你!”“我倒想见识见识。”而这个片段在电影中没有提及,因“在电影中,暗示就是原则,……电影是省略的艺术。”[8]53
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红字》侧重海斯特的形象在大众面前的转变,而1995年由罗兰•约菲执导的同名改编电影则把中心放在了她和牧师的爱情上。小说的结尾是牧师受不了内心的煎熬,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的罪过后死去;而电影中,牧师在信仰与爱情的取舍方面似乎更加符合当代人的观念,最后他既没违背上帝的信奉,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也勇敢保护了海斯特和明珠,甚至还与她们远走高飞,过上了的幸福生活。
哈丽雅特•斯托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谢尔贝先生,与电影中(1965年版)的刻画一样,都是假仁假义的形象。电影减少了细节刻画,故事情节上也有出入。“小说中许多精彩的议论和抒情,许多复杂的心理描绘,有时是很难表达成画面的”[9]120,电影省略了原小说中伊丽莎在逃亡中的心理独白——“她暗自诧异何以忽然之间自己力气这么大,因为她觉得怀中的孩子简直轻如鸿毛,而且每受一次虚惊,那股鼓舞她前进的神奇的力量便与之俱增”[5]25,这种省略也导致读者无法体会伊丽莎那种强烈的母爱的力量。另外,伊丽莎的儿子在小说中是一个已经稍稍懂事的小孩,而在电影中则是还在襁褓中的婴儿。
F•司格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教材选读第三章描写了舞会的奢华和尼克第一次见到盖茨比的情境,电影(2013年版)中的相关片段将盖茨比城堡每个周末的盛大舞会的奢华场景逼真呈现——舞蹈、音乐、美酒、灯光、甚至泳池……应该说,电影在视觉上下足了功夫,普拉达的华服、蒂凡尼的珠宝,让人赏心悦目,置景极大限度地贴合小说中的描述。小说里盖茨比的出场比较低调,尼克和同桌陌生男子闲谈时,说自己虽被盖茨比邀请但从没见过对方,那名陌生男子“朝我望了一会儿,似乎没听懂我的话。‘我就是盖茨比。’他突然说。”[5]192而在电影中,盖茨比似乎无处不在,不像小说描写的那样神秘,电影的结局也与小说不符。当枪手的子弹穿过盖茨比的心脏,黛西没有像小说描述的那样悄然离去,而是选择了留在现场试图给汤姆•巴切南打电话。这个意外的改编代表了大多数好莱坞编剧解读小说的方式,美化了堕落拜金的黛西和汤姆夫妇,破坏了小说的思想。
四、总 结
总之,以开放性问题为主导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模式,侧重师生之间的互动,给予学生极大的自由权,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电影片段与教材作品的对比教学,引导学生以现代性和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经典文学,拓展学生的思维。“完善我们的思考的办法就是进行批判性思维,也就是说,像思维的教练一样对自己的思想展开批判。”[10]3另外,两种教学方法的特点就在于把主动权交给学生。“开展批判性思维教育,就应该切实转变教师观和学生观,扭转教师主导作用侵夺、替代学生主体地位倾向,把课程实施主体地位和权利还给学生,重建合理‘双赢’的师生关系。”[11]132相信这两种教学手段能有效提高高校英美文学课堂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1] 黄源深.思辨缺席[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7):1-19.
[2] 吕丽塔,张葳,史宝辉.看电影学英美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3] [美]尼尔·布朗,斯图尔特·基利.学会提问[M].吴礼敬,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4] 吴伟仁.美国文学史及选读1[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5] 吴伟仁.美国文学史及选读2[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6] 吴伟仁,张强.美国文学史及选读学习指南2[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7] [法]莫尼克·卡尔科-马塞尔,让娜-玛丽·克莱尔.电影与文学改编[M].刘芳,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8] [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
[9] 王红.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点》——小说与同名改编电影评析[C]//张冲.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0] Parker, Richard & Moore, Brooke. 批判性思维[M].朱素梅,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11] 刘义.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研究:概念、历史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张新玲)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b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SU Dongliang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In the past decade, as higher education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n universitie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lass has now become a matter of prime importance for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urriculum reformation. Based on the demonstrating teach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 with the textbook compiled by professor Wu Weire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open questions and a comparative teaching of textbooks and adapted movies are helpful for improv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pen questions; adapted movies; critical thinking
G64
A
1009-8135(2016)02-0125-04
2015-11-23
苏冬凉(1979-),女,福建泉州人,泉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英美文学。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的重点课题“批判性思维下的高校英美文学教学”(项目编号:2015CG2346;立项批准号:FJJKCGZ15-07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