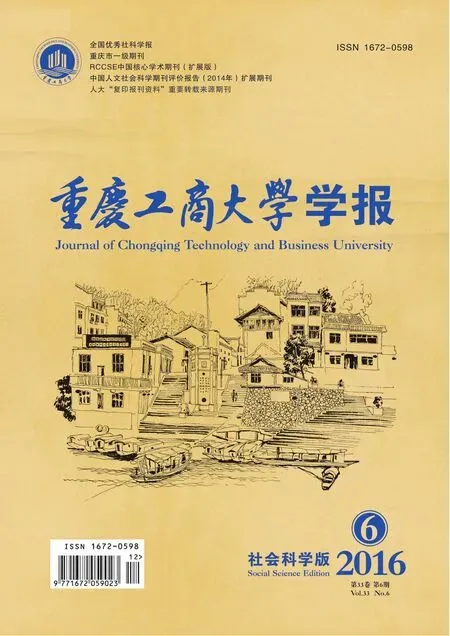从日本歌论来看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对和歌的影响*
徐 凤
(曲阜师范大学 翻译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从日本歌论来看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对和歌的影响*
徐 凤
(曲阜师范大学 翻译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文化话语含蕴”。细读日本古代著名和歌歌论著作,就会发现,中国阴阳五行思想1600多年前东传日本,不仅影响了日本古代和歌的起源,还从内容到形式,即从五七五七七句调的固定形式到“花”“心”“实”等关键歌论概念,都对日本和歌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在日本古代和歌歌论中的话语蕴含,可为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域外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和理论基础。
阴阳五行思想;日本古代和歌歌论;影响
和歌作为日本民族文学的独特形式,一直是日本文学研究和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主题之一;阴阳思想作为中国先秦和汉代的百家之一,也一直是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课题之一。国内目前有关和歌的研究成果大都局限在和歌与汉诗、和歌意境、和歌汉译等单纯的文学方面,有关阴阳思想的研究大都局限在阴阳五行的成立、思想结构、影响、阴阳五行与中医、先秦阴阳家等单纯的哲学思想领域,提及中国阴阳五行思想与日本和歌关联性的研究寥寥无几,主要有《〈今昔物语集〉中的物忌故事》(山东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土公信仰在日本的传播与流变》(浙江工商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道家思想对日本近世文化的影响》(武汉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等极个别成果,但这些成果中没有涉及中国阴阳五行思想与和歌关联性的具体论述。朱水涌教授在《文化冲突与文学嬗变》(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中说“文学往往在文化冲突中充当了极为活跃的角色……表现出文化撞击中人的精神想象和文化风貌,并且承载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内容”。本文以该文学文化学观点为出发点,从日本著名和歌歌论中探讨中国阴阳五行思想东传日本之后对日本和歌起源、和歌形式、和歌内容产生的影响。
一、阴阳五行思想对和歌起源的影响
中国阴阳五行学说是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的合体,虽然国内学界对阴阳起源的说法不一,但胡适提出的阴阳五行为“齐学”的正统观点为大多数人接受,毕晓乐进一步提出阴阳观念来源于氏族时期山东齐地原始宗教信仰之一的“八神崇拜”中的天地崇拜和自然神崇拜,主要包括天、地、阴、阳、月、日、四时等[1]。阴阳本意指充斥在天地间的“阴阳二气”,用以指代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左右、春夏秋冬、君臣、夫妇、雷电雨雪、奇偶、动静、开合、花实、生死、律吕、依违向背、阴间阳间等一切互相对立有互相关联的现象,表现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五行观念形成于夏商时期,但阴阳概念和五行观念合流之后,就演变为抽象的哲学概念,并且催生了中国儒学和道教。阴阳五行学说的核心思想是“道分阴阳,合于五行”这一道教思想,阴阳学著作《周易》中明确主张“一阴一阳谓之道”。老子在《道德经》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意指阴阳化合而生万物)”。故阴阳五行思想既有具象所指,又有抽象概念,既指世间万物的运转质态,又指宇宙运行的根本力量。
日本最古书籍《古事记》(712)中开篇记载的最原始的日本和歌就是伊耶那岐和伊耶那美阴阳二神在天浮桥相会时分别赞美对方的歌:“あな にやし えおとこを(啊哪 可爱的美男子)”“あな にやし えおとめを(啊哪 可爱的美女子)”,且文中描写的情景几乎照搬了汉籍《艺文类聚》中“天左旋,地右旋,犹君臣阴阳相对之义”。[2]105二神唱和的这首歌就预示着他们的结合将会创造更多的后代,《古事记》后面的内容就记录了二神结合生出造化三神和“乾道独化”地上二神,形成神世七代,接着又生产了八大岛国、海洋、山川草木等八百万神,然后生出日神、月神和速须佐之男神等三贵子,最后是从速须佐之男神的各身体部位生出了五谷。由此可见,《古事记》记载的日本祖先神的产生都是男女阴阳结合的结果,按照中国古代“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观念来看,日本祖先神的产生均是按照“阴—阳—阴—阳”的顺序产生的。后来的《日本书纪》(720)中首先描写的是五畿七道诸国司的产生,也明确使用阴阳两极、阴神、阳神来记述神世七代的产生、八百万神的出现和人世五谷的出现。在其他各种《风土记》著作中,必然编修的内容也只有地名、物产、土地状况、山川原野、古老旧闻这五项内容,可见,五、六、七、这些阴数与阳数在日本国土产生说和日本古代和歌发生论中的影响。所以,叶渭渠先生说从日本各种《风土记》的内容来看,叙述的也是日本本土祖先神和自然神的神话和传说,从神仙思想的端倪来看,也的确映现出中国文化对日本本土古代文化产生了某些启蒙的作用[2]144。由此可见,日本创世神话的产生过程恰恰映照了中国“一阴一阳谓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的阴阳思想,同时也体现了原始阴阳观念中对自然神和天地神的崇拜意识,更证明了《黄帝内经·素问》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3]的阴阳观念,也吻合了男女结合繁衍后代的基本阴阳观念。故叶渭渠在论述日本和歌形态初现时说“在文艺诸形态未分化之前,古代的原始歌谣与祭祀的咒语、舞蹈等同,与神话、传说共存,它尚未成为独立的歌谣,是一种最简短、最原始的口诵形式……——这种实为感动词的‘歌’的存在,是古代歌谣乃至古代文学之始源。”[2]101-103可见,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对日本原始神道、对日本原始和歌的起源产生了深刻影响。
最早用文字记录日本原始歌谣的是《魏志·倭人传》,但没有明确提到阴阳观念传到日本。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是《日本书纪》中五经博士段杨尔于513年、汉高安茂于516年先后把阴阳术文献《易经》等典籍带回日本,施德王道良、王保孙等人554年把中国占卜书、历书等书籍带到日本,中国易经历法在日本发展起来。后来,观勒于602年把大量阴阳书、天文地理书、风水书、占卜书带回日本。日本于675年设立“阴阳寮”,勘定全国的阴阳地相、五行风水、占术祭祀等[4]。但这时的日本阴阳思想已经融合了道教咒术、密教占术和日本原始神道文化,形成了日本最初的阴阳道文化,其基本内容包括易经和历法两方面。可见,中国阴阳五行观念远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产生以前就已经传入日本了,说阴阳五行观念影响《古事记》中原始和歌的产生也就更加有理有据了。
如上所述,阴阳观念中的自然崇拜和天地崇拜意识影响了日本创世神话的产生,影响了日本原始神道的自然神信仰和祖先神信仰观念,也影响了日本最原始和歌的起源。
二、阴阳五行思想对和歌形式的影响
在中国,阴阳观念产生之后又产生了五行学说,贺娟说五行可指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材料、东西南北中五种方位、天上五大行星、五时气候(春、夏、季夏、秋、冬)和生化特点、身体手脚的五指等不同解释[5]。王位庆说阴阳为地球运动之本,为地球周期运动的力量[6]。 “宇”指的是一切的空间,包括东、南、西、北等一切地点,是无边无际的;“宙”指的是一切的时间,包括过去、现在、白天、黑夜等,是无始无终的,这与《庄子》中所说“上下四方为宇,往古来今为宙”之宇宙观一致。中国最早的五行学说著作《管子·乘马》中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就是说阴阳与五行一起运转。《黄帝内经·灵柩》中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也”,也是说阴阳与五行互不分离,融为一体。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说“夫阴阳、四时、五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总之,五行与阴阳在天地之间、上下之间、季节之间、方位之间等互相消长和运转。
从形式上看,伊耶那岐和伊耶那美二神初次相会互相唱和的最原始和歌就是阴神和阳神的结合,而且和歌的基本形式由五五调上句和五五调下句构成。有不少学者指出,这首和歌中的五言句式是受到五言汉诗的影响。但日本最早的和歌理论家空海(774—835年)把歌论著作《文镜秘府论》按照阴阳方位分为“天、地、东、西、南、北”六卷,并在另一歌论著作《文笔眼心抄》中说“凡文章之体,五言最难。声势沈浮,读之不美。句多精巧,理合阴阳,包天地而罗万物,笼日月而掩苍生。其中四时调于递代,八节正于轮环。五音五行,和于生灭,六律六吕,通于寒暑”[7]11。还引用《易经》名句‘文明健’,岂非兼文美哉”及“云从龙、风从虎”。藤原滨成(724—790年)在日本最早的歌学书《歌经标式》中说“六义有三:性六义,体六义,形六义。‘性六义’者,心读六义也。‘体六义’者,四季之体(中略)‘形六义’者,一首宜六义也”。此外,藤原还写道:“昔自一桥之下,男女定阴阳之义,八岛之上,山川分流岐之义”[7]18;在《石见女式》中说道“和歌之道者,天地应身,万法妙体。两句者天地阴阳,胎金二界也……五七五七七者,五行、五常、五方、五季也。第一句春也,春自东方来,方万物始……次第二句,夏自南方来,火方也,火性赤,万物尊敬之方,修行方也,土也,次第三句,秋也,自西来,金体也……菩提方也,菩提无常也……此句弱,则无大地,难立五行……次第五句,冬乃句也。冬自北来……三十一字,文字之极事。夫和歌三十一字,与神佛御座相当。三十一神,各守护和歌作者故也。若有三十二三字,皆是一字可纳者也。若一字之有善恶,神怒也。故文字善恶调句正可读也。所谓三十一神有……”[7]25。日本著名歌人、国学家契冲(1640—1701)在《古今余才抄》的《古今集假名序》注释中曾经说过“和歌上段则天,十七字,为阳数;下段法地,十四字,为阴数;五句则代表五行、五常、五伦;三十一字就是‘世’(由‘卅’和‘一’构成)字。周而复始,以致无穷”[7]243。连歌师心敬(1406—1475年)在著名的歌论著作《私语》中说“和歌五句分别为‘篇、序、题、曲、流’五点,相当于和歌的‘五体’(指头、颈、胸、首、足),‘六义’相当于和歌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还说道“篇、序、题、曲、流,由五大要素(地、水、火、风、空)构成,显现五佛、五智、圆明。‘六义’即是六道、六波罗蜜、六大无碍、法身之体”[7]342,346。可见,和歌论著中多次出现“五常、五伦、五佛、五智、五行”这些常见的阴阳五行术语,并且都是与道教、佛教、儒教中的阴阳五行观念融为一体,这些论述本身就说明连日本人自己都承认和歌与中国阴阳五行思想的关联性。
读完上述歌论,可明显看出:和歌上句和下句的组合是受到中国阴阳结合思想的影响,而且一阴一阳结合的形式还可以包罗天地万象,运转于天上日月和地上山水之间,既有刚健之阳气,也有智美之阴韵。同时和歌共有五句这一点也受到中国五行学说的影响,和歌歌论中的五行概念也同样包括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春、夏、季夏、秋、冬五个季节,金、木、水、火、土五种形态功能,眼、耳、鼻、舌、身五种部位,既有时间的动态运转,也有空间的动态运转,这与最初的中国五行学说的概念所指完全吻合。不但如此,藤原滨成还用五行学说解释了和歌共有五七五七七共五句的根本缘由,及全文共有三十一字的根本原因。和歌为“三十一字之咏”是因为日本原始神道中的三十一位神灵的存在,采用上下句的结合是因为阴阳结合的思想,上句代表天,用五七五句调,共十七字,十七属于阳数,下句代表地,采用七七句调,共十四字,十四属于阴数,整体采用五七五七七共五句形式是因为受五行学说的影响,每一句只有五音或七音,也跟“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之中国基本阴阳观念有关,并不是单纯受到五言和七言汉诗形式的影响或是受到日本人气息定量的影响。再细致观察,还可以发现上述和歌歌论中出现了“五常”“六义”等中国文化术语,“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之儒家伦理思想中规定的人之品德,“六义”指空海和藤原借用汉诗理论中的“风、雅、颂、赋、比、兴”之文艺概念。“五伦”本意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基本的人伦关系。但自从汉代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说发展儒学之后,“五常”“五伦”和阴阳的关系就合二为一了,其基本图式为“父子—亲—仁—木、夫妻—别—智—水、长幼—序—礼—火、朋友—信—信—土、君臣—义—义—金”。 也可以说,除了阴阳五行思想以外,和歌歌论还受到了“五常”等儒学思想和“风雅颂赋比兴”等汉诗诗学的影响。但全文共三十一字的固定形式却是受到日本原始神道中有三十一位神灵之说法的影响逐渐固定下来的,当然同时也表现了阴阳五行宇宙观中“周而复始、无边无际、生生不息”的思想,特别是连歌五七五七七循环往复的形式更是蕴含着同样的阴阳五行宇宙观。因此,可以说,在日本和歌逐渐定型的过程中,中国汉诗、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儒学思想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既不是单纯的五言汉诗或七言汉诗的影响造成的,也不是日本人单独的口头传承过程造成的,在根源上是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
日本学者古桥信孝说原始和歌在口头传承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固定形式[8],土田杏村在《日本文学之发生》一书中断言“语音数定型之原因,必得归于汉诗之影响。在此之前,歌谣的长短句中,也不乏五音七音之例,但并未形成定型……以五音七音定型,无疑是受到中国五言诗的刺激,从而有意识地对其模仿的结果”[9]12。日本诗人岩野泡鸣在《新体诗的作法》中说“七五调的成因之一,在于它是十二音律的一种,而日本人的音量一般以十二音时为极限,气息的定量与句调有极大关系。”[9]13中国学者王勇在《日本和歌格律探源》(《日语学习与研究》,1990)中说“五七五七七音数律是日本民族和日本语言的特殊产物”。但从以上引用的日本歌论原文来看,以上四种观点都只是说到了日本和歌形式形成的某一方面原因,并没有触及最根本的原因。古桥的说法、土田的说法、岩野的说法、王勇的说法都仅仅论证了和歌每句采用五音或七音形式的某一原因,但没有说明和歌总体分上下两段、五句共三十一个音律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没有触及和歌发生论的最根本的思想根源,如果研读了日本古代和歌歌论著作之后,就会明白和歌整体格律形式产生的思想根源。
三、阴阳五行思想对古代和歌内容的影响
王向远在《日本古代文论的千年流变与五大论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2)中总结了日本歌论历史及主要概念:13世纪之前,是日本歌论概念、范畴与理论命题初步提出时期,在《怀风藻》等汉诗集的序言中、在《文镜秘府论》《文笔心眼抄》《歌经标式》中提出的歌学概念都基本照搬了道、心、气、文、歌经、风雅颂、赋比兴、意象等中国诗学概念范畴,只有“慰”字才初具日本韵味。纪贯之在《古今和歌集·假名序》里为刻意摆脱汉诗影响,明确提出了“心”“歌心”“情”“词”“诚”“花”与“实”等歌论用语,壬生忠岑在《和歌体十体》中也初步使用了“词”与“义”“幽玄”“余情”等日本歌论概念,藤原公任在《新撰髓脑》和《和歌九品》中明确提出“心”“词”“姿”。13到16世纪是日本连歌论和能乐论确立、巩固时期,提出了“幽玄”之最高境界和“花”之最美状态。江户时期是日本俳谐论、诗学、戏剧理论成熟期,提出“俳谐”之风格论、“物纷”之方法论,“花”之能乐论。从词源来看,以上各种古典歌论中最常用的“道”“心”“花”“词”“实”“幽玄”等关键词,本身都具有汉字原来的表意功能,也与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和道教思想息息相关。
和歌歌论中最常用的“心”字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凡心之属皆从心”。可见“心”字是五行中的土,也是五行中的火,以心配土,土为中央,表示人心不仅是五脏四肢的主宰,而且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中枢,而所谓“火”,指人体的内热,但更多用来形容内心的激动情绪等无法压抑的情感。随着儒学、佛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中国之“心”以及关于“心”的种种言说,特别是中国儒学中的心性之学、阳明心学、佛教禅宗中的“佛即心”的佛性论,也都传到了日本,必然会对日本古典文论的概念范畴的形成、理论体系的构建产生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影响。“心”遍布于和歌的整体中,位于歌论的中心,是作品的精神内涵[10]。因为五行家认为“心”处在五方位置的中心,主宰人的“情”“性”“德”“气”等情感体验、思维活动、思想认知等,所以《说文解字》解释“情”为“人之阳气有欲者”,解释“性”为“人之阳气性善者也”,解释“气”为“云气也,象形,凡气之氣皆从气”。日本最早的和歌论著《文笔眼心抄》里,作者空海模仿中国诗学概念的说法用了“心抄”做题目,文中还出现了“写心阶”“意阔心远以小纳大体”“质气体”“情理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苦心竭智”“即须凝心”“以心击之”“心中了见”“气生乎心,心发乎言”“诗人用心”“心通其物”等二十处与“心”有关的说法;此外还出现了“质气体”“情理体”“凡文章兴作,先动气”“四时气象”“气霭虽尽,阳气正甚”“气霭未起,阳气稍歇”“诗工创心,以情为地”等与“情”“气”等有关的歌论主张,很明显,这些“心”“气”“情”等关键概念词都具有中国阴阳之“心”、五行之“心”的基本含义。在《歌经标式》中也有“通达心灵”“在心为志,发言为歌”的说法;在《古今和歌集假名序》里有“以人心为种”“其‘心’有余,其‘词’不足”等说法,还多次出现了“歌心”这一概念;《新撰髓脑》中明确提出“‘心’深、‘姿’清”之歌论观点。在这之后的歌论著作中,虽然具有阴阳本意的“气”逐渐淡化,但具有五行思想本意的“心”却成为固定的中心概念。为何“心”或“歌心”成为和歌论的中心概念呢?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言“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
再看歌心术语“花”和“实”。“花”,甲骨文本字为“华”,像一棵树花开满枝的样子,小篆写作“花”,意为草木所开之花朵,造字本义指草本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就好比女性生殖器官,所以“花”还指“女子”,故属“阴”。“实”字,造字本义表示家有宝贝,指充实的、殷实的意思,也指“植物结的果实”,就好比男性生殖精物,故属“阳”。因为生命的阴阳观作为《周易》所构建起的具象化的阴阳体系之一,普遍存在于古代信仰中。[11]但日本歌论中的阴阳观不是具体事物观,而是阴阳中和的文论观,因为“阴阳交而生和”“阴阳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纪贯之在《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评论之前的和歌使用了“其实皆落,其花孤荣”“以之为花鸟之使”“其词华而少实”“如萎花虽少色彩而有熏香”“如病妇之著花粉”“如田夫之息花也”“少春花之艳”;在《古今和歌集假名序》里评论和歌使用“如枯萎之花,色艳全无,余香尚存”“如樵夫背柴,于花荫下小憩”;在《新撰和歌集序》里明确提出“花实相兼”之说。之后的《新撰髓脑》和《古来风体抄》等歌论也提到“花”字,但主要将“心”“词”“姿”作为和歌歌心进行论述。直到藤原定家在《每月抄》中提到“所谓‘实’就是‘心’,所谓‘花’就是‘词’,古歌中使用多的词,未必可称为‘实’。即便古人所咏和歌,如果无‘心’,那就是无‘实’。今人所咏和歌,如果用词雅正,那就可称有‘实’之歌(中略),‘心’与‘词’兼顾,才是优秀的和歌,将‘心’与‘词’看成如鸟之双翼,假如不能兼顾‘心’与‘词’,与其缺少‘心’,毋宁稍逊于‘词’”[7]108。可见,“花”与“实”不是阴阳对立关系,是阴阳同构关系,是阴阳中和关系,强调的是和歌创作不能单纯追求花朵一样的美丽外形,也不能单纯追求内在的精神实体,应该里外一致,两者兼顾,形神兼备,由“花”结“实”,“花”“实”一体,物心合一。实际上,“花”与“实”兼顾,指的是阴阳虚实的结合,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与中国古典文论中主张的阴阳同构中和美如出一辙,因为“阴阳中和美论讲究文艺创作时诸种情感发抒的适度性、合宜性以宣导人情,使艺术接受者‘温良恭谦’‘温柔敦厚’的理想人格得以塑形,这一点也是阴阳观念在人的情感投影方面所决定的”[12]。
畅广元教授在《文学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中说“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行为,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标志,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文化话语含蕴”。综观以上论述,可见代表日本古典文学的和歌,从原始起源、到五七五七七调的固定句式、再到主导和歌一切理念的“心”“花”“实”等重要术语关键词的意义蕴含,都与中国阴阳五行思想息息相关。换言之,和歌文学是中国阴阳五行思想文化在日本的再创造,是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域外发展和延伸的代表,日本古代著名和歌歌论著作,都不可否认地表明了阴阳五行思想对日本和歌起源、和歌形式、和歌内容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同时也让我们反思日本和歌对中国阴阳五行思想文化的引进、吸收、融合、发展的历史特点,反观中国传统文化走进日本的历史轨迹,为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域外研究和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
[1] 毕晓乐.齐文化与阴阳五行思想的起源[J].东岳论丛. 2005(5):102-104.
[2] 叶渭渠.日本文学史(古代卷上)[M].昆仑出版社,2004: 101-103.144.157.
[3] 赵文.论阴阳五行学说及其产生的时间[J].宗教学研究,2010,141.
[4] 王静.日本阴阳道成立端委探析[J].华侨大学学报,2014(2):79-80.
[5] 贺娟.论五行学说的起源和形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7):439-440.
[6] 王位庆.论阴阳五行的科学基础[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638-639.
[7] 王向远.日本古代文论选译古代卷上[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1-15.18.25-26.243.242.246.108.
[8] 古桥信孝,著.徐凤,付秀梅,译.日本文学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17.
[9] 王勇.日本和歌格律探源[J].日语学习与研究,1990:12-13.
[10] 王向远.日本古典文论中“心”范畴及其与中国的关联[J].东疆学刊.2011(3):23-24.
[11] 刘文英.阴阳家的生态观念及其历史地位[J].文史哲.2005(1):29
[12] 许劲松.阴阳同构与中国古典文论话语研究[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11(12):97-98.
[13] 王向远.日本古代文论的千年流变与五大论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2:116-119.
[14] 周振甫.周易译注[M].中华书局,1991.
[15] 李耳.道德经[M].中华书局,1962.
[16] 福永武彦译.古事记.日本文学全集一[M].河出书房,1968:14-17.
[17] 山本健吉译.日本书纪.日本文学全集二[M].河出书房,1968.
[18] 汉·陈寿.三国志·魏志·倭人传[M].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校:朱德东)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Japanese Waka
XU Feng
(SchoolofTranslationStudies,QufuNormalUniversity,ShandongRizhao276826,China)
“Literary creation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discourse”. By Reading ancient Japanese famous Waka theoretical works, we can find that Chinese Yin 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 eastward spread to Japan 1600 years ago, not only gave birth to the ancient Japanese Waka, but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of Japanese Waka from content to form, from the fixed form of “five seven five seven seven” tune to the theoretical keywords of “flower” “heart” “fruits” and other key concepts. Studying the discourse containing of Chinese Yin 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 in ancient Japanese Waka theoretical works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hich can als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verseas studies of pres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Theory; ancient Japanese Waka theoretical works; influence
10.3969/j.issn.1672- 0598.2016.06.017
2015-12-28
2014年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2014345)“中日阴阳文化比较研究”
徐凤(1973—),女,山东枣庄人;曲阜师范大学日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日汉互译研究。
I313.072
A
1672- 0598(2016)06- 0113-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