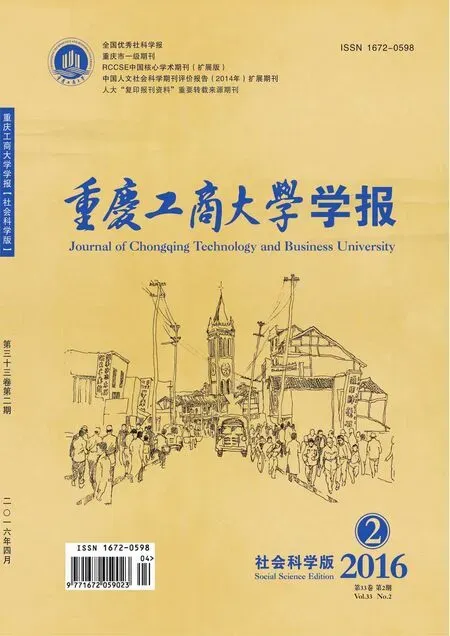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重庆市白虎村为例
周绍宾,李连辉(.重庆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系,重庆 4033,. 重庆市沙坪坝区民政局,重庆 400030)
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治理
——以重庆市白虎村为例
周绍宾1,李连辉2(1.重庆师范大学 社会工作系,重庆 401331,2. 重庆市沙坪坝区民政局,重庆 400030)
摘要:在农村社区急剧转型,农村社会依然弱势并不断衍生新的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的实务经验表明,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加强和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服务农村社区及其居民、保持农村社会有序稳定、推进农村社会发展进步,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社会工作;农村社区;社会治理
一、充分认识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以来,中国农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和提高,农村社会的治理和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相关研究表明,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城乡差距过大,农民增收的空间和幅度不大而支出居高不下,乡村集体经济薄弱,普遍负债,村民自治、民主建设与制度设计尚有距离,干群关系冷漠、冲突和各种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或危机,这些都直接关系农村社会的进一步转型进步,关系亿万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也影响到中国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1]
以重庆市白虎村为例。由于地处城郊,区位优势明显,村民外出务工经商较为方便,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及医疗、教育等资源相对丰富,加之这些年也获得了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诸多支持,成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因此,较之一般边远农村地区,白虎村的各方面条件及村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更好一些。但是,白虎村也有自己的特点和问题。一是地处城乡结合部,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难以纳入城市。因为根据地方政府产业发展和土地利用规划,白虎村的未来定位是“乡村生态休闲观光旅游度假区”,农业用地的性质将长期不变。但是这几年地方政府的发展重心在于发展加工制造、物流及商务等,白虎村的美好前景都还仅仅限于规划中,实际的推进并不明显。二是白虎村的城乡结合区位是突发式、跨越式的,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几年前,这里都还是距市区相对偏远的纯农区,向东到沙坪坝市区要翻越歌乐山,向西到璧山区要翻越缙云山,都在二三小时车程左右。后来因为建设大学城、微电园综合保税区、物流园区等,与其一步之遥的各个村庄骤然间被城市化了,这种突发式、跨越式的变革,带给村民的不仅是对邻村的羡慕,更使得村民们在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些难以适应,也使得许多村民既有纯农区的质朴,又多了几分城市的精明和算计。有些村民为了点滴利益就会变得计较甚至“刁蛮”。三是土地流转率高,但开发利用不充分。由于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使资本看到了“圈地”的高额利润回报,广大村民在还不熟悉政策与市场的情况下就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把土地流转出去了,但又因为随即而来的产业发展和土地利用规划,使土地流转企业陷入两难之中,土地的农业开发非其本意,改变土地利用性质又不可能,都撂荒在那里,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的收益和转移就业也就成了一个难题。四是村民的非农就业率高,但大多属于离土不离乡。这与中西部许多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不同,因为大学城、微电园综合保税区等项目的建设,产生了大量的用工需求,但大多村民只能从事那些技术含量低或者体力型工作,如保安、物业保洁、园林管护等,工作时间长而收入不高。第五,问题多、矛盾大。虽然相对于过去,村民的收入增加了,村里的基础设施改善了,但在已经打破了传统平静的白虎村,各种矛盾和问题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如政府产业规划、土地利用性质的限制与村民的意愿之间的矛盾,土地流转企业流转土地的目的与政府产业规划、村民利益诉求的矛盾,村民想发展农家乐的愿望与政府职能部门要求只有星级农家乐才能获批的矛盾,过境高速公路、进城快速通道、天然气管道等占用土地补偿费的分配问题,土地二次转包引起的利益矛盾,集体荒地、林地流转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土地流转后村民的就业问题,部分进入新村的村民“农转非”后既不能完全享受市民待遇又不能享受有关惠农政策的问题,新村村民房屋产权难落实的问题,新村建设预留地和建成房闲置的问题,群众不信任干部导致的干群关系紧张问题,以及空巢老人问题、留守儿童、女性发展问题、大病重病患者与残疾人问题,等等。
这些特点、矛盾和问题,不仅仅白虎村存在,在重庆以及其他城市城郊农村甚至边远农村地区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有的甚至更为严重,成为城乡矛盾和问题的多发地,成为村庄治理、城市发展和城乡统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依靠和利用传统的农村工作方法已经越来越难以有效化解,因此,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农村社会治理能力,进而构建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迫在眉睫。这就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契机。
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治理的可行性
社会工作是指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遵循专业伦理规范,坚持“助人自助”宗旨,在社会服务、社会管理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活动。[2]社会工作最终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工作的专业魅力体现在它所秉持的专业价值和理念,在社会工作者看来,人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联合体,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都应受到尊重,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是有潜能的,人是不断发展的,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也必须帮助别人。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体现在它所坚持的人人平等,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接纳个体的价值、尊严和特点,以人为本和自我决定,维护人权和社会公正,赋权与发展等工作原则以及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直接和间接相统一、既关注人的改变又注重环境的建设。个案、小组、社区和政策倡导等工作方法相结合。这些价值理念、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与当下的农村工作和社会治理是非常契合的。
同时,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在乡村社会治理和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原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曾概括了社会工作者的五个有利于,即社会工作者依托政府支持,通过宣传倡导、组织动员、资源协调,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效率;有利于形成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有利于推进社区建设;有利于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发挥社会工作者系统化、多样化、个性化解决群体问题和个体问题的专业能力,为社会成员提供政府不便和市场不愿或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利于激发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3]
如果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来说,农村社会的急剧变迁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凸显,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相当广阔的活动空间,如农村发展、妇女发展、助残助学、社会扶贫与社会救助、社区服务与社区管理、社会犯罪与社会矫治、家庭暴力防范以及老年人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医疗社会工作、精神康复社会工作,等等。
从白虎村社会工作介入前的需求调查和评估也充分证实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及迫切性。在介入之前,我们采用访谈、实地观察及问卷等办法,对五类人群进行了调查、走访和评估,即儿童(包括留守儿童、单亲儿童、辍学儿童等)、妇女(包括留守妇女、受家暴妇女、疾病妇女等)、老人(包括空巢老人、散居老年党员、孤寡老人等)、残障人士和在村的耕种人(主要是村里的果农和为土地流转企业打工的村民)。
调查发现,白虎村的儿童,上学路程较远,留守儿童比例高,隔代教育突出,平时学习任务重,假期缺少计划性、娱乐性和成长性教育。儿童青少年时期正是人的“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年龄稍大的孩子又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成长的过程需要更好的教育与引导。从个人、家庭和社区来分析,该村的孩子们大多缺少正确的引导。通过走访了解,白虎村的妇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年龄在20~40岁左右的妇女,大多数外出打工,且工作范围基本上是在重庆市主城区、临近的大学城等,不上班的时候她们通常会回家与亲人团聚,她们中的大多数学历较低,从事的工作也是一些体力劳动如保洁、园林管护之类的;一类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妇女,她们大多数留守在家,主要工作是照顾小孩,有的会经营一小块已经流转出去的土地,种些自己吃的蔬菜瓜果,空闲时间很多,生活较为单调,娱乐活动以看电视、打麻将或者聊天为主。在人际交往方面,不仅入住新村和散居旧房的村民来往很少,即便住在新村的大妈们也时常觉得很“冷清”“冷漠”,她们中的大多数希望村里或者社工能够组织大家开展有意义的、热闹的文体娱乐活动。老年人方面,白虎村的老龄化比较严重,60岁以上的老人在25%左右,90岁以上有十多个,最高龄的是97的黄婆婆。因为一直生活在农村,体力劳动较多,一般上了60岁的老年人的身体都会出现各种不适,健康状况堪忧,再加上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周边无较好的医疗机构,当地的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距离比较远,不利于老人们出行就医。多数年轻人白天外出务工经商,晚上娱乐应酬,早出晚归,没有时间和心思照料家庭事务,不仅不愿照料老人的日常生活,相反,这些老人还要帮忙照看小孩。老年人已不再满足于“带孙子、享清福”,对文化、健身、娱乐,有更多的需求,“求知、求健、求乐”欲望较强,表示只要能走动,都愿出门走走、看看,或者参加一些文体娱乐活动。村里虽然组建有老年协会,但常规性的活动开展得比较少,不能满足老年人群的需要。
总之,社会工作优秀的专业品质和强大的行动能力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类问题以及农村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巨大的社会需求,决定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服务各类人群,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和紧迫性。
三、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社会治理
根据当下农村的需求和社会治理状况,社会工作如何有效介入?有学者认为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肩负着至少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4]
以白虎村为例,从2012年开始,在市、区两级民政部门的支持下,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团队进村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结合白虎村上述问题,确定了社会工作服务的基本方向和内容,一是农村社区弱势人群个体层面的社会工作服务,包括生活照料、反家庭暴力、精神慰藉、心理支持、行为纠偏及能力建设等;二是农村社区弱势群体团体层面的社会工作服务,包括老年互助团体、女性互助发展小组、儿童激励成长小组、科普小组、邻里支持计划等;三是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社会工作服务,包括社区归属及认同、社区参与及民主管理、社区资源的评估及整合、社区组织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等。基于上述三个层面的不同问题和需求,并充分考虑到服务人群的共性与差异,社工团队整合运用个案、小组和社区方法,灵活开展服务。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以整合各方力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为导向,以通过服务提升社区及居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为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
第一,基于能力建设的实务模式,激发农村社区居民的信心,提升其发展潜能。社会工作非常重视能力建设,这也是社会工作“助人自助”宗旨的体现。白虎村的村民虽然多数衣食无忧,甚至有部分人已经比较富裕,但是,在村庄利益日益分化的格局下,也有不少人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对于一些长期生病、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和个人,不仅现实的生活是困难的,而且难以看到未来,对未来没有信心。社会工作的介入,在改善其生活品质的同时,还有效地疏导了他们的心理压力,树立了他们的生活信心。一些经常觉得“社会不公平”“生活没盼头”的非正常情绪得以弱化,为创新村级社区治理营造了更加良好的社区心理和人际氛围。
第二,基于地区发展的实务模式,通过组建各类互助组织来增进村民的参与和合作。由于农村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市场化的影响,农村的原子化趋势越来越厉害,传统的熟人社会在弱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思想普遍存在,社工通过协助村里不同村民自组织的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以互助活动增强村民的责任感和办事能力,以成功的合作经验鼓励居民参与村级社区公共事务。如组织老年互助小组,引导村里的老年朋友树立积极老龄化意识,支持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针对白虎村退伍军人比较多,而且其中能人也较多的情况,组织退伍军人联谊会,发挥德高望重的老退伍军人在调解村庄纠纷和矛盾中的作用,发挥中年退伍军人在村社区组织和经济活动中的带头作用;针对白虎村农家乐经营户各自为阵的情况,组织水果专业合作社和农家乐联谊会,开展农户对接,分享彼此的经验等。这些活动都有效促进了农村社区参与和村民团结,为农村社区治理奠定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第三,通过与村“两委会”合作开展社区活动,重塑村“两委会”的权威,提升村“两委会”的形象。实事求是地讲,白虎村的两委会成员,在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医疗、社保以及其他便民服务等方面,还是为村民做了很多实事、好事,为村民争得了很多利益,但在“利益最大化”的心态下,好些人还是对村干部不满意、不信任,造成干群关系或疏离或紧张。社工在组织社区主题活动以及其他服务的时候,都是以村“两委会”和社工室联合主办的方式,经常邀请村书记或主任到场讲话、助威,招募村委会成员作为活动志愿者。同时,针对目前农村工作方式“办公室模式”,每年都举行村社干部社工知识宣讲、培训,把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和技巧“嵌入”到“两委会”和村民小组的工作机制中,使村社干部在理解和接受社会工作“尊重、平等、接纳、助人自助”等理念后,逐渐“社工化”,工作作风和效率大为改善,从而改善了干群关系,使农村社区治理逐渐朝着善治方向发展。
总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通过组织开展系列的专业服务,一方面传播和推广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提高了社会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同感,另一方面确实充分发挥了促进农村社会治理的功能,提高了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水平。
[参考文献]
[1] 戴利朝. 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0).
[2] 甄炳亮.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制度建设[R]∥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198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
[3] 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在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会上的讲话[EB/OL]. http:∥sw.mca.gov.cn/article/ldjh/200710/20071000002609.shtml.
[4] 钱宁.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5] 周绍宾,张明.新城郊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反思[J].中国社会工作,2014.8(上).
(责任编校:杨睿)
Social Work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Taking Baihu Village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ZHOU Shao-bin1, LI Lian-hui2
(1.SocialWorkDepartment,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2.BureauofCivilAffairs,
ChongqingShapingbaDistrict,Chongqing400030,China)
Abstract:Under the situation of rapid transition of rural community, being still vulnerable of rural society, and continuously having new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in rural area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y shows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social work has positive impact on enhancing and innovating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effective service to rural community and its residents, keeping the order and stability of rural society, pushing forwar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rural socie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whole China.
Key words:social work; rural community; social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 0598(2016)02- 0068- 04
[作者简介]周绍宾(1967—),男;法学硕士,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社工系主任,主要从事社会工作实务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29
doi:12.3969/j.issn.1672- 0598.2016.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