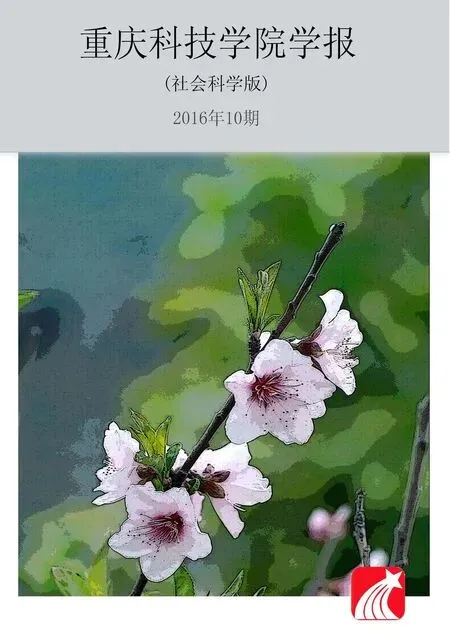《妻妾成群》中的季节叙事与女性救赎
李晓文
《妻妾成群》中的季节叙事与女性救赎
李晓文
《妻妾成群》是苏童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陈佐千一家的悲剧故事,反映了传统中国女性通过屈从或反抗2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寻求自我的保护与救赎,却难逃封建家庭束缚与压制的宿命。小说以几位年轻女性的命运映照季节之中的夏之热烈,秋之阴郁,冬之萧瑟,却唯独没有春之希望。这种没有“春天”的生活,隐喻女性救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妻妾成群》;季节叙事;女性救赎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上颇负盛名的作家之一,苏童长于以细密绵润的笔调刻画人物繁复精微的内心活动,在日常事物的描摹中寄托无限的人性内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苏童打破了20世纪主宰中国文坛的启蒙主义文学语式关于时间的叙述图式,他对时间的非线性认识,对事物轮换、人事反复的体验,使他更能深入中国人的性与命的深处,挖掘那具有民族史志色彩的人性蕴含。”[1]以苏童最具盛名的作品《妻妾成群》为例,可以一览苏童独特的时间体验对于人物性格塑造的巨大影响,这表征为一种现代以来女性救赎的巨大隐喻。
一、夏之热烈:颂莲、梅珊对生命自由的热烈追寻
小说中历来不乏以四季变换来展现世事沧桑、生命更替的描写,或是以四时节气的特点来体现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西方小说家兼文论家戴维洛奇曾指出:“我们都知道天气影响人的情绪,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发明各种天气状况以适合他(她)制造的某种情绪。”[2]夏季天气是炎热难耐的,就如《妻妾成群》中颂莲和梅珊的性格一样,刚烈且炙热。她们对于封建家庭的种种不满大都以泼辣的言辞、极端的行为来展现,生命如夏花一样绚烂,但是也预示着这种生命追求所导致的短暂。
在《妻妾成群》中,梅珊和颂莲都对自己身处的生存状态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并以各种方式进行挣扎和反抗。具体看来,戏子出身的梅珊通过和医生偷情这种方式,试图实现其作为女性存在的价值。在陈府这种迂腐、封建的男权家庭中,梅珊不甘于受人摆布的命运,对以大老爷为首的男权制度有本能的怀疑,但这种认识终究是朦胧和无意识的。梅珊的性格热烈而刚烈,犹如夏季炙热的天气,让人不得安宁。且不说她与医生的偷情是出于真爱还是肉体所需,但毕竟在陈家这样等级森严的家庭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梅珊敢于向沉闷、固执的家族挑战和反抗是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进步,是以一己之力向男权社会中没有自主的婚姻的决然背离。她以女性身体的背叛挑战了男权制度的绝对权威,这是对男权制度最忤逆、最严重的挑战。然而,现实的残酷总会让她为此付出代价,梅珊的行为最终是被封建家庭所不容,其被弃之于井中的命运映照着夏季的短暂和易逝。这种飞蛾扑火般的反抗,无论成败都是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决绝反抗和勇敢尝试。
与梅珊一样有着夏日般炽热性格的还有颂莲。颂莲是一个受新思想影响的女青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比梅珊更为系统和自觉的女性意识。她疑惑着“女人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3]。她感叹着女人在男权社会中没有价值的存在,女人们在男人的压迫和强权下苟延残喘,没有自由,没有感情,逐渐沦为封建家庭的牺牲品。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颂莲表现出了对陈家大院的封建阴郁气氛的反感和反抗。一方面她以一个进步女青年的身份进入陈家,行为、言语都展现出知识分子的明晰和激烈,生存状态也犹如夏花一样绚烂;但另一方面,这种不为男权家族所接受的状态并不能在森严戒备的陈家大院维持多久,很快颂莲就被物质和欲望所钝化,失掉了女性反抗的光芒。她逐渐接受了陈佐千小妾这个身份,极尽所能地讨好大老爷,以求在这个家庭和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由此,颂莲便成为整部小说中最悲情的人物,她这种明明清醒却无法改变的无力感,正是身处封建家庭中知识青年的真实写照。她深谙男权的黑暗,清楚地知道女人在男权之下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无法反抗。在这个了无生机的封建家庭中,她不想与毓如和卓云同流合污,成为男权社会的维护者,却又没有勇气像梅珊一样进行决然反抗。她清楚地知道现实的残酷却无路可走。于是她选择“疯”,以此来控诉与男权制度的不相容和不妥协。然而,颂莲最终还是被封建家庭所遗弃,灿若星辰的生命就这样在枯死的家庭中被悄然耗尽。
二、秋之阴郁:卓云阴郁悲凉的性格写照
古人往往由自然之秋联想到人生之秋,进而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秋天属金,对应的是刑杀,是五音中的商音,而‘商’即是‘伤’。另外,民族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都在潜意识中指向同一种典型情绪——悲”[4]。然而,苏童笔下的秋天,在悲凉上又萦绕着一丝阴郁的气息,“秋天一天凉于一天,枫林路一带的蝉鸣沉寂下去,枫树的角形叶子已经红透了,而梧桐开始落叶,落叶覆盖在潮湿的地面上,被风卷起或者紧贴地面静静地腐烂,从高处俯瞰枫林路的秋景,这条街道竟点缀着层层叠叠的红黄暖色,过路人极易忽略高墙里侧医院的存在,也极易忘记从你身边掠过的是一个疾病和死亡的王国”[5]。因此,苏童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也有如他笔下所描摹的秋天一般,阴郁且肃杀。《妻妾成群》中的二太太卓云就是如此。在众妻妾中,卓云没有大太太的地位和权利,没有颂莲和梅珊的年轻和貌美,她的生命状态就像深秋一样,阴冷灰暗。
在妻妾成群的陈家大院中,二太太卓云的身份很尴尬。她没有“母凭子贵”的资本,也没有梅珊和颂莲的如花似玉,唯有对陈佐千曲意逢迎和对其他太太笑脸相迎才有存活下去的可能。她表面上极力维护大太太,其实内心却有自己的小算盘,希望通过大太太来为她铲除梅珊和颂莲。颂莲初入陈家时,卓云也是表现得极其热情,但内心却是阴险狡诈,处处算计。为了在陈府安身立命,她对陈左迁极力奉承,她的笑脸之后却是无比歹毒和阴暗的心。她的告密害死了梅珊,然而杀死梅珊的却不只是卓云。卓云阴险、扭曲的性格源于陈家和笼罩在整个社会的男权制度和价值评判标准,唯有曲意逢迎,才能将这把专门威胁和残害女性的利刃化为己有,使之不伤害自己。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许多女性的罪状是由于女性的可怜,其实这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们的可怜。野蛮的社会制度把她们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们头上[6]。在男权的压迫下,卓云早已变成一个扭曲的形象,表面上唯唯诺诺,内心里却阴险歹毒。卓云的存在就像《妻妾成群》的秋天一样,阴郁且苍凉,又充斥着心酸和无奈。
不只是卓云,整个陈府都弥漫着深秋一样阴郁、氤氲的死亡气息,营造着陈佐千在生命的最后垂死挣扎、苟延残喘的压抑氛围。卓云有着对死亡、对终结的恐惧,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这死灰一般的家庭中保持自己仅有的生存价值——讨好陈佐千,算计颂莲,揭发梅珊,铲除竞争对手以安然立足于陈府。然而,季节在轮回,人事在变迁,即便梅珊死去,颂莲发疯,陈家大院依然是以往的样子。来年,陈家又迎来新的姨太太文竹,卓云的心计或许又可以用在这个姨太太身上,但她的生命依然如同深秋一样,始终是在进行垂死挣扎。
三、冬之萧瑟:毓如对死而不僵的封建家庭的维护
北方的冬天总是大雪皑皑,一片肃杀的情景。冬季是没有生机的,一切生命个体都在蛰伏,一片荒寂。《妻妾成群》中更是将冬季这种凄冷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大太太毓如的性情就如同这冬季的寒冷一般,冷若冰霜,阴冷萧瑟。毓如是陈家的大太太,掌管着陈家大院的一切,对于不断娶妾回来的陈佐千,她无可奈何,对于陈家大院中性格各异的妻妾,她仍然采取漠然的态度。
以陈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大家族中,男性数量远远小于女性,却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一位男性“老爷”至少拥有一妻一妾,若干陪房丫头,以及随时等待召唤的女佣人无数。“她们每个人不得不压抑着人类渴求性爱的单一性的本能,与几个女人拥有一个丈夫,她们所能争取的并不是与男人在性爱、婚姻中平等相处的权利,而不过是‘太太、奶奶’这妇女道德所允许的一点可怜的名分。”[7]《妻妾成群》中,作为大太太的毓如可以说是陈家大院中男权制度的忠实拥护者和捍卫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封建家庭的牺牲者。她试图通过对封建家庭的维护和捍卫来保全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以此来逃避男权的压制。毓如年老色衰,早已失去了用美色获得宠爱的资本,她的存在对陈千佐来说犹如冬天的沉寂一样,毫无生机和活力,所以她只能借助念佛消解自己的欲望,做出不屑和其他人争斗的姿态。作为陈家大院的女性掌权人,从某种程度上讲,毓如是要维护男权制度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因为只有这样她才可以维护自身在陈府的地位。可以说,毓如是封建男权制度下女性的替代者。每当府里有冲突,毓如都要出面来充当权力者和执法者。但她表面的强势正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焦灼和恐慌,如同颂莲刚见她时,她手中的珠子却掉了一地,她捡珠子时蠕动的肥胖身体,如同在诉说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凄凉,这份凄凉如同冬季寒风的凛冽,刺骨且无奈。
四、结语
《妻妾成群》可谓是季节叙事的一个典型文本,“所谓季节叙事,是指叙述者在小说文本中以四季的流转变迁为叙事内容,通过四季中春、夏、秋、冬的交替变换与循环往复表现世事沧桑与生命体悟的叙事手法,就其形态而言,包括四季叙事、节气叙事和物候叙事。”[8]四季有轮回,然人生无常在。无论是绚烂泼辣的梅珊、如花般年轻美丽的颂莲,还是冰冷阴鸷的卓云,抑或是垂垂老矣的毓如,她们的生命自嫁进陈家之后便走向了衰亡,迎不来温暖复苏的春天。在男权体制的束缚和制约下,她们没有自由,没有希望,尝试着自我救赎,却难免走向死亡。
《妻妾成群》反映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中浓郁的男尊女卑思想,以及在此压制下女性被扭曲的灵魂。整个家庭中的女性的生命状态通过季节变换来体现,更是苏童作品的一大特点。在小说中,季节不仅仅是时间坐标,更是陈家大院里人世沧桑更迭的预示。颂莲初夏进入陈府,历经秋天的沉郁阴暗,冬天的荒凉萧瑟,唯独没有看到春天的生机盎然,就像她的生命一样由夏的炙热逐渐糜烂萎缩。同时,季节的变换也对应着陈府中妻妾的人物图景,梅珊炙热刚烈的性格如同夏季之热烈,卓云内心的阴暗犹如秋季之阴郁,大太太毓如就如同冬季般了无生机。然而,陈家这个囚笼似的庭院虽然困住了女性的行动自由,但困不住女性内心的欲望,磨灭不了女性在男权体系中感受到的难以名状的苦闷。由此,这种独特的女性体验和无意识的抗争,成为有别于传统女性一味依附、浑浑噩噩的现代性特征。且不论梅珊、颂莲、卓云、毓如的反抗或迎合是否有效地打击了男权体制的主导地位,但这种对于大家庭生活的不安和危机意识,就已经隐喻了女性自我救赎思想的觉醒。至于觉醒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就值得现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一同来探索了。
[1]葛红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J].社会科学,2003(2).
[2]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95.
[3]苏童.妻妾成群[M].台北:台海出版社,2000:35.
[4]郝相国.四时的美学意义[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7:30.
[5]苏童.樱桃[J].作家,1994(3).
[6]鲁迅.中国文与中国人[G]//鲁迅杂文精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27.
[7]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9.
[8]陈红凌.明清小说季节叙事论:以六大古典小说为中心[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2:1.
(编辑:文汝)
I207.67
A
1673-1999(2016)10-0066-03
李晓文(1990-),女,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273165)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2016-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