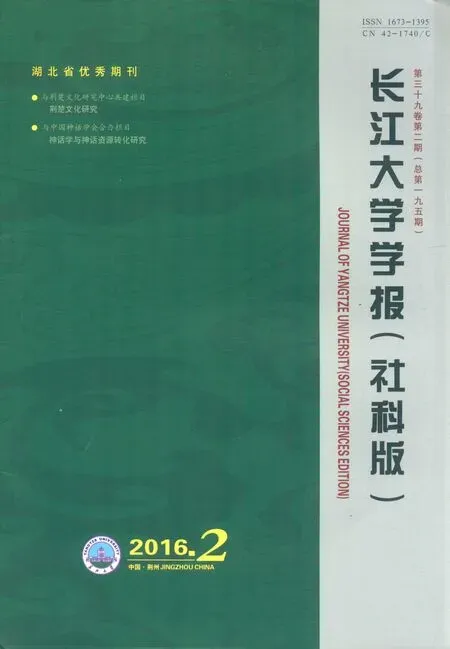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比较研究
——陈岗龙神话学研究述评
沈玉婵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比较研究
——陈岗龙神话学研究述评
沈玉婵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陈岗龙教授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蒙古民间文学、民俗学和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其神话学研究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个案研究,二是比较研究。研究重点也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蒙古族神话的比较研究与东方神话体系的建构及比较研究。陈岗龙教授的神话学比较研究并非单一的、平面的比较,而是在多民族文化视野中多角度、多层次、跨学科、跨体裁的立体研究。从比较研究的角度选择具体的题目进行个案的研究,以独立的个案研究探讨神话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这一研究方法贯穿了陈岗龙教授的学术思路和研究实践。
关键词:蒙古族神话;东方神话体系;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逐步扩展、不断深入,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在搜集整理大量的少数民族神话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多方法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陈岗龙教授在蒙古族神话的比较研究方面成果颇丰。陈岗龙教授涉猎广泛,在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等多个研究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蒙古民间文学、民俗学和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并就此出版多部专著和几十篇论文,其中对蒙古族神话的研究更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具有开创性意义。
陈岗龙教授的神话学研究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个案研究,二是比较研究。从比较研究的角度选择具体的题目进行个案的研究,以独立的个案研究探讨蒙古族神话乃至蒙古族民间文学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这一研究方法贯穿了陈岗龙教授的学术思路和研究实践。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结合将微观的研究与宏观的思考联系起来,由个案研究中产生的结论与宏观思考得到的观点相互印证、互为补充。陈岗龙教授对蒙古族神话个案的比较研究,既为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实践意义的方法论,也为我国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综观陈岗龙教授的神话学研究,其研究重点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蒙古族神话的比较研究与东方神话体系的建构及比较研究。陈岗龙教授的神话学比较研究并非单一的、平面的比较,而是在多民族文化视野中多角度、多层次、跨学科、跨体裁的立体研究。
一、多民族文化视野中的蒙古族神话比较研究
陈岗龙教授认为,蒙古民族的神话具有多元和多层次的特征,这种特征是在蒙古族与周围民族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因此,“我们研究蒙古神话只有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用多元文化的观点才能深入探讨蒙古神话丰富多彩的文化史内涵”。[1](P2)只有将蒙古族神话放在“更广阔的多民族文化背景下进行探究”[1](P1),才能从整体上把握蒙古族神话不同于其他民族神话的特点,才能探寻到蒙古族神话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这一思想和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2001年出版的《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一书中。
在此书中,陈岗龙教授通过对“蒙古族潜水神话的比较研究”、“蒙古族搅拌乳海神话的比较研究”、“蒙古萨满神话与阿尔泰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蒙古洪水神话中的基督教观念”四个个案的研究,梳理了蒙古族神话与北方阿尔泰民族神话之间、蒙古民族内部不同部落群体的神话之间、蒙古族神话与古代印度神话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点,梳理了蒙古族神话发展及演变过程中所受到的藏传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因素的影响。
在对“蒙古族潜水神话的比较研究”这一个案的研究中,陈岗龙教授将蒙古族潜水神话置于潜水神话这一神话类型所分布的大的文化圈内进行考察。他指出,潜水神话在西伯利亚、亚洲北部和北美洲最为集中,而且有潜水神话传承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各民族和北美洲印第安人均为狩猎民或游牧民,他们同属于萨满文化圈。在对萨满文化圈潜水神话进行论述的基础上,陈岗龙教授继续对蒙古族潜水神话与阿尔泰潜水神话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比较和深入的探讨。他指出,蒙古族潜水神话中的很多母题来自阿尔泰神话,如不断膨胀的大地拯救创造者和万物,敌对者不满创造神所创造的世界放出害虫和动物等。
在对潜水神话的研究中,陈岗龙教授还注意到创造神与其敌对者的关系,他对大林太良关于“潜水神话是创造神及其协助者(敌对者)共同创造世界的神话”的观点进行了发展和补充。他指出,蒙古族神话中的潜水神话是诸神神话的雏形,创造神创造世界的行为就是一种秩序的建立,而敌对者(潜水者)想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是不为创造神所接受的行为,由此产生创造神与协助者(敌对者)之间的矛盾。因此,潜水神话是“诸神神话的最初原型,因为潜水神话中创造神及其协助者或敌对者的矛盾就是诸神神话中诸神之间斗争的起因”[1](P7),而这也是蒙古族潜水神话与阿尔泰潜水神话的共通之处,“可以说,蒙古族潜水神话和阿尔泰神话是同一母胎中孕育出来的萨满创造世界的神话”[1](P7)。
陈岗龙教授认为,蒙古族潜水神话与阿尔泰潜水神话关系密切,是同一个神话母胎中孕育出来的,但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蒙古族潜水神话离潜水神话原型越来越远,与阿尔泰潜水神话之间的区别也愈大了。他在书中提供了布里亚特蒙古、喀尔喀蒙古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四个潜水神话文本,通过与阿尔泰潜水神话文本进行对比发现:布里亚特神话保持最古老的形态,喀尔喀神话体现了佛教的早期影响,而在内蒙古东部的神话中佛教的元素已经浸润其中。因此,“蒙古族的潜水神话离阿尔泰神话的中心越远,发生的变化就越大”[1](P6)。这一结论的得出是顺理成章且具有说服力的。蒙古族潜水神话的佛教化还体现在“由潜水创世类型和原人尸体化生世界的类型复合而成的乌龟神话逐渐代替了蒙古族古老的潜水神话”[1](P14)。而通过蒙古族潜水神话发生、发展、演变、变异过程的分析,不难推断出蒙古族神话与北方阿尔泰民族神话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佛教对蒙古族神话的影响,而这也证明了蒙古族神话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特征,这是蒙古族神话乃至蒙古族民间文学最重要的特质。
“蒙古族搅拌乳海神话的比较研究”通过追溯蒙古族搅拌乳海神话的印度原型,分析了人类的原罪、违反禁忌、恶魔降世等母题,比较蒙古族与印度搅拌乳海神话的异同,得出“蒙古族搅拌乳海神话属于创世神话范畴,而印度神话则属于诸神神话的范畴”这一重要结论。陈岗龙教授指出,蒙古族搅拌乳海神话不同于印度神话的地方在于:印度神话搅拌乳海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不死甘露,日、月是作为不死甘露的附属品出现的;而蒙古族神话搅拌乳海的目的是为了求得日、月,获得光明,黑雾(蟒古思)、甘露等则是作为光明的附属品出现的。之所以蒙古族神话将日、月作为搅拌乳海的目的所在,是因为在潜水神话、乌龟神话等创世神话中,创造神没有完成对光明的创造,“只有神创造了日月,才能拯救陷入黑暗和混沌的宇宙和人类”[1](P21)。在对此个案的研究中,陈岗龙教授还探讨了蟒古思故事、《格斯尔》史诗与搅拌乳海神话、尸体化生神话在主题、叙事模式上的相同点和相似性,指出蒙古族英雄史诗与蒙古族原有的萨满神话之间的渊源关系。这个结论打破了神话、史诗之间的体裁限制,从神话与史诗的叙事结构入手,结合蒙古族民间文学和蒙古族文化特点而提出,是具有突破性的学术观点,笔者将在下文中就此观点进行专节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蒙古萨满神话与阿尔泰神话的比较研究”集中探讨了神鸟、神与恶魔的斗争,萨满拯救人类,地下世界的旅行等在北方阿尔泰—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民族神话中普遍流行的主题,对蒙古族特别是布里亚特蒙古的萨满神话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通过对阿尔泰萨满神话与蒙古萨满神话的比较研究,对萨满的职能进行了阐述。这一研究从布里亚特蒙古的萨满神话入手,通过对神话中“神鸟”主题的分析,指出萨满作为人神交流媒介的功能及其巫术医治的职能,而萨满的职能与到地下世界拯救和医治人类的神话主题密不可分,萨满神话就与英雄神话发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一些关于格斯尔下凡降魔的主题来源于布里亚特蒙古最初的萨满神话。陈岗龙教授还指出,“在萨满与萨满灵魂附体与转换的观念中,有关鹫和熊的神话在结构上是对等的。”[1](P32)萨满与神鸟的神话中,萨满以鸟的姿态成为神人之间交流的中介,而到后期,萨满与熊的神话则警示了萨满灵魂离开肉体的危险。
“蒙古洪水神话中的基督教观念”从布里亚特蒙古创世神话的两个系统入手。陈岗龙教授指出,保留原始萨满教信仰的神话主要反映布里亚特蒙古先民的氏族社会,而比较晚的时候伴随基督教观念传入布里亚特民间后形成的创世神话渗透了基督教观念。他认为,“布里亚特蒙古人的两种神话系统表达了土著的原始宗教和后来接受的外来宗教的关系。”[1](P35)基督教所创造的有秩序的世界受到布里亚特蒙古本土文化和萨满教的反抗,而“古老的创世神话被赋予了新的宗教学涵义”[1](P36)。此外,陈岗龙教授还探讨了蒙古族的洪水神话。他指出,虽然布里亚特蒙古的洪水神话情节来源于《圣经》,但却具有独特性,是蒙古族洪水神话中最有特色的,他认为布里亚特蒙古的洪水神话不同于《圣经》洪水神话的人类再起源主题,它更多地反映了文化的再起源,“大洪水就象征着基督教文化的洗礼”[1](P38)。他提醒读者注意布里亚特洪水神话拒绝上大船的兽王猛犸象,强调猛犸象作为西伯利亚各民族神话中的创造神,是土著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保护者。“猛犸象拒绝搭乘神指使人建造的大船——按照基督教教义建造的大船而被毁灭,实际上隐喻了西伯利亚土著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拒绝……洪水使人类和猛犸象切断了联系,即与最初创造世界的创造神切断了联系。”[1](P38)布里亚特蒙古的洪水神话还可能隐喻了作为民族宗教的萨满教被国家宗教基督教(东正教)的替换。
传统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往往是“重知识、轻思维”“重分数、轻应用”, 主要体现在:教师在课堂上注重概念定理及计算方法的讲解,忽视知识方法的探索过程——思维的形成过程,即强调讲清楚“是什么”,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应试教育的影响没有改变,教师、学生无法脱离考试成绩的束缚,教师关心的是通过率,学生学习的目的多以通过课程考试为目标,忽视课程学习是以“用”为目的的, “学不能致用”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如何在教学中着眼于课堂教学中的思维活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与应用创新能力,是概率统计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陈岗龙教授对以上四个个案的研究借助比较的方法,分别从蒙古族神话与其他民族神话之间的关系、蒙古族神话与印度神话的关系、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因素对蒙古族神话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入手,选取了潜水神话、搅拌乳海神话、萨满神话和大洪水神话这四个流传较为广泛且各具特点的神话类型作为研究对象,以探求蒙古族神话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发掘蒙古族神话的独特性。这种多民族文化视野下的蒙古族神话比较研究的方法贯穿陈岗龙教授的学术思路。而在具体实践中,他从具体的个案研究入手,使用丰富的蒙古语第一手材料,通过对神话类型、情节模式、母题、主题等具体而微又层层递进的分析和论述,以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理论,辅以扎实的文本分析,对蒙古神话所蕴含的蒙古社会文化史意义和蒙古族神话与其他民族神话之间的渊源和影响关系,做出了深入的探讨,为蒙古民族与其他民族广泛而长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切实而详尽的证据。
二、突破体裁限制的蒙古族神话比较研究
陈岗龙教授在蒙古族神话的比较研究中,对传统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突破是显著的,这一点还体现在他对蒙古族神话与蒙古族英雄史诗关系的思考上。通过对蟒古思故事、《格斯尔》史诗中各种类型神话的分析,考究蟒古思故事、《格斯尔》史诗与蒙古族神话在叙事模式、情节单元、母题和深层结构上的相同点和相似性,探究蒙古族神话在蒙古民族史诗的起源、发展以及内容结构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种研究方式“从神话的形态学研究转变为神话学、史诗学和民间信仰研究等多学科内容相互交叉的综合研究”[2](P4),这种突破体裁限制、跨越多个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对探索我国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是我国神话学和史诗学研究上的方法论创新。
上述研究方法和学术思路在《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和2003年出版的《蟒古思故事论》两部著作中得到了详细阐释和具体实践。陈岗龙教授指出,流传于东蒙古的扎鲁特—科尔沁史诗蟒古思故事和布里亚特史诗《格斯尔》中,均保存了丰富的神话内容,既有古老的萨满教神话,也有后期受到印度文化和藏传佛教影响后发展变化的宗教化的神话,这些神话的汇集“形成了一个诸说混合论的体系”[2](P286),既构成了蟒古思故事和《格斯尔》史诗的重要内容,又为他们提供了“天神下凡人间,为人类斩妖除魔”的叙事模式。
陈岗龙教授分析了蟒古思故事开篇叙述的“搅拌乳海,提取日月,从而创造宇宙光明”主题,指出其原型是蒙古族搅拌乳海神话,且可追溯至印度教的诸神神话。他重点分析了“违反禁忌”与“恶魔的产生”这两个在蟒古思故事和蒙古族搅拌乳海神话中都非常重要的母题。在蟒古思故事中,蟒古思的产生是违反禁忌的结果,由于众神搅拌乳海时违反禁忌,超出限度,恶魔蟒古思就出现了,从而天神下凡人间是蟒古思故事和蒙古族搅拌乳海神话的共通主题,它实质上反映的是创世神话中创世神对宇宙秩序的确立和敌对者对宇宙秩序的挑战并尝试确立新秩序。在蟒古思故事中,蟒古思主要是被瓦齐日巴尼用金刚杵打死的恶魔拉胡的尸体化生而来的;而在布里亚特蒙古《格斯尔》史诗中,东方恶天神之首被汗霍尔穆斯塔·腾格里打败,尸体掉落后化生了三个恶魔。陈岗龙教授认为,蟒古思故事和《格斯尔》史诗中对恶魔起源的叙事模式是相同的,它们共同脱胎于蒙古族的尸体化生神话。
陈岗龙教授还分析了东蒙古蟒古思故事和布里亚特蒙古《格斯尔》史诗中的天神下凡降妖除魔的主题,他认为蟒古思故事和布里亚特蒙古《格斯尔》史诗中的降魔主题“不仅仅是从西藏和印度搬来的,它还有着本民族萨满教和古老神话的基础。而东蒙古蟒古思故事中天神下凡的主题也和《格斯尔》史诗有着不可切割的联系”[2](P305)。他比较了阿尔泰神话、《格斯尔》史诗和蟒古思故事中的神话内容,指出三者在“渊源和叙事模式上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而且,各神话形象之间具有亲缘关系”[2](P309)。此外,在《格斯尔》史诗的开篇,东西方天神之间的争斗导致恶魔的降生,因此天神格斯尔下凡拯救人类的主题与蒙古族神话中东西方善恶天神争斗,恶天神作祟引发疾病和死亡,萨满拯救和医治人类的主题是相似的,从这一点来看,《格斯尔》史诗开篇的主题是蒙古族萨满神话中萨满拯救和医治人类的神话主题的翻版。因此,他推断,“格斯尔下凡降妖除魔的主题出胎于蒙古古老的萨满起源神话。即格斯尔下凡的主题是蒙古最初萨满神话和《格萨尔》史诗西藏原型相结合的产物”[2](P306)。他进一步论证并指出,藏族格萨尔下凡的主题是在藏族原始崇拜和印度传入的思想理念等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而蒙古族萨满教和蒙古族神话观念中神魔交战或善恶神交战引起疾病和恶魔,人类需要萨满医治和拯救的古老主题,正是适合移植《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土壤,二者从叙事模式上是相通的。继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蟒古思故事等史诗中天神下凡降妖除魔的主题和叙事模式很可能是西藏《格萨尔》史诗和蒙古族原有的最初的萨满神话在主题和叙事模式上的结合。
陈岗龙教授对蒙古族神话的分析突破了民间文学体裁的限制,将蒙古族神话和史诗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主题和叙事模式上综合考察二者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探讨二者相似性的根源。他以蟒古思故事和《格斯尔》史诗中的降魔主题的来源为研究重点,分析表现降魔主题的蒙古族神话在蒙古族英雄史诗的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上述研究,探究作为蟒古思故事和《格斯尔》史诗等蒙古族英雄史诗产生和传承前提的民众叙事模式,以及他们通过神话和信仰表现的世界观,而这种民众的世界观正是蒙古族神话与史诗在主题,特别是叙事模式上存在相似性的根本原因。传统的观点通常认为,史诗是神话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史诗与神话之间具有承继的关系,史诗是以古代神话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对神话与史诗关系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并没有深入至神话与史诗的本质和深层结构。此外,这种观点是在研究西方神话与史诗特别是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这些神话与史诗从源头和结构上看更为单一,而东方神话与史诗,例如蒙古族英雄史诗与神话,则更为复杂,具有多元、多层次的特点,上述对神话与史诗关系的判断就显得流于表面了。陈岗龙教授对蒙古族神话与蒙古族英雄史诗关系的分析和判断,为我们探讨神话与史诗的关系开拓了新的思路:二者之所以在主题特别是叙事模式上具有相似性,也许并不能简单地被判定为谁继承了谁的关系,这种相似性的根源,是民众独特的世界观、思想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这种独特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决定了某一民族的民众在构建其社会形态、构思民族神话和民族史诗时在结构和模式上的一致性。
综上,陈岗龙教授对蒙古族神话的比较研究并非单一的、平面的比较,而是在多民族文化视野中多角度、多层次、跨学科、跨体裁的立体研究。首先,在研究范围上突破了国别神话比较的视域,对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的神话、一个民族内部不同部落的神话等进行比较,如蒙古族和印度搅拌乳海神话比较,蒙古族和阿尔泰潜水神话的比较等;其次,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相结合,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相联系,除了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部落神话的比较,也重视某一特定民族或部落的神话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如布里亚特蒙古的潜水神话的不同文本就反映了同一神话类型在布里亚特蒙古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再次,在研究方法上坚持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并不将神话研究仅仅限定在文学文本的研究,而是广泛使用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如对萨满神话的研究就考察了成为萨满的仪礼和巫术治疗等萨满仪式,借助对萨满职能的阐述,将萨满神话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最后,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体裁限制,将史诗和神话结合起来,将神话的形态学研究转变为神话学、史诗学的综合研究,如对蒙古族神话与蟒古思故事、《格斯尔》史诗中各类神话在叙事模式、情节单元、母题和深层结构上相似性的探讨。坚持蒙古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一思想贯穿陈岗龙教授的学术思路和实践。
三、建构东方神话体系的设想与东方神话比较研究
2001年,陈岗龙教授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持工作,担任第二主持人,他的学术重点也从对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转向对东方民间文学的研究,先后主编并出版《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东方民间文学概论》(四卷本,昆仑出版社,2006年)、“东方民间文学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第一批书于2008年出版)等学术著作。随着近年对东方民间文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梳理和探讨的不断深入,陈岗龙教授结合神话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尝试探索东方各国神话的趋同性,建构超越一国神话的东方神话体系。虽然尚未出版专著或发表论文,对东方神话体系的建构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论述,但相关的思想和表达散见于陈岗龙教授近年的学术成果。
陈岗龙教授在论述东方民间文学与东方文学的关系时提出,随着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加强及文化多样化的强调及比较文学研究的盛行,在东方各国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将东方民间文学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将成为研究的主要趋势,这是我们进行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他指出,研究的目的,并非“建构一个强调和突出异质特征的东方民间文学价值体系来与西方对立,而是通过描述东方民间文学的实质内容和整体性的历史逻辑,补充和完善民间文学理论中那些根据西方或欧洲民间文学的经验得出的理论和观点,使人类一般性民间文学的描述和理论更加全面和多样化”[3]。同理,对东方神话体系的建构以及对东方神话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也是出于补充和完善西方神话学理论和观点的目的。那么,建构东方神话体系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季羡林先生在谈到文化体系时指出: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发展的文化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且影响较大、基础统一且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形成独立的体系,就可以称为“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衡量,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可以归并为四大古老的,且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前三种属于东方,最后一种属于西方。这样形成的文化体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季先生进一步强调,东方三大文化体系之间,交流活动是经常的,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是既接受,又给予的,没有一个文化体系是封闭的,因为封闭式的文化是没有发展前途的。[4](P498~501)季羡林先生对东方三大文化体系的论述为我们建构东方神话体系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所谓东方神话的概念,并非是相对西方神话而提出的,“而是在人类民间文学规律的探索中更加注重东方文化区域性规律的描述与探讨。我们强调的是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交流和接触比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接触发生得更早、更广泛、更深远”[3],这也是东方各国、各民族神话之间具有更多趋同性的根本原因所在,深入探讨东方各国、各民族神话之间的渊源关系和趋同性,是“更好地探讨人类民间文学的共通规律”[3]的基础。
陈岗龙教授认为,如果将东方神话作为一个整体的神话体系,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此部分内容为笔者根据陈岗龙教授在北京大学亚非系所授东方神话专题研究课程的课堂笔记整理。。
首先,对东方神话的研究要从古代东方神话和现代活形态神话的研究两方面入手,二者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不同。我们所接触到的古代东方神话均以文献的形式记录和保存,例如《金字塔铭文》和《亡灵书》中所记载的天牛之书与奥西里斯神话等,苏美尔泥板和楔形文字所记录的吉尔伽美什与大洪水神话,吠陀经典特别是《梨俱吠陀》及两大史诗中保存的印度神话等。因此,在考察古代东方神话时,根据文献资料,从口头传统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还要注意对神话文本的辨别,注意神话文献与口头性的关系,注意东方宗教典籍对神话的改编和再造。而现代东方神话则仍以活形态的形式在一些地区和民族口头传承。对于这些活形态的神话,一方面要根据学者搜集记录的可靠的神话集来研究,另一方面要进行民俗学田野调查,在民间口头表演中进行研究。此外,我们还应注意这些国家或民族在文献典籍中保存的古代神话与现今仍以活形态形式传承的现代神话之间的关系。以印度神话为例,其古代神话大部分保存在《梨俱吠陀》和两大史诗中,但要注意的是,印度神话并不等同于梵语神话,也不等同于史诗神话。印度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活形态的神话极少被主流认识和接受,事实上,两大史诗在印度的许多地方仍以活形态的形式口头传承,正确认识古代印度神话和现今仍以活形态形式传承的现代印度神话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古代东方神话不仅仅是文学样式,它也是古代东方文明的一部分。对古代东方神话的研究,要注意古代东方文明与神话学研究相结合,因此,正确处理神话与国家起源的关系、神话与宗教的关系、地方性神话与国家神话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以印度神话为例,印度神祇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复杂,且神祇的神格不断发生上升、下降或移位等变化,而这些变化与社会、宗教发展密切相关。例如,因陀罗神最早以自然神出现,随着雅利安人东进,其神格发生变化,成为战神,并不断提高至至高神,在婆罗门教确立后,因陀罗被赋予刹帝利的种姓品格,神格下降,后又被佛教利用,作为佛教护法神,因陀罗成为了佛教思想的载体。
最后,古代东方神话中所反映出的古代东方相似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古代东方神话中存在着很多共同的母题,如大洪水神话在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希伯来、古代印度和古代伊朗等地广为流传。共同母题的背后,蕴藏的是古代东方各民族相似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例如,古代东方神话强调人、神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由整个古代东方思维的特点——平衡性与整体性所决定的。又如,古代印度神话、古代埃及神话和古代伊朗神话中创世的循环,所反映的是古代东方人思维中循环的时间观,而这一点与西方神话所反映的线性的时间观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综上,东方神话体系的建构是合理且可行的。陈岗龙教授认为,“研究东方文学首先要着力于东方各国的民间文学和它们之间的历史的、文化的联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趋同性……从而建构超越一国民间文学的东方民间文学。……不是东方各国国别民间文学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从东方各国民间文学内容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一般性的‘民间文学’,而是通过分析东方各国民间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和久远的历史接触关系,揭示其共同的区域特点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显现其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有机整体”[3]。东方神话作为东方民间文学的重要体裁,其研究方法也应遵循上述原则。陈岗龙教授强调,东方神话与东方各国、各民族的神话不能简单被认定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挖掘各国各民族神话“之间的历史联系和由此形成的共性,用这种历史联系和共性来建构超越”[3]国别和民族的具有东方特点的区域性神话体系,是东方神话研究和东方民间文学研究的要求和目的所在。
四、结语
回顾陈岗龙教授的学术思路和研究实践,从蒙古族神话研究到东方神话研究,比较的方法作为重要的方法论贯穿始终。他将民间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相结合,将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联系,运用民间文学、比较文学和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通过个案研究,深入探讨民间文学所体现的民众思想及其蕴涵的文化史意义,通过微观的个案研究,来探讨和论证神话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问题,将微观的具体研究与宏观的理论探讨相结合,对我国神话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事实上,在比较文学发展的初期,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就是密不可分的。季羡林先生在《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中指出:没有民间文学,就不会有比较文学的概念。[4](P521)既然比较文学研究与民间文学研究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在面对民间文学材料和文本时应该怎样进行比较?应该从何处入手?陈岗龙教授的学术实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角度和视域。
陈岗龙教授对神话学的思考,还体现在他对西方神话学与东方神话之间关系的思考上。他反对简单地将某一种西方神话学理论直接套用。他强调,在对中国或东方某一个神话类型或神话文本进行研究时,理论和方法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否则就是用东方神话的个案为西方神话学理论做了注脚。西方神话学理论是在西方学术话语中提出并发展的,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局限性。作为中国神话或东方神话的研究者,其任务是描写出那些西方民间文学理论还不能完全概括的人类文学多样性中的中国神话或东方神话内容,用实际内容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3]
陈岗龙教授在神话学研究领域的贡献并不仅限于上文所述,但最为突出的是,他对神话学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为后续的研究者开辟了神话学研究的新疆域。
参考文献:
[1]陈岗龙.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陈岗龙.蟒古思故事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陈岗龙.东方民间文学与东方文学[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4]季羡林.季羡林全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琛E-mail:qiangchen42@163.com
A Comparative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Cultures——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Chen Ganglong’s Mythology
Shen Yuchan
(ForeignLanguageDepartment,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Professor Chen Ganglong’s academic contribution lies in Mongolia folk literature,folklore and oriental folk literature research,which research focus on two aspects:one is the mythology of the case study,two is comparative study.Research also has experienced two stages,namely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yth of Mongolia and 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mythology system and comparative study.A comparative study on Professor Chen Ganglong’s mythology is not a single,flat comparison,but is multi angle,multi-level,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 genre study in the view of multi-national culture.From angle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lection of specific subject to conduct a case study,with independent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the rul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myth,this approach throughout Professor Chen Ganglong’s academic ideas and research practice.
Key words:Mongolia myth;oriental mythology system;comparative study
收稿日期:2016-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B071)
作者简介:沈玉婵(1983—),女,河北唐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方民间文学和神话学研究。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6)02-00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