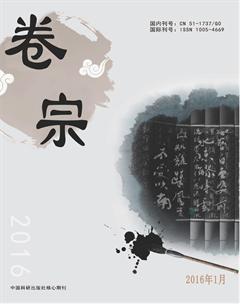探究新石器时代的储水器
魏美丽
摘 要:泾渭流域属于非常典型的考古文化区域,本文研究的泾渭流域的范围基本在泾水(东)—西汉水流域(南)—湟水流域(西)—渭水流域—河套地区(东北)的区域之内。泾渭流域地形主要为高原与冲积平原,其中包含了多条山脉与河流,为该地区远古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传播等提供了非常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关键词:泾渭流域;新石器时代;储水器
1 泾渭流域新石器时代储水器的研究意义
泾渭流域具有非常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这促使该地区成为了远古文化考察工作的重点区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与考古学家的广泛关注。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在泾渭流域发现了六种考古文化遗存,拉开了泾渭流域远古文化考察的大幕。直到80年代初,甘肃省博物馆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秦安大地湾遗址、王家阴洼遗址等,丰富了泾渭流域远古文化的内容,明确了泾渭流域各类遗存的文化面貌与特征,为泾渭流域远古文化深层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考古学文化在结构方面是具有层次性的,在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从浅到深逐渐的深入,从而对考古学文化中所包含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行揭示[1]。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储水器是最具特征的陶器之一,同时也是最为常见的、必不可少的陶器。与其他的陶器相同,陶质储水器同样具有质地脆弱的特点,且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经常移动,很容易破损。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储水器的形态变化非常的频繁,且较为敏感。不同形态的储水器与相对应的陶器群形成比较稳定的组合,通过这些陶器组合能够对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进行直观反映。
在器物的组合中,陶质储水器是普遍存在的,对储水器的产生、发展、形态变化等进行研究,有利于对考古学文化的产生、发展与传播等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实现对固定时空框架中人类共同体的客观、准确考察[2]。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陶质储水器就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是陶器组合中最具典型性的类型之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新时期时代晚期的半山文化、马厂文化中。储水器经历了将近四千年的发展,其共同点是储水器在陶器组合中始终是最具典型性的器物,不同点是储水器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形态。通过对储水器发展过程中形态变化进行分析,有利于对器物发展演化的渐变规律进行探究。
从考古学角度来讲,新石器时代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进入磨制时期,标志着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3]。泾渭流域地形主要为高原与冲积平原,其中包含了多条山脉与河流,为该地区远古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传播等提供了非常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泾渭流域的储水器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级阶段储水器主要代表为小口球腹凹底壶,中期储水器主要代表为尖底瓶,晚期储水器主要代表为平底壶、平底瓶。不同发展阶段的储水器自成序列发展与变化,但是相互之间又存在着相互的联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考古学问题。因此,很多考古研究者都将泾渭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储水器作为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典型标准器。
2 泾渭流域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储水器研究
仰韶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范畴的文化。各种储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特征,故也称为彩陶文化[3]。依据已有研究中提出的“仰韶文化”时代概念,将泾渭流域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仰韶文化为新石器时代发展中期,将早于仰韶时代的新石器时代视为先仰韶文化,将晚于仰韶时代的新石器时代视为后仰韶时代。本文从这三个阶段对泾渭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储水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需要说明的是先仰韶时代中的大地湾文化等并不是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段,由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储水器遗存较少,本文不做分析。
在泾渭流域,先仰韶时代古文化较为发达的为泾渭流域,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研究发现,泾渭流域先仰韶时代古文化与陕晋豫交界区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泾渭流域先仰韶时代的遗存主要包括大地湾文化。大地湾文化中的储水器代表为小口球腹凹底壶,是迄今为止泾渭流域发现的最早的陶质储水器,其主要的特征包括造型简洁、实用性较强,陶器的质地比较疏松且胎中夹细砂,储水器的表面处理较为粗糙且存在斑状[4]。通过这些特征可知,该时期的陶器制造业还处于原始发展阶段。大地湾文化的储水器经过发展,在小口球腹凹底壶的基础上实现了瓶颈、瓶耳的创新,器表开始用磨光工艺。这说明该时期的陶器制造技术得到了发展。
本文选取了大地湾二期遗址作为研究对象。本遗址地处渭河中上游地区,与半坡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同。储水器多为附双腹耳葫芦形口的尖底瓶,陶质多为细泥或者是泥质红陶,陶器的烧制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5]。
先仰韶时代的典型器小口球腹凹底壶经过不断的演变,在仰韶时代转化成为了尖底壶。小口细颈平底瓶在仰韶时代的早期非常的流行,只是该器的使用功能出现了变化,原来的双耳也逐渐消失。通过对大地湾遗址资料的分析,泾渭流域在仰韶时代早期较为流行的储水器为葫芦形口尖底瓶,与之同时流行的还有小口细颈平底壶与葫芦形口平底瓶,其中小口细颈平底瓶起源于先仰韶时代晚期,葫芦形平底瓶则与葫芦形口尖底瓶出现时期相近。
从器物形态学角度进行分析,泾渭流域先仰韶时代的储水器演进的规律为:口部从简单到繁琐;颈部从无到有再到高颈的发展;最大腹径从上到下不断移动;器耳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整体器形从矮胖逐渐向着瘦长发展。
在对泾渭流域仰韶时代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本文选取了大地湾三期遗址作为研究对象。
在仰韶时代中期,典型器为重唇尖底瓶,但是葫芦形口尖底瓶并沒消失,且非常常见[6]。从重唇尖底瓶与葫芦形口尖底瓶两者的形态分析,重唇尖底瓶不可能是从葫芦形口尖底瓶演化而来的,由此可以推断重唇尖底瓶的起源另有所属,但是由于相关的资料有限,不能更深层次地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但是储水器发展过程中与重唇尖底瓶相关的迹象却值得引起重视,在老观台文化龙岗寺的小口瓶口部形态、半坡文化的小口瓶口部形态等都与重唇尖底瓶的瓶口形态存在一定的渊源。当前,通过已有的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证明,与重唇尖底瓶相比,杯形口尖底瓶的产生阶段要略早一些,但是两者的产生、发展与演进都是遵循着各自的路径,原始形态都可以追溯到仰韶时代早期甚至是先仰韶时代晚期。通过陶器的演进过程与器形形态变化规律的角度进行分析,杯形口尖底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演进成为葫芦口尖底瓶。
晚期盛行的为退化重唇口尖底瓶与平唇口尖底瓶。在泾河以西的地区,文化在大地湾三期之后就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其中一条通过石岭下类型文化的不断向西发展,与当地的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之后形成了马家窑文化,其中心为洮湟流域;另外一条经过大地湾上层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了常山下层文化,其中心为泾渭流域。以大地湾四期遗存为代表进行研究,其中石岭下文化中最具特征的储水器为平唇口尖底瓶,继承了中期的重唇口尖底瓶的重唇退化而形成。随着文化不断向西发展,使的尖底瓶在洮湟流域也有所普及[7]。
在大地湾四期遗存后段中出现的喇叭口尖底瓶在泾水以东地区沿用了较长的时间,直到后仰韶时代的各种文化中已经比较常见;在泾水以西地区却并未沿用较长时间,很快就被喇叭形口平底瓶所替代。喇叭形口平底瓶出现取代了贯穿整个仰韶时代的尖底瓶[8]。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喇叭形口平底瓶意味着仰韶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后仰韶时代的开始。
在后仰韶时代的早期,比较流行的储水器为喇叭形口平底瓶,这种类型的储水器是由喇叭形口尖底瓶发展而来的[9]。因此,在后仰韶时代初期,虽然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大量盛行喇叭形口平底瓶,但是在这些地区依旧可以看到少量的喇叭形口尖底瓶。陕西扶风案板一期文化盛行的喇叭口广圆肩平底瓶、泾渭流域常山下层文化所流行的短颈喇叭形口平底瓶,在经过了侈口高领折肩罐之后发展到后来齐家文化的双耳折肩罐。泾渭流域的马家窑文化中最常见的长颈喇叭形口平底彩陶瓶对半山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河西走廊则比较常见粗直颈瓶式平底彩陶壶。马厂文化流行的侈口瓮式平底彩陶壶是兰州地区黄河沿岸的特征性器物之一[10]。
3 总述
甘肃省发掘的遗址较为重要的包括秦安大地湾遗址、王家阴洼遗址等,丰富了泾渭流域远古文化的内容,明确了泾渭流域各类遗存的文化面貌与特征,为泾渭流域远古文化深层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以泾渭流域为研究对象,选取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储水器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新时期时代泾渭流域的储水器从先仰韶时代的壶逐渐发展成为了仰韶时代的瓶,到后仰韶时代又演化出了形态多样的壶,储水器的这种变化符合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泾渭流域新时期时代的储水器研究还存在着很多空白需要填补,而填补的过程中必须依赖该地区大量的重要遗址资料的公布,以便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研究泾渭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点。
参考文献
[1]董广辉. 泾渭流域新石器文化演化及其环境动力研究进展与展望[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13,04。
[2]李志等.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羊毛开发的动物考古学研究[J]. 第四纪研究,2014,01。
[3]邓振华. 泾渭流域新石器时代聚落时代变迁与区域对比[J]. 华夏考古,2014,04。
[4]苏海洋. 甘青宁新地区石器时代遗存的地理分布及其自然背景[J].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02。
[5]石硕. 从新石器时代文化看黄河上游地区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0。
[6]石硕. 藏彝走廊地區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类型及其与泾渭流域的联系[J]. 中华文化论坛,2006,02(59)。
[7]李映福. 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狩猎工具看经济形态的转变[J]. 四川文物,2007,04(68)。
[8]孙永刚.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述论[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