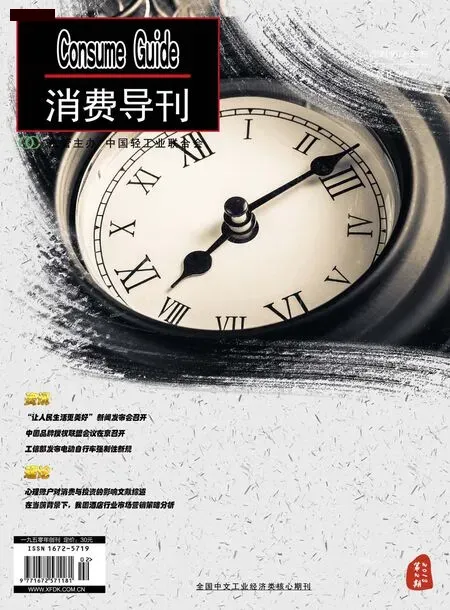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关系研究
刘海珠 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关系研究
刘海珠 最高人民法院
摘 要:随着民法典编制工作的有序开展,关于知识产权是否应当入编的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笔者拟将知识产权与物权进行对比研究,指出虽然由于调整对象的不同,二者有诸多区别,但知识产权和物权一样,属于一种支配性的私人财产权,知识产权应当编入民法典,适用民法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知识产权 物权 关系
探讨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关系之前,需要先确定知识产权的性质,关于此问题,目前学界观点不一,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以可以产业化的符号表达为对象的私人财产权。
一、知识产权的性质
(一)知识产权是私权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知识产权是私权”。这是知识产权私权性的规范来源。知识产权是私权指的是:一知识产权权利的交易主体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人,即在知识产权权利流转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平等。二知识产权是私有的权利,即与公有相对,是为特定人享有的权利。三知识产权是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权利。因此,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使和保护适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离开民事权利体系,知识产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找到其相应的归属。[1]
知识产权法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浓烈的公法色彩,来源于特许制度。同时由于知识产权对象自身的特性,无法像物那样由权利人绝对的支配控制,因此需要法律的拟制之力予以保障,并且下文将讨论的知识产权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其需要大量公法规范予以明确。因此法律规范上含有不少程序法和公法规范。另外,知识产权对象的取得必然需要利用公有领域的知识资源,其天然具有社会性,会受到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限制。这些因素导致知识产权法乍看有公法色彩,但其仍然是以实体法为基础的私权制度。其权利的取得、管理、变动、救济程序无一不是以创造权利为中心,并且是权利决定义务,而非义务决定权利,即以权利为本位。在规范方法上以授权性规范为主要内容,在立法重心上,以保护创造者权利为首要。[2]知识产权的程序法和公法规范主要是为了规范权利的取得程序、确定权利的范围、公示权利的流转,都是为了保障私权的正常流转、最大限度降低交易成本,相当于物权中的公示制度。物权法对于不动产也有相应的程序法和公法规范,但不能否认物权的私权属性。
综上,知识产权法是在平等主体之间分配财产关系,并不涉及公共事务,知识产权是私权。
(二)知识产权是财产权
从现行的法律规范上看,我国著作权法既规定了著作人格权,又规定了职务作品,法人可以成为作者,导致立法规范的前后矛盾;同时规定视听作品、部分职务作品的作者仅享有署名权,而没有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与人格权的内涵又有冲突。
从社会经济活动来看,将知识产权视为纯粹的财产权,更符合经济活动的现实。作为第二性的法律制度,是服务于社会、经济活动的,不能脱离现实发展的需要。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对公元900年到公元1700年这800年时间里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的原因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个提供适当有效的个人刺激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之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3]
综上,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而非人格权,更符合概念的明确、立法的体系化及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知识产权是以符号为对象的财产权
本文赞同符号论的观点,即把知识产权的对象解释为符号组合。符号是人为创设的、具有指代功能的信号。符号具有信号的共性,能够反映一定的信息。[4]知识产权的对象在客观上具有一个突出的共性:价值不是来源于自身的物质属性,而在于能够描述来之不易的信息。[5]知识产权的对象表现形式是符号组合,其本质是能够反映知识。
符号论与形式论、信息论相比,其优势在于能财产的存在形态上很好得将知识产权的对象统一起来,概括了所有知识产权形态的共性,能清晰得与物权、债权进行区分,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财产权体系。
符号论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如在商标领域,商标就是一种商标权人向消费者传递商品信息的符号,也是消费者用来获得商品信息、识别商品的重要工具。在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时,除了要考虑商标是否相同或近似,还要考虑商品是否相同或类似。即使是相同的商标,但是使用在不同或不类似的商品上,也不一定就构成侵权。商标的外在表现仅仅是符号,但是构成其权利的基础在于其特定的指代功能。因此,构成侵权的前提是是否破坏了这种指代功能,也即是否造成混淆误认。
二、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区别
根据传统物权理论,物权的客体是确定的有体物,与知识产权的界限明显,但随着科技进步与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为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物权客体的范围逐渐扩大,物权客体呈现出抽象化、数字化、证券化、无形化的趋势。物权的客体是物,物是可被人感知的,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必须是特定的物,物之特定性为物之可支配性提供了可能,即物能依其自身属性加以确定。物权的特定性既包括物理上之确定性,也包括依据一般社会观念或经济观众而具有之确定性。[6]
与之不同,知识产权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一、知识产权的对象虽然是产业化的符号组合,但这仅是其形式,其权利的内容并不确定。而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二、知识产权分配了基于产业化的符号组合所生之利益。一方面,符号是人类据以沟通、交流的工具,与各国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相比于物权,有更明显地地域性,各国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定差异更大。各国技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为更好地保护创造性成果传播,当然会在保护水平、执法力度方面有所差别,即同样的知识产权在不同的国家的保护的范围及强度有所不同。同时,即使在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关于知识产权的内容也会有很大不同。三、知识产权的载体数量及形式具有不确定性,即其载体作为知识产权商品或产品具有独立的价值,并且
载体与载体之间存在形态并不完全一致。承载着相同知识产权的载体在物权法上属于不同的物。四、知识产权是能产生市场利益的符合表达,即能进行产业化,与数字化的物权客体有明显不同。五、知识产权相比物权,权利状态具有不稳定性,易被无效或撤销。
产生知识产权不确定性的原因在于,作为知识产权对象表现形式的符号本身是需要解释的,同时这种解释又受到文化、传统、经验的影响。而同样是符号形式的数字财产或虚拟财产用了数字作为表现形式,就不会受到这种指代不明的困扰。
三、知识产权与物权的联系
虽然有上述区别,从传统的物权和债权二分的财产权体系来看,知识产权与物权更接近,都表现为支配权,都不需要特定人的主动作为即能实现权利。民法对财产关系的反映往往要采取确认权利和具体的行为规则的方式。物权在本质上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与物权是对物权的论述并不矛盾,前者是从物权关系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的角度着眼,从这个意义上说,物权关系表现为一种绝对法律关系,体现的是特定权利人因为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与不特定第三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它区别于在特定人之间发生的相对法律关系。[7]与之类似,知识产权关系也是一种绝对法律关系,体现的是特定权利人因为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利用而与不特定第三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
知识产权权利对象本身作为一种符号,进入流通领域,必须依附一定的载体而存在,此时的商品或产品上既有知识产权又有物权。知识产权必须依附一定的载体而存在,就成为二者重要的联结点。
综上,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而在财产权制度中,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关系最近,同物权一样,是一种支配性的财产权,因此,知识产权同物权一样,在编制民法典时,与物权有着同等地位。
参考文献:
[1]吴汉东.知识产权本质的多维度解读[J].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2]吴汉东.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3]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一版序言IV
[4]李琛著.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126 页
[5]李琛著.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127 页
[6]高新玉.物权客体范围之扩展[J].载于中国知网.2015年12月21日访问
[7]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