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理想的诗——关于刘洁岷的诗歌
■但红光
写理想的诗——关于刘洁岷的诗歌
■但红光
在书写越来越自由的时代,诗歌在我心中,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走向。一种存在于广大媒体的调侃之中,他们的作者为了眼前的功利(如“鲁奖”等),罗织出了一批被称为“xx体”的诗歌,激发出大家对现代诗歌的不屑和进一步疏离。另一种则基于个人的阅读和写作实践。对我而言,古典诗歌的难度似乎更多地局限于声律和用典上,在意义阐释上难度似乎小得多,其技法演变缓慢而易于觉察。现代诗歌理论却更为激进、多变,个人或流派风格更为明显,其语体的讲究、意象的安排、语词的拈用、节奏和排列的匠心似乎都与古典迥然不同;在阅读中,我常常疑惑该取哪条路径才能更加准确地逼近其真实意旨,因为在“85”之后,我甚至不知道现代诗歌理论又经历了哪几代发展,当今代表性的诗歌流派有哪些,而偶尔为之的诗歌试笔,更是让我缺乏展示的勇气,那些直白或意象简单的、押韵的长短句和许多现代诗歌相比,更像打油诗或口水段子。刘洁岷说“做一个优秀的写作者的前提之一是──成为一个杰出的读者。” 但是,诗歌在我心中更象一座被抽掉阶梯的圣殿,只能仰望,却不得其门径而入。
我相信我的诗歌阅读体验在读者群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许我们违反了诗歌阅读的大忌:在小说、散文等叙述文体的误导下,过于寻求阅读的精确性和明晰化。因此,在阅读刘洁岷诗歌的过程中,潜意识里,我始终带着对当代诗歌的求解和刘洁岷诗歌的求解两大疑问在逐步推进。有鉴于此,本文只是一篇粗浅的阅读体会。
谈及其诗歌理念,刘洁岷说“我们的选择只能是在不理想的时代写理想的诗,在理想的时代背诵、默写、测考、反刍理想的诗篇。” 我认为“理想的诗”是解读刘洁岷诗歌的一个好的切口;其“理想的诗”既指内容上写“理想”的诗(写什么),也指形式层面上“理想的”诗歌特色(怎么写)。
一、写“理想”的诗
对现代诗人而言,“理想”似乎是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意味强烈的词汇,也许它更适宜青春热血的年纪和某一特定时代(如革命年代)或某些特定的人;也许对某些诗人来说,它无异于浅薄与幼稚,尤其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但理想不应只在社会或政治意识形态上求解,它亦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个体化的诗意选择。在理想层面上,刘洁岷的诗歌都属文人诗歌,浓厚的精英意识与文化思考贯穿始终,纵使其底层关注和口语取向上特色明显亦未能遮蔽其时代特色显著的理想抒情。

刘洁岷
翻看其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作品,虽然时代已经远去,技法已经融入了“非风格化”和日常场景及社会生活的琐屑关注,但80年代书写“墓志铭”,寻求“钥匙”、“光明”、理想,文明和高蹈文化精神的印记依然未能擦除,在《刘洁岷诗集》中,其1992到1995年的诗作密集地出现了天空、月光、云端及白鸟意象。如
“你的足音残留在空远的溪谷
书翻了两页
画涂了几笔
你的门前,是一派河上风光
云端的鸟群
房间的啁啾”(《房间的啁啾》1991)
“最初的日子
美丽的白云从天空中飘过
脸一下子就红了
亲眼看到数不清的少女”(《在最初的日子里》1992)
“一只白鹭飞来
滑入附近的杉林
这事,我对二三个人
提到过
一行白鹭回翔着
在一小片杉林上
那天,我开始写信
我说,那是真的
被一场暴雨惊醒
我起身奔向那片林子
林间黑糊糊的,而幼鸟
白花花铺了一地”(《白鹭》1992)
“黄昏,沐浴的人们散开
留下一张空桌子。桌上蹲着
一只快飞死的鸟
鸟,和低狭的天空
都笼罩在
一片漫射光的色调里”(无论何时,无论何方,1993)
熟悉的身影在曦光中消失
海边亮晶晶的白房子
你走了,留下的寂寞几乎失真”(《被遗忘的人》,1993)
“因为拥有一个卓越的集体
因为奶罐遍布了整个大地
按照规划,满树满阳台的水果
白蒙蒙的光线洒在那片绿茵上”(《阐释》1994)
我已成年,我在我的纪念品中间
做的只是象征的,凋敝的买卖
怀着主妇的羞耻与逻辑,这不
我又还原成一个悲哀的好人(《我在我的纪念品中间》,1995)
这些诗歌有着浓烈的20世纪80年代特色与海子影响印记,“云端”、“少女”、“纪念品”、“白鸟”、“奶罐”都是一些习见的、圣洁的诗歌意象,它们可以看作是刘洁岷前期的诗歌理想。
1995年前后,其诗歌中的圣洁意象逐渐褪隐。这是大环境下,现代诗人群体们的一种集体选择。“经过公元1989的剧烈转折,1990年代的诗歌已不再像饥饿中的粮食和阳光中的火焰,它的魅力在不断流动,聚散,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平凡、自足而又饱含对应中的感召。”意识形态的转换始终是落后于时代的,所以这种转换稍显迟滞,在西川等诗人的作品中,这种迟滞与惯性更加强大。如果说刘洁岷1995之前的诗歌是对天空歌唱的诗歌,1995之后,其诗歌更多地回归到生活,与生活对话,与他人对话,是地面上的、对话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大多有一个“我和你”,或“我和它”的对话。如《电动熊》(1996):
我所描述的都在世间存在,快点,快点
现在让我们开启它的愤怒装置
它开始冒烟喷火:请转告
我20年没见过面的母亲
我一直,对她怀有很深很深的恐惧
和厌恶——也许是我把她
与一个穿黄制服的家伙弄混了
她严峻地对我说,请干正事!意思是:人在清醒时别忘了往怀里揣苞谷
这非关盲人或者残疾人的事
但确实,有些人活着,但眼睛早死了
没看到幽默的死者在幽暗的空中
向我们反复投掷镜子
而它嘛不过是玩具柜里的电动熊——
现在,大伙儿听好了:关掉椰子糖
作品对以电动熊为意象,嘲弄了某些人的物欲和假正经的生活方式,前期关于天空的意象被给人现世简朴快乐的玩具代替。同期的《日志》开篇:
“伞。票。文件夹
一个称呼
一辆车。蛀牙。订婚照
金属制品。证件”
让人联想到于坚的《0档案》,其琐碎与庸常与前一时期的高蹈大为不同,但在诗句的后半部:
“人们的青铜双颊泛起潮红娱乐中心门口的灯火,与刚刚升起的星光
混成了一片”
表明不变的先锋意识与启蒙精神依然留存。其中娱乐的“灯火”与初升的“星光”是一对相反的喻体。
其后的《戏剧人》、《从一个句子推断三个关键的词》、《一些事,许多问题》(1997),《看那蝴蝶》(1998),《在蚂蚁的阴影下》(1999)等诗作,都能见出正反二极的对话的形态和通过对话突出的作家的精英文化心态,如果说前期作品的中理想是抽象的真善美,是星空和道德法则,此一期的理想更趋近于具体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特质,如崇尚单纯简朴,反对物欲和放纵,崇尚人际的坦诚与信任,反对猜忌与欺诈。
囿于阅读和领悟所限,2000年以后刘洁岷的诗作更加自由,更难概括;但仍可看出,其与世界与他人的争辩意识,启蒙大众的心态似乎更进一步消泯,其诗作更多展示的是我之所见的蛛丝马迹,和我思我悟及个人的生活场景呈现;同时随着年岁的增长,似乎更多了一些对世界的淡然与恬适。如果说此前他的诗作中有高高的星空,有相对而立的启蒙者,在此期,他的诗作进一步沉到地面,有的是场景和物象,不再有说教。如他作于2007年至2013年的诗集《词根与舌根》基本是这一意旨的体现。《词根与舌根》的辑一《蛛丝集》即为代表。如:
“许多娃娃脸在一堆课本里
讨伐胖子的声浪不绝于耳
亲人渐老,未曾涉足的景点越来越远
撕肝裂胆的猪八戒在黄埔江沉浮
心,与星际空间里最遥远星系的一片蛮荒汇合(《失题》,2013)
所看所想似乎都有呈现,若明若暗,但作家克制了此前的说理的冲动,文中没有出现与叙述者对立的“你”或“他”,只有呈现。
再如《信》(2013):
“不知道是昨晚还是今晨
总之吧是醒着的时候
我在想写一封信,迷糊中想写
不知是手写还是电脑写,也不知
如何发出去发给谁
下午我看了一本书,书很薄
书里有个老人在等信等了五十年
穿着新郎的衣服每周五
去江边等破旧的邮船,观察
从船上跳下的邮递员的一举一动
我是先想写信后才发觉书和信有关
不过他是在等信而我想写信
信的内容在不清醒状态时
似乎都已经拟好:是真的拟好了
现在只感到一片灰烬
这些诗作,作者不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很淡然地呈现,呈现真实的生活情态,自已的所读所感;也许他有观点亮出,但其观点尽在读者意会。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诗作给人一种笙歌散尽,繁华退场的真切,一种生活的本真和淡然。
二、写“理想的”诗
“理想的”诗是关于诗“怎么写”的问题,是诗歌理想或诗歌形式层面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好诗的问题。作为一位有着四分之一世纪的诗歌创作者和新汉诗的代表诗人,刘洁岷认为“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对诗之‘好’的标准探求不但不是一个伪问题,而且兹事巨大——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或标准混乱的行业是没有前景的。” 他于诗歌创作有自己独到的且较为成熟的理论。这一理论在不同场合他有不同的阐述,在《新汉诗诗学法则》中他提出了“言说”、“观念”、“多义”等30条法则 ,在《﹤新汉诗﹥的办法》中,他提出了思路、行动和内容一共6条。综合种种,我认为,其核心的诗歌理论主要有如下几点:一、诗意先于诗歌;二、诗歌要口语化;三、诗人的诗作要非风格化。“非风格化”主要从诗歌批评角度谈诗人的整体创作,认为创作不要固化,要尝试多种题材和表达方式,要做到不能“被定义”。而“口语化”则是部分包蕴在“诗意”中的,因此,我们主要就“诗意”谈“理想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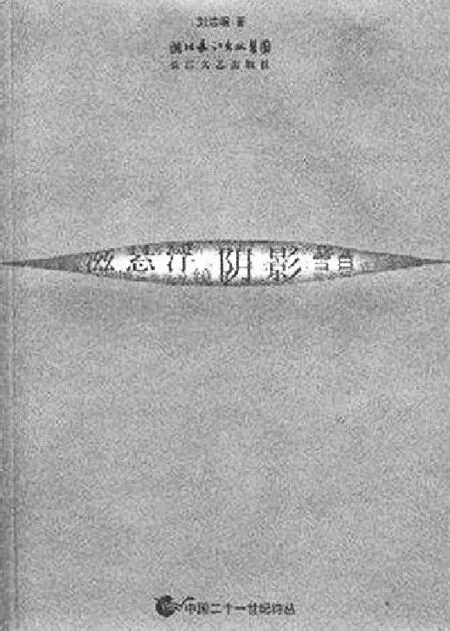
《刘洁岷诗选》
刘洁岷认为诗意先于诗歌。他说“诗意早于语言,语言没有诞生时,诗意在;诗歌同步于语言,语言在,诗在。” 也就是说诗歌是凭借语言表达的诗意,没有诗意即不为诗歌,诗歌是语言与诗意完美结合的产物。但何为诗意,刘洁岷似乎从未明确指出,他说诗歌“既不是在模仿实在之物也不是为了表现梦幻遐想,而是一种旨在揭示内心生活和语言内在奥秘的艺术。” 根据他在多处提及的梦境和混沌的概念,我认为他所说的诗意是类同于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感受。为了呈现诗意,刘洁岷提出了“口语化”、“非风格化”、“混沌”等一系列的诗歌标准,我认为这些标准实际都是为了体现诗意,呈现诗意的技术手段。当然,这些技术手段是否能真正抵达诗意暂且存而不论,但它们至少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诗意的特征。
刘洁岷说:“未来的诗歌创新将势必建立在一个多向度的,深湛而繁丽的平台之上。正如时代、传统、生活、现实与我们的诗歌是偏移和相互构成的一样。我们未来的诗歌与这个平台也是偏移、相互构成的,而不仅仅是‘在……之上’。而且未来的诗歌创新将意味着更为艰辛的修练和劳作。因为单纯的一个方面的革命式反拨恐已不能奏效,甚至已不易赚得有起码美誉度的‘知名’。” 这里的“未来的诗歌”也即“理想的诗歌”,而“深湛”、“绮丽”、“多向度”等都是其为避免诗作的过分明晰化、简单化而采取的加深诗歌混沌感,增强诗意的方式。具体的实例在刘洁岷近期的诗作中更容易得到体现。以前文提及的《失题》和《信》为例。前诗乍一看不知所云,但又都似曾相识。“许多娃娃脸在一堆课本里”似乎说的是今天的“减负”和应试教育问题,“讨伐胖子的声浪不绝于耳”说的是当今世界的肥胖问题,“亲人渐老,未曾涉足的景点越来越远”似乎说的是旅游热潮或自己的人生感慨,而“撕肝裂胆的猪八戒在黄埔江沉浮”似乎说的是江浙一带的死猪事件,各事件毫无相关性,但每一事件都可以引人作其他联想,或可以有其他隐喻,因此显得张力十足;而最后一句“心,与星际空间里最遥远星系的一片蛮荒汇合”,却具有总领作用,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和个人的无能为力表达出个人内心和世界整体的“蛮荒”感觉。
《信》与之类似,诗中个人平淡生活中的两个小片断似乎不具关联性,正如马原的先锋小说,但刘洁岷远比马原高明之处在于他通过“信”这一意象将他们联结起来,使两件或三件事都各自具有生发性,整体阅读既浑然一体,且更进入了另一层意义空间。
在另一篇文章中,刘洁岷谈到如下三个三个方面对诗歌写作极为重要。他说:“一是‘快慢’:诗的快慢不仅是节奏、情绪和语境的变化,还有许多许多,伴随诗句行进的始终。快慢在诗中常常相互缠绕,快中有刻意的打滑,慢中也会设置隐秘的微型加速器。二是‘精确’:诗歌语言固然不是科学语言,它可以讲究暗示、双关甚至歧义,以呈现事物的多侧面,多重意义,但这种异质性又必须回到统一的语境中来。我们掂量、安排、调整语词时也就必须百般琢磨这个自我悖反的‘度’,把握好了这个度,我们就具备了使诗歌语词达到精确的能力。三是‘玄思’:诗歌中的玄思如果看起来就玄之又玄那是蹩脚的,我倾向于具体可感的玄思,还有那种貌似笨拙的方式,或许还包含有一种延迟的体悟。” 这三者是实现诗意的另一种表达。也是刘洁岷诗歌写作日趋成熟之后的理论阐述,即诗作应该从容、平淡,在不经意中写出,不应有“作”的意味——这与他的“口语化”理论较为契合;诗歌应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感和“欲辨忘言”的余韵;而且要把这种余韵通过合适的语言比较妥帖地表达出来。
而这种比较合适的语言就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是生活化或时代化的语言,不必是刻意的口头语,也不必是过分修饰的词汇。从而让诗意在多彩、多层面的生活中,在混沌的事件中呈现潜在的诗意和美感。
作者简介:但红光,博士,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