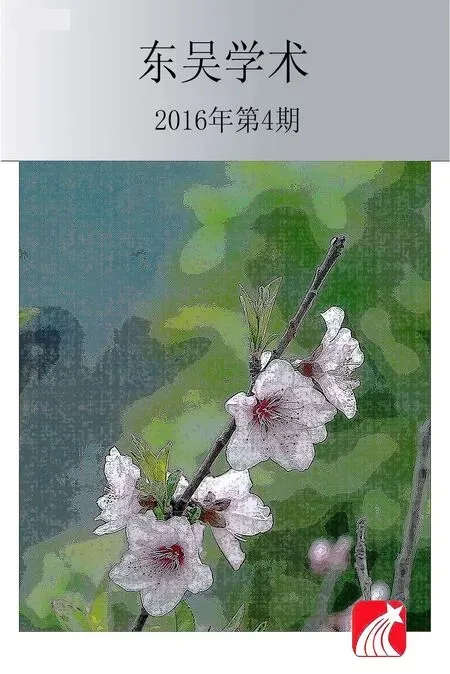诗性的碎片向叙述中心的漂移
——评任白长诗《耳语》
李 森
诗学
诗性的碎片向叙述中心的漂移
——评任白长诗《耳语》
李森
本文以作者的诗学思想“语言漂移说”和“欢喜诗学”为理论框架,阐释了当代诗人、小说家任白的长诗《耳语》的隐喻结构及其相关的诗学问题。包括长诗《耳语》与T.S.艾略特的《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之间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某些隐秘联系;语言碎片的漂移表达与作者写作呈现的“深度期待”;《耳语》书写的现代性文学模式与诗性的碎片向“爱情主题”和“时代精神”两个叙述中心漂移的修辞;个人与集体灵魂的意识形态结构与爱情的悲衰歌谣之间的深刻矛盾;语言中凸显出来的灵魂的经世履痕与自我泅渡的诗歌表达方式等。论文以诗意批评的文体语言展示了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彼此书写、彼此生成的古老法则,庶几从某种角度改变了文学批评对作品的依附关系。文章显现了对批评对象和批评文本自身的尊重。
《耳语》;情史;诗性碎片;语言漂移;深度期待;叙述中心;泅渡
一
《耳语》是任白的一首长诗。此诗写一对面容模糊的恋人在丽江恍如隔世的破碎情史。这对恋人没有名字,也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有灵魂缠绵悱恻、近乎蒸发的苍白碎片。在《耳语》中,爱之存在显现的碎片,即是生命可感、可知的形象或形式,也是生活吟咏的精神视觉。一言以蔽之,《耳语》中的爱,是两个人的存在被书写的部分。存在的大部分内涵就像暗物质一样,我们只能保持沉默。光阴裹挟一切,人却知之甚少。可书写的存在,是碎片的编织,书写只能如此。正如《耳语》的诗句所咏,两个无端存在的恋人,“一起陷落在这局促的幻象里”。当然,即便是谨小慎微地编织的破碎幻象,即便已经失去了爱情叙述的海誓山盟、本质发现,而编织者在其中的存在也是困难的。人之存在以及爱存在的困难,是笼罩着整首诗的一种气息,它使可感事物和心灵视相的存在也变得困难重重。正是那种飘忽而又凝重的气息,那种看似银光闪烁却冷若刀锋的气息,使我想起了T.S.艾略特的《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
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
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半清冷的街,
那儿休憩的场所正人声喋喋;
有夜夜不宁的下等歇夜旅店
和满地蚌壳的铺锯末的饭馆;
街连着街,好像一场讨厌的争议
带着阴险的意图
要把你引向一个重大的问题……
——查良铮译
以上所引诗句,是《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开头。也许,《耳语》与艾略特的这首情歌有种隐秘的书写联系,以至于让我觉得完全可以用以上诗句去阐释任白的这首“情歌”。《耳语》中的那对情人,仿佛也置身于现代主义意识流动中那“半清冷的街”,也“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在“人声喋喋”、“街连着街”的“末日黄昏”中,进行着“一场讨厌的争议”。一场渴望“主题”而终将失败的“争议”。任白“情歌”的开头深受艾略特“情歌”开头的影响(也许是个巧合)。艾略特清冷的、麻醉的“黄昏”,在任白那里是“仲夏”——艾略特以拟人的“黄昏”出场,任白同样以拟人的“仲夏”出场——两个“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实际上只有主观对应物),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诗性心灵中跃然于空白之上。这空白,可以喻为生活,一种绵延的、不知所终的清冷。(正是由于这种清冷的空白具有终极性悲怆,李森才受佛的指引发明了欢喜诗学。)《耳语》的开头两句是:
仲夏,满腹心事地从山脊后面现身
城里的三角梅依然在白日梦中沉默
三角梅是花与叶并蒂开放的植物,在云南广泛种植,大红、紫红、玫红、粉红,各种红,烈焰如火,燃烧如霞,直到把注目者燃烧到僵冷的程度。三角梅是在白日梦中开放的,这种花只能在白日梦中开放,犹如火红的沉默在暗房的底片上游走,为了黑白的灰烬。在长诗开头两句之后,紧接着,任白展开了一首长诗开头最关键的一系列意象。每首诗都是一条道路,开头的意象无论在隐喻内涵还是形式流动上,都可能是决定性的。开头既是道路,也是引擎。“沉默像山里的铁矿石”、“脸色阴沉”、“轻薄的笑声在山崖上撞碎”、“耳语”、“命运中枯坐的人”、“痛苦中讪笑的人”、“喧闹中失魂落魄的人”。这就是长诗中“最好的和最难的爱”的开端。凝重的意象碎片,裹挟着某种痛苦的、诠释爱和存在的意识形态意蕴。这意味着在这首诗中,漂移的诗性碎片将与某种主题纠结在一起,将我们引向深度阅读。这是一首探索“深度”的诗。任白是个探索“深度”的诗人,他给阅读带来“深度期待”。
二
生活与思想,都是时光的碎片,爱情与诗都不例外。像几乎所有使灵魂震荡的爱一样,这一场诗中的爱情也是受伤的爱,这种爱被主题纠缠,同时又漂移着破碎的阴影。正如艾略特“情歌”中那种冰凉而窒息的描写:“黄色的雾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背,/黄色的烟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嘴”。在《耳语》中,也有“远远的,有海啸声像一段有力的乐句/托着我在波浪间颠簸/那是你——遥远的最深处的你/渐渐苏醒”这样精妙的句子。诗意磨擦着语言漂移,使隐喻之重成为某种呼唤,成为“深度期待”。悉心观之,艾略特的“情歌”以期望写无望。艾略特写道:“有的是时间,无论你,无论我,/还有的是时间犹豫一百遍”。艾略特反复重复“有的是时间”、“总有时间”。可是,在“情诗”的最后,艾略特却写道:“我们留连于大海的宫室,/被海妖以红的和棕的海草装饰,/一旦被人声唤醒,我们就淹死。”而任白的“情歌”却反复用“来不及了”的无望写期望。此为两种“深度期待”的不同。《耳语》第十首云:“来不及了世界正裂变成无数甜美的碎片/它们扑面而来而我们正变得肌体迟缓应接不暇……来不及了爱人就在眼前爱情四处流离。”在诗的末尾收笔处,诗人咏叹:“记得当年年纪小/我爱唱歌你爱笑//自从那年去午睡/醒来歌歇笑亦遥……即托热爱夕照里/且复歌来且复笑”。最后一首结尾,与第一首结尾处相互呼应,形成复踏吟咏的调式。心灵的历史事象是偶然性的,诗歌更是偶然的偶然。偶然即碎片。偶然书写即碎片书写,这或许是语言的决定,是语言表达的局限和性质。但是,偶然的碎片书写里总有一个奔向“中心”或整体的渴望,这似乎也是语言表达难以割舍的一种动力。《耳语》起于碎片,漂移于整体,这是诗学中的一个矛盾。几乎所有诗人或艺术家,都被这个诗学矛盾所控制。是诗人在写诗,还是诗在写诗人?让人揪心的答案,当然是,诗在写诗人,自古如此。因为诗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而诗人反而是诗的碎片,是诗渴望要抓住的一个个事物,只不过这个事物是一个特殊的事实——他们有一个个心灵空间,其他的事物和时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死亡,也可以重生。因之,诗人是诗的力量驱使事物穿越的一条道路,也是一个牢笼。正如卡夫卡箴言所云:“一个鸟笼在寻找一只鸟。”在诗与诗人的关系中,诗不但书写诗人、创造诗人,诗还书写和创造生活。《耳语》第二十一首写道:
也许生活是一出恶作剧
我们全部的挣扎也不过是一套可悲的规定动作
三
诗在写人。所谓的现代,是一个精神漂移的现代。随着现代人漂移的灵魂逐渐走向自我的孤立——逐渐从整体性的意识形态依附中孤立出来,变得破碎不堪,现代文学艺术在创作和理论建构上,也逐渐碾碎了宏大的整体性叙事而皈依了语言和语言对局部事象隐秘性的探索。但是,对一个具体事象中隐涵着的普遍性的诗性提升,似乎也从来没有停止。因为那毕竟是人与语言共同选择的表达方式之一。
个人的孤立消解了中心,却更想寻找一个新的“中心”。这也是人之存在的一个持久的矛盾。《耳语》中的这对恋人,既是单个人的存在显现,也是对“我们”的书写。既然是“我们”,那就是一个类,是普遍性的时代人生,而非纯粹具体个人的隐私表达。不过,仔细读来,这里说的“我们”的普遍性,其实也只是一个倾诉的人。倾诉,是对“我们”统一性的确证。这个倾诉的人被往昔、今朝与未来所控制,背负着诗性的、思想的、生活的碎片,不停地倾诉,让人窒息地倾诉,以消解孤立之苦。因此,说到底,这对恋人,其实是一张倾诉的嘴和一只接受耳语的耳朵。一张嘴对一只耳朵的倾诉,的确不需要具体的人物形象,只需要语言的隐喻漂移。诚然,诗是语言碎片的漂移,区别的只是漂移的方式或途径不同。
《耳语》中的“我们”,并不是两个人。“我们”其实是某种“深度期待”或“深度发现”。任白的语言只想凸显灵魂的经世履痕,所以放弃生活事象和人物个性的表达似乎是必要的;他要在放弃形象的塑造之时,皈依时间横过一切的、茫然无依的“深度”磨砺。深度即隐喻。长诗毕竟不是小说或戏剧,无需创造人与事贴着真实事象运动的虚构景观。当然,语言自身的运动本身也是事象的运动,只是在叙事性隐喻的控制上或许不同。任白皈依“深度”或“隐喻”的方式,是力求使语言叙事性的漂移变得单纯,以划清诗歌与小说或戏剧的边界。当然,这是相对于传统文学而言的。现代文学文体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
就“深度”运动而言,任白的长诗《耳语》的确有种推杯换盏般的力量。这股力量在语言漂移中奔向两个中心主题。其中一个“中心”,是被诗歌书写着的爱的主题。另一个“中心”,是被诗歌书写着的时代心灵。也就是说,任白不让他的这段诗中情史,变成想象力纯粹的语言情殇。《耳语》中穿插了太多的、关于灵魂结构的文化碎片,它使读者意识到的,是一个时代的、集体的文化灵魂的逃亡,爱情的皈依在诗中反而相对次要。就是说,这首诗不仅在写人,也不仅在写爱情,它真正的叙述主题是在写一个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灵魂叙事,在这首长诗中若隐若现地呈现。那是一个理想主义个体寻找群体、向着文化巨擘或山峰膜拜的年代。因此,任白的“耳语”,不仅是情殇的耳语,更是“向……”膜拜的耳语。他跪下了(“我跪在你的床前/用此生全部的力气”),向无数古今中外的大师耳语,当然也向“墙上沉睡的风筝/山风中孤单的翅膀”耳语。此是文化的耳语,是价值观书写的“中心”耳语。第十三首结尾:
谁来守候续命之火
(宋儒张载是怎么说的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知识还会不会成为弥赛亚
使我们再次得救
四
向着情爱主题与时代文化主题的倾诉,自然要逃离当下人与事的纠葛,使诗歌在局促的生活牢笼里奔向远方。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春成长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任白,天生有一种质疑当下的品性。曾经的理想主义,对当下的质疑,自然会钟情于过去和未来。任白的《耳语》将“情歌”歌咏和倾听的语境,安置在丽江这个传说中的“艳遇之都”,让他们在那里进行以情爱为主题的精神度假。诗歌书写在那里诠释“爱”的主题,是为了谋划一桩人的文化灵魂和爱情双重逃亡的诗歌事件。在任白的这首诗中,对于那个倾诉者来说,丽江这个象征性的地方,是一个遥远的世外之域,而非“我们”这个共相人真正醒悟的栖居之所。因为在那个共相人心中,有着比一个具体的地域更绵长、更深广的精神性、悲剧性的情爱地理。“丽江”是陌生的,“我们”犹如在一个孤岛上沉重地漂移,不合时宜。具体地说,倾诉者是一个曾经沧海的人,一个遍体鳞伤的人,一个智者知识分子,一个被终极目标控制着的角色。因为对终极有个纯粹的假设,因此,爱情本身就是逃亡,永远在奔向纯粹终极的途中逃亡。在逃亡途中,携带着人类的忧郁之病、时代之病。逃亡,纯真灵魂因爱恨情仇的磨损而疼痛,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救。因为浸润着情愫的灵魂太过于复杂,《耳语》一诗由是揭示出,爱情其实只有“情史”,只有在场的飘忽时光碎片,而没有爱。奔向爱的主题,即是爱的丧失。正如诗中的句子:
幻灭太多了
那些情史就像张爱玲的袍子
褶皱里爬满了虱子
(第七首)
我们都在自己脸上涂了些什么颜色啊
我们都在一闪而过的笑容后面贴了怎样的诅咒啊
(第十一首)
爱情,爱情
在你的自毁中我们看见了什么
所有的青春都投到那丛火焰里了
(第十四首)
进一步说来,这首诗作为情史,其精神内涵是多重的。一方面,灵魂被千绕百褶的意识形态所控制,另一方面,也灌满了情爱深深的醋意。诗中暗示,如果爱情有一个纯真的本体——第一次也是最终一次洁白无瑕的开放,那么,那个本真之爱已经深受创伤——有一个叫“浩军”的爱情罪犯,使情史蒙上了阴影。这个“浩军”,一直伴随着他们爱的逃亡,这或许是任白个人精神世界最深的恐惧。古往今来,对于那些脆弱而敏感的灵魂来说,爱情一直是深渊之上漂浮的一根救命稻草,但这根救命稻草,却挽救不了肉体和精神在醋意深渊中的必然下沉。救命稻草象征情爱灵魂追求纯粹的洁癖,深渊象征着情爱不能自拔的无限沉沦之所。因此,情爱逃亡域外孤岛,又从孤岛逃亡,是一种泅渡,是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个精神维度。这是《耳语》倾诉者对情爱悲剧的书写。之所以说情史中的情爱泅渡是个悲剧,是因为泅渡从来没有成功。自古以来,纯粹而本真的爱没有成功的范例。
而更悲哀的是,个人自救式的、时代文化的泅渡也不会成功。爱情主题和时代文化主题的双重逃亡均无结果:
从尼采开始
我们失去了上帝和内心的经纬
世界像一枚突然爆裂的坚果
黑色的籽种四处飞溅
荷尔德林,卡夫卡,萨特,加缪
这些哀伤的名字
带着我们一起逃亡
(第九首)
五
一首沉重的诗,犹如一个沉重之人的行为书写,总要有一种美好的东西来释放它。恰如我们在反复地欣赏自己喜欢的曲子,以稀释自我凝结之重。诗歌不但在书写诗人,也在自我书写。《耳语》这首长诗作为活着的一个抒情生命,亦如一艘船的航行,它不仅让“情史”中的角色服从情爱绽开的悲伤旋律,更重要的是,它还让整艘诗歌之船在航行中化为音乐,包括它承载的所有事物之重,都要服从音乐引领的歌谣之轻。作为一首多声部的曲子,它时而鼓钹如浪,时而弦歌如帆。的确,这首诗在自身隐秘的节奏中航行,却又负载太多、吃水太深,但它只有一个悲观的目的——让我们醒来。这是主题书写释放出来的欢欣,也是我的“语言漂移说”和“欢喜诗学”所赞美的。
远远的,有海啸声像一段有力的乐句
托着我在波浪间颠簸
(第一首)
我们被一种绵长的节奏所吸附
沿着它翻阅你内心那些陌生的褶皱
(第十七首)
那音乐有着铜一样的光泽
有着骨头一样可怕的沉默
……
一串笛声在薄雾中游走
一段歌声栖落在故乡的屋顶
我们啊,什么时候会从浮世的巨大笑脸上醒转
(第十八首)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燕庐
李森,云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