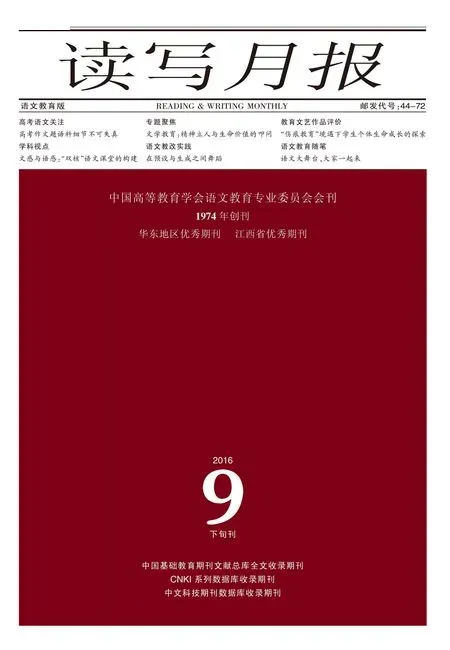文学教育:精神立人与生命价值的叩问
余聪聪
文学教育:精神立人与生命价值的叩问
余聪聪
在当下社会与文化语境中,文学教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个中原因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当今的文学教育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共识;其二,人们依然对未来的文学教育充满着期待,这样,对于文学教育的规划与设计就是一个必须去试图完成的重大工程了。我们应该明白,文学教育的价值显然不仅仅是传授给人知识、技能及谋生的本领,在其深层意义上是使人成为人,在精神上立人,进一步讲,是依据生命的特性,遵循生命发展的原则,引导生命走上完整、和谐与自由的境界。
一、大众时代,吁求真正的文学教育
无可置疑地,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大众化时代。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我们依然需要考量和探索文学与文学教育的价值与功能问题。作为文学功能的一种存在方式,文学教育并不局限于它词义指向的领域,还关涉到文学生态、文学创作、审美旨趣,同时也表征着时代精神、社会风尚、民族心灵。然而,在当下,文学教育正遭遇被解构的危机。在大众消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艺术与商品的边界逐渐消失,文学成为供人消费的商品和娱乐手段。随着市场化时代的推进和发展,文学开始陶醉于享用之中,大众普遍认为享用生活和快乐、享用平庸和琐屑是生命的本性和文学的本性。这样,市场化时代的文学充斥着流行的世俗幸福、性情趣、私人空间、利益满足等,从而忽视了其时代价值与生命价值,使得文学从对生命的崇高思考和永恒追求坠落至个人利益的满足与现实快感的实现。而这些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文学本身独一无二的、深刻的意味性。也就是说,在大众时代下,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被追求物质享受与实时的感官刺激所遮蔽,已有的传统文学价值体系随之被颠覆与重构,而文学所固有的教育功能也随之被大众文化逻辑所取代。我们每个人都不敢也无法确证自我的存在,而倾向于在大众指向中寻求避身之所,人的存在开始向庸俗滑行。庸俗化的生存催生庸俗文学的产生,文学在世俗化趋势中,已经没有可以给人带来精神享受的品性。这固然是文学的悲哀,同时也是文学教育在文学世俗化进程中遭遇到的重大挑战。无疑,基于以上对于文学的认识前提下的文学教育是不可避免地会走上歧途的。
迎着新世纪的步伐,我们在摆脱现代性的阴影,而进入一个“人”的世纪。“以人为本”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为了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彻底反思文学教育现代性的阴影,以至于超越文学教育的现代性,走上以生命为本的新时代。在蒙上现代性阴影的时代,文学教育中所秉承的生命意义随之被消解、生命本质也逐渐被异化,比如“人文教育的失落,失缺了生命的另一半”。文学教育缺失了人文关怀、人文精神,脱离了生命的本原;文学教育与生活割裂,丧失了生命的意义;“绝对主义的客观知识,泯灭生命的灵性与创造”;“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培育无根的生命”,甚至“规训、压抑自由的生命”……[1]面对文学教育领域中“人的缺场”这一现实问题,如何以“人的在场”来重新树立起人们对于文学教育的信心。科学主义的甚嚣尘上和工具理性的至高无上使得文学教育的根本旨趣受到挤压与曲解,文学教育的对象所产生的疏离感、陌生感不断增加,本来以“立人”为本的文学教育在不知不觉中异化为钳制人的工具。相应地,生命是文学的本质观念及文学教育的根本方向这一命题遭到了破坏,文学教育在尊重人的多重生命形态与可能质地的基础上追求人的“诗意的栖息”这一构建与诉求中遇到了阻碍。
人作为一种特殊的、有意识的生命存在,不断地追求自身生命价值的升华。文学是对于生命的一种评价形式,而回到生命、直面生命、珍视生命是文学教育的一种天职、一种本义,更是文学教育的一种追求。那么,立足文学本质观念,从生命的视角思考文学教育的发展就显得更为迫切与必要了。但长期以来,比如20世纪70年代强调“双基”,因为“知识就是力量”;80年代强调“能力”,因为面对科技革命的挑战;90年代强调“情意”,因为技术时代的唯理性教育……我们的文学教育语境并不紧密关乎人的生命,对文学教育的关注不是因为人本身的需要,而是把文学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工具”,这无疑造成了对生命的遮蔽。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清楚地意识到文学教育的真正内涵,文学教育是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收,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2]那么,文学教育归根到底是为了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呢?这是文学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学者达拉礼这样说到,“教育成为制造劳动者的一台机器,通过教育的塑造,人被变成追求物质利益的人,掌握生产技术成为受教育的全部目的,这样,人愈是受教育,他就愈被技术和专业所束缚,愈失去作为一个完整人的精神属性。”人是具有内在潜能的生命整体,而成“材”的教育,把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归结为“材”,使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机器”。哲学家尼采说:“由于这种非人格化的机械和机械主义,由于工人的非人格化,由于错误的分工经济,生命便成病态的了。”[3]
人不仅生存在现实世界中,还生活和发展于精神世界里,精神追求是人生于世的永恒命题。如果人们在精神消费中丧失了意志、情感、信念、理想和对未来的憧憬,势必导致人的价值世界的迷乱和精神品格的丧失,在狂欢中将生命消解殆尽。因此,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吁求真正的文学教育就显得急切而紧迫了。新世纪的文学教育应该走出“异化的洞穴”,创造一个有助于生命舒展、生命涌动的环境,“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4],进而为人类的根本存在作证,回归生命的本原。
二、文学教育:回归人本,精神立人
文学是人学,是社会现实中从事实际生活活动的人的“精神分析学”,其核心指向是“人”,而“人”是有生命的“人”。“在静态上看本体生命的存在,人实际上有三重生命,一是自然生理性的肉体生命;二是关联而又超越自然生理特性的精神生命;三是关联人的肉体和精神而又赋予某种客观普遍性的社会生命。精神生命作为一个‘中介’,将肉体的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5]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文学教育的本体性价值在于“精神立人”。
在中国,文学教育伊始,就确立了培育人精神品行的目标,并且在后来也得到了良好的贯彻。《尚书·尧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典乐言诗,是要培养胄子的精神品性与审美情趣。《论语》中这样记载,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这里,孔子强调了诗教对于人的品德养成的必要性。明代的汤显祖《牡丹亭》弘扬“至情”,冯梦龙《山歌》张扬“真情”,袁宏道小品文宣扬“性灵”,这样,文学教育也形成了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时代潮流,这显然有助于培植主体的自由精神,充分展示文学教育的人本内涵。但在随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学教育的工具性、功利性日益凸显,这严重遮蔽了文学教育的人本目标。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与实利主义以及日益发展的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趋向,迫使文学陷入边缘化的境地。在讲究效率、利益的时代,忙碌的现代人越来越感到精神世界的狭窄,失去了文学滋养的心灵渐渐丧失了价值理性的自觉,在这一时代境况下,文学教育更是迷失了精神的导向及其根本诉求。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文学的真正力量在于精神上成人、立人,文学教育应该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人类精神救赎与精神建构的历史使命,这也就是说,文学教育的根本功能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神价值观。
何谓“精神”?王坤庆先生说:“‘精神’一词,主要指对人的主观存在状态的描述与定位,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基本属性,以及发展过程的理想归属”。[6]雅斯贝尔斯曾说:“我们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们怀有一颗崇敬之心,并且让精神的内涵充斥于我们的想象力、思想以及活力的空间。”文学所蕴含的“精神”是感性与理性的交融,是基于自我生命的,其指向个体在成长中的内省与觉悟。文学教育的一个内在功能就是展示、张扬这种精神,让生命存在体在教育过程中感悟、接纳这种精神。
文学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 “精神立人”,但把文学教育提到“精神立人”的高度来认识,并不是要求文学教育走上“虚化”道路,使文学教育实践失去可操作性。“所谓‘精神成人’,即个体生命在精神生命 (生命的灵性层面)做到自觉、自主,在精神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精神成人’的根本内容和根本路径,不在于从外面习得某种‘精神’或者‘灵性’,而是让自己的‘灵性’从沉睡状态觉醒,进而能够以自己的灵性精神指引自己的身体行为和心理个性。”“所谓‘精神成人’,便是以自己觉醒的灵性引领自己的身、心,成就自己的现实人生。”[7]“精神立人”的实践意义在于更加突出文学教育的潜移默化和价值导向特性,突出文学教育对于人类精神的救赎与建构作用。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远远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受教育者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要求,他必须获得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精神立人就是对于人的一种建构,而且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受教育者能够自觉形成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审美趣味与德性品质,无疑,这样的教育实践可以把文学教育引向一个更为高远的境界。
文学教育的精神指向是丰富的,它给予人理想、美好和信念。文学教育必须回归人本目标,把培养人的精神品性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历史反复证明:背离文学教育之人本目标,就会出现道德异化、精神物化现象,从而走上人性的反面;而坚守文学教育的人本之道,培养人的精神品性,建设人的精神家园,才能够建设和谐社会。文学教育说到底是一种“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精神活动,它所指向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是让个体生命去寻觅、体悟、创造出自我的生活的真意与诗意的世界。
三、生命的内蕴及评价生命的文学教育
文学作为生命评价的形式,相应的文学教育活动是立足于人的生命并直面人的生命的一种活动,而追求生命质量的提高、构建生命的意义是文学教育活动的最终诉求。文学教育活动的开展要尊重生命个体的特性,挖掘生命的内在潜能,因此,对生命的内蕴进行认识就成为了文学教育活动开展的前提。《辞海》关于“生命”的解释是这样的,“由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物质组成的生物体所具有的特有现象,能利用外界的物质形成自己的身体和繁殖后代,按照遗传的特点生长、发育、运动,在环境变化时常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能力。”而对于生命观的阐释早在中国古代孔子的 《论语》中就得到了体现,比如,《论语》所解释的生命主题,即成就道德人格,实现生命价值。无论是《论语》中的“仁与礼”对生命主题的双向展开;抑或是“学与习”所体现的生命教育思想。同时,恩格斯曾提出了生命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不断地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8]显而易见,这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生命。除此,冯友兰指出:“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9]在这一意义上,哲学就是一种生命教育、人生教育。海德格尔也在其早期的《那托普报告》中明确指出:哲学对象就是人的此在,“哲学问题关涉实际生命的存在”,“哲学问题关涉那种在当下被称呼存在和被解释存在之方式中的实际生命的存在”。[10]关于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概念及人的“生命本性”,哲学家们可谓各有诠释。古希腊哲学的生命观,即“人们把追求幸福、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格的完善和美满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等伦理学命题;“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则从自然主义思想出发,强调要自然地对待人的生命,要把人的天性归还给人,要尽力把人真正成为人的可能性发掘出来”;“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认为,唯有人的生命的存在是真实的,要使人的生命获得意义,就要人去进行自由选择”。[11]另外,非理性主义哲学也对生命观有一定的阐释,比如叔本华提出的“哪儿有意志,哪儿就会有生命”[12]以及人本主义倡导符合人生命本性的生活,强调人的生命的自由精神和独特精神等等。除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13]马克思把人的生命活动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相比较,指出人的生命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一观点也表明了人的生命存在的“超越性”特征。因此,人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超越性存在。
众所周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但即使进化成人类,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动物界,未能摆脱动物固有的种种习性,仍从属于整个大自然。所以,人不仅有自然生命,且包括温饱、安全、休息、活动、繁衍、归属等生命需要及其行为方式在内的自然生命活动的内涵,从根本上讲,人亦与动物的本能需求及活动相一致。因此,人本身的种种需求和行为方式,在我们的祖先猿猴身上都可以找到源头,生存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存在方式,而这种自然生命正是人建构其全部生命活动的原发点。但是,人毕竟是生活在整个历史文化环境里的,人身上处处打上了文明社会的烙印,从而自觉的生命理念就成为了当今人的主流生命意识,即“以主体自觉性的确立为生命成熟的标志,以有目的、有意识的加工制造过程(改造世界的活动)为其表现形态,并将通过这一活动方式所达成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视以为生命价值的实现”。[14]然而,在这两种生命方式之外,人更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它不同于自然生命的生存需求,亦有别于实践活动中的现实功利需求,而表现为超脱于这些实际生活需求之上的一种对生命终极寄托的需求,通常所谓的“终极关怀”,指的就是这种需求了。在终极关怀里,人的生命活动指向生命意义之究竟,它摆脱了一切现实的阻碍及功利的欲求,直奔那最高的自由境界,故而最能显示生命对自由的终极向往。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说,就是生命质地的“超我”阶段。萨特曾经将人的存在归结为“自由”,并宣称人“命定是自由的”。如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词云:“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从这幅气象恢弘、色彩绚丽的秋意画里,处处能感受到生命的跃动,生机勃发、动静飞潜皆有自由。再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不体现其对自由生命的向往与追寻。
人是什么?简单地说,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具体的、完整的、丰富的生命存在体。文学教育是以具体的、现实的人为对象,就是要以生命为本,直面人的生命,关怀人的生命,提高人的生命。同时,关注人的生命的文学教育,必须凸显生命的质地与灵性,因应文学教育与生命的必要方向。灵动生命的文学教育是遵循学生生命发展的内在本性的,在这方面卢梭早给我们以启蒙:“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15]作为个体存在的灵动生命是有其自身的发展次序的,而文学教育需因应、遵循自然生命发展的规律和轨迹。人不仅是实体的存在,更是意义的存在,灵动生命的文学教育是追求生命自由,懂得追寻生命的意义的。我们知道,意义应是充盈、富有质地的生命形态,是发挥和展现自身的自足感、自由感的内在精神力量,是生命向死亡、向一切摧残戕害自己的力量抗争的不屈感、悲壮感,意义则是使人的整个生存得以维系和升华的生命之神韵。总之,灵动生命的文学教育应是一种“唤醒”,是一种对个体生命形态的有力的“唤醒”与“建构”。文学教育是一种“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行为,是在领受诗意情感的过程中叩问生命价值、展现自由德性的精神活动。其力量在于受教育者在知识构建的过程中满足审美的需求,获得洞见人生的力量,涵养自由之精神,架构健全之人格,使文学教育真正成为“人的教育”。文学的学习以“人的教育”为目的,在文学精神的领悟和陶冶中,思考人生、人性问题,培植有益于未来人生的对美和道德的判断力,提升对生命的感悟力,以此唤醒沉潜的人格力量。这就是蔡元培所说的:“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责任。”这是所有教育的共同目标,而文学教育又是其中颇具力量的。
生命是文学本质观念与文学教育的根本方向。生命是完整的,是自由的,是独特的,致力于生命的全面而和谐、自由而充分、独特而创造地发展是文学教育的一种天职、一种本义,更是文学教育的一种追求。
四、文学教育与生命价值的叩问
叔本华认为,人的每一天都是一个生命过程:“每一天都是一次短暂的生命:万物苏醒,获得一次新生,每一个清晨都是一次初始,尔后,万物都要静止安息,睡眠如同一次短暂的死亡。”于是,在这位冷峻的哲学家看来,死亡可能有两种:永恒的死亡一生一次,短暂的死亡一天一次。那么,面对“生命的一次性”,追寻生命的意义就显得更为迫切。众所周知,生存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起点,也是人存在的最基本要求,但“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他总是牵涉到意义。而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正如空间的向度对于恒星和石头来说是固有的一样……人可以创造意义,也可以破坏意义,但不能脱离意义而存在”。[16]当一个人从孩提开始走向成熟,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人生的重要问题时,他就一直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我过怎样的一生才能使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生命变得有价值?这种思考就意味着人开始了对自己人生意义的探索,对生命价值的叩问。“对现代人而言,解放自己的心灵,摆脱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融入自然,融入宇宙,与万物对话、交流,悲天悯人,培养博大而深沉的情怀,确认良知对人类的重要作用,无疑是生命意义的首选价值。”[17]所以,真正的文学教育不是忽视生命的需要、消解生命的意义,淡漠对人的心灵和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情感和人格的陶冶,使人成为了被社会需要所驱动和钳制的实用“工具”,以此放弃了对生命的感悟,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真正的文学教育是一种追问生命意义的教育,是一种唤醒心灵和充实心灵的教育,是一种生命价值的教育。
“对于作为个体生命的人来说,生命是一种当下既有的‘存在’,是我们个体领受天、地、人的恩赐而自我呈现的‘存在’,是一个从无到有又似乎要从有到无的自我创造的‘存在’。”“每个个体生命一开始都只是一个‘点’。”[18]因此,生命应当有着自我敞现的维度,比如:人生维度、人文维度、精神维度、人性维度……那么,文学教育作为生命自我敞现、自我省视、自我觉悟的活动,也便有相应的使命,即在人生维度、人文维度、精神维度、人性维度上领悟生命的长度、开拓生命的宽度、实现生命的厚度、增加生命的亮度。这样的生命是充满着价值、意义与德性的存在体,我们需敬畏生命、丰富生命、充盈生命。
人是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的双重存在,无论是自然生命的发育完善,还是精神生命的成长都离不开文学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被矛盾和困惑折磨的存在,关注人的生命是人生存反思的需要,也是一个难题。我们知道,真正的文学教育可以为这一难题寻求解决方案。然而,文学教育对人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却又是一个需要人去积极寻求解决的难题,而且是文学教育本身的一个难题。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有意识的生命存在,人不断地追求自身生命价值的升华。文学教育在促进人对生命自身的超越、提升人的生命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寻求和创造人的生命意义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生命教育就必须根植于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之中。文学教育应当关注生命个体的存在,回到生命、直面生命、珍视生命是它的一种天职、一种本义,更是其重要追求。因为,“只有回到生命,才可以理解作为生命表达的文学教育。回到生命,就意味着回到了文学教育的本源,在生命中对文学教育展开理解,也就意味着在文学教育中理解文学教育。这是一条真正的理解之路”。[19]因此,文学教育需 “返回到人生的亲切处寻找它的原始命意”。文学教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存所要掌握的生活知识和技能,而最根本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文学教育本质上不是一种本能性活动,而是一种价值性活动,是与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休戚相关的价值活动。
“人是不会满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的生活的,总是利用这种自然的生命去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人之为‘人’的本质,应该说就是一种意义性的存在、价值性实体。”[20]人的存在就是不断地去成为人,不断地去追问生命并热爱生命。因此,在这种存在形式中,生命是人的主要形态,做人的本质就是珍视和舒展自己的生命,使生命在涌动中体现自身的价值。然而,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的生命质地,还需要把别人的生命当作自身关注的对象,既要思考自身的生命体态,同时还应该立足于广阔的外在世界,关注他人现实的鲜活生命体态。文学作为以“人”为中心的活动,要为人创设舒展生命的空间。真正的文学教育是“从调顾人的心灵入手,以知识的陶冶与智慧的激发来 ‘照料人的心魄’,使人的心智保持健康和良性运作的姿态,实现生命内在的和谐和心灵的善美,提升人的生存境界,在此过程中实现人生的幸福追求”。[21]因此,文学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启迪人的精神世界、建构人的生活方式,以实现人的价值生命的活动;文学教育应以提升人的生命质量、拓展人的生命价值为目的,使人的“生命之流”时刻涌动。
人用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不只是为了满足物质生命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理性、精神生命的需要,获得生命美的享受。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纯感性或纯理性的生命,作为一种育人活动的文学教育理应培养健全的生命,塑造理想的人性。文学教育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与尊重是毋庸置疑的。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最基本的就是尊重生命的存在。如陈毅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在这里,诗人不是要认知“青松”的客观属性,而是他发现了“青松”与社会个体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对“青松”倾注了情感,挖掘出青松顽强不屈的品性,更是诗人关于坚强有韧性的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对生命存在、生命价值存在的庄严的确认。
文学教育实践需要明确生命发展的方向,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于生命价值的叩问过程。它不在于造就人力机器,不是塑造单面的“有用”的人,而是培养鲜活的生命个体,培养时代与社会语境下的完整的人、自由发展的人。这样的生命个体能够自觉地对自身的生命质地进行营构和谋划,在关注更为广阔的外在世界的同时,追求生命的诗意化、圣洁化,从而,在斑驳而繁复的世界里保持相对独立而清醒的个人判断,寻找由生命通向灵魂自由的方向,让真正的生命韵致得以绽放。[22]
注释:
[1][5][17]冯建军:《生命与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58页,第208-209页,第173页。
[2]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基本特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页。
[3]转引自冯建军:《当代主体教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6]王坤庆:《论精神与精神教育——一种教育哲学视角的当代教育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18-19页。
[7][18]何仁富:《大学生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第94页。
[8][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77页。
[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10][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孙周兴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11]刘恩允:《大学生生命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9-40页。
[12][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77页。
[13][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14]陈伯海:《回归生命本原:后形而上学视野中的“形上之思》,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4页。
[15][德]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页。
[16][美]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47页。
[19]杨一鸣:《理解教育》,《上海教育科研》,2001年第3期,第29页。
[20]高海清:《人就是“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3页。
[21]刘铁芳:《沉重的书包与教的权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4年第4期,第105页。
[22]詹艾斌参与了本文的立论与修订工作。
本文是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高校文学课程教学德性培育可行性研究”(项目编号:15YB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李运
责任编辑:金润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