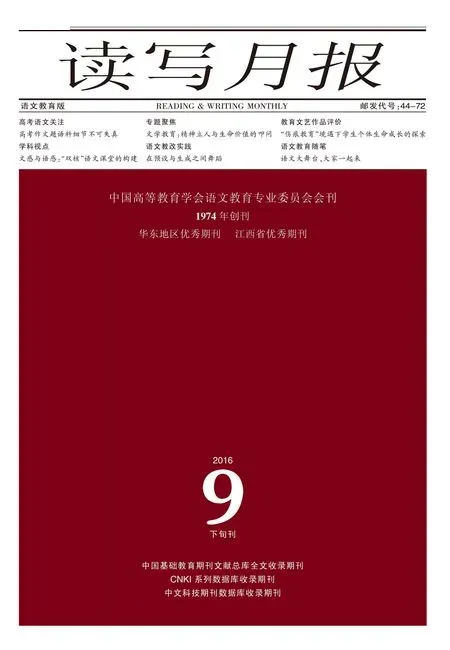“伤痕教育”境遇下学生个体生命成长的探索
——从孙敏瑛的中篇小说《暗伤》说开去
邬艳君
“伤痕教育”境遇下学生个体生命成长的探索
——从孙敏瑛的中篇小说《暗伤》说开去
邬艳君
受现代化教育思潮的影响,当下教育的面貌焕然一新。许多学者都倡导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对学生的要求逐渐向自由、全面的方向发展,并在此领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然而,在社会功利化的背景下,少有人关注到许多教师和父母都已经沦为了应试教育的附庸品,他们更注重的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忽略了对孩子生命本真的教育,“人”的生命意识显然被淡化了。
孙敏瑛的中篇小说 《暗伤》是一部直面当下教育弊病的反思性小说,主人公方晓容 (小容)在学校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侮辱与嘲笑,在家里也很少得到父母的关心和呵护。实际上,这正是从孩子的世界出发去叩问当下教育之痛的一种做法,进而也引导着我们去关注当下弱势群体中的孩子的生存、生长乃至生命困境。本文试对《暗伤》中的困境少年——小容的生活状况和教育需求做出相关的描述和分析,并希望以此而更清晰地展现在此般境遇中的底层少年的实际生活状况及他们尚未得到基本教育需求等现实问题,并尝试着在此基础上探索孩子个体生命成长的可能。
一、教育藩篱之网——“伤痕教育”
尊重和关爱学生本是教育领域应关注的中心问题,然而近年来,“以分数论英雄,把升学率和成绩作为教书育人的唯一指标”的这样一种应试教育理念却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学校本是一个充盈着欢声笑语的地方,是孩子们获得自由发展、培养其健康人格的理想场所,如今,学校却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应试教育的附庸品。而在这之中的教师亦是如此,他们呈现了庸碌化的面貌,忽视了学生个体心理的健康成长。部分教师依凭着自己的权威而轻易凌驾于处于弱势方的学生之上,对学生动不动就无端地斥责、谩骂、冷嘲热讽、横眉怒对甚至冷眼相加,根本无心于尊重和关爱学生,毫无民主、平等可言。小说 《暗伤》的主人公方晓容是一名初中生,处在享受国家义务教育的阶段,可学校教育带给她的却是无尽的“暗伤”,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的嬉笑、嘲讽,都给她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打击。明庆华在 《论教育中弱势子女受歧视问题》一文中谈到了现阶段学校教育中出现的歧视问题,即存在对弱势群体子女的自尊心和爱心进行毫无底线的践踏和不公平的待遇等现实状况。[1]杨美美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没有尽到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无端地斥责、谩骂、歧视学生”是她的惯常行为,她还动不动就让学生扫地、罚站等。特别是她按学生的成绩来排列三六九等、以捐钱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学生的爱心,及不换座位 “拥护”成绩好的学生等做法,更使很多学生的心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暗伤”,进而也导致学生们唯分数、唯利、唯财是从,忽视了学生其它向度的发展。老师杨美美秉持 “没有惩罚的教育是无力的教育”[2]这一教育理念,在学生小容看来,这其实是一种“破教育理念”,小容对老师虚伪而做作的造谣事件也十分不满。在一次语文课上,小容指出了老师的发音标准问题,老师就用手指戳小容的额头,训斥她、恐吓她,最后还让小容写检讨。最终,小容的检讨里写的虽然全是对老师杨美美的溢美之词,她的内心却强烈否认,似乎感觉自己什么时候也变得如此虚伪讨厌。杨美美对小容的刻薄话语及老师间的相互逢迎、应和,导致其他同学也对小容产生了排斥和嘲讽心理,“她显得孤孤单单,她总是把头缩在她的红围巾里,像一只鸵鸟”。在这个无法相融的集体里,由于她的成绩差、家庭条件不好等因素,小容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错的,她的命运里逐渐写满了 “伤痕”二字。可以看到,在学校教育的困境中, “教师、同学和弱势孩子如何相融”可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的有机统一,那么,岂能废弃家庭教育,让孩子失去这一可靠的教育资源?刘良华在其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一文中指出,首先,家庭的经济情况会影响孩子在学校的学业成绩,孩子需要最基本的文化资源;再者,父母不要因为教育孩子而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休闲生活,为了孩子而忘记自己,这样破釜沉舟式的期望使孩子遭受沉重的压力,父母以爱孩子为借口,同时也以爱的名义破坏了孩子的成长。[3]小容的母亲素云是个在菜市场卖菜且没有多少话的人,后来还积劳成疾,父亲则是个蹬三轮且善良诚恳的人。他们整天都在为生活疲于奔命,和小容的沟通甚少。孩子内心的压抑太多,她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渐渐在寻找寄托而又无望的过程中失去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家庭的经济条件是支撑整个家庭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柱,父母为经济而奋斗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可是当这件事与孩子的培养相冲突时,取舍之间就是父母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肩扛着家庭未来的重担外出务工的父母越来越多,孩子呆在祖父祖母或外公外婆身边,逐渐沦为了“留守儿童”。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父母虽然切实地呆在孩子身边,却形同空气,这样的行为会让孩子的内心越发渴望得到关爱,实际上,这种情况对孩子的伤害和影响是最大的。孩子是一颗萌动的种子,它需要阳光和净水,而不仅仅是时常的机器修剪和外在打理。种子也需要长出枝桠,汲取各种营养,自由茁壮地成长。有些父母不顾 “种子”的内在渴望,一味地希望将孩子塑造至自己心中的完美形象,甚至将自己未完成的人生理想强附在孩子身上,然而,这却也同时成为了残害无辜生命的葬场。小容的父母不清楚其在学校的生活状况,总是一味地要求她好好读书、有一个好成绩,也总认为孩子所受的 “教育”全在学校,从未和她有过心与心的交流。小容多次想和母亲倾诉自己的内心想法、理想职业以及在学校的委屈,可是因为母亲工作太累和没有时间而一一被忽视和略过了。虽然母亲每次挣的钱都要小容帮助整理,希望于眼见母亲的辛劳中给孩子以学习的动力,但是这也同时给一个尚未成年的、心思纤细而脆弱的孩子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当小容发现假钱,自己将枕头下的真钱给母亲、将假钱撕掉时,引来的却是母亲的一顿怒骂,小容心里很是委屈。而父亲则早已对小容的成绩失去了信心,每次看见女儿就心情不好、在背后唉声叹气,给了孩子太多的负能量。小容曾想 “如果能成绩优异,老师、同学,还有爸爸妈妈,至少能待我好点吧。”在家里清冷的氛围中,她无法感受到爱的温暖,甚至对自己的存在有些绝望。中篇小说 《暗伤》确实折射出了当下家庭教育中的 “藩篱”,呈现出的可谓是一种 “伤痕教育”。如此,真正的关怀之意又何处可寻呢?
二、教育救赎之路——“以人为本”
在当前的教育视阈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有着如下意蕴:“第一,尊重和关爱学生的生命本性是起点和奠基石;第二,培养学生丰富的社会属性和鲜活的个性是核心内涵;第三,观照学生的全面持续发展是终极目的。”[4]然而,在大工业化生产的背景下,这似乎是一纸空文。因为,此一背景下强调的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具体而言,人们为了追求效率,舍本逐末,过分注重对孩子进行知识和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了对学生生命情性的培养。
笔者认为,在学校教育方面,师德建设的灵魂主要是关爱学生,其中,教师的行为举止对学生健康成长的影响尤为关键;在家庭教育方面,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是一个温暖的港湾,父母的关怀与呵护无论在何时,都是孩子成长道路上坚定的陪伴。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曾说: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者谢禾华、袁海林也谈到:第一,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是师德建设的基础;第二,热爱教学、关爱学生是师德建设的核心。[5]首先,教师应为学生树立榜样,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树立正确的育人观。教师的行为举止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并且,孩子由于尚未成年,自主辨识能力较低,教师的负面行为更容易成为孩子们学习的参照。我们需要铭记的是:“生命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归宿,关怀是教育的责任,也是教育的态度。”[6]再者,教师要经常与学生和家长进行对话交流,以便建立一种彼此间的相互信赖。对话交流是教师与家长共同培养孩子的基础,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必要保证。小说中的老师杨美美就明显地缺乏与学生及其家长的互动交流,从而轻易地对学生产生了偏见的情绪,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内在心理需求和学生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培养。最后,教师应对学生所做的符合正确价值观的事情给予认可和鼓励。对学生的最大尊重,莫过于认可和信任,这是建立 “关怀教育”这一师生关系的奠基石。我们可以猜想,如果老师能对小容将亲手折的千纸鹤送给同学这一行为予以赞扬而非批评,小容的内心或许就能因此获得一些安慰吧。
“家庭”应该是 “温暖”的一个代名词,对于孩子而言,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家”,而更是父母在实际行动上的呵护和关爱。而 “当前的家庭教育中功利主义与工具主义盛行,只关心儿童对生存所需的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而忽视儿童更深层的精神生命的成长;只一味地迎合学校教育,忽视了家庭教育独特功能的发挥。”[7]首先,父母是守护孩子生命的天使,在相处的过程中,作为家庭教师的父母首先应以身作则,做到事事躬为,保持高尚的节操。这是教育孩子的有效方式之一,让孩子知其然、明其道,塑造起健康、完善的人格。“假钱”一事中,小容母亲的做法就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示范;其次,父亲和母亲之间要加强沟通,密切关注孩子的发展状况。父母间的微妙关系必然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母爱和父爱的融合,是促进孩子完善人格的重要条件。为生活而疲于奔命是小容父母的真实写照,生活的艰辛压抑了这一家人,母亲每天在菜市场卖菜早出晚归,最后生病住院了,而父亲蹬三轮车,因此,两人每天回家言语少之又少。及至小说末尾,当父亲在听完小容的倾诉后,才感受到自己的女儿居然承受了那么多,他的内心感觉沉甸甸的,一种后悔、一种自责油然而生;再者,父母要学会放松自己,给自己一些自由活动空间,让孩子感受到生活环境的自由与快乐。小说中有多处关于生命重要性的片段描写:小容母亲生病了,差一点就延误病情,得不到救治;一个年轻妈妈的孩子从六楼摔下不治而亡;一个年轻的单位领导人由于喝牡蛎粥不慎噎死了。生命的无常让父亲感受到 “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孩子能读好书自然最好……那干脆让她活得轻松快乐一点。没钱人有没钱人的苦,有钱人有有钱人的苦。”父母应从生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及时反思、反省自己,充分理解孩子的感受,让生命教育成为一种可能,让孩子在自己的心灵花园中自由翱翔。
三、教育的力量——探索孩子个体生命成长的可能
“‘天命之谓性’是 《中庸》开篇提出的第一个基本命题,是对 《中庸》中的生命思想的集中表达和总体概括,揭示了生命的本源性、普遍性、目的性。”[8]生命的成长本就是追求本性的一个过程。如是,以孩子的自然天性来培养他,何乐而不为呢?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自然万物的一种化身,他们在教育领域作为不同的角色而分工合作,教育者起着主导作用,受教育者是学习活动的主要对象。可小说中所呈现的却是反其道而为之,杨美美机械地教育学生,并未真正尊重学生的生命,忽视了对学生生命情性的培养,只注重学生在应试成绩上的进步。父母对孩子也未能做到生命本真的教育,自己没有生命意识的存在,每天都在外在的物质世界疲于奔命,他们在忽略了自己精神世界发展的同时,甚至对孩子也实施了强迫性和阴霾性的教育,致使孩子陷入了孤单的境地,直至最后丧失了宝贵生命。我们不能确定谁是扼杀孩子的真正凶手,但是我们知道,良好的教育已成为了一种共同的呼声,唯有这样,孩子个体生命的健康成长才有实现的可能。
这是一篇直面当下教育弊端的小说,值得我们大家共同反省:我们该如何尊重孩子个体生命的成长?作者孙敏瑛是一名矿工的女儿,在童年时代,她曾经历矿区生活的困苦和艰辛,明白如何直面生活:“一个人,如果终日只为追求物质埋头努力,而不去理会精神的花园,那么这个人的内心将会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孙敏瑛曾写过一篇散文——《旧痕》,反映的是她少女时代的一场红色梦魇:因家里穷,母亲只买了一匹红布,因而总给小敏瑛穿红布衫,遭至班主任的歧视和忽略,这条旧痕至今纠结于心、无法释怀。因此她认为,小草一样的孩子,最幸运的莫过于能遇到一个温和亲切、灵魂洁净的好老师了。她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书写小说,以孩童视角去观照当下社会的教育弊病,这是一名作家对底层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同情和关怀,也是她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在 《暗伤》这一小说创作中,孙敏瑛强调教师面貌和父母角色的重要性,表达了作者对孩子个体生命成长的关怀。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关爱学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教育方式,这既是对学生生命的体察和关爱,又是对自身生命状况的反思和总结,家庭教育亦是如此。在强烈的生命关怀意识的推动下,孙敏瑛展现出对底层群体的同情、对当下教育的忧虑,以及对生命成长的批判,她试图通过孩童的教育困境,来调整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对生命成长、生命教育的盼望。
当然,孙敏瑛的教育小说所反映的问题只是教育领域的冰山一角,教育作品的创作要持续直面当下的问题,以敏锐的笔触痛寻问题深处的根源。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在自我对文学价值认识的基础上,需要依据自己的生命活动形态,遵循人的主体意向,自由自觉地表现出对教育的看法和思考。并且,文学与时代又是相互联系的因子,好的作品能 “反映出文学对人性,对时代精神的深刻精神的观照方式的深刻变化。”[9]当下,许多作家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创作愿望,着力于反映当下教育问题,寄托自己的教育希冀。例如:程维佳 《二〇〇九年的招生》反映的是在高考教育制度下,教师功利化的悲哀;季栋梁 《教育诗》反映的是教育的歧视问题对学生造成致命的危害;俞莉 《宝贝》反映的是家庭教育的失败等。在我们看到作家们对生命生存状态的书写、对生命个体的观照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作家们对教育理想的追求。这些创作,让我们能够从不同视角看待教育问题,对开展我国教育现状的思考和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借鉴甚至是指导性价值。
当前,加强社会对学生个体生命成长的关注是关乎教育命脉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无论是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还是微小的局部调整,对教育本真形态的回归是其题中的应有之义。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教育要想从根源上摆脱困境,就必须要淡化教师的功利化观念;必须要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切实地把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落到实处,铸造民族精神。否则,中国的现代教育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教育质量普遍下降的趋势和困境,最终的后果就是侵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教育的真正本愿应是以人为本,以爱为中心,从而使孩子的生命成长成为一种可能。
注释:
[1]明庆华:《论教育中弱势子女受歧视问题》,《中国教育学刊》,2003年第5期,第11页。
[2]孙敏瑛:《暗伤》,《清明》,2015 年第 1 期,第 43页。该作品引文出处下文不再一一标注。
[3]刘良华:《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中国德育》,2009年第3期,第47页。
[4]姚姿如、杨兆山:《“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蕴意》,《教育研究》,2011年第 3期,第 17页。
[5]谢禾华、袁海林:《关爱学生铸造师魂——由近日二则案例谈新时期下的师德建设》,《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7期,第158页。
[6]程瑞娟:《关怀教育理论视阈下学生个体生命的成长》,2009年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刘济良,第80页。
[7]李莹:《生命化家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初探》,2013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孙峰,第3页。
[8]李卯、张传燧:《“天命之谓性”:〈中庸〉的生命思想及其教育哲学意蕴》,《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24页。
[9]陈晓明:《文学与时代及其个人经验》,《文艺报》,2013年4月22日,第003版。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舍予
责任编辑: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