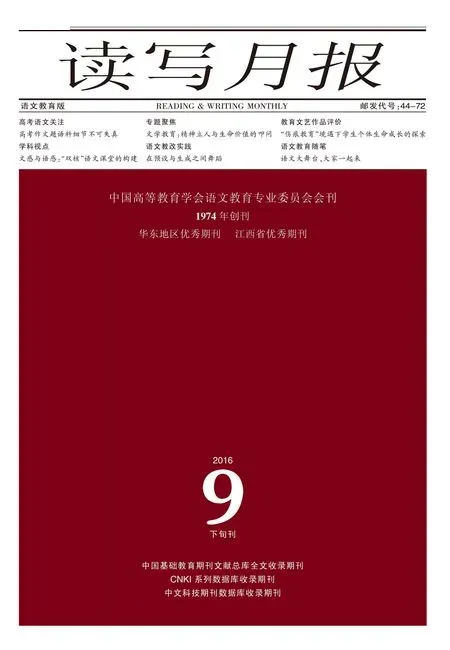师与生的生命之歌
——日本影片《北方的金丝雀》解析
杨舒晴
师与生的生命之歌
——日本影片《北方的金丝雀》解析
杨舒晴
日本影片《北方的金丝雀》于2012年作为东映公司创立60周年的纪念作品上映,其在“悬疑”的外壳下,关乎的是一段缓缓流动的师生情。影片中,在冬日孤绝的皑皑白雪的映衬下,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交互上演,这之间的温暖也因此沁人心脾。老师川岛春和六个学生在相互的敞开与慰解中共同谱写了一曲成长之歌,同时更鼓舞着我们,即便生活艰难有时,坎坷有时,无情有时,我们也应该记得——歌唱生命。
影片伊始的几个空镜头展现的是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苇草摇曳、海涛拍岸、鸟鹰盘旋之景铺展在我们眼前。旋即镜头朝向穿着厚实大衣、提着行李箱步步走来的川岛春,旧相识见到春好奇地张望又急忙关紧木窗,或而直接停下手边的活计挤进屋内。屋外之狗也朝着春吠叫,春心头一紧,清冷舒缓的配乐响起。瞬即转头看到了学生铃木信人(小信)的春露出了笑容,亲切地朝着少年走去。雪花飘飞中,小信却突然向春老师扔过来一枚硬石,春的额头上流出了鲜血,小信径直跑走,留下春呆立在木屋旁。接着,画面切换到了二十年后作为书店的图书管理员的春最后一日工作时的场景,她还特意取下、翻开一本画册,看到了往日的彼地雪景。随之,相关情节展开。
一、汇聚“爱”之图景
《北方的金丝雀》由推理小说家凑佳苗的作品改编而成,正如原小说名为《往复书简:二十年后的作业》,影片穿梭在横亘着二十年时光的生活两端,为交错式的电影结构。紧接前述,刚退休不久的春迎来了两位刑警的到访,她得知曾执教过的六名少年中的一人——小信卷入了一场杀人事件。在种种疑问中,春接连走访了另外五名学生(户田真奈美、生岛直树、安藤结花、藤本七重和松田勇)而试图了解情况,过往的种种也在与学生的会面里再次浮现。昔日小小个、围绕在老师身边的孩童,如今都已成年、超过了老师的个头,孩童时代和成年之后的学生使用了两组演员来演绎,而二十年前后的川岛春这一角色虽均由演员吉永小百合担任,但在服装及发型(二十年前的春是齐肩中长发;二十年后的春则是短发)的处理上均有差别,因此,观众在观影中也很容易区分两个时空。并且,在场景运用中,过去的空间场景多是在低矮、破旧的校舍及其周围,黑板、书包、课桌、书柜、地球仪等物件很快地就能将观众带回校园生活中。而反转之处在于,影片后端,我们才知道,老师在先前就知道小信杀人之事,她其实是借由这样一种方式聚集其余五名同学回到小岛,陪伴最珍爱童年岁月中的纯真情谊的小信走过入狱前的最后一段路,给他再度去爱的力量。至此,可以说,笼罩于观影者情绪中的那团疑问之云也随之散开,进而还产生了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明之感。
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中,在芥川龙之介小说的情节基础之上,采用的是一种多重的平行叙述手法来结构影片:以不同的人物视点多角度地展示同一事件,而在这些讲述的版本中,“真相”既相互重合又相互冲突,充分表现了人性中幽暗、复杂的诡谲之相。凭借该影片,黑泽明在威尼斯影展上斩获金狮奖,成为了金狮奖历史上的首位亚洲导演。而这一独特的多重性的叙述视角与同一事件不同版本的叙事方式,也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罗生门’叙述模式”,对其后的大批影作产生了影响。这一多视点叙述方式在影片《北方的金丝雀》中也十分明显:二十年前,春和丈夫行夫来到位于北海道的一座寒冷的小岛上,春成为当地仅有六名学生的小学的老师,孩子们都十分喜欢这位温柔可亲的老师。然而,在一次户外烧烤的活动中,一场意外夺去了行夫的生命,春也在村民的指责中被迫离开小岛。这一事件在六个孩子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甚至让原本亲密的好友之间充满龃龉。时隔二十年,已经长大的孩子们一一向春老师叙述起自己记忆中的这次事件,因此,影片中穿插了六次这一事件的“重现”。我们知道,《罗生门》中,每个人的独白都是整个事件的碎片,人人都只讲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一面。而在 《北方的金丝雀》中,在同一事件对象的讲述中也存在差异,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某部分记忆,但无一例外的是,孩子们都将刀刃朝向了自己:他们都对当年的事件怀抱了一份自责和愧疚,在线性时光的流淌中,在孩童时代最敬爱的老师面前终于有了勇气说出那句“对不起”。这也不禁让故事之外的我们思索,在自我的成长过程中,那个小小的自己是否也曾对某事留有阴影,是否也曾对某人怀抱歉意?可是,在心底深深扎根却又藏匿起来的这些小豆苗,真的可以像这个故事里那样,总有一天能舒展开来,化解那份遗憾、解开那个心结吗?至少,在影片《北方的金丝雀》的多视点叙述中,我们能看到“时光”之于个人的一种意味:在时光河流中或浸染或荡涤,我们开始知晓这个世界的复杂,开始学会理解和感同身受,进而也还可以开始在救赎中得到宽恕。
可以说,这部影片虽然涉及死亡、杀人等“悬疑”因素,但包裹着的内核还是“爱”——老师对学生的爱、学生对老师的爱、同学与同学之间的爱、丈夫对出轨妻子的爱、妻子对绝望者的爱、父亲对女儿的爱、成人对孩童时代的爱……影片在上述言及之交错式结构与多视点叙述间汇聚而成的俨然是一幅“爱”之图景:在这里,“爱”不再是单一的纯美情调,其呈现的是一种交织的、矛盾的却也清澈的复杂存在。就最核心的师生关系而言:对身处于孤岛的这六个孩子,春老师的出现与离去就像是一道意外照进不久又消失的光束。一方面,这段虽然短暂但却快乐异常的日子能让孩子们在时隔二十年后还感知得到余温,抑或可以说,老师在教育孩子们时表现出的平等、友善与责任也无意间化作了一簇“爱”之火苗,在学生们的心灵里长久地点燃并照亮了一方角落,使他们尔后行走在人生的暗夜时也能依旧葆有内心的暖意。可同时,另一方面,当老师带来的光亮戛然而止,孩子们觉得自己就像是被丢弃在后山的金丝雀,嗓音清亮的他们不再歌唱。在春走访学生、与之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当年老师的不辞而别对孩子们的伤害,小信面对着即将驶行的轮船,愤怒地掷过来最爱的木质玩偶,结结巴巴地呐喊着让春老师不要离开。也许,春老师多陪伴小信一段岁月,这个失去双亲、将春视为母亲的小少年的性格缺陷也能更完善一些,或许就能避免其在冲动之下杀人之事的发生。在对往事的回顾中,春双手抚摸着行李箱上系着的早已泛旧的木偶,也终于说出了那句:“我对你们,做出了无情的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春二十年后的这次回访,也可视为是对自己的一次找寻与谅解之心灵旅程。而若把学校教育比喻为养分,家庭教育则更近乎是土壤:当我们将影片中孩子们的行为举止追溯至家庭生活的影响,也明显能看到在家庭教育的缺失或缺陷之下,这些少年的心迹中的踉跄步伐。
二、生命的映照与歌唱
值得一提的是,凑佳苗的小说《告白》曾被导演中岛哲也改编为同名电影(2010年上映),并荣获了第3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奖及第34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奖。同样是改编自一个作家笔下的推理小说,这两部电影在两位导演的镜头中却呈现着不一样的风格,而这也正是日本电影乃至日本文化中的两大美学风格的展现:中岛哲也的《告白》华丽而残忍,阪本顺治的《北方的金丝雀》清雅而婉约。
导演阪本顺治在电影《北方的金丝雀》中拍出了接近昭和年代里的那种如和歌、如柳絮般的幽婉哀情。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日本的艺术展现了一种纤细、绵密之美。在文学方面,《源氏物语》、俳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川端康成等接续、发扬的都是这样一个传统。在日本电影中,因此也尤为重视自然景物之美的拓展意境及其对情感的渲染作用,“樱”和“雪”在这样一种传统的审美情趣中倍受推崇,前者代表着短暂、伤逝之美,而后者则兼具孤独哀伤与春晓萌动两种意蕴。影片《北方的金丝雀》放置在日本最北的利尻岛及礼文岛拍摄,平日较少人迹的该地风景秀丽、生机恣肆,因而全片呈现出一种如画卷般的唯美镜像。大片大片的雪景作为人物背景或空镜头场景多次出现,奠定了影片哀而不伤的情感基调。片头,川井郁子演奏的悠长的小提琴声响起,导演在此运用了多个影调共同表现天光云影之景:青灰色、暖黄色、灰绿色、蓝绿色的光线色调下,倒映着亮光的海水翻腾不息,最末一个画面,一轮朝阳自海平面溢出。可以说,这也正是老师川岛春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在显现的隐喻,六个孩子在成长岁月里都曾抱怀某份“秘密”,但影片中大多是一个倾听者的春无疑才是全片中内心色调最斑斓的焦点人物,在春为数不多的絮语及回忆的画面中,我们却能拼凑起更全面的事貌:丈夫行夫患了脑肿瘤,行夫最喜欢学生时代所在的小岛,希望于此安享最后半年的生命光阴,因此春和他才会回来,春也才会成为孩子们的老师。然而,面对自己的死亡是一件非常痛苦之事,行夫一次次纠缠在犯病的疼痛和幻觉里,身体还不时不能自主,妻子春目睹这些,显然也是不容易的。就在这时候,春遇见了一个因为直面人质的死亡而深感无能无助因此试图自杀结束生命的警察阿部英辅,因为担心阿部会再次觅死,春多次去见他,也因为两人对“绝望”的共同体会,他们之间也产生了一种相互依偎、相互扶持的“绝望之爱”,两人多次拥抱,进而还忘情拥吻。在影片的第55分钟,春和阿部第一次遇见前,导演剪辑了一个呈现着灰蓝色调的海景空镜插入:天色黯淡而清冽,云朵低垂,画面偏右下侧的海波在光照下泛着冷光。接连的特写空镜就指向这片海水,其粼粼翻动之状更为明显。同时,在海水声之外,还有鸥鹭之清脆、悠远之鸣。这也就暗示着春的内心即将经历一定程度上的波动,而同时,也正由于此,她也获得了自我情感的某种安放。面对着春的父亲对女儿这一行为的道歉,行夫理解、宽慰地说:“春她是想着我的事情,太痛苦了”。接着,就是行夫溺水去世的“意外”发生。可得知,孩子们窥见的只是光谱中的某一小段,因着年幼,对于春老师“出轨”之事他们只能从外在的伦理、道德层面上进行单一认知,也因着年幼,伤害与撕裂感在他们稚嫩柔软的心田里也扎根得更深。而影片中,二十年后,当同样成为了一名警察(也直面了某些无助之境)的松田勇向春老师当年的行为表达出某种理解之后,切换到的是这样几个画面:大全景下,一片开满野花的绿意盎然的原野里,老师带着六个孩子唱着欢乐的民谣从画面右侧入画,当他们走到画面中部时,镜头随之跟拍;坐在海边礁石上的阿部朝向画面的右侧,听着歌声的他舒缓了一口气,随即往后躺下,身边鸥鹭翩跹飞过;镜头切换到丈夫行夫时,其也是与老师及孩子们入画的方向相对而坐,在美好纯澈的歌声中他不禁留下了眼泪。可以看到,孩子们的歌声与这两个身处在困境中的男人之间,是交汇、激荡起了某种触动与感动的。
的确,影片中孩子们的“歌唱”,不仅使他们发觉了自己的音乐才能而获得了一些自我肯定,也凭借着这一能够使人产生共鸣的艺术载体,他们也在向大人们传递生命的力量。影片末尾,长大了的他们依循着童年的步步温馨足迹,穿越风雪相聚只为了唱一首童年的歌谣,这群被遗忘在北方的金丝雀在爱的包围中终于再次歌唱:
忘了歌唱的金丝雀啊
要用柳条抽打吗
不行,不行,那样太残忍了
忘了歌唱的金丝雀啊
象牙的船儿银质的浆
游荡在月色下的海上
想起了早已忘却的歌
隔着清晰又模糊的往昔时光,这时候的歌唱也就融入了这二十年里的甘甜与困厄,也就是一曲为自己的生命而唱的歌了。这里的一个镜头是从外面的窗户拍进来的,操场里孩子们玩耍的两个器械在反光的玻璃上十分显眼:一个是秋千,一个是鸟笼样式的转盘,暗示着长大后的道路,一半是飞翔的自由与欢乐,一半却是牢笼的沉重与束缚。而在这个秋千旁,即将被锁上手铐带去监狱的小信,也向春老师回忆起行夫的溺亡,在他的视角和记忆里,行夫在被波浪吞噬时告别似的挥了挥手,那一瞬间他就像如释重负般心安了。春也终于释怀般地失声痛哭,如果行夫是这般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也只有一个理由,他希望春能不那么煎熬、痛苦地活着。由上可以说,导演在场景的剪辑与景物的运用上较为用心,从而使得外在景观映照出了片中的人物生命。而在静默的雪山与旷朗的天空下,作为观影者的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望见了自己,也许还产生了诸如海子的那句“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1]般的心解与慰怀。金丝雀拥有清丽美妙的鸣叫声,而我们,也应当在生命的乐章中成为一只善于歌唱的金丝雀。
注释:
[1]海子:《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见《海子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舍予
责任编辑: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