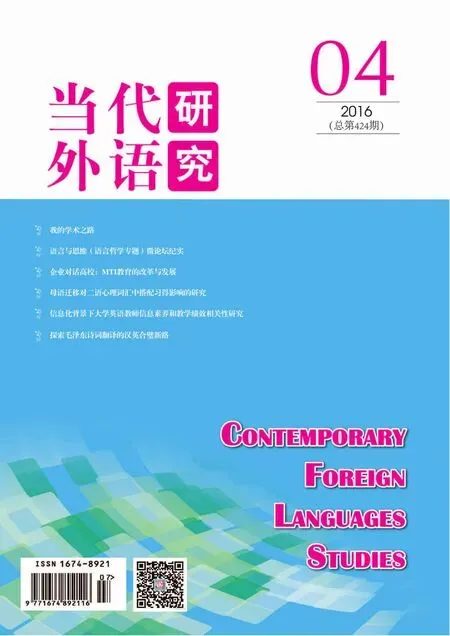英汉笔译中的物理规律
——翻译单位的时空界限与形式标志
陈友勋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402160)
英汉笔译中的物理规律
——翻译单位的时空界限与形式标志
陈友勋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402160)
摘要:英汉笔译是围绕翻译单位而展开的语际转换活动,能否运用可靠的形式方案对翻译单位的操作过程进行简化和规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英汉语言中的无标记表达暗含着人类的认知共性,可类比于简单的物理运动,而语言中的标记性表达结构则体现了语言使用者对这些认知规律的人为操纵和刻意控制,集中反映了英汉语言的个性特征和语用风格,凸显了两种语言基本结构之间的时空关系。因此,研究英汉语言中的形式标记,特别是原文和译文中虚词的时空特征及其相互间的映射关系,可以在英汉笔译过程中为语际转换提供重要的认知参考,简化笔译过程并规范笔译操作,帮助译者顺利实现对翻译单位的认知操作。
关键词:形式标记,翻译单位,时空关系,英汉笔译
1. 引言
当下的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李德超2005)。但这方面的任何实证研究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关于翻译单位的讨论。因为任何翻译实践在形式上都必然表现为一种拆分原文并重组译文的操作过程,所以翻译单位历来是翻译研究(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内容和主攻方向。人们分别从语言学、社会符号学、认知心理学、脑神经科学以及其他各种交叉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也得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发现和结论,如认为翻译单位实质上是一种认知转换(Lorscher 1993;汤君2001;耿强2003;陈友勋2011:31-33),受制于译者的工作记忆的容量限制(Miller 1956;陆丙甫、蔡振光 2009),在翻译实践中表现为译者连续性思维的中断(Jaaskelainen 1993),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翻译单位的认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翻译单位中折射出的语言对比、社会文化、生理基础、心理特征和认知本质。
但是,翻译单位本身作为翻译实践的基础和产物,其基本功能应当是指导翻译实践,而前面的理论研究大都和翻译实践相去甚远,很难对翻译实践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Bell(1991:25)认为翻译理论是一种无形的(intangible)东西,需要借助模式才能具体化(A model is a realization of the theory),或者说才能对翻译实践产生直接的作用。而国内的陆丙甫(1993:9-10)也认为这种理论的“形式化”是一切现代学科的基础,因为只有“形式化的概念才能在思维中得到明确、有效的操作”。联系翻译单位在实践操作中的形式特征,学者们的这些精辟的见解似乎在启发我们,对翻译单位的研究如果要弃繁就简,应当直接从翻译单位的表现形式入手,因为只要找出某种固定的形式标志并确定其中的先后关系,就可以作为在原文中划分翻译单位的界线,并进而在译文中调整它们的相互位置。这样,译者对翻译单位的掌握也就简化成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操作模式,从而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于是,现在的问题变成了:能否在原文中找出具有这种功能的形式标志,并将其简化到人人都能识别并运用的程度?本文结合英汉笔译的实例,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们认为:翻译单位的划分和组合都依赖特定的时空坐标,其中暗合简单的物理规律。译者只要结合基本的语法知识,找出原文中起连接作用的相应虚词就可还原出翻译单位中的时空关系,并进而以此为依据将这些翻译单位在译文中进行重新组合。为此,我们在下文中将具体阐述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英汉语言的时空共性与翻译单位的认知前提;第二、英汉语言的表达个性与翻译单位的划分标志;第三、翻译单位的时空异位与译文重组。
2. 英汉语言的时空共性与翻译单位的认知前提
译界早有定论,英汉语言对比之下的一个最明显差别,就是二者对形合与意合的各自偏重,如连淑能(1993:48)在《英汉对比研究》中将它们在表达形式上的区别总结为在遣词造句过程中是否需要借用连接成分(connectives)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汉语表达中“少用甚至不用形式连接手段”,注重“隐性连贯(covert coherence)”,以神统形,属于偏“意合(parataxis)”语言;而英语造句“常用各种连接手段”,注重“显性接应(overt cohesion)”,以形显意,所以属于偏“形合(hypataxis)”语言。这是英汉对比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这个结论简洁明确,易于理解;并且由于它紧紧结合了两种语言在表达层面的基本形式特征,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此成为少数几条能够真正对翻译实践起积极指导作用的理论之一。但这个结论只是总结了英汉语言的形式差异“是什么”,没有深究造成这种差异背后的 “为什么”问题,即导致英汉表达呈现迥异特色的认知原因,或者说造成差异的产生机制。而这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程度是不足以让该理论成果模式化或形式化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英汉语言形合、意合的认知机制。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包括翻译在内的一切语言现象在本质上都属于人类的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而认知活动是主客观之间的互动,所以必然体现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的基本特征。语言在前者上的表现就是“不悖于人类大脑神经的基本事实”(Lamb 1998:4;程琪龙2001:17, 273),比如语句表达中离散语块的数量不能超出工作记忆的最大容量范围;语言在后者上的表现就是必然在特定的时空范畴中展开,所以客体世界中那些基本的物理特征也会在语言表达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这方面研究较多的是关于语言中的临摹现象,如语序在时间上一般都是遵循自然界的先后规律,在空间上一般都遵守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的固定次序(Haiman 1983)。这种语言外部的物理、生理规律已经固化成人类认知活动中的本能反应,一般不为使用者的意识所觉察,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潜藏在语言现象的最底层,对语言产生深刻的规约、限制作用,所以成了语言表达中的默认表达或缺省形式,属于“无标记”结构,体现了语言之间的共性特征。
受制于人类认知处理的容量限制以及语言线性表达的物理特征,客观世界的时空规律通过临摹方式投射到语言中的集中表现就是:语言结构的基本形式只能表达一种时空状态。这是英汉语言表达的共性。如果借助传统语法知识,无论英语还是汉语,简单句都以一套主谓结构为常态。因为主语必须是名词或相当于名词的结构,而名词在认知上体现的是一种空间概念;而谓语一般是动词或相当于动词的结构,而动词在认知上体现的是一种时间概念,所以传统语言研究实质上已经观察并总结出了英汉语言的时空共性,只是表达措辞各有不同而已。
由于简单句属于语言的基本结构,属于默认的缺省形式,不需要进行特别说明,所以采取的是无标记的表达结构。反过来也就是说:英汉语言中的“无标记”结构都应当体现上述时空规律。如英语中的“I love flowers”和汉语中的“我喜欢花”描述的都是在一个时间维度上(“现在”)展现的一个空间维度(作者的基本心理倾向:喜欢花),符合基本的时空规律,所以采取的是无标记的表达结构。于是,这种经验事实也验证了前面的理论推测。
同时,从上例中可以看出,“无标记”结构由于体现了英汉语言中的思维共性,所以在翻译中处理起来是最轻松自然的,基本上直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英汉笔译中遇到的都是这样具有时空共性的“无标记”的表达结构,那也就没有必要讨论翻译单位了,因为人类的认知具有天生的惰性(Zipf 1949:1;马尔丁内1980:4-5),只要能达到预期的认知效果,人们会倾向于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
但翻译实践中翻译单位的大量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其实从反面证明了我们使用翻译单位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认知前提,即:翻译单位的存在是为了降低翻译操作的难度,至少是把翻译任务分解成译者能够处理或轻松处理的地步。此外,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角度切换到语言形式上,那译者对翻译单位的依赖性也证明英汉语言在笔译过程中存在很多相反的例子——即“有标记”表达在英汉语言中大量存在,否则也不会出现前面所说的关于“形合”与“意合”的对比差别了。不过这倒是提示我们在笔译实践中首先要明确一点:即怎样才能把原文中的标记性结构分解还原成 “无标记”的表达,从而可以轻松地完成语际之间的转换任务。这可以说是划分翻译单位的基本目标或努力方向。
3. 英汉语言的表达个性与翻译单位的划分标志
如上所述,无标记的表达体现了语言的共性,成为翻译中可译性的基础。与之相对,有标记的表达则体现了语言的个性,是造成语言表面形式千差万别的直接原因,也是阻碍信息交流的形式障碍,因此自然成为了实证翻译中需要重点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首要问题。根据人类认知的惰性原理(或认知经济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Zipf 1949:1),只有对那些不符合基本时空规律的表达结构,人们才会在语言中添加额外的形式手段,从而形成标记性结构,提醒读者此处表达异于常态,应当根据标记进行相应的调整。
联系到英汉语言的具体情况,笔者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可以类比为物理运动中的时空状态,即在无标记的表达结构中,每个语句中涉及的事物(主语)永远只可能存在一种时空运动状态(谓语),除非遇到显性的形式标志(有标记表达)才可能人为地改变这种默认的运动状态;或者也可理解为,由于语言中显性标记的存在,就可以扩展语言的基本结构,使其具有容纳多个时空状态的可能性。所以,只要语言表达主要依照这种自然属性,那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使用形式标志进行显性连接,比如汉语侧重意合就属于这种情况。以前人们早就观察到汉语的特点是短句、流水句居多(连淑能1993:67;刘宓庆2006:200),这种表达形式特点其实说明,在认知层次上汉语喜欢把表达结构和时空状态直接对应起来。一个单句只表达一种时空状态,没有和其他时空状态相杂糅,这符合了人们的基本认知习惯,相互之间不会造成混淆,所以不需要添加过多的形式标志来指明彼此之间的时空关系,因此汉语短句就可以依次直接排列起来,像小河流水一样往前不断延伸、自然流淌。这充分说明了汉语遣词造句对时间关系的倚重性。当然,这样的特点也决定了汉语在表达复杂的时空状态时往往必须进行分解操作,从空间关系中提取独立的主语构成单句,从时间关系中提取主语对应的谓语并决定单句之间的排列关系。所以汉语的“意合”倾向于通过“分空间、重时间”的方式来描绘具体的时空状态,而这样的认知特点渗透到语言的表层结构上就表现为汉语中可以少用或不用显性的形式标志。
与之相对,英语习惯在描述一种时空状态时借助于丰富的形式手段,顺带描绘多个时空状态,这也就造成了它形合的特点是“合空间、重时间”,所以具体的表达结构往往显得庞杂、繁复,而为了把这些彼此交叉的时空状态交代得有条不紊、层次清晰,英语中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形式标志,包括关系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代词、连接副词)、连接词(并列连词、从属连词)、介词以及形态变化(词缀、词性转变)和语法手段(主谓一致关系等)(连淑能1993:48-52),这些形式手段历来在传统语法中被称为“虚词”,因为它们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交代的是实词之间的时空关系,主要起谋篇布局、理清思路的作用,引出与描述事件相关的实际要素并按一定的时空关系将其组织起来,所以提供的是表义的框架。但这些虚词在翻译过程中对理解和表达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朱纯深(2008:163)将其深刻地总结为:“句法上,一个句子是由功能词(虚词)和实词共通负载认知信息。句子的意思是由实词携带,并有功能词标定界限并串联成序。”本文中为了便于表述和分析,笔者把英语中这些起连接作用的虚词分为空间标志和时间标志两大类。前者包括如“when,while,as,before,after,since,until,till,then,as soon as”等直接表示时间关系的连接成分。此外还包括那些虽然不是直接表达时间先后关系,但在认知上完全可以模拟为一种逻辑思路的运动方向,即它们所引导的语句内容要么是顺着前文的思路前进,要么是改变了前文思维的发展轨迹。总之还是和时间的一维性相关,所以在逻辑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具有时间先后关系的连接成分,如“because, therefore, consequently, so, thus, and, also, too, in addition, furthermore, but, still, yet, however, nevertheless, nonetheless, even though, just as, for one thing, for another, on the contrary”等;后者包括“near (to), far (from), in front of, behind, beside, beyond, above, below, to the right/left, around, outside”等以及那些虽不是直接表达空间关系,但在逻辑意义上可以比较范围大小的连接成分,如“whose, in which, moreover, that is, just as, for example”等。
通过比较发现,英汉语言中的时间标志区别不大,根据时间的方向可以分为向前(before, however, nevertheless)、向后(after, since, until, therefore, consequently)和同时(when, while, as, as soon as, for one thing, for another)三种状态,其中向后的时间状态是人类认知的自然方向,所以在语言中可以缺省表达。而其他两种时间方向必须明确地加以说明,否则会让意义混淆,比如听到回家睡觉会下意识地理解为先回家、再睡觉(go home and have a sleep),但如果不是这样的心理时间顺序,则必须在表达中加上形式标志,说成回家之前先睡觉(before we go home, we will have a sleep first)。但英语在空间标志上则比汉语丰富得多,可以详细地阐述两个事物在空间范围上包含(如whose,in which,for example等)、等价(如and, that, which, just as等)或递进(如above all, in brief, generally speaking等)等各种复杂关系。
根据语言标记的基本原理,只有标记性才真正体现了语言的个性(沈家煊1999:22-42;石毓智2004:183-190)。换言之,只要找到这些形式标记就可以剔除语言的个性,或将其还原为具有共性的无标记表达。这个推论对英汉笔译中如何操作翻译单位尤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它已暗示英语中的这些形式标记其实就是可以直接帮助我们划分翻译单位的参考点,并且从这些形式标记中还原出的时空关系也是译者随后安排译文语序的直接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语言的形式标记入手操作翻译单位,正如数学家在解析几何中添加了辅助线,既可以简化过程、降低难度,又能统一标准,便于英汉笔译经验和技巧的学习、掌握和传播。
于是,我们可以认为,笔译中要操作的翻译单位其实就是剔除语言个性特征之后剩下的表达共性,即基本结构而已。其实这样的结论在其他关于语言的研究中已经有人触及,只是当时还只局限于一门语言的内部,没有像本文这样直接将其扩展到两门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中进行观察和讨论。如国内的陆丙甫(2010:3-13)和石毓智(2004:179-190)都曾从认知角度分析出英汉语言中存在着基本的表达结构,它基本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显得极为稳定,是构成更大表达结构的备用成分或预制体,可以不改变次序就直接嵌入表达中使用,并认为这一特点“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译中看得更清楚”,因为我们可以把这种基本结构视为“最小对等单位”,将其逐一翻译好之后,再“根据各语言不同的词序习惯来调整位置,句子对译就基本上完成了”(陆丙甫2010:10)。石毓智则结合汉语明确指出这种基本结构就是小句,因为小句是句子“内部的构成成分”、“基本结构”和“无标记结构”,其语法格式代表的是汉语句子在理想状态下的情况,因此“不受上下文等语境因素的干扰”或“制约”(石毓智2004:180, 183, 190)。而Catford(1965:27-31)和Toury(1986)则是联系翻译现象进行讨论,认为在各种翻译单位中,小句(clause)是最佳选择,因为语言通常是在分句的层面上来表现事件的,且在分句这个层次上不同语言之间的区别更为明显。无独有偶,Malmkjar(1986)在讨论翻译单位时也认为小句(clause)是理想的翻译单位,认为“只有在小句层次上,从意义到意义的翻译才最有可能与从结构到结构的翻译联系起来”。可惜这些翻译学者们没有联系认知科学进一步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所以不能明确地指出译者划分翻译单位的认知实质就是在寻找一种单一的时空状态,而单一的时空状态在语言形式上就是无标记的表达结构。而任何事物在哲学上都是有无相生,或相待而立的,因此可以根据有标记的形式特征去还原无标记的表达结构,这个过程在翻译中也就体现为以翻译单位为中心的一系列操作组合。
4. 翻译单位的时空异位与译文重组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英汉笔译中操作翻译单位的前提,同时也是操作的重点,就是在原文中寻找起连接作用的形态标志,从而区分各个时空状态及彼此之间的时空关系,这样才能为后续操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下面我们结合一个译例来进行介绍。
例1:A conservative women’s group will issue a report today contending(1) that while most college women embrace marriages as a life goal(2), their pursuit of that objective is undermined by the prevalence of relationships on college campuses(3) that feature sex without commitment(4). (From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6, 2001)
上例中起着连接作用的分别是“(contending) that,while和that”,其中除了while是时间标志,其他两个都是空间标志。凭借这些形式标志,可以还原出原文中的四个时空状态,将其加上下划线并分别标记为(1)、(2)、(3)、(4),也就是说,翻译这句话需要处理四个翻译单位,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确定它们之间的时空关系。
由于英汉语言在时间标志上差别不大,因此翻译之中如果主要涉及时间标志,处理起来较为容易,因为译者一是可以寻找相应的汉语时间标志直接对应,这就是典型的直译过程,如把“You can make your choice after having a taste of them”直译成“你可以在决定是否购买之前,品尝一下它们的味道”;二是可以根据从原文中还原的时间关系,直接按照汉语的规范重新组织语句表达,这也就是典型的意译过程。如前面这句英语就可以意译成“你可以先品尝它们的味道,再决定是否购买”。
但是,由于英汉语言在空间表达标志上差别很大,它们在组句过程对空间关系的依赖程度明显不一样,这就造成了英汉笔译中操作翻译单位的难点在于从空间到时间的过渡转换,即译者要善于从英语的空间组合中还原出可供汉语使用的时间关系。这种时空转变,连同前面的时间重排,可以统称为翻译单位中的时空异位,是翻译过程中最棘手的地方,其中参杂的译者主观因素成分较大,所以见仁见智,是造成译文多样化的直接原因,也是最能验证译者功力,体现译文整体质量的地方。如在“He falls for his dance partner who is so gentle and beautiful”之中的连接标志是关系代词“who”,指代的是先行词“his dance partner”,因此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它属于一种空间标志,但稍作分析,都能理解这其实暗含了一种因果关系,即因为“His dance partner is so gentle and beautiful”,所以才会出现“He falls for his dance partner”。由于原因在时间上应当先于结果,这句话在汉语中的正常表达应当是:“他的舞伴如此温柔美丽,让他不禁心生爱慕。”这就是典型的时空异位的例子。同样,根据常规语法分析,例1中的第二个“that”是前面“relationships”的关系代词,引导的定语从句是对中心词进行补充说明,所以容易翻译成:“她们对婚姻的追求被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的没有承诺的两性关系所削弱了。”但从逻辑上理解,“that”分隔出来的两个翻译单位(3)和(4)所代表的两种时空状态其实在认知层次上属于因果关系,因此宜译为:“由于大学校园里两性关系缺乏承诺,泛滥成灾,这就降低了婚姻在女生心目中的地位。”
划分翻译单位的实质是认知经济原理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但英汉笔译中操作翻译单位时无论是主要参考时间标志还是空间标志,都涉及一个局部经济和全局经济之间的选择问题。前者体现为译文和原文在形式上亦步亦趋,后者往往表现为译文对原文结构做出较大的改变。从翻译单位的角度研究,这主要是译者在分析原文形式标志之间的时空关系时,其考察范围的大小存在差异造成的。如果译者只是集中精力考察相邻两个翻译单位之间的时空关系,此时虽然省去了考虑这部分表达和原文其他内容之间关系的麻烦,从认知上固然比较省力,但由于这样做的视野较窄,没有将个体的翻译单位纳入原文的整体表达框架中进行考察,所以可能造成译文的局部表达符合认知经济原则,但整体表达框架不符合译文语言文化习惯,甚至显得迂回曲折或臃肿庞杂,所以全局效果反而不符合经济原则。按这种方式,例1可能会译成:“一个保守的妇女组织今天将发布一份报告,其中指出:虽然大多数大学女生把婚姻当成自己的终生目标,但她们对该目标的追求被大学校园里四处泛滥的两性关系给削弱了,因为这种两性关系缺乏承诺。”这种译文采取的是顺句驱动原则,翻译时紧跟原文结构,有效地降低了单位时间内的认知负荷,让译者可以顺利完成整个翻译任务。但这只是一种不得已为之的权宜之计,因为译者在翻译时只考虑局部内容的转换,而没有把握它与全局结构之间的关系,往往造成译文整体表达不是很通顺自然。这在口译实践中可以理解,因为口译现场的时间紧迫,能否顺利完成口译任务是译者最大的考虑,所以口译的要求相对较低,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达意即可。
但笔译之中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因素,反而是鼓励译者多花时间和精力去反复研究原文结构并斟酌译文措辞,因此理想的做法是在参考原文形式标志操作翻译单位时,对形式标志的个体分析也应当体现整体观,即在原文整体结构下分析单个的形式标志所体现出的时空关系,确保这样分析还原的时空关系具有层次感,从而才能保证局部经济和全局经济的辩证统一。结合例1,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第二个“that”在整个原文逻辑中表示的是一种原因,因此宜交换(3)、(4)之间的时空位置,将整个译文表达为:“一个保守的妇女组织今天将发布一份报告,其中指出:虽然大多数大学女生仍把婚姻当成自己的终生目标,但是,由于现在的大学校园里两性关系泛滥,彼此之间缺乏承诺,这就降低了婚姻在大学女生心目中的地位。”
5. 结语
本文围绕英汉笔译实践中的一项基本操作和核心过程,即如何划分和重组翻译单位而展开讨论,认为这是认知经济原则在笔译之中的贯彻或落实,即译者是通过操作翻译单位而达到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认知转换工作。这在形式上表现为译者可以根据原文的形式标记把复杂的语言结构还原为无标记的基本结构,而这种无标记的基本结构体现了语言之间的共性,在认知上可以类比于一种物理运动,其中暗含基本的时空规律,符合人类的心理直觉和认知常识,所以在语际转换中显得轻松自然,能够有效地降低翻译难度。同时由于形式标记本身较为客观和通用,所以借助这种方式有望把以前隐蔽在译者大脑黑匣内部无法言说的心理操作外显化、固定化,从而有利于翻译经验的交流和分享,这样也就间接地提高了翻译实践中的操作规范。
参考文献
Bell, R. T. 1991.TranslationandTranslating:TheoryandPractice[M]. New York &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Catford, J. C. 1965.ALinguisticTheoryof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iman, J.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J].Language59(4): 781-819.
Jaaskelainen, R. 1993.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In S. Tirkkonen-Condit & J. Laffling (eds.).RecentTrendsinEmpiricalTranslationResearch[C]. Joensuu: Faculty of Arts. 99-120.
Lamb, S. 1998.PathwaysoftheBrain:TheNeurocognitiveBasisofLanguag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Lorscher, W. 1993. Translation process analysis [A]. In Y. Gambier & J. Tommola (eds.).TranslationandKnowledge[C].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Center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95-212.
Malmkjar, K. 1986/2004. Unit of translation [A]. In M. Baker (ed.).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86-288.
Miller, G. A. 1956.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J].PsychologicalReview(63): 81-96.
Toury, G. 1986. Monitoring discourse transfer: A test-case for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translation [A]. In J. House & S. Blum-Kulka (eds.).Interlingualand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DiscourseandCognitioninTranslationan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Studies[C].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79-94.
Zipf, G. K. 1949.HumanBehaviorandthePrincipleofLeastEffort:AnIntroductiontoHumanEcology[M]. New York: Hafiner.
陈友勋.2011.认知翻译法[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程琪龙.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耿强.2003.论翻译单位的动态生成[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118-121.
李德超.2005. TAPs翻译过程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1): 29-34.
连淑能.1993.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宓庆.2006.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陆丙甫、蔡振光.2009.组块与语言结构难度[J].世界汉语教学(1):3-16.
陆丙甫.1993.核心推导语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陆丙甫.2010.汉语的认知心理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马尔丁内.1980.语言演变的经济原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
沈家煊.1999.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石毓智.2004.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汤君. 2001.再探翻译单位[J].山东外语教学(3):38-44.
朱纯深.2008.翻译探微——语言、文本、诗学[M].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管新潮)
作者简介:陈友勋,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与翻译、翻译理论与实践。电子邮箱:youxunchen@163.com
*本文系2014年全国教育技究专项课题“信息技术与英汉笔译课程的深度融合”(编号146232118)、2014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生态翻译视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研究”(编号14SKM12)以及2016年重庆市教委高校人文社科研一般项目“一带一路新形势下重庆高校凸显职业特征的笔译教学模式研究”(编号16SKGH1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921-(2016)04-0062-05
[doi编码]10.3969/j.issn.1674-8921.2016.0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