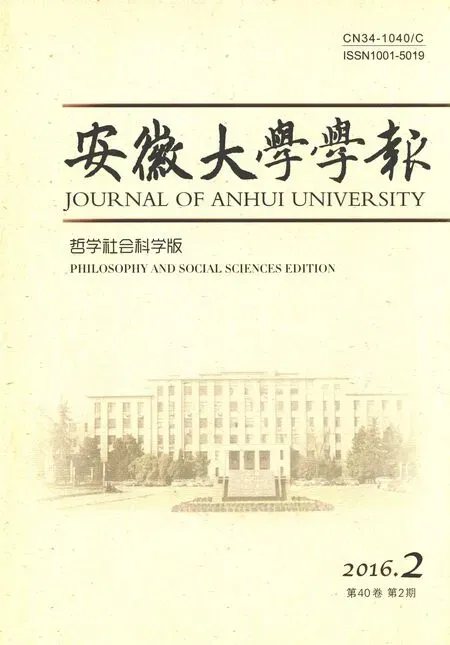汉语领属结构的领格类型
吴早生
汉语领属结构的领格类型
吴早生
摘要:从世界语言的领格类型来观察现代汉语被领者带有定/无定标记词的特殊表现,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汉语领属结构既有类似于限定性领格语言的特点,也有形容性领格语言的性质。它是一种类形容性领格特点的限定性领格语言,这一表现可能与汉语量词的描摹功能密切相关。
关键词:领属结构;领格类型;限定性领格语言;形容性领格语言
Lyons认为世界语言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领格类型,一种是限定性领格语言(determiner-genitive language),另一种是形容性领格语言(adjectival-genitive language)。前者简称为DG语言,如英语、爱尔兰语等;后者简称为AG语言,如意大利语、希腊语等。Lyons还具体讨论了两者的差别:
第一,两种领格语言的领属语在结构内占据位置不同。DG语言中,一般不出现定冠词和其他限定词,而由领属语占据该位置;而AG语言中,限定词与领属语共现,领属语处于形容词或其他非限定位置。这是两种领格语言的本质差别。
限定性领格语言(DG),如爱尔兰语:mo/do hata(我的帽子)hata an fhir(那个人的帽子)
my hat(my hat)hat the+GEN man+GEN(the man’s hat)
*an mo/do hata(我的帽子)*an hata an fhir(那个人的帽子)
the my hat(*the my hat)the hat the+GEN man+GEN(*the[the man]’s hat)
形容性领格语言(AG),如意大利语:it mio itbro(我的那本书)un mio libro(我的一本书)
the my book(my book)a my book(a book of mine)
第二,正因为DG语言Det位置特征,我们可以通过领属结构推导出整个名词短语的定指性;而AG语言没有这一领属语占据Det位置特征,因而领属结构不能推导出整个名词短语的定指性,而是通过定冠词、限定词推导整个名词短语的限定性。
最后,Lyons还指出了领属语位置特征与定指性的关系:“限定性领格结构是领属语位于Det位置的结果,而不是其他相关原因。”*Lyons Christopher, Definitenes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2-26.
Catherine Macdonald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有些冠词和领有者兼容的语言,还会表现出有无移情的形式差别。如Tongan语中,a、c跟b、d的差别是定冠词与不定冠词的差别,而a、b跟c、d的差别是有无主观移情的差别*Catherine Macdonald (U. Toronto), A Hierarchical Feature Geometry of the Tongan Possessive Paradigm, The 3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p.71.。a.he’ekn heleb.ha’sku hele
DEF.SUBJ.1EX.SG knifeINDEF.SUBJ.1EX.SG knife
“the-my knife(the knife which is mine)”“a-my knife(a knife which is mine)”
c.si’eku hele d.si’akn hele
DIM.DEF.SUBJ.1EX.SG knifeDIM.INDEF.SUBJ.1EX.SG knife
“the-my little knife”“a-my little knife”
刘丹青认为,汉语属于Lyons所说的形容性领格语言,其依据是:汉语的领属结构虽然在语用上容易“理解为有定,实际上没有固定的指称属性,可以通过限定词决定其指称,如有定(我那本书丢了)、无定(我的一本书丟了)和类指(我的书很多)”*刘丹青:《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中国语文》2008年第1期。。
但是我们发现,汉语中通过限定词决定指称的现象极为有限。根据吴早生统计,汉语被领者上很少出现领有者以外的有定/无定限定词(这里是指相对几率,虽然绝对几率看似不少*吴早生:《现代汉语光杆被领者的指称性质》,《语文研究》2012年第1期。。后文把这种不受有定/无定限定词“一/这/那”修饰的被领者,简称为“光杆被领者”),此为其一。汉语中被领者上的很多所谓的限定词并非是用于限定,而是有着其他的语用意义,此其二*吴早生:《主观非数量评价性的“NP1的一量NP2”》,《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1期;张伯江、吴早生:《释汉语“指·量短语”的两种意义——兼论定冠词问题》,《现代中国语研究》,东京:朝日出版社,2012年总第14期,第70~79页。。即使是可以决定领属结构指称性质的那部分有定/无定标记词,也不完全符合Lyons的形容性领格语言的判定标准,因为汉语的领有者往往要求强制性地居于其他限定词之首。
一、汉语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形容性领格语言
汉语领属结构的表现较为特殊,似乎与DG和AG语言都有相似的地方。到底汉语属于DG还是AG语言成了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汉语领有成分和限定词的表现情况如下:汉语中的领属成分,既有类似于意大利语、古希腊语的方面,即,领有成分不借助于介词就可以跟领有者之外的某些限定词(指示词和“一+量”)同现,如:
(1)我的一本书
我的这本书
我的那本书
也有类似于爱尔兰语和英语的方面,领有成分可以不跟领有者之外的某些限定词(“那/这/一+量”)共现,如:
(2)我的书我的数学书
他的车他的宝马车
上文已经指出了前人的统计结果:汉语非光杆被领者虽然绝对数量不少,但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光杆被领者。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汉语领属结构表示不定指意义一定是有标记的:一是如果处于叙述主线的环节,汉语被领者要受到无定标记词的修饰(有标记)才能表达不定指意义;二是处于非叙述主线环节(有标记),光杆被领者也有表示不定指意义的可能。
如果处于叙述主线中的领属结构,其被领者没有无定标记修饰,一般表示定指语义。这一点是跟Lyons(1999)DG语言定义的第二条相吻合的:正因为DG语言Det位置特征,我们可以通过领属结构推导出整个名词短语的定指性。例如:
(3)a. 你的书呢?b. 哦,我的书(≠*我的一本书)落在教室里了。
如果缺少“处于叙述的主线的环节”这个条件,也就是说处于偶现新信息环节,就有可能出现光杆被领者领属结构表示不定指的现象。如下面的例子就可以省略无定标记词而不影响基本语义。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整个领属结构不是处于叙述性的线索当中,它们对听话人来说都是不重要的信息,没有必要说得那么清楚,因而这时的无定标记可以省去而不影响交际,甚至整个被领者直至偶现结构都可以替换为模糊性词语或省略而不影响交际。例如:
(4)A:你干啥去?B:去教室,我的一本书(≈我的书/我的东西)落在教室里了。
总结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当被领者无标记时(不受有定/无定标记词修饰且处于叙述主线),汉语领属结构一般理解为定指的指称意义,当然,受到有定标记修饰仍理解为定指;只有当被领者处于有标记状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或者受到无定标记修饰,或者不受有定/无定标记词修饰但处于非叙述主线中,或者兼而有之)汉语领属结构才有可能理解为不定指的指称意义。下面我们将通过领属结构限定成分的语序位置和限定性概念来具体讨论和判别“被领者带限定词‘一/这/那+量’的汉语领属结构”的限定性类型。
(一)汉语被领者上“一/这/那+量”的限定性判定之一——是否居首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汉语被领者带有定/无定标记词的领属结构,其有定/无定标记词所处的位置,绝大部分都是位于领有者之后的非居首位置(即:领有者+一/这/那+量词+被领者)。据我们的统计,占据这一位置的倾向性达到了96%。例如:
(5)我又收到了他的一/这/那封信,“我在船上,……我那么难以遏制对你的思念。”
(6)那年,乌尔班前往南非拜访他的一/这/那位笔友。
而“一+量+[领+被领]”,使用频率极低,是“领有者+一+量+被领者”的4%:
(7)1955年的元月,我突然收到一/这/那封他的来信。
(8)牧羊人递给我一支他的烟。
有些看似“一/这/那+量+领有者+被领者”构成的结构,但其中所谓的“领”已经不是领有者了,而是表示性质特点,其作为领有者的特点已经接近于零:
(9)她虽然是个农民,却有着一/这/那双艺术家的手。
(10)我看见了一/这/那辆女人的汽车。
从我们统计的结果来看,修饰被领者的“一/这/那+量”中,有高达96%的用例都不处于Lyons所定义的AG语言位置。如果“一/这/那+量”是冠词的话(冠词的限定性很强),应该位于领有者之前,即限定词det的位置。
但恰恰相反,绝大部分情况下,汉语领有者占据了定冠词或其他限定词应该占据的最外围的位置。也就是说,尽管汉语类似限定词的“一/这/那+量”,有时可以与领有者共现,但它很少占据最外围的位置。而Hawkins指出,“指别词、数词、形容词分别出现在核心名词两端的共性:任何情况下,不可能形容词前置于核心名词而指别词或数词却反而后置于名词”*J. A. Hawkins, Word Order Universa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pp.119-120.。Greenberg认为“当指别词、数词、描写性形容词中两个以上前置于名词之前时,它们总是以这种语序(指别词—数词—描写性形容词)出现。如果它们是后置,语序则依旧,或者完全相反”*J. H. Greenberg,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Universal of Language (2nd ed), London: MIT Press, 1966, pp.73-113.。据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汉语的居首位置才是限定性最强的位置(指别词位置),才应该属于限定词det位置。据此我们推断:汉语的“一/这/那+量”的限定性要弱于居首的领有者,即汉语居首领有者才是领属结构的最强限定词。
也就是说,刘丹青把汉语定位为AG语言似乎不完全符合Lyons所定义的AG语言的位置特征,也不完全符合Hawkins和Greenberg的人类语言语序共性特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
即便那些有定/无定标记处于居首位置的极少数反例,也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而不完全是被领者造成的居首。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弱化了语音的独用“一/这/那”和独用“量词”(即不是“一/这/那”和“量词”的组合),与“一/这/那+量”的使用差别,来说明这一点。
从语法化的角度来说,独用的“一/这/那”语法化程度更高,其限定性这一语法功能应该要比“一/这/那+量”强,按理说更有机会进入领有者之前的限定词位置,但是,从实际的语料来看,很少出现“一/这/那+领有者+被领者”的例子。也就是说,汉语的“一/这/那”还未虚化到可以随意进入冠词、限定词位置的程度。例如,“一/这/那+量”可以进入的(11a)(12a),其独用的“一/这/那”却不能进入同样的位置,如(11b)(12b)。应该说(11a)(12b)中“一/这/那+量”并非是由于强限定性造成居首的,可能还有外在的其他原因(如,宾语位置的要求,而非居首要求等)。
(11)a.1955年的元月,我突然收到一封他的来信。
b.*1955年的元月,我突然收到一他的来信。
(12)a.牧羊人递给我一包他的烟。
b.*牧羊人递给我一他的烟。
同样,独用“量词”一般也不易用于(11b)(12b)中相应位置上,如(11′)(12′)。这进一步证明了这里的“一+量”不是领属结构上的强限定词,可能还有外在的其他原因(宾语位置,特别是直接宾语的位置要求,而非居首的要求等)。
(11′)?1955年的元月,我突然收到封他的来信。
(12′)*牧羊人递给我支他的烟。
(二)汉语被领者上“一/这/那+量”的限定性判定之二——是否限制性
除了从居首位置可以判断汉语领属结构的限定性,我们还可以从“一/这/那+量”的限制/描写性角度做出直接的判断。
陈玉洁对限制性与非限制性做出了如下的定义:“限制性与非限制性是修饰语在具体运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语用功能,如果修饰语是对指称有贡献的成分,是必有信息,去掉影响所指的范围,它就是限制性的,如果它对指称没有贡献,是可有信息,去掉之后,不影响所指范围,它就是非限制性的。”*陈玉洁:《指示词的类型学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7年,第119~122页。他同时指出,汉语中不存在语法手段标记的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的对立,并制定了汉语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的判定标准:第一,是否能够省略:如果修饰语成分能够省略而不损害句子意义,那么它是非限制性的,如果不能省略,就是限制性的,非限制性的句子只是增加了一些有用的或有趣的信息,但对于句子的意义来说并非是必需的,不影响NP的指称范围。第二,限制性限定了它所修饰的核心的范围。通过比较“核心”与“修饰语+核心”之间指称范围的大小,可以做出有无限制性的判断。如果“修饰语+核心”指称范围小于“核心”,则为限制性的;如果所指范围相等,则是非限制性的(一般不存在“修饰语+核心”指称范围大于“核心”的情况)。
陈玉洁的这一定义与判定标准虽然主要是用来判定关系从句的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的,但同样适用于判断其他修饰语的限制性。
(13)我读过他的(一本)书。
(14)他的(这/那本)书很难懂。
这两句话中被领者上的“一/这/那(+量词)”一般不能省略,如果省略以后,就会影响指称的范围。例(13)省略前表示指称范围限于“一本”,而省略后,数量是不确定的,可能是一本,也可能是两本或很多本。例(14)省略前表示听说双方共知的那本书很难懂,而省略后表示他所有的书都难懂,而且核心(他的书)与“修饰语+核心”(他的那本书)之间构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而,我们判定:这里的“一/这/那(+量词)”具有限制性。
这是就单个句子而言,如果在语篇中(14)例的“这/那本”往往也是可以省略的,因为一般都有语境信息可以补足所指,这时的“这/那”从指称角度说,已经是不必要的了,因而也是非限制性的。
还有那些唯一性指称或整体唯一性指称的领属结构被领者上的“一/那/这”,也完全可以省略。例如:
(15)他的(一/那/这张)嘴从来就没绕过人。
该例中的被领者上的“一/这/那(+量词)”完全可以省略,省略以后,不会影响指称的范围,即省略“一/这/那(+量词)”前后,其指称都不会发生变化。因而,我们判定:这里的“一/这/那(+量词)”属于非限制性的修饰语。
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具有限制性作用的修饰语,我们才可以说它们具有不/定指性,才有可能成为不/定指性的标记;而非限制性的条件,主要是具有描写性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例(15)、篇章语境中的例(13—14),其领属结构的所谓不/定指性标记都是纯描写性的,表达的是描写性语用意义。
下面我们再来看汉语领有者的强限制性,因为同样的省略测试,用在领有者上语句则是不通顺的。例如:
(16)(他的)*一/这/那张嘴从来就没绕过人。
这就容易明白:为什么Lyons所说的形容性领格语言,有定/无定标记词都是前置于领有者的。汉语不是前置于领有者,至少可以让我们明白,在这一类例子中,汉语的有定/无定标记词“一/这/那(+量词)”还是具有很强的描写性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汉语被领者上限制性的“一/这/那+量词”,其描写性的功能也还很强大,还没有完全虚化到冠词的作用,还具有一定的描写性,因而以置于领有者之后为常,而不是相反,这也就完全符合Hawkins(1983)和Greenberg(共性二十)了,同样也就符合DG语言的特点了。因此,把汉语称为“类形容性领格(AG)的限定性领格语言(DG)”,也许更为贴切一些。
二、汉语领格类型探因
“一/这/那(+量词)”的描写性与汉语量词的大量使用有很大的关系。即使在吞并量词的“一”*刘祥柏:《北京话“一+名”结构分析》,《中国语文》2004第1期;董秀芳:《北京话名词短语前阳平“一”的语法化倾向》,吴福祥、洪波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6~180页; 吴永焕:《北京话“一个”弱化的原因》,《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当中,不能不说还有量词的影子在起作用。从现有的关于汉语量词的研究成果来看,汉语量词除了具有个体化功能外,还具有很强的描写性。
(一)汉语量词的个体化功能
汉语中的量词“个”能够起到个体化和实体化作用,相当于其他语言中不定冠词的功能。例如:
(17)你们这儿有老师吗?
(18)你们这儿有个老师吗?
大河内案宪认为,上面例子的场景是:到公寓拜访一位老师,如果问话人意识中已经有了特定的人,这个人是从事教师工作的,这时容易说后面一句而不是前面一句。而后一句适合于按照名单调查附近是否有从事教师工作的人,而对于这个人是谁毫不过问,它不适用对问话人已经知道的特定的那个老师进行提问。他认为“量词的个体化功能体现于此”,因为用上“一个”容易在脑子里浮现语境中的那个人物*大河内案宪:《量词的个体化功能》,《汉语学习》1988年第6期。。
奥田宽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你们还算得上一个模范学生吗?”,认为加上“一个”后,人们明显地感觉到脑子里有一个具体学生的形象,而跟数没有关系*奥田宽:《说“一个”》,《中国语学》1982年229号,第57~61页。。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汉语的量词具有个体化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是以形象的联想作为个体化的主要手段的。也就是说汉语量词的个体化功能是与汉语量词的描写性密切相关的。这可能与汉语重视意象有关。
(二)汉语量词的描写性
汉语量词跟事物的维度密切相关,不同的量词表示不同的维度,具有很强的形容性和描写性。石毓智认为:“表二维概念的名词只能用‘条’或‘张’等修饰,三维概念的名词则只能用‘根’‘片’‘块’等修饰。”他并指出:“对二位概念来说,‘宽维’和‘长维’的比值趋于1时,用‘张’,‘宽维’和‘长维’的比值趋于0时,用‘条’。”*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页。这实际上就是刻画了量词对事物不同形状的描述。当说出名量词还未说出中心语时,我们已经基本上能够判断出该中心语的大致形状或特点了。
有时这种描写还会加入人们的主观评价意义。例如我们称“一伙人”“一帮人”“一堆人”,这些量词本身表现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其描写性要比“条”“根”等更强。例如:
(19)正待他得意之时,刚抬脚想溜之大吉,抬头猛见一员大将横刀立马档在桥头,他那刚刚紧把起来的筋骨一下便瘫软下来。
上例中的“员”一般用于人的计量,这里的“员”用于“大将”,说明人们对武艺高强的人的一种赞许,具有很强的描写性和主观色彩。
一些文学作品更是充分利用量词的这种描写功能,使文章更加形象生动,例如“一弯新月”“一轮明月”“一丝希望”“一缕青丝”等。何杰认为:“汉语量词具有格调色彩。格调色彩有不同的类别,这些量词的不同格调是由于适应不同的语境而形成的,相反它又以不同的格调色彩在创造不同语体风格中起了重要作用。”*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例如:
(20)仰望细雨划过的天空,总能发现飘着闲散白云的蓝天,还是穿射出一丝阳光。
例句(20)中的“一丝”,准确而又细腻地表现了作者对阳光的期望,对人生积极的态度,用一丝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表现力。
从上述两个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汉语的量词本身就具有描写性和限定性两个方面的功能。当名词短语本身的限定性在没有量词就已经达到交际要求时,这时的量词主要是用于描写的,反之是用于限定的,当然在限定中还不乏描写性,这正如形容词的双重功能。关于形容词的双重功能,我们以下面两个例子来说明:
(21)勤劳聪明的中国人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中国人(非限制性)
(22)只有勤劳聪明的中国人才会有所作为。≠中国人(限制性)
前者没有形容词“勤劳聪明”就已经可以达到交际的基本要求,因而“勤劳聪明”是描写性的;而后者没有形容词“勤劳聪明”却不能达到交际的基本要求,因而具有限制性,而这种限制性的形容词仍具有描写性特征。
(三)“一(量)+[领有者+被领者]”中领有者限定性/描写性测试
汉语中“一/这/那+(量)+[领有者+被领者]”,其中的“一/这/那+量”的限定性明显强于领有者(“一量”吞并量词后的独用“一”更是如此),因为这里的所谓领有者已经带有很强的形容性、描写性了,领属结构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属结构了。如上面例(9)中的 “艺术家”只是表明了一种身份,是无所指的成分,不再充当真正的领有者了。也许这种结构才是Lyons真正意义上的形容性领格结构。
一个很好的测试,便是将“一/这/那+(量)+[领有者+被领者]”中所谓的领有者更换为限定性很强的代词或专有名词时,便不能成立。例如:
(23)*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小王/他的播客
(24)*两人抛接床边脱落的铁护栏玩,结果一/这/那(根)小王/他的手筋被划断了。
(25)*我买了一/这/那(辆)小王/他的摩托车,他的发票和购车手续都丢了……
(26)*一/这/那(个)小王/他的鬼把戏被我揭穿。
(27)*公布一/这/那个小王/他的电话。
有些大众人物作为领有者时,似乎可以出现上面例子中的格式,这时的领有者实际上弱化了专有名词的特点,而是表示某种风格特点,表示的是属性义,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领有者了(犹如“一双艺术家的手”中的“艺术家”)。例如下面两例中的刘德华和琼瑶,主要让人联想到的是刘德华的歌的风格特点和琼瑶小说的风格特点(与张伯江交流)。
(28)A.昨天晚上,你唱了首什么歌?
B.一/这/那(首)刘德华的歌,歌名是《假装》。
(29)A.最近,你看了本什么小说,这么入迷。
B.一/这/那(本)琼瑶的小说。
这两句话中的专名一般也不能换成代词,下面换成代词后,仍然是不自然的,如果量词被吞并,使用独用的“一”则是完全不成立的。例如:
(30)A.昨天晚上,你唱了首什么歌?
B.*我最近迷上了刘德华的歌,我唱了一/这/那(首)他的歌,歌名是《假装》。
(31)A.最近,你看了本什么小说,这么入迷。
B.*我最近迷上了琼瑶的小说,我看了一/这/那(本)她的小说。
由此可以推测,有些领属结构,领有者前的“一/这/那+(量)”,当不能理解为修饰领有者时,其所谓领有者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有者了,而是表示形容性的、描写性的成分了。也就是说,真正典型的领有者前面带有被领者的“一/这/那+(量)”,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或者是不合法的,或者是领有者的修饰语而非被领者的修饰语。
三、结语
现代汉语被领者上的无定/有定标记词“一/这/那+量”实际上还是以描写性的功能为主,因而一般仍然位于领属限定词之后,但仍然属于限定性领格语言。
只有在那些限定词位于领有者之前的结构才表现出形容性领格语言的特点,但这种用法在汉语中是极为有限的,而且是受到非常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甚至这时的汉语名词短语已经不能称为领属结构了,当然也就谈不上是哪类领格语言。
现代汉语中,与领有者共现的,特别是非居首的“一/这/那+量”表现出了很强的描写性,甚至可以用于专门表现说话人的主观评价和态度(主要出现在领属结构已经是唯一所指或所指范围很小的情况下,或者是领属结构的限定性已由篇章语境确定的情况下),因此汉语领属结构是类形容性领格的限定性领格结构。
WU Zaosheng, Ph. D. and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责任编校:徐玲英
The Genitive Types of Possessive Structure
WU Zaosheng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ecial performance of possessum with definite/indefinite determiner in Chines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world’s languages. It is found out that possessive structur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corresponding to determiner-genitive language(DG) as well as to adjective-genitive language(AG). In other words, it is of DG with some characteristics corresponding to AG,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descriptive function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Key Words:possessive structure; genitive types; determiner-genitive language; adjective-genitive language
作者简介:吴早生,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安徽 合肥230601)。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2-0099-07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