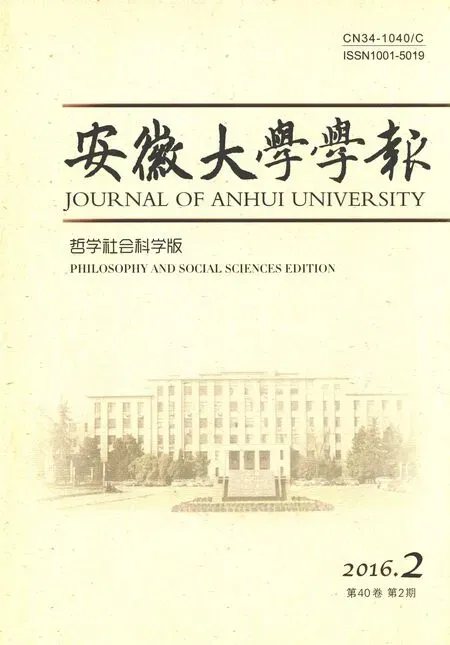《文章源流》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文体学研究
刘春现
《文章源流》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文体学研究
刘春现
摘要:高步瀛的《文章源流》是一部效仿《文心雕龙》而作的文体学著作。此书不仅吸收了自挚虞、刘勰、吴讷、徐师曾、姚鼐、曾国藩等以来的文体学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新变。将曾氏三门十一类的文体类别,变更为“论议门” “记载门” “词章门”涵盖下的十六类文体。其中,传注类文体的独立,显示出独到的文体视角。在具体的文体阐释中,融合了传统的“序题”“序目”形式,构建出新的解说方式。体例上,注疏、考证与批评兼备的著述方式亦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清末民国新的时代与学术思潮下,此书对古文文体的研究极具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高步瀛;《文章源流》;文体分类;传注体;文体阐释
目前学界对高步瀛的相关研究仍停留在对其身世、交游、著述的考辨上*如赵成杰《高步瀛交游新证》,《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2期;《高步瀛著述考略》,《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7期。其他如马菲《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诠释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郑凯歌:《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研究》,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聚焦于其所著《文选李注义疏》《古文辞类纂笺证》之上,而对《文章源流》这部异常重要的文体学论著缺乏足够的关注。在高氏的传记、事略、评传、年谱等研究中*参见姚渔湘《高步瀛的思想与著作》、董璠《高步瀛先生(1873—1940)事略》,见《大陆杂志语文丛书》,第一辑第4册,第232~234页,台湾:大陆杂志社,1963年。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高步瀛先生评传》,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81~296页。尚秉和:《高阆仙先生传》,《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69~770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此书或未被提及,或一带而过,只有零星的论述散见于关于民国讲义或者文学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之中。
《文章源流》是高步瀛讲学北平师范大学、莲池书院期间的讲义。据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记载:“先生论文,无骈、散,应先辨体。韩退之直追迁、固,而文体多所破。述文章流变体制正讹,为文章流别新论上下两卷。”*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董璠《高步瀛先生(1873—1940)事略》亦载“《文章流别新论》二卷”*案:董璠,1917年左右就读高等师范学校,程金造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据此,此书大概著于1917年左右。参见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董璠》 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4页;汝信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程金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程文作于高氏逝世后第二年,董文亦载于当时报刊,二人所言《文章流别新论》应是此书本名,后来研究者所说《文章源流》或为高氏于莲池书院讲学期
间所改定后的版本(1928年以后)*案:《文章源流》有北平和平印书局铅印《莲池书院讲义》本、民国北平师范大学铅印本。北平师范大学铅印本书名为《散文源流》,稍后的《莲池书院讲义》本,改名为《文章源流》。此书虽包含骈文词赋,但并未涉及诗歌、词体、小说、戏曲等文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此书原名较贴切。 尚秉和先生说此书“为时势所限,未能终篇” ,或许可以推测,书名的改定乃由于计划扩大文章论述范围亦未可知,惜乎其未能终篇也。《莲池书院讲义》本不但在体例上增加了引文出处和原文,而且内容上增多两节——《作文之要义》《本讲义之门类》,使本书体例更为完善,内容亦较丰富。。与《文选李注义疏》及《古文辞类纂笺证》一样,本书在体例上表现出鲜明的特色,“贯串古今,穷原竟委。其注解在形式上虽附于某篇某句之下,实则是独立的一首考证文字”*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
本文拟就这部久被忽视的文体学专著加以分析,对其编写体例、文体论特色、影响以及局限性进行研究,以进一步观察清末民国时期学术界的文章与文体学观念。
一 、《文章源流》文体分类学上的创新
总集以及选本作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学观念的载体,具有重要的价值。继《文选》以来,后代综合性的文章总集及大部分选本,延续了“以体叙次”编选体例,《文选》分文体为赋、诗、骚、七、诏、册、令三十九种。《唐文粹》只选古体,分“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表传录、述序”*姚铉:《唐文粹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文鉴》录北宋一代诗文,分为六十一体。宋人真德秀《文章正宗》概括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启发后代“以类编次”的思路。清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将八大家古文分为六类三十体;姚鼐《古文辞类纂》分为十三类;曾国藩分为三门十一类: “著述门”(三类)、告语门(四类)、记载门(四类)。可以看出,古代文体分类学的“分类与归类”特征*参见吴承学、何诗海《文章总集与文体学研究》,《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4期;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第四章《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高氏批评《文选》中“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者也”,《文苑英华》“各类之中分目甚繁”,《唐文粹》《宋文鉴》“失于烦琐”,《文章正宗》“有纲无目,又失之广莫”,储欣《八大家类选》“纲目悉张……但限于唐宋八家”,《古文辞类纂》“有目无纲”,《经史百家杂钞》标列门类“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然著述、告语范围太廓,分界为难;而以词赋入著述门,尤多龃龉;其记载门增入叙记、典志二类,则曾氏之卓识,超越前人矣”*以上引文均见高步瀛《文章源流》,《历代诗话续编》本,第1354页。本文所引高氏论述,皆出于此,仅在文中标明页码,不另注。。其论述源流、利病堪称明辩中肯。在斟酌诸家之后,高氏提出将文体析为十六类,以“论理”“记载”“词章”三门总括:
论议门(七类):论辨类 、传注类、序跋类、赠序类、诏令类、奏议类、书说类。
记载门(四类):传状类、碑志类、叙记类、典志类。
词章门(五类):词赋类、箴铭类、颂赞类、哀祭类、诗词类。
其文体分类明显地以文体内在的体性来划分。如论议门中包括“论辩类”“传注类”“序跋类”“赠序类”“诏令类”“奏议类”“书说类”,涵盖了曾氏列为“告语门”中的诏令、奏议、书牍,“著述门”中的序跋;替换了曾氏“著述”“告语”之间的混合模糊地带,文类显得更为清晰明确。与储欣将奏疏、序记、论著*储欣评:《唐宋八大家类选》,见《古文选七种》,清光绪九年(1883)版。各自为类相比,亦更具概括力。记载门延续曾国藩的思想,增加“叙记”“典志”,可见高步瀛对文章经世作用的重视。又,词章门的单独归类,既是对储欣分类法的继承,也可见其对文学性质的准确体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书尚未全部完书,其词章门中虽有“诗词”类,然书中并未有此部分内容。但是相较储氏、姚氏、曾氏书来说,“诗歌”类入目,词章门的独立,使其体系更为全面完善。
传注文独立为一个文类,是一大亮点。晚清至民国,朴学研究重心由经学转而为诸子,再转为集部,包括诗文评、总集、别集。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为代表的诗文评研究的兴起,为当时的学术研究开启新的范式。黄侃弟子李曰刚云:“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则不外校勘、评解二途……”*转引自牟世金《“龙学”70年概观》,饶芃子编《文心雕龙研究荟萃》,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19~20页。“突破以笺注、评点为主的传统读经之法,综合“选学”派重视文采和朴学派注重考据的因子,开创‘龙学’界文字校勘、资料笺证、理论阐释三结合的研究新法”*贺根民:《〈文心雕龙札记〉——古代文论研究现代转型的一个典型文本》,《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此种融汇文字校勘、笺证、理论阐释的研究范式,实则以经学之方法移用于集部研究,一时成为热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校教师教授古典著作,往往以“讲疏”命名。如黄侃《诗品讲疏》、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顾实有《〈汉书·艺文志〉讲疏》《〈庄子·天下篇〉讲疏》等,均可归属于此类型的研究。。
高氏正是此种研究范式的典型代表,其所著历朝文举要、《古文辞类纂笺证》等,正是将校勘、笺证、理论阐释结合以研究集部文学。实际上,《文章源流》的部分内容来源于其《古文辞类纂笺证》一书中。 “传注类”的独立为类,正是这一特定学术思潮与其研究方法契合的产物。曾氏《经史百家杂钞》中将传、注、笺、疏、说、解等文体,归入序跋类,对注疏类文体,开始关注。王葆心《古文辞通义》著述门下有“传注”类,曰:“他人之著作,疏其词义,溯其源委”,列经类29体*王葆心编撰,熊礼汇标点:《古文辞通义》“古文门类各家目次异同比较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8页。29体分别是“通、故、微、注、疏、笺、解、集解、释考、章句、论说、问难、辨疑、讲义、外传、衍义、类例、表谱、图、音、考正、名物、篇、章、序、解、七纬、逸经、拟经”等。。高氏于“传注”下题解:
传注类者,其源出于《十翼》之释《易》,左氏、公、谷、邹、夹五家之释《春秋》,历代相沿,其用益广。萌芽于经,旋及子、史,而后施于集焉。王仲任(充)曰:“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世儒当世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论衡·书解篇》)盖以文章、传注判而为二,与后世以为经学、古文不能合为一途者,同一见解。故古来选文者,皆不设传注一类。然以广义言之,传注者亦文章之一体,安得置之不论?且即以文论,《春秋三传》已为文家所则效;而王辅嗣(弼)之注《易》、郭子玄(象)之注《庄》,亦往往驰骋其辞,发抒其论;郦善长(道元)之《水经注》,模山范水,后世文人为游记者,有时摹仿而叹弗及焉。夫文家虽不设传注一类,而曾氏《杂钞》于序跋类数之,曰传、曰注、曰笺、曰疏、曰说、曰解,已开文家之门户,而径纳之矣。窃谓此等类目,不数则已,如数之,实非序跋类所能该,必别建一类而后安。王氏《古文辞通义》因就曾氏著述门中加入此类,用意甚善;然举目太烦,仍不能备;而七、纬、拟经亦入此类,似嫌蛇足。今括以十目:曰传、曰记、曰说、曰解、曰注、曰笺、曰疏、曰议、曰考、曰校。(1372页)
传注原为解经方法,后施用于子、集,是中国古代文章中比较独特而重要的体裁。但作为一种经学体裁,此前的古文选本多不注目于此,曾氏实有先见之明,高氏则更为明确、自觉。所分十类,大致涵盖了传统的训诂章句之学。
有清以来考据、词章、经济泾渭分明,古文、经学异途的历史背景下,高氏将考据类学术文章纳入文学范畴,可谓独具胆识。据程金造记载:“先生注疏,多属诗文。或谓何不诂经?先生曰:‘吾国自清代乾、嘉而后,搜采经、传遗文,补苴古训,鲜有余遗。今学者致力,约有二端,或本诸家已就之书,从而萃辑,如长沙王氏《两汉书补注》《集解》者,此将风行,亦省日力。至如李善之《文选》,王逸之《楚辞》,皆视若经子引申、评注,俾成大观,是则应为倡导者也。’”*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可见,自清代以来,朴学重视经、子的学术趋向发生转移,开始对此前略受冷落的集部著作发生兴趣,高氏则表现出这种学术思潮转移的自觉性。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具有复杂性,在“体”与“用”之间,常常有所变化。正如黄侃所说:“详夫文体多名,难可拘滞,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6页。其深层原因,即刘勰在《通变》篇所言:“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也?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19页。正所谓“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初编》,第189页。。古代文体的“辨体”与“破体”总是相伴相随,相反相成*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第六章《辨体与破体》。。往往一体有多名,或者名同而体异的现象。
以“书”体为例,宋人题跋类文章,有直接名为“书某”的,如林希《书郑玄传》;有策书、制书、玺书,以及上书等朝廷文书;更多的是往还书信类文章。吴讷《文章辨体》有“书”体,曰:“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于北山、罗根泽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0页。意识到“书”有臣僚上书之“书”,以及用于朋友往还之书信。徐师曾细分为“上书” “书记”(包括书、奏记、启、简、状、疏)、“书”(121、128、138页)。姚鼐《古文辞类纂》中,分“上书”(属奏议类)、“书说类”(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姚鼐:《古文辞类纂》,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6、8页。。曾国藩沿袭姚氏,有“书”(属告语门奏议类)、“书”(书牍类)。高氏按照文体的不同功用,“书”体分别见于“序跋类” “诏令类” “奏议类” “书说类”中。古代文体命名,多源于功用。不同的身份 、地位使用的文体名称亦有区分。而且古代文体自身具备延展性,可灵活变化,以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如“解”,于经传中,相当于注、释,于文章中相当于论、辨。高氏将“解”分别隶属于论辩类、传注类、奏议类。如此区分,势必造成文体类目的数量增多,同一名称的文体出现在不同的门类之中。但站在对古代文体整理、研究的视角来看,在纲目清晰的前提下,辨析细致入微,契合中国古代文体的特殊性要求。
名同而体异的现象,即文章名为某体,实则以别的文体做成,造成体裁与文章名称不符。如墓志本以叙述墓主生平、爵里、亲族、行治等,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则以小说体做成。记体,本以叙事,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则用铺陈的手法抒情言志,此乃“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体做法。高氏对此类现象加以仔细分辨。如“箴”体,曰:
他如韩退之《守戒》,当属论辩;柳子厚《三戒》当属叙记;至于曹大家《七诫》、郑康成《戒子书》、王子渊《酒训》,当属诏令。选文者或入铭箴类,则昧于文之体制矣。(1586页)
这种细致的文体辨正,正源于对文体本身体性的明了与尊重。
高氏在文体辨析中,还涉及当世通行文体。如 “诏令类”题解,叙述历代沿革之大略后,接着说:
民国既建,制诰概无所用,而下行之文:一曰令,公布法律条例,或其他法规预算、任免官员,及有所指挥时用之;二曰训令,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有所谕饬或差委时用之;三曰指令,上级机关对于所属下级机关,因呈请而有所指示时用之;四曰布告,宣布事件或有所劝诫时用之;五曰任命状,任命官员时用之;(民国十七年六月颁行《公文程式条例》。)又官署对于人民之请求,或驳或准,则有批示,皆下行所用者也。(1424页)
可见其文体研究不仅着眼于古代,亦立足于当今。对古老文体在当下的存废加以说明。如曰:“民国既建,上行公文,惟有呈而已。”(1442页)“民国既建,谕之名遂不复见矣”,“至官署对人民陈请,或准或驳,则有批示,亦省曰批,至今用之”( 1431页)。 文体论述亦侧重于当时行用文体,“今国体既更,则所谓哀策者,仅成历史上之陈迹,故于哀辞后类及之,不复列其目焉”( 1602页)。对某些新出现的文体,考察其历史上的渊源,如曰:“民国以后,官吏莅任皆有宣誓,考之于古,韦殷卿《誓文》,颇能相合。”(1607页)考虑到“现行文书体式,自有专书”,因此高氏只是简略言之。但相比此前文体著作而言,不仅限于对昔日旧文体的追溯,对民国时所用文体的关注,显得更为全面。
二、新的文体阐释方式
自《文心雕龙》以来,后代文体阐释多延续“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要终,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序志》,第725页。的思路。明代作为文体辨析的一次高潮,“序题”成为新的形式,如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等,简略的文体叙述,“假文以辨体”的形式,对其后的文体著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第八章第二节“序题:一种流行的批评方式”。。《古文辞类纂》在序言之后,目录之前,对于十三类文体均有一段“序目”*参见吴承学、何诗海《〈古文辞类纂〉编纂体例之文体学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直接叙述一类文体的渊源,因其是文选性质,标明选文缘由,对选目作一简单说明,其重心在于文章。
高氏在已有的文体辨析范式基础之上,融合“序题” “序目”两种形式,对文体研究范畴做了大量扩充。不仅每种文类有概论,类目下二级文体论述更为细致,兼及相似文体间辨析。取其“论”以做比较。先引《释名》释“论”,引《文心雕龙·论说》,加案语曰:
《论语》之外诸子,以论名篇者,《庄子》有《齐物论》,《吕氏春秋》有《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六论,凡三十六篇;《荀子》亦有《礼论》《乐论》等篇。而桓君山(谭)之《新论》、王仲任之《论衡》、王节信之《潜夫论》、徐伟长之《中论》等,且以名其书矣。惟贾子《过秦》本无“论”字,而《吴志·阚泽传》始目为论,左太冲《咏史诗》因之,《昭明文选》遂题为《过秦论》矣。
论虽一体,析言则繁。西汉之论《石渠》,东京之论《白虎》,王子雍(肃)之《圣证》,此属于经论者也。曹子建(植)之论汉二祖,张世伟之论魏武帝、刘玄德,夏侯太初之论乐毅,何平叔之论白起,此属于史论者也。裴逸民之《崇有论》、范子真之《神灭论》,则宗乎儒术。何平叔之《无为论》、阮嗣宗之《达庄论》,则主乎道家。沈休文之《形神论》,傅事宜之《明道论》,则归乎释氏。王景兴之《相论》,李遐叔之《卜论》,且及于术数矣。若夫虞世龙之《九州论》,卢子蒙之《冀州论》,则属乎地舆。曹子建之《食恶鸟论》,元次山之《化虎论》,且推及物类。若夫刘子房之《丧服释疑论》,李永和之《明堂制堂论》,则究心于礼制。江应元之《徙戎论》,何承天之《安边论》,则留意于边防。至于崔子真之《论政》,陈元方之《论刑》,皆主复肉刑者也。自丁彦靖、夏侯太初之论出,而其议寂矣。曹元囧之《六代》、陆士衡之《五等》,皆主行封建者也。自李重规、柳子厚之论出,而其说熄矣。且也读魏文帝之《论文》,而知文章之所以重;读裴几原《雕虫论》而知文笔之所以分;观杨遵彦《文德论》而知有文无行之足戒。他若吾丘子赣之《骠骑论功》、王子渊之《四子讲德》则主乎颂扬。韦宏嗣之《博弈》鲁元道之《钱神》、刘孝标之《广绝交》、韩退之之《论诤臣》则主乎讽刺。然此言其大要,一一数之,实更仆不能终也。
贾生《过秦》,雄骏闳肆,可为后世之矩矱;班叔皮《王命论》,浑原朴茂,尚有西京风味,然视贾生则藑乎远矣。自此以后,文采渐缛,气亦阐缓。李萧远《运命论》,沛乎有余,亦时间精光,但亦稍失之繁。《六代论》气雄词骏,追步西京……陆士衡之《辨亡》上下、干令升之《晋纪总论》,摹拟《过秦》,微嫌未化,然亦一时之雄作也。由是文笔分途,笔或枯澹而不华,文或藻缛而害意,然齐梁骈俪之论,亦颇有佳制,以别有专科,故不复论……元明清诸家文,亦不逮一一枚举矣。(1362~1365页)
首先,释名章义,引刘勰之说辨明文体。其次,将《文心雕龙》中的简单论述进行扩充。刘勰只说论始于经书《论语》,高氏补充诸子里的论。刘勰分论为四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序引共纪。”*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论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6页。又,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论分为八品,“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论,四曰史论,五曰文论,六曰讽论,七曰寓论,八曰设论”*于北山、罗根泽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131页。,则兼内容与笔法而论之。高氏在两人基础上,详细区分为有关经、史、儒术、道家、释氏、术数、地舆、物类、礼制、边防、刑法、政治、文章、颂扬、讽刺等类。
除了整体上总论文类外,对每一种文体的具体解说, “校”体,实乃校雠学之简要概述;记载门“志”体中以表格列出自汉至明诸史志之目,崖略显豁可知。这种形式更像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专篇论文,正是在明代盛行的简明扼要的“序题”形式以及《古文辞类纂》式的“序目”基础上的新变。
最后,延续刘勰以来“选文以定篇”的传统,以及《类纂》“序目”中列出目录的思路,高氏于每一文体之中列出佳作。如“论”体举出贾谊、班固、李萧等人作品的典范意义。《古文辞类纂》风行后,各种评注本相继出现。民国间,有《百大家批评新体注释古文辞类纂》《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吴闿生辑《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等书,一时汇聚了众多评点。此书多选录吴闿生所辑《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等书中的评点(1648、1651、1668页),如曰:“昌黎《诤臣论》一篇,姚氏评其风格出于《国》《左》;柳子厚《封建论》,真西山评其间架宏阔,辩论雄俊,可为作文之法”云云。又如“序”体中,“刘子政录《战国策序》一篇,且评云:‘冲溶浑厚,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王介甫《三经义序》,方氏谓其辞气芳洁,风采邈然……至韩退之《张中丞传后叙》,方望溪谓其‘生气奋动处,与《史记》相近’” (1407页)。
综上,高氏吸收了《文心雕龙》文体辨析的思路,以及“序题”“序目”的批评方式,并加以扩充,使每类文体流别、内容更为详细、具体。
三、注疏、考证与文体学结合
章太炎《国故论衡·明解故上》辨析古书校注体例,论述校雠中“校” “故” “传” “解”四种文体, “传”作为注解之一体,其曰:“是故有通论,有驸经,有序录,有略例”*章太炎:《国故论衡》,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09页。,所谓“驸经”,即“当句为释者”,也就是随文注释。“传”体本用于释经而推广于子、集。“注者,著也,言为之解说,使其义著明也”*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大体上“传” “注”同用。“疏”,《汉书·杜周传》颜师古注曰:“疏,谓分条也。”*(东汉) 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杜周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60页。“取于疏通分析”(1387页)。
有着深厚朴学根底的高步瀛,把传统训诂学中的注疏,运用于集部。书中多条列前人观点,并于随文中加以注释。如“论”体中,引《文心雕龙·论说》,并对刘勰所说“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加注释曰:
《书·周官》:“论道经邦。”乃伪古文。《考工记》曰:“坐而论道。”《乐记》:“伦论无患。”亦出《论语》后。然《诗·灵台》:“于论鼓钟。”《毛传》训“论”为“思”。《易·屯》象传:“君子以经纶。”《释文》据郑注本作“经论”,是《论语》前非无“论”字。彦和之意,特谓《论语》前未尝以“论”字名所著之书耳”。(1362页)
诸如此类的随文注疏随处可见。或注释引文语句;或补充前人言论,见于何书何卷,如“状”体,引刘彦和曰“状者,貌也”云云,注明“《文心雕龙·书记篇》”(1477页);或对征引观点进行阐释,或对自己的案语加以补充,如“疏”体中 “传者惟黄侃《论语义疏》最为完全”句下,补充曰:“《八佾》篇‘夷狄有君’章,清四库本改窜原文,然《知不足斋丛书》第七集初印本尚未经改窜,余今日本本合。”(1387~1388页)是乃补充版本。这类注疏,通常以小字夹注于文中。除此之外,此书第一部分的理论论述中,征引了许多他人观点,高氏统一在一节的末尾注明出处。
中国古代文体多源于特殊的差等秩序下产生的复杂的礼仪、制度,高氏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对某些文体所涉及的制度、礼仪加以翔实考证。如“奏议”中,据《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明史·职官志》《清会典事例》等史书,考证自唐以后下级达于上级所用文体,虽统括为奏议,而实际各朝代之中,不同的身份、地位上所用文体各有不同:
刘彦和谓七国:“言事于主,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吴敏德曰:“或曰上疏,或曰上书,或曰奏札,或曰奏状。”……唐代下之通于上者,其制有六:一曰奏钞,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露布以上,由门下省审之……尚书省所司,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辞、牒。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上于皇太子……宋沿唐制,奏议之体大致相同。明制: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清)奏折尤为通行……纂修书籍告成,则用表;国有庆典,亦有贺表。以上皆达于皇帝者也。人民上达官署,则有呈。属吏进言于长官,或用条陈,或用说帖。(1442页)
奏议在历朝的使用情况,在不同的使用对象、场合下的变化,一目了然。这种注疏与考证结合的论著方式,近于李善注《文选》中所谓“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萧统撰,李善注:《文选·两都赋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的文学注释原则与方法。对文体之源流本末,一一疏通辨明,使此时期的文体论著作表现出新的特征,臻于新的高度。
高氏不仅将各文体作史的梳理,更进一步作为其文学批评的载体。如词章门“赋”体,详述自汉至清赋体之变迁,实乃一部赋的文学史以及批评史。高氏罗列了《毛诗序》、班固《两都赋序》、挚虞《文章流别论》、皇甫谧《三都赋序》至《文心雕龙·诠赋》中论赋诸说,“自汉魏以迄六朝,论赋之词,虽迭相沿袭,而趋向实有不同。”又大篇幅引王芑孙《读赋卮言》、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后加案语,曰:
(王惕甫)不过就班孟坚之言而申衍之,无甚精意。张皋文评衡诸家,洞中肯綮……顾皋文以汉赋为主,故于魏晋以后赋,时有不满之词。然时运所趋,不当执一格以绳,即如齐梁之赋,故不免轻浮,而其骨秀,其神远,其词艳而清,其味隽而永,生香活色,亦他代所无,不得概以淫荡目之。故习六朝者,或目汉赋为堆砌,皆一偏之论也。
其对汉赋及六朝赋可谓独具只眼,以通融的视角,作比较全面的评价,这种学术视野正是此前文体学著作所缺乏的。学术判断继之以重要作家作品点评。唐代律赋“要为齐梁之余响,而非汉魏之流风也”,重点论述宋代古赋,而略提明清赋,结尾处概括曰:“有明之赋,古律杂糅,罕能入古,付之郐下可也。有清词赋,实胜明代,然规模魏晋六朝者,尚不乏人。”(1546页)然清代词赋中兴,名家众多,高氏一笔带过,稍显不足。
比较此前的文体论,文体之源流、辨析,举出名篇佳作,是其所同。排列篇章、概括每类文体的主题内容,附加评点等,是其所独有。作为一本学堂讲义,这么编纂的目的在于使“学者诚能熟读深思,则看前人文字,自有权衡”(1365页)。作为全书重心和精华的文体论部分,在文体门类划分、文体辨析以及写作体例上,表现出在前人基础上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特色。当然,其文体论亦非完美无缺的。诗歌、词、小说、戏曲、散曲等体裁在书中的缺席,亦不可不提及。排除作者认为诗歌词曲别有专科教授,故而从略的考量外,对小说文体的忽略,也可以看出传统上视小说为小道、不予重视的痕迹。
四、文体学在新时期的阐述方式
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国内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悄然发生,文学观念、教育、学制、文章、文体、语体等都发生着巨变。在这个“世变大异,旧学寖微,家肄右行之书,人诩专门之选,新词怪意,柴口耳而滥简编”的形势下,古文辞的存在受到了怀疑,有曰:“三十年以往,吾国之古文辞,殆无嗣音者矣。”*严复:《涵芬楼古今文钞序》,见吴曾祺编纂《涵芬楼古今文钞》,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10年,第1页。尤其新式学堂兴,古文辞教育明显受到轻视。陈澹然《文宪例言》中载“今学堂之兴,辄本东西文为教育,甚乃请罢六经四子,专事东西。嗜古之儒,又或别启一堂,毅然取昔时训诂、性命、词章,尊为国粹。新旧殊绝,靡所折衷。”*陈澹然:《文宪例言》,《历代文话》本,第6804页。在此背景下,一批学者选择坚守传统,融贯西学,以传统文论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回应新的时代思潮。陈氏即其中一员,其书中选文摒弃词章,说:“义归经世,文必雅驯,摒词赋一门,尽刊浮藻,约其目,曰纪述,曰典制,曰策论,曰书疏,而以诏、令、箴、歌广其术。”*陈澹然:《文宪例言》,《历代文话》本,第6806页。其重视经世与学行,文体中重纪述、典制度,延续曾国藩以来重文章经世思想。又如,姚永朴提倡 “明道”“经世”鼓吹义法论、自觉的辨体意识*如姚氏曰:“欲学文章,必先辨门类。”《文学研究法》,《历代文话》本,第6863页。其他如唐恩漙《文章学》中曰:“为文宜先知体制”,《历代文话》本,第8737页。。
鉴于传统文体的衰微,亦有人起而捍卫之。吕思勉曰:“近人选本凡例,有谓诏令奏议,体制与现今政体不符,故概不录入。又谓碑铭传状,乃应酬之作,非实用所急,故均不选授者,此真耳食之谈。不知奏议文字,多明畅锐达,其势力之雄厚,他种文字,莫与为比。说理论事之文,可以牗起初学者,无过于此。志铭传状之类,其叙事亦多可法,若概以体制不合而弃之,则今日之诏令呈文,前此竟何所有?讲悉授以民国以来之公牍乎?抑译诸法美瑞士而后授之乎?志铭传状之叙事,皆不可法,则作叙事文者将何所法?其悉授以史传之宏篇乎?抑竟授以分章分节新体之传记邪?”*吕思勉:《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18~519页。案:此文见《拟中等学校熟诵文及选读书目》,1923年作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专修科。可见,在此种新旧争流的时代思潮之下,古已有之的传统文体开始面临被选择、捡汰的命运。随着美的纯文学观念流行于国内,以文体为载体的中国古文辞经历了新一轮的整理整合之后,不行于时的文体逐渐隐没于历史之中,呈现出一种辉煌而后至于没落的研究历程。
自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教授“文学研究法”“ 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张百熙等:《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见苏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206页。等课程以来,中国古文辞的研究便主要在新式学堂、学校中进行。不论是文章源流还是文学史类课程,文体研究都是其中一个重点。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关于“文学教授案”的会议决定说:“教授文学史所注重者,在述明文章各体之起源及各家之流别,至其变迁。”*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0页。如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章太炎《讲文学》、王葆心《古文辞通义》(1906)、黄侃 《中国文学》*据陈平原《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读书》 2005年 第03期,《中国文学》(即《文钞》)一书的目录页,后有“右文百三十五篇,凡《文选》所具者不更缮印,此略依时序编次,讲授则依照便宜为后先”字样。《文式》包括赋颂第一,论说第二,告语第三,记志第四等,规模颇大。、周祺《国文述要》(1914年)、姚永朴《文学研究法》(1914年)、张相《古今文综》(1916年)等,均论及文体分类与辨析;抑或是文章选本中的文体论述,如吴曾祺《涵芬楼古今文钞》附录《文体刍言》(1910年);以及文体研究专著,如王兆芳《文章释》(1901年)、高步瀛《文章源流》等。一时形成一股合力,使中国古文辞与文体研究放射出别样的光芒。
此时期,大部分古文论仍从传统文论中吸取养料,《文心雕龙》的影响尤大。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和文体学研究的基石,《文心雕龙》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被称为文体论,“论文叙笔”,阐明写作各体文章的基本要求。中国古代文学素来重视文章之体制,“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宋)王应麟:《玉海》卷二○二引倪正父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92页。,“文辞以体制为先”*吴讷撰,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凡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9页。。古来文章总集、选本亦多以文体为纬,加以分门别类。《文选》开后世总集、选本以体分类的做法。自姚鼐《古文辞类纂》开始将文体分为十三类,曾国藩进而归纳为三门十一类: “著述门”(三类)、告语门(四类)、记载门(四类)。古代文体辨析、门类划分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延续至民国,如章太炎强调文各有体,以合体论工拙。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门类”中分三类十六种文体,并对“著述”“告语”*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年。详加论述。《汉文典》“文章典”,以文体为纬论述文章法式。《古文辞通义》提出“以至简之门类,檃栝文家之体制”,概括文体为三门十五类*《古今文综》:论著序录类、书牍赠序类、碑文墓铭类、传状志记类、诏令表奏类、颂赞箴铭类、祭弔哀诔类;《古文辞通义》:告语文、解释文、记载文、议论文;《文学研究法》:论辨、序跋、诏令、奏议、书说、赠序、箴铭;词赋、诗歌、哀祭;传状、碑志、典志、叙记、杂记、赞颂。。文体论部分较简略,散布于《历代国文述要》《文体辨要》《诗体辨要》《学文述要》*周祺:《国文述要》,《历代文话续编》本,第919页。等小节中。《涵芬楼古今文钞》分文体为十三类,213种文体子目,每体下有题解;《古今文综》分6部12类,400余目,每类之中分论文体体制、作法;值得注意的是,时代较早的《文章释》则可能因受明代吴讷、徐师曾、贺复徵影响较大,更注重单一文体体式辨析,与后来的部类、门类、科的分类观念表现出较大差距。总体来说,基本不出姚、曾的分类法,或详或略,或增或删而已。
高步瀛《文章源流》明显可见对传统与时人文体论的参考与借鉴。此书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总论文章的内涵,包括文章的名义、起源、类别、形式内容、性质功用、学文功夫。约略相当于《文心雕龙》前五篇的总论。第二部分则是论述文章门类,探讨各文体之起源与变迁。正与《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相对应。“作文要义”中,列出“立意” “谋篇” “造句” “炼字” “用笔” “设色” “和声” “行气”等理论,与《文心雕龙》“写作方法统论”部分照应。文学本原、文章性质功用、分类、文法、文体、作文要义等面面俱到。而占全书最大分量的文体论部分,呈现出以文体贯通文学史的新视角。大体延续姚、曾的分类方法,以及《文心雕龙》以来文体辨析的思路,论述文体源流演变。文体分类上,归纳为三门十六类,以简驭繁,更适合学堂教授之简便明晰的需要。与上述此时期涌现的文体论相比,详尽的文类、文体源流论述、考辨,鲜明地体现出总结和新创的高度。
综上所述,《文章源流》作为一部以文体论为主的文学讲义,不管是从庞大而相对完善的体例,纲目清晰的文体类别划分,具体而微的文体论述,还是颇具现代学术规范的论证方式,此书都表现出在清末民初学术新思潮下,对传统文体论著作的辩证吸收,综合融汇,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特色。然而,新思潮涌入,旧学渐趋衰落,正如马炯章在《效学楼述文内篇》所言:“近数十年来,欧学输入,众流争鸣……当夫学术迁变绝续之交。”*马迥章:《效学楼述文内篇》,《历代文话续编》本,第1739页。晚清民国作为一个过渡时期,伴随着国体更张、制度改换、文学分科等现代化步伐,文体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呈现的辉煌光环慢慢消去。
责任编校:刘云
作者简介:刘春现,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27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102)
中图分类号:I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2-0067-09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