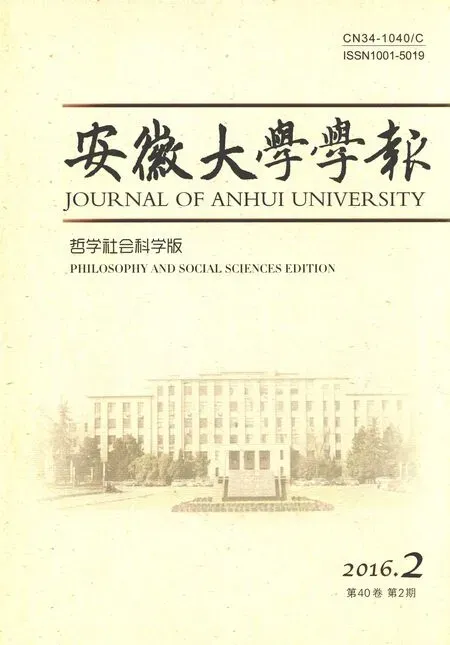怀疑论与可废止推理
戴益斌
怀疑论与可废止推理
戴益斌
摘要:怀疑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怀疑论直接否定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第二种怀疑论既不肯定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也不否定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而是将这个问题悬置起来。然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能证明第一种怀疑论是错误的,并由此得出肯定的结论,即我们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就能很容易否定第二种怀疑论。约翰·波洛克提出可废止推理思想为我们反驳怀疑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它不但能帮助我们驳斥第一种怀疑论,获得肯定的结论,同时又能废止第二种怀疑论。
关键词:怀疑论;可废止推理;约翰·波洛克
从哲学史的发展进程来着,认识论的每一次发展都与怀疑论紧密相关。怀疑论质疑知识的可能性,哲学家们为了捍卫知识必然奋起反击,为知识寻找新的基础,进而推动认识论的发展。这一过程类似于库恩所说的“科学的发展进程”,不同之处在于,在科学的发展进程中,问题伴随着新范式的提出而消失,但怀疑论所提出的问题一直存在。对于这些问题,每位认识论学家在发展自己的理论过程中都必须考虑,它不会因为认识论的发展而销声匿迹。
一
怀疑论者和认识论学者争论的对象,即知识,一般由句子或命题p表达。对于p,我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态度:1.肯定,即支持p;2.否定,即支持非p;3.对于p持保留态度,即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是主张将这个问题悬置起来不作考虑。当然,我们承认存在其他的态度,比如欣赏、喜欢等,但它们与知识问题关联不大,因此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由于上述三种态度可以适用于任一命题,因此,当命题p的内容为“我们可以获得知识”时,对命题p的三种态度便代表哲学史上三种不同的认识论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大多数认识论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有能力获得知识。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则是怀疑论者所持的观点,其中,第三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皮浪式的怀疑论。对于这种怀疑论,古希腊哲学家皮浪的追随者泰门(Timon)做出了以下的解释:“事物之间是中立的、不稳定的并且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感官和信念既不能告诉我们真,也不能告诉我们谎言。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应该信任它们,而是应该不保留任何意见,不持有任何倾向,并且毫不犹豫地说,单个的事物本身,其所是不会比其所不是更多,或者即是又不是,或者既不是其所是,又不是其所不是。泰门说,采取这些立场的人的结果将会是保持沉默。”*转引自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古代怀疑论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skepticism-ancient/。也就是说,由于事物本身是不确定的,我们不应该相信它们,而应该保持沉默,既不做出肯定判断,也不做出否定判断,因为任何判断都会引起反对者的质疑,都会引起争论。与之不同的是,第二种观点则直接否定获取知识的可能性。怀疑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比较多。而且,这种观点随着哲学史的发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认为,得出这种观点可以依据两种不同的理由:a.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是有缺陷的,因此,我们不能获得知识;b.不能排除我们获得的一切知识都是假象的假设,如笛卡尔在其普遍怀疑方法中所提出的邪恶魔鬼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我们获得的知识是真正的知识。虽然对p“我们可以获得知识”的第二种态度和第三种态度不同,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某些关联,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我们不能获得知识”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并因此得出肯定的答案,即我们能够获得知识,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反驳对于p的第三种态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将主要分析对于p的第二种态度。
二
我们首先分析对于p的第二种态度即怀疑论的第一种观点的第一点理由: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是有缺陷的,因此,我们不能获得确定的知识。一般来说,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有以下几种:1.感觉;2.记忆;3.归纳;4.演绎。但怀疑论者认为,以上四种获得知识的方式都不能确保我们获得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至少不能确保我们获得经验知识。
首先,对于感觉,笛卡尔认为:“直到现在,凡是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接受过来的东西,我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不过,我有时觉得这些感官是骗人的;为了小心谨慎起见,对于一经骗过我们的东西就决不完全加以信任。”*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页。笛卡尔的论述表明笛卡尔式的怀疑论对待感觉的基本态度,他们普遍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有可能产生错误,因此,感觉不能成为知识来源的基础。虽然笛卡尔本人不能被当作怀疑论者,但我们有理由谈论“笛卡尔式的怀疑论”,因为“笛卡尔阐明了笛卡尔式怀疑论的立场,并与之斗争”*Steven Luper, Cartesian Skepticism,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Epistemology, Edited by Sven Bernecker and Duncan Paritchar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416.。
关于记忆,也就是关于过去事情的记忆,它与知觉相同的地方在于二者都有可能出错,但在确信度上,记忆甚至不如知觉。因为感觉至少是当下发生的,而记忆的内容则是关于过去的,是已经消失的。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为感觉辩护的话,为记忆辩护似乎就变得更为困难。刘易斯曾在《知识和价值的分析》一书中通过检测明显记忆(ostensible memories)之间的融贯度为明显记忆辩护。诺曼·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也曾通过论证明显记忆是分析的而为其辩护。但斯文·贝尔尼克尔(Sven Bernecker)认为,“为明显记忆辩护的任何策略看起来都不能成功,我们似乎不能先质疑对记忆的信赖,然后证明被给予的明显记忆的可靠性”*Sven Bernecker, Memory Knowledge,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Epistemology, Edited by Sven Bernecker and Duncan Paritchar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333.。如同罗素所言:“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任何记忆命题是可证实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在现在或将来使得过去的事情具有必然性。”*Bertrand Russell, 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intro. by T. Baldwin, London: Routledge, 1995, p.194.
归纳所面临的问题同样严重。归纳推理是一种扩展性的推理,它主张主体可以从个别推知一般,从过去已发生的事实推知将来要发生的事实。休谟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归纳问题,他的基本思路为:有些信念是由归纳推理形成的,如果想要为这些信念辩护,那么就必须证明归纳是有效的,但归纳本身不能为自身辩护,因为这样将会形成恶循环,同时演绎也不能为归纳辩护,因为演绎不是扩展性的,这样,为归纳辩护的两种可能性都被排除,因此,归纳本身将得不到辩护,由归纳而来的信念自然也就不能算作知识。
演绎根据一定的规则从前提推出结论,它能保证推理的有效性,绝大多数哲学家不会怀疑这一点。但问题在于如何能确保前提为真。斯特劳森曾指出:“在感觉的意义上,演绎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建立经验必然涉及对象的知识。”*Peter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London: Methuen, 1966, p. 88.但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至少大部分的演绎都会失败的”*Stephen Engstrom, The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and Skeptic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32, no. 3, 1994, p. 359.,因为笛卡尔式的怀疑论已经排除了为感觉辩护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确保经验知识的有效性,那么怀疑论者有理由将演绎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即先验知识之中,而不允许其应用于任何经验知识。这样,演绎对我们而言将只具有理论意义,对经验生活没有什么帮助。
如果我们满足于演绎的必然性至少保证了部分知识的正确性,那么怀疑论的第二点理由,即我们不能排除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都是假象的假设,将会剥夺我们最后的一丝满足感,因为它否定了现实世界的可靠性,甚至否定了我们自己本身。
怀疑论者最容易提出的一个质疑是:你如何判别自己是清醒的而不是在做梦?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以至于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就曾提出过“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的问题。笛卡尔说:“仔细想想,我就想起来我时常在睡梦中受到过这样的一些假象的欺骗。想到这里,我就明显地看到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标记,也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使人能够从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来。”*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6页。即使我们根据个人经验相信自己此时此刻是清醒的,笛卡尔仍会向我们提出质疑,这个质疑即他的邪恶魔鬼的假设。笛卡尔的推理如下:1.如果我们所相信的一切都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魔鬼给我们设下的骗局,那么我们自认为自己所获得的知识也将只是假象; 2.我们无法否认存在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魔鬼;结论:我们无法否认自己所获得的知识只是假象。笛卡尔的论证似乎是有效的,即使有人批评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恶魔最多只有逻辑的可能性。当然,如果有人以逻辑的可能性不足以确保现实的可能性来反驳笛卡尔邪恶魔鬼的论证,普特南钵中之脑的思想实验就可以为怀疑论者避免这种质疑提供了更好的怀疑版本。因为在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背景下,钵中之脑的假设似乎具有更强的合理性,更接近于现实,更难以反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认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不是魔鬼给我们制造的假象,不是超级计算机通过脉冲刺激在我们大脑中制造的幻象?在这种情况下,想排除这些假设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怀疑论者都可以认为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只不过是魔鬼或超级计算机通过脉冲给我们制造的假象、幻象。当然,我们可以说笛卡尔已经通过“我思故我在”排除了魔鬼的假设,普特南则通过对指称和对象的分析排除了钵中之脑的假设,但是否有其他的理由否定这些假设呢?我们认为,的确有其他的理由否定这些假设的有效性,而且这种理由能帮助我们恢复获取知识的有效性。这一理由源于可废止推理(defeasible reasoning)的发现。
三
可废止推理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只在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得到发展后才引起学者的重视。罗德里格·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比较早地提出了关于可废止推理的基本思想,虽然他并没有使用这一语词。他认为,当我们看到事物具有F的性质,那么该事物对于我们而言,看起来具有F的性质。“看起来”这个语词不但表示行动者可以有一个信念,而且表明该事物具有性质F的信念最后有可能被证伪。
约翰·波洛克(John Pollock)发展了齐硕姆的这一思想,他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初始理由(prima facie reasons)和废止者(defeaters)。理由一般与辩护概念相关,一个理由之所以称为理由,是因为它能为其他事情辩护。因此,在理解什么是理由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什么是辩护。虽然哲学家们对什么是认识辩护持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往往倾向于首先提出C是S相信p在其中得到辩护的辩护条件,然后证明这些条件C的确是辩护条件。这一倾向在盖梯尔问题提出来后变得更为明显。波洛克认为这一做法是从认识的结果出发,而忽视了认识的发生过程。因此,他主张从认识发生的角度关注认识论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认识辩护理解为:“一个信念是得到辩护的,当且仅当它的持有遵循认知者的认识规范。”*波洛克、克拉兹:《当代知识论》,陈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很明显,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分析方式,而且,辩护问题被具体落实到对主体认识规范的理解之上。由于认识规范只存在于人类认知能力之中,对认识规范的理解意味着需要理解人类认知能力。波洛克采取设计的立场来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是通过设计一个合理的类人的存在来理解认识规范。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波洛克将其称为奥斯卡(OSCAR)工程。通过奥斯卡工程,认识规范不再被理解为某种单一抽象的规范性原则,而被理解为具体认知成功的保证*Cf. John Pollock, How to Build a Person: A Prolegomen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9.。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遵循认识规范能保证信念得到辩护,但是认识主体并不总是遵循认识规范,就像我们虽然知道骑自行车的规范,但仍然有可能摔倒一样。这是波洛克十分强调“能力”与“表现”之间区分的原因,也是促使他提出可废止推理的原因之一。
基于对认识辩护和认识规范的理解,波洛克将“理由”定义为:一个人S的状态M是S相信Q的理由,当且仅当S基于身处状态M而相信Q从而得到辩护地相信Q逻辑上是可能的。“初始理由”也是一种理由,它同样能为结论即相信Q辩护,只不过这种辩护并不是决定性的,而只是初始辩护。“初始理由”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波洛克并没有将辩护当作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与我们印象中的辩护概念不一样。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一个理由为某件事情做辩护,那么这种辩护必然是决定性的。但波洛克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一个信念可以仅仅只得到初始辩护。他对“初始辩护”的定义如下:“对一个人S来说,一个信念得到初始辩护,当且仅当只要S有理由认为她不应该持有它,她就没有得到辩护地持有该信念(与此等值的说法是,必然地,如果S持有该信念,并且没有理由认为她不应该持有,那么她就得到辩护地持有该信念)。”*波洛克、克拉兹:《当代知识论》,第241页。因此,对于初始理由而言,它所具有的初始辩护功能仅仅只是临时的,一旦出现其他的理由,则有可能否定由初始理由得出的结论。
初始理由的否定者即废止者(defeaters),它的定义可以表述如下:如果M是S相信Q的理由,一个状态M*是这一理由的废止者,当且仅当同时身处状态M和M*的组合状态不是S相信Q的理由。波洛克区分了两种废止者:反驳式的废止者(rebutting defeaters)和中断式的废止者(undercutting defeaters)。反驳式的废止者很常见,也比较容易理解,它直接否定初始理由的结论。波洛克将其定义为:“如果M是S相信Q的一个可废止理由,那么M*是该理由的一个反驳性的废止者,当且仅当M*是一个废止者,并且M*是S相信~Q的一个理由。”*波洛克、克拉兹:《当代知识论》,第242页。中断式的废止者并不直接否定初始理由的结论,而是攻击初始理由与其结论之间的联系。当然,它并不肯定结论一定是错的,而只是说,在中断式废止者的作用下,从初始理由并不一定能得出之前的结论。比如说,当我们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张纸是红色的,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张纸是红色的,因为我们具有一个初始理由,即“我们感知到这张纸是红色的”这个感知状态为我们的信念“这张纸是红色的”提供了初始辩护。但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房间的灯光是红色的,那么之前的结论,即这张纸是红色的,就是不成立的。因为白色的纸在红色灯光下也会呈现出红色。当然,我们并不能说这张纸一定不是红色的,而是说,在灯光是红色的条件下,仅凭感知到这张纸是红色的并不能得出这张纸一定是红色的这一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将“灯光是红色的”称作是“我们感知到纸是红色的”这一初始理由中断式的废止者。波洛克将中断式的废止者定义如下:“如果相信p是S相信Q的一个可废止的理由,那么M*是该理由的一个中断式的废止者,当且仅当M*是一个废止者,并且M*是S怀疑或否认下述判断的一个理由:除非Q为真,否则p为假。”*波洛克、克拉兹:《当代知识论》,第243页。
通过提出这些核心概念,波洛克构建了可废止推理的基本模式。虽然波洛克并没有为这些推理提供可靠性与完全性的证明,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使用可废止推理。
因为首先,可废止推理符合我们的直觉。根据波洛克,我们有两种可废止推理的模式,一种是反驳式的可废止推理,一种是中断式的可废止推理。这两种推理的运行模式都依赖于初始理由与废止者之间的关系。而在直觉上,我们很容易接受波洛克对初始理由和废止者的解释。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找不出这些解释与我们的直觉有任何冲突的地方。如果波洛克对初始理由与废止者的解释是对的,那么这些推理模式就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推理模式事实上就蕴含在对这些概念的解释之中。
其次,可废止推理在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推理:前提1:天鹅a1是白色的;前提2:天鹅a2是白色的;前提3:天鹅a3是白色的……前提n:天鹅an是白色的;前提n+1:自然界具有齐一性;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推理是有效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都相信这样的推理。然而,17世纪后,我们发现有的天鹅是黑色的,这与结论相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推理中肯定有某个环节出错了。由于在这个推理中只包含有两种因素,即前提和结论,而结论来源于前提,因此,这个推理出现错误的原因只可能存在于前提之中。通过对这个推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前提1到前提n+1的集合可以看作是初始理由,“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可以视为该初始理由的结论,而“有的天鹅是黑色的”则是该初始理由反驳式的废止者,因为“有的天鹅是黑色的”使我们相信“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前提n+1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多,而所有这些推理都可以算作是可废止推理。
四
站在可废止推理的角度,我们可以破除怀疑论的质疑。首先,让我们重新思考第一种怀疑论的第一点理由,即通过质疑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来否定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笛卡尔式的怀疑论之所以质疑通过知觉获取知识可能性的原因在于知觉有时候会误导我们,而我们无法区分什么情况下知觉不会误导我们,什么情况下知觉会误导我们,而如果通过知觉所获得的信息是误导我们的,那么我们由之而获得的信念就不能算作知识。但从可废止推理的角度来看,知觉有可能出错并不能成为障碍,因为“一个信念是否得到辩护,重要的是知觉状态……辩护部分地是知觉状态自身的功能,而不只是我们关于知觉状态信念的功能”*John Pollock and Joseph Cruz,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Knowledge, Totowa, N. J.: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p. 25.。基于这点理由,我们知道知觉状态本身为知觉信念提供了初始辩护,不论知觉信念的对象或内容是模糊的还是明确的,都不影响由此而形成的知识是可废止知识。这表明,基于知觉的认识应属于可废止推理的范畴。
记忆的情况与知觉类似,我们同意贝尔尼克尔的观点,我们不可能先质疑对记忆的信赖,然后证明被给予的明显记忆的可靠性,也同意罗素的观点,没有什么能证实记忆命题的必然性,但这些都不妨碍我们接受记忆知识。因为从可废止推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首先质疑对记忆的信赖。相反,可废止推理信任记忆的初始状态,它为记忆信念提供了初始辩护,只不过这种初始辩护是可废止的,由此形成的知识也是可废止的,虽然它不具备罗素所要求的必然性,但仍然可以称为知识。
至于归纳法,站在可废止推理的角度来看,这同样不成问题。质疑归纳法的理由在于没有什么能为归纳法辩护,归纳本身不行,演绎也无法做到。对于这种质疑,我们并不反对。但我们可以转换思路,将这些众多的个别事例或已发生的事当作初始理由,而将一般的性质或将要发生的事当作这个初始理由的结论,这样我们就可以赋予归纳法可废止的特性,同时又保证归纳具有初始辩护的功能。比如说,当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很多只天鹅都是白色时,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当然这样的结论是可废止的,一旦发现有天鹅不是白色时,就相当于发现其反驳式的废止者。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将归纳法做这样的转换,原因在于在可废止推理的框架下,归纳法属于可废止推理的一种,它的特殊性只在于要求归纳前提是众多事例或许多已发生事情的集合。
通过恢复知觉、记忆和归纳获取知识的有效性,怀疑论者对演绎的质疑自然而然就会瓦解。因为,我们可以获取先验知识之外的知识,即经验知识。而一旦确认经验知识的有效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演绎应用于经验知识,就像斯特劳森指出的那样,建立起经验必然涉及对象的知识。只不过这种知识不是必然知识,而是可废止知识,因为演绎的前提是可废止知识,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演绎不再被局限于先验知识之中。
同样,在可废止推理的框架下,第一种怀疑论者质疑我们获取知识的第二点理由,即我们不能排除我们所获得的知识都是假象的假设,也是不能成立的。怀疑论者认为我们不能区分我们到底是醒着的还是在做梦,也认为不能否认可能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魔鬼在欺骗我们,或者我们只是超级计算机控制之下的钵中之脑。然而站在可废止推理的立场之上,我们可以驳斥这种观点。
首先,对于我到底是醒着的还是在做梦的这个问题,我有大量的事实表明我现在是清醒的,比如说,我刚才亲自打开了空调,现在正面对着电脑写论文等等,这些大量的事实使我有理由相信自己处于清醒状态,它们为我是清醒的提供了初始辩护。笛卡尔认为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能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但即使我们承认没有可靠的迹象并不意味着现存的迹象就不能为我们辩护,因为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初始辩护,并不需要那么可靠的迹象。当然,我承认,有可能我的确是在做梦,这被包含在可废止推理的框架之下,就像我承认我们的知识有可能是错的一样,可废止推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问题在于,这种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只能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它要成为废止者,必须要得到辩护,不论这种辩护是初始辩护,还是决定性辩护。
针对笛卡尔的恶魔假说和普特南的钵中之脑假说,我们认为,这在可废止推理的框架下同样不成问题。笛卡尔的恶魔假说和普特南的钵中之脑的假说具有相似的推理模式,即利用无法证伪的假设来质疑现实世界的可靠性。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推理模式似乎是有效的,因为如果无法排除这样的假设,那么我们也就无法断定自己是否真的属于现实世界,而不仅仅只是幻象。问题在于,这个推理中的前提是否为真?如果前提为假,那么即使推理有效,它的结论仍然为假。显然,笛卡尔和普特南各自的假设既不是先验知识也不是经验知识,我们无法从经验之外或之内为其寻找依据。也就是说,恶魔假设和钵中之脑假设仅仅只是假设,没有任何理由为之辩护。以笛卡尔的恶魔假说为例,我们可以重构他的论证思路,初始理由:生活中的大量事实;结论1:世界是真实的,知识是可能的;废止者:可能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恶魔,并且它欺骗我们;结论2:我们无法确定世界是真实的,同时也无法肯定知识是可能的。可以看出笛卡尔的假设实际上是一个中断式的废止者。但是根据废止者的定义,即“如果M是S相信Q的理由,一个状态M*是这一理由的废止者,当且仅当同时身处状态M和M*的组合状态不是S相信Q的理由”,笛卡尔的这个假设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废止者,因为作为初始理由的废止者,它要求我们能同时处于初始理由与废止者的状态之下。也就是说,废止者必须是真实的理由,并且有事实依据,不论这个事实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但笛卡尔的假设仅仅只是一个得不到辩护的假设,我们不可能处于假设的状态之中。而一旦破除了笛卡尔恶魔假说的废止者地位,我们就可以恢复从初始理由到结论1的整个推理过程。同样,普特南的钵中之脑假设也适用于此种分析。
至此,我们利用可废止推理不但恢复了获取知识的几种方式的有效性,同时也反驳了认为知识可能只是假象的假设。这样,我们就已经证明了怀疑论的第一种态度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实际上已经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即我们能够获得知识。
同样,利用可废止推理,我们也很容易反驳第二种怀疑论,因为在可废止推理的框架下,第二种怀疑论的主要理由,即事物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因为可废止推理所允许的初始辩护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可废止推理允许废止者的存在。我们的感官和信念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我们应该信任它们,需要注意的是,由它们获取的知识是可废止的。
五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怀疑论是错误的,我们能够获得知识。怀疑论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知识的可废止性,并且试图用未经辩护的可能性去反驳已得到初始辩护的可废止知识。
对于这个论证,可能还存在以下两点质疑:
首先,我们一直在可废止推理的框架下论证怀疑论是无效的,如果不在可废止推理的框架下,那么怀疑论是否就有可能是有效的?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提问者赞同从可废止推理的角度反驳怀疑论,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理解到可废止推理是人类认识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已经阐明,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情况都会使用可废止推理,它是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方式。因此,只要我们的论题与认识相关,就必定会牵涉可废止推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可废止推理是推理的唯一模式。事实上,除可废止推理之外,演绎推理也是推理的一种模式。二者的区别在于:演绎推理是必然有效的,它对应的形式为“如果p,那么q”,而可废止推理是可废止的,其对应的形式为“如果p,那么可废止地q”。而具体到认知过程中,我们可以认为“可废止推理是规范,演绎推理只是例外”*John Pollock, Defeasible Reasoning, Reasoning: Studies of Human Inference and Its Foundations, Edited by Jonathan Adler and Lance Rip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69.。因此,当提问者指出“不在可废止推理的框架下”这样的问题时,提问者没有意识到在讨论认识时,我们不可能不在可废止推理的框架下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其次,可废止推理承认初始辩护,并认为知识是可废止的,这就意味着知识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这种理解似乎与我们关于知识的一般理解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就像演绎推理和可废止推理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最好还是延续将知识分为两类的传统,一类是先验知识,另一类则是可废止的知识。先验知识是必然的;而可废止的知识则是临时的。这里“临时”的意思与具体时间无关,而是表示在废止者被发现之前,可废止知识都可以被当作知识。一般而言,我们倾向于将数学和逻辑称为先验知识,而将经验性的知识称为可废止知识。当然,将数学和逻辑称为先验知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数学和逻辑中的某些知识可能由于数学家或逻辑学家个体认识的因素也是可废止的。但在此强调的是,在认识过程中,知识的可废止性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找出绝对的永远不会出错的知识。
责任编校:余沉
作者简介:戴益斌,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2-0009-07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