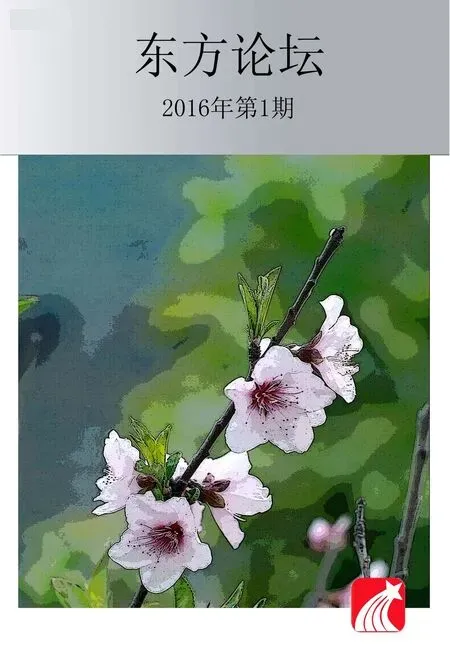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
耿 达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
耿 达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部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作为一个阶层群体,部曲有其鲜明的特征,即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重义。部曲主要依附于庄园地主,在庄园里从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部曲的活跃时期反映了兵户制的瓦解和私兵制的兴起,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提供条件并影响了国家统一进程。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部曲;宗法关系;生产劳动
部曲是军队编制的名称,到魏晋南北朝时演变为私兵,其成分随之扩大和混乱,但只有编成军队才成部曲[1](P15)。在魏晋南北朝时,部曲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主要源自于宗族乡里和门生故吏,也有许多是自行招募和赏赐所得。此时,部曲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2](卷31《鲁广达传》)、“方镇屡革,边戍仍连,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3](卷31《五行志》)。当时的部曲已不单是一种军事组织或私家兵,而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阶层或群体。虽然部曲依附于宗主豪强,为宗主豪强履行各种义务,主要是战时作战和闲时务农。但其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是有其鲜明的特征和内在属性,有着属于他们的劳动生活方式,并且对当时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部曲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重义
中国儒家推崇的宗法观念和道德伦理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和凝聚力。在战乱频繁的魏晋南北朝,个体小农很难自保,于是依附于有势力的宗族或地主豪强以求生存发展。许褚聚“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4](卷18《许褚传》);田畴“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干敝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4](卷11《田畴传》)。部曲具有很强的宗族意识,由于具有某种血缘或情感方面的引导,于是号召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和容易。而对于宗族自身来说,“御寇”作战当然是正义的,并且在以宗族为核心的部曲组织里,有很强的道德伦理观,因此得到乡里百姓的支持。如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有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5](卷62《祖逖传》)。这些“亲党”经祖逖的组织和武装后就成为了他的部曲。祖逖对这些“宾客义徒”,“遇之如子弟”。在这里,祖逖不论存在何种目的,他所表现的是一种“义”,并且感染了其“亲党”,得到了其认可和推崇。其后,当祖逖北伐时,司马睿任其为豫州刺史,仅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不给铠仗,“使自招募”。祖逖“仍将本流徒部曲百余家渡江”,并以这百余家部曲为基础,“屯于江阴,起治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5](卷62《祖逖传》)。在这个过程中祖逖无疑是经过宣传动员的,宣传的内容除了“收复失地”等,更为有力的就是“义”,有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味道。祖逖“有情有义”,爱护部下,因而得到百姓的拥护,纷纷加入。
在种种关系里面,“义”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而宗主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也会将这些依附者武装起来,组建成自己的部曲。如孙坚起兵时,其弟孙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4](卷51《孙静传》),霍笃“于乡里合部曲数百人”[4](卷41《霍峻传》)。宋明帝泰始初,青州刺史沈文秀举兵反叛,刘善明“密契收集门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斩关奔北海”[6](卷28《刘善明传》)。高欢讨伐尔朱兆时,高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7](卷21《高乾传附弟慎传》),参加作战。高乾弟高慎,太昌初,“时天下初定,听慎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7](卷21《高乾传附弟慎传》)。这些以宗族部曲、门宗部曲、乡曲相称的,都带有以宗法关系为纽带,而且这有一个相当的好处即以宗主或情感或义的名义迅速纠合。这些部曲依附于有势力有道义的宗主之下,具有很强的凝聚力。部曲依附于宗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在道义上的表现为“义”,一旦这种“义”根植于心,就有可能“请死相报”[7](卷32《王琳传》)。徐湛之叛乱时,曾谓范晔曰“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其亦当解人此旨,故应得健儿数百”[3](卷71《徐湛之传》)。沈众在侯景之乱时,“众表于梁武,称家代所录故义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口口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入援京邑,顿于小航,对贼东府置阵,军容甚整,景深惮之”[2](卷18《沈众传》)。对这些“故义部曲”,清代学者赵翼指出:“六朝时所谓门生则非门弟子也,其时仕宦者许各募部曲,谓之义从。”[8](《陔余从考》卷36《门生》条)因此,早期部曲与宗主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明显,并且在表象上更多的是以“义”相称。宗主对部曲也格外优待。羊侃因抗击侯景叛乱有功,萧衍赏其金五千两,银万两,绢万匹,“以赐战士”。羊侃坚辞不受,但却对自己的“部曲千余人,并私加赏赉”[9](卷39《羊侃传》)。侯景之乱,荀朗“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赈赡,众至数万人”[2] (卷13 《荀朗传》)。可见,宗主与部曲之间的关系似乎相当亲密。当然,也有一些部曲依宗主之势为非作歹,“多有部曲,时为侵扰,城邑苦之”[10](卷71《李元护传》),弄得“部曲残横,民颇厌之”[9](卷9《曹景宗传》)。但大多数部曲还是相当重义,特别视恶如仇,哪怕是自己的宗主。孙皓凤凰三年,临海太守奚熙妖言惑众,“熙部曲杀熙,送首建业”[4](卷48《孙皓传》),沈充与王敦构逆,“为部曲将吴儒所杀”[5](卷89《沈劲传》)。
二、部曲的生活状况
部曲由于身份地位相对平贱低下,其劳动生产生活状况史书和现代史家论及的不多。但根据一些相关资料还是可以推断和设想的。众所周知,部曲的主要职能是作战,是士族地主为维护其政治地位和庄园财产而设置的家兵。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已越来越广泛的被用于农业生产,与佃农的境况相似。在法律上,门阀地主有权占有佃客和部曲,于是“注家籍”的佃客和部曲就成了庄园里的主要劳动者。而此时,佃客和部曲已无多大区别,在史籍上开始连称。那么,庄园经济的主要劳动生产便是佃客和部曲了。于是,部曲的劳动生产生活我们可以从门阀庄园中窥见一斑。
《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称: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美宅,背有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钩游鲤,乜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
这是曹操统一北方后,门阀庄园兴起的反映。仲长统所企求的这种“良田美宅”,就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庄园。虽带有幻想,但可以肯定这是符合当时老百姓的劳动生活心理的。依山傍水,家庭和谐,生活无忧,也是一般劳动人民的普遍渴求。在“良朋萃止”和“嘉时吉日”这类重要聚会和重要风俗节日之际往往是美酒佳肴以奉之。而那奇美的庄园风景和悠然的庄园生活给人美好憧憬。因此许多小自耕农沦为流民后甘愿依附于门阀地主以成为佃客部曲,在庄园里继续着他们的生产生活。
《晋书》卷三三《石苞传附子崇传》称:“有司簿阅崇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这里石崇的“苍头八百余人”和他的水碓、珍宝、货贿、田宅一起登记在“簿”,可以说明石崇的家籍上也一定登记有大群的佃客和部曲,而其相当部分是用于服役和从事歌舞游乐的生活。
在士族庄园里佃客和部曲的主要农业劳动是“力田”。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士族庄园很重视水利灌溉。如宋元嘉二十一年晋陵大旱,“承陂之家”却“并皆保熟,所失盖微,陈积之谷,皆有巨万”[3](卷91《徐耕传》)。“承陂之家”大多是士族地主。可以肯定的是,佃客部曲等劳动者用汗水和智慧创造了抗旱保熟的稳产田。
除农业外,庄园里还有园林业。占山法指出,士族地主占山是为了“种养竹林杂果”。而士族地主为了显示其品味和生活情趣,便使佃客部曲广植各种果树花草。谢灵运的庄园中“罗行布株”,遍植果树,诸如桃、李、杏、梨、桔、柿、枣、梅、枇杷、林檎等,应有尽有。此外还有竹园,《山居赋自注》称“缘崖下者,密竹蒙迳。从此直南,悉是竹园,东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其它树木如松、柏、桐、榆等,也漫山遍野。士族庄园里还饲养着大量的禽畜。樊宏的庄园里有“六畜放牧”,在石崇的金谷园里有“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颜氏家训》卷一《治家篇》称“鸡豚之善,塒圈之所生”。可见,饲养禽畜是一般庄园里都有的。这也是在“良朋萃止”和“嘉时吉日”这类重要聚会和重要风俗节日之际往往会有这么多美酒佳肴以奉之的原因了。
另外,佃客部曲在庄园里还从事着手工业生产。主要有纺织、酿造、用具制造、造纸、药物生产等。这些都在《山居赋》中可以查阅得到[11]。在士族庄园里,部曲为庄主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资,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为庄主服役,极大的满足了士族爱慕虚荣和所谓优雅风趣的田园般生活,为士族文化耗尽了他们的劳力和脑力。士族庄园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组织,作为其主要劳动生产者的部曲,在山区水滨进行经营,也对庄园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对江南经济的开发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部曲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影响
(一)促进了兵户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私兵制的兴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士兵的主要合法途径是兵户制,即“兵户”“军户”,与一般编户齐民相区别,另立不同于民籍的“兵籍”或“军籍”,使之世代相袭为兵[12](P300)。这种兵户制在社会动荡不安、人口死亡与流动很大的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但由于兵士身份低微以致兵户不乐为兵而不断逃避和解脱兵籍,使得兵户数量减少,加之魏晋南北朝连年战乱对士兵的需求量极大,这一矛盾十分突出。随着地方豪族门阀势力的兴起膨胀,许多将帅为扩展自己的实力,采取招募流民成为自己的部曲。如董卓之乱后,关中部分流民重返故土,“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卫觊在给荀彧的书信中谈到此事言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竟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4](卷21《卫觊传》)在南朝,“将帅以下,各募部曲”[6](卷27《李安民传》)的现象很普遍。如宋明帝刘彧宠信阮佃夫等人,阮佃夫“广募义勇,置为部曲”[10](卷97《岛夷刘裕传》);陈后主时期,还“敕遣征收募兵士,自为部曲”,“旬月之间,众近一万”[2](卷29《蔡征传》),数量很是惊人。夏侯夔为豫州刺史“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9](卷28《夏侯亶传》)。祖逖北伐时的主力也是自行招募的部曲。侯景之乱时,各地方将帅纷纷招募部曲以讨伐的名义扩充自己的实力。
部曲私兵制的发展,极大地削弱了由国家兵户组成的军事力量。各地军府将领及地方长官召募部曲发展私人武装,促长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国家也基本上默认了部曲私兵制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在中央,也靠召募部曲以维持统治。如北魏孝武帝为摆脱高欢挟持,“置内阁都督部曲”,“皆选天下轻剽者以充之”[10](卷80《斛斯椿传》)。随着部曲数量的增加,私家部曲制就顺理成章取代了国家兵户制。
(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提供条件并影响了国家统一进程
如前所述,地方将帅广招部曲扩充自己势力,形成地方上的实力派。他们以门阀为根基,以庄园提供独立的经济来源,加之手中握有大量的部曲,俨然成为国中之国。一些将帅往往以部曲为政治资本,必要时可以举兵威胁中央统治,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4](卷28《邓艾传》)就是如此。萧衍起兵时,曹景宗“聚众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从军”[13](卷55《曹景宗传》),全力支持萧衍。梁雍州刺史萧詧“蓄聚货财,折节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数千人”,准备“图大功”[14](卷159《梁纪》),夺取政权。而当皇权尚不强大时,最高统治者就以罢“质任”的方式笼络部曲拥有者。如司马炎在即位之初为笼络豪强部将,曾“罢部曲将长吏以下质任”,“降除部曲督以下质任”[5](卷3《武帝纪》)。总之,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即部曲私兵制的发展壮大、国家兵户制的瓦解,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和士兵数量有限,而地方豪强部将握有数量众多的部曲。
魏晋南北朝经历了长期分裂,期间的南朝三次北伐由于各种原因而失败,而最终却由文化相对落后经济欠发达的北方统一文化高度繁荣经济比较富庶的南方,这又是何故?有所谓地缘因素的影响,但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南朝的中间阶层。南朝的门阀地主势力太过强大,可以世代为官,也就垄断了进仕的道路;可以有庞大的庄园,也就有充足的经济来源;可以自行招募部曲,也就能够组建自己的武装。虽然北朝也有类似的坞壁组织,但其经过北朝政府的不断改革后开始瓦解。而南朝的门阀始终握有独立的经济体系和私人武装。中间阶层的过于强大,使得国家中央政令不能有效下达和贯彻实施,反而与国家争夺土地和人口。国家直接掌控的自耕农不断破产,沦为士族门阀的佃客和部曲。而部曲这一庞大群体不仅为士族门阀进行生产,还为其提供武装军事支撑。所以部曲私兵制的大量存在和发展,成为士族门阀的坚强经济生产者和武装军事支撑者,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提供条件并影响了国家统一进程。
部曲作为地主豪强势力的私属,在许多历史记叙中也只是附属,没有单独的专门提及和描述其生活劳动状况。我们所见到的是其作为一种附属品或工具被奴役和利用,没有独立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部曲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且人数众多,在一定时期发挥了极大的历史作用,应该有其独立的生活和思想状况。部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频率比较高,虽然分散,零星分布于各传记中,没有专门记载,但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至隋唐时期,随着部曲身份的卑微化和其不断演化,部曲这一名称也湮没在历史之中[1] (P21)。
参考文献: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3]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7]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8] 赵翼.陔余从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0]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 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12] 高敏.魏晋南北朝史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3]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责任编辑:侯德彤
Private Army in the Period of Wei ,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GENG Da
( Research Center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
Abstract:Private army underwent great changes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s a class, this group of people was characterized by linkage through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nd stressing mutual loyalty. Those people mainly clung to landlords of manors, engaging in farming, handcrafts, etc. Their prosperity refl ects the collapse of the soldier system and the rise of the private army system, which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frequent regime changes and infl uenced the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unifi cation.
Key words: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rivate army; patriarchal clan relations; productive labor
作者简介:耿达(1988-),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
收稿日期:2015-11-03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1-007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