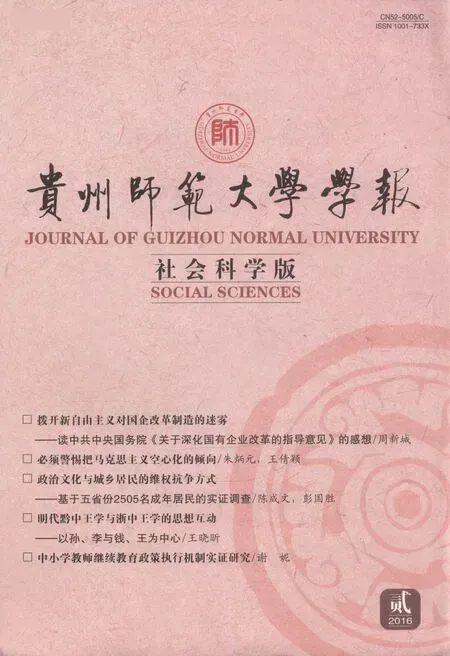青年马克思与反犹主义的思想关系新探
——重新思考《论犹太人问题》与反犹主义的关系
李彬彬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青年马克思与反犹主义的思想关系新探
——重新思考《论犹太人问题》与反犹主义的关系
李彬彬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91)
《论犹太人问题》并不是反犹主义的文献,马克思也不是反犹主义者。尽管马克思对“犹太人”和“犹太精神”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但是马克思批判的并不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而是犹太人生活于其中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中以发财致富为最高目标的“犹太精神”是控制着庞大商业帝国的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根本原因,《论犹太人问题》提出了变革市民社会的要求,是犹太人唯一可以期待的尘世的“福音书”。
反犹主义;日常的犹太人;安息日的犹太人;宗教信仰
认真清理最近几十年的学术史,不难发现,青年马克思与反犹主义的思想关系一直是争讼不休的话题。而这个问题是由马克思1844年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引起的。由于《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激进立场,青年马克思常常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思想标签。例如:伯纳德·里维斯(Bernad Lewis)认为《论犹太人问题》是“反犹主义宣传中的一部经典文献”[1],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甚至认为青年马克思文章中“强烈的反犹主义声音影响了共产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态度”[2]。当然,反对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分析“反犹主义的起源”时就提到“马克思常常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反犹主义”[3],埃里希·弗洛姆甚至认为“说马克思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只是冷战的宣传”[4]。除了正反双方针锋相对以外,还有一批中间派,例如什洛莫·阿维纳利(Shlomo Avineri)一方面把马克思具有反犹主义思想说成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必须防止用“马克思在哲学上对犹太教的批判掩盖马克思在政治上对解放犹太人的支持”[5]。可以说,在青年马克思与“反犹主义”思想关系的问题上,“打倒”马克思和“保卫”马克思的较量形成了《论犹太人问题》研究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据尤利乌斯·卡勒巴赫统计,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有近百份著述讨论这一问题。纵观学术史上对马克思主义与反犹主义关系的争论,它们主要围绕两个焦点问题展开。第一个焦点问题是,马克思对犹太人及其解放事业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日常的犹太人”的批判。今天,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敞开学术史关于这一问题争论的焦点话题,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澄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学术史上争论的第一个焦点问题: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情感及其对解放犹太人的态度如何
关于这个焦点问题,埃德蒙德·西尔伯纳与赫尔穆特·希尔施的相关著述反映了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截然不同的认知。首先来看埃德蒙德·西尔伯纳对马克思的责难。埃德蒙德·西尔伯纳(Edmund Silberner)是名犹太学者,他于1949年在《犹太历史》(“Historia Judaica”)第11期上发表的《马克思是个反犹主义者吗?》,试图证明马克思是个典型的反犹主义者[6]3-52。由于西尔伯纳动用了即使在今天看来都非常完备的素材来写作这篇文章,因此该文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引用。
在《马克思是个反犹主义者吗?》这篇文章中,西尔伯纳提出了很多有冲击力的观点和结论。他的第一个观点是,尽管马克思有着纯粹的犹太人血统,但是他对犹太人没有任何情感。西尔伯纳首先考察了马克思的家谱。在卡尔·马克思的家族中,他的爷爷是特里尔的拉比(相当于基督教神父),其叔父是犹太大公会的成员,担任萨尔区的大拉比,卡尔·马克思的奶奶和母亲的家族也都是拉比世家。卡尔·马克思有着非常纯粹的犹太人血统。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却改变信仰,改宗了基督教。对于亨利希·马克思改信基督教的原因,卡尔·斯波尔格(Karl Spargo)提出了“信仰皈依”的解释,弗兰茨·梅林提出了“自由决定”的解释。西尔伯纳认为,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一个血统纯正的犹太人为什么会改变信仰,他认为唯一的原因就是,在那个时代放弃犹太教不仅意味着“宗教上的自我解放”,而且意味着“社会解放的行动”,“只有改变信仰才能交换到融入欧洲文化的入场券”[6]10。亨利希·马克思改宗基督教表明,卡尔·马克思的父辈对犹太教和犹太人民已经没有强烈的感情了。西尔伯纳还提到,亨利希·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是如何教导卡尔·马克思的,这是马克思传记作家的一个“禁忌(taboo)”[6]9。由于传记作家没有交代这件事对于马克思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具体影响是什么。但是皈依行为造成的影响不一而足,只有少数人在改变信仰之后还对犹太人保持尊重,大多数人都陷入对犹太人自负的厌恶之中。“马克思显然属于后者”[6]12。在接受洗礼之后,马克思在全新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他没有受过任何犹太教育,因而更加容易受到基督教社会的影响,而基督教社会——就算在莱茵省不是直言不讳地反犹的(outspokenly anti-Jewish)——对待犹太人至少是冷漠无情的。”[6]12马克思一家因为皈依基督教经济上更加有保障,连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的姻缘也因皈依基督教而少了很多困难。西尔伯纳还提到,马克思曾经轻蔑地批评别人“改叛信仰”,从这件小事能够看出“马克思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已经没有什么意识了”[6]13。
西尔伯纳的第二个观点是,尽管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说过要帮犹太人写请愿书,但是他并没有写过任何请愿书,这更加暴露了他对犹太人的敌意。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提到过要为科隆的犹太人请愿。西尔伯纳对这件事提出了质疑。他说,由于卡尔·马克思对于犹太教没有任何知识,也没有任何好感,1842年科隆“当地的犹太人领袖”为什么会找马克思写请愿书?科隆的犹太人地方志和研究材料都没提到有这么一个领袖,1842年科隆犹太人的领袖是谁?同时,《莱茵报》经理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有两位兄弟西蒙和亚伯拉罕,这两位银行家都曾为犹太人请过愿,当地还有更有名望的加布里尔·里瑟尔,这三个人都是忠诚的犹太人,科隆的犹太人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对犹太教没有感情的人来为犹太人请愿?关于这个问题,梁赞诺夫曾经提出过一种观点,即那个找马克思的人是马克思的亲戚。西尔伯纳并不认可梁赞诺夫的说法,因为马克思明确提到这个人是科隆当地人,而马克思在科隆没有亲戚。关于这份请愿书,西尔伯纳的看法是,马克思很有可能没写这份请愿书,就算马克思已经起草了请愿书,它之所以没有流传下来,也是因为当地犹太人发现请愿书只能带来更多伤害,因此没有采用这份请愿书。西尔伯纳还提到,马克思在写给卢格的同一封信中还提到他讨厌犹太人的信仰,鉴于马克思此时还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很显然对于马克思这个无神论者来说,犹太人的信仰之所以尤其讨厌,是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充满了早年获得的偏见。”[6]20-21
西尔伯纳的第三个观点是,《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结论充满了异想天开的救世精神,没有任何说服力,完全站不住脚。在《论犹太人问题》的结尾,马克思提出了“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西尔伯纳对这一结论的评价是:“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提出的福音,它本应把犹太人问题纳入新的轨道。按照梅林的说法,这是一项‘根本研究’,它不需要任何评论,任何评论都只会弱化它。在梅林看来,马克思这几页的研究比从那以后出现的所有有关犹太人问题的研究都更有价值。不过,伟大导师的另一些资质不错的研究者,例如卡尔·考茨基(《人种和犹太教》,1914)在处理犹太人问题时甚至连《论犹太人问题》都没提一下。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对犹太人的看法空洞无物,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看法没有解释力。”[6]26在评述《论犹太人问题》之后,西尔伯纳又用了六个小节来分析马克思的其他著述以及他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最后总结道:“不论愿不愿意,马克思在他的基督徒追随者中间都强有力地唤起或强化了反犹偏见,而且使得很多仰慕他的犹太人与自己的民族疏远。因而,他在现代社会主义的反犹传统(这是一个可以使用而且必须使用的新术语,也是一个合适的术语)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6]52
为了反驳西尔伯纳提出的“马克思是一个反犹主义者”的论点,同为犹太人的赫尔穆特·希尔施可谓殚精竭虑,他先后发表了两篇有影响的论文:《马克思与争取犹太人平等地位的请愿书》和《所谓的丑陋马克思:对一个“直言不讳的反犹主义者”的分析》,以及一部专著:《马克思与摩西: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和犹太人》(Marx und Moses, Karl Marx zur Judenfrage und zu Juden)。
在《马克思与争取犹太人平等地位的请愿书》中,希尔施质疑了马克思没有写作请愿书的观点。他提出,尽管马克思1843年3月13日写书信给卢格之后是否起草这份请愿书已无从考证,但是确实存在一份“科隆1843年5月”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是以科隆参议员海因里希·梅尔肯斯博士的“有关犹太人和其他市民地位平等的申请”的附件形式提交给莱茵省议会的。1843年5月22日,《科隆日报》公布了这份请愿书。《莱茵报》的所有成员都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不乏马克思当时非常密切的朋友。这份请愿书是谁起草的已无从考证,是否马克思所写亦不可知。不能武断地说马克思与这份请愿书没有关系[7]229-245。除此之外,还有一份题为“特里尔,1843年6月10日”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信息:第一,有一个名叫“约瑟夫·马克思(Josef Marx)”的犹太家畜商人在这份请愿书中署了名,并不能排除这是卡尔·马克思的亲属。在这个问题上,西尔伯纳简单地否定梁赞诺夫有些草率。第二,请愿书中有与《论犹太人问题》相近的思想,尽管梁赞诺夫说马克思为特里尔的亲属起草了请愿书并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但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希尔施提出了一个更有分量的质疑,他说,马克思之所以告诉卢格自己愿意为犹太人写请愿书,是因为他支持犹太人的解放事业[7]。马克思并没有像西尔伯纳说的那样,不耻于在朋友面前提及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赫尔穆特·希尔施提出,马克思对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与对其政治命运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不能简单地因为马克思批判过犹太教,就认为马克思敌视犹太人,更不能因此把马克思归为“反犹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个从青年黑格尔派阵营中成长起来的理性主义者,他对于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没有好感。这是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大气候造成的,不能因此得出马克思敌视犹太人。希尔施还找出证据证明,马克思事实上并不敌视犹太人。马克思对斯宾诺莎充满了好感,对于犹太人拉萨尔去世深表惋惜。这些生活中的细节都表明,马克思对犹太人也并不像西尔伯纳所说的是一味的憎恨[8]160。希尔施还提出,马克思在政治上对于犹太人的解放事业一直都在竭尽全力地支持。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古斯塔夫·菲利普逊、萨缪尔·希尔施以及加布里尔·里瑟尔对鲍威尔的斗争,为犹太人的解放事业摇旗呐喊。为了支持犹太人的政治权利,马克思不惜激烈反驳自己曾经的师友,直至与自己的老师反目成仇。这表明,马克思对于犹太人的诉求并不像西尔伯纳所说的一无所知,相反,马克思一直关心犹太人的政治诉求,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希尔施通过这些材料证明,把马克思定位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反犹主义者”(an outspoken anti-semite)从而丑化马克思的做法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他在《丑陋的马克思:对一个“直言不讳的反犹主义者”的分析》中提出,“在将来,没有哪个哲学文库会认为马克思在评论文章《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一个血腥的梦想——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的世界,我们对此满怀信心。”[8]162
二、学术史上争论的第二个焦点问题:马克思对“日常的犹太人”的批判是针对犹太人的,还是针对市民社会的
关于这个焦点问题,尤里乌斯·卡勒巴赫与盖瑞·奥尔格尔的交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尤里乌斯·卡勒巴赫同样是犹太人,他写出皇皇巨著《卡尔·马克思与对犹太教的激进批判》,试图把马克思钉在反犹主义的耻辱柱上。卡勒巴赫虽然注意到了马克思支持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但是他认为这是马克思选择了“政治解放”这一概念之后不得不做出的让步,“像阿维纳利和麦克莱伦那样证明马克思捍卫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并不十分正确,这一点将会变得很明显。马克思的政治解放概念使得他不可能排除市民社会的任何一分子,这样说才更正确。”[9]165他还提出:“如果马克思在第一篇文章中很大程度上强调的还是他的方法的普遍性,因为他把每一个论证都从犹太人扩大到基督徒、宗教徒身上,他在第二篇文章中的方法就大为不同了,因为他在这里尽管也说了些关于货币的事情,主要考虑的还是‘现实的’犹太人。”[9]170卡勒巴赫认为,马克思对“‘现实的’犹太人”的批判暴露了他对作为一个种族的犹太人的敌视。他说:“如果马克思把他对犹太教的分析局限在社会议题上,那么,下面这些主张:马克思真正谈论的是商业社会,犹太教‘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很少的宗教内容,其种族内容甚至更少’,马克思只是在‘嘲弄鲍威尔’,或许还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分析犹太教的‘社会意义’。他明确支持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对犹太教和犹太历史的批判,而且加入了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甚至更加傲慢,而且肯定比他的前辈透露出更少的善意。”[9]170
为了把反犹主义的罪名加到马克思头上,卡勒巴赫还把马克思与希特勒捆绑在了一起,这才是这本书能够在同类著作中垂范的原因。他说:“马克思的第二篇文章和路德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看法有相同的品性。和他们一样,马克思对犹太教知之甚少,而且很少关心经验现实。路德想要改变(convert)犹太人的信仰;马克思想要消除(abolish)犹太人;希特勒想要驱逐(expel)以致剪灭(exterminate)他们。马克思是路德和希特勒之间不可或缺的逻辑链环。他传递出的很多观点都可以在希特勒的观念体系中找到。”[9]352必须指出,卡勒巴赫如果要在三个相距四百年的人之间搭建思想桥梁,他必须做谨小慎微的思想史考察,而不能以一句“马克思的很多想法在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中都能找到”这种捕风捉影式的总结就把马克思和纳粹元首用“逻辑链环”捆绑在一起。事实上,稍微翻阅一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就能很轻易地发现,希特勒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张解放犹太人。希特勒写道:“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将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永存的自然,凡是逾越其命令者势必将与以前严厉的惩罚。所以,我发信心,谨遵造物的意旨;和犹太人斗争,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10]在希特勒的思想中,马克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太人,是他要消灭的对象,而且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都是他要根除的对象。
面对卡勒巴赫的批评,盖瑞·奥尔格尔作出了非常有启发性的辩解。奥尔格尔并没有过多地纠缠于卡勒巴赫的论证细节,而是抓住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所一直批判的“日常的犹太人”?马克思之所以一直饱受包括卡勒巴赫在内的学者诟病,就是因为他严厉地批判了“日常的犹太人”,马克思批判“日常的犹太人”的言辞被视为他敌视犹太人的铁证。奥尔格尔抓住重点,直击卡勒巴赫所有论证的要害。
奥尔格尔指出,马克思看到像鲍威尔那样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一个纯粹的宗教问题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彻底抛弃了鲍威尔思考问题的路子。鲍威尔认为犹太人的全部本质都在宗教信仰上,他所关注的其实只是“安息日的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犹太人有着更加丰富的生活,他们的宗教信仰的根源也在于这种生活。所以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命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但不是像鲍威尔那样,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考察日常的犹太人”[11]49。这个命题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思考犹太人问题的整个思路都已经发生改变。因此,任何一个试图理解马克思的学者,都必须牢记这种转变。奥尔格尔指出:“在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现实的、日常的犹太人与安息日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是犹太精神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后一种关系是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卡勒巴赫想要从字面上理解‘犹太人’和‘犹太教’。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理解‘真实的、日常的’犹太人。对于马克思来说,‘现实的’犹太人是揭开宗教面纱的分析产物。但是当神秘的外壳消除以后,我们所看到的无非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马克思之所以能把分析往前推进,并不是因为他抓住了犹太人,而是因为他抓住了市民社会中的资本家。”[12]247对照马克思的原文,奥尔格尔的观察无疑是正确的。“日常的犹太人”是一个有着明确内涵的概念,它与“安息日的犹太人”有着明确的区别:“安息日的犹太人”是一个宗教概念,它指的是信仰犹太教的人;“日常的犹太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指的是以赚钱牟利为最高追求的人。综合《论犹太人问题》全文来看,马克思对“日常的犹太人”的批判是一个以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为指向的批判,与其说马克思敌视的是犹太人,不如说马克思敌视的是市民社会中人与人相互敌对的生存状态。如奥尔格尔所理解的那样,正是因为看到理解市民的切入点是“私人”,马克思才把关注的焦点从“安息日的犹太人”转向“日常的犹太人”[12]248,这一转变让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中异化的“最高的现实表现”:自私自利的经商牟利行为。马克思关于消灭经商牟利及其存在的前提从而实现人的解放的主张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做出的。
三、《论犹太人问题》支持犹太人获得“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
《论犹太人问题》是一篇政论性论文,马克思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是批判德国当时的犹太人政策,为德国犹太人的解放事业鼓与呼。1842年,德国政府企图恢复中世纪的犹太人同业公会制度,试图一劳永逸地把犹太人与基督教社会隔离开,拒绝承认犹太人的公民权。这是一项非常倒退的复辟政策。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旗帜鲜明地支持犹太人的解放事业,反对德国的复辟制度。在当时的报刊文章中,支持政府行为的是《科隆日报》及其主编海尔梅斯,反对政府行为的主要是《莱茵报》。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就曾经多次撰文批判海尔梅斯的保守言论和德国政府的保守法令。在《莱茵报》被查封之后,马克思又在《德法年鉴》上批判德国的犹太人政策。正是得益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进步学者的批判,德国政府才最终放弃了设立犹太人人同业公会的设想。马克思的论文为德国的犹太人解放事业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论犹太人问题》是一篇论战性的著作,马克思选择的论战对象是布鲁诺·鲍威尔。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是,只有当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放弃了宗教信仰,犹太人才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为了反对鲍威尔的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谬误,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德国的犹太人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们要求的是“政治解放”。法国和美国都已经完成了犹太人的政治解放,那里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依旧保持着各自的信仰,这个现实的例子表明,“政治解放”并不需要以放弃宗教信仰为前提。这证明了鲍威尔的主张是错误的。马克思指出,完成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犹太人生活于其中的国家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德国为例,德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政治生活受宗教的限制和束缚,所以德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从宗教出发,公民权利偏向于基督徒,不信仰基督徒的人都会受到排挤和压制。实现德国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就是把国家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建立像美国一样的现代国家,确保犹太人和基督徒享有同等的权利。
马克思提出,完成“政治解放”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在此之后还需要推进“人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完成之后,国家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社会并没有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社会生活中依旧存在各种各样的宗教。在马克思看来,“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4在“政治解放”完成之后,宗教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成为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还存在着宗教,这表明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还有没得到解决的苦难,所以才需要宗教这剂鸦片来抚慰创伤。马克思以解决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为出发点,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点。
从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消灭宗教,必须把社会从犹太精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为了找出宗教存在的根源,马克思从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转向考察“日常的犹太人”,并提出了“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11]49的论断。由此,马克思污蔑、敌视犹太人似乎就被坐实了。必须指出,如果忠实于马克思的思想并遵循马克思的文本顺序,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犹太人”并不是人种学或宗教学意义上的犹太人,而是以“经商牟利”为“世俗礼拜”的“犹太人”,即“日常的犹太人”,否则“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11]52的说法就无法解释。市民社会从自身内部不断产生出来的只能是“日常的犹太人”,这是马克思为了区别于宗教意义上的“安息日的犹太人”而创制的概念,其内涵是以经商牟利为世俗信仰的人,其外延是指现代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现代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被发财致富的梦想控制住了,为了发财致富而把其他所有人都视为手段,从而使得市民社会中人对人的关系变得如同狼对狼一样的关系。人在社会生活中感觉不到“类属性”带来的温暖,所以投身宗教的怀抱祈求上帝的关爱。马克思提出的从社会中消灭“犹太精神”的主张也不是针对犹太教的,马克思所说的“犹太精神”是为了发财致富不择手段的精神,这样的精神才是马克思所要最终消灭的。
四、反犹主义起源于资本主义的自我仇恨,《论犹太人问题》是犹太人的“福音书”
《论犹太人问题》是犹太人唯一可以期待的尘世的“福音书”,这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重要观点。他们认为,反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产生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之一,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简单地说,反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自我仇恨发酵而最终酿成的悲剧。《论犹太人问题》中“人的解放”的观点是解决“反犹主义”问题唯一可行的路径。
按照唯物史观的看法,思想观念是现实生活过程在思想中的表达,“反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心态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反犹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特定发展阶段及其孕育的知识、心理、文化密切相关。首先,在经济基础的层面上,资产阶级之所以打出“反犹主义”的口号,是因为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需要把自己打扮成与工人处于同样地位的生产者,并不断强化这种意识形态。“劳动契约的真实本质以及经济体系的贪婪本性”在资本家也在从事生产劳动的意识形态之下被掩盖起来了。犹太人参与其中的流通领域被宣传为剥削的根源,所有阶级在经济生活中遭受到的不公最后都追究到了他们身上。他们认为,反犹主义可以视为资本主义社会投射到犹太人身上的自我仇恨,犹太人不遗余力地传播、推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成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替罪羊:“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不同的国家,同时也把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的仇恨集中到了自己身上。”[13]160其次,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反犹主义之所以能发展到把残害、焚烧其他有生命的人作为一种发泄乃至娱乐,是因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削弱了人的“反思能力”。“由于大工业利益集团通过消除独立的经济主体,通过替代经营自主的商人,通过把工人变成工会的对象,彻底摒弃了道德选择的基础,因此,反思也不得不一步步走向萎缩,而可以带来自我罪责意识的灵魂,也会遭到彻底破坏。”[13]183按照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观点,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延续,犹太人或者和犹太人有相似处境的群体必然会成为迫害的对象。要想根除“反犹主义”的精神疾病,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具有反思行为的认知模式。只有这样,人才能从敌对的种族发展成为一个类,建立起人类社会。把人从相互敌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消除经商、货币和资本对人的奴役,这恰恰是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最为重要的主旨。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也提出,在现代的市民社会中,“人的一切类联系”都被扯断了,“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11]54。“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11]54,所谓“犹太精神”就是指以挣钱为最高目标的精神,犹太人因为掌握了金钱的势力,所以在经济领域已经解放了自己,但是政治权利一直受到限制,所以在现代的政治国家中,犹太人掌握的金钱越多,他们越容易成为其他民族砧板上的“鱼肉”,“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11]50,在“犹太精神”的驱动下,其他民族对犹太人所掌握的金钱帝国很难无动于衷,犹太人遭受洗劫甚至迫害在所难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把现代社会从犹太精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11]55,只有社会中的人不再受犹太精神的控制,不再把获取金钱作为最高目标,作为商业民族的犹太人在现代社会才能安心地生活下来。正如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才真正指出了消灭反犹主义的根本途径,即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3]184。《论犹太人问题》不仅不是反犹主义的“檄文”,反倒是犹太人唯一可以期待的尘世的“福音书”。
五、小结
《论犹太人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为犹太人的解放事业鼓与呼的一篇论文,在历史流转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反犹主义”的恶名被加到了这篇文章上面,并附带着让整个马克思主义都背负上了“反犹主义”的罪名。其结果是,过去100多年的学术史中,研究《论犹太人问题》的学者总是无法摆脱马克思主义与反犹主义关系的争论。当然,谁都无法否认《论犹太人问题》激烈地批判了犹太人和犹太教,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和犹太教,否则,“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11]50,“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11]52之类的论断就成为无法理解的了。事实上,马克思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答案——“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11]55——为现代社会解决犹太人问题提供了唯一可行的道路。正如阿兰·巴丢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IS的恐怖主义是在中东国家试图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享受与西方人一样的高品质生活的努力失败之后衍生出来的愤怒。这种新型的法西斯主义的根源,表面上看起来是宗教引起的,其实根源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14]。跳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言,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现代社会中的货币拜物教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在当代也具有积极价值。
[1]LEWIS, B.. Semites and Anti-Semites: An Inquiry into Conflict and Prejudice[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112.
[2]BERLIN, I..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99.
[3]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M]. 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73.
[4]MARX, K.. Early Writings[M].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 B. Bottomore, Forword by Erich From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3:V.
[5]AVINERI, S.. Marx and Jewish Emancipation[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64(03):445.
[6]SILBERNER, E.. Was Marx an Anti-Semite?[J]. Historia Judaica, Vol.11, 1949.
[7]HIRSCH, H.. Karl Marx und die Bittschrift für die Gleichberechtigung der Juden[J]. Archiv für Sozial Geschichte, VIII Band, Hannover: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Zeitgeschehen GmbH., 1968:229-245.
[8]HIRSCH, H.. The Ugly Marx: Analysis of an “Outspoken Anti-semite”[J].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vols.2-4,1977-1978.
[9]CARLEBACH, J.. 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10]HITLER, A.. Mein Kampf [M]. fully annotated by John Chamberlain & Sidney B. Fay etc.,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1:84.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ORGEL, G. S.. Julius Carlebach, 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J].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21 ,1980.
[13]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4] 阿兰·巴丢.“文明”世界病入膏肓的真相——为什么一个月就忘了巴黎?[J/OL].(2015-12-16)[2016-03-10].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51216131498.html
责任编辑李兰敏英文审校孟俊一
On the Thought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Marx and Anti-Semitism——A New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 the Jewish Question” and Anti-Semitism
LI Bin-bin
(College of Marxism, Central CPC Party School, Beijing 100091, China)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s not an Anti-Semitism paper, and Karl Marx was not Anti-Semite, either. What Marx criticized in this paper is not the religious belief of Jews but their “civil society”, where “Judentum” led to their ultimate goal of making fortunes and to the persecution on those who have controlled a huge business world. In other words, Marx did not criticize “the Sabbath Jew” whose essence was religious belief, but “the private individual” whose supreme pursuit was his or her “self-interest”. “On the Jewish Question” proposed the reform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it is the only “Gospal” that Jewish people can rely on.
Anti-Semitism; Everyday Jew; Sabbath Jew; religious belief
1001-733X(2016)02-0033-08
2016-01-2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神圣家族》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5CKS001)、中央党校校级课题“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李彬彬(1983-),男,河南息县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早期思想。
A12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