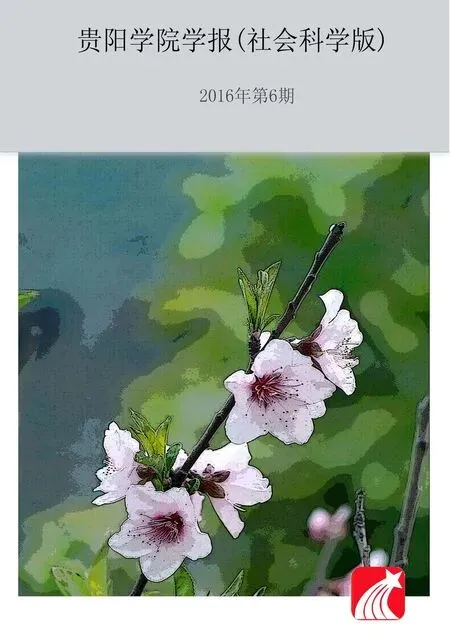略论“包容型”刑法文化的特征与意义
陈 鸿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略论“包容型”刑法文化的特征与意义
陈 鸿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包容型”刑法文化是一种涵容善良仁爱的群体化刑法精神模式,也是一种特殊的教化公民、预防犯罪的过程。谦抑性、人道性、和合性是包容型刑法文化的基本内涵及特征。弘扬“包容型”刑法文化,有利于我国公民更深入认识刑法的精神实质,有利于我国社会稳定、民族兴旺与国家强盛,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包容;刑法文化;谦抑性;人道性;和合性
刑法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刑法领域的体现,是国家相关法律设施、刑法规范等外化法律实体的内在精神部分,具体地表现为一个国家的犯罪观与刑罚观。不同的刑法文化孕育着不同的犯罪观、刑罚观。犯罪观、刑罚观影响甚至决定犯罪预防与控制的不同方式,从而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制与刑事政策。综观当前刑法文化领域,国外的刑法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人权型刑法文化、经济型刑法文化、专政型刑法文化;在我国,传统的刑法文化主要有工具主义刑法文化、重刑主义刑法文化、泛道德主义刑法文化,也存在“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刑法文化。但无论是中国传统刑法文化还是西方社会的刑法文化,其所彰显的不外乎人类共同的东西——人性以及不同国度与民族中特色的东西——习俗。在当今国际关系日趋复杂的环境下,在人们对传统封建的重刑型刑法文化与现代西方双重标准的人权型刑法文化都开始质疑的情况下,笔者以为,“包容型”刑法文化是当今社会刑法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我国刑法文化的时代注脚。
一、“包容型”刑法文化的特征
笔者所称“包容型”刑法文化,是指注重谦抑性、人道性、和合性的刑法之群体性精神模式,以及基于人权、人性的基本价值预设,以多元化、均衡化、人权价值最大化的原则教化公民、预防犯罪的过程。
(一)“包容型”刑法文化是一种涵容善良仁爱的群体化刑法精神模式
作为刑法实体的内在精神部分,首先,“包容型”刑法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群体化精神模式,亦即特殊的犯罪观、刑罚观及其方法论之体系。这种体系应当涵容善良仁爱,具有鲜明的谦抑性、人道性、和合性的内涵特征。
1. 刑法谦抑观—“对尽量少的人定罪处刑”
谦抑,亦即谦让、退却之意。所谓刑法的谦抑观(The principal of compress and modesty),按照通说,即指刑罚的必要性、非滥用性的基本观点。日本主观主义大师宫本英修博士在其专著《刑法纲要》中最早提出了刑法的“谦抑性”一词;在我国,甘雨沛教授和何鹏教授则最早提出了“收缩或压缩”刑法的刑法谦抑精神说。其后,专家学者对于谦抑性的论述渐趋系统化。我国当代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对刑法的谦抑性从立法角度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1]日本著名刑法学者平野龙一则从司法的角度阐释了刑法的谦抑性,他明确指出:刑事制裁的成本要高于其他任何制裁方式的成本,因此,“即使刑法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罚的补充性或者谦抑性。”[2]
“包容型”刑法文化的谦抑观,主要表现为对刑罚对象范围的包容(宽容)——“对尽量少的人定罪处刑”,亦即让尽量多的人被包容在正常社会成员之内,被排除在刑罚对象范围之外。其一,从刑法与他法的关系看,刑法是一个国家其他所有法律的保障法,是(非战争时期)维系与规范社会基本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说,只有在对于那些社会秩序—法秩序侵犯行为人缺乏更好的遏制办法时,才不得不搬出刑罚这尊大神。刑罚用得太滥,也就不神了。其二,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犯罪行为是行为人在其“病态心理”驱动下实施的一种“病态”行为。对于“病人”,最好的办法不是将这个“病人”一棒子打死,而是设法找到其病因,然后因病施治。亦即应给予法秩序侵害行为人一个“治病”机会——改过自新的机会,一个尽量好的“治病”环境—非监禁的环境。其三,从刑罚功能本身看,刑罚阻止犯罪、预防犯罪功能有限。刑罚本身就是一种国家之恶,刑罚具有明显的正反两面性。正如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所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3]用得适度得当,刑罚是阻止犯罪、预防犯罪的正能量;用得不当,刑罚是弊大于利的有害社会负能量。不容否认,如何正确把握刑罚的度,是现实社会中的难题。中外历史证明,刑罚的不当,即刑罚的过厉过滥或者过缓过少(更多的是前者),往往给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明显的消极影响。
“对尽量少的人定罪处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尽量少的人定罪”。对于犯罪证据不足,尤其是犯罪关键证据缺乏者,坚持“疑罪从无”;对于符合刑法形式犯罪构成,但是主观恶性较少、“情节显著轻微”者,不以(或不宜)犯罪论处。其二,“对尽量少的人适用刑罚”。亦即对于被判决有罪者,刑罚是重要选项但非必要选项。对于轻微犯罪者以及后果不是十分严重的过失犯罪者,只要悔改态度好、不具备再次犯罪危险或者犯罪能力,获得受害方谅解的,应以非刑罚方法处置。诚然,此种“对尽量少的人定罪”、“对尽量少的人刑罚”之刑法谦抑观,亦为刑法之善的表现。
2.刑罚的人道观—“对犯罪人适用尽量轻缓之刑”
人道(humanity),顾名思义,即关爱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与价值的道德。人道观,或称之为人道主义(Humansnistas),亦即注重人的本性、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之观点。苏联哲学家布耶娃认为,“人道主义意味着‘人是最高价值这一原则’不容怀疑”。 1974年第15版的英国《新大英百科全书》写道:人道主义是一种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的概念。把人和人的价值放在首位意味着“生存主义的第一原则”[4]。
“包容型”刑法文化的刑罚人道观,是指在刑事法律之制定与适用过程中,注重如下三大体现:体现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最基本权利的尊重,将其放在首位;体现人的可塑求变、趋利避害属性即人性之基本规律,弘扬人性的积极面并抑制人性的消极面;体现人的追求成功之价值属性,弱化刑罚的惩戒功能并强化刑罚的改造功能。概言之,刑罚人道观表现为对犯罪人处罚程度的包容—“对犯罪人适用尽量轻缓之罚”。所谓轻缓,一是厉度的轻缓,尽量不判死刑、坚决避免酷刑;二是速度的轻缓,尽量避免超短自由刑,适度延长重罪的自由刑;三是环境的轻缓,适度扩大缓刑、管制以及监外执行。此谓刑罚之仁。
(1)原则上反对死刑
死刑是对人的最重要、最基本权利的践踏,是对公正与社会契约的违背。其一,死刑并不能产生最佳威吓效果。从对人的心理威慑效果看,刑罚的延续性远过于刑罚的严厉性。其二,死刑使得错误的审判完全失去纠正的机会。自从刑法诞生以来,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与地区能与错误审判绝缘。另一方面,“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而求荣”[5]。一个人因为过错或者罪恶而受到一定惩罚时,其本身往往具有进取、求荣的内在动力,但是一个死刑却一次性剥夺了其全部机会。从这个角度看,死刑无论误判与否,都在相对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正义的实现。因此,“当死刑不是必需时,它是非正义的”[6]。其三,死刑会毒化人们的心灵。死刑会引起人们对犯罪人的同情,会强化人们尤其是犯罪方“冤冤相报”的仇恨心理。
(2)坚决禁止酷刑
酷刑,既造成人的身心极大痛苦,也是对人的健康权的严重侵犯、对人格的极端侮辱。因此,刑罚的人道观旗帜鲜明反对酷刑。其一,反对刑讯逼供。正如贝卡利亚所言,这种方法能保证强壮的罪犯(能够经受酷刑而不招)获得释放,使软弱的无辜者(经受不起酷刑而屈打成招)被定罪处罚。因此,刑讯逼供除了对人身心的伤害,就是冤假错案的温床。其二,反对严酷刑罚。一方面,酷刑之刑罚并不能更好地控制与预防犯罪。“严刑峻法不仅不能有效遏制犯罪,而且还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7]。另一方面,反对酷刑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1984年召开的联合国反酷刑大会明确声明:“没有什么例外情况可以使酷刑成为一种正义的行为,无论是战争状态,还是战争威胁;无论是内部的政治动荡,还是任何公共的紧急事件。”而且,大会制定的《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于1984年10月开始实施,于1988年11月3日在我国生效。
(3)适度扩大缓刑、管制等环境轻缓刑
我国刑法第67明确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如果确有悔罪表现,且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适用缓刑。对于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短期自由刑适度扩大缓刑、管制刑以及特殊情形下的监外执行,不仅可以节省国家的经济开支与司法资源,更重要的在于可以让缓刑犯避免监所的“交叉感染”,可以继续与亲人在一起,这些均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国内外有关资料研究表明,被执行缓刑等环境轻缓之刑者,其再犯率普遍较低,具有较好的社会效应。
(4)尽量避免超短自由刑,逐步增加长期刑
笔者以为,超短自由刑不利于罪犯的改造。主要依据有二:其一,超短刑期并不人道。人道人道,人性之道。刑罚的人道,不但注重人的尊严与价值,还在于合乎人的本性。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之基本表现。超短的自由刑并不能让犯罪人感觉服刑是明显的害,并不感觉服刑是太大的代价,因此其规避犯罪之意识同样不强烈,不利于改造。其二,超短刑期堵塞了犯罪人改造的时空与过程。在当今的各类犯罪中,绝大多数属于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在犯罪人的“病态心理”或者极端思想引导下出现的极端行为。而人的病态心理或者极端错误思想的转变是一个渐变过程,需要时间的磨合。因此,十天半月、一月两月等超短刑期对犯罪人的改造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国家在杜绝死刑、酷刑的同时,应严格限制超短自由刑、增设限制减刑的长期刑以及终身监禁刑、从严把握重罪的减刑、假释的程度与速度。2015年11月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在贪污罪、受贿罪的处罚中增设了终身监禁刑,显然是我国刑罚改革的一个良好开端。
3.刑法的和合观—“对所有犯罪人处施尽量促生罪刑”
和者,相应、相配之意;合者,结合、相生之谓。所谓刑法的“和合观”,亦即坚持和合协同、有序对称、整体和谐、融合出新的罪刑观。 “和合辩证思维是中华文化之根”[8],也是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精神的体现。概括说来,刑法的和合观主要表现为对定罪处刑施刑科学性的包容——“对所有犯罪人处施尽量促生罪刑”。所谓“促生罪刑”,就是“罪刑适宜,由刑促生”,亦即通过一个“弘扬公正、合乎情理、注重过程”的罪刑配置、实施体系,促使犯罪人中的尽量多数真心服法,诚心服刑,致力改造成社会新人,获取新生。此为刑法之良,亦涵刑法之爱。具体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1)和合立法观
立法的和合,主要在于罪名的完善以及罪与刑的合理对应。其一,罪名应当全面完整覆盖现有各种危害行为。或者说,任何一种严重社会危害行为都有一个罪名与之搭配对应,从而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其二,轻重罪名与不同刑种、刑度的合理对应。应当针对不同的罪名、不同危害结果、不同主观恶意程度做到调配合理度、实用度的最大化,从而做到“罪刑对价,轻重有别,严而不厉,简而不繁”。其三,注重过程的体现。勿需置疑,罪犯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刑法的完善发展也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死刑的废除、自由刑期的延长,不能一步到位,不能大跃进,应当根据国情循序渐进。应该说,我国刑法从1979年第一版的100多个罪名到1997年第二版的400余个罪名,从第八个刑法修正案后的450余个罪名到第九个刑法修正案后的460余个罪名,以及兜底性罪名的出现等,表明我国在罪名的系统完善上,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的进步。另外,随着刑罚的不断修正,保留死刑的罪名从1979年的68个减少到第八个刑法修正案后的55个,再到第九个刑法修正案后的46个以及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行贿罪等个别罪名量刑的适度加重,表明我国罪刑调配的合理性得到了增强。但是,与美国、德国等发达法治国家相比,我国的刑事立法在罪名的无缝对接、处罚的简约科学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和合空间。
(2)和合司法观
在包容型刑罚观看来,司法的和合,重在“有据、有节、有情的融合”。其一,就法院来说,坚持“科学判决”。刑事案件的判决应严格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证据不足,应坚持“疑罪从无”;在犯罪事实清楚无误的前提下,除非属于绝对法定刑,量刑尽量不顶格判处,一个行为不管同时符合多少个罪名,均杜绝加重处罚、数罪并罚;对于危害较轻、善后工作尽心尽意,已经获得受害方谅解的情形,法院可以在双方取得一致的条件下,主持实施刑事和解;相反,对于罪行恶意很深、悔意不足、民愤甚大之人,即便其善钻法律之空子,也不能轻易让其逍遥于法网之外。法院的最终定罪量刑应当让犯罪人、受害人认为在理合理,口服心服。其二,就公安、监所来说,坚持“人性执刑”。首先,应当严格依据法院的判决执行刑罚,让犯罪人感受到服刑是自己所犯罪行的应有代价,这是必须明确的基本前提。必须避免“一味宽缓优待、甚至变相享受”的刑罚执行方式。痛苦与代价是犯罪人思想震动、转变的重要条件,只有必要的痛苦与代价,才能有效促使犯罪人“避犯罪之害,趋新生之利”;其次,刑罚执行部门必须避免简单的“冷、厉、压”方式,注重改善软硬设施,营造一个人性化的执法环境,充分利用刑法关于减刑、监外执行、假释等成文规定以及相关刑事政策;再次,充分利用社会关爱力量。“社会化是实现罪犯改造人性化的重要路径”[9],自始至终要充分调动犯罪人的亲朋好友以及社会诸方的关爱力量。通过上述人性化执刑举措,让犯罪人在服刑中充满动力,看到希望。
(二)“包容型”刑法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教化公民、预防犯罪的过程
1.文化的本质就是教化人的过程
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理解。其一,从实体层面看,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有形产品的总和。其二,从理论的层面看,文化是指一定社会的意识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的环境因素在人的观念上的反映,是一种由物及人的人化过程及其状态,主要包括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以及一切典章制度等。其三,从功能的意义上看,文化有如《周易》所云:“观乎天文以观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以“文化”来教化天下[10],在这里,文化就是一种管理手段,亦即通过既定的精神理念、价值观念来规范人、调控人、改变人,亦即教化人(化人)的过程。
2.“包容型”刑法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教化公民、预防犯罪的过程
刑罚,作为一种特殊典章制度,其判决与执行过程是一种特殊的“化人”过程。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刑法的实质就是儒家化的“伦理刑法”,“表面上为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以礼入法”[11],刑法之罚,其主要目的在于教化百姓遵守封建礼教秩序,服从封建统治。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刑罚制度本身则具有多种积极功能,其中教育改造功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包容型”刑法文化氛围凭其谦抑性、人道性、和合性的特点优势,有利于导引公民遵纪守法,有利于增强犯罪人服刑改造的内在动力,更好更快地将罪犯教育改造成社会新人(教化人)。
二、“包容型”刑法文化的意义
(一)“包容型”刑法文化有利于人们更深入认识刑法的精神实质
刑法现象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意识现象与过程,要认清其精神实质,有赖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从结构层面看,刑法可以分为显性层次与隐性层次。通常人们直观的刑法立法机构、司法部门以及现成的刑法条文及其解释,只不过是刑法的外化、物化部分—显性层次,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最多也就是“知其然”的浅层面,由此产生的诸如各种立法问题、司法问题或困惑并不能得到很好解决。有专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外化物化的刑法就好像木偶,而刑法文化才是木偶表演后面的提线与操作者。也就是说,刑法文化是刑法的隐性部分,只有通过它才能了解刑法内在运作机制与规律,才能把握刑法认识与实践的精神实质与核心灵魂,进而让人们“知其所以然”。建立在中外刑法文化比较与我国国情基础上“包容型”刑法文化,自然有助于人们认识刑法的精神实质及其运行规律。
(二)“包容型”刑法文化有利于社会稳定与民族兴旺、国家强盛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复杂期、风险积累期。期间,随着经济的社会化、人口的城市化以及交流的信息化、自由化,诸如单位、户籍等传统社会控制手段逐步弱化甚至失灵,而新的社会治理与管控模式尚未完全建立;另一方面,公民收入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国外敌对势力十分猖獗。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小小问题,处置不善,往往演化成一个破坏性巨大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独狼”现象,[12]从而导致各类犯罪现象高发。如何善处当今高发的各类犯罪?无疑,在非战争时期,刑法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最重要手段。然而,无数事实表明,一味的酷刑、死刑,或许能够短期治标,但绝对不能治本。即便是我国1983年开始布署的定期“严打”(从重从快严厉打击重大犯罪)运动,其稳定社会的边际效益快速下降,甚至出现弊大于利的状况。依据1983年~2001年《中国法律年鉴》统计,1982年至1986年,全国公安刑事立案从748476起降到547115起;但是1987年突升至827594起,以后一直在高位徘徊,2001年高达4457579起。因而,重刑、酷刑、滥刑等等,都不是解决高发犯罪问题的最好办法。尽最大可能保护绝大多数,坚决处置穷凶极恶的一小撮,尽最大努力分化、改造犯罪者中的最大部分,这才是解决高发犯罪问题的有效举措。而这,正是“包容型”刑法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包容型”刑法文化通过对刑罚的谦抑、人道、和合的阐释,让公民充分认识到基本刑罚的必要性、代价性,从而努力避免犯罪,尤其努力避免犯重罪;也让犯罪人认识到刑罚的必要性、有限性以及执刑过程的人道性,从而增进对服刑的理解,使其在服刑中看到希望,进而专心于劳动改造,早日成为重新适应社会、有益于社会的新人,降低再犯率。因此,“包容型”刑法文化对维护、促进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历史证明,包容型刑法及其执法理念有利于民族兴旺、国家强盛。一方面,我国历史上两个大一统的短命王朝,其短命大都与暴政、酷刑相关。一是秦朝。从秦始皇首建大一统到秦二世亡国,总计不过15年时间。期间,“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以刑杀为威”[13](秦朝的此种做法还成为汉初统治者认定为秦二世亡国的教训[14])。二是隋朝。从隋文帝杨坚强势建国,到隋炀帝杨广被杀亡国,也仅有37年时间。虽然隋炀帝改革失去地主贵族集团支持,是其亡国的重要因素,但是隋炀帝重役、酷刑、滥杀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执政方式让其彻底失去民心,是其灭亡的根本性原因。比如在平定杨玄感时竟认为:“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15]。另一方面,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大盛世王朝。虽然“盛世”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翻开我国的法律思想史不难发现,我国的每一个盛世,都与谦抑、人道的刑法思想与执法理念有着直接的关联。汉代“文景之治”期间,汉文帝先后废除了残忍的因言论而治罪的“诽谤妖言法”、因一人犯罪而株连九族的“相坐法”,汉景帝废除了夏商、秦朝以来的酷刑用具,引领了执刑人道化的改革;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期间,从唐太宗到唐玄宗,都信奉“以仁为本,以刑为末”的刑罚理念;至于清朝的“康乾盛世”及其延续,诸多学者以为,康熙及其以后皇帝倡导的具有前瞻性、开创性的“罪疑惟轻”的刑罚思想以及“以德化民,以刑弼教”[16]的刑法理念功不可没。
(三)“包容型”刑法文化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社会主义法治是人民民主的法治。人民依法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是法治的目的和核心内容,这里就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公民的民主法治素养问题。公民没有良好的民主素质与法律素养,法治国家只是一纸画饼,一幕海市蜃楼。公民良好的民主法治素养包括树立良好的法律理念、法律思维习惯以及良好的法律运用操作能力。首先,公民必须树立良好的法律理念、法律习惯,这是基本前提与关键所在。人是理解的动物、机会主义的动物,只有懂得法律的重要,人才会去学法、用法。而法律文化通过法律内在精神本质、基本功能的探究,可以让公民真正懂得法律(良法)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发展规律,进而逐步树立起法律意识、法律理念、法律习惯。其次,公民必须具备良好的法律运用操作能力。法律文化通过不同法律的比较,通过法律的宣传普及,营造一个法律的氛围。这个氛围,有利于促进公民自觉、不自觉接触法律、学习法律、熟悉法律、运用法律。刑法,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作为其他所有法律的保障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包容型”刑法文化有利于加深公民对国家现行刑法的理解,有利于加深对国家刑事立法、司法改革的理解,其对培养公民法治素养的积极作用不可或缺。
[1]陈兴良.刑法的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
[2](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6.
[3]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0.
[4](法)萨特.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30.
[5]商鞅.商君书.算地第六.古诗文网[EB/OL].(2013-11-19) [2106-11-01]http://www.gushiwen.org/guwen/shangjun.aspx.
[6]林海.贝卡利亚.向酷刑与死刑宣战的意大利贵族[J].法律与生活,2015(13):51.
[7]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59.
[8]左亚文.和合思想的当代阐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17-218.
[9]李雪峰,范辉清.人性化—罪犯改造理论的基石[EB/OL].(2014-10-26) [2106-11-01]http://blog.163.com/xuefeng,2014.
[10]刑法基础理论探索[M].赵秉志,主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64.
[11]任喜荣.伦理刑法及其终结[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1.
[12]陈鸿.当前我国暴恐犯罪的新特点及其应对[J].广州大学学报,2016(8)34.
[13]杨永泉.两汉以学社会批判愢潮管窥[J].南京社会科学,2008(6):52.
[14]张武举.刑法的伦理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45.
[1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2[EB/OL].(2013-07-27) [2106-11-01]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1zztj/179.htm.
[16]陈鸿.略论刑法特性与社会和谐功能[J].政法学刊,2007(12):39.
[责任编辑 何志玉]
On the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of “Tolerance” of Criminal Culture
CHEN Hong
(Guangdong Justice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510520, Guangdong, China )
The “tolerance” of criminal culture is a group spirit mode of criminal law which is featured with kindness and benevolence. It is also a special process of enlightening citizen and preventing crime. Modesty, humanity and harmony are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lerance” of criminal culture. To promote the “tolerance” of criminal culture will be propitious for the citizen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criminal law, for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f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goal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ruled by law.
tolerance; criminal culture; modesty; humanity; harmony
2016-10-10
陈 鸿(1968-),男,湖南邵阳人,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与法律文化。
D914
A
1673-6133(2016)06-00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