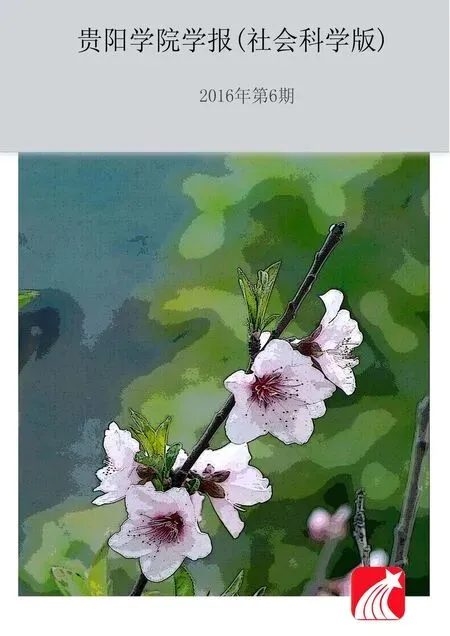“良知”的沦陷及其省思
——知识化解释的向度
李承贵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良知”的沦陷及其省思
——知识化解释的向度
李承贵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在20世纪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良知”的失落遭遇了一种意外的情形,即“知识化解释型失落”。但这种“知识化解释型失落”,不仅将科学知识与德性的复杂关系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且让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到“良知”本质,同时对于诠释的作用及如何应用诠释有了更为切实的觉悟。“良知”虽或蔽或放,但其体恒在,这或许正是科学知识与“良知”本有的情愫。因而人应该在正确理解与把握科学知识与“良知”的关系中,信守“良知”的本根价值。
良知;沦陷;省思;知识化解释
有一种德性既让人欢喜又让人恐惧,没有人不为被夸其有此德性而洋洋得意,也没有人不为被指其无此德性而羞愧难当,这种德性就是“良知”。在中国哲学史上,发明“良知”的老祖宗应该是孟子。孟子认为人先天即有良知良能,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但他发现“良知”有时也会失落,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这段话揭示了人爱财胜于爱德的心理,对于主张“舍生取义”的孟子而言,当然看不下去,所以在那里表现得无奈无辜的样子,似乎是他自己“放心而不知求”。孟子是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君子,对于为什么出现“放心”现象,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觉得还是“利欲”在那里捣鬼。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欲望很少,即使不努力保存良知,那也不会减少太多;相反,如果一个人欲望太多,即使努力保存良知,那所保存的良知也会很少。显然,孟子将“良知”的沦陷归于利欲的膨胀。这在提醒人们,拥有“良知”并免去失落“良知”的恐惧,减少或控制欲望是前提。孟子的这一思想,在一千七百年之后的王阳明那里被完整地传承下来。王阳明说:“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1]62-63这是说,“良知”虽然是普遍存在的,人人具有,但仍然会有被遮蔽的时候,即有沦陷的时候,而被遮蔽的原因是物欲,因而必须去人欲以存天理(良知)。王阳明说:“减得一分人欲,便复得一分天理。”(《传习录》上)可见,孟子、王阳明都认识到先验的“良知”会有沦陷的时候,但这种沦陷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隐而不现”,是“被遮蔽”,因为“良知”之体从来就没有沦陷过。而“隐而不现”的原因是私利欲望。这种“良知沦陷私欲说”是大家熟知的“经典”性判断,人们也因为这个判断而努力修养,以抵御利欲的侵袭而避免“良知”的沦陷。虽然孟子、王阳明都将这种沦陷定义为“隐而不显”,但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选择了利欲而放弃了“良知”,似乎不能说他还有“良知”。因此,孟子、王阳明的说法只能从本体意义上去理解,即“良知”虽然因为利欲而在个体的行为中沦陷,但作为本体的“良知”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诚如阳明所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但人不知存,则有时而或放耳;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有时而或蔽耳。虽有时而或放,其体实未尝不在也,存之而已耳;虽有时而或蔽,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谓良知亦有起处,则是有时而不在也,非其本体之谓矣。”[1]61-62换言之,“良知”有“体”“用”之别,作为“体”的“良知”是众善之源,而作为“用”的“良知”,既可能与“体”的“良知”完全等同,也可能与“体”的“良知”相悖,而表现“体”的“用”是多样的。这就意味着,“良知”的沦陷会有不同呈现。那么,除了“利欲型沦陷”之外,“良知”的沦陷还会有怎样的表现形式呢?
一、“良知”的认识论解释
所谓“‘良知’的认识论解释”,就是指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良知”进行解释。但在进行这种解释时,“良知”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良知”缺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支持,“良知”丧失了认识论语境中生存的知识根据,从而遭到驱逐。
1.“良知”否定了感性认识
依马克思主义知识论,任何思想观念或知识理论都来自感觉器官,即由感官这第一通道获得,世界上不存在不经过学习能获得的知识、不经过思考能得到的观念。不过,“良知”却是这样的知识或观念,所谓“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1]71。所谓“不由见闻而有”,就是说“良知”可以不通过感官便能拥有,这就意味着“良知”在马克思主义知识论中找不到根据,没有根据支持的“观念”当然就是不合法的,就是不存在的。侯外庐说:“既然‘良知’即‘人心’,为‘人人皆有’,那么,所谓在‘良知’上下功夫,必然不是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因而更不是向客观世界去探求事物及其规律的知识,而是一种放弃任何对自然与社会的斗争的方术,即神秘的、顿悟式的‘不假外求’与‘向内用力’的安眠剂。”[2]892在侯外庐看来,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知识”都必须通过感官获得,都是人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探索、考察、研究获得的。而且,由于“良知”在王阳明哲学中属于内在于人心的先验知识,因而即便在“良知”上用功,也与客观事物毫无关系,与生产实践、阶级斗争毫无关系。张岱年虽然不否认“良知良能”的存在,并正确地理解为道德意识、道德观念,但认为作为道德意识的“良知”不应是先验的,而应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他说:“良知、良心是应该肯定的。但孟子所谓‘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却不符合事实。人的良知、良心即是人的道德觉悟、道德意识,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认识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种社会性历史性的认识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道德意识、道德觉悟。具有这种意识,达到这种觉悟,谓之有良知、有良心。启发这种觉悟,培养这种意识,正是文化教育的任务。”[3]不难看出,张岱年所肯定的“良知”是经验的良知,是社会性、历史性的认识在人们头脑中积淀而形成的道德意识、道德觉悟。这当然不是孟子、阳明所讲的“良知”,是用经验的“良知”取代了先验的“良知”。萧箑父则认为,“良知”是认识秩序的颠倒,他说:“他(王阳明)通过片面夸大对于‘见闻’之知的指导作用,把‘良知’吹胀为可以脱离‘见闻’基础而独立自在的绝对,认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这就颠倒了认知次序;并进一步断言:‘良知之外,别无知矣。’这就用‘良知’代替了‘见闻’之知,把感性认识排斥在认识过程之外,割断了认识来源,使‘致良知’成为主观自生、随意扩充的神秘参悟了。”[4]128-129在这个评论中,感性认识与“良知”被对立起来,坚守感觉器官是获得认识的唯一通道,而“良知”并非来自这个通道,那么,“良知”就成了没有“出身”的观念,没有“祖籍”的观念,就是不存在的观念。
2.“良知”拒绝了客观对象
依马克思主义知识论,认识的获得必须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即客观对象的存在是认识产生的基本前提。但“良知”似乎不需要这个前提,它不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即“良知”的产生与有无客观对象没有关系。王阳明说:“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吾子所谓‘气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1]46这就是说,“良知”在心,完满自足,若是以为“良知”未足而向外求索方能丰满增益它,则是离心、理(良知)为二,因为学问思辨笃行所要做的,不过是获得“良知”、实践“良知”而已,因而“良知”之外还有什么知识可求的呢?既然“良知”自足完满,“良知”之外无知识,当然就无需向外求索;既然无需向外求索,也就意味着“良知”既不需要从社会中获得,也不需要从自然界获得。可是,依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知识必须从自然界求得,或从社会中求得,这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因此说,“良知”取消了客观对象,取消了获得知识的基本关系,即主客关系。侯外庐说:“认识不能离开‘客体’(客观存在)与‘主体’(人的思想意识)这两个方面,不能离开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斗争的实践活动。像王阳明那样,既用‘良知’并吞了‘物’,否认了客观存在,又把‘认识’规定为‘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的自我认识,难道这不正是取消了认识论问题而把人们引向蒙昧主义吗?”[2]893由于认识的产生是主体与客体张力的结果,是主观反映客观的结果,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否认了客观对象的存在,也就否认了认识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否认了知识的来源,否认了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因而萧箑父认为,“良知”就是切断了与外界联系的神秘知识。他说:“认识能力的取得,既‘非由于闻见’的经验积累,也非由于对‘事变’的‘预先讲求’,(《传习录》上)而是由于先验能力的自然流露。”[4]127既然“良知”不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不是从客观对象获得的知识,而是先验能力的自然流露,那么它就不能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语境中。因此,如果说任何知识的获得都来自主观对客观的反映,都来自主体对客观对象的求索,这就意味着,“良知”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语境中没有存在的合理性。
3.“良知”取消了实践标准
依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认识是否正确的检验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但“良知”自己就是标准,而且,“良知”之外再无别的标准。王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5]92“良知”是每个人心中先天具有的准则,是每个人言行的先天根据,也是判断是非的标准。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5]11既然人们为文学、出言谈的依据是“良知”,既然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是“良知”,既然“良知”之外再无标准,那么,认识是否正确并不需要放在实践中检验,事情的是非曲直也无需用实践来衡量。质言之,“良知”即是最高标准,是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根据。但依马克思主义知识论,一种认识是否正确,检验的方法与标准是实践,只有将认识置于实践中,才能验证其是否正确。因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言,第一,“良知”标准是主观标准论,即用一种观念判断另一种观念。萧箑父批评说:“以主观是否符合客观来判断是非成了‘乖谬’,而以客观是否符合主观标准来衡量是非反而成了‘真知’。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颠倒是非观。”[4]129既然“是非”的标准是观念,那就意味着“是非”没有现实的标准了。第二,从内容上看,“良知”属于道德标准,不属于知识标准。张岱年说:“王守仁认为,这良知就是道德行为的基础,依照良知做去,便自然合乎道德标准,因为一切道德标准都是从‘良知’出来的。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孝,见兄自然悌。’(《传习录》上)离开‘良知’就没有一切道德。”[6]371既然“良知”所判断的是道德上的善恶,那么,“良知”在内容上也构成了对认识论标准的否定。沈善洪、王凤贤说:“‘是非’是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指人们的某一判断是否合乎实际,或合乎某种原则,‘合则是,不合则非’。而‘好恶’即‘善恶’,则是伦理学范畴,表明人们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因此,这两者性质是不同的。判别‘是非’,唯物主义者依据是否符合实际为标准,客观唯心主义者则依据外部某种原则为标准。总之,都不是依认识自身为标准。因为依认识自身为标准,在逻辑上等于取消了标准。王阳明把‘是非’等同于‘好恶’,也就是用伦理学准则,取代了认识论上的准则。”[7]72在沈善洪、王凤贤看来,“良知”是非标准论,不仅有悖唯物主义的是非标准论,甚至连客观唯心主义是非标准论都不如,因为它们至少还有“客观的坐标”,而“良知”是非标准论是自己检验自己,将认识标准的客观性要求消融于主观观念之中,当然是认识标准的取消。质言之,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良知”标准论都是对实践标准的否定。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被尊为绝对的“真”和绝对的“善”的“良知”并没有其安身之地,因为“良知”本身即是需要检验的对象,“良知”能否存在取决于其在实践中被认可的程度。因而“良知”只是一种孤芳自赏的花朵,张锡勤说:“王守仁的良知说完全是神化自心,无限夸大人的认知能力。他把意识是人脑(心)的属性、机能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歪曲为吾心先天地具有先验之理、先验之知。王守仁正是在这一谬误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良知说。依据他的良知说,既然良知是世界的本原、完美的真理、唯一的真知,又是判断是非、识别善恶、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人们认识和修养的唯一工夫乃是‘致良知’。”[8]77这样,就认识检验标准角度言,“良知”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语境中也无法存活。
如上考察表明,依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良知”否认感官认识、否认认识对象、否认实践标准,而其内容又是道德伦理,正如张岱年所说:“王守仁取消了物的客观意义,取消了‘致知’的科学意义。这样的‘格物致知,也就是使自己的所思所念完全合乎封建道德的准则。”[6]369亦如张锡勤所说:“王守仁所鼓吹的乃是一种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在王守仁的认识中,心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认识对象,同时也是认识的标准,三者皆合于一心。他所谓的认识,不是主观认识客观,而是自心体悟自心。他使认识完全限制在主观的范围,实际上取消了认识。”[8]77因此,在马克思认识论语境中,不仅没有“良知”的位置,而且完全被驱逐出境,“良知”由此而沦陷。
二、“良知”的科学方法解释
所谓“‘良知’的科学方法解释”,就是指以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对“良知”进行解释。但在进行这种解释时,“良知”不能满足自然科学原理的要求,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良知”缺乏自然科学原理的支持,“良知”丧失了科学语境中生存的科学根据,从而遭到驱逐。
1.“良知”不合科学思维
按照科学知识产生的思维规律,归纳思维是基础性思维,就是说,任何知识的产生形成,基本都遵循从博到约、从杂多到归一的路径。但“良知”并不遵循这条路径,王阳明说:“‘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只是要存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真知便粗了。”[5]110就是说,“良知”的获得,并不需要满世界去求索,并不需要事事物物都去接触,并不需要任何现象都去钻研,因为“良知”就是一切知,并且在心中。不过,虔诚崇信归纳法的严复绝不承认世界上有归纳之外的知识,他说:“独至公论,无所设事。然无所设事矣,而遂谓其理之根于良知,不必外求于事物,则又不可也。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于此见内外籀之相为表里,绝非二途。又以见智慧之生于一本,心体为白甘,而阅历为采和,无所谓良知者矣。”[9]在严复看来,任何公理性知识都由归纳而来,因为归纳出来的公理是由杂多现象中抽出,因而它必须通过接触具体事物才完成,按照这样的科学理路,先天的“良知”自然被排斥。梁启超认为,“人性善”或“良知良能”是不是可信,并不能以孟子的讲说为据,也不能以宋儒的争论为凭。他说:“譬如说‘性是善’,或说‘性是不善’,这两句话真不真,越发待考了。到底什么叫做‘性’?什么叫做‘善’?两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说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说的义理咧、气质咧,闹成一团糟,那便没有标准可以求真了。”[10]795这就是因为孟子的讲说与宋儒的争论都不是科学根据,因而是不可靠的。那么,什么才值得信赖呢?科学精神与方法,因为科学精神的特质之一就是求真。因而只有根据科学思维、科学方法获得的认识才是可信的。梁启超说:“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的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杂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10]795所谓“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杂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所谓“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所谓“综合各部、各组研究的结果发现出各个体相互间的普遍性”,这就是归纳法。换言之,“人性善”或“良知”要被人们信奉并接受,必须告诉人们它是经由科学归纳得来的,反之,则是不可信、不存在的。可见,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将“良知”视为“公例”,而“公例”必须由归纳而得,必须求诸于具体的物事,但“良知”是天赋的,是排斥经验的,是无需通过从杂多中抽象出来的德性,因此,以“公例”性知识标准而言,“良知”以其不符合要求而遭到驱逐。
2.“良知”违背科学实验
根据自然科学精神与原理,任何学说或理论如要被人们承认和接受,必须能够被实验验证。但“良知”似乎不受此限制,王阳明说:“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议拟增损于其间也。”[11]969就是说,“良知”是绝对至善的,是圆融无碍的,是不可损益的。王阳明说:“手指有见有不见,尔之见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着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岂以在外者之闻见为累哉?”[5]122-123就是说,“良知”既无需见闻上说有,也无需实验上说有,因而在感觉上和实验上用功对“良知”的有无并无任何帮助,亦无任何意义,但若能在不见不闻中体悟“良知”,在戒慎恐惧中亲近“良知”,才是真正的工夫。不过,在崇信科学万能的思想家那里,这种排斥科学实验的“良知”是不可信的。严复说:“良知与元知绝异。穆勒之论乃辟良知,非辟元知。元知与推知对,良知与阅历之知对。”[12]严复所谓“元知”何意?“元知”即是感性认识,所谓“人之得是知也,有二道焉。有径而知者,有纡而知者,径而知者,谓之元知,谓之觉性;纡而知者谓之推知,谓之证悟。故元知为智慧之本始。一切知识皆由此推。”[13]作为一切智慧之本始的“元知”与纡而知者之“推知”都不能混淆,先验的“良知”更不能与后天的“元知”相提并论。所以严复也否认“良知”的存在。他说:“盖呼威理所主,谓理如形学公论之所标者,根于人心所同然,而无待于官骸之阅历察验者,此无异中土良知之义矣。而穆勒非之,以为与他理同,特所历有显晦、早暮、多寡之异;以其少成,遂若天性,其实非也。此其说洛克言之最详。学者读此,以反观中土之陆学,其精粗、诚妄之间若观火矣。”[14]在严复看来,呼威理(呼倚威勒William Whewell,英国人,哲学家,生于1794年,卒于1866年。约翰·穆勒
3.“良知”臣服科学成果
在信奉科学万能的思想家那里,“良知”必须承认并接受科学研究与发展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良知”是科学所揭示的某种自然现象进化的产物,而不是神秘的、天赋的德性,我们将此现象称为“良知臣服科学成果”。而这种“臣服”即意味着“良知”的沦陷。根据进化论思想、细胞学说,人的知觉和意识是人脑长期进化的结果。但“良知”似乎不存在进化的问题,“良知”是先天的,是本来就有的。王阳明说:“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裕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16]但在信奉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的思想家那里,先天的、自足圆融的“良知”是无稽之谈。孙中山说:“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动植物状态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议者,生元之构造物也。生元之构造人类及万物也,亦犹乎人类之构造屋宇、舟车、城市、桥梁等物也;空中之飞鸟,即生元所造之飞行机也;水中之鳞介,即生元所造之潜航艇也。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里氏发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后,则前时之哲学家所不能明者,科学家所不能解者,进化论所不能通者,心理学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贯通,另辟一新天地为学问之试验场矣。”[17]法国生物学家圭哇里(Carrel)认为,细胞如同蚂蚁、蜜蜂一样,带着与生俱来的机能,称为“预先的知识”。孙中山赞同圭哇里的科学成果,认为孟子的“良知良能”跟“细胞有知”说是一回事。在孙中山看来,“良知”就是“元知”,而“元知”是物质长期进化而形成的认识,因而不是先天的。其具体内涵包括:第一,生元是万物的始基,万物的存在及千姿百态乃生元所为;第二,“生元”之知乃物质长期进化而生;第三,知觉依“生元”而有,也依“生元”而无,因而“生元”之知并非永恒。按照孙中山的这个解释,“良知”就是“生元”之知,就是物质长期进化的产物,是依附于物而生者、感觉经验者。不过,“良知”与“元知”完全异趣。就是说,“良知”若被理解为“生元有知”,则不再有“良知”。与此同时,当时风行的进化论也成为“良知”的残酷杀手。由于进化论主张物质进化,精神也进化,“良知”也必须是进化的,若“良知”不能进化,或拒绝进化,说明“良知”与进化论相悖,与科学相悖。梁启超说:“盖以为道德者,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无始以来,不增不减,先圣昔贤,尽揭其奥,以诏后人,安有所谓新旧焉者?殊不知,道德之为物,由于天然者半,由于人事者亦半,有发达有进步,一循天演之大例。前哲不生于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复起,其不能不有所损益也亦明矣。”[10]217梁启超用进化论解释道德现象,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变化的事象,即便是道德现象也在一刻不停地变化,生灭存亡随时而现,因而也就没有不变、不灭的“良知”。这样,“良知”不得不消失于人们对伟大科学成果的惊人盲从之中。
可见,科学强调知识必须通过归纳方法获得,“良知”不能遵守此规则;科学强调知识必须接受实验验证,“良知”不能接受此要求;科学认为人的知觉和意识是经由长期进化而发生、成长的,而“良知”是天赋的;进化论主张知识是可损益增减的,“良知”则是圆满无缺的。显然,如果信奉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良知”就无法继续生存于科学语境中。
三、“良知”的阶级学说解释
所谓“‘良知’的阶级学说解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对“良知”进行解释。但在进行这种解释时,“良知”无法满足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要求,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良知”缺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支持,“良知”丧失了唯物史观语境中生存的理论根据,从而遭到驱逐。
1.“良知”否认时空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是历史的、具体的。“良知”作为封建社会意识也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换言之,“良知”只能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这就是它的时空特性或时空限制。可是,“良知”偏偏是无定所、无定时的。王阳明说:“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1]74就是说,“良知”扎根人心,充塞宇宙,它是普遍的、超越时空的,既无主体之别,亦无时空之限。王阳明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1]79而且,“良知”若发用流行于宇宙,其效应是“欲释蔽开”,世界大放光明。王阳明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1]69可见,无论是就性质,还是就功能言,“良知”都表现为超时空性。不过,李大钊不能认同这种没有“户口”的“良知”,他说:“良心之起,对于他人全不知觉的事也起,对于四周的人都夸赞奖赞叹的事也起,甚至对于因为对于同类及同类间的舆论与恐怖而作的行为也起。……依了这样的说明,我们可以晓得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18]这就是说,“良知”是因事而起的,必须是特定时空、特定物质基础的产物,而非空穴来风。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岱年明确指出,“王守仁说的‘良知’,实际上就是封建道德意识。”[6]369而侯外庐则对“封建道德”内涵做了更具体、更详细的解释,他说:“王阳明所说抽象的‘是非’标准,即‘良知’,实质上是封建的道德律,即统治阶级的‘是非’,这和人民的‘是非’是恰恰相反的。从而统治阶级的疾痛困苦和人民的疾痛困苦也是相反的。……王阳明的真正用意所在,即所谓‘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这一结论,即从心理的‘无对’达到社会的‘无对’,这样好像就使人民的‘是非’同于统治阶级的‘是非’,使人民的好恶,同于统治阶级的好恶,也即人民就放弃自己争生存权利的斗争,而屈从于地主阶级的‘至善’。”[2]896所谓“封建道德”,就是指“良知”的时空性、主体性,其时空是封建社会,其主体是封建统治阶级,因而如果“良知”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那只能是“封建社会”的,只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从而“良知”不可能是人民的是非善恶准则。沈善洪、王凤贤说:“良知既然是性、是理,那它就不是一般的先验道德意识,而是内心固有的封建道德准则了。”[19]319因此,王阳明将“良知”说成是人人先天具有的道德准则或是非准则,即意味着混淆人民的“是非”与统治阶级的“是非”,进而使人民在温柔漂亮的语言中接受统治阶级的剥削。总之,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良知”不可能是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超时空、超阶级的“良知”是不存在的。
2.“良知”否认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都是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的社会意识是有差别的,甚至是对立的。而孟子、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是人人皆备、圣凡皆有,他们的差别只是圣人能够觉悟良知的存在并把它彰显出来,因而“良知”是抽象的,而这抽象的“良知”与社会意识的阶级性是矛盾的。王阳明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1]49按着王阳明的论述,“良知”是圣人、凡人皆有的,只不过,圣人能够觉悟到“良知”的存在,而凡人不能觉悟到,这正是圣人、凡人差别所在。凡人之所以不能觉悟到“良知”,乃是因为昏塞所致。既然“良知”是人人具有的,那就意味着不同阶级的人都有,因而其推论便是阶级没有差别。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先验本有而论,“良知”虽然不分圣凡,但圣人与凡人是有差别的,从而保留其圣贤观。张岱年分析说:“王守仁断定人人都有‘良知’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而他所讲的这种道德意识的内容是忠、孝等封建道德,因之,他讲人人有良知,实际上就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说成为各阶级的人的生来固有的东西,这就是让人认为封建道德不是强制的而是内发的,使人更容易接受封建道德的约束。其次,它以灵活的良知代替那些烦琐礼节的教条。他只确定了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则,而在实际行动上却可以灵活运用,随机应变。这可以说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更有效的方法。”[6]372在张岱年看来,王阳明的“良知”说,就是想把封建道德说成是人人具有的品质,从而使人们能自觉接受,而用“良知”代替礼教,是为了使封建道德实行起来更灵活、更方便,因而“良知”说的阶级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沈善洪、王凤贤进一步分析说:“他(王阳明)的这套理论,就其实质来说,不过是把封建道德准则说成是人人具有的‘良知’,要人们自觉的一体遵循而已。然而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善恶观。”[7]73可见,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都有阶级性,但“良知”这种“社会意识”宣传是普世的,它超越了所有阶级界线,为所有阶级所共享,这就意味着“良知”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从而遭到驱逐。
3.“良知”否认工具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意识都有其特定的服务对象,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意识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工具。但“良知”似乎并没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并不能简单地界定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王阳明说:“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1]84-85这是说,“良知”就是真诚恻怛之德,这种真诚恻怛之德表现在事亲上便是孝,表现在事兄上便是弟,表现在事君上便是忠,因而从兄的良知与事亲的良知、事君的良知都是贯通的。换言之,如果一个人能够致得从兄的良知,就一定能致得事亲的良知和事君的良知。因此,“良知”虽然因其所事而异其名,但其“体”不会因为所事对象的差异而受到限制,即“良知”在本体上并不属于哪个团体或哪个阶级。所以,“良知”好比天地日月,天覆盖万物不会有偏私,地承载万物不会有偏私,日月照耀万物也不会有偏私,因而不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也不存在为某个特定阶级服务的问题。而且,“良知”也是天地万物一体的基石,王阳明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5]107宇宙万物之所以成为一体,乃是因为“良知”贯通其中,乃是因为“仁”成其血脉,因而万物虽异却为一体。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11]698既然“万物一体”理念是由“良知”或“仁”为基础的,那么,“良知”就不会也不应被“万物”分割成多个部分并分别归属之。可见,王阳明的“良知”不可能属于某个阶级,从而也不可能为特定的阶级服务。也就是说,“良知”是普遍的德性,是每个人自由精神。但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学说,“良知”必然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只能是阶级服务的工具。张锡勤说:“他们(陆、王)的目的是企图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意志来冒充全体人民的精神意志,让人们以统治阶级之心为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不论是思孟、禅宗还是陆王,他们讲心(良知)都是指统治阶级的精神意志,他们的目的都是企图让人们把统治阶级的精神意志变成自己的主观精神、主观意志,而不是要鼓吹什么个人的‘自由意志’。”[8]74这就是说,王阳明的“良知”看上去是所有人的意志,但实际上是用统治阶级的意志代替全体人民的意志,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仅如此,“良知”还在道德上武装了统治阶级,使统治阶级的统治更具欺骗性。沈善洪、王凤贤说:“良知是判断‘万事万变’之是非、善恶的准则。王守仁的这一论断,提高了地主阶级在道德上的主动性。”[19]320这就是说,“良知”不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且强化了统治阶级用道德为自己服务的自觉。因此,“良知”是统治阶级的精神世界,是统治阶级用于欺骗、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良知”的光芒照射着被统治阶级,就是使其由愚而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社会中的身份而不出其位。李石岑说:“王阳明以为心的本体即是良知,已经有些费解,况且完全拿禅家的话头解释孟子的良知,更是奇特。……唯心论者总是把世界分成两截,一种是精神界,一种是物质界。精神界不变动而可以支配物质界,物质界变动却须受支配于精神界。这种宇宙观,应用到伦理上或政治上,精神界便属于统治阶级,物质界便属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不变动,而可以支配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变动,却须受统治阶级之支配。而且统治阶级是‘恒照’的,是‘昭明灵觉,圆融洞澈’的,是‘自然会知’的。这是何等深切著名的封建教理。所以王阳明的学说,不仅为封建主义的中国所欢迎,更为帝国主义的日本所欢迎。”[20]可见,对于唯物史观而言,任何社会意识都具有明确的服务对象,都是服务统治阶级的工具,但“良知”似乎不属于某个特定阶级,没有特定的服务对象,“良知”内容及其服务的性质与范围并非“工具”所能尽诠,这样,“任性”的“良知”便遭到驱逐。
概言之,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良知”应该是封建社会的反映,但“良知”显然超越了特定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有其阶级性,因而“良知”应该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但“良知”显然不局限于某个阶级;社会意识的提出,必为提出者服务,即“良知”应该是服务于某统治阶级的工具,但“良知”的服务区域和性质都不为某个阶级所限。因此,“良知”之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学说,找不到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从而被下“逐客令”。
四、“良知”沦陷之省思
可见,笔者所陈述的“良知”沦陷现象证明了阳明所谓“‘良知’或蔽或放非其体”观念的正确性。只不过,此“沦陷”现象发生的原因与王阳明所认知的并不相同,并因此对“良知”所造成的伤害也不同。那么,它究竟属于哪种形式的沦陷?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其根本原因又在哪里?我们能从中获得哪些有价值的启示?如下便是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回应。
1.“良知”沦陷的原因及其危害
显然,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科学原理解释“良知”,与二十世纪席卷全球的科学主义思潮存在密切关联。当习惯于传统思维的人们突然面对一种崭新且极富现实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时候,迅速而虔诚地拜倒在科学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学说脚下是再自然不过的。他们相信科学万能,如胡适说:“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方法是万能的。”[21]他们将科学视为任何学说或理论的试金石,如蔡元培说:“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22]马克思主义学说则被当成解释一切的最有效的方法,如任弼时说:“马克思的唯物论在一切社会科学中要占主脑的地位,它是各种科学去研究各种现象的总和,它是指导各种科学怎样去研究各科现象的总和,它是指导各种科学怎样去研究本科内一切现象的科学方法。”[23]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对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崇信和迷恋可见一斑。在这样的背景下,“良知”被降格为一种普通的知识、科学理论或意识形式,是合乎人们思维逻辑的。但在这种置换中,认识论、科学原理、唯物史观成为了“良知”的试金石。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开始对“良知”轮番质疑与考问,“良知”的性质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良知”遍体鳞伤而无处申冤,正如张君劢所指出的:“有些近代心理学派可能将良能或良知解释为本能。可是,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里,良知是个哲学概念,包含意识生活的三方面:知、情、意。”[24]即“良知”不属于认识论、科学学说、阶级学说范畴的概念,即不属于知识性质的概念。正是这种错位的解释,“良知”被残忍地化解。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认识论、科学方法、阶级学说的解释,之所以能够霸气地将“良知”从自己的“辖区”赶出去,更深的原因是他们都具有近代功利主义品质。知识论所强调的感官第一、实践第一,科学原理所强调的归纳主义、实验主义,阶级学说所强调的阶级性、工具性,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精神,而“良知”所具有的超越性、理想性、高尚性、浪漫性正为其所不能容忍。因此,“良知”的知识解释性沦陷也泄露了这种解释的趋利动机与可预见的后果。那是怎样一种后果呢?“良知”的沦陷虽然是知识性、观念性的,但由于这种解释是基于人类的基本的知识理论、科学理论和社会学(阶级学说)理论展开的,即是说,认识论所主张的那些基本理论、科学学说所主张那些基本方法、阶级学说所主张的那些基本原则,属于人类心灵中的“常识”。因此,认识论解释、科学化解释、阶级化解释,必然导致人们关于“良知”的思想意识基础的破坏,动摇人们对于“良知”的信念,即信奉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且不能理性地把握其特性,那么,“良知”的思想意识基础将不复存在,而“良知”的先验性、至善性、绝对性等特质即被化解,“良知”也因此从人们心灵中失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知识化解释所导致的“良知”的沦陷,具有釜底抽薪式特征,是颠覆性、毁灭性的。
2.“良知”沦陷的形式及其性质。
与“利欲型沦陷”相比,应如何定义文中所讨论的“良知”沦陷形式?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析、检讨本文陈述的解释“良知”的三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中,“良知”被认为否定感官认识、否定认识对象、否定认识标准;在科学方法解释中,“良知”被认为排斥归纳思维、否弃实验方法、背离科学成果;在阶级学说解释中,“良知”被认为否定时空性、否定阶级性、否定工具性。那么,这三种解释具有怎样的共性呢?第一,观念的,非现实的。认识论解释所涉及的是获取知识途径与知识检验的标准,属认知知识;科学原理的解释所涉及的是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属科学知识;阶级学说的解释所涉及的社会意识及其主体归属,属社会知识。可见,此三种解释都是在“知识”范畴中进行的,这就是它们的共性,故可定义为“知识化解释”。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系统中、阶级学说系统中、科学原理系统中,“良知”找不到其存在的“知识”根据。但必须认识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抑或科学原理,不仅是“知识的”,也是“观念的”,也就是说,所谓“认识论化、科学学说化、阶级学说化”解释所导致的“良知”的沦陷,是“观念”层面的沦陷,是“思想意识”中的沦陷。第二,解释的,可选择的。无论是认识论解释、科学方法解释,还是阶级学说解释,都属于理论解释活动,即“良知”的沦陷是在被解释中沦陷的。但任何理论解释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并完成的,即在不同的语境中可有不同的解释,因而解释是可以选择的。这就意味着对“良知”的解释可以是多种方式并存。因而即便在认识论、科学方法、阶级学说解释中,“良知”出现了沦陷现象,但在其他解释方式中“良知”则可能得到保护,比如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所展开的人文主义解释。第三,现象的,非本体的。就是说,不管是认识论解释、科学方法解释,还是阶级学说解释,“良知”的沦陷都是现象的沦陷。为什么这样说呢?认识论解释是批评“良知”不是来源于感觉器官,科学方法解释是批评“良知”不能被验证,阶级学说解释是批评“良知”超越时空超越主体。可是,“良知”的根本特质就在于它的本有性、先验性、超时空性和超主体性,这也是“良知”的精髓和血脉所在。就是说,“良知”之体是恒在的,万象变幻对“良知”的存在无任何影响,更不会伤害“良知”之体。因此,认识论解释、科学方法解释、阶级学说所导致的“良知”的沦陷,都只是现象的。既然认识论解释、科学方法解释、阶级学说解释的特征是:观念的而非现实的、解释的而可选择的、现象的而非本体的,那就意味着“知识化解释”虽然对“良知”带来了很大困境,但并没有彻底沦陷。
3.“良知”特质的凸显
认识论解释、科学方法解释、阶级学说解释,不仅没有彻底导致“良知”的沦陷,反而意外地使“良知”的特质得以凸显,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和把握到“良知”的特质,即“良知”至善性、先验性、绝对性特质,更亲切地感受到“良知”的可爱。“良知”的认识论解释,是指“良知”排斥感觉器官、否定认识对象、否弃实践标准,这就告诉我们,“良知”是超验的、是本有的。正如牟宗三所说:“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本身即是一种呈现。又如孟子所说之‘四端之心’,它也是当下即可呈现的;所以王学中的王龙溪喜欢说‘当下良知’。如果良知只是一个设准、一个假定,而不能当下呈现,那么讲一大套道德法则,根本就毫无影响力可言。”[25]“良知”的科学方法解释,是指“良知”否定归纳思维、否定实验方法、背离科学成果。这就告诉我们,“良知”是至善的、圆融无碍的、不可言状的、不证自明的。正如默里·斯坦因所说:“在每个人的心理生活中,良知是一种情结,一种深藏的品性。事实上,它采取了如此多的形式,如此多地潜入我们的判断和情感反应中,以致于要掌握住它和把它当作一种单独的心理因素加以分析变得极端困难。”[26]2“良知”的阶级学说解释,是指“良知”否定知识的时空性、否定知识的主体性、否定知识的工具性。这就告诉我们,“良知”是无主体归属的,它不属于哪个特定的集团或阶级,正如美国《韦伯斯特大辞典》所云:“良知即个人对正当与否的感知,是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意图或品格在道德上好坏与否的认识,以及一种要正当地行动或做一个正当的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人做了坏事时常能引起自己有罪或悔恨的感情。”[26]21概言之,“良知”是先验地存在人身、绝对至善、无时不在的道德本体。诚如牟宗三所说:“若谓孟子所说之良知良能,有孩提之童而指点者,乃是自然之习性,或自然之本能,则大悖。此定如康德所说,乃是超越的道德本心。”[27]正因为“良知”属于道德范畴,其功用必定是有限的,即不能将“良知”泛用于所有领域,不能要求“良知”解决所有问题。韦政通说得好:“阳明的良知,不限于人类的范围,它是普遍于一切物而言的:‘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这是极端的泛道德主义的讲法,这个讲法的严重后果,当时的罗钦顺就已经提出来,他说:‘今以良知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无复本然之则矣。’泛道德主义的结果,以道的律则,代替了自然和物理世界的律则,在这样一个道德世界里,经验知识怎么占一个地位?”[28]因而我们一方面需要检讨知识解释对“良知”造成的伤害,另一面也不能怂恿“良知”的娇情,任其狂妄自大。“良知”应该位其所位而有所为有所不为。
4.“良知”沦陷的人文与科学关系视域
在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的解释中,“良知”与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似乎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但实际上,既然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中存在否定“良知”的机理,这说明“良知”的彰显、强大,亦可以抵御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的侵袭,即“良知”对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等具有反制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良知”具有永久的价值。唐君毅曾说:“我们之主张发展中国之科学,便完全是从中国文化中之仁教自身立根,决非出自流俗之向外欣羡之情,或追赶世界潮流之意。”[29]其所谓“以中国仁教立根”,就是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良知”“仁”“本心”“道心”等所蕴含的善的力量,对于发展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技术的根本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知识化解释致使“良知”的沦陷对人类而言是极为恐惧的事件。因此,科学知识与“良知”需要的并不是相互贬抑、相互排斥,而应该相敬如宾、竭诚合作,以“良知”激发出内在于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中的“善”,以认识论、科学原理、阶级学说引发出“良知”对知识、科学、阶级学说等的关怀和智慧,使道德与知识、人文与科学各显其能并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生命的成长作出贡献,这或许是本文思考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卢梭说:“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没有你,我就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优于禽兽的地方;没有你,我就只能按我没有条理的见解和没有准绳的理智可悲地做了一桩错事又做一桩错事。”[30]也许我们需要自觉牢记“良知”遭遇的“不幸”,但更需做的是重新拾取对“良知”的信心,人的高贵并不在于他有多博学,而在于他是否遵循心中的道德命令,在于他的心灵是否圣洁,在于他的心灵是否明亮。王阳明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5]93因此,“良知”对科学知识虽应保持必要的敬意,但绝不能俯首称臣,甚至自暴自弃,被知识所牵引、所稀释而失落自我,而应成为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发生、成长道路上的灯塔,照亮其行程,引领其方向。
[1]王阳明.传习录(中)[M]//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张岱年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662.
[4]萧箑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王阳明.传习录(下)[M]//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7]沈善洪,王凤贤.王阳明哲学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8]张锡勤,霍方雷.陆王心学初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9]严复.穆勒名学: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1050.
[10]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王阳明.大学问[M]//王阳明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2]附语[M]//穆勒名学. 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18.
[13]引论[M]//穆勒名学. 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
[14]按语[M]// 穆勒名学. 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49.
[15]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M]//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82.
[16]王阳明.答南元善[M]//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11.
[17]孙中山.建国方略[M]//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21—122.
[18]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C]//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 陈崧,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29-230.
[19]沈善洪,王凤贤. 中国伦理学说史(下卷)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0]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0—61.
[21]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M]//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313.
[22]高平叔.蔡元培哲学论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175.
[23]任弼时.马克思主义概略[J].中国青年·四卷(七七、七八号),1925(5).
[24]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69.
[2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86.
[26](美)默里斯坦因.日性良知与月性良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27]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55.
[28]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M].上海:上海书店,2003:870.
[29]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31.
[30](法)卢梭.爱弥儿(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17.
[责任编辑 何志玉]
The Fallen Conscien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Dimension of Interpreted Intellectualization
LI Cheng-gu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In the 20thcentury, the loss of conscience of Chinese ethics history encountered an unexpected situation, which known as the loss of interpreted intellectualization. Not only did it clearly present the complicate rel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morality, but also let us grasp the essence of conscience profoundly. Meanwhile, made us realize the effect of illustration and how to apply it specifically. Conscience can be either simple or sophisticated, but its true meaning will always remain, so that is probably the original sentim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conscience. Above all, human beings should stick to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conscience while appropriate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conscience.
conscience; fallen; reflection; interpreted intellectualization
2016-11-12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人性论义理结构与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5AZD031);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招标课题项目:“儒家生命诠释学”(项目编号:13YBA36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学经典诠释中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3ZX002)阶段性成果。
李承贵(1964-),男,江西万年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B222.5
A
1673-6133(2016)06-0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