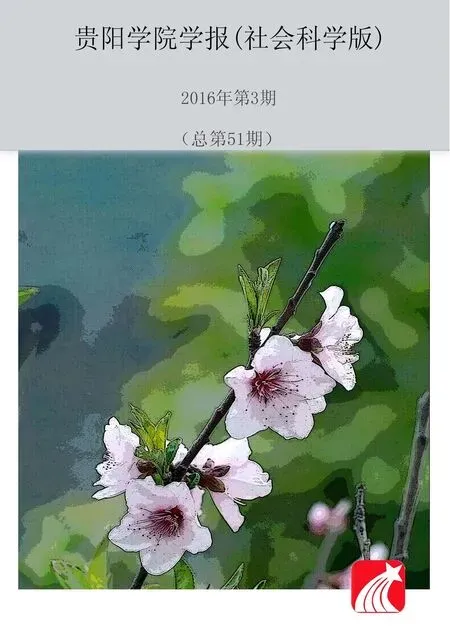试论慈湖的“觉”——以工夫论为中心*
陈碧强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试论慈湖的“觉”
——以工夫论为中心*
陈碧强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觉”在慈湖心学中的地位颇为关键,贯穿于其思想的本体、工夫、境界,乃彻上彻下之道。受佛学的影响,慈湖的觉悟体验有一些神秘的倾向。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觉”乃是在不断深入思考和踏实践履的基础上获得的对于身心性命之学的体认。抛开神秘主义的外衣,他的觉悟体验乃是“渐悟”,其中蕴含着强烈的自我批判与否定的精神,且呈现出浓厚的实践品格,需要艰苦探寻、反复求索才能得到。本文从工夫论的角度切入,希望澄清一些误解。
杨慈湖;心学;觉悟;工夫论;自我批判
一、引言
“觉”是中国古典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孟子·万章上》“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说法是其观念之发端。“觉”又和“悟”紧密相关。赵岐说:“觉,悟也。”《白虎通》说:“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说文》曰:“觉,寤也。从见,学省声。一曰发也。”“寤”指的是从睡梦中醒来,其观念可以追溯到《尚书·顾命》:“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悟”与“寤”同。后来,由于“觉”、“悟”二字在表达观念方面有一致性,所以二者往往相互训释,构成同义复合词。“觉悟”的观念在《荀子》和《韩非子》中都有所见,基本含义为“醒悟”、“明白”,进而引申为对道的“体认”和“认识”。张岱年指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觉和悟,都是说对于“道”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儒家、道家都讲“闻道”,觉悟即“闻道”。[1]
与“觉”有相同或相近内涵的,还有“省”、“醒”、“惺惺”等概念。受程颢“以觉训仁”说的影响,在宋明理学的心学一脉中,“觉”的问题被大量谈及,但像慈湖这样重视“觉”的,恐怕不多见。他不仅有多次觉悟体验,也常以此教人,并颇有绩效:“比一二十年以来,觉者滋众,踰百人矣,吾道其亨乎?”[2]199
清儒说:“宋儒之学,至陆九渊始以超悟为宗。诸弟子中,最号得传者莫如杨简。”[3]黄宗羲也说:“慈湖所传,皆以明悟为主。”[4]2506二者不约而同提到了“悟”,“悟”即“觉”。由于慈湖重“觉”,他被不少学者批评为“阳儒阴释”,围绕在他身上的误解颇深。罗钦顺说:“慈湖顿悟之机,实自陆象山发之。”[5]钱穆曰:“简之后学又张扬师说,谓其师大悟几十,小悟几十,真俨然成了禅宗一祖师。”①*①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联经出版社,1993年,第26-27页。钱穆“禅宗一祖师”的说法,很可能由陈淳而来:“朋徒私相尊号为祖师,以为真有得于千载不传之正统。”(《宋元学案》卷七十四,《慈湖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78页)在罗钦顺和钱穆看来,慈湖的“觉”就是禅宗的“顿悟”,二者没什么实质区别。陈来从顿渐问题的角度出发考察慈湖的思想,认为顿悟、渐修一类问题在儒学内出现,与佛教讨论的影响有关。[6]
必须指出,无论从实际行为还是精神追求,抑或是终极关怀来看,慈湖思想都不是禅学。那么,慈湖对“觉”是如何规定、阐述的?在他的思想脉络中,“觉”有什么内涵?“觉”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觉”?心学的“觉”与佛禅的“顿悟”以及神秘主义有何联系与区别?讨论慈湖的“觉”,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心学工夫论、境界论的了解,同时也能对心学与佛禅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笔者以工夫论为中心,试图展示慈湖之“觉”的不同面向,希冀一定程度上澄清围绕在慈湖心学方面的相关误解。
二、慈湖的觉悟体验
慈湖一生有过多次觉悟体验,以下,笔者将围绕其中比较重要的七次觉悟经历进行分析和检讨。他的第一次觉悟体验发生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时年28岁,历史上称为“徇理斋之悟”: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学之徇理斋。时首秋,入夜,斋仆以灯至②*②钱时在《行状》里的记载是“尝入夜,灯未上。”(《慈湖遗书》卷十八,第431页)笔者认为“灯未上”的记录更为可信,因为在黑夜中人与各类事务(物)暂时隔离开来,没有任何干扰,更利于自我反省,从而引发思想的飞跃。。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尝有训曰“时复反观”。某方反观,忽觉空洞无内外,无际畔,三才、万物、万化、万事、幽明、有无,通为一体,略无缝罅。畴昔意谓万象森罗、一理贯通而已,有象与理之分,有一与万之异。及反观后所见,元来某心体如此广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际畔,乃在某无际畔之中。[2]449
在这次觉悟经历中,慈湖体验到了万物一体、一理贯通、心体广大三方面的主要内容。这是对他自少年以来对“道”的思索和追求的初步回应③*③杨慈湖曾回忆道:“少读《易大传》,深爱‘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窃自念:学道,必造此妙。”(宋)杨简:《杨氏易传》卷二十,载《儒藏》(精华编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13-714页。。“道”无所不通,“心”亦遍在宇宙,“道”就是“心”,二者异名同实。万物纷然只是表象,其实质乃心之变化,心具有最高的统一性,同时亦超越而内在。他以心容物,以己摄他,以一统万,将一切存在纳入到心体中来。此心非血气形质之心,亦非仅为思虑知觉之心,而是形上之心,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创生意义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心体即是道体。
慈湖对心体的认识奠定了他日后学问的大方向,是他“进入心学门槛的标志”[7]30。需要注意的是,慈湖“万物一体”的觉悟体验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以及象山“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在内涵上并不完全相同。孟子和象山的体悟皆从道德本体的角度出发,以道德性的本心为内容。本心内在于每个人,是人成就道德的根据,只需要涵养本心并向外推展,便能“亲亲、仁民、爱物”,继而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相较于孟子和象山浓厚的道德意识而言,慈湖对心体的认识则更多地偏向其超越面和高明面,是一种境界论的理路。尽管提到了 “心体广大”和“一理贯通”,但何谓“心体”?如何“广大”?何谓“一理”?如何“贯通”?类似关键的问理论题,他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答。
第二次觉悟体验发生在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时年31岁:
某二十有八而觉,三十有一而又觉,觉此心清明虚朗,断断乎无过失,过失皆起乎意。不动乎意,澄然虚明,过失何从而有?某深信此心之自清明,自无所不通,断断乎无俟乎复“清”之。于本虚、本明、无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之意,千失万过朋然而至矣,甚可畏也[2]193。
此次觉悟提出了过恶从何而来的问题,并引申出他“不起意”的工夫论。他说:“此心即道。”[2]183深信“人性皆善,皆可以为尧舜,特动乎意则恶”[2]182。认为本心清明虚朗,自善自灵,断不会有过失,过失皆是由于起意。一旦起意,本心就会陷溺、遮蔽,不能正常发用。“清明虚朗”的说法跟家庭教育有关,如其父杨庭显说:“人心本自清明,本自善,其有恶,乃妄心尔”①*①《慈湖遗书》卷十七,《纪先训》,第429页。慈湖心学思想的来源颇为复杂,既有家庭教育的熏陶,也有象山的启迪,且前者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后者。例如,从对心体的认识来看,慈湖后来对“心”的解读和描述在许多方面(如澄然虚明、广大无际、非思非为、寂感一如、自备万善等)与其父类似,他对“我”的区分直接启发了慈湖的“毋我”思想;另外,慈湖心学工夫论中的“觉”和“改过”也从杨庭显那里继承而来;境界体认方面,杨庭显的“乐”与慈湖的“永”亦可相发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慈湖二十九岁拜象山为师,那个时候,他的学说大纲已基本奠定,象山对他的作用或许更多体现在点拨和提升上,也就是慈湖说的“触其机”。从二人的学问路数、学说基调、气质人格、经典诠释、发展方向等方面来看,二人的差异也很明显。。
朱熹说:“意者,心之所发也”②*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阳明受朱熹影响,他对“意”的界定也由朱熹而来:“心之所发便是意。”(王守仁:《阳明传习录·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儒家讲的“心”既有体也有用,所以它要在经验世界中表现自己,通过人伦道德、社会事功等自我证明,自我成就。“心”如何应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这就需要一个中介,来实现“心”与“物”的沟通,这个中介便是“意”,也叫“意念”,它代表了人的意向性思维,其存在有一定的必要。
从这个角度说,慈湖并不会反对朱熹对“意”的界定。但是,他在“发”的问题上比一般的思想家思考得更深。“心”怎么“发”?有两种情况:一是“意”顺着“心”的要求而发,而是“意”违逆“心”的要求而发。前者是理想情况,后者则是大多数人时常经历的现实情况。之所以会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其原因在于习气和物欲对人心的干扰,导致了本心被遮蔽和陷溺,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功用。慈湖认为,“心”与“意”“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则为心,二则为意,直则为心,支则为意,通则为心,阻则为意。直心支用,不识不知,变化云为,岂支岂离”?[4]2476可见他是在本质和非本质两个层次上论“意”的,本质状态的“意”与“心”合一,表现为“直心直用”,也叫“直心直意”;非本质状态的“意”则与“心”分离,表现为分别、比较,是一种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知性思维方式,人一旦陷入这样的思维方式中,就必定会有所偏有所倚,无法得本心大中至正之道。慈湖认为,求知和求道属于两个不同层次,在方法上也并不完全相同,有必要做出区分。慈湖心学注重如何“发明本心”③*③全祖望说,对于“发明本心”的态度,“陆氏但以为入门,而文元遂以为究竟,故文元为陆氏功臣”。(《宋元学案》卷七十四,《慈湖学案》,第2479页),挺立道德主体,故对后者更为看重,但并不能说他提倡“蒙昧主义”[8]或“彻底推倒了知识系统”[9]。
通过以上两次觉悟体验,慈湖扼要地勾勒了他的心性论和工夫论,心学思想初具雏形。从他整个思想发展历程来看,这两次觉悟对与他影响很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第三次觉悟发生在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时年32岁,史称“扇讼之悟”:
至是,文安公新第归,来富阳。长先生二岁,素相呼以字,为交友,留半月,将别去,则念天地间无疑者,平时愿一见,莫可得,遽语离乎?复留之。夜集双明阁上,数提“本心”二字,因从容问曰:“何谓本心?”适平旦尝听扇讼,公即扬声答曰:“且彼讼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谓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闻之,忽觉此心澄然清明,亟问曰:“止如斯邪?”公竦然端厉,复扬声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语,即揖而归,拱达旦,质明正北面而拜,终身师事焉。
象山对慈湖的点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本心”就是仁义之心,乃先验的道德潜能,人人先天具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二,“本心”知是知非,能接应各种事务,是非观念即本心在面对扇讼时的自然表现。三,万物各有其理,但万物之理不外于“本心”,心即是理,明心便能明理,所以“发明本心”乃是为学大头脑。总之,“本心”既是宇宙万物的存在依据,又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本动力,它是兼具“物之则”与“心之理”的存在。至此,慈湖对“本心”的体认更为完整:“本心”乃是一种清明虚朗、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而又无时不在、感而遂通的道德本体,它是人的本质规定。
另外,“本心”还有极强的实践品格,需要在日用平常中落实。慈湖在听了象山的解答后“忽觉此心澄然清明”,说明他已经对“本心”的道德属性有所契合,但仍有疑惑。“止如斯邪”即表明他希望在理论方面进一步认识“本心”,但陆象山“更有何也”的回答给他以当头棒喝。象山认为,“本心”就是“本心”,就是仁义礼智之心,千言万语不出于此。所以,关键不在理论上将“本心”分析梳理得多么清楚,而是在明了“本心”之后如何踏实践履。慈湖后来也领悟到了这点,从此笃实践履,他说:“日用平常实直之心,事亲自孝,事君自忠,于夫妇自别,于长幼自序,于朋友自信。”[2]208可见,他对“本心”的体认的确有所进步,故象山表扬他“一日千里”[10]。
在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慈湖34岁时,他有了第四次觉悟体验:
淳熙元年春,丧妣氏,去官,居垩室,哀毁尽礼,后营圹车厩,更觉日用酬应,未能无碍。沉思屡日,偶一事相提触,亟起旋草庐中,始大悟“变化云为”①*①“变化云为”一语出自《易·系辞下》。之旨,纵横交错万变,虚明不动,如鉴中象矣。学不疑不进,既屡空屡疑,于是乎大进。[2]432
亲人的逝去能够让人瞬间从繁忙的世俗生活中摆脱出来,撕掉各种虚伪的包装,显露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这种真实的情感流露便是“本心”的发用,“本心”是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的合一,故其发用必定自然而然、不假思维而又能靡不中节。“鉴中象”的比喻说明,“本心”知是知非,好善恶恶,它自身不动,而万物之动静变化无不显现于其中。这里的“不动”是就存有论的层面而言,“本心”的存在先于万物,在万物产生之前,根本谈不上动和静;但从功能和作用的层面看,“本心”又具有健动的属性,可以应万物而不为万物所累。
然而慈湖对“本心”的体认还不够深,不能做到完全的信任②*②慈湖在多处表达了人应该自信自重,相信本心的力量,不要自暴自弃。他说:“某心人心即大道,先生遗言兹可考。心之精神是谓圣,诏告昭昭复皜皜。”(《慈湖遗书》卷六,《宋黄文书侍郎赴三山》,第235页)又说:“兢业初无蹊径,缉熙本有光明。自觉自知自信,何思何虑何营?镜里人情喜怒,空中云气纡萦。孔训于仁用力,箕畴王道平平。”(同上,《熙光》,第235页)。正由于此,他的“日用应酬”依然“未能无碍”。《绝四记》言:“通则为心,阻则为意。”[4]2476“无碍”便是“通”,“通”即通达,它和“道”、“圣”同义,皆强调“本心”的无所不至,无时不有。如果自信“本心”,便能超越纷杂的现实生活,获得精神的提升。若起意则为“阻”,便是“不通”。象山说:“某每见人,一见即知其是不是,后又疑其恐不然,最后终不出初一见。”[11]这也是一个怀疑“本心”、不能自信“本心”的例子。
然而,母亲的逝去让他对“本心”的信任进一步加深,他对“本心”寂感一如、当下呈现的特点有了真切体会。他说:“略察曩正哀恸时,乃亦寂然不动,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颜渊而不自知,正合无思无为之妙。”[12]“本心”具有先天的道德属性,“为恻隐为羞恶为恭敬为是非,可以事亲,可以事君,可以事长,可以与朋友交,可以行与妻子,可以与上,可以临民”[2]210。喜、怒、哀、乐等情感乃是“本心”的自然流露,无需造作,不必刻意。
慈湖为了认识“本心”而“沉思屡日”,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思考的过程便是消化、吸收以及深入理解前面觉悟体验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觉”主要是反思、自省的意思,理性成分居多,并非仅仅是感性知觉,也不是佛教“一了一切了,一悟一切悟”式的顿悟。全祖望认为慈湖“非恃扇讼一悟为究竟”[4]2480,此论可谓平实。
虽然慈湖努力体认“本心”,但旧习难除,学问始终未有大进步。他说:“学者初觉,纵心所之无不玄妙,往往遂足,不知进学。而旧习难遽消,未能念念不动,但谓此道无所复用其思为,虽自觉有过,而不用其力,虚度岁月,终未造精一之地。……予自三十有二微觉,已后正堕斯病。后十余年,念年迈而德不加进,殊为大害。”[2]385-386“进学”一词再次表明,“觉”是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入,需要建立在学问思辨的基础上,不可凭空而发。经过不断地反思,慈湖在在52岁至54岁时获得了第五次觉悟体验:
偶得古圣遗训,谓学道之初,系心一致,久而精纯,思为自泯。予始敢观省,果觉微进。后又于梦中获古圣面训,谓简未离意象,觉而益通,纵所思为,全体全妙。其改过也,不动而自泯,泯然无际,不可以动静言。[2]386
“久而精纯”、“微进”二语很关键,说明觉悟需要过程,蕴含了时间的向度,并非一次性洞见真如本体,也不是有了“微觉”的体悟后便可造“精一之境”。慈湖的“觉”一方面是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是为认识深化而进行的思辨行动;另一方面,“觉”又是境界的描述语,表达出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自觉体认。这种通贯无碍、一理圆融的境界有时候超越一切名相,惟有默会,不可言传。正如慈湖本人所说的那样:“益信人心自灵妙,莫执人神定名号。”[13]239然而,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前提,只有在长期深入思考和积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思想上的提升。“不可以动静言”再次说明,“本心”超越动静,乃精神性的道德实体,并非经验界中的具体之物,它“动而不动,静而不静”,故“不可以动静言”。通过“不起意”的工夫,人可以超越“意象”的干扰,直接达到对终极本体的把握,此乃“觉”的实质内涵。
“古圣遗训”是《孔丛子》中的“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叶绍翁说:“慈湖杨公简,参象山学犹未大悟。忽读《孔丛子》,至‘心之精神是谓圣’一句,豁然顿解。自此酬酢门人、叙述碑记、讲说经义,未尝舍心以立说。”[14]尽管慈湖对《孔丛子》有所怀疑①*①他说:“详观《木瓜》之诗,所谓木瓜、木桃、木李与夫琼琚、瑶玖,皆为喻尔,非实有是物也。而《孔丛子》言孔子读诗曰:‘吾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未必果圣人之言也。《孔丛子》所载亦有乖戾不可信者,不止于《木瓜》也。”(杨简撰,王承略、陈锦春、王正一、张春珍校点:《慈湖诗传》,儒藏·精华编二五,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83页),但对“心之精神是谓圣”这句话却笃信不改,认为此乃圣人言语,体现了圣学宗旨。“精”表示“心”的“纯粹无杂”,“神”表示“心”之“神妙莫测”。他说:“心之精神,无方无体,至静虚而虚明,有变化而无营为。”[2]183这里的“体”是体象、形质的意思,而非“本体”即根据的意思,“心”的作用和境界层面具有虚灵妙应,无形无相的特点,但本体上则保持至善性,是人性的本质设定。
何谓“圣”?慈湖说:“孔子语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圣’亦无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尝不圣,精神无体质无际畔,无所不在,无所不通。”[2]190可见,“圣”是对“心”的描述,是一个形容词,整句话的重点落在“心”上而非落在“圣”上。“心之精神是谓圣”和慈湖的另一个命题“心即道”在内涵上比较接近,都是强调“心”的超越性,无所不通,无所不在。这和他之前对“心”的体认不谋而合,“心”不仅有创生道德的涵义,还具有无所不通,无所不能的力量。至此,他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心学体系,其思想核心和理论旨趣更加圆融,愈发成熟。
慈湖61岁即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时,他经历了第六次觉悟体验:
十一月九日清晨,忽觉。子贡曰:“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知也。”二子之言仁,异乎孔子之言仁矣。十一日未昧爽,又忽醒。孔子之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必继之以“勇者不惧”,何也?知及之,仁能守之。知,知道。仁者,常觉常清明之谓。然而亦有常清明,日用变化不动,忽临白刃鼎镬,犹未能不动者,此犹未可言得道之全,故必继之以“勇者不惧”②*②(清)冯可镛、叶意深编,李春梅校点:《慈湖先生年谱》,载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第十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第6631页。按,李春梅原文点校为:“知及之仁,能守之知,知道仁者,常觉、常清明之谓。”此处点校有误,今改之。。
通过之前的五次觉悟,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心学体系,但对心体的体认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全祖望说:“慈湖斋明严恪,非礼不动,生平未尝作一草字。”[4]2480对儒者而言,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二者不可偏废,理性思辨可以满足人求知的需要,但知识的力量需要在行动中才能体现。相对于理性思辨,行动事业则充满了未知性和不确定性,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有危险。一个人即便做到了“知及”和“仁守”,能够按照“本心”的要求而为,但在面临重大事务时,往往起心动念,缺乏坚定的执行力,此时勇气就变得很重要了,否则无法得“道之全”。
陆象山认为心学就是实学,受此影响,陆门弟子多勇毅果决,践履笃实,不尚空谈。朱子对此颇为欣赏,甚至流露出一丝钦羡:“如今浙东学者多陆子静门人,类能卓然自立,相见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辈朋友又觉不振。”[15]他对慈湖的评价是“学能治己,才可及人”[2]503。慈湖本人性格娴静,但内心却充满了刚毅果敢的精神,《行状》曾记载他为下属和同行据理力争,不惜得罪上司甚至皇帝的事迹。如果没有“勇者不惧”的大丈夫气概,此举不太容易做得出来。
第七次觉悟体验发生在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此时他68岁:
某自以为能稽众、舍己从人矣,每见他人多自用,某不敢自用。亦简自谓能舍己从人,意谓如此言亦可矣。一日偶观《大禹谟》,知舜以克艰稽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尧能是,是谓己不能也。三复斯言,不胜叹息。舜心冲虚,不有己善,虽稽众舍己从人,亦自谓不能。呜呼,圣矣!舜岂不能稽众者?岂不能舍已从人?岂虐无告?岂废困穷?无告,常人之所不敢虐;困穷,常人之所不忍废。而今也圣人曰已不能。呜呼,圣矣!惟舜冲虚如此其至,故益赞舜徳自广运,自圣自神,自文自武。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时简年已六十有八,平时读《大禹谟》未省及此。[2]272
他自认为已经能够做到“稽众”和“舍己从人”,并将他人和自己的行为进行对比。这说明他的思维深处还有人我之别,意态尚没有完全消除。这与他在二十八岁体认到的三才一致、万物一体并不能完全契合。可见,消除人我之分别见和比较心并非易事,一时的觉悟并不能保证必然成德,道德修养工夫必须时时做,几乎伴随人的一生。
舜做到了“克艰稽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这些都是舜的优点,但他却说自己“不能”。舜的心中真正做到了“无我”,所以能够舍己从人,“冲虚”一词乃是对圣人境界的描述。圣贤事业绝非轻易所能成就,不仅在理论创建方面要经历一番艰苦的探索,在实际行动方面也需要不断的磨炼,提升工夫修养的境界。对天道的认识可以在瞬间觉悟,但工夫的践履却要一点一滴积累,所谓“理虽顿悟,事须渐修”是也。
慈湖在六十八岁时觉悟“克艰稽众”、“舍己从人”等圣贤品格,并反观自照,再次发现并承认了自己的不足。该觉悟也再次证明:“觉”的真义乃是不断地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自我超越,在此过程中努力提升自我,朝圣贤的目标迈进。张岱年说:“中国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先在身心经验上切己体察,而得到一种了悟;了悟所至,又验之以实践。”[16]慈湖思想整体上呈现出比较浓厚的境界论色彩,但这种境界不是个人的主观感悟,也非一时光影,乃是考之于言,证之于心,反之于身的切实体会。他说:
某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无所知。曷以称塞?钦惟舜曰“道心”,非心外复有道,道特无所不通之称。孔子语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圣”亦无所不通之名。[2]190
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17]141《易》曰:“天下何思何虑?”[18]《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9]“一无所知”乃无所不知,其真实内涵为:“本心”无思无虑却又无所不思,无所不虑。可见,“本心”的发用如此神妙莫测,人在不起意的情况下,顺应“本心”的要求而为,就能做到无所不通,无所不为,虽不去刻意求知,但却无所不知。慈湖的“觉”展现为一个追求成为圣贤的过程,他对“觉”的目的和层次有着清晰的规定:
知者觉之始,仁者觉之纯。不觉不足以言知,觉虽非心思之所及,而犹未精一。精一而后,可以言仁。[2]199
“觉”的目的是求仁,成己成物,此乃儒学本旨。求仁非一步到位,而是要在自我批判中逐步实现,其间有次第,不可躐等。“觉之始”和“觉之纯”的区分,乃是知性和超知性的区分。知性的认识总是有条件的,它受制于经验事实和思维规则,但“本心”超越经验和知性,是绝对自由的。“本心”即是仁,只有充分汲取知性并扬弃之,并不断地在事上磨炼,才能最终臻于“精一”之境。
三、余论
以上,笔者从工夫论的角度考察了慈湖对“觉”的言说。工夫论和本体论(存有论)紧密相关,后者对前者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心学一脉,工夫和本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即本体便是工夫”,这与理学派“由工夫以达本体”的路径不同。所以,慈湖的“觉”体现出先天之学的特点,简易直截,当下用力,直趋本根。心学的工夫看似简易,甚至给人以无工夫可言的印象,要真正做到却不容易。人首先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守护心体,涵养本源,同时也不能脱落后天的修为,只有将觉悟和修持结合起来,道德才能最终成就。有学者将慈湖的工夫论概括为“以觉为则,以修为功”[20]。
慈湖思想在不断地觉悟过程中形成,其建构却充满了理性思辨的张力。叔本华说:“直观是一切真理的源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21]107柏格森则认为哲学来自于直觉:“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22]慈湖的学说是一个整体,既有“讲明”,又有“践履”,他的七次觉悟体验具有前后的连贯性、阶段性,皆不可轻视。慈湖说:“思而忽觉,觉非思也。”[2]193又说:“觉非言语心思所及。”[2]200“觉”要建立在“思”的基础上,但“思”又不能完全和“觉”画等号,“觉”容纳并超越“思”,是一种高级的思想形态。要之,慈湖是在和圣贤、经典、自我不断对话和辩难的基础上,通过全面地自我批判和反省,最终才达到觉悟的。因此,这种神秘体验只是形式上的,慈湖的“觉”与其学问进步紧密相关,乃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基础上并超越之的结果,跟神秘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另外,人性的规定是多方面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可能只有一种。我们如果揭开“顿悟”、“神秘主义”之类的面纱将发现,他的觉悟甚为平实,是很多求道之人都会有的思想经历。
对于慈湖的觉悟体验,曾凡朝说:“这种反观内省的悟觉具有极大的不定性、偶发性和随意性。他必须经由个体的独自体认,难以通过普遍的规范加以传授,进而,其普遍有效性和可靠性难以保证,这种内省悟觉的结果并不表明悟觉主体必然把握到了真正的客观实在。”[7]32应该说,这样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不够深入。在慈湖那里,“觉”贯穿了本体论、工夫论和境界论,乃其“精一”之旨的体现。就本体论而言,“觉”即是觉悟先验的“本心”(也叫“一”),“本心”人人皆有,至善圆满,循“本心”而为,就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从工夫论的角度来说,“觉”是精一,是反观内省的修养方法,使“本心”时时呈现,自作主宰,不为“意”所遮蔽,以达到“常觉常明”;就境界论而言,“觉”便是“永”的境界,这是道德践履臻于纯熟后的最高体认。他说:“文王之德之纯,永也;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永也”,“所以能范围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发育万物者,此永也。”[2]194这种境界是对作为万物终极根据的“本心”的自信和自足。虽然从表现的形式上看,慈湖的“觉”显得偶然而随意,但实际上,这却是慈湖心中长久积累的疑虑在特定时刻的自然表现。
综上,觉悟的体验建立在努力进学和长期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此乃“渐觉”,而非“顿觉”,所以与禅宗的顿悟并不相同①*①张实龙说:“‘觉’是一种神性思维,是对理性思维的超越并且包容。”“神性思维”的提法颇具新意,值得参考。详见张实龙:《杨简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慈湖觉悟的对象是道德本心,而非真如实相,二者的差别在于是否承认道德本心创生实有的能力。此外,觉悟是在不断思辨、积累的前提下,通过一些偶然因素的触发而形成的,其本身乃包含有大量的理性思考成分在内,因此也不同于和某种至上实在合一的神秘主义。更为重要的是,慈湖的“觉”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重视觉悟之后的修持,并非以“觉”为一劳永逸的方法,觉悟是为了成就道德,而非为了宗教解脱。
“子不语:怪、力、乱、神”。[17]108慈湖以圣人之徒自居,整体上也继承了儒家理性主义的传统,他对道教科仪非常熟悉,但在具体的实践方面则将儒家的精神贯穿其中,对其进行理性化改造。由于家学熏陶和个人性格等因素,慈湖学说充满了很强的悟境色彩,呈现出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学的诸多特点,这在“觉”的问题上尤为体现得集中,但仍不出儒家矩矱,全面考察“觉”的问题,对于我们深化对慈湖思想的认识不无益处。
[1]张岱年.说觉悟[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1(1).
[2]杨简.慈湖遗书[M]//四明丛书本.台北:国防研究院印行,1966.
[3]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7:1253.
[4]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罗钦顺.困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2.
[6]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7.
[7]曾凡朝.试论悟觉对心学构架的意义——以杨简为例[J].兰州学刊,2009(5).
[8]崔大华.南宋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46.
[9]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93.
[10]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488.
[11]陆九渊,王守仁.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89.
[12]杨简.杨氏易传[M]//儒藏(精华编四). 曾凡朝,点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14.
[13]张实龙.杨简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39.
[14]叶绍翁.四朝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9:41.
[15]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751.
[16]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
[17]杨树达.论语疏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18]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41.
[19]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26.
[20]张伟.慈湖心舟:杨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1-68.
[2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07.
[22]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4.
责任编辑 何志玉
On the enlightenment experience for Yang Cihu——focusing on the theory of moral cultivation
CHEN Bi-qi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In the theory of Cihu heart-mind study, enlighten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penetrating many aspects in his thought. He got a lot of inspiration from such experience and used it to teach his discipl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because of Buddhism’s influence, Cihu’s enlightenment experience seems a little bit mysterious. However, with careful analysis, we can find that such experience is based on deep consideration and sincere practice. Without the real recognition about oneself and the soul, the experience will be impossible to obtain. Throwing away the vest of mystery, we can see that Cihu’s enlightenment experience is formed gradual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quiry, strong sense of self-critique and self-deny are included. In a word, the enlightenment will not be easy to get unless one tirelessly inquires and peruses. This easy aims to investigate Cihu’s enlightenment experience from the aspect of the theory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tries to clarify some historical misunderstandings.
Yang Cihu; Heart-Mind Study; Enlightenment Experience; Theory of Moral Cultivation; Self-Critique
2015-11-22注:本文系作者以教育部公派留学生身份(CSC NO.201306100067)参加复旦大学和日本九州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项目(2013.10-2015.4)的中期研究成果。
陈碧强(1985-),男,云南昆明人,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南宋心学。
B244.99
A
1673-6133(2016)03-003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