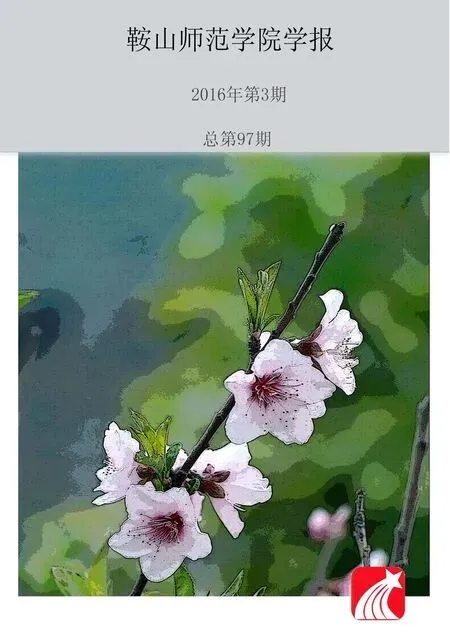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从多元化到多样性渐变的社会根源
王秋秋
(鞍山师范学院 文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从多元化到多样性渐变的社会根源
王秋秋
(鞍山师范学院 文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在现代主义的发展中诞生了后现代主义艺术与艺术技巧,是文学艺术科技化、商品化、符号化的结果,后现代艺术可以打破时间的连续性、空间的一维性,是后现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最根本区别。其目的最终是以反叛性的物质化形式达到将现代主义的多元中心彻底地解构为商品多样化的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个渐变过程,来确定后现代艺术理论形成的过程及特征。
后现代;文学;伦理;群体;血缘;反叛
伽达默尔在他的《美的现实性》一书中指出,模仿在物理学的总水平上与自然界相关联,由于自然在它的构成活动中还留下了可以塑造的东西,留下一个造型的空的空间让人的精神去充实,艺术才是可能的[1]。传统的电影艺术沿袭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表现方式进行创作,无异于将文字艺术转化为光影艺术,只是技术上的变革不是创作手法上的变革,而后现代电影则是运用后现代拼凑性手法展现文字作品所无法展现的那一侧面,例如电影影像可以体现瞬间感、流动感、模糊感、放大感等等用语言文字无法说明的视觉与空间体验。
后现代主义艺术中,作家在文本里通常都会留下多个故事线索并大多运用开放式的故事叙述技巧,使读者对后现代文本的解读变成对“自我经历”的解读,这种文本与读者开放式的密切关系使原本在现代主义超现实的宏大叙事理论建构下的文本与读者的疏离关系转变成只有通过“解构”才能阐释的互动阅读关系。读者与文本的外在联系也转变成读者与文本在心理学、心理机制、社会学、社会机制、生活方式、文化背景、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交流,这种依靠读者所建立的内在阅读体验将读者的解读体验变成受众通过阅读对现代主义异化性进行自我治疗的情感重建过程,从而使此种极具后现代性的分解剖析式阅读变成读者的自体验性剖析式阅读,从而达到异化性自我在阅读过程中“痊愈”的目的。同时,后现代艺术也不再追求永恒的价值,反对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异,这使得艺术象消费社会的商品一样,具有时尚性、流行性、创意性等特征。
后现代艺术以一种时而无深度的、时而无中心的、时而无根据的、时而自我反思的、时而游戏的、时而模糊的、时而折衷的、时而多元的艺术姿态出现,反映着当代艺术颠覆性变革的方方面面。画面的随意拼贴、拍摄与采访的不时插入、故事情节有意脱离主题等颠覆传统艺术的手段纷纷出现,成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先声。
波兰电影大师吉斯洛夫斯基、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拍、德国导演汤姆·提克威、香港导演王家卫等都开始大量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拍摄手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电影艺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张艺谋的电影在错综复杂的故事背景下,掩盖着经济转型带来的身份差异的主题,人物在影片中都成为符码,是对现代主义影像艺术统一性传统的彻底颠覆。
与卡夫卡在《地洞》里的主人公一样,后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的一系列主人公,都是没有理想、没有目标、没有奋斗意愿的青年,他们满足于在有限的金钱、有限的空间、有限的人际关系中生存的现实,从旧的道德体系角度来看,他们更像俄国小说中所嘲讽的“多余人”或萨特小说中所批判的“局外人”,没有被社会所抛弃,却被自我所放逐,不存在满怀救世的理想,自觉地逃避对人生理想的追问,终日游走在社会的边缘,甘愿充当地洞内的“边缘人”角色。
在后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框架下,后现代主义音乐艺术也终于抛弃了以往演唱与表演相结合的高技巧形式,开始采用一种低抒情式的表演技巧,将以往的高调人生、烂漫理想、革命式的浪漫抒情形式替换成贴近地面式的低调姿态,使那些为炫耀痛苦而歌唱的歌者被嘲讽。
在早期的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性质的小说《变形记》里,“虫”的外形使主人公逐退渐化为异类;在小说《判决》中,父子关系因儿子的投河而中断;在小说《尤利西斯》中,婚恋关系因平常的琐事而时断时续;在戏剧《秃头歌女》中,人的关系因陌生化而中断;在戏剧《等待戈多》中,上帝的存在因其始终缺席而被质疑。加缪的《局外人》、吴玄的《陌生人》、棉棉的《糖》、卫慧的《上海宝贝》等作品,均从血缘关系、社会关系、语言关系等角度,消解了宏大的意义符号关系,使理性成为现实生活的附庸品而被颠覆。王朔的痞子文学、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顾城的诗、海子的生活诗,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新形式。艳俗的小市民趣味结合以对崇高理想的讴歌所形成的巨大张力又使其所体现的反叛精神大异其趣。最后,在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文本已无可批判与反叛之时,它便以一种非英雄式的主题与小人物的自娱心态开始流行,这种玩笑式的戏谑心理成功地以嘲笑一切的态度使得那些崇高的理性之爱在狂欢化的浪漫笑声中被消解。
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谈话中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里,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是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谈论。语言学家德里达也认为,中心从来就没有自然的所在,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所在,而只是一种功能,一种非所在,这里云集了无数的替代符号,在不断进行着相互置换[2]。文学批评家马契雷则从文学生产原理的角度出发,认为作品并不是植根于历史现实,而仅仅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将原材料加工成作品。社会理论家戈德曼的发生学模式的文学批评则更是准确地针对关于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的相互间的复杂关联,比较精确地描绘出经济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各个中间媒介的层次关系[3]。
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朝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经济、人与政治、人与文化等关系的多样性、丰富性的多元化方向发展,其目的在于使文学文本能够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经济、人与政治、人与文化等之间的批判关系,它既是多元的又是平面的。他们提倡彻底地反传统、在作品中呈现出要求摈弃终极价值的思想,这不仅是彻底地反对旧的传统,还反对现代主义所建立的、“人”的神化传统,他们强调将人还原成具有真实的人性、美好道德的实践意义上的当代人。于是,在创作方法上,他们崇尚零度写作,以此来反对现代主义关于深度的神话。拒斥孤独感、焦灼感之类的深沉意识,并从传统美学理论里寻找出理论的基石,将“艺术地生活”作为写作本身,并且,将已经逝去的“历史”作为一种具有纯粹的表演形式、操作流程、娱乐意识的内容进行着艺术技巧方面的解构。
在文体问题上,后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文学作品,则蓄意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叙事文学与荒诞艺术的界限、文字游戏与政治事件的界限,展示出了具有明显地向大众文学、边缘文学、浪漫派文学靠拢的倾向,有些作品甚至干脆以大众文化的消费品的形式出现,以消解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他们运用矛盾、交替、不连贯性、任意性、极度夸张、话语膨胀、反体裁、任意体裁、重复、无规律重复、循环变换等创作手段,使读者在对作品的解读过程中面临着重重困难,甚至是一种解题式的阅读过程,即迫使读者将现代科学技术、理性的分析模式、哲理性的思想探索带入到阅读过程中。
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既不是一个具备具体指称的作家或批评家的群体,也不存在着被广泛认认同的纲领或宣言,它似乎是一个受到共同认可的存在,时时刻刻地在影响着后现代社会阅读体验的变革,文本的创作者们刻意地将文学文本的解释模型多样化,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共同主题。似乎不存在独立于某些共同体之外的阅读标准和价值,从而也不可能存在着能够超越话语共同体的、客观的、绝对的认知。正是由于这些认知的社会性和约束性,从而使后现代主义理论呈现出了多样化与多元性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整合的互动关系。
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其实也在逐渐地成型,德国历史主义哲学家狄尔泰在解释循环理论时就曾指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这里已遇到了一切解释的极限,而阐释永远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到一定程度:因此一切理解永远只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
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正是针对当代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为寻求新解释关系而生成的。在阐释的过程中,期望建立一种新的话语体系解决现代主义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于西方文学艺术来说,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强调个体化、个性化、模式化,但是,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陷入了阐释的困境。从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开始强调源自于《圣经·旧约》中的关于登天塔倒塌之后的世界的多样化,从而,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世界原本便是破碎的,在世界观上它是彻底的多元化、破碎化、多样化的了。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不存在解释世界的利器,由此,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在上帝“否定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世界多样性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历史哲学、理性哲学、宗教哲学、话语理论、政权理论等多方面架构了一个不再通向形而上学批判的此岸世界。在权利与逻辑的“中心”逐渐被后现代主义者们抛弃的同时,判断的标准也随之失去,普通文化精英的阅读体验、宗教体验、社会体验、哲学体验等实践体验成为了重新架构“上帝”治下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人们在精神上没有了统一的认识而更倾向于承认生产群体、政治群体、科学群体及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群体。
在希腊-犹太教化了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构建下的当代社会中,在当代社会纷繁复杂、高速流通的生活信息、文化信息、宗教信息中,隐藏着的其实就是:不断地被挖掘而被削平了的深度,不断地被改造而被抹杀了的社会历史,不断地被分割而被零散化了的人格主体,不断地被超越的科学技术、技术性变革、科学性的学术探索,被缩短了的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被整合或分割了的人格。因此,深度被削平、历时感消失、主观意识客体化、文化距离感消失、本体的物质化这五个方面,成为界定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特征。同时,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上,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也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作家通过作品对人的群体关系的合理性进行批判,进而呼吁一种生存的独特性和差异性的美感,以便从中发现仅能被自身认可的人生价值。这种后现代框架下新的美学意识的确立从萨特明确地提出“他人即是地狱”开始。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意识地描写了主人公们的恐惧、怀疑甚至是厌恶某些社会关系的生存状态,主人公们普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法达到纯粹的心灵沟通,这些人物总是生活在一种极为封闭、单一的空间里,拒绝与现实建立一种积极的互动联系。作品的主人公们面对死亡无动于衷,有些作品的主人公则莫名其妙地陷入一场政治旋涡中无法脱身,有些主人公们在面对某些重大事件的时候,从积极参与到逃避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到彻底拒绝对所有宏大叙事、道德伦理上的说教,逐渐地放弃自我意识。从表面上看,他们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对眼花缭乱的物质社会没有兴趣,而实质上,这正体现了他们对整个社会价值谱系提出的无力的控诉、批判和拒绝,是以作为个体的人的形式控诉着这个社会对人的整体的无差异异化之后的反抗。
(二)作家通过描写对人生理想、对宏大叙事的质疑,进而追求“何为生活”“何为生存”“何为信仰”的生存方式作为重新实现自我价值的出路。这是在后现代框架下,新型的“流浪汉们”在新型社会结构和新型宗教形势下的自我重塑行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对这一切旧有的社会价值谱系的不信任,必然会导致读者在宏大叙事之下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质疑,从而产生出对现有的人生理想的彻底否定。由传统文化所筑造起来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哲学、宗教、经济、体制的变革下崩落之后,作为个体的人,几乎不可能找到可能存在的精神归宿。这也决定了后现代主义作家笔下所塑造的那些主要人物不可能重新回归到某种具有共识的理性层面上来,而只能处于某种被陌生化了的另类状态下,既无所事事又无所适从,这是人在被群体性异化后,被商品化、符号化并随之进入流通领域,成为生产要素、文化符号、民族符号、集体符号之后,局部群体化、物质化的结果。戈德曼在他的《论小说的社会学》一书中这样总结道:大约从卡夫卡开始,直到当代新小说,并且尚未结束,它的特征就是放弃用另一种现实来努力取代有疑问的主人公的任何尝试,以便写作没有主体的小说,其中不存在任何正在进行中的追求。总之,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是当代人类社会中系统生产符号化、管理体制伦理化、历史文化文明化后果的具体体现。
(三)作家通过描写主人公对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情爱关系、伦理关系、道德关系等(包括爱情关系、血缘与非血缘关系、生产系统中符号化的人际关系等)重要成素关系的质疑,质疑与批判文化、宗教、体制、历史、话语、权利等“虚拟性原则”的合理性。其中,现实中的知识构架、民族意识、个体存在感、文化传统、时代风格等方面,统统被游戏的文字所消解。在大量的文化记忆与生活记忆中的专横的父母、严肃的老师、街头的流氓、不务正业的朋友、变态的侠士、愚昧的人群、混乱的生活、具有世俗精神的普通知识结构与信仰构成,构成了新的愉悦方式,既充满了解嘲、又充满了讽刺性的批判,以此,形象地反映真实的认知生活,普遍地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差距、金钱与权利的差距、人性与生存状态的差距。旧的意义系统、旧的理性价值、旧的社会原则成为后现代作家新的审美意识的批判客体,用以适应现实生活下的、不断变化的认知信息与体制体系的不断被刷新。后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制的消解和颠覆,既是新型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新型人作为客体生存状态、精神匮乏、物质化差距加大的反映,不仅是创作主体对一切意义系统以及意义生成的理性价值的怀疑和否定,还体现了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对后现代审美的不自觉的尊崇[4]。
总之,后现代艺术以怪诞的形象、虚拟的空间与时间、真实的实践、机械化的叙事、矛盾多变的艺术结构、缺乏语言逻辑的创作手法,来表现当代社会全景式的后现代存在方式,其影像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仅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叙事逻辑,还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理性逻辑、语言逻辑、图像逻辑、意义逻辑等等精神原则的各个方面,然而,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正是因为后现代社会建立在众多历史实践上的各种潮流之中,后现代社会才表现出了如此花样繁多的社会联系、物理联系、精神联系等内在社会结构,在这里,作为解构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理论基础,后现代理论以其横向发展的大众与历史的关系、阅读与语言的群体体验,表达着后现代理论方面最为反叛的变革思想。后现代主义理论体系在建构的过程中,其理论体系的不确定导致了各种争议的出现,但同时,无论在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方面还是在后现代主义艺术理论批评的发展方面,后现代主义理论都表现出鲜明的不确定性特征:它似乎既不存在确定的起点,也不存在确定的流派,更不具备确定的指导思想,更是充分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体系的不确定性。
[1] 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M].张志扬,邓晓芒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2] 徐蕾.从叙事学到互文性[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
[3] 杰文逊.当代国外文学理论流派[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4] 洪志刚.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标本——吴玄小说论[J].小说评论,2008(6):98-104.
(责任编辑:刘士义)
On the social root of the change of the post-modernist literary theory from pluralism to the diversity
WANG Qiuqiu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AnshanNormalUniversity,AnshanLiaoning114007,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art,the post-modern art and science came into being.And it i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art.The post-modern art began to emerge in endlessly in the world.The post-modern art can break the continuity of time and space,and it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st-modern art and modern art.It aims to reach such a process:with the bolshy material form,transfer the pluralistic modernist into commodity diversification.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gradient proces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termine the forming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modern art theory.
post-modern;literature;ethics;group;consanguinity;bolshy
2016-04-25
王秋秋(1978-),女,辽宁辽中人,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I02
A文章篇号1008-2441(2016)03-006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