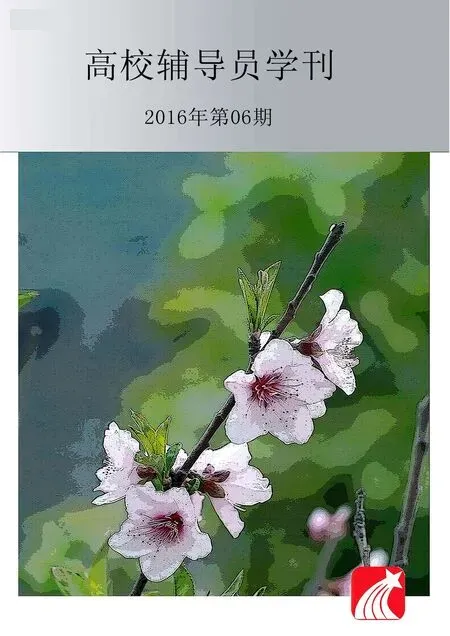“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
——从朱自清《经典常谈》阅读史谈起
陈文忠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
——从朱自清《经典常谈》阅读史谈起
陈文忠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一、《经典常谈》75年阅读史
作者是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其作品最权威的阐释者。1942年初,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了《经典常谈》并写了“序”,这部著作迄今已有75年的生命史,同时也已有75年的阅读史。《经典常谈》75年的阅读史,折射出的是一百多年来,在整体性反传统主义背景下,在持续不断的“废经”声中,有眼光的新文学家和现代学者,为经典辩护,为“经典训练”辩护,为传统文化辩护的曲折历程。不过,这是一个欲说还休、进一步退两步的艰难历程。
朱自清的自序,是为《经典常谈》辩护。他的辩护,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二是写作此书的理由:“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三是此书的自身特点:经典训练需要理想的经典读本,“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1]4。这三点辩护,前后两点明确地道出了本书的意图和用途,对我们今天阅读此书,依然是切要的指导原则。不过,把“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作为写作此书的理由,虽然说得辩证而机智,但无论如何,总让人有一种底气不足,强为之辩的感觉。“读经的废止”,就是“不读经典”;“不读经典”,又怎样进行“经典训练”呢?进而,既然“废止”了读经,再去“训练”读经的能力,还有什么用呢?
然而,只要我们了解了民初以来一拨又一拨的“废经”运动,了解了五四以后新文学家们批判“四书五经”,批判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就能理解同样是新文学家的朱自清,为什么要用“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这句机智的矛盾语来为《经典常谈》辩护了。朱自清当然比我们更清楚这一背景,《序》中的下面一段话,正概括了此前三十年“废经”与“读经”的交锋史:
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古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有“使学生从本国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1]3
这段话一波三折,内涵丰富。首先,朱自清站在新文学家的立场,批判了旧日“读经教育”的偏枯失调;这实质也是民初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废止读经”的基本理由。接着,回顾了民国以来“一两回”读经运动“失败”的历史。仔细说来,不是“一两回”,而是“三回”:一是民初(1905年)康有为与“孔教会”的“尊孔读经”;二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章士钊主政教育部时决议中小学的读经;三是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辟“读经专号”讨论学校的读经问题。三十年“三回”的读经运动,都“失败”了。其中,“十四年的读经”为时最短,影响却最大。因为,鲁迅写了《十四年的“读经”》,对读经和读经派作了最彻底的批判。鲁迅的判词,影响了此后近百年的废经史,也影响到《经典常谈》75年的阅读史。不过,首先影响到的应是《经典常谈》的写作,这时朱自清只能搬出“教育部制定的课程标准”来为自己辩护,并最后说出了“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这句机智的矛盾语。一个学者搬出教育部门的“红头文件”来为自己的学术行为辩护,这无论如何让人有一种学理不足、底气不足之感。不过,了解了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我们就知道,这是深知传统不能割裂,薪火必须相传的朱自清,所能说出的最圆融、最智慧的话了。在稍后发表的《古文学的欣赏》开头,朱自清几乎用同样的理由来为自己提倡“古文学的欣赏”辩护。
叶圣陶是除作者之外,《经典常谈》阅读史上最重要的“第一读者”。1945年,他写了《读<经典常谈>》,1980年,他又写了《重印<经典常谈>序》。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显示出叶圣陶对经典和读经的态度,在朱自清“进一步”的基础上,似乎“退了两步”。1945年的文章中,叶圣陶认同朱自清“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这句开宗明义的话。然后,笔锋一转,又对直接的“经典训练”作了坚决的否定:
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2]35
赞同“经典训练”,却声称“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这种“买椟还珠”式的主张,显然是有违朱自清通过《经典常谈》“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的“本心”的。1980年的“重印序”,叶圣陶似乎又后退一步,他说:“在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对朱先生和我自己的这样考虑——就是,经典训练是中等教育里的必要项目之一——想有所修正了。”“修正”后的结论是:“我想中学阶段只能间接接触,就是说阅读《经典常谈》这样的书就可以了。”[2]120
20世纪的中国语文教育,是以反传统为背景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读经”到“废经”;二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三是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把“文”从“经、史、子”中独立出来。深入了解这一教育文化背景,了解1945年和1980年的社会思想背景,叶圣陶的“退两步”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读者”的意义,在于奠定阅读史的基调。叶圣陶的看法,以其在语文教育界的崇高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经典、对“经典训练”、对《经典常谈》的看法和评价。二十年后的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把《经典常谈》收入“蓬莱阁丛书”出版,钱伯城先生撰写了长篇“导读”。“导读”开篇,钱先生细心地指出,《经典常谈》“可以同时适应三个层次读者的需要”;继而谈到“经典训练”问题,钱先生马上亮出“废经”的坚定立场:“我们知道,经典训练并不就是恢复读经教育。恢复读经教育是开倒车,这是‘五四’运早已解决了的问题。”[3]3转而,钱伯城先生以大量篇幅指导我们欣赏《经典常谈》的“散文特色”、“通俗化手段”,以及“采择近人新说”和朱自清“平和宽容”的学术器度等等。钱先生的这些论述精辟而精彩,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作者,认识作者的学问,认识作者用散文手法介绍古代经典的本领。然而,我总感到有一点缺憾,那就是没有像朱自清所期望教育者的那样,最终目的是“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
回顾《经典常谈》75年阅读史,可以发现,从朱自清、到叶圣陶、再到钱伯城,有一个共同立场,那就是首先坚定撇清与“读经”的关系,然后再来谈经典,谈“经典训练”,谈《经典常谈》。那么,“读经”真的那么可怕吗?不“读经”怎么进行经典训练?“四书五经”究竟是洪水猛兽还是民族瑰宝?
二、“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
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语文教育史,是“废经”与“读经”的交锋史。自民国初年废止读经后,几乎每十年都有人发起一场读经运动。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者“国学热”,读经活动在民间兴起,在社会推广,并逐渐深入校园课堂。
从晚清民国到改革开放后的共和国,为什么不断出现国学热,为什么不断有人发出读经呼声?对这种不断出现、不断重复的文化现象,是不能简单斥之为“复古”、“保守”、“开倒车”的,其深层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一种思想观念或学术思潮的兴起和衰亡,无不具有社会文化的必然性,其背后无不体现了特定时代人们的心灵诉求。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是当今西方世界呼吁“阅读经典”的著名学者。他在研究西方文学史上“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西方正典》中,有一句名言:“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在第一章“经典悲歌”的结尾,布鲁姆写道:
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经典,因为不管我们是谁,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莎士比亚赐予我们的不仅是对认知的表现,更多的是认知的能力。莎士比亚与其同辈对手的差异,既是种类的也是程度的差异。这一双重差异决定了经典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4]29
那么,为什么“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实质上,歌德老人早已给我们作出了回答: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前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再思考而已。[5]3
歌德所说的“前人”,指的是哪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处于笼统理解的状态。当我读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了解了他关于“轴心时代”的深刻论述,恍然大悟:歌德所说的“前人”,就是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
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出现在什么时期?雅斯贝斯认为,可以“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人类最不平常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例如,“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总之,“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源端”。这也是轴心时代最重要的特征。
雅斯贝斯进而指出,“轴心时代”的文化,在轴心期以后的世界历史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写道: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6]14
雅斯贝斯认为,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不断回顾“轴心时代”的文化冲动,从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就是“六经”的时代,就是“诸子”的时代,就是“孔、孟、老、庄”的时代。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不断出现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正是这种回顾“轴心时代”的文化冲动的表现,其深层动机就是从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从中获取历久弥新的生命智慧。“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雅斯贝斯的思想,同样包含在鲁迅这句智慧的格言中。
“现代人”是多么傲慢啊!傲慢的现代人无不抱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偏见:既比上一个时代的人更聪明,也比下一个时代的人更睿智。真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自我为老大!在傲慢的现代人看来,历史从我开始,我在开创未来,几千年前的古人古书,怎么可能为现代人指点迷津,怎么可能给现代人以智慧启迪?
然而,《圣经》作了肯定回答:“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谢灵运作了肯定回答:“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钱锺书作了肯定回答:“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古今哲人对文化的古今相通性的肯定。
为什么文化具有古今相通性?为什么我们需要到经典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朱自清说得好:“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7]27我愿对这句“常谈”更进一解:文化是生命的升华,生命的一次性决定了文化的重叠性。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次性,决定了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而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层累重叠性。扩而言之,人类文明五千年,个体生命一百年;个体生命是重复,文化生命是重叠。因此,五千年的哲学史,是百年人生问题反思史;五千年的文学史,是百年人性情怀咏叹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千年的人类文化,只有一百年的生命长度。因此,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够以个体百年生活史,理解五千年人类哲学史;以个体百年情感史,体验五千年人类文学史。
杜牧《阿房宫赋》曰:“嗟呼!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陆象山《杂说》曰:“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所谓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质必然。这一切的深层根源,就在于生命的一次性所决定的文化的重叠性。因此,历史是教育的核心,经典是智慧的源泉;割断了历史,失去了经典,我们将一无所有。“历史从我开始”的无知之见,是以庸俗进化论为基础的线性时间观导致的对人类智慧史的误会。
经典是传统的载体,传统依赖经典得以延续,读经典就是学传统,学传统必须读经典;
经典是智慧的源泉,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都已经思考过了,没有经典,我们就会停止思考;经典是心灵的导师,个体的精神发育史,是一个人的经典阅读史,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品味和阅读经典的水平;经典是治学的起点,读透一部经典,学会一种方法,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门学问。
三、“经典训练”必须“亲近经典”
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经典训练,必须亲近经典。《经典常谈》由13篇关于经典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构成,其目的是“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朱自清说:
如果读者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1]4
75年前,《经典常谈》是为当时的中学生写的,朱自清的“本心”是“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今天,《经典常谈》被列入“国学修养”必读书,大学生们更应当“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亲近经典,见识经典,到源头去喝水!
那么,当今的大学生,无论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亲近”、“见识”了哪些经典,可以算具备了基本的“国学修养”?《经典常谈》前九篇论及的10种书,除了《说文解字》,当然都是首选读物,但只涉及经、史;后四篇谈到的诸子、辞赋、诗、文,因为书太多了,只叙述了源流。
书目是治学的门径,也是亲近经典的门径。这里不谈纪昀的《四库总目》,也不谈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对当今大学生有点“大而无当”。让我们且从20世纪20年代,胡适和梁启超分别为当年清华学生开的两份“国学书目”谈起。
1922年冬,胡适应清华学生要求,开了一份书目,题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所列书籍共184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要说明的是,是184种,而不是184本;其中,《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唐诗》、《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等等,此类总集性的书籍,只算一种。此书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华周刊》一位记者的来信置疑,认为胡适所说的国学的范围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学史,而单就思想史和文学史而言,又显得太深。随后,梁启超也发表了《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提出批评,认为书目的“误处”,一是“在不顾客观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二是“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适的”。[8]102
1923年春,梁启超应《清华周报》记者要求,也开了一份题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书目。梁启超在书目“前言”中写道:“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他的书目包括五大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廿四史算作一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浏览书类,30种。总共141种。梁启超的书目,不仅列出书名,每种书之后大都有导读式的说明。因此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启超的书目显得道高一丈;他所撰写的简明扼要的“读法”,即使在今天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不过,梁启超随即发现,这份总共141种书的书目,与“初学”所需,仍不能吻合,于是又拟了一个《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其文不长,转录如下,以备参考:
右所列五项,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所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
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记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9]207
这份“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按经、史、子、集顺序排列,共25部,除《资治通鉴》、《宋元明史记事本末》、《文选》这三部是大书外,其余22部篇幅都不大。而把《四书》至于《五经》之前,置于书目之首,是有特别用意的。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把《论语》、《孟子》置于开篇,并写下了全目篇幅最长的导读。他指出:“《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头,《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9]253并对《论语》、《孟子》最重要的注疏版本,从朱熹的《四书集注》、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孟子正义》等等,作了扼要介绍。
在书目之后,梁启超又特别指出:这份《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并非只对“文科生”而言,“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这份《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也是作为“中国学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修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与梁启超的“必读书目”,只要做一仔细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思路和范围是何其相似啊!在我看来,今天的文理科大学生,若能细读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进而尽可能多多“亲近”梁启超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就能获得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也可以无愧“中国学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称谓了。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6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2] 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
[3] 朱自清.经典常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 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M].程代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6]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7]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 胡适. 胡适文存(第2册)[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
[9] 梁启超.饮冰室书话[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俞晓红)
陈文忠(1952-),男,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0.13585/j.cnki.gxfdyxk.2016.06.020
G641
A
1674-5337(2016)06-00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