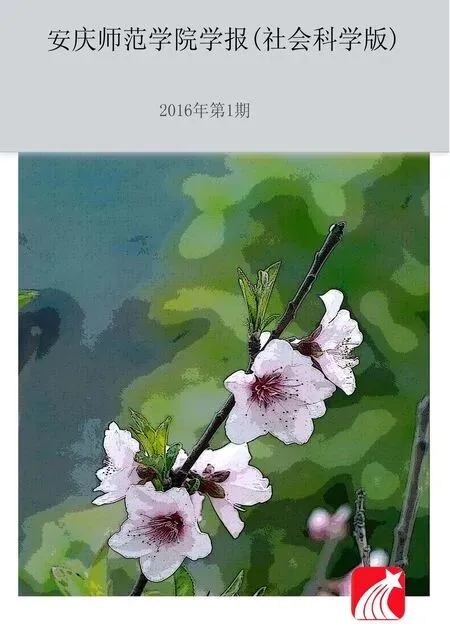清初科举生态与戴名世的时文理论
洪 桐 怀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北京 100083)
清初科举生态与戴名世的时文理论
洪 桐 怀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戴名世的时文理论建立在他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时文的反思与批判之上。戴氏在桐城派作家中首次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这种“援古入今”的思路加以阐释,试图合古文与时文为一体,给时文创造一种新的局面,以文风之变促世运之变。戴名世的时文理论和实践不仅体现了戴氏较强的“问题意识”,而且直接开启了方苞关于古文与时文的诸多主张,对桐城派影响颇深。
关键词:科举制度;戴名世;时文理论;援古入今
在明清科举笼罩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古文乃一种雅正的文言官话,是承载传统文化的主要语言形式;时文乃官方选举人才的规定文体,是读书人进身仕途的必经之路,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多数读书人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桐城派作为清初颇具影响的古文流派,与时文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是方苞的古文理论,被指“在内在精神上与八股相通”而招致学界很多非议[1]。值得注意的是,后世论者在论及桐城派“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时多将其追溯到方苞的义法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明清文学的发展走向,这种“援古入今”的思路并非桐城派首创,而是明清以来文坛的一种共同趋势,而且,桐城派作家中对此问题的首倡者亦非方苞,而是戴名世。戴名世的时文理论直接开启了方苞的论文思路,方苞的很多文章思想与其一脉相承,他的义法理论是对戴名世时文思想的深化与拓展,使得古文沟通时文的方向和努力都有了更为具体的路径可求。唯其如此,结合清初科举文化生态来探讨戴名世的时文主张和思想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
科举是从隋朝正式建立的考试选拔制度,经历唐宋发展日益完善,至明清两朝达其鼎盛。清代开国之初,于顺治三年开科取士,沿用明代八股取士的方法。至康熙朝,科举制度作为清初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沿袭前朝科举体系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变革,形成了从童生到庶吉士更为完整、严格的考选制度。
自明末清初以来,关于科举的研究和评价,一直伴随着科举的施行和发展,直到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最终被废除的这一历史事实,使得多数论者都将科举作为一种鄙弃的对象而加以抨击,但对于这一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却往往忽略不论。
钱穆先生曾言:“总观国史政制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惟其如此,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所不能摇,宰相所不能动者。”[2]钱先生在这段不失公允的论述中,将科举选拔人才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演进的一大推动力,并且说明科举相对于皇权和相权的独立性,充分肯定了科举的作用。实际上,清初科举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清代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学术、文学等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清廷统治者将科举作为教化与选拔人才的一种有效途径,无不认真加以对待,仅从清代科场案惩罚的力度之大就能看出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重视。
近些年,作为与有清一代几乎相始终的一项文化制度,科举及其赖以存在的主体形式八股文(时文)对清代的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已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可是,相对于历史学和社会学对科举制度的兴趣与重视,有关清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蒋寅先生指出:“盖明清以来对八股文的鄙弃和抨击,已使这种文体及其写作难以进入当代的文学史叙述。这一看似顺理成章的结果,无意中竟伤害了文学史生态的完整——当八股文这一庞大的写作事实被文学史话语遮蔽时,明清时代笼罩在科举阴影下的文学生态也部分地被遮蔽了。”[3]既然八股为明清两朝的流行文体,举业是士人谋求仕途的必由之路,在经典学习的基础上如何处理时文与古文的关系,进而使二者发挥良性互动而非相互排斥的作用,就成了当时读书人赠序与书信往来中经常性的话题。
桐城地处江南文化繁盛之地,自明代以来就形成了人文荟萃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读书、科举而走上仕宦之途是多数读书人的选择。据道光七年《桐城续修县志》记载,明清两代桐城有进士265人,举人589人,其进士和举人之多,远超临近郡县[4]。正因此,科举之风带来文学之盛亦是考察桐城派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桐城派作为有清一代最大的古文流派,其绝大部分作家在创作古文的同时也是时文名家,对时文都有一番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桐城派早期作家戴名世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方苞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他们既是科场成功者,又以时文名天下。如此一来,桐城派作家与科举的联系便成了研究桐城派绕不开的话题。
我们看到,自戴名世、方苞主张“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以来,关于桐城派与时文关系的批评就一直存在,尤其是五四前后和上世纪六十年代,受意识形态的主导,对桐城派批判的理由和标准主要都依据其与八股文的关系。但是,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与其作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不如深入当时的文化生态之中,以“同情了解”之心态,考察他们面对的困境以及面对困境时的反思与突破,借此加深对文学史上这一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的认识与理解。
二
《清史稿·戴名世传》记载:“(戴名世)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淹郁,气逸发不可控御。……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5]468从戴名世的简单经历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和清初所有士人一样,戴名世选择的也是一条以科举谋求功名的道路。尽管戴名世在文集中多次为自己从事科举之业开脱,然而,这一代读书人的矛盾恰恰在于,不愿从事时文却又不得不为之,批判八股之后往往又不得不以课授时文为生。戴名世虽多次称述自己不好时文,教授时文乃是不得已的选择:“余本多忧,而性疏放,尤不好时文”、“余非时文之徒也,不幸家贫,无他业可治,乃以时文自见。”但他在时文领域的造诣却为世所称许,从他的自叙中我们可见一斑:“故余生平之文甚多,然皆出于勉强,非其中心之好,而散佚零落不自收拾者,不知其几矣。箧中所存尚无虑五百余篇,往者常自择别,分为两集,集各近二百篇,韩公及武曹、大山、百川为叙而行之于世。海内学者,翕然信之,不以为非,转相购买,几于家有其书矣。”[5]118-119家有其书的盛况说明戴氏时文在当时颇有市场,据其年谱我们可知,戴氏授徒时曾自编有《意园制义》,“告以文章之源流,而极论俗下文字之非是”[5]123,坊间还刻有《戴田有四书文》、《戴田有时文》。他亦整理过自己的时文集,编为《自订时文全集》。“举业之家辄多以文章相示”以求指正,可见戴名世的时文在清初士人中间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从他自述的语气中亦能感到一种自得与自负。
八股被称为时文,当然是相对于传统古文而言,就其所承载的经义内容而言是一种知识形态,就其形式而言又是一种文学形态,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受人诟病,在大部分读书人的眼中,八股时文不仅没有促进知识和文学的发展,反而起到了阻碍知识和文学的作用。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面对明代灭亡的沉痛反思,当时的士人儒者对八股文均给予了相当激烈的抨击与批评,明清之际的大儒如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对八股和科举均有所批判,可以说,批判八股是易代之际士人的一种共识。其中尤以顾亭林的批判最为尖锐并具代表性。其《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一条说:“今满目皆坊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辑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6]又其《生员论》曰:“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7]顾亭林对八股的批判主要站在尊经、尊学问的立场,认为八股无益于学问,八股使人不学,其主要锋芒不是针对经义的内容,而是针对八股的形式,而他对八股形式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八股自身,不如说是针对明末以来形成的世俗和流弊而发。
到了戴名世生活的康熙年间,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更加激烈,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并基于自身的学习体会,戴名世虽为八股名家,但他对八股文的批评,不亚于清初任何学者。翻检戴名世文集,随处可见他对科举的批判。而且他能追本溯源,觉察出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端。例如,他认为明季文武大臣的缺乏识见,贪赃枉法和自树门户等弊病,都是科举制度失败的结果,进而提出“亡明者,进士也”的观点:
呜呼,当明之初,以科目网罗天下之士,已而诸科皆罢,独以时文相尚,而进士一途遂成积重不反之势。二百余年以来,上之所以宠进士,与进士之光荣而自得者,可不谓至乎,然而卒亡明者进士也。自其为诸生,于天人性命、礼乐制度、经史百家,茫焉不知为何事。及其成进士为达官,座主、门生、同年、故旧,纠合蟠结,相倚为声势,以蠹国家而取富贵。当此之时,岂无有志之士,振奇之人,可以出而有为于世?乃科目既废,而偃蹇抑塞,见屈于场屋之中,徒幽忧隐痛,行吟于荒山虚市而无可如何。[5]58
此外,他又指出,“自科举之制兴”,天下便没有真正读书的人,把天下之事交给他们管治,自然会把“天下之事”弄致“决裂”。虽然,当科举之制初兴时,亦不是完全没有人才,当时“在上者长养以为廉耻,而在下者亦不务为苟得”,所以“功名犹有可观”。可是到了“晚节末路”,大小官员“相习为速化之术”,从此“风俗之颓,人才之不振,其流祸至于不可胜言”,这就是他“叹息痛恨于科举之设”的原因[5]136。至于科举制度腐败的原因,戴名世认为是以科第为人生最终目标的错误观念所致。他指出,“自科举兴”,便很少有士人能够“以功名垂于世”。因为他们“研精覃思”,不过“从事于场屋之文”,参加科举考试。成功者,“往往登高第,为大官”,而流俗的人,“相与艳羡”他们,而他们“亦莫不自以为功已立,而名已成”[5]87,“今之世尤可患者,有所为科第之文,世皆从事于此,而不知更有人生当为之事”[5]21。
戴名世认为“制科之不足以得士”,是因为士人在“举业而外”,其他如“古文辞”,“至于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之属,凡圣人之大经大法,而伥伥焉一无所知”。他引汪武曹的话慨叹道:“时文兴而先王之法亡。世之从事于举业者,冥冥茫茫,不以通经学古为务,其于古今之因革损益,与夫历代治乱废兴之故,无所用心于其间。则虽其文辞烂然,而识不足以知天下之变,才不足以应天下之用,是举业有累于先王之法也。”[5]100戴名世对明代以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受讲章时文之荼毒”,固然痛心,而清廷不以明代的覆辙为鉴,“踵之者愈甚,而世益坏”,更使他扼腕痛恨。另一方面,士人研读经义和八股,不过把他们作为“奔走势利之具”,因此,名为读四书五经,名为代圣人立言,其实是败坏了这些经典、歪曲了圣人的言论,所以他痛斥“四书五经之蟊贼,莫过于时文”。又批评士人“当大比之年”,每每拿取他们所研治之经,“删而阅之”,选择其中可以命题的,“为雷同腐烂之文,彼此抄袭,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入格”。由于“士风之苟且至于如此”,五经岂有不芜没的道理?他在《自订周易文稿序》中指出《周易》遭遇俗儒与时文之徒的毁坏:“先是余之学《易》也,一二师友皆教余勿看讲章,勿听俗儒讲说,余从之,果有得焉。已而见近世所刻衷旨诸书,其荒谬不通不可胜举,而时文总之,而《易》几亡矣。自始皇、李斯焚烧诗书百家之语,而《易》独不与其祸,至今几二千年,而乱于鄙夫小生之训诂与科举之业。”[5]60总结经义与八股的流弊,戴名世作出了与顾炎武一样的判断,得出“今夫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的结论[5]138。
此外,戴名世认为科举和八股不但荒废经学及窒息读书风气,而且形成一种庸俗的文学观念。因为他们从事科举时文,不外“以为文学者而趋利,其收效而获多,必倍于农工商贾。”由于习文学的人唯利是尚,于是那些不是“奔走势利之具”的文体,就无人问津了。他以“论”这一体裁为实例,说明了文学盛衰与科举的关系:
文章风气之衰也,由于区古文、时文而二之也。时文者,时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于下,下之所以为得失者,则今之经义是也。至于论者,则群以为古文之体,而非上之所以取于下,下之所以为得失者,则遂终其身而莫之焉。夫经义者,天下之人,童而习之,至于白首而犹茫不得旨趣,而况于论者,群震以为古文之体,且又以为非功令之所在,而终其身而莫之为。以朝夕从事于时文犹茫不得其旨趣之人,而使之为古文,宜其惊愕皇惑而不能执笔也。顷者功令又以小学论一篇试童子,与经义而并行,则是时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于下,下之所以为得失者,将又在于论,论亦且化而为时文。时文之谬悠庸烂,浸淫蔓延,屡救而不能振,于今数十年,而令又以其谬悠庸烂者出而为论,于是乎经义与论且同归于臭败而后已。[5]90-91
作为一个拥有强烈时代感的读书人,戴名世对科举制度败坏文风和文运,自然痛心疾首。在他看来,“今之世所习者时文耳,时文之徒未闻有廓然远见,卓然独立者也,即其所习之文,不过记诵熟烂之辞,互相抄袭,恬不为耻,然亦止用是以为禽犊而所以邀虚名,而希苟得者又不区区尽恃乎此,而特其心则不无好同而恶异,苟有异己者之出于其间,辄相与诽笑诟厉,不壅蔽遏抑之不已。”[5]17科举风气如此,文运的衰颓也就可想而知。
基于以上认识和批评,戴氏认为士人若要卓然自立,“必去其富贵科第之见而后可与共功名”,“必罢去场屋之文而后可与语读书”[5]87,而且他坚持“欲天下之平,必自废科举之文始”[5]109、“讲章时文不息,则圣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扫除而更张之无疑也!”[5]137从戴名世这种愤激的话语表述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是传统文人在易代之后道统失落的时代氛围中所产生的一种焦虑与不满。
三
诚如上述,在清初科举文化环境中,批判时文是当时学界的一种时髦话语,发点牢骚并不太难,但是批判并不等于可以逃避,科举虽有诸多弊端,但它是通往权力、财富和声誉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途径。除非绝意仕途,遁迹山林,否则不得不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排斥八股却又不得不为之。因此,我们在戴名世、方苞等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文集中,常常看到一种对时文言不由衷或相互矛盾之处。
那么,一种现实的策略为:既然举业无法逃避而耗费了人生大部分的光阴,就有必要寻找一种出路来给时文创造出新的局面。
清初有不少思想家提出废除科举的言论,但戴名世亦很清楚,在现实社会中,这无异于一个空想,“天下之士非科举之文无由进”[5]132。因此,戴名世提出种种改良八股文的方法,并身体力行地通过写作、评点、选文等努力,企图给科举注入一些新鲜的养分。而这种近乎绝望的努力,同样是基于对一个儒者应尽的社会责任的理解,所以他为自己写作时文辩护说:“余之为是也,非苟易也。根柢于先儒理学之书,未之敢失也;取裁于六经诸史以及诸子百家之言,未之有遗也。”[5]123
如前所述,戴名世认为文风的败坏是由于“区古文、时文而二”造成的,所以他提出“以为时文者,古文之一体”,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体现了其补救划古文与时文为两端造成的流弊而欲沟通二者的意图,这也是他在无奈的社会现实面前采取的一种通融妥协的办法。其论曰:“夫所谓时文者,以其体而言之,则各有一时之所尚者,而非谓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为之也。今夫文章之体至不一也,而大约以古之法为之者,是即古文也。故吾尝以谓时文者,古文之一体也。而今世俗之言曰:‘以古文为时文,此过高之论也。’其亦大惑矣。”他指斥时文之法“谬悠而不通余理,腐烂而不适于用”,是“竖儒老生之所创,而三尺之童子皆优为之。”至于古文之法,“则根柢乎圣人之六经,而取裁于左、庄、马、班诸书”,两者高下优劣显而易见。学习制举之文应由古文入手,“不从事于古文,则制举之文必不能工也”[5]88-89。因此他提出时文与古文宗旨一致的说法:
余平居读书从事文章之际,窃以为制举之文,亦古文辞之一体也。世之人废古文辞不观,而别有所以为制举之文,曰“时文之法度则然”,此制举之文之所以衰也。今夫文之为道,虽其辞章格制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此自左、庄、马、班以来,诸家之旨未之有异也,何独于制举之文而弃之。且夫制举之文,所以求得举也,然而得失之故,初不系于此。其得之者,未必其文之皆工也;其不得者,亦未必其文之果不工也。而特君子之所以为之者,必不肯卤莽灭裂以从事,而得失之数不以介于心。是故其制举之文即古文辞,其旨莫之有二也。[5]105
“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的观点,在戴名世文集中多次出现,可视为他论文的一个核心观点。如《送萧端木序》中说:“盖余平居为文,不好雕饰,第以为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文如是,止矣!”[5]135又如《与刘言洁书》中:“仆平居读书,考文章之旨,稍稍识其大端。窃以为文之为道,虽变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即至篇终语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5]5在此,戴名世从文章追求自然的风格与旨趣的层次上来沟通古文与时文,揭示了思考时文与古文关系的一种思路。
既然古文与时文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自己的体制与要求,那么沟通古文与时文,也必然从这两个方面来入手。从戴名世对时文的批判来看,他主要将焦点集中在时文内容的庸陋上。时文以经义为主要考察内容,所谓经义就是其阐述的义理必须根于经,不能脱离儒家所规定的经典,从这些经典引申和阐发义理。戴名世认为阐发经义就是“从数载之后而想像圣人之意代为立言,而为之摹写其精神,仿佛其语气,发皇其义理。”他还以画画为喻,其境界的高低在于能否“传神”,“代圣人立言”就是要深知圣人之意,亦能做到传神。如何达到这一境界?他说:
夫惟沉潜反覆于《论语》、《孟子》、曾子、子思之书,以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与夫濂溪、横渠、明道、伊川之所论著,考亭之集注,并其师弟子间往复辨难答问之言,贯穿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因遂旁涉于《左》、《国》、庄、屈、荀、韩、马、班、韩、柳、欧、曾、苏、王之文章,夫而后一题入手,相其神之所在而举笔貌之,而圣人之天可察,而圣人之意可得矣。[5]99
方苞所谓“言本心之声,而以代圣人贤人之言,必其心志有与之流通者,而后能卓然有立也。”[8]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戴名世学习时文的经验与学习古文实为一途,这又在学习的方法上沟通了古文与时文。
戴名世又引述前朝艾南英的观点,指出时文“道”、“法”、“辞”三者兼备的要求:“在昔选文行世之远者,莫盛于东乡艾氏,余尝侧闻其绪言曰:‘立言之要,贵合乎道与法。而制举业者,文章之属也,非独兼夫道与法而已,又将兼有辞焉。’是故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5]109“道”固然代表了圣人之言,“法”又分为“行文之法”和“御题之法”:“御题之法者,相其题之轻重缓急,审其题之脉络腠理,布置谨严,而不使一毫发之有失,此法之有定者也。至于向背往来,起伏呼应,顿挫跌宕,非有意而为之,所云文成而法立者,此行文之法也,法之无定者也。”既介绍具体的如何御题,又有抽象的行文之节奏,便于学习者领悟掌握。如此一来,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结合,还需要“又贵其辞之修焉”。戴名世指出“辞有古今之分”,所谓“古之辞”是指“左、国、庄、屈、马、班以及唐、宋大家之为之者也”,“今之辞”是指“诸生学究怀利禄之心胸之为之者也。”那么,“其为是非美恶,固已不待辨而知矣”。戴氏主张博采经史以及汉唐宋诸家之长,显然针对明末以来文坛空疏风气的弊端而发。可以看出,戴名世的言论虽然是针对时文而发,但改造或者说提升时文品质的资源均来自古代先贤所流传至今的文学传统,时文与古文在戴氏思想中始终交融为一体。
看得出,戴名世在前朝文人中,最推崇艾南英和吕留良。艾南英在明末不满“天下之为选政者,以草莽而操文章之权”。艾氏认为他们所负“转移人心”的作用,其实和“宰执侍从及督学之官”等同,因此有待“大儒者”充任,为房屋之文,“别黑白而定邪正,使天下晓然知所去取”。另一方面,“当是时,释老诸子之书盛行,学者剽窃饾饤,背义伤道,汩没其中而不知出,盖文之敝极矣。千子慨然悯之,取一代之文,丹铅甲乙,辨其黑白,使天下晓然于邪正,知所去取,如溺者之遇舟而起,病者之得医而生,其功可谓盛矣。”[5]104
然而戴名世认为艾氏之书,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而引以为憾,“而近日吕氏之书盛行于天下不减艾氏,其为学者分别邪正,讲求指归,由俗儒之讲章而推而溯之,至于程朱之所论者;由制义而上之,至于古文之波澜意度,虽不能一一尽与古人比合,而摧陷廓清,实有与艾氏相为颉颃者”,“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余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5]101-102
戴名世在他的著作中,一再提及自己评选八股文取法自吕留良和艾南英。如他在己卯科“诸行卷中,录为小题文一书,兢兢奉艾氏之绪言”,又如选辑九科大题文时,所选的文章便是上接吕留良选本的年限,“以补吕氏之所未及”。如此来“使读者可以考数十年来文章之盛衰得失,而艾、吕两家之绪言,犹可于此书得之也。”其次,戴氏八股文选本编书的方法亦参照吕、艾两氏。一般时文选本只取上乘之作,艾南英编《四家合稿》和吕留良《十二科程墨观略》所辑的,均包括好坏两种。戴名世编《己卯科乡试墨卷》也是采用这种方法,使“得失互见,瑕瑜不相掩,而各为略指其美恶之所在。”[5]96
对天下士人所从事的科举之业,戴名世的建议首先是士人将眼界放宽,不“以科举富贵为功名”,不要“以从事于场屋之文为读书”。他指出“文章之事,学问中之小者;制举之文,又文章中之微者”[5]21,那么怎样才算学问有成呢?戴名世说:
学莫大于辨道术之邪正,明先王大经大法,述往事,思来者,用以正人心而维持名教也。且独立于波靡之中,而物诱不足以动其中,富贵贪贱不足以易其节。苟其得志也,持是而往,恢恢乎有余也;苟其不得志也,亦若将终身焉。此则真所谓功名者也!此则真所谓读书之有成也。[5]79
既然“时文非学也”而制科非功名也,那么大家学习时文挣扎于举业的意义何在呢?名世在编选《己卯科乡试墨卷》时透露了自己的希冀:“余之所望于有志君子者,由举业而上之为古文辞,由古文辞而上之,至于圣人之大经大法,凡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之属,悉以举业之心思力才,纵横驰骋于其间,而不以四子之书,徒为进取之资,是则余区区之志也。”[5]96
艾南英在《四家合稿原序》中说:“举业至万历之季陋极矣,自四家之文出,而天下知以通经学古为高,原其意以为圣贤之理,推而上之,至于精微广大而要当,使之见于形名、度数、礼乐、刑政,以为先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存焉。”[9]上述戴名世的言论显然是脱胎于艾氏的这篇序文,但这种欲以时文立名、立言的努力,在道统衰落的时代近乎是一种绝望的努力。
戴名世关于科举时文的批判言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其关注社会、重视现实的儒家入世精神的一种独特体现,在其观念中,时文和古文代表了两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形式,他要借着这种独特的话语来表达一种对现实和世运的关怀,像他这样具有强烈经世愿望的士人,试图通过挽救文风来改变世运,显然是明末以来以科举问政思想的继续,这实际上已为后来的《南山集》案发生埋下伏笔。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76.
[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中华书局,1996:14-15.
[3]蒋寅.清代文学论稿[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2.
[4]金鼎寿.桐城续修县志[M].民国庚辰重印本.
[5]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顾炎武.日知录[M].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936.
[7]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
[8]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00.
[9]艾南英.天傭子全集[M].道光年间刻本.
责任编校:汪长林
DAI Ming-shi’s Theory on Eight-legged Essays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ONG Tong-huai
(School of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eight-legged essays (stereotyped writing), DAI Ming-shi founded his own writing theory of eight-legged essays. Among writer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he was the first to put forward the proposal that classics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used in the writing of eight-legged essays, on which he elabor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nt and form. He tried to create a different writing style by combining the writing features of classical essays and eight-legged writings in order to change society through literature. DAI Ming-shi’s theory and practice not only reflected his strong “problem consciousness” but also inspired FANG Bao’s theories on classical and eight-legged essays, thus exerting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ongcheng School.
Key words: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DAI Ming-shi; theory on eight-legged essays; incorporate the past into the present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6)01-0001-06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1.001
作者简介:洪桐怀,男,安徽桐城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15YJ080129)。
*收稿日期:2015-10-17
网络出版时间:2016-03-09 13:49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60309.1349.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