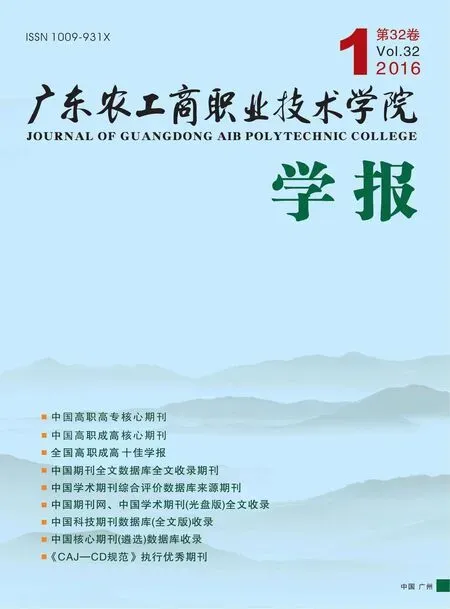农民工融城身份变迁历程中的制度跟进研究
王立娜(中共涟源市委党校,湖南涟源417100)
农民工融城身份变迁历程中的制度跟进研究
王立娜
(中共涟源市委党校,湖南涟源417100)
摘要:实现农民工身份转变是人口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当前,经由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不同程度所建构的农民工身份呈现出流动者——定居者——融入者三种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也集中反映在农民工的阶段性制度需求上。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跟进路径应充分考虑农民工融城身份的阶段性特征,以一种动态的视角来破解现有农民工制度的不均衡现状并推进农民工向市民的身份转变。
关键词:农民工;阶段性身份;制度需求;制度跟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人口城镇化以提高城镇化质量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1]人口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主要衡量指标是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城市居民人数的增加。从理论上讲,这两大指标的逆向变动应是同步的。而在我国的特殊背景下,人口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农民工数量的激增,由农民工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却迟迟未能完成。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经历流动者、定居者、融入者三种阶段性身份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推进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持。然而,随着农民工内部分化日益明显和特殊的二元制度使然,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缺失和制度不当并存,[2]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身份转变的进程。不同于既有研究往往将农民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和研究的二元对立分析思路与视角,基于农民工的异质性,以一种动态的视角,在农民工融城身份变迁历程中来重新探究农民工制度问题,将会有哪些新的收获呢?笔者依托人口城镇化的大背景,以动态的眼光来探究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阶段性制度需求,试图通过满足农民工阶段性制度需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跟进来加快农民工身份转变进程。
一、农民工阶段性身份分析
农民工融入城市不仅是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个体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3]从此意义上来讲,农民工不同的身份特征经由其不同的城市融入程度所建构。在农民工渐进式城市融入过程中,农民工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阶段性身份:流动者、定居者和融入者。依循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与农民工阶段性身份的对应关系,作为流动者的农民工其城市融入程度主要停留在经济融入层面;作为定居者的农民工其城市融入程度主要停留在社会融入和制度融入层面;而作为融入者的农民工其城市融入程度则主要基于文化心理融入层面。
(一)作为流动者的农民工
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处于流动者身份阶段的农民工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生存适应,经济层面的融入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最为关注的是在城市中的工资收入、消费水平、就业情况和居住情况等方面。近些年来,农民工在经济融入方面有了较大提高。但整体而言,农民工群体的经济地位仍较为低下,具有较强的经济诉求。从工资收入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月均收入不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2014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收入为4164元,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695元,而全国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收入为2864元,比城镇在岗职工和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水平分别低了1300元和1831元。如果再加上住房补贴和医疗补贴等,其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从消费水平来看,2014年外出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944元,比上年增加52元。另外,加上作为农民工的主要消费之一的子女教育费支出,多数农民工月均花费达至2000元左右,与其月均收入相对照,农民工消费所占比重偏高,面临着低收入、高消费的困境。从就业情况来看,95%的农民工集中在第二产业如制造业(31.3%)、建筑行业(22.3%)以及第三产业如批发和零售业(11.4%)、服务业(10.6%)里干着强度高、风险大、工时长、收入低的工作,且大多是临时工、短期合同工或是个体经营者。从居住情况来看,有近一半的农民工没有从雇主或单位那得到免费住宿和住房补贴。2014年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居住支出为445元,占去了其工资收入的15.5%。这种高成本生活与农民工的低收入现状给农民工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对于绝大部分农民工来说,通过在城市买房实现定居则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二)作为定居者的农民工
在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和住所之后,农民工开始进入定居者身份阶段。作为定居者的农民工有一个社会适应的过程,他们需要通过与城市建立良好互动,形成相应的身份认同并开始扩展自身各项资源。[5]农民工中的定居者主要追求的是城市社会融入和制度融入。他们更为关注的是社会参与、权益保障、子女教育方面的情况。相比于流动者身份的农民工,定居者身份的农民工已不再是浅层次的经济融入,而是开始重构城市社区结构,形成新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属于更深层次的城市融入。在社会参与方面,多数农民工仍愿意选择传统的休闲方式(如看电视、睡觉、打牌等),仅有少数农民工会选择现代的休闲方式(如看报纸、逛街、跳舞等);农民工的交往对象以老乡为主,多为同质性群体,与城市居民交往多为利益交往,少有情感交往,且部分农民工感觉在城市受到了歧视;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参与过城市社区选举,也没有加入过工会等团体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活动的意愿不强。在权益保障方面,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超时劳动现象仍显严峻,其中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40.8%,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4%;虽然农民工合同签约意识有所增强,但2014年仍有62%的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虽然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所占比重(0.8%)较2013年有所下降,但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额(9511元)较2013年增加了1392元,增长17.1%;虽然农民工参加“五险一金”的比例有所提高,但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率相比还是低不少,农民工参与除工伤保险以外的其他“四险”的比例均在20%以下,而有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仅占5.5%。另外,农民工能获得的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甚少。在子女教育方面,虽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率逐年上升,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农民工子女入学基本不成问题,但部分学校变相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的现象仍然存在。
(三)作为融入者的农民工
作为流动者的农民工只有完成了经济层面的融入后才能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转移,并向定居者身份转变,这一定居者身份加强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交往互动,逐步形塑了农民工的现代性,但此时的农民工还只能称得上是准市民,只有通过再社会化,形成城市认同和归属感,成为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才能向融入者身份转变。农民工中的融入者追求的是心理适应,主要关注的是城市认同、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文化心理融入方面的情况。在城市认同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城市生活更好,在城市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等。在文化传统方面,农民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习得城市各方面的行为规范、模式和制度。他们和城市居民在文化方面的沟通得到不断加深,代沟也在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乡村文化也给城市现代文化以传统洗涤,为城市社区增添了多一分温情。在价值观念方面,农民工原有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工,其重男轻女的观念明显下降,有更为理性的生育观。而他们对人生的追求也开始慢慢由满足生存需要向追求生活质量转变。
二、农民工融城身份变迁中的制度需求分析
当前,实现农民工的身份转变,需要突破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外表现形式的“显性户籍墙”和以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隐形户籍墙”。[6]就制度变迁和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农民工就业制度,还是社会保障制度,亦或是户籍制度,都是在朝维护农民工利益并促进农民工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的方向上努力。然而,在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下,农民工群体内部发生着快速分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上便是农民工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使农民工制度呈现出不均衡特征。因此,基于人口城镇化的大背景,明确农民工在其融城身份转变过程中的制度需求有利于破解当前农民工制度不均衡的现状。
(一)流动者向定居者转变:生存需求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首要的便是就业。然而,农民工因就业制度不够完备、效率性不足以及适应性不够等原因导致流动中的农民工或多或少地在用工规定、劳动合同、就业培训和职业地位等方面遭受到歧视。首先表现为用工方面的歧视。当前,虽然《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对用人单位的劳动用工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现实中多数用人单位仍以自身盈利为目的,在选聘农民工时持有明显的歧视心理,表现为选人时有偏见以及聘人后待遇有偏差。其次表现为劳动合同方面的歧视。一是农民工和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合同,发生纠纷和事故后很可能被用人单位直接辞退,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二是尽管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但多半是霸王合同。对于本是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来说,在城市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下,面对用人单位的不规范制度与霸王条款,他们中的多数只好委曲求全。更甚的是,有些单位还变相加班,农民工实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都超过了《劳动法》的明文规定。再次表现为就业培训方面的歧视。虽然当前各地劳保部门和部分企业有为农民工开设一些培训项目,但由于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的不足与较弱的职业技能以及培训项目的针对性与单一性,农民工的培训效果收效甚微。而为补充用人单位提供的免费培训项目,社会上开设的职业技能培训班多半是要缴费的。经济上的压力致使农民工通过职业培训提高自身职业技能的愿望多半落空,通过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来提高农民工的工作待遇并进而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显得异常困难。最后表现为职业地位方面的歧视。城市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用人单位虽然为农民工提供工作,但往往是一些较低层次的工作。另外,本着城市本位主义的地方保护政策,用人单位中的一些轻松安稳的工作机会也会优先分配给城市工人。
对于农民工来说,要在城市定居下来,除了通过就业满足经济诉求,居住诉求的满足也必不可少。从农民工的居住方式看,农民工在城市居住主要靠三种渠道解决,即用工单位提供住房、自主租房和购房。目前,虽然部分城市提供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住房,但多数农民工因诸如户型大小、交通便利度、租金高低、申请条件限制等等因素而未能如愿入住。另外,虽然一些地方开始采取措施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但覆盖农民工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7]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公共住房基本上不对农民工开放,游离于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外的农民工要在城市实现定居显得异常困难。
(二)农民工向市民转变:社会需求
相比于生存需求,社会需求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农民工能享有与市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与保障是其身份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其融入城市的重要体现。然而,当前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8]使农民工的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
一方面,嵌入户籍制度之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供求失衡。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只能得到有限的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当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大多是如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等基本保险,而缺少社会福利、救济以及优抚方面的供给,而且这些项目的保障水平也比城镇职工低得多。二是农民工参加现有项目的社会保障存在“两低一高”现象,即参保意愿低、实际参保率低、退保率高。究其原因,其一是社会保障设置的门槛过高。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农民工要想在务工地的社保机构领取养老金,就必须以一定的基数和费率连续缴足一定年数(一般为15年),这与农民工的较强流动性是相悖的。其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移接续。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市职工的利益以及自己的政绩,阻碍农民工保险的跨统筹区域转移。而我国农村和城市的社保制度无法接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现象。
另一方面,与户籍制度直接挂钩的现行选举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享有平等的民主政治权利。而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是满足农民工的参政需求,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手段之一。农民工长期游离于城市政治生活之外,利益诉求难以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得到充分反映。当前,虽然个别地区为农民工参与城市基层公共事务管理出台了一些措施,在城市社区居住满一定时间(通常为1年以上)的农民工可登记为社区选民,参加选举的相关活动,行使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就措施实施效果来看,多数地方农民工参选比例仍较低。选举制度降低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而社会保障制度剥夺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户籍制度给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身份转变建筑了一道深深的藩篱。
(三)定居者向融入者转变:心理需求
农民工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并不是最终意义上的融入,从定居城市到融入城市还有一个逐步增强心理适应力的过程。社会网络的建立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手段和途径。[9]一般而言,网络成员越多,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农民工越容易融入城市社会。[10]因此,满足农民工的心理需求需依托农民工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内嵌于这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非正式制度①非正式制度是指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及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起到非正式约束的规则,是与正式制度相对的概念。对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前,虽然与市民化相关的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这些改革取得的实际效果却不如预期所想。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诸如城市旧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滞后于市民化理念。一是市民因长期享有各方面的优惠待遇,有极强的心理优越感,在思想上对外来农民工带有较强的排斥和歧视。二是当地政府因观念落后,害怕农民工影响市民就业率,不利于城市社会秩序管理,在社会服务上对外来农民工带有一定的排斥与歧视。三是部分农民工尤其是老一代农民工思想封闭,带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农村思想意识和观念,再加上城市和市民的排斥与歧视,产生了一定的抵触情绪。非正式制度的不协调使得农民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强关系”网络,也没有在此基础上扩充其“弱关系”网络。由“强关系”网络构筑的“熟人社会”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社区这个“陌生人社会”中无法形成心理认同和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另外,社团组织作为农民工(特别是村民自治权闲置或流失后的那部分农民工)的民主权益组织,对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着重要意义。当前,工会作为服务劳动者的组织,是农民工容易接受并愿意加入的正式社团组织。然而,当前农民工因工会的准入门槛而较少加入工会;当农民工发生劳资纠纷时,工会很多时候并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在就业服务方面,工会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市民而非农民工。工会的缺位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并不能有“家”的感觉,对城市缺乏心理归属感与认同感。
三、农民工融城身份变迁中的制度跟进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一个长期命题,采取分步推进的策略已成学界共识。经济融入是作为流动者的农民工的最核心问题。这一阶段应以推动农民工稳定就业、获得经济收入为主要目标,保障农民工最基本的生存权益。作为定居者的农民工需要有更多的社会权利,对具体政策的诉求也从生存型政策转变为了赋权型政策。这一阶段应以提供就业、医疗、住房等一系列均等化服务为重心,适应农民工扩大化的利益诉求。如何在城市实现发展是作为融入者的农民工最关注的问题。这一阶段应以推动农民工的公共参与,营造其作为城市主体的价值感与尊严感,保障农民工的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为着力点,加强农民工的文化心理认同。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可尝试摒弃以往从整体出发将农民工作为一个同质性群体来制定的思路,把握好时效性和针对性,依循农民工在其融城身份变迁历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制度诉求这一路径来做好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跟进。
(一)以补救型社会政策促进农民工由流动向定居状态转变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首要驱动力是经济因素。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农民工定居城市的首要需求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流动中的农民工只有达到了经济层面的融入才会去追求更深层次的社会融入。因此,促进农民工由流动向定居状态转变,应以补救型社会政策为主。
一方面,要完善就业制度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对于流动者身份的农民工来说,挣钱是其最主要的目的。相比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更关注的是能否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换句话说,对于这部分农民工来说,如果在城市中付出努力但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他们是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的,更不会去贪图一个市民的称号。因此,要完善就业市场准入制度保证农民工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要缓和劳资关系保证农民工获得平等的劳动报酬,要在平等就业制度的基础上保证农民工获得平等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除此之外,由于当前城市发展和技术进步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有关政府机构应将职业教育和农民工技能培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形成政府、企业、劳动者和培训机构共同推进,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为目标,充分尊重农民工自主选择权的教育培训机制。
另一方面,要完善住房制度以落实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农民工能否实现安居是其融入城市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政府要通过完善农民工住房支持政策,建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一是给予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鼓励其为农民工提供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工作宿舍;二是建立规范有序的房屋租赁市场,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交通方便、生活功能齐全、价格便宜的普通住房房屋租赁市场;三是建立农民工能承受的商品房市场,为有购房意愿的农民工提供能承受的新建商品房或二手商品房;四是逐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补贴制度、财税支持制度、金融服务制度、土地供应制度、规划保障制度相互补充的农民工住房政策体系。[7]
(二)以赋权型社会政策促进农民工向市民身份转变
公民身份一直是农民工权益问题的关键点。农民工从流动者转变为定居者并不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终结点,其中还有一个农民工身份转变的问题。农民工以何种身份在城市有尊严地住下来,需要依托于赋权型社会政策的支持。2014年两会期间,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议,户籍制度改革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相当重要,要尽快制定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法》。具体来说,赋予农民工合法权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要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一是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在农民工社会保险的推进次序上,可以根据有关风险对农民工危害程度以及农民工的自身需求,按照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依次推进的次序优先解决农民工目前最迫切的需要和最突出的问题。二是要逐步建立社会救济体系。为农民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对年老、伤残、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民工以提供经济救助为主,对暂时性失业但仍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工以提供劳动机会和“公共劳动”为主。此外,在农民工合法权益受损或遭受不公平待遇时,政府和有关民间机构应维护农民工权益,建立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制度,将农民工纳入法律援助对象范围。
另一方面,要推进农民工行使民主权利。农民工在城市行使民主权利,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要建立健全农民工依法参加城市社区民主选举和管理的办法,使农民工的利益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要构建平等开放的城镇社区,创建多种形式的农民工参与城市管理渠道;要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要推动农民工参与社区的公共活动、建设和管理,使城市社区成为农民工和市民共建、共管、共享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要逐步增加农民工在流入地党代会、人代会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额,推动农民工参政议政,以民主促民生。
当前,我们应该认清完全取消二元户籍制度的不现实性,应通过出台赋权型社会政策来弥补户籍制度给农民工身份转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着力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中渐次赋予农民工市民身份。
(三)以增能型社会政策促进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个与市民保持良性互动关系的问题。农民工从社会融入到心理融入,既需要农民工具备有适应城市社会和文化的心理,也需要农民工在与市民的社会互动中进行适度的继续社会化。农民工从定居者身份转变为融入者身份,需要依托于增能型社会政策。
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农民工的心理融入。农民工社会资本薄弱,本身的资源非常有限,由“熟人社会”所构建的关系网络不能使农民工很好地适应城市社会环境。因此,政府要帮助农民工建立适合其在城市实现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其更好地去应对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比如多数农民工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大城市所特有的竞争与压抑氛围的影响,甚者,部分农民工会因此而产生心理问题。这时候就需要社会支持网络(社工组织)来帮助农民工摆脱心理困境,重塑其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组织制度促进农民工的文化融入。一是要为农民工建立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具体来说,社区工作者要协助农民工建立农民工工会,并通过农民工工会来促进农民工和市民形成良好互动,增进农民工与市民的感情。二是要在农民工居住的社区开展相应的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化的感染作用逐渐消除农民工的自我封闭心理和市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和歧视心理,营造一个彼此尊重、理解和友爱的空间环境。具体来讲,社区可多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工的政策,以增加农民工对各项方针政策的了解与认识;注重对农民工中好人好事的发现与宣传,并对其给予充分的鼓励和适当的奖励;在社区内开展文明市民实践活动,运用标语或图案把规范表现出来,在有形和无形中规范农民工行为,形塑农民工的现代性。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新华网:http://www.hq.xinhuanet.com/ focus/2013-12/16/c_118567236.htm.2013-12-16.
[2]王竹林,王征兵.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阐释[J].商业研究,2008(2).
[3]方向新,秦阿琳.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在何方[J].中国乡村发现,2014(3).
[4]国家统计局. 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N].北京:国家统计局,2015.
[5]陈诗达. 2007浙江就业报告:农民工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331.
[6]黄馄.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D].武汉:武汉大学,2009.
[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十二五”时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要点[J].发展研究,2011(6):6,10-11.
[8]陈凤莉.从农民工到市民还有多远[N].中国青年报,2011-03-08.
[9]Zhao,Y. H.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The Case of China[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4),2003:500-511.
[10]李树茁,等.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8(2):1-8.
[经济与管理]
Research on the Following System in the Course of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the City
WANG Li-na
(CPC Lianyuan Municipal Party School, Lianyuan 417100, China)
Abstract:Realizing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t present, the identit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which are constructed by different degrees of city in⁃tegration,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periodical identity of the flows, the settlers and the integration. This kind of char⁃acteristic is also concentratively reflected in the system demand of migrant workers. The path of system building to urbanize migrant workers should take full account of the phas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workers’identity. This paper is aimed at realizing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aking a dynamic perspective to crack the current unbalanced situation ofmigrant worker’system.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periodical identity; system demand; system follow-up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931X(2016)01—0072-06
收稿日期:2015-12-17
作者简介:王立娜(1990-),女,湖南涟源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