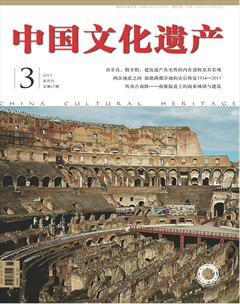真非真,假非假:建筑遗产真实性的内在逻辑及其表现
陆地
摘要:建筑遗产的真实性是种旨在确定遗产价值,对其各方面是否名副其实的判断。随着人们对建筑遗产价值构成的认识深化,也经历了“文献信息真实性”“作者真实性”“文化传统真实性”这三种真实性的认识扩展,但真实性的理论模型与内在逻辑始终是一样的,作者真实性始终是建筑遗产价值及其真实性的决定性因素,并反映在各种国际保护文件与实践中。
关键词:真实性的内在逻辑;文献信息真实性;作者真实性;文化传统真实性
正如大多数讨论建筑遗产真实性的文章表明的那样,从对象本身纷繁的构成内容——形式与设计,材料与物质(substance),传统、技术与管理系统,位置与环境,语言和其他形式的非物质遗产,精神与情感,以及其他内在与外在因素——是否是原来的对象,或是否在各种维度上与原来的对象对应的角度,试图经验地说明真实性的方式只会使该问题混淆不清。
就是否是原来的对象方面,4月25日发生的尼泊尔强震就使很多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重建后的遗产还有真实性吗?此外,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普遍的突出问题:一模一样(identical)是否就等于真实性?1999年,考虑到魏玛伊姆河畔公园(Park an derllm)里的歌德故居无法接待日益增多的观众,人们在距该故居约100米的地方建起了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故居,甚至完美复制了所有室内家具与物品上的磨痕和墨迹,两个故居相互对望,引发了激烈争议,也达到了包豪斯大学大众媒体系院长恩格尔(Lorenz Engell)的目的:激起人们对建筑遗产真实性的思考。
于是,和经验主义相反,我们必须首先从真实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内在逻辑说明这些问题。
一、语源学维度上的“真实性”考古
对英语里的真实性(authenticity)进行一番词源考古学的探究显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真正含义。“authenticity”是形容词“authentic”的名词形式;“authentic”在中世纪英语里拼写为“autentik”,源于古法语“autentique”,而后者则源于晚期拉丁语“authenticus”,再向上可追溯至古希腊形容词“αυθεντικοξ”(authentikos),源于古希腊名词“αυθεντη”(authentes),由“αυτοξ”[autos,自我(self)]和“εντηξ”[hentes,完成者(accomplisher、achiever)]构成,其本意是完成某物或某事的“作者”(author)与“行为者”(doer)。
而根据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费拉拉(Alessandro Ferrara)在存在主义意义上解读,“authentikos”是“eauton”和“theto”的组合,后者在语源学上与“论点”(thesis)相关,因此,“authentic”指的是“自我申张”的个人,或者说是那些“将自己设定为论点”的个人。
无论何种语源学解释,我们都可以看出,真实性首先是一个与完成某物或某事的作者,而非某物或某事直接关联的词,是某物或某事是否为某个作者所做,或是否得到了该作者的合法授权(authorize)。
二、真实性的内在逻辑
在有形遗产领域,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逐渐认识到,真实性在本质上并不在于对象的物质本体本身:一切存在的东西均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现代保护理论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布兰迪(Cesare Brandi,1906~1988年)早在1963年的《论造假》中就阐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虚假性不能被视为对象的固有属性,即便在伪造物主要是由某种不同材料依据构成的极端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2014年爆出的淘宝售卖的假欧元硬币,其合金材料并不是假的,而是真实的;然而,即便这种硬币在材料、加工工艺和外形上与真币一模一样,以至于可以骗过欧洲的自动售卖机,却仍被视为假的。
于是我们看到,对象的真实与否事实上在于人们的判断:“判断某物是赝品,就如同判断分配给一个特定主体的述语,看述语的内容是否符合主体和主体所声称的概念的关系。于是人们在对虚假性的判断中——依据主体应该拥有,却不拥有,但又假装拥有的各种本质特征——认识到了某种有问题的判断。因此在对虚假性的判断中,人们确定主体并不和其声称的概念相一致,从而宣告对象本身是赝品。”
在布兰迪的这段经典表述中,我们看到了真实性的建构性判断本质,即判断对象明示或暗示的各种属性是否与其实际属性名副其实、表里一致,是否作伪。而这种判断的最终目的在于确定对象的价值,这就是《奈良文件》第9条所说的:“我们理解文化遗产价值的能力,部分取决于与理解这些价值有关的信息源的可信(credible)或如实(truthful)程度”,而无疑,“对所有类型及所有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源于遗产自身的价值”。没有价值,我们就不会保护相应的对象。
三、真实性判断的两类内容及其历史发展
然而,在名副其实的判断中,人们面临着“其”到底指什么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不断的认识发展才是引发巨大争议,使真实性问题模糊不清的根源。我们从建筑遗产保护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相继被人们所认识到的两种真实性:文献信息真实性与作者真实性。
1 文献信息真实性
早在古代晚期的基督教学术辩论中,真实性概念就常被用于确认经文在流传过程中是否存在改动。一个手抄本古书,只要其文本内容未经更改,无论重印多少次,字体与版面格式如何,在文本内容层面上都是真实的。这种辩论与认识隐含了现代遗产保护首先发展出来,并认为最重要的真实性,即现有对象与原件在各种文献信息层面上的符合程度。在建筑遗产中就表现为,只要重建物(或重建部分)的结构、形制、材料与工艺(即我们常说的“四原”)等文献性信息与原初的、最辉煌时期的或采取保护干预前的信息相符,就被视为真实的。
但正如前文所言,真实性的最终目的在于价值判断,而文献信息对应性仅仅反映的是建筑遗产某一时刻或某一方面的史实信息,只具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教育与欣赏价值,并不代表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价值。仅仅基于这种真实性,就无法解释即便对古书而言,即便真迹已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在原初的文献信息这一真实性维度上已多多少少丧失,即便人们能传真式地翻版,或采用新字体重制能更好传达原初文本信息的新版,真迹的价值为何在人们心中仍远远高于翻版与新版。一件日本二玄社完美复制的《快雪时晴帖》,即便乍看上去能骗过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但是一旦人们知道那是复制品,其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和在市场上的价格当然也与真迹截然不同。否则的话,人们就不可能费力保护那些脆弱的,在最初的文献信息真实性层面上已多多少少丧失的真迹,真迹和翻版的价格在拍卖行将是一样的,无数的文物鉴定师将是多余的。endprint
于是我们看到,文献信息维度上的真实性对于有形遗产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以作为价值指向的保护立足点。
2 作者真实性
一枚欧元假币之所以假,本质上不在于其合金成分与外形是否与真品一致,而在于它不是欧洲央行发行的;一幅徐悲鸿的赝品之所以是赝品,并不在于它看起来多么像徐悲鸿画的,而在于它事实上不是徐悲鸿画的。一座重建的建筑,即便其结构、形制、材料与工艺与一座已实存千年之久的建筑一模一样,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也完全不同。
在类似的大量实例中我们看到,对终极目的在于价值判断的真实性而言,正如本文一开始的词源探究说明的那样,在于对作者的判断,这也就是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与符号学家埃科(Umberto Eco)在《阐释的极限》所说的:作者真实性(authorial authenticity)才是真实性概念的核心。
由于建筑以往常被视为没有作者的作品,更由于正如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年)在《现代的古迹崇拜》中所言,“将19世纪称为史实的世纪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它比古往今来更热衷于探寻与研究单一事实的乐趣,热衷于各种单一事实纯粹原始的史实状态……”。也就是说,18世纪末现代保护肇始以来,人们首先认识到的是建筑遗产对某个历史时刻所反映的成就的史实证言价值。这一时刻首先是建筑刚造出来那一时刻,即李格尔所说的使建筑具有新物价值(Neuheitswert)的那一时刻,布兰迪所说的保护对象的“第一史实”;其次是建筑最辉煌、最完整的那一时刻。而人们面对的遗产或多或少都已残损、经过历代加建与改建,在文献信息维度上无法反映这种单一历史时刻的真正面貌,于是在这种维度上被视为不真实的,使得人们热衷于根据考古资料进行各种复原。
这种复原无疑破坏了建筑遗产随着时光变迁的各种历时性变化,即遗产自刚建造出来起,直到采取保护干预之前所经历的漫长“第二史实”的真实性;而且最重要的是,无视原创者的“授权”,正如维奥勒-勒-迪克(Viollet-le-Duc,1814~1879年)提倡的那样“试着把自己放到原来建筑师的位置上”,以天衣无缝的做法假装复原物就是原物,隐藏现代干预的历史,即遗产“第三史实”的真实性,隐藏作为这种第三史实真正作者的现代干预者。因此,无论干预结果在文献信息维度上的真实性如何,在对于有形遗产最重要的作者真实性方面都是一种作伪。伊姆河畔公园里复制的歌德故居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在于人们分不清楚哪个才是现代作者的产物,无法判断各自的价值,从而说明了文献信息维度上的真实性并非有形遗产真实性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对绝大多数人类产品而言,作者真实性无疑才是其价值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品牌(brand)价值,品牌的原意就是作者在产品上的烙印,是其真正作者的显形。只有对那些完全没有附加的文化价值,纯粹只有实用价值的产品,人们才可能不考虑作者真实性。但是,只要我们本质上是因为精神与文化价值而保护文化遗产,作者真实性就是其具决定性的价值因素,除非人们试图否定这种遗产的精神与文化价值。
就作者而言,早在19世纪中期,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年)就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反复强调,建筑的作者不仅仅在于其原初建造者,在于它所产生的时代、地点等等与原创有关的背景,更在于时光这个所有事物都无法逃避、具有天赋权利的作者对建筑的各种作用。正如法国著名文学家和评论家尤斯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后来所言:“时光是最强大的雕塑家”。而作品的原创者无法复活,作品产生的背景以及时光对作品的再加工既无法伪造,也不可能回复。所以埃科说,人们正是在这种作者真实性维度上才将有形遗产看成不可复制与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而非单纯文献信息维度上可以还原与复制的史实资料。
这种作者真实性无疑是种感性的、艺术品维度上的真实性。这正是《威尼斯宪章》第3条明确指出的:既将古迹作为史实证据,也将其作为艺术品而护卫。而且应特别注意的是,这里采用的句式是:“不亚于”史实证据的艺术品(no less as works of art than as historicaI evidence)。其隐含的认识就是布兰迪一再强调的,对于有形遗产,艺术品维度的保护要求应始终“大于等于”史实证据的保护要求。否则的话,我们就抽离了这种遗产最重要的精神性,仅将其当成抽象的文献信息,可以随意还原与复制,谈不上对遗存本体的真正尊重,从而导致在我国大量发生的“拆除性保护”。
《威尼斯宪章》里基于布兰迪的理论认识所说的艺术品,显然和我们通常的艺术品认识非常不同,并非指只体现对象第一历史与新物价值的艺术品,而是真正的历史艺术品,即体现第二历史与历时性时光作用的艺术品,后者才是将真正的历史遗存与所有新造物的艺术价值区别开来,使之带有历史灵韵的关键所在,也是有形遗产为何源于新物,但高于新物的真正所在。于是正如李格尔所言,随着现代艺术观念的形成,人们在19世纪末逐渐发展起来了对遗产“老化价值”(Alterswert),即历时性时光真理的认识。而且也正如他的预言,随着人们所接受的艺术教育的转变,这种新的价值将逐渐战胜传统的新物价值。作为这种新的价值与真实性认识的最近例证,普通大众对上海外滩原三菱洋行大楼被喷涂一新的强烈愤慨就很说明问题,认为古迹一旦丧失了历史年轮,就丧失了最核心的价值,成了真赛假的古迹。而这其实是在“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这句充满讥讽意味的俗语中早就反映出来的传统价值认识。
这也是李格尔为何长篇累牍地阐述老化价值,布兰迪为何反复强调“古锈”(patina)对真正的历史艺术品的重要性:“即便从史实角度看,如果史实证据被剥去了——可谓是——它们的古老性,就必须承认这就是一种史实伪造。也就是说,如果材料被迫焕然一新,获得干净利落的轮廓,就形成了一种同它所证言的古老性相矛盾的证据。”从这种真正的历史艺术品的真实性出发,既要求保护原作残留的所有物质本体,也要求尊重原作在采取保护干预之前的所有历时性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清理与整合。因此,《威尼斯宪章》强调保护干预不应追求风格与形式的统一,应始终基于现状,而非原状,其目的在于“保护并尊重已经传承给我们的那部分作品的完整性,使这部分的未来不再有危险。”endprint
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人们在遗产保护中对各种历时艺术品意义上的作者真实性,尤其是时光作者真实性的重视,人们已经认识到,从包含第二史实的全历史维度认识遗产的史实与艺术价值,基于现状的保护才是真正的客观与现实主义,才具有史实与艺术理性;各种试图抹杀遗产第二史实真实性的还原反而被视为了18世纪晚期以来浪漫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
四、体现在《威尼斯宪章》中的真实性:当代作者的显形
尽管《威尼斯宪章》既没有定义,也没有列举说明什么是真实性,似乎留下了巨大的争议空间,但人们无疑意识到《威尼斯宪章》极其强调真实性,这就是到处体现在宪章里的“可识别性”,即第9条所说的:“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之作都必须与该建筑的构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带有某种当代印记。”
2011年,在英国王室的支持下,国际传统建筑与城市网络(INTBAU)的创始人哈迪(Matthew Hardy)组织编写了一本专门批判《威尼斯宪章》、厚达830页的“巨著”,其批判焦点就是《威尼斯宪章》第9条的可识别性。而一旦放弃了可识别性,《威尼斯宪章》事实上就崩溃了。
1 道德要求维度的作者显形
对于这种批判,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可识别性事实上首先出于当代作者显形的道德要求。
从更宏大的背景看,人们对有形遗产真实性的讨论事实上只不过是现当代文化领域真实性讨论的很小一部分。19世纪中后期以来,思想与文化领域讨论最激烈,也对现当代文化影响极大的就是哲学维度上的存在感本真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讨论。这种本真性讨论由克尔凯郭尔在宗教维度上首倡,经尼采的非宗教化,海德格尔艰涩的哲学论述,直到萨特通过各种文学作品更大众化的普及,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主导思想。正如费拉拉对真实性的词源探究说明的那样,指的是个体的自我申张,将自己设定为论点,从而实现自我存在感。而且正如萨特的名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篇名所言,存在感本真性被当成了一种人之为人的道德,也被当成了社会发展的必备动力。
到了19世纪后期,这种存在感本真性使得“艺术家开始将艺术等同为他们自身的完全存在”,开始认识到艺术的本质并非模仿与复制,而是自身感悟的表现,遗产干预者既然处理的是艺术,干预本身事实上具有艺术属性,干预者及其行为在保护中的显形本身被视为了这种存在感本真性的道德要求。
仅就文献信息真实性的复原而言,正如菲利波(Paul Philippot)所言,人们也开始普遍认识到:“……仅就作品的外貌而言,也从未有过将其重建到某个真正史实时刻的成功案例。”这种不可能性源于复原不仅基于证据的可靠性与翔实度,而且基于人们的主观分析、判断与重构,会随着史料的发掘程度、修复者的主观好恶而变化,总有取合和精确度问题,即便在文献信息上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与过去完全一致,无论何种精度的文献信息复原,事实上仍是一种主观假想性的当下建构。
既然干预者的干预是一种真正的史实活动,无论如何都在制造历史(make history),就应该行知合一地、光明正大地显现出来:“人们的修复行动就不能偷偷摸摸、且几乎置身于时间之外。由于修复是一种人类活动,因此就必须被强调为真正的史实事件,被塑造为艺术品传承的插入过程。”以往化腐朽为神奇的修复是“魔术般的、偷偷摸摸的方式”,但我们的干预却应该被塑造为“一种现象中的现象,并且正因如此并不是隐藏起来的,更多地是夸示出来的,从而能被他人体验到。”
也就是说干预者及其活动的真实显现应该置于纯粹的审美享乐之前。没有真,就谈不上真正的善,也不可能有健康的美。
2 作者隐形导致的假
假币之所以假,不在于其有形成果是否与真币一模一样,而在于令人误解其真实作者,导致价值误判,为其赋予不相称的价值。人们在各种重制、复制与仿制中为何要隐藏现代作者及其干预呢?无论这种方式是否具有主观恶意,是否单纯出于审美需要,客观效果仍是误导价值判断,使受众付出不应有的代价。这种误导与欺骗随着文化产业在20世纪下半叶有组织的汹涌兴起,愈演愈烈,在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攸关的博弈中,也恰恰导致了对真实性前所未有的激烈讨论。在几乎所有故意隐藏作者的遗产处理中,我们都能看到文化产业的阴影。
而在以往的建筑领域,古人并不会有意作假。就这点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人在新建或整补与改扩建时,总是依照当时流行的风格与形式,而非复辟过去的风格与形式。也就是说,当一座唐塔在宋代倒塌后,为了延续场所精神,人们会按宋代而非唐代的风格进行重建;当一座明代的大殿在清代倒塌后,人们会按清代而非明代的风格进行重建,只是这种风格演变比较缓慢而已。岳阳楼、黄鹤楼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不断演变的重建史就很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方面的一个特例是日本神道教神社按照原有形式进行的周期性造替,一方面,这种大张旗鼓的造替制本身就是作者的显形,人们很清楚面对的是近几十年重建的建筑;另一方面,日本的绝大多数建筑并非如此。否则的话,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建筑史学家就不可能根据风格与形式判断一个古建筑真实的建造时代,就不可能有按时代展开、丰富多彩的建筑史了。
早在19世纪,维奥勒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论修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古人从没有风格与形式上的复原:“对于这一事实的证明就是,在拉丁文中没有一个能与我们如今对‘修复一词的理解真正对应的词。拉丁文里的‘instaurare‘reficere‘renovare都不是‘修复的意思,而是‘重构或‘重建一新的意思。”“我们必须看到,以往的修复或重建都是按照那个时代的方式而进行的,所有的重建都是根据当时流行的风格和方式。”几乎在同一时期,莫里斯在《英国古建筑保护协会宣言》里也明确指出:“在以往的时代,由于建造者缺乏对以往风格知识的掌握,缺乏将古建筑带回过去的本能意识,这种伪造是不可能的。如果需要整修,如果人们的雄心或虔诚促使人们改变建筑,这种改变必然会烙上那个时代显而易见的风尚。”我们在青海热贡传统民居自发的更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尽管由于地处偏远,总体上仍延续着以往的风格,但也已经带有像现代瓷砖、金属防盗门那样明显的现代烙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