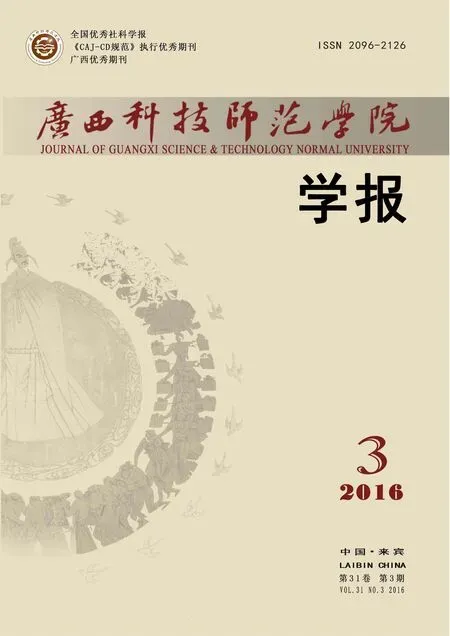复仇意义的终极追寻
——写在《哈姆雷特》和《铸剑》之间
王光祖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复仇意义的终极追寻
——写在《哈姆雷特》和《铸剑》之间
王光祖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和鲁迅《故事新编》中的历史小说《铸剑》有着相同的主题——复仇。从对两部著作的复仇情节的对比、复仇主题的深层透视、复仇意义的终极追寻等方面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认识两位文学巨匠对同一主题进行不同演绎的深层原因,进而挖掘复仇主题本身在两个文本中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复仇;主题;《哈姆雷特》;《铸剑》;对比
复仇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种极端的历史文化现象,它记载着人类痛苦的历史实践和复杂的生命体验。而作为文学史上反复被表现的文学主题,复仇主题又具有极大的生成性,在中外文学的百花园中不断被演绎和书写。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曾说,“血腥的复仇”这类有价值的主题,“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尽管目前尚属罕见——可以对理解和阐释不同作家的天才和艺术以及读者大众情感的变化提供新的角度”[1]。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哈姆雷特》和鲁迅的历史小说《铸剑》都是复仇主题的具体演绎。
一、复仇文本的对比
文本是文学主题的载体。从文本对比中我们可以考察具体情节和母题组合的异同,进而分析出这种异同所体现出各自文本生成的内在机制和深层原因。从文本情节结构来看,哈姆雷特和眉间尺为父报仇的故事是典型的血亲复仇行为。人类的复仇情感,深深扎根在其种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有着深远的人类学背景。王立指出:“复仇,是人类几乎各民族都盛行过的的文化现象、习俗,有着自身独特的亚文化伦理,最早的复仇现象当追溯至远古时代的血族复仇……‘以血还血’的信念强固了氏族群体意识,并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建构和维续了复仇伦理。”[2]中西方复仇故事中的情节结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该类复仇故事有着相对固定的模式:亲人被害;复仇者艰难复仇;大仇得报,自身付出巨大代价。哈姆雷特和眉间尺的血亲复仇故事基本上遵循着上述模式。但是在具体情节的母题组合方面又有着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对复仇精神和复仇意义的对比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亲人被害情节。两人都遭遇了亲人被杀的厄运,都要担负起报仇雪恨的重任。哈姆雷特回国后发现父死母嫁,新王即位。老国王亡魂于深夜把真相告知其子,王子继而肩负起复仇大任。《铸剑》中,遗腹子眉间尺因其年近十六,仍性情优柔,其母告知他复仇重任和复仇信物,复仇重任是被动承担。这个故事属于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教授所指出的第960型B1①丁乃通教授根据阿尔尼和汤普森的AT分类法,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共列入843个民间故事类型和次类型,并为各类型故事编排号码。该类型就是其中之一。“儿子长大后才能报仇”[3]的故事类型。而哈姆雷特的复仇起因则是“亡灵托付”母题的演绎,由父亲的鬼魂告知哈姆雷特真相。老国王被害距哈姆雷特复仇前后仅差数月,复仇的大任直接落在哈姆雷特身上。此外,两个复仇者的身份也不同:一个是优柔寡断、尚未成熟的乡间少年,一个是新旧交替时代有着深刻思想力的高贵王储。这也是造成其复仇过程不同的主观因素之一。
第二,艰难复仇情节。两人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艰巨的复仇重任对两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哈姆雷特的敌人的是其叔父、继父,同时也是丹麦国王。王子几乎是身陷重围。而眉间尺境况更甚,一个乡间少年去充当刺客,何其艰难,当黑衣人告诉他国王捉他时,更是担惊受怕,可见其对复仇对象的畏惧和对复仇信心的缺乏。哈姆雷特选择的复仇方式是不断试探和反复思虑。他先是装疯卖傻,接着导演戏中戏,遇见叔父忏悔却错过复仇,巧施妙计返回丹麦,最终决心复仇。眉间尺的复仇没有跌宕起伏的过程,复仇重任的降临并不能改变他优柔的性格,但遇见黑衣人时却果断地把复仇大任连同自己生命和复仇信物都交给了他,以求得到复仇成功。由此可见,哈姆雷特更注重复仇过程中复仇自身合法性的确证以及复仇中自我精神的历练和探寻;眉间尺式的复仇更强调复仇结果本身和复仇策略的选择。
第三,大仇得报情节。两个主人公都不是单枪匹马,都有同伴相助。哈姆雷特某种程度上是在两位心腹和雷欧提斯的间接帮助下杀死仇人的。眉间尺虽然在滚锅里和国王的头撕咬,但最终的复仇是与黑衣人宴之敖者共同完成,且复仇者最终都与仇人同归于尽。大仇得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复仇的艰难以及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哈氏虽然自我毁灭,但复仇并未结束,对人性的终极追问也未终结;眉氏的复仇最终也沦落成看客的“看资”,其深层的意蕴还将延续。
二、精神历练与时代启蒙:复仇主题的深层透视
诚如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论历史的意义》中的观点:“最伟大的精神作品就是过渡时期的精神作品,亦即处在时代交替时期的作品……精神历史的最伟大的现象,既是过渡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它的终结。”[4]福柯则从话语的生成转换角度对这种过渡性历史秩序做了阐释,他提出了“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有着更深层次的,我们从来没有阐发过的经验——一种基础的文化代码,决定着语言、观念、交换模式,这个决定性的经验系统规则就是认识价”[5]。福柯归纳了16世纪以来的四种认识价:文艺复兴认识价、古典认识价、现代认识价和当代认识价,认识价之间的关系非继承,而是断裂。这种基于认识价的话语理论,从微观的角度和雅斯贝尔斯宏观的历史观点形成了呼应和参照。我们以此来观照两个复仇文本,不难看出他们均是产生于时代变迁、精神文化过渡、文化范式更迭的历史时期,莎士比亚和鲁迅在表现其复仇主题时亦体现出文化过渡和转型期各自迥异的文化内涵的表征和显现。
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时处在伊丽莎白统治时代,此时的英国不仅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而且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进行海外扩张和资本原始积累。与此同时,在文化领域,文艺复兴之风也已吹向古老的英国,人文主义的反封建、反神权思想广泛传播,天主教的精神统治已出现危机,中世纪的蒙昧正在被近代黎明的曙光驱散。这种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时代的过渡正体现着雅斯贝尔斯和福柯所论述的过渡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成模式。哈姆雷特身上被莎士比亚赋予了人文主义者崇尚理性、善于思考的人文主义思想特征,寄托着莎翁对时代精神内涵的解读和对现实的美好愿望。但同时也能看出,在哈姆雷特身上曾出现的宿命观、宗教意识、英雄史观等,也打上了中世纪的烙印。这种新旧交替、方生方死的时代和文化特征在哈姆雷特悲剧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于哈姆雷特而言,复仇这个行为本身包含着两个意义:第一是父亲的仇,第二是国家的仇。哈姆雷特是老王的独子,国家的法定继承人,而王位被夺本身也就意味着国家的尊严受到威胁和挑战。因此,对于哈姆雷特而言,复仇是天经地义。然而,复仇行为本身意味着以暴易暴,意味着杀戮和血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由于复仇就是报复,所以从内容上说它是正义的,但是从形式说复仇是主观意志的行为,主观意志行为每一次侵害中都可体现它的无限性,所以它是否合乎正义,一般来说,事属偶然,而且对他人来说也不过是一种特殊意志。复仇由于是特殊一直的肯定行为,所以是一种新的侵害。”[6]在黑格尔看来,复仇从形式上容易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要避免个人复仇。哈姆雷特的复仇过程就要不断寻找合法性的确证,让他能够顺利复仇而避免或者减少对于自我的问责。
同是作为为父报仇的故事,哈姆雷特和眉间尺从复仇方式、复仇策略、复仇具体实施等方面均有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正体现着两位作家对复仇主题的不同表现。首先,哈姆雷特的复仇过程完全是他的复仇心态史,他在复仇的各个阶段都会产生若干内心独白,这些独白恰好体现了哈姆雷特在该阶段为复仇寻找合法性确证的心理变化。在他刚得知父亲的死讯时的一系列表现已然是其复仇的前奏:
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干的路人。
事情有些不妙,我恐怕这里面有奸人的恶计。
(《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7]309
丹麦的王子显然比乡间蒙昧少年要聪慧得多,敏感得多,他显然对父死母嫁的事实有了一定的猜度。当他决定复仇时,面对强大对手,他只好选择装疯的韬晦策略以求继续查寻父亲死亡的真相。一番躲闪之后,哈姆雷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了自责:
可是我,一个糊涂颟顸的家伙,垂头丧气,一天到晚像在做梦似的,忘记了杀父的大仇……啊!复仇!——嗨,我真是个蠢才!我的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我这做儿子的却像一个下流的女人似的,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
(《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7]355
哈姆雷特选择用戏中戏的方法来确证叔父就是凶手。当他已经确证了杀父仇人时,莎士比亚却放慢了哈姆雷特行动的速度,让他错过了直接杀死叔父的绝好机会,他对自己的行为又产生了无比的懊恼和自怨:
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啊!从这一刻起,让我摒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
(《哈姆雷特》第四幕,第四场)[7]366
当他再次坚定复仇信念时,克劳狄斯也在密谋杀害哈姆雷特。整个复仇的过程全然是哈姆雷特一个人自我精神的历练和内在心灵的煎熬,对复仇行为的一再追问,期间还有一闪而过的宿命论、封建迷信色彩,让他陷入了对生与死的冥思与对复仇行为的怀疑,哈姆雷特深陷自我“黑洞”不能自拔,丧失了复仇的主动权。
中国的复仇习俗发轫于远古时代的氏族社会时期,古老的血亲复仇行为体现了其对凝聚族群力量的功利化价值立场和伦理化的道德色彩。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复仇故事也体现了父仇子报、凝聚亲族等儒家实用性的价值观念和维护政治伦理秩序的精神立场以及传统大团圆式的叙事方式。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时,复仇主题所蕴含的原型性文化内涵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嬗变,这主要归结于现代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现代文学诞生之时,中国传统文学生命力正不断耗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而复仇主题文学所承载的思想的容量与内涵的深刻和复杂,已经远不是古代文学中的复仇故事所能比。这一时期的复仇文学,就复仇起因来讲,它已经不仅仅是承载匡扶家族、整饬国家的伦理使命,他的复仇对象也已涉及到更加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如王立所说:“与整个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任务相适应,与黑暗社会现实和急剧变化的时代政治风潮相联系,复仇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先于具体事件本身、个别恶人及伦理实现,而是整个封建社会、内外恶势力及至传统文化、国民性弊端。”[8]这也正是鲁迅创作《铸剑》以及鲁迅本身复仇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和价值立场的倾向性极其复杂,但与传统文化相承接的一脉是强调文学“为人生”的社会功利作用,鲁迅选择历史传说而古为今用的文学创作本身也是复仇这一古老文学主题的现代性转变的内在动力。
哈姆雷特的复仇过程跌宕起伏,悬念丛生,而他自身反反复复陷入形而上的思考,也表明复仇主体本身在复仇过程中所受到的精神煎熬要比复仇的结果更加具有审美效果。相比而言眉间尺的复仇过程要简单的多,作为复仇主体,面对同样有着绝对权威和力量的国王,他心中充满胆怯和畏惧:
自己得见国王的荣耀,以及俯伏得有怎么低,应该采作国民的模范等等,很像蜜蜂的排衙。直至将近南门,这才渐渐地冷静。“走罢,眉间尺!国王在捉你!”他说,声音好像鸱枭。眉间尺浑身一颤,中了魔似的,立即跟着他走;然后是飞奔……
(《铸剑》)[9]439-440
漫无目的的游荡,遇见国王时的怯懦,对传言的惊骇都能看出眉间尺对复仇心里的毫无准备和复仇信念的极度缺乏。因此,他对能够帮助自己的黑衣人十分信任,把复仇重任连同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他。
鲁迅对眉间尺复仇过程的叙述中,一方面有对传统复仇主题的继承,即复仇指向最终结果,不重乎过程,这是和哈姆雷特复仇故事的一大区别。其原因在于眉间尺的复仇故事原本脱胎于古代历史传说,传统的父仇子报,惩恶扬善、褒贬分明的复仇模式对小说情节安排仍有影响。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对他做了改造,让眉间尺的复仇过程由两个人来共同承担,复仇主体从开始的幼稚优柔,转而成为了英勇无畏的勇士,最终杀死暴君,完成复仇重任。鲁迅是有着复仇情结的,最早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盛赞各民族为了正义事业而复仇的英雄,他对复仇情绪有着深刻的体验。黑衣人冷峻的外表,神秘的气质,倔强的性格,冰冷的语言,拒绝一切温情和赞美,只是复仇。“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给你复仇。”[12]这里的黑衣人“宴之敖者”大致是鲁迅自己文学镜像的投射。
完成了复仇仪式的交接后,黑衣人便继续了复仇的重任。和眉间尺相比,黑衣人的复仇行动显然要更加成熟、稳重和机智,也更加讲求策略。他扮成一个会“异术”的人,诱骗王到金鼎边上,伺机砍下国王的头,接着又砍下自己的头,和眉间尺的头合力战胜了王的头,最终复仇成功。
不难看出,眉间尺的复仇,黑衣人的出现是重要的转折点。眉间尺的复仇不在乎过程的跌宕起伏、玄机四伏,而注重复仇过程中复仇主体自身的精神启蒙。只有从内在到外在的主体自身脱胎换骨的变化,才能完成自我的重生,进而实现复仇重任。
总之,哈姆雷特的复仇过程注重复仇者主体精神的历练,这与西方文学自古希腊以来注重个体价值,追求个人权利、尊严,崇尚个人主义精神的文化根源有关。眉间尺与黑衣人的复仇更强调复仇主体的精神自觉,虽然与哈姆雷特的主体精神锤炼有相似的地方,但鲁迅所处的时期,对启蒙精神的呼唤,对国民性的改造以及对文学“为人生”的呐喊,更具有时代精神的指导意义。
三、复仇意义的终极追问
《哈姆雷特》的最后一幕中四个人几乎同时死亡,复仇的最终结果俨然是一出血腥的死亡剧。而对于生与死这个问题,哈姆雷特独有的追问响彻整个复仇的过程,第一幕中,他就坦言过自杀的念头:
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片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不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
(《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7]309
对生与死的思考,最著名的当属那段“To be or not to be”的经典独白。哈姆雷特的追问,隐含着人类对于死亡本能地焦虑以及对生死本质的认识。哈姆雷特在冥思生与死的问题时,主要有两点顾虑,一是基督教禁止人自杀,第二担心死亡的“身后事”。而后者则是他产生这种顾虑的更深层原因。
对于王子哈姆雷特而言,他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和精神追求的人文主义者,一个有着高贵理性、追求完美人格的理想主义者,是时代的骄子,命运的宠儿。然而对这样一位有着强烈出世情怀的人来说,蓦然强加在他身上的极具世俗性倾向的复仇重任,和他对完美自我的追求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但复仇本身“重整乾坤”的重大使命感迫使他不得不去迅速行动,他还来不及在完成俗务的“小我”和追求理想的“大我”中做出选择,复仇之剑即被交在自己手中。因此跌宕起伏的复仇故事就在这两者强烈的张力中铺展开来,把整部复仇剧推向了高潮。哈姆雷特对自我产生了深切的怀疑,这种怀疑源自一种对残酷命运的躲避,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深切拷问,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思考以及对人存在的最普遍问题的痛苦自觉。
哈姆雷特因承担起替父报仇的使命,面对穷凶极恶的险境和周围人的无知与邪恶,他来不及做出更加纯熟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无法躲闪这残酷命运的追逐,只能跌跌撞撞走向复仇。在复仇中,他长于思索而倦于行动。这种思考最初来自于它对父亲鬼魂的话是否应该相信,“我所看见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形状出现,魔鬼是有着本领的;对于柔弱忧郁的灵魂,他最容易发挥他的力量”[7]366。从本质上说,这也是对自己复仇合理性、合法性的怀疑,那么如何让这种怀疑彻底消失呢?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自己。这无意中拨动了西方哲学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知与无知,认知的能力和限度。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过:“我们一无所知,因为真理隐藏在深渊之中。”[10]苏格拉底也曾说道:“有知的人是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11]反观哈姆雷特,他是一个有着精神自觉的人,他的反复冥思正证明了他在努力认识自我。但问题是他能否正确认识自我,认识行为的意义何在,即人类认知的能力究竟如何。他因父死母嫁而怀疑爱情的忠贞,因对周围一干邪恶的嘴脸而怀疑一切人性,他坟场对话骷髅进而怀疑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悲哀,却不能为他打开心中那个最根本的结——复仇的心结。可见,哈姆雷特已经在自我选择的道路上产生了分裂,他对这种分裂是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反省的,然而人对命运的无知和对无知的无法释怀反复纠缠把他推向了自我认识的黑洞,他在痛苦与焦灼中流露出浓重的虚无感,正是这种虚无感让他一再延宕,迟于行动。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复仇故事,复仇对象主要是现实生活中的作恶者,抑或与复仇主体亲友等有旧仇宿怨的人。复仇对象类型的过于单一,在一定程度上使复仇表现拘泥于形式,复仇结果只在乎复仇对象肉体的消亡,因而限制了复仇更深远意义的表达。鲁迅对传统的复仇主题做了改造和突破,在《铸剑》中,眉间尺和黑衣人虽然在最后与复仇对象同归于尽,然而复仇者的死亡不是传统复仇故事中大仇得报的“大团圆”结局,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反讽意味:眉间尺自杀献头后,尸体被一群狼撕咬;与王决战胜利后,却落得个众人区分头骨,百姓祭拜王的结局。复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杀死仇人性命,而是在复仇者和复仇对象同时死亡的结局中获得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形而上意义:启蒙者死于启蒙,被启蒙者成为无动于衷的看客。小说的结尾流露出一种反讽和荒诞的意味,伟大的复仇行为到头来却充满着虚无感,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鲁迅心中那种受挫后的绝望与无法排遣的阴郁,而且可以深切体会到他内心深处因浓重的虚无感而产生的痛苦的搏斗和挣扎。
尼采曾说过,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自我贬黜[12]。鲁迅内心深处是有着虚无感的,这来自于他一以贯之的、彻底的怀疑精神。但这种虚无感绝不会让其丧失行动的果决,他是有着强烈的复仇情结的,性格倔强的鲁迅对复仇不仅偏爱,而且常发带有偏爱倾向的思考,但他所理解的复仇是关乎人格的庄严和自尊,涉及个体存在与社会责任的关系,直指民族精神最深处的阴霾。《坟·杂忆》中他还谈道:“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13]鲁迅对复仇的态度是毅然决然的,而且这种复仇行为完全取决于复仇主体的认知,他不像哈姆雷特一样在复仇时总是充满了对复仇合法性确证的怀疑和自我认识的忧虑,而是跳过了这一切外部因素的束缚,直指复仇行为。鲁迅绝不仅仅停止于《铸剑》文本中反讽的结局,他对复仇精神更有一种伟大的超越。《野草·复仇》中的复仇者也沦为“鉴赏”的对象,而他们“以死人似的眼光,鉴赏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9]177。由此可见,鲁迅对复仇的怀疑更彻底,因而行动得更果决。
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面对邪恶、强大、神秘命运的追逐,俄狄浦斯直面命运,与其殊死搏斗,体现了人的价值、勇气和尊严。然而到了哈姆雷特,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强大精神力量已荡然无存,令人扼腕。张沛指出:“以往的悲剧英雄都对自身选择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深信不疑,而哈姆雷特对此却具有充分的自省意识,他朦胧看见世界的无情本质而质疑命运的终极目的,于是产生了一种形而上的、对于存在本身的失望。”[14]由此,充满英雄主义气息的复仇行为最终因怀疑、反思而导向虚无主义。时代的前行和发展并未给人类带来精神的进化,失落、迷惘、虚无、颓废等情绪无情地把人类滞留在了精神的荒原上,剩下的唯有对荒诞与虚无最真切的体验。
相比于莎士比亚,鲁迅笔下的复仇人物,虽然也经历了启蒙的失败,复仇行为也未可避免的陷入虚无和荒诞。但鲁迅绝不让复仇沦入无休止的虚无之中,他在希望中漫漫求索,在绝望中苦苦挣扎,在希望与绝望的起伏交战中经历着冰于火的煎熬,努力摆脱虚无,砸碎荒诞,冲破铁屋让呐喊之声响彻宇宙。诚如钱理群所言:“真正伟大的复仇者,必定是伟大的牺牲者。”[15]因此,莎士比亚让哈姆雷由怀疑走向了彻底的虚无,鲁迅不止于怀疑的虚无,而是于怀疑中战胜虚无感,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对时代、文明与自我精神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45.
[2]王立,刘卫英.传统复仇文学主题的文化阐释及中外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
[3](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郑建成,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313.
[4](英)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92.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07.
[7]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8]王立.鲁迅复仇观念的文化根源片——兼及鲁迅对传统复仇观的继承和改造[J].渤海大学学报,2011(3):31.
[9]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06.
[11]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0.
[12](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80.
[1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6.
[14]张沛.哈姆雷特的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
[15]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9
(责任编辑:雷凯)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26(2016)03-0045-05
[收稿日期]2016-03-11
[作者简介]王光祖(1991—),男,山东菏泽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4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Vengeance: Written between Hamlet and Molding Sword
WANG Guangz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Hubei,Wuhan,430072 China)
Abstract:Shakespeare’s tragedy Hamlet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Molding Sword from Lu Xun’s New Stories have the same theme of vengeance.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comparison of vengeance,the deep perspective analysis of vengeance and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vengeance meaning of the two works which is conduciv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wo literary giants to the deep reasons of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me theme,revenge theme and mining itself in two contained in the text of the meaning and value.
Key words:vengeance;theme;Hamlet;Molding Sword;comparison
——广西警察学院侦查学院